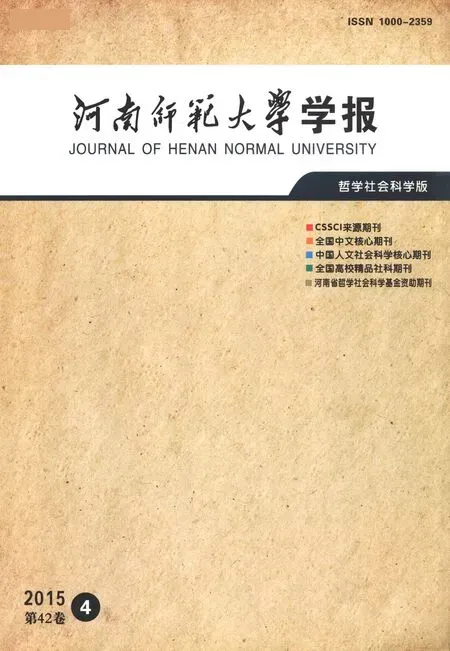论汉代职官选拔制度对汉赋的影响
于淑娟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职官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部分,对社会文化乃至文学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众所周知,汉承秦制,汉初职官制度并无变化,但自景武之际,因社会发展的需要,汉朝在职官制度上多有创建。正如王国维所言:“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1]职官制度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汉代社会文化,使汉代文人在文学创作中被无形的力量所裹挟,最终对汉赋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汉代职官选拔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征辟和察举,大多数官员都由这两种途径进身,其余如任子、赀选、试吏、太学擢选等,皆为补充,并非仕进主流。
征辟制度中有朝廷征聘、征召的区别。朝廷征聘是由皇帝直接下旨诏进,是汉代最尊荣的仕途。对士人来说,这是一夕之间平步青云的捷径,也是对自身才能的肯定和莫大的荣耀。西汉时期的朝廷征聘也分等级,最高等以“安车”相征,武帝时期共有两例:
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2]3608
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2]2365
这两例征聘皆法先秦之例,安车蒲轮以显尊荣之至。两人中,申公因明经得见征召,而由枚乘死后武帝“问乘子,无能为文者”来看,枚乘显然是因文章而见召。枚乘平生著述以散文、大赋见称,《汉书·艺文志》于十家之外别列诗赋,其中记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有枚乘赋九篇,其《七发》一向被认为是汉赋的奠基之作。另据《汉书》,其子枚皋“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使匈奴”[2]2366。枚皋得武帝召见,并因赋为郎,可侧证枚乘得武帝征召正在于其赋才。武帝征聘枚乘、召任枚皋之举,始开汉代因赋仕进之途。
枚乘之后,司马相如是因赋征召的显例。《史记·司马相如传》:
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赋奏,天子以为郎。[3]3042-3043
司马相如在被征召为郎之前,曾“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长侍”。学者多以为司马相如纳赀为郎与后来被武帝征召为郎并无实质差异,但实际上两者差异很大。
在中国古代官制中,入仕之途向来为人所重,汉代诸多的入仕途径中,纳赀为郎最为人轻视。
首先,纳赀为郎名义上为廉士入仕之途,但其所需资财颇巨,故名实难副。景帝后二年五月颁《重廉士诏》:“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赀又不得官,朕甚悯之。赀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颜师古引应劭注:“十算,十万也。”[2]152景帝将入赀资财由十万减为四万,似乎广开普通士人入仕之途,但对大多数平民来说,这仍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巨大资财。武帝时“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2]1429。武帝改变了汉初抑商的政策,使原本地位低下的商贾也可纳赀为官。此时选官正如董仲舒所论:“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2]2512由此可知,汉代“以赀为郎”者,多为家产殷实者,并非为人所敬重的廉士,也不以德望见称,加上传统贱商思想的遗留,故以赀入仕者不为世人所重。
其次,纳赀为郎在武帝时即因过滥而被轻视。据《西汉会要·鬻官》条:
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选举陵迟,廉耻相冒,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后府库益虚,乃募民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其后四年置赏官命,曰武功爵。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除故盐铁官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召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4]
据此,入赀为郎谋得的不过是六百石的低级官职,只能作为晋身之阶,并且在西汉时期即因过滥,以至于郎选衰落。
东汉末期吏制败乱,以赀为官成为常态:“刺史、二千石及茂长、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5]2535即便官场买官如此普遍,清流也仍以入赀入仕为耻。《后汉书·崔寔传》记载,崔烈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
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烈于是声誉衰减。久之不自安,从容问其子钧曰:‘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钧曰:“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为然也?”钧曰:“论者嫌其铜臭。”[5]1731
崔烈本为名士,但因买官而声誉大损,可见纳赀在汉代一直是被士人轻视的入仕之途。
再次,纳赀为郎往往难以得到升迁机会。《汉书》所记因入赀得官者仅两人,即张释之、司马相如;因入钱升职者一人,即黄霸。实际人数当远多于此,但不见载于史籍,一方面故因入赀者多为平庸之辈,另一方面也因其入仕之途为人所鄙,故升迁机会渺茫。张释之“以赀为骑郎,事文帝,十岁不得调,亡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免归”[2]2307。汉代骑郎无定员,属闲职,与郎官级别相似,秩比一百石至三百石。黄霸以赀财求职,“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后复入谷沈黎郡,补左冯翔二百石卒史”[2]3627。侍郎谒者属光禄勋,最高级别的常侍谒者不过秩比六百石;卒史更是一百至二百石的小官。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任武骑长侍,据《汉官六种·汉旧仪》:“期门骑者,陇西工射猎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行出会期门下,从射猎,无员,秩比郎从官,名曰期门骑。置仆射一人,秩六百石。”[6]527骑者仆射不过秩比六百石,骑者长侍并无定员,且官秩俸禄当更低。由上述三人之例可知,以纳赀仕进无从得任高官。故马端临以为,张释之、司马相如“盖其初非以德选,遂为世所轻,而宦亦不达,故资产之富厚者反因游宦而贫。虽以释之之才,相如之文,苟非一日他有以见知人主,自致显荣,则必为赀郎所累,终身坎坷矣。士之所以进身者,其发轫可不审哉”[7]335!纳赀入仕者前途黯淡,正是司马相如轻辞郎官、称病去梁的主要原因之一。
司马相如因赋征召为郎,任武帝侍从,虽仍属郎官,但与之前的骑郎差异很大。郎中、中郎即指帝王的侍从官,职责在于随时以备顾问及差遣,官阶虽小,却是重要的仕进之阶,董仲舒曾指出当时“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2]2512。至东汉,从事文字工作的郎官如郎中、侍郎,仅秩比四百石,仍是仕进捷径,有“台郎显职,仕之通阶”[5]1872之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载相如常从侍武帝左右,谋议政事,著书进谏,并因平定巴蜀而拜为中郎将。《汉旧仪》:“五官中郎将,秩比二千石,主五官郎中。左右中郎将,秩比二千石。”[6]527司马相如因贿免官后恢复郎官之职,再未能仕途显进,也与个人志向相关,《史记》本传记载其“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间居,不慕官爵”。两人虽未同朝为官,但时隔未久,此记载当可确信。
诚如郭预衡先生所言:“以一篇赋而为天子所知,受到召见,并由此得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后代文人对于这个际遇一直是羡慕的。”[8]司马相如之后,献赋之风日盛,渐成文人入仕捷径。《汉书·地理志》:“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2]1645司马相如不仅为蜀人所循迹,天下文人皆有踵武之意,如钱穆所论:“故武帝外廷所立博士,虽独尊经术,而内廷所用侍从,则尽贵辞赋。”[9]
成帝时因赋才得征召者有扬雄。《汉书·扬雄列传》:
顾尝好辞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2]3514-3522
待诏属于汉朝给未出仕但有文才之人的候补职,待诏地点不定,但以公车最为普遍,其他当为特例。承明庭是汉代著书校书之所,扬雄待诏承明庭当有彰显其文才之义。待诏多为有专才之人,虽然品阶不高,但前途无量,“所有待诏者都是皇帝的近臣,西汉甚至是‘内朝官’的补充”[10]。“待诏虽为预备官员,但宦途无限,一旦得到皇帝宠信,便可大用”[11]。刘向以任子入仕为辇郎,其后“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待诏金马门。刘歆“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2]1967。刘向、歆父子为刘氏宗亲、王侯之后,皆曾为待诏,可见其职亦当为仕宦通阶。扬雄除为黄门侍郎,也属于皇帝身边的近臣,曾“与王莽、刘歆并”,但却与王、刘二人浮沉异势,累年不迁,“三世不徒官”,部分原因在于其为人“恬于势力”,“用心于内,不求于外”[2]3583,是个人的选择而非缺少机遇或仕途出身不佳。
司马相如、扬雄之后,汉晋六朝因献赋而仕进者代不乏人。至唐代,献赋已成为常举、制举之外文人晋身的重要途径。李白、杜甫都有献赋的经历,杜甫长安十年科举未第,最后于天宝十年因献三大礼赋而获出身。钱起“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12]的感慨,也透露出唐代文人对献赋仕进的热望与执着。
由以上史实可知,征聘、征召是汉代职官选拔中较尊荣的仕进途径。自武帝时起,作赋、献赋渐成仕进之捷径,汉赋创作盛况空前,如班固《两都赋序》所言: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13]21-22
西汉文人因献赋风气创作出数量惊人的汉赋,而东汉时征召已非文人创作赋的主要动力。光武以来,帝王多重谶纬经学,征召者以经学、德行见称,即便帝王喜好辞赋亦少征召之举。另,东汉时期征召、察举已趋浮滥,这使有真材实学的清流名士往往征而不就,如周勰、张衡、董扶、杨厚、黄琼、徐穉、姜岐等,皆有拒征之举,甚至多次拒征。因赋入仕已成狭途,征召亦非复旧日尊荣,东汉时期征召制对汉赋创作的影响渐趋衰绝。
二
征召制主要依托于帝王的喜好,如武帝、宣帝、元帝、成帝皆好辞赋。帝王喜好固然能引领一世风尚,但并非常制,相比之下,汉代职官选拔制中的选试对赋的影响最为长远。
汉人重视官吏的文化素养,汉初萧何采摭秦律,官吏选拔对知识水平有明确的要求,《汉书·艺文志》:“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2]1720这里的“史”当指卒史,秦代即有设置,汉代在中央及地方郡属皆设卒史,是职官系统内的低级文吏。另据《史记·儒林列传》,“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3]3119,一至二百石的文官品秩极低,然亦尚需“能讽书九千字”。东汉的选试制也有基本要求:“尉律: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14]汉代对官吏的基本要求是知识才能而非品行,正如贾谊所言:“胡以孝弟循顺为?善书而为吏耳。”[15]
汉代不仅小吏要经过选试,孝廉、茂材、贤良方正与文学等,虽属察举征召之途,也往往要经过考试方得任用。考试分为天子策试和公府复试,天子亲加策试者,多为诏令特举之士。文帝、武帝、成帝、光武,皆有此例。如文帝“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2]127。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盖宽饶、何武等人,皆经对策擢选为官。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来看,对策内容多为国家政治。这类上层文官通文字、掌名物、明训诂、谙掌故、晓政道,代表了西汉最高的知识文化水平。汉代帝王也从小接受优良的教育:“汉兴,太宗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贾谊教梁王以《诗》、《书》。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5]1328
下级小吏的选试制度、中上层官员的策试及复试制度,使汉代社会中的官吏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考选制的施行使字书成为重要的教材,并出现了大量编纂的现象。司马相如编《凡将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长作《元尚篇》,扬雄作《训纂》《方言》,另有《别字》《苍颉传》等。这些字书的编写目的之一即是为了便于学习者快速掌握文字,如《急就篇》开篇明言,“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既强调其实用便利,又坦言识字后可期许的利益。《急就篇》创作之后,“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16]。考选制催生出汉人学习文字知识的热情,吏选对文学创作影响甚巨,正如金秬香先生所论:
自来诵读之业,恒与经济相资,并欲使全国之才,奔赴于文字一途,以隐增其意智,则考试尚焉。……故汉廷之作,上焉者可与贾疏董策相颉颃,次则虽多浮夸矜诩之词,而揆厥所由,亦犹承纵横家弃信尚谖之流弊,盖其时除公室考校外,尠所专习者。余如官方职司,私家著述,亦无非由举业研究而来,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其发达之速率,诚有如平子所云鼎沸者。论者谓上古之文,出于民间,中古之文,出于史官,汉以来之文,出于考试,此又发达之关于风尚也。[17]
汉代文人竞于文字之途,辞书编纂是直接的体现,而大赋创作则是间接的体现,既以此来彰显才华,亦为时人所诵习。汉赋不仅是可娱耳目心意的文学作品,更有其实用性:“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且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18]钱钟书也认为,类书“不堪讽咏,安能及词赋之口吻调利、流布人间哉。……足以谓《三都赋》即类书不可,顾谓其兼具类书之用,亦无伤耳。挚虞《文章流别论》:‘赋以情义为主,事类为佐’,可资参悟。”[19]汉代推崇博学洽闻之士,以为通晓物理人事可资政教,故汉代经学成就卓著者被立为“博士”。司马迁、班固、范晔的史书中都曾论及以博物而见长的人物。汉赋因其举物连类、文字玮奇、韵律和谐的特点,便于诵习文字,增智广识,成为时人重视的文体。
考选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赋的流播,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兼具经学、小学知识的汉赋创作、欣赏群体。正如刘勰所论:“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颂,总阅音义,鸣笔之徒,莫不洞晓。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20]623这不独是对汉赋文字特点的总结,更道出了汉赋的文字之玮怪瑰奇,正在于当时文士普遍具有的高超的小学水平。
两汉虽未行科举,但官吏选试制度对文字水平的要求对汉赋产生了推动作用。汉赋增智广识、记诵文字的实用功用,使它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同时也培养了一个创作、欣赏群体。
三
东汉职官制度虽承续西汉,但实际情况并不相同,至东汉,征召、察举制已名不副实:
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兢。权门贵仕,请谒繁兴。自左雄任事,限年试才,虽颇有不密,固亦因时识宜。……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斯亦效实之征乎?[5]2040
由范晔所述光武中兴之后的吏选制度及情况,可知东汉时察举制已沦为权贵的利禄之门。左雄以选试整顿吏制,廓清吏选,亦不过十余年时间。故王符有论:
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嚚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21]虽言辞激切,但所言大体真实。
东汉官吏选拔制度的混乱确乎使官吏群体良莠不齐,但汉赋的创作依旧兴盛。由《后汉书》各人物列传及《文苑传》可知,赋家及其赋作在数量上并不亚于西汉。究其原因,东汉时太学制度作为职官选拔制度中的一种,培养了一大批才学文士,成为汉赋创作的主力。
汉代太学创始于武帝,董仲舒于《天人三策》中提出建立太学: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2]2512
汉代开设太学的目的是为皇帝求贤良材士以辅政教。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奏请“置博士弟子员”。马端临《文献通考》:“为前此博士虽各以经授徒 而无考察试用之法,至是官始为置弟子员,即武帝所谓兴太学也。”[7]382自此,博士弟子经考试后可选补官吏,成为汉代职官的候补队伍。
从西汉到东汉,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据《汉书·儒林传序》,太学建立之初,仅设博士弟子五十员,昭帝时增为百人,宣帝末增为两百人,元帝时“能通一经者皆复”,增至千人。成帝末,至三千人,后仍恢复为千人。王莽时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东汉光武帝复兴太学,“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5]2545。明帝、顺帝时期太学不断增科扩建,到质帝本初元年,太学博士弟子多达三万人。
汉代太学制度较为完备,首先,太学师生都要经过较严格的选拔。太学中的老师即两汉时期的博士,多选择德才兼备的名儒才士担当,如辕固生、申公、韩婴、夏侯胜、戴德、戴圣、梁丘、京房等。太学生也需经过选拔和考试,《汉书·儒林传》:“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辄课试。”[2]2394太学生不同于官吏,进入学校后还要经过学习考试,故相较于征召、察举类的官吏选拔,更为可靠。
其次,太学博士及太学生欲入仕,皆需再经课试。博士在成帝时即有明确的三科之制,《汉书·孔光传》:“是时,博士选三科,高为尚书,次为刺使,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光以高第为尚书。”[2]3353太学生也需通过考试方可选补官吏,设甲乙两科,射策课试。太学生员日渐增多,因入仕比例极低,竞争激烈,故大多数太学生学习勤奋,如兒宽、翟方进、沙穆等,虽贫寒而勤苦过人;仇览、魏应、鲁恭等皆以不事交游、闭门苦读而为人称道。
东汉太学学风相对纯粹,太学生经历数年的努力学习,普遍具备较高的文字及学术水平。东汉明帝时期辞赋较为兴盛,以班固为首的赋家多出于太学。班固于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至建武三十(公元54年),于洛阳太学求学八年,“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5]1330,为他创作大赋提供了学养。这从他对经学与辞赋关系的认识中可以得到侧证,《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13]21-22班固认为辞赋渊源于诗,并认为辞赋的文体风格及目的也与经学相似。这种对赋学的体认,显然与他在太学期间对经学的深入学习密切相关。
与班固同时求学于太学的还有傅毅、崔骃、贾逵等人,傅毅同样擅长辞赋,有《洛都赋》《反都赋》《琴赋》等;崔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5]1708-1722;贾逵“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闲事”[5]1235。其永平十七年所作《神雀颂》,收于《事类赋》,学界也有观点认为应归属赋类。
东汉的另一辞赋大家张衡,也曾就读于太学。《后汉书·张衡传》:“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5]1897张衡在太学期间通五经六艺,这在他后来的辞赋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马融为东汉辞赋名家,亦讲学于太学。另有太学生刘陶“及上书言当世便世、条教、赋、奏、书记、辩疑,凡百余篇”[5]1851;高彪“游太学……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异之”[5]2650。服虔“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学受业。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所著赋、碑、诔、书记、《连珠》、《九愤》,凡十余篇”[5]2853。
东汉赋家大多有太学经历,这并不是一种偶然,它揭示了汉赋与经学的内在联系,也是东汉时期太学制度影响汉赋发展的直接表征。太学的教学内容是经学,而经学与辞赋关系密切,正如《文心雕龙·辨骚》所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駟虬乘鷖,则时乘六龙;崑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20]46经学中的名物典章、铺陈讽喻确乎是辞赋艺术的渊薮。汉赋的博物洽闻与经学的名物掌故联系紧密,而附属于经学的小学也正是辞赋创作的基础。太学中满腹经纶的博士及太学生成为东汉大赋的重要创作、欣赏群体,太学制度客观上推动了汉赋的发展。
东汉时期,另一个与辞赋密切相关的职官制度是“鸿都门学”。据《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鸿都门学生”。李贤注:“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勑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5]340-341鸿都门学征召赋家入学,看似有益于汉赋的发展,实则不然。
《东汉会要》:“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22]钻营名利、无行趋势者得以破格提升,甚至“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5]1998。这与大多数太学生虽饱读诗书却不得任用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汉书·儒林传》:“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2]3569王莽有意增加太学生任官名额,但也不过百人而已,与为数众多的太学生相比,录取率极低。东汉时灵帝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开特例,“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5]338。选拔一百多名六十岁以上的太学生,已经是特例,但对于大多数太学生来说,入仕机会仍十分渺茫。
鸿都门学引起了当时太学生及正直官员的愤慨,“士 君 子 耻 与 为 列焉”[51998]。《后 汉 书 · 酷 吏传》:
(阳球)奏罢鸿都文学,曰:“……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託权豪,俛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销天下之谤。”[5]2499
献赋作为邀宠谄媚的行径,批判中首当其冲。
汉赋的发展受文体特点、传承与衍化规律、语言文字等多种因素影响,同时也受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汉代职官的选拔标准、选任方法、培养教育等制度,通过文人的仕宦命运,最终影响了汉赋的发展。
[1]王国维.王国维全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30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徐天麟.两汉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466.
[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孙星衍,校.汉官六种[M]//续修四库全书:七四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7]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郭预衡.汉赋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龄出版社,2004:3.
[9]钱穆.秦汉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98.
[10]陶新华.汉代的“待诏”补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5(6).
[11]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M].济南:齐鲁书社,1985:351.
[12]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2675.
[13]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
[15]贾谊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48.
[16]颜师古.急就篇注叙[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2.
[17]金秬香.汉代词赋之发达[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4-15.
[18]浦铣.历代赋话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
[19]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1151.
[20]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1]汪继培.潜夫论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75.
[22]徐天麟.东汉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