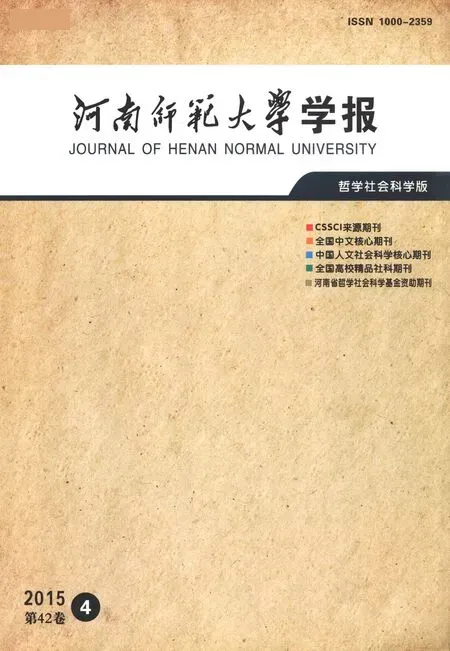论行政自我规制现象:经验与问题
岳 琨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088)
规范行政权力是行政法的使命,同时也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传统行政法治的控权逻辑强调的是外部规制,然而随着行政的专业化微观化的发展,行政主体的自我规制也可以而且应当成为重要的规范权力的机制。在美国,“规制”是联邦政府用来实施法律以及达到行政目标的基本工具,称为行政法律或者行政规则[1]。而自我规制指通常发生于一个特定群体内采用专业的方式控制这个群体成员及其行为[2]。这种行为被称为“最低限度的法律环境模型”(minimalist legal environment model)或者是一种权力下放的“立法”(decentralized emergent lawmaking)[3]。具体到行政自我规制而言,意为行政机构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如某一法规)限制自己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为。[4]实证研究表明,行政自制的最大优势是节约社会成本,并且会在以限定自由裁量权以及输出、结果导向的行政行为中发挥最大效用[5]。“行政自我规制”以规范行政权为目标,以行政主体自身及公务员行为为对象,为实现行政权合法、合理和有效行使,进而实现行政正义、增强行政回应性等价值的自我规范的制度、方式和手段总和。这种行政现象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不容忽视的推动行政法治的力量[6]。奥里乌曾指出:“行政机构的处理措施受其自身的严格监督,其中存在着一种自发的控制。”[7]可见“行政自我规制”作为自我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存在于行政权的运行领域,对行政权的规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行政自我规制实践效果如何,是否合法与适当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行政自我规制的正面经验
行政自我规制的现象可谓丰富多样。政府对自我规制的态度也经历了“冷漠-积极-依赖”的演变过程,这不单单因为自我规制的效率性、节约社会成本等基本特征,而且因为其可以作为行政规制的有益补充或者完全替代。然而,作为一种理论或者制度化的行政自我规制所研究的对象应该主要是现代行政法视野下的控权现象。基于此,对行政自我规制正面例证的研究,限定于当前行政权运行领域的自我规制现象。
(一)裁量基准制度的建立
行政裁量权广泛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实现裁量正义也是行政法所关注的问题。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就是行政主体为自己开的药方,它是一种行政自我规制的实践。裁量基准通过本身所具有的情节的细化和效果的格化[8],来实现对行政裁量权的控制。
在我国,裁量基准的实践先于理论的探讨,可以说是实践推动了理论的研究。裁量基准源于地方执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富有实践性和专业性。根据学者的考证,行政裁量基准实践的开拓者是浙江金华市公安局[9]。为了解决公安执法中存在的“执法随意、裁量不公”的问题,金华市公安局要求各县市局和分局选择一至两个治安状况复杂、案件数量较多、执法比较规范的科所队作为试点单位,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再确定一至两种最易滥用处罚裁量权的热点、难点违法行为展开裁量基准试点。经过近一年的试点,在进行总结和完善的基础上,金华市公安局制发了《关于推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的意见》,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通过对于金华市裁量基准制度的生成路径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实践中的裁量基准是行政自我规制的实践。裁量基准的设定主体是行政主体自身;其规范的对象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裁量行为;目的是为了在合法的前提下,通过对法律规定的裁量权进行细化,以确保行政裁量权合理行使,防止裁量滥用的发生,维护裁量正义。其次,裁量基准起于实践,具有问题指向。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主体在执法实践中对执法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而不是理论的演绎,具有实践先行的意味。同时,行政裁量基准的出现与实践中存在的“执法随意、裁量不公”问题有关,因而,裁量基准制度是应时所需,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出现的。再次,行政主体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金华市公安局制定裁量基准并非源于法律的明确义务,也非基于上级的指示和命令,是公安系统主动进行的执法制度的创新。这一实践事例表明,行政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进行行政自我规制的积极性。而从各地裁量基准的实践来看,制定裁量基准以书面文件表现是通例,即实现裁量基准规则的成文化。
(二)审裁内部分离的自我实现
当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时,自由就不复存在了,这一点尤其适用于行政处罚等侵益性行政行为。为了防止行政职权的过分集中,衍生出了行政职能分离制度。审裁分离是行政职能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负责人对于行政处罚案件的调查、裁决等都有决定的权力,因而我国并没有在实质上建立审裁分离制度。然而在实践中,行政主体通过制定本部门的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等方式,不同程度地确立了执法机关内部案件调查和处理决定由不同部门负责的制度。株洲县审计局的查处分离制度即是其中之一。
2003年3月,在总结多年审计执法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株洲县审计局制定了《株洲县审计局查处分离暂行办法》。通过该暂行办法,株洲县审计局正式确立了查处分离的制度。查处分离制度的基本内容是:第一,在组织机构方面,打破原来的处(科、股)室界限,对其进行重新组合,按人员结构、特长和工作需要内设若干个审计现场查证组和一至二个审计处理处罚组。第二,在工作职责方面,明确分工。一方面,取得审计证据、编制审计日记和审计工作底稿由查证组的审计人员负责。另一方面,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由审计组组长(主审)负责。查证组与处罚组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同时相互制约和监督。株洲县审计局的实践表明,查处分离制度起到了较好的效果[10]。
通过株洲县审计局的查处分离制度可以发现:从主体上看,查处分离制度的设立主体是审计部门自身,符合行政自我规制的主体要求。从目的上看,审计局设立查处分离的制度是为了防止审计职能的过分集中,将查处和处罚职能分配给不同的工作机构,使它们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和配合,从而提高行政效率,确保行政公平更好地实现,体现了自我规制的目的。在法律没有规定审查分离制度的情况下,株洲县审计局主动结合自身经验,将查处权和处罚权进行严格分离,体现了行政主体进行行政自我规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株洲县查处分离制度的确立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查处分离源于实践经验,是经验积累的结果。第二,审计局通过规范性文件的方式,确立了查处分离的制度。第三,查处分离并非基于法律的要求,而是行政主体主动进行的制度创新,在客观上具有行政自我规制的效果,体现了行政自我规制的积极性;在实践中不仅取得较好的行政效果,而且极大节约了实施行政目标的社会成本。
二、行政自我规制的负面例证
现实中,行政主体所进行的自我规制行为并不都是正面积极的。行政主体基于不当的利益或者使用不合理的方式而进行自我规制,不仅没有起到规制行政权的效果,反而造成了不利的后果,侵害了行政相对人和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行政执法指标制度和违法的工作责任制。然而,无论是执法指标,还是工作责任制,都是行政主体为了督促自身和公务员积极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而确立任务或者责任,是行政主体对自身和公务员行为的一种制约,因而也是行政自我规制的重要组成。
(一)行政执法指标制度
执法指标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自我规制措施。它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够促使下属单位和公务员积极履行职责,减少行政不作为的发生几率,但是,从实践的操作看,其消极意义显然大于其积极意义。譬如,《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以前,在整治城市秩序和外来人员的执法活动中,某一街道地区规定每月应遣送的指标为近千人。为了达到指标要求,执法人员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往往会不择手段,以致出现了各种侵犯人权的现象[11]。行政执法指标制度的滥用是钓鱼执法和运动式执法的内在动因。由于执法指标的完成度直接关系到公务员的奖金、晋升,完成不了指标甚至要受到惩罚,迫于压力,行政人员就会采取各种方式来完成指标,钓鱼执法、运动执法就成了行政执法人员的救命稻草。
行政执法指标制度作为行政主体在实践中摸索出的行政自我规制的措施,对于督促行政人员履行职责具有一定的意义,且效果非常明显。但是,各地的实践却使得它逐渐与法治精神相背离,成了各种违法现象的罪魁祸首。这种行政自我规制方式的合法性备受质疑。
(二)违法的工作责任制
实践中,工作责任制是行政主体进行自我规制的重要方式。通过实施工作责任制,可以确保公务员责任明确,提高行政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督促其积极履行职责,从而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并为公众提供良好的服务。但是,现实中存在行政主体违法实施工作责任的现象,严重侵害公务员的合法权益。湖南嘉禾拆迁过程中出现的“四包两停”工作责任制就是典型的反面例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交付各种证件及妥善安置等工作;不能认真落实“四包”责任者,将实行“两停”处理——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12]。
湖南嘉禾县的“四包两停”工作责任制的违法之处昭然若揭:首先,行政主体无权作出这样的命令。尽管地方政府有经济管理权,但是其无权发布命令要求公务员负责其亲属的动员和拆迁工作,法律未曾赋予其此项权力。其次,从公务员的义务来看,公务员虽然有执行上级决定和命令的义务,但是,这个决定命令本身应当是依法作出的,而且,应当与其自身的政府职责有关才是有效的。对自己的亲属进行拆迁动员和安抚,并非公务员的职责所在,政府却以此为工作责任的内容实属荒唐。“四包两停”工作责任制无视《公务员法》对于公务员职权保护的规定,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
三、行政自我规制存在的问题
管窥作为现象的行政自我规制实践,可以发现行政自我规制的实践与行政自我规制理论所倡导的原理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现实世界中的行政自我规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行政自我规制的动力不足,有效性难以保障,合法性受到质疑。
(一)行政自我规制的动力不足
行政自我规制的动力因素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否则自我规制就会欠缺动力基础。行政自我规制内在动力不足体现为动力的不稳定性和随机性;外在规制不足则体现为自我规制的持续性不强。
1.内在动力的不稳定性和随机性
行政自我规制的内在动力应当分解为:行政主体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公务员自我实现的需求。出于长远利益和生存利益的考量,行政主体会主动实施行政自我规制,然而,行政主体能否判断长远利益则有赖于行政主体的组织构成和机关文化,而这些在不同的行政主体中差异较大。尽管公务员都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和可能,但只有与良性道德相契合的自我实现需求才有可能促使其推动和认可行政自我规制。由于公务员选拨机制,特别是领导层面公务员选拨机制的缺陷,行政系统中公务员的道德素质参差不齐。部分公务员内在道德素质的缺失,使得行政自我规制的内在动力有所减弱。由于行政主体和公务员存在差异,因而行政自我规制的内在动力不具有稳定性,并且可能伴随着随机性。
2.动力缺乏持续性
行政自我规制的动力还有赖于外在的压力机制,因为外在压力机制可以转化为内在的动力。然而遗憾的是,外部规制在我国仍处于尚未成熟的阶段。就权力机关的规制而言,尽管宪法和组织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在监督和控制行政权问题上的至高权威,但是,并未改变人大在监督和控制行政权中所处的尴尬地位。一方面是由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要职能在于立法和修法,监督和控制政府显然是副业。尽管各级人大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况且其在重大法律事件上的妥协,使得它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人大对于行政权的依赖性不断加强,其授予或者默认了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权,这使得人大在监督行政权方面更加力不从心。就社会力量监督而言,我国的公民社会仍在发育过程中,还没有形成一种持续的和有效的控制力量。总之,外在规制的疲软使得行政权的生存压力较小,因而自我规制的动力不足也就不足为奇。
(二)行政自我规制的有效性缺乏保障
1.行政自我规制有效性欠缺的表现
作为现象的行政自我规制实践方式多样、政出多门,行政自我规制的规范性不足,并且往往遭遇有效性尴尬。以各地实施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为例,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问题,但是,裁量基准规则的有效性还是打了折扣。执法人员脱逸裁量基准的情况比较普遍。行政自我规制有效性欠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主要体现在规则制定比较随意,且更改比较频繁;自我规制的措施往往刚开始时效果比较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自我规制措施的有效性就可能减损,不具有持续性。其二,过分依赖领导的态度,一项自我规制措施如果得到领导或者上级的支持,就能起到较好的效果,否则就可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对于领导的过分依赖使得行政自我规制可能陷入一种人治的误区。其三,约束力和权威性不足。行政自我规制的措施往往都源于行政主体的执法实践,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这种情况下,行政自我规制措施的约束力和权威性就可能存在不足。
2.有效性欠缺的原因
作为制度性的自我规制理论,行政自我规制有效性欠缺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在于欠缺制度化和缺乏系统性。
首先,行政自我规制欠缺制度化,因而权威性和稳定性不足。实践中的部分行政自我规制现象具有显著的“运动式”规制的倾向。究其原因在于没有将行政自我规制的规则和措施制度化和正式化。行政自我规制的措施往往比较随意,人为因素和意志因素比较强。欠缺制度化生成,就使得行政自我规制往往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其次,行政自我规制措施缺乏系统性,未能形成规制的合力。从理论上讲,行政自我规制应当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治理。就目前而言,行政主体的自我规制实践大多还只停留在单个方式创新层面,自我规制的措施和制度只是散见于不同的行政主体内部,欠缺系统性和综合性。
(三)自我规制的合法性难保证
自我规制作为一种法律“间隙”中存在的“改良”(improved)设计[13],由于各种原因,现实中存在的行政自我规制实践面临着合法性困境,行政自我规制的正当性也有时受到质疑。欠缺合法性的行政自我规制,不仅不可能稳定地起到规范行政权的作用,反而会损害行政主体或者公务员的合法权益,损害法治的精神和原则。行政自我规制合法性的欠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人治色彩浓厚
某些行政自我规制措施从创制到实施整个过程,都是某个或者某些领导意志的结果,而且行政自我规制的实施和保障也过分依赖于领导的态度。人治色彩浓厚的行政自我规制,可能在领导的支持下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根本上是与法治的精神相违背的。
2.随意性
现实中,部分行政自我规制的做法具有随意性,从制度的创制、规则的制定和执行等一系列环节都欠缺规范性。行政自我规制的随意性一方面使得其效果的稳定性难以保障,另一方面也会使得行政自我规制措施的权威性无法得到满足。法治是恣意的敌人,行政自我规制的随意性会使得行政自我规制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四、行政自我规制问题的解决思路
行政自我规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在于动力不足、有效性无法保证以及合法性困境三个方面。解决这三个问题的重要思路是:通过增强外部规制,为行政自我规制提供动力机制;通过行政自我规制措施的制度化和系统化,促使行政自我规制有效性的实现;为了保证行政自我规制合法性,应当实现行政自我规制的法治化,遵循法治的路径。
(一)加强他制动力
从外部规制与行政自我规制的关系来看,外部规制可以为行政自我规制提供持续的动力。外部规制作为促进行政自我规制的动力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有效的外部规制使得行政主体面临一定的生存压力和行动压力。外部规制要求行政主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承担不利的后果。而行政主体进行自我规制则可以减少因为触犯外部规制所依据的规则而负担的成本,因而在有效的外部规制下,行政主体有选择自我规制的动力。其二,有效的外部规制作为一种持续性的监控机制使行政主体长期处于一定的压力状态,能够为行政自我规制提供持续的动力机制。加强外部规制一方面可以增加行政自我规制的动力能量,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行政自我规制动力的持续性。
(二)推进制度化
制度是一种系统化的规则体系,其基本功能在于解决特定的问题。制度化意味着将一定的规则系统化和明确化,从而确保规则的有效性和持久性,因而制度化是使得一项措施和理论永葆生机的关键。要确保行政自我规制的有效性,应当着重强调行政自我规制的制度化。制度化对于行政自我规制有效性价值在于:其一,通过制度化可以增强规则的明确性,从而使得规则和措施更加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其二,通过制度化可以加强自我规制措施和手段的权威性,而权威性又是确保规则被尊重和遵守的重要保障;其三,通过制度化可以确保自我规制措施和手段的稳定性。自我规制措施的稳定性是该措施能够持续的有效保障。
(三)走向法治化
解决行政自我规制的合法性问题,应当遵循一定的法治化路径。行政自我规制本身并不是法律规定的产物,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不应当遵循法治化的路径。相反,恰恰是由于行政自我规制往往是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制度和措施,因而其才更需要遵循一种法治化的路径。行政自我规制的法治化主要是借助法治的精神和原则、制度对其进行改造,使其与法治原则相契合,从而能够体现一种实质的合法性。
[1]Susan E.Dudley,Jerry Brito.Regulation:A Primer[M].Fairfax Virginia:Mercatus Center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2012:1.
[2]Robert Baldwin,Martin Cave,Martin Lodge.Understanding regula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125.
[3]Jeanne Pia,Mifsud Bonnici.Self-rugulation in Cyberspace[M].Hague:T.M.C.Asser Press,2008:23.
[4]Magill,Elizabeth.Agency Self-Regulation[J].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2009(June).
[5]Michael,Douglas C..Federal Agency Use of Audited Self-Regulation as a Regulatory Technique[J].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1995(Spring).
[6]沈岿.行政自我规制与行政法治:一个初步考察[J].行政法学研究,2011(3).
[7]莫里斯·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M].龚觅,等,译.沈阳: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488.
[8]周佑勇,熊樟林.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的区分技术[J].南京社会科学,2012(5).
[9]周佑勇.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以行政自制为视角[J].法学家,2011(4).
[10]颜泽云,罗才红.论审计查处分离制度[J].中国审计,2004(2).
[11]张建.评执法指标[J].政治与法律,2003(5).
[12]杨建顺.行政强制法18讲[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265.
[13]Levin,Harvey J.Limits of Self-Regulation[J].Columbia Law Review,1967(Apr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