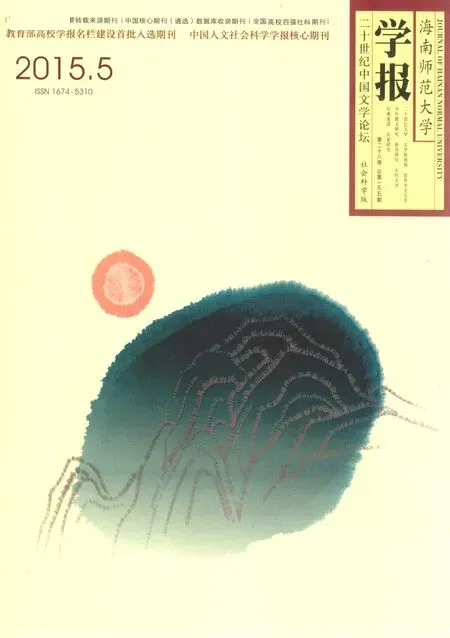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救济方式研究
唐欣瑜
(海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海南经济特区法治战略研究基地,海南 海口571158)
法律作为具有最高权威性及国家强制力的社会调控手段,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调整无疑是最理想的。但“如果无人维护权利,那么在法律中确立权利就是毫无意义的”[1]。近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应是维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现状[2],但由于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特殊性,立法逃避了对农民集体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权利主体的制度抉择,只静态地规定了“农民集体”。在我国的现行立法中代表农民集体行使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相关权利的有乡(镇)、村、村民小组三类集体组织主体,但不论上述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行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集体”,都是非常模糊而无法清晰界定。救济主体的不确定直接导致权利遭到侵害时农民及其集体找不到一种有效的救济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仅无法发挥法律制度应有的功能,法律的目标和价值也难以实现。因此,探讨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受到侵害时的权利救济方式具有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以司法救济为主的国家公力救济方式是权利受侵时的重要保障,但同时也不能忽视私力救济方式的重要作用,应在提高农民集体组织化程度、增强其自身谈判能力的基础上完善私力救济方式。各救济方式相互衔接,建立健全从事前的规范到事后监督追溯各环节的法律法规体系[3],共同保障我国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
一、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司法救济
“如果没有健全的司法机构来制约政治上的强权,农民将很少有法律上救济的途径。”[4]从国家角度而言,当权利主体的合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人民法院根据法律和事实、依循庭审程序作出裁判,以国家强制力对侵害行为进行制裁,补偿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就是司法救济。从农民集体角度而言,司法救济是指农民集体所有权权利运行受阻或受到侵害时,权利主体以诉讼的方式请求法院对其所有权与所有权中相关权利进行保全的救济方式。基于农民集体的特殊性,笔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重点讨论。
(一)救济主体的确定
研究集体所有权受侵害时侵权责任请求权主体很有意义,是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向社会宣示集体所有权的主体以及集体所有权的民事权利性质,从而维护集体所有权的司法实践活动。[5]由于现行法律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设定难以落实,导致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受侵害时不能明确认定受害人,相应地,由谁享有侵权请求权和代表农民集体行使起诉的权利也难以确定。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物权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2006)①2006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指出:“以村民小组为当事人的诉讼应由村民小组长作为主要负责人提起,村民小组长以村民小组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的规定,目前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及所有权中相关权利的救济主体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乡(镇)、村、村小组三级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可以申请救济;另一类是包括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在农村生产生活中具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即行使主体。农民集体的成员个人也可以是救济主体,但要区别的是,集体成员享有的权利救济(撤销权)来源于其成员权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63 条第2 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与前两类主体的权利基础是不一样的。集体成员个人行使救济权的客体是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侵害村民权益的决议行为,当然,并不是任意一项决议行为集体成员都能请求救济,只有该项决议行为的具体内容与集体财产权益相关并已直接影响到全体村民时,成员个人才具备救济主体的法定资格。它主要是在集体内部发生联系,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也只是内部的决议,并不享有可以代表农民集体对外请求救济的主体地位。
笔者认为,在救济制度上,应由村集体代表农民集体对外请求救济,改变以往因集体所有权主体不明而导致救济主体难以界定的情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村农民集体财产权益受侵害的侵权责任请求权和诉讼权行使的基本形态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村民集体行使侵权责任请求权和提起诉讼,法律赋予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在村集体财产权益受侵害时对外请求救济的权利。第二,许多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倒闭后,土地仍作为集体财产留用,此时再发生土地所有权的侵害,乡镇集体组织缺位而由乡镇人民政府代理乡镇农民集体行使侵权责任请求权和提起诉讼的权利。乡镇人民政府是行政主体,即使作为所有权代表也只能代表国家,而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意义上的民事主体,由乡镇政府起诉本身就是一种行政越权,反而会混淆集体土地所有权真正主体。此时再由乡镇的集体成员或者乡镇范围的村民委员会起诉,其主体资格的不适格很可能导致在法院审查资格时拒绝受理。将农民集体明确为村集体,直接由村集体行使侵权责任请求权和提起诉讼的权利,可以避免乡镇政府的行政越权。第三,就村民小组而言,尽管最高院的复函确定了其可以作为诉讼主体,但司法实践中往往对村民小组的诉讼主体地位产生怀疑。村民小组是村民委员会在村范围内依据村民的居住状况划分的村民集体,并没有进行登记的程序,许多村民小组也没有公章与对外的身份。如果没有经村委会盖章同意,在法院审查资格时村民小组的起诉很可能不能立案,也可能会被以村民小组的组织性不明确的理由被拒绝受理。笔者认为,直接由村集体行使侵权责任请求权和提起诉讼的权利并不是要否定村民小组的诉讼主体资格。村民小组不是离开村民的一个组织,它是小组范围村民集体的自身,侵害了本村民小组集体成员的利益从整体上而言就是村集体权益受侵害,村集体直接行使侵权责任请求权和提起诉讼的权利是有成立依据的。在村民小组集体土地财产权益受到侵犯,村集体负责人怠于行使侵权责任请求权或者本身就是侵权人之一的情况下,村民小组可以通过代位诉讼的方式行使侵权责任请求权,起诉侵权人,村民小组同样不会丧失救济主体的地位。
现行法律规定行使农民集体财产的救济权必须履行集体成员的法定合意程序,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团体源自半数以上的村民,而村民个人与救济客体往往难以构成法定的直接利害关系,允许个人起诉会引起滥诉。[6]笔者认为应借鉴公司法上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农民集体权益遭受侵害,村委会作为村集体负责人作为救济权利的行使主体怠于行使侵权责任请求权,当村委会或其管理人员本身就是对农民集体权益侵权行为实施者,集体成员可以自行直接提起诉讼,追究实施侵权行为的相关人员侵权责任,维护集体财产权益。具体可以参照《公司法》中关于股东代位诉讼的第150 条、152 条、153条规定设立农民集体成员代位诉讼,集体成员个人也应当成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侵权中适格的救济主体,既可以一个人,也可以联合多名集体成员提起诉讼,维护集体土地所有权相关权益。
(二)救济程序的设定
一项权利最终能获得救济,离不开实体规定与程序保障。救济主体行使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及相关权利救济权时,所依据的是《物权法》等相关法律的明文规定。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农民集体财产权救济的专有程序,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创制了相关救济程序①参见2006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履行民主议定程序,即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原本是为村民小组的起诉制定的,但在实践中同样也应当被村委会以集体名义起诉时沿用。由村民大会上的集体成员民主议定后村委会再以集体名义提起诉讼的程序在一般情况下是有其积极作用的,请求救济前的民主议定可以有效防止村委会擅自行事,避免其在诉讼过程中作出私下处分行为,在集体成员不知情的情况下造成集体利益损失。但民主议定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限制村民小组或成员个人所进行的代位诉讼,应该还要另行规定村民小组与集体成员个人可以不经过民主议定程序,直接向侵害集体权益的侵权人提起诉讼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村委会的失职,在集体利益持续受损的情况下仍不提起诉讼,甚至不召开村民大会;第二种情况是紧急情况,集体即将遭受更大的损失,需要通过及时起诉来制止。
二、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私力救济
私力救济是权利主体因情况紧急而不待寻求公力救济,凭借其自身力量保全相关权利的一种救济方式。私力救济在农村社会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较之城市居民,农民本身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常常因不懂法律而怯于诉讼,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也不大习惯于将打官司作为一个很好的权利救济手段。因此,在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能实行或难于实行之虞,农民集体往往会以集体之力作出相关处置,采取自我保全方式。另一方面,当农民及其集体失望于国家公权力为自己财产权利提供的保护时,走上私力救济的道路是其一种价值理性行动。“大道不畅,小道必昌”,农民集体及其成员为为了维护自身对土地的财产权,有时以围堵、吵闹等非正常途径对公权力进行群体性抗争与个体性抗拒,有的农民集体甚至在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全体出动,不通过诉讼手段解决问题而采取非法行为。
私力救济具有成本低廉和解决侵权问题迅速的优势,应该对农民集体的私力救济方式进行适当的引导。随着外来力量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渗入,除了国家的征地行为外,企业等相关主体越来越成为侵犯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重要主体。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农民群体一般首先选择协商谈判的私力救济方式与侵权主体交涉,由乡村精英或者村干部出面,并在谈判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的组织性,较之个人的私力救济而言,这种组织性是私力救济方式上很大的一个进步。但是,也要看到,农民及其集体因组织化程度较低而缺乏谈判能力,在要求损害赔偿的博弈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实际受损的具体判断,农民往往是先妥协的一方,企业给予农民及其集体相对低廉的损害赔偿金难以弥补其实际遭受的损害。正如奥尔森所言,农民集体是“最具迫切共同利益的无组织集团”,但由于“没有形成代表自己的游说疏通团体,不能够形成压力集团,于是也就饱受其苦”。[7]因此,引导农民集体的私力救济,需要大力普及农村法律知识,提高村民依法维权意识,拓宽农民维权渠道[8]。有必要成立农民自身的维权组织,发挥农民集体组织化的作用,一来可以集中集体智慧,在组织的指导下发挥集体力量与侵权主体进行谈判与对抗,能够获得较大的补偿;二来也可以让农民集体明白,非法的私力救济不但不能维护集体权益反而导致侵权损害,即使是私力救济也要进行合理维权,从而维护社会的整体稳定。
三、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救济方式的衔接
(一)司法救济中实体法与程序法应结合考虑
在诉讼实践中,大多数涉及农民集体的相关权利纠纷是由村民委员会直接以原告身份起诉,法院在认可村民委员会身份并将其列为原告的基础上将胜诉的实体权利判归其所有。笔者认为,虽然村民委员会以原告的身份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由来已久,并在诉讼实践中得以实现,但结合考虑到民事实体法,村民委员会虽为依法设立的村民自治组织,只是实践中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而不是民法实体意义上的“农民集体”。因此,法院在审查救济主体行使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及相关权利的救济时,应当结合考虑实体法与程序法,明确将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集体列为原告,村委会列为代理人,并以村民委员会主任为诉讼代表人,而不应将村委会这一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列为原告;相应地,在村民小组或集体成员代位行使集体的侵权责任请求权时,法院应将提起诉讼的村民小组集体成员列为原告,以村民小组组长为诉讼代表人,并按照代位诉讼将其代位主张的权益判归被代位的集体所有,确保胜诉的结果归属于村农民集体,而不是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
确定被保护的利益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利害关系是现代民事诉讼的核心,一般而言,实体的权利义务主体被认为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而利害关系人当中的另一类间接利害关系人指的是特定公益性质的案件存在实体的权源基础的权利主体。[9]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是具有公有性质的,集体土地事关国家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加上农民群体在自身维权上的弱势,农民集体土地权益的救济往往被看成具有一定的公益性。既然如此,就应当赋予检察机关代位农民集体诉讼的权利,规定在民事性重大公益案件中,一旦涉及侵害农民集体的土地权益、涉及集体成员的生存和国家粮食安全、环境生态等重大问题时,可以由人民检察机关作为农民集体的代位诉讼人,提起维护农民集体正当权益的相关诉讼。
(二)信访救济、私力救济与司法救济应进行程序衔接
信访是我国民间阶层比较熟悉的一种维权手段,是农民集体与成员在表达利益诉求时常常采用的维权方式,但由于信访救济程序的缺陷,基层政府从维护稳定出发,基本会采用缓和的行为策略来应对农民集体及其成员的相关诉求。在抗拒行动效果甚微的情况下,现实中农民集体与成员进行维权时会出现一些“非常”手段,为达到向地方政府施压的目的而进行群体性的信访,并会侥幸地认为“法不责众”。当农民及其集体仍然失望于国家公权力为自己财产权利提供的保护时,群体性的信访就容易演化为群体性的私力救济,而不再是在信访救济的合理范围内。为了缓解社会矛盾,避免群体性事件带来的不良后果,需要在信访救济、私力救济与司法救济之间进行程序衔接。信访虽然为公民政治参与及民主监督提供了制度化渠道,但它毕竟不是解决民间社会现实矛盾行之有效的手段,解决问题的行政机关也不具备司法机关的相关职能,只能是在对司法进行查漏补缺的情况下纠正公权力行为,并不能解决由此带来的所有纠纷。因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救济应强调以程序正义为特征的法院作为权利救济最后途径与最后防线,但同时也应看到,当司法拒绝或者不能有效给予农民土地财产权救济时,特别是在针对地方政府的行政诉讼中,信访的力量与群体性的私力救济力量是强大的,高层政府通常会对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矫正,弥补当地的司法救济因顾忌地方公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网络而力有不逮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救济应以司法救济为主,私力救济与信访救济为有效补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农民集体的组织性与主体性,实现各类救济方式的相互衔接,共同保障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
[1]〔英〕麦基文.宪政古今[M].翟小波,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62.
[2]窦祥铭.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及具体政策选择[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107.
[3]唐欣瑜.农垦农地法律制度突出的问题及其对策[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64.
[4]〔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复杂地权的代价:以中国的两个制度为例[J].清华法学,2012(1):15.
[5]韩松.农民集体所有权和集体成员权益的侵权责任法适用[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2):129.
[6]张旭勇.集体所有、村委会管理与村民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兼论“村”的公法人地位[J].浙江社会科学,2012(2):53.
[7]〔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5.
[8]符青松.关于保障农村集体土地权益的思考[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7):31.
[9]李喜莲.民事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人”之界定[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