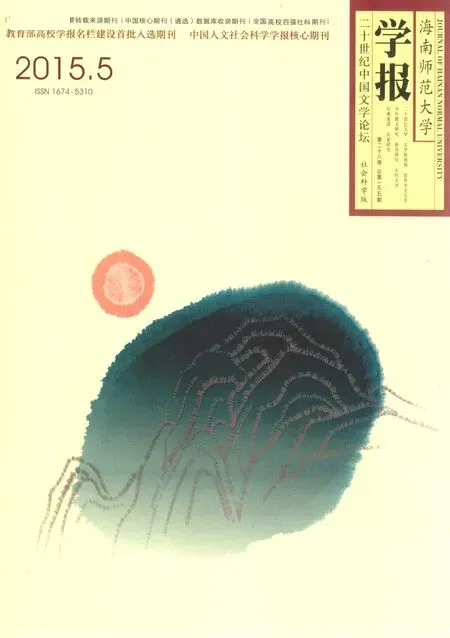传播学视野下的平衡的张力——论曾庆江《媒体平衡论》的三大学术特色
传播学视野下的平衡的张力——论曾庆江《媒体平衡论》的三大学术特色
钱浩君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曾庆江先生的《媒体平衡论》是一本聚焦当下、透视媒体在新时期发展情况的理论著作。作者从媒体的本质、形式、内容、价值、理念五个角度出发,构建了25对二元对立统一的概念,展现了它们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并努力寻求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和平衡点,结构严谨,脉络清晰。书中既有对经典案例、最新案例的分析应用,又有作者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构建的独特理论框架,在真正契合传播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要求下,条分缕析,向传播学理论研究者、实践者及读者阐释了平衡论的理论,为媒体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具有方法论意义。
一、时新性:聚焦当下,应运而生
“时新性”是作者自己在书中所采用的一个概念,强调“媒体在第一时间对新闻事件做出反应进而报道”[1]85。作者所采用的“时新性”揭示了新闻的“新”字之义。实际上,曾庆江先生的这本凝聚着新闻传播学界最新理论研究成果的著作,也鲜明地体现着时新性的特色——它在第一时间对媒体传播领域的失衡现象进行了描述,并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媒体的发展轨迹也随之改变,由垄断管制渐变为以服务为核心、以市场为主导的经营模式。但是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媒体偏离服务本位、哗众取宠乃至抛弃社会责任的现象屡见不鲜。加之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媒体也不断发展、创新,在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之外,产生了网络、手机等新兴时尚的信息传播载体,它们加快了信息的制造与传播速度,使人类在几未察觉的状态下迈入了所谓的“大数据”时代,一个浩瀚无穷的信息的宇宙由此呈现在世人眼前。每年,海量的信息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被生产,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被卷入信息传播数量和速度的狂欢,又在狂欢之中消解了意义、迷失了方向。当下媒体发展之中乱象丛生,失衡的现象无处不在。针对目前传媒领域的种种失衡现象,曾庆江先生凭新闻工作者敏锐的嗅觉,在第一时间抓住这个新问题,将著作着眼于“平衡”二字,致力于探索一条媒体发展的平衡之路,可以说是应运而生,颇具时新性。
“平衡”,一个原本属于力学的概念,在当今社会被频频应用到经济学、法学、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中,足见“平衡”对于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重要性。而它出现在新闻传播学的系统理论著作中还属首次。著者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在大众媒体狂欢的时代探讨其利弊,并给以相应的解决之道,因此时新性又体现在书籍具有较强的预见性这一点上,一定程度地展现了著者的眼光。以媒体大众化和小众化的平衡为例,众所周知,媒体是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桥梁,传播者要做的是将信息传播到尽可能多的受众之中,因此,大众化无疑是媒体最根本的属性之一。然而,作者也指出,在媒体竞争日趋激烈、受众市场逐渐饱和的情况下,受众对媒体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为了保证现代传媒的持续发展,媒体传播的大众化向分众化、小众化转变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于这种未来趋势,“差异化、对象化是其根本……最直接、最重要的做法就是体现媒体市场的细分化”[1]164。多数学者的论述即止步于此,但是作者却进一步探究了大众化与小众化之间的尺度该如何拿捏的问题。因为市场营销理论又决定着它不可能被无限细分、实现信息“一对一”的传播。那么,“大众化”与“小众化”该如何区分、怎样把握?平衡的意义就于此彰显了。作者的论述逻辑缜密,环环相扣,水到渠成地得出寻求平衡是解决问题根本之道的结论。结合实际预见未来,又给出对策,让作者少了些理论的掣肘,多了份论证的自如。
《媒体平衡论》旨在针对性地解决媒体中现存的诸多问题,立足当下,写前人所未写,时新性是它不可被忽视的一大学术特色。
二、完整性:构建媒体平衡的理论框架
媒体平衡论是新闻学领域一个崭新的学术增长点,前人对新闻传播过程中“失衡”与“平衡”现象的论述散见于一般的学术论文中,而《媒体平衡论》则是当今学术界第一部架构体系、独立成书探讨媒体平衡理论的著作。对于这部首开媒体平衡论研究先河的著作而言,它在体系的构建、内容的展开等方面表现出了较强的完整性。
前文曾指出,《媒体平衡论》从媒体的本质、形式、内容、价值和理念五个方面的平衡理论横向展开,又分别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纵向剖析,涉及新闻传播理论的方方面面,不可不谓之全面。著者立足全局,宏观把握,为读者呈现了清晰的叙述思维和文本脉络。作者在《媒体平衡论》中构建并论述了25组对立统一的概念,强调事物既对立又统一的属性,也即媒体在发展过程中既有良性的一面,又有不好的一面,既有主要的一面,又有次要的一面,两面结合才能概括当下媒体发展的整体格局。例如在媒体形式平衡论中的全国影响和地方保护一节中,作者指出,追求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是媒体发展的目标,然而地方保护的现象却使媒体的某些报道囿于一隅,二者矛盾之时靠平衡;而作者在媒体理念平衡论中的社会伦理与媒体伦理一节中则认为社会伦理是基本,职业伦理当从属于社会伦理,二者冲突之下有主次。作者从正反两个角度切入,对比论证,避免了对现象描述的片面化而体现出论证的完整性,同时,一正一反的论述手法相得益彰,既让理论更加通俗易懂,又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
在理论的阐发之余,发现问题并揭示其本质是本书作者始终秉持的一个观念,它增强了文本的深度,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建构了此书内容上的完整性。现实生活中并不缺乏为媒体的繁荣和贡献高唱颂歌的报道,也并非没有对某一不良现象加以揭露和批判的行为,但我们缺乏的是对大众传播领域的辩证而理性的反思,缺乏的是问题意识和对媒体真正价值和意义的探究。我们可以看以下例证:与媒体曝光社会不良现象、维护社会风气相对的是,当下一些媒体不顾被报道者的感受,擅自披露当事人的隐私;与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无偿服务于人民与社会相对的是,有偿新闻篡改事实、成为媒体谋取私利的手段;与媒体传播优秀文化、便捷知识学习相对的是,人心浮躁、学术造假之风盛行;与关注国事要闻相对的是,“凤姐”、“芙蓉姐姐”等被炒作的无意义噱头污染着传媒环境……作者在此类对比论述中为读者揭开了当下媒体一派繁荣发展下的面纱,将媒体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狂欢的表象劫持了意义,横亘在媒体面前的残酷现实是信息泛滥与真理遮蔽之间的对抗、公益与私利之间的博弈、大众普及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较量,这些问题怎样解决?媒体未来的发展将何去何从?在对以上问题深入思索的前提下,著者提出的媒体平衡论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平衡、该如何去平衡,该书例证丰富,论证严谨,不仅阐发理论,而且针对各种实际问题展开论述,生动而富有实践意义。
综上可以看出,《媒体平衡论》不论是在体系建构还是内容书写方面都有着很强的完整性,力求全面、准确,这是此书的第二大学术特色。
三、现实性:社会责任担当与人文关怀
与传播学理论通识教材的过于专注学术性不同,《媒体平衡论》在学术之外还鲜明地体现了著者的社会责任担当和人文关怀意识,这也是本书最大的特色。
回溯媒体的诞生,纸媒无疑是其最原始的形态。近代中国报业兴起于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时期,率先凸显了我国近代报人救亡图存、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志向,后历经王韬、梁启超等几代报人的探索,初现我国现代报业的雏形。诚然,有学者将中国近代报业的办报理念与西方屡作对比,指出近代中国报纸几乎无不局限于办报人的政治诉求中,往往成为特定政治主张的宣传阵地,而缺乏西方报纸之独立精神和自由理念。但是,抛开经济基础、政治形态或文化渊源等深层次原因,其实,中国近代报业形态的诞生本身就意味着以这些办报先驱为代表的中国人对国事的关注、对国家民族之未来的关心,这是他们不做国之兴亡旁观者的宣言,而不做旁观者、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也是作者开篇即引梁启超《呵旁观者文》之雄文想传达的坚定理念。
然而,是什么使得一些原本立足于救国、唤醒民众、传播正义和自由的报纸及各种新兴媒体陷入了旁观者的境地?报纸兴盛之后,收音机、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体相继诞生,新的形式促进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也扩大了信息覆盖的范围,伴随着传播媒体的发展,作为信息接受者的个人也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作者在书中分析道,“在传统媒体的架构里,传者和受者是壁垒分明的两个部分”[1]64,但是“新媒体时代,传受之间的互动前所未有的增加……传受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且经常互换位置”[1]64-65。如今,曾经的受众也可以轻松地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之中,为媒体的“言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众媒体真正进入到狂欢化时代。但是,隐患与狂欢如影随形,一方面,大众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民主化和无与伦比的便利;另一方面,面对利益,媒体竞相追逐眼球新闻而漠视社会民生,信息泛滥、信息异化等灾难不可回避,传媒工作者们在丰厚的经济利益诱惑面前承受着职业操守的严峻考验。旁观便由失责的媒体发展而来。面对这种情况,作者在《媒体平衡论》开篇批判了当代媒体发展中的“旁观”现象,并在全书贯穿了媒体工作人员要严格履行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理念,把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放在了媒体工作的首要位置。
《媒体平衡论》是一部指导媒体如何良性发展的书籍,追求平衡、扑灭乱象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和谐和人自身的发展,可以说,人文关怀是它的核心理念。为了媒体在良性发展基础上提高服务层级,作者把这个观念渗透于媒体中,批判了当今社会上一些漠视信息接受者的需求、或者为迎合部分人群的口味而弃职业操守于不顾的媒体,并在末章强调了社会伦理及媒体伦理的规约作用,论述了媒体教育和实践应当如何平衡作用,以培养出能力强素质高的媒体工作者,打造合格优秀的媒体服务工作者队伍。在此意义上,《媒体平衡论》不仅完善了学界在此方面的理论研究、为社会媒体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更向读者传达出了深切的人文关怀。以风靡一时的英剧《黑镜子》为例,它在第一部第一集为观众呈现了一出媒体暴力下酿成的政治悲剧、人类悲剧。公主清晨被绑架,绑匪要求首相在当天下午与一头猪做爱,并向全世界直播。虽然政府封锁消息,但是媒体工作人员通过贿赂、色诱内阁官员获取并即刻爆出消息,广泛传播于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络上。在各种努力均告失败后,首相只好就范。殊不知,在这场荒谬的闹剧直播前半小时,绑匪就已将公主释放。可惜,所有人都在电视机前围观首相与猪做爱的笑话,而没有及时结束这场闹剧。这场令人咋舌的闹剧实际上是在媒体的助长下酿成的,可以想象,如果媒体恪尽职守,不为赚取眼球而进行炒作,如果群众没有漠然围观及时发现公主已经获救,绑匪就不会如此轻易地达成目的、制造丑闻。人类被媒体——被自己发明的科技——愚弄了却浑然不知。这个故事发人深省,警示媒体该将目光转向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而不是一味地追逐经济利益。
社会责任担当和人文关怀是崇高的精神,曾庆江先生不仅立足媒体的平衡发展提出了这样的现实期望,更于此彰显了其个人的情怀。著者所言即所行,这是他作为一名学者对自身研究的突破,也是他作为一名社会成员对责任的自觉担当。
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来火种,纵使陷自身于万劫不复之地,却为人类带来了幸福的生活。感慨于普罗米修斯的无私博爱的同时,反观这神圣的火种,却也有因用之不慎而带来的灾厄种种,如战火纷飞、烧杀劫掠。时代和媒体的发展也犹如一粒火种,它生命力旺盛,它势不可挡、可成燎原之势,只是我们一定要加以善用,方可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助益。否则便会激发它潜在的危险,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灾难。
王蒙曾撰文《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直陈信息时代的忧患,控诉其种种弊病。他给人们的寄语
参考文献:
[1]曾庆江.媒体平衡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2]王蒙.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J].读书,2013(10).是:“越是触屏时代,越是要有清醒的眼光,要有对于真正高端、深邃、天才与创造性的文化果实苦苦的期待。”[2]王蒙的话是站在受众的角度而言,即便信息世界纷纷扰扰,人们也要独善其身。而《媒体平衡论》则站在信息传播者的角度,凝聚着青年著者与王蒙同样的期待和苦心,在时新性、完整性、现实性的三大学术特色的基础之上,以期探索一条媒体走向和谐、文明发展的道路,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袁宇)
A Discussion on Three Academic Features in Zeng Qingjiang’s Media Equilibrium Theory
QIAN Hao-j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作者简介:钱浩君(1990-),女,山东临沂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3-0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5)-05-014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