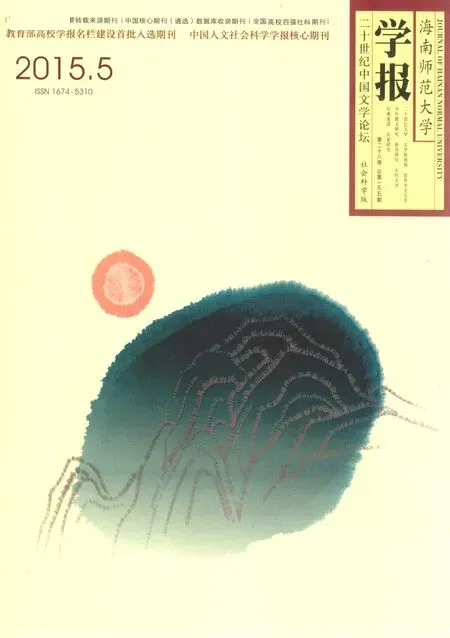唐诗修辞的境界与唐诗修辞研究的境界——评段曹林《唐诗修辞论》
唐诗修辞的境界与唐诗修辞研究的境界——评段曹林《唐诗修辞论》
吴礼权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200433)
熟悉中国文学史者都知道,唐代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并非只有诗歌创作一个方面。小说创作、散文创作与词的创作等等,其实都是成就斐然的。但是,只要一提到唐代文学,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首先想到的则都是唐诗。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恐怕主要还是与唐诗特殊的影响力有关。
说到唐诗的影响力,大家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它与唐代的诗赋取士制度有关。因为唐代读书人由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最主要的途径便是通过科举考试。只要进士及第,不仅可以不负十年寒窗之苦,“一举成名天下知”,还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享受世人投来的无限的羡慕眼光,而且可以真正体会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荣耀,实现由民到官的身份转换,从“修身齐家”跃升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境界。而这种人生境界,是有唐一代所有士子所心向往之,并终其一生而孜孜以求的。正因为做诗与自己的命运穷通有直接的干系,所以读书人自然要在做诗方面狠下功夫。由于以诗赋取士是一种制度,这就自然而然地影响到社会风气,造成整个社会对做诗与做诗之人的崇拜。这又在客观上促动了做诗之人对做诗的用心,在字句上讲究。即使是已经考上进士,并且是功成名就的文豪,也醉心于诗歌字句的锤炼推敲。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苦吟》),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等“夫子自道”,都能让我们真切地见出唐人是如何地重视诗歌修辞问题。正因为如此,唐诗与它之前的历代诗歌相比,在修辞的整体水平上明显有很大的跃升。应该说,唐诗历经千余年,至今仍有永不衰歇的生命力,有着无限的艺术魅力,不能不说与它高度的修辞境界有关。
除了现实的功利因素外,唐诗修辞境界的大幅提升,还与唐代的修辞研究水平有关。熟悉中国修辞学史者皆知,“大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为鼎盛的时代,亦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鼎盛时代”[1]12。由于“诗歌发展的鼎盛,导致了有唐一代微观修辞哲学的发展严重偏倾于诗歌方面。如唐代辞格论多着重于以诗歌为对象,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字句篇章修辞论、文体风格论等,亦是就诗歌而为主体阐发的”[1]12-13。如“对偶”问题,是诗歌特别是唐诗最重视的方面,唐代的很多学者(有些人本身就是诗人)对此都有很深的研究,撰有专门的著作,提出了很多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如上官仪的《诗苑类格》一书,是“专门讨论诗歌格律的,其中提出了诗歌对偶的‘六对’、‘八对’说”[1]130。元竞写有一部专书,叫《诗髓脑》,“专论诗歌创作与修辞技巧,其中论及到对偶时提出了六种对偶类型。”[1]131著名修辞学家崔融则著有《唐朝新定诗格》一书,“其中论及对偶者提出了三种对偶法”[1]131。著名诗僧皎然则撰有《诗议》一书,“亦有论对偶者,其中提出了八种对偶法”[1]132。至于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诗格》,则是专论作诗法的专书。“其中论及对偶时,曾提出了五种对偶法。”[1]133又如诗歌中的“比喻”问题,唐代的修辞学家们讨论得也很多。僧人虚中在其《流类手鉴》一书中提出“善诗之人”必须“心含造化,言含万象,且天地、日月、草木、烟云,皆随我用”的比喻原则。诗人贾岛在其著作《二南密旨》中则提出“四时物象节候者,诗家之血脉也”的观点,认为“‘造化之中,一物一象’对比喻皆有用途”。诗人白居易在其修辞著作《金针诗格》中对历来文人以“日月比君臣,龙比君位,雨露比君恩泽,雷霆比君威刑,山河比君邦国,阴阳比君臣,金石比忠烈,松柏比节义,鸾凤比君子,燕雀比小人”等现象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诗有物象比”的学说。至于僧人淳大师的《诗评》中所提到的“象外句格”,则是“从比喻与对偶相结合的角度来论比喻的”,[1]133皆是对诗歌创作的修辞实践有启发意义的。至于诗歌中如何“用事”才算贴切,如何“婉曲”达意才算高妙,在齐己的《风骚旨格》、皎然的《诗格》、王昌龄的《诗中密旨》、徐寅的《雅道机要》等修辞著作中都有论述。在诗歌字句篇章修辞方面,唐代诗人与学者也有研究心得。诗人王昌龄的《诗格》、僧人文彧的《诗格》、徐寅的《雅道机要》以及白居易的《新乐府·序》都有论述。
我们都知道,学术研究都是旨在推动某一领域的实践活动的,为其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唐代诗人或学者热衷于唐诗修辞规律的总结,并提出许多修辞原则与理论见解,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为学子或做诗人提供修辞理论指导,从而使所创作出来的诗歌作品符合科考的需要,或是使诗歌作品更为人所传诵。正因为唐代有很多学者包括诗人在诗歌修辞方面有丰富的理论,所以近体诗格律最终能在唐代得以定型,从此开创了近体诗一千多年的辉煌创作历史进程,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由于学术研究的促动,诗人们的诗歌创作在修辞上都有相当的自觉性。这当然有现实功利的因素(科考),但是也有艺术上的追求。如果说在协韵、平仄等修辞技巧方面下功夫是与科考的功利目的直接有关的话,那么其他修辞手法的创新则不能完全说与功利有关,而应该说是诗人在修辞技巧与艺术创新上有所追求。比方说,以名词或名词短语连续铺排的“列锦”修辞手法(或称“名词铺排”[2]),虽然不是唐代诗人的创造发明,而是“在先秦的《诗经》中就已经萌芽”[3],但是列锦修辞手法不仅在唐诗中广泛运用,而且“结构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新模式都陆续创出”[4]。仅初唐诗歌中就创出自先秦、两汉直至魏晋南北朝时代都没有的六种新的结构模式,分别是:“(一)两个‘偏正式复合名词(或名词短语) +偏正式复合名词(或名词短语)’形式的短句并列对峙而成列锦”,[5]98“(二)两个‘名词+偏正式名词短语’形式的短句并列对峙而成列锦”,[5]99“(三)两个‘偏正式复合名词+偏正式复合名词+名词’形式的短句并列对峙而成列锦”,[5]100“(四)两个‘名词+名词+偏正式名词短语’形式的短句并列对峙而成列锦”,[5]100“(五)毗邻成对的二句中有一句是列锦的模式”,[5]100“(六)由三个以上短句并列对峙的名词短语句群而构成的列锦模式”。[5]101直到中唐时,诗歌中仍有四种列锦结构形式的新模式创出。[6]我们都知道,列锦修辞手法在汉语修辞史上并不是什么特别常用的手法。但是,在唐代这一修辞手法还有如此多的结构模式的创新。由此可见,唐代诗人在修辞上力求创新的企图心是多么大。
正因为唐代诗人在诗歌修辞上有很大的企图心,所以唐诗才会有其他许多时代诗歌所没有的巨大魅力,让人一提中国诗歌就会首先想到唐诗。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每当人们谈到唐诗或唐诗的魅力时,往往都会将注意力集中于唐诗的意境、思想内容等方面,而对于构成唐诗巨大艺术魅力的修辞手法的探讨则较少。自古及今,对于唐诗中许多名篇,都有人谈论,赏析的文字不知有多少。但是,仔细看看,绝大多数都很少触及唐诗的修辞问题。即使偶有触及,也往往语焉不详。至于对唐诗修辞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令人欣喜的是,时至21世纪初,从修辞的视角切入,对唐诗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终于出现,这便是段曹林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唐诗句法修辞研究》。此书虽是专谈唐诗的句法修辞,但切入的视角好,开掘深入,因此获得答辩专家的一致肯定,认为是从修辞学角度研究唐诗最有力的论著。此书2005年由海风出版社出版,在修辞学界产生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之后,段曹林教授又再接再厉,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唐诗的修辞问题予以深入探讨。在武汉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段曹林教授选择的课题是《唐诗修辞研究》。从选题的名称看,我们便知道,这一次他对唐诗修辞问题的研究已经不满足于句法修辞一途了,而是要对唐诗修辞的方方面面进行全面的观照与探讨。2014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修辞论》,呈现在学界面前的正是一部全方位多层面探讨唐诗修辞问题的专著。它是在作者武汉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打磨而形成,不仅相较于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很大的跃进,也比博士后出站报告有了跃进,是一部非常严谨、系统性非常强的研究唐诗修辞问题的专著。从中国修辞史的角度考察,这部专著可以说是目前研究唐诗修辞问题最权威、最有力的学术专著,是非常值得修辞学同行关注的。
《唐诗修辞论》一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唐诗的语音修辞”,包括“唐诗的语音选择修辞”、“唐诗的语音组配修辞”、“唐诗的谐拟修辞”等三节;第二章“唐诗的语义修辞”,包括“唐诗的同义选择修辞”、“唐诗的语义配置修辞”等二节;第三章“唐诗的语法修辞”,包括“唐诗的词法修辞”、“唐诗的句法修辞”等二节;第四章“唐诗的篇章修辞”,包括“唐诗篇章修辞方法的运用”、“唐诗篇章修辞的审美效应”等二节;第五章“唐诗的风格修辞”,包括“唐诗言语诗体风格的丰富与创新”、“唐诗言语时代风格的统一和变迁”、“唐诗言语个人风格的独特和多样”等三节。
由全书所列的章节,我们就能清楚地见出此书对唐诗修辞的研究是全面的,语音、语义、语法,甚至一般修辞学著作很少涉及的篇章与风格,也都论及。因此,从整体架构来看,全书对唐诗修辞研究的思路是相当严密的,体现了鲜明的系统性特点。这是从宏观上看。如果从微观上看,我们还能发现作者在研究中有很深刻的思考,有明显的研究详略倾向。全书五章,第二章至第四章都是每章两节,但是第一章论唐诗语音、第五章论唐诗风格则都是三节。表面看来,这只是章节安排问题,实则不然。这里体现了作者对于唐诗修辞研究诸方面有所侧重的思想。我们都知道,诗歌不同于一般文体,它不仅可以阅读,诉诸于视觉感官,还要诉诸于听觉感官,通过吟唱给接受者一种审美享受。因此,韵律修辞是自古以来诗歌创作一直孜孜以求的一个重要修辞“标的”。唐代诗歌创作的主流是近体诗,对格律有具体的要求。因此,在语音修辞上着力,乃是基本的要求。作者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建构唐诗修辞研究的学术体系时,特意加大了对唐诗语音修辞研究的力度。体现在篇章结构安排上,就比其他方面多出了一节内容。这样的研究倾向与章节安排,我们认为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相当具有合理性的。事实上,我们读这部著作,首先觉得眼睛一亮的就是第一章谈语音修辞的部分。应该说,这一章的内容是其他修辞学者从未涉及过的,是作者的创新突破点所在。如果要追究作者之所以会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研读一下作者对于语音修辞研究价值的观点,就能了然于胸。如第一章开篇明义部分,作者就有这样一段话:“语音修辞方法不仅能利用语言建筑材料的音乐性建构言语动态过程的音乐美(整齐美、抑扬美、回环美等),带来声音方面的修辞效果;而且能利用音形、音义结合关系的多样性以丰富表情达意的手段,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强调、关联、变化、情趣、含蓄等),强化意义方面的修辞效果。”[7]1通过对唐诗语音修辞的深入研究,作者形成了自己对唐诗语音修辞的整体看法,明确指出:“在唐诗中主要运用的语音修辞方法有双声、叠韵、叠音形式的选用,响音字与衬音字的选用,声韵调的协调与呼应,音节的协调与呼应,音组的协调与呼应,谐音修辞、拟音修辞等。在实际运用中,古体诗和近体诗在这些方法的分布、用法、作用等方面又有差别。作为语音修辞方法,在唐诗中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建构诗歌的音乐美,产生语音修辞效果;但又不一定局限于声音方面,很多时候追求的是声情并茂,而语音的特点和联系也有可能只是媒介或手段,其目的则在表现视觉形象或含蓄达意、生动表意、多重表意,如谐音修辞是典型的借音表义,而拟音修辞往往也是绘声传情兼具。”[7]1-2这种对于唐诗语音修辞的整体认识,如果没有长期对唐诗进行全面研究的扎实功底,没有对唐诗语音修辞进行过深入探讨,那是无论如何也提不出如此鞭辟入里的见解的。
正因为作者对唐诗语音修辞研究得比较深入,所以不仅在宏观上对唐诗的语音修辞大势把握得相当准确,而且在微观研究上更是新见迭出,令人不得不由衷感佩。如作者在谈唐代近体诗的四声递用问题时,总结出三种突出的表现:“第一,韵脚平声字阴阳相间”,[7]15“第二,奇句句脚仄声字四声俱全”,[7]15“第三,一句之中四声交递”。[7]17对于每一种表现,作者都予以举例论证,从而总结出规律。如对于第一点,作者通过对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的定量统计分析,进而明确指出:“(杜甫这五首诗)每首都有阴有阳,有一半是阴起阳接或阳起阴接的有3首,完全做到阴阳相间的只有第二首,这就带来了韵脚的清浊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字句不亮’的问题。这五首诗对阴阳相间的运用情况,也可看作唐诗在这方面的一个缩影:不是所有的人都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只有声韵感觉细腻的诗人有可能注意到这种细微差别,而真正会否将这一方法付诸实施以及实施的程度,还取决于内容表达和格律条件的限制下还是否存在讲究阴阳相间的可能,以及这种可能有多大。”[7]15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又比方说,近体诗中的“拗救”问题,是诗歌语音修辞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对此予以了高度重视,不仅进行详细论述,而且根据自己对唐诗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拗救’有被动的补救,因为近体诗格律严格,诗人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不得不采用一些拗句,进而利用平仄调配规律,通过救对拗句进行补偿,使诗句达到新的平衡。但在多数时候成了化被动为主动的一种修辞策略,用于追求一种高古的风格,或者用于在满足诗歌声律要求的前提下,争取表情达意的更大自由。有的拗救甚至不是先拗后救,而是为救先拗,利用拗救的方式,解决特定位置平仄和表意之间的矛盾,使意义、词类等合适而平仄不合的词可以用于对仗。如常用数目字只有三、千两个平声,其余都是仄声,这就带来了对仗时数字相对的困难,用拗救法为问题找到了一种有效的解决途径。”[7]14这种从修辞的视角而进行的分析,明显与一般谈诗歌格律的著作不同,是相当具有理论穿透力的。
上面我们说过,《唐诗修辞论》除了在唐诗语音修辞的研究上有很多创获外,在唐诗篇章修辞与风格修辞方面也多有新突破新收获。如第四章第一节谈唐诗运用句法手段谋篇时,作者细致地总结了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不仅令人对唐诗谋篇的修辞技巧有了真切的认识,也对唐诗魅力之形成有所感悟。比方说,在谈运用“管领词语”谋篇时,作者指出:“以包含‘君不见(闻、能)……’等管领成分的固化句式引发注意、领起议论等,是《行路难》等乐府诗开创的重要开篇技法。《乐府解题》曰:‘《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唐古体诗继承并拓展了这一技法,在不同诗体发议论时都用,不仅用于发端,还用于诗中诗尾。其特点是引导内容、形式都与前后诗句大不一样的多个诗行,起标志、切分语义段落的作用。如岑参《走马川行》的‘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引导位居篇首的三句诗,同时又提纲挈领,开启下文。而白居易《春寒》‘君不闻靖节先生尊长空,广文先生饭不足’则出现在诗末,就事生议,总结上文。”[7]135“以‘请君’句直接对话读者,或转换人称,以提请注意,也是唐诗谋篇技法之一。查《全唐诗》‘请君’句共出现53次,几乎都属此类。有的引领下文,如张旭《柳》:‘请君细看风流意,未减灵和殿里时。’有的回应上文,如常建《送楚十少府》:‘心事则如此,请君开素书。’”[7]135“以‘安得’、‘安能’、‘焉得’、‘焉能’、‘呜呼’一类表诘问、感叹的语词标记、引发抒情、议论,是又一类唐诗谋篇技法。主要见于古体诗,皆融于句内,也有‘呜呼’独立成句的。”[7]135诸如此类细致入微的谋篇技法的总结归纳,书中还有很多。我们都知道,对于篇章结构修辞,历来是汉语修辞学界所较少涉及的。即使有所涉及,往往多与古代的文章学划不清界限,或是说得笼统模糊。像作者这样能够抓住篇章结构修辞的重要因子予以深入讨论的,实在不多。这种具体而微的讨论与规律性东西的总结,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唐诗谋篇布局的修辞技巧,也可从中看清汉语诗歌篇章结构修辞演进的历史。又如第五章论唐诗的言语时代风格的统一和变迁问题,所提出的许多观点都不乏真知灼见。比方说,在讨论唐代七言古风的言语时代风格时,作者指出:“七古在唐代一开始就走的歌行的路子:乐府民歌与诗体律化的倾向相结合。‘初唐四杰’引进六朝辞赋的表现手法,排比铺张而宛曲流动;刘希夷、张若虚淘洗铅华,笔触流动细腻;高适、李颀、王维、崔颢诸家在此基础上吸取律体优势,形成典型的盛唐歌行(入律古风) ;元、白《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等增添错落章法等流动因素,晚唐韦庄《秦妇吟》等也是这一派的嗣响。与此同时,李白、岑参等人,开创了唐人歌行体的变调,杜甫、韩愈更进一步,构成不入律的古风。不入律的古风与有律化倾向的传统歌行体,在中唐以后始终如二水分流,并行不废。除题材内容上有所分别外,这两种七古的所谓‘正体’和‘变体’主要是在语言运用及其风格上各具倾向和特色。”[7]184这种提纲挈领的总结,如果没有多年对唐诗七古深入细致的研究功夫,那是不可能概括出来的。除了从宏观上予以整体观照外,作者还重视从微观上予以描写。为了使人对“初唐四杰”所创作的七古的言语风格有一个具体鲜明的印象,作者特意提点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一诗为例予以了深度分析,指出《长安古意》突出的言语风格是“绚烂和繁丰(铺陈),跟六朝相比,‘一变而精华济亮;抑扬起伏,悉谐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诗薮》内编卷三)。一是在内容充实基础上讲究词语华美、声韵和谐、节奏整齐。配合内容更迭换韵,一般四句八句一换韵,大量穿插句间和句内对偶,多用复叠形式,借助比喻、用典、夸张、对比等辞格描绘,同时,在转意换景处多用顶真句法和分合句法衔接,节奏鲜明灵动,言辞绮丽悦耳。二是主要采用繁丰的赋法,不惜用繁笔极力铺叙长安都市繁华热闹的场景和骄奢淫逸生活的细节,结合纵横对比,以寓托‘桑田碧海须臾改’的感慨。”[7]185因为有了这番细致入微的分析为基础,所以接下来作者才对初唐七古言语风格进一步概括道:“初唐七古还有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名作,言语风格都与《长安古意》近似。”[7]185另外,作者还对唐诗的入律古风与不入律古风在言语风格上进行了比较,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持论有故,令人信服。比方说,对于不入律古风的言语风格,作者指出:“总的特点是破偶为奇,化整为散,引入散文篇法,风格偏于明快、繁丰。具体还有两类:一是句式参差、转韵的,有绚烂、刚健等倾向。如李白《蜀道难》、《远别离》、《梦游天姥吟留别》、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征西》诸作,在七言基础上错杂采用杂言,结合转韵以传达情感起伏和意境变幻。二是句式整齐,几乎不转韵的,多用拗句拗调,有平淡、通俗或拗峭等倾向。如杜甫、韩愈等人的此类诗作,引入散文语汇、句法、章法,音韵体制力避律化,多用三字尾。”[7]186前文我们说过,对于唐诗的研究与分析,自古以来就不乏其人其文,但是像这样具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系统研究,特别是着重从修辞角度予以观照的,则难得一见。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界也有很多人喜欢谈作品风格包括诗歌风格,但走的都不是着眼语言三要素的路子,因此往往流于空泛或曰空灵,让人没有亲切感与确凿感。读《唐诗修辞论》中谈唐诗风格的部分,我们的感受是具体的、亲切的,觉得作者所说都是言之凿凿的,值得信服。这一点,再一次足证该著立足语言修辞科学求证的独特功力和魅力了。
《唐诗修辞论》作为一部系统的研究唐诗修辞的学术专著,其在学术研究上的创获还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不复一一。不过,相信读者只要认真研讨一过,就会自有公断。
参考文献:
[1]吴礼权.中国修辞哲学史[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2]吴礼权.名词铺排与唐诗创作[C]/ /蜕变与开新——古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东吴大学,2011: 125.
[3]吴礼权.晚唐时代“列锦”辞格的发展演进状况考察[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2(1) : 114.
[4]吴礼权,谢元春.明清词“列锦”结构模式的发展演进考察[C]/ /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三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282 -283.
[5]吴礼权.“列锦”辞格在初唐的发展演进[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3).
[6]吴礼权.由《全唐诗》的考察看中时代“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 117-118.
[7]段曹林.唐诗修辞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王学振)
A Review of Duan Caolin’s On the Rhetoric of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WU Li-qu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作者简介:吴礼权(1964-),男,安徽安庆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导,中国修辞学会会长,日本京都外大、台湾东吴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湖北省政府特聘“楚天学者”,研究方向:修辞学。
收稿日期:2015-01-30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5)-05-013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