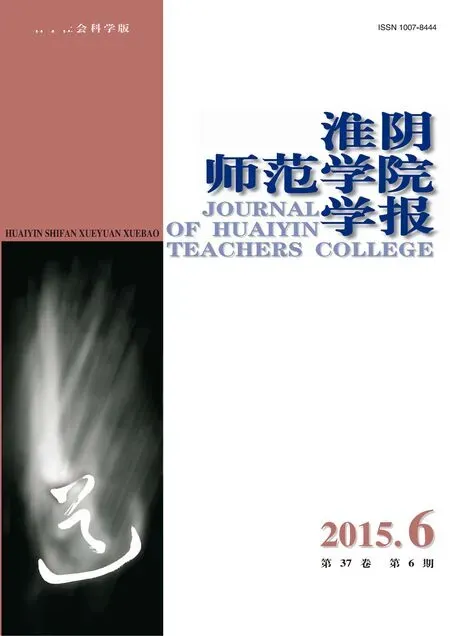何焯《瀛奎律髓》批评钩沉
——以稀见评点本为中心的考察
田金霞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何焯《瀛奎律髓》批评钩沉
——以稀见评点本为中心的考察
田金霞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瀛奎律髓》是唐宋诗学的重要著作,曾引起明清时期诸多评点家的极大重视,清人何焯就是代表性的一家。何焯的评点,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把“疏”的注释方式引入评点领域,促进了评点形式的创新;注重考证、校勘,批评态度颇为严谨;在清初唐宋诗之争愈演愈烈的诗学氛围中,尊崇唐诗,又不废宋诗,诗学观念较为通达;以儒家诗教论诗,重视诗歌“诗言志”的讽谏功能和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与清初儒学复兴的诗学思潮合流。然而这些方面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全面重视,故以稀见评点本为考察重点,在致力于新文献挖掘的基础上,全面探讨何焯的诗学批评思想,必将有助于唐宋诗学及清代诗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何焯;《瀛奎律髓》;评点;诗学思想
明清以来,《瀛奎律髓》在诗学界引起极大关注,品评者多达十余家。何焯的评点,以其“考订之细,书法之工”而“为艺林所仅见”*上海图书馆藏过录有许士模抄录冯舒、冯班、査慎行、何焯评点本《方虚谷瀛奎律髓》,许士模题识。。何焯(1661—1722),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字屺瞻,号义门,晚号茶仙,学者称义门先生。康熙中以拔贡生值南书房,赐举人,复赐进士,官编修。有《义门读书记》《道古斋识小录》等。对于方回《瀛奎律髓》,何氏一生凡两次批阅。其手批原稿几经辗转,今已不可见,其点评之语藉时贤及后人传抄得以流传。李庆甲先生《瀛奎律髓汇评》“以过录有冯舒、冯班、查慎行、何义门评语的清康熙五十二年石门吴之振黄叶村庄刻本《瀛奎律髓》为底本”[2]2,辑录何焯评语系于所评诗歌之后。但李氏《汇评》搜罗版本、辑录评语并不完全。今上海图书馆所藏过录有沈廷瑛抄冯舒、冯班、何焯评点本(以下称“沈抄本”)及过录有许士模抄冯舒、冯班、査慎行、何焯评点本(以下称“许抄本”)《方虚谷瀛奎律髓》,皆为李氏所未见,堪称稀见的评点本。沈抄本与《汇评》所录都是何氏首次批阅之评语,但是,由于《汇评》所据过录本对原评有所删减,故沈抄本评语为《汇评》失载者甚多。许抄本所录为何氏“续阅”之评语*据许抄本正文前二题识可知。一为吴绍澯识:“此书先生(按,何焯)所阅旧刻,二冯评语颇详。向藏余家,后为涧泉秦师携去。此本当是先生续阅者,其墨笔所传大冯评语,朱笔传者小冯也,议论较初本颇加芟削。下阑皆先生自评。此非经世不可离之书,而批阅乃至于再。呜呼!可谓好学也已。”一为许士模识:“义门先生生平手不释卷,丹黄点勘不下数百种,考订之细,书法之工,为艺林所仅见。先生没于京邸,遗书尽归广陵马氏。既而马氏式微。余友吴太史苏泉不惜重资购得大半。……未几,苏泉物故,书渐散失。从弟倚青以白金十镒买数十种,余曾作诗赞之……此本为乾隆庚戌寓扬时借录,距今二十有四年,元本已不知何在。……”另外,许抄何评皆不见于《汇评》及沈抄本,可以推知,《汇评》、沈抄本所录为何氏初评者。,这些评语皆为世人所未曾见。此二本对于何焯及《瀛奎律髓》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和理论价值。本文即在新辑何焯评点《瀛奎律髓》文献的基础上,参合李庆甲《汇评》本,对何焯《瀛奎律髓》批评展开综合讨论。何氏寓学问于评点,晚年两次批阅的《瀛奎律髓》精义纷陈,其要有四:第一,把“疏”的注释方式引入评点领域,促进了评点形式的创新;第二,注重考证、校勘,批评态度颇为严谨;第三,在清初唐宋诗之争愈演愈烈的诗学氛围中,尊崇唐诗,又不废宋诗,诗学观念较为通达;第四,以儒家诗教论诗,重视诗歌“诗言志”的讽谏功能和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与清初儒学复兴的诗学思潮合流。至于《汇评》本未及的评语,笔者另有《〈瀛奎律髓汇评〉失收何焯评点辑补》一稿(待刊),可以参阅。
一、独特的批评方式:“疏”
疏,是古籍注释的一种方式,以疏通文义、阐释义理为主。汉儒最早用以注解经书,旨在疏通经文大义、阐释儒家之道。魏晋南北朝以后,进一步广泛使用于各种典籍的注释中。宋代评点之学兴起,评家喜以简练的语言点评诗歌并逐渐蔚为风尚。但这种评点往往简略直观,颇难揭示作品的深层涵蕴。
何焯在评点中大量使用疏的注解方式,在疏解中表现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其诠解不仅出人意表,更能挖掘出作品的深层意涵。这种点评方式,使诗人、评家和读者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相通,减少了隔膜。何氏于疏解之后一般不作点评,然而,情到之处,亦偶加评论,疏评结合,以发抒其感慨。下面举实例说明:
1.疏解诗句者。如疏杜甫“愁来梁父吟”句云:“老居戎幕,欲与故人共奖王室,若忽忽入冬,仅陪军宴。如山简之日醉习池,不顾洛阳倾覆,负我从来出处之心矣,故曰‘愁来梁父吟’。”深刻揭示出杜甫欲赴国难而又抱负难展的悲壮凄哀之情,比方回所云“山简非得已而醉,诸葛又何为而吟?皆所以痛时世也”[2]470更为具体细致,“负我从来出处之心”的解读,更是深入诗人内心,将其矛盾无奈的心情全盘托出。卷三十九李商隐《安定城楼》诗,其“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二句向来为人所激赏,然而,方回对此不着只字评论,冯班评之“如此诗岂妃红俪绿者所及?今之学温、李者得不自羞”?空疏而又矫激。査慎行云“细味之大有杜意”,却未作细论。唯有何焯在疏通其诗意的基础上指出其“有杜意”处在于“回旋天地”、欲济苍生的高尚情怀:“言所以垂涕于远游者,岂为此腐鼠而不能舍然哉?吾诚‘永忆江湖’,欲归而优游白发,但俟回旋天地功成,却‘入扁舟’耳。”[2]1461
2.疏解全诗者。卷二十八温庭筠《陈琳墓》,何焯疏曰:“见遗文不独诧孔璋之才,正深服魏武之度也。不惟罪状一身,而且辱及先世,乃曹公但知爱才,一不介于胸。今我于斯世,岂有此嫌,乃使我流落如此乎?”[2]1239寥寥数语便概括了诗歌大意,并揭示出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懑情感。又疏解韩愈《广宣上人频见过》云:“自叹碌碌费时,不能立功立事,即有一日之闲,徒与诸僧酬倡,究何益乎?言外讥切此僧忘却本来面目,扰扰红尘,役役声气,未知及早回头,不顾年光之抛掷也。”此诗方回评道:“观题意似恶此僧往来太频。”[2]1738何焯同意此说:“似亦有之。”[1]其疏解更申方回之说,并将诗人“恶此僧往来太频”的原因归之于“自叹碌碌费时,不能立功立事”,即诗中所云“久为朝士无裨补”,抓住了诗歌所表达情感的关键,颇为中肯。
3.疏评结合者。戚戚于心之处,何氏偶尔也会于疏解后加以简短的评论。其疏柳宗元《柳州峒氓》诗并评云:“后四句言历岁逾时,渐安夷俗,窃衣食以全性命。顾终不之召,亦将老为峒氓,岂复计其不可亲乎?哀怨不可读。”诗人之所以变“异服殊音不可闻”为“欲投章甫作文身”[2]187-188,在于其应诏回朝之无望,仕途命运之难卜。一句“哀怨不可读”,令人睹见何氏于灯下搁笔扼腕、叹息数四之情状。
二、严谨的批评态度:重考证、校勘
受王阳明心学影响,晚明学风空疏肤廓,游谈无根。清初学者力矫此弊,注重考证校勘,提倡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何焯生当此季,治学亦重考校,以扎实严谨而著称。这种态度也表现在他的评点学之中。
何氏评点《瀛奎律髓》,于考证和校勘用力颇勤,言必有据,不作空疏之论。
1.考证。何焯于考证,“咸有义据,其大在知人论世,而细不遗草木虫鱼”[3]1289,内容极为广泛。和后来乾嘉学派为考证而考证不同,其考证往往以有助于理解诗歌为目的,服务于诗歌点评。读其诗,须知其人,论其世,正是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何氏对作者、诗歌创作时间、创作背景及诗歌本事作了大量考证。卷三《永宁遣兴》考其作者张耒云:“张耒字文潜,以问东坡讣,为弟子服,遭贬。后得自便,居陈,因号宛丘。”[1]考叶梦得《送严壻侍郎北使》曰:“时高宗因和议成,下劝农之诏。结语亦缘时政而广之也。”[1]使尾联“寄语遗民知帝力,勉抛锋镝事耕桑”[2]1093得以坐实。卷二苏轼《卧病逾月请郡不许复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锁院是日苦寒诏赐官烛法酒书呈同院》诗,何氏考并评曰:“案,此诗乃元祐二年所作。何云世局将变耶?身虽进用而从前所历忧患已多,且母后垂帘亦不得为盛际,安能不思退归之乐也?”[1]明其作于元祐二年,并结合东坡生平经历,认为其退归之思乃是因“从前所历忧患已多”、有感于仕途险恶而生,颇能发见诗歌的深层意涵。
对名物、风俗、制度、事典等所作考证,亦有助于诗歌之解读。如黄庭坚“霜林收鸭脚,春网荐琴高”句,“琴高”,宋任渊注云:“‘琴高’,鲤鱼也。《列仙传》:琴高为宋舍人,后乘赤鲤,见其弟子。”[4]59认为是以人名代鲤鱼。冯舒据此讥切道:“若‘琴高’可作鲤鱼字用,则苏武可替羊,许由可替牛,孟浩然可替驴,又不止右军、曹公之为鹅与梅子矣。山谷再生,我亦面诮。”何焯则详考典籍,纠正了任注与冯评之误:“琴高鱼事详赵与时《宾退录》,二冯似未见此书,以为琴高代鲤鱼用者,反误于任渊注也。宣城有琴高鱼,纤细如柳叶,碧色无骨,土人甚珍之。大冯此谓,未谙风土也。”[2]177考订琴高乃鱼之一种。如此,山谷以“鸭脚”对“琴高”便不难理解了。卷十八曹邺《故人寄茶》诗,何氏考唐代阳羡风俗云:“月团是孟谏议所送,孟简为常州。则阳羡时亦是饼茶。”[1]此语旨在揭示诗中之茶为饼茶,其形似“月”,“开时微月上,碾处乱泉声”,“月余不敢费,留伴付书行”[2]713,切题处正在此。卷二十四岑参《送李太保充渭北节度》何氏考:“汉哀帝改御史大夫为司空,东汉仍之。”[1]正是对“副相汉司空”句的注解。考事典亦不乏其例,如注苏轼《再用韵》(其二)谓:“‘不道盐’出《张融传》。”[1]许浑《金陵怀古》何焯注云:“隋平陈,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第四实事也。”[1]
何焯考证之语,大多言简意赅,不同于乾嘉学者之广征博引、条举例析。这一方面是由评点短小自由的形式所决定,另一方面,也与何氏一丝不苟、“不肯轻著书”的治学态度有关。全祖望《翰林院编修赠学士长洲何公墓碑铭》引何氏门人陆君锡语:“吾师最矜慎,不肯轻著书,苟有所得,再三详定,以为可者,则约言以记之。”[3]1279为我们提供了个中信息。
2.校勘。何氏在评点过程中也重校勘。何焯校勘所用的底本,是明嘉靖间建阳书林刘洪慎独斋重刊龙遵叙紫阳书院本(亦称“闽板”),此外,他还大量使用别集、选集、类书、实录等进行他校。其校本涉及韦縠《才调集》、褚藏言《窦氏联珠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等选集,《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玉篇》等类书,欧阳修《六一诗话》以及《顺宗实录》等。而最具特色、最能体现何氏用力之勤、造诣之深的是其细味诗歌、广阅典籍而进行的推理式校勘,即理校。此类校勘,超越了斤斤于文字的机械做法,达到了诗歌校勘和评点的较高境界。如卷二十三王建《原上新居》(其五)有“石田无力及,贱赁与人耕”句,何氏认为“石田”当作“名田”:“‘石田’,集作‘名田’为是。‘董仲舒请限名田,以赡不足。’注:‘名田,占田也。’方与‘无能及’三字相关,若作‘石田’,亦不得云‘贱赁’也。”[2]966不仅征引典籍,而且因“名田”与“无能及”“贱赁”等词意相照应而取之。这也体现了何氏注重起承转合、前后照应的诗歌结构。其校黄庭坚《和师厚接花》“妙手从心得”句亦颇有得:“此诗固可厌,然读者似未喻。起句本作‘妙手从公得’,山谷自言得句法于谢师厚,与接花同也。‘公’字贯注后四句。讹‘心’字一诗瞎却眼矣。”[1]又以史实校对罗隐《筹笔驿》诗云:“孔明不曾‘东讨’,只可以东盟北伐。”[1]他还借用典籍记载校补宋本佚文,从而证实方回传写之误。卷四十二窦巩《忝职武昌初至夏口书事献府主》诗,末句云:“莫遣鹤猜钱。”何校云:“宋本《联珠集》‘鹤’下缺一字,余谓当作‘请’字。虚谷殆又传写从模糊之本而误也。《墨庄漫录》引曾彦和云:‘唐幕官俸谓之鹤料。’盖云不须请俸耳。”[1]明了“鹤料”指称官俸,则“请”字是,“猜”字无理。
三、通达的诗学观念:尊唐亦不抑宋
唐宋诗之争是宋代以后诗学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清初,唐宋诗之争掀起了新一轮高潮,众多学者投身其中,或主唐,或主宋,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此诗学氛围中,何焯对唐诗尤为倾心,表现出尊唐的倾向。但是,他对宋诗也不完全排斥,诗学观念较为通达。
1.尊崇唐诗。这一观念在其对方回选诗标准的批评中得到了体现。《瀛奎律髓》选诗表现出重宋诗的倾向。“入选诗人三百八十人,其中宋人二百一十七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入选诗歌二千九百九十二首,其中宋诗一千七百六十五首,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九。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品,宋诗的比重都超过了唐诗。”[5]对此,何焯深表不满。评“寄赠类”云:“唐人寄赠诗佳者仅多,虚谷所取全无,手眼尤可恨者,宋人七律选入五十篇,殊无谓也。”[1]于“节序类”漏选崔涂《除夕》、杜牧《齐山》诗,何焯评道:“崔涂《除夕》诗佳甚。何弃之不录,而乃多选宋人诗也?”[2]575“小杜《齐山》亦未可少。”[1]对方回多选宋诗而少选唐诗表示了质疑。
2.不废宋诗。何焯对宋诗的名篇佳制大加激赏,表现出宽厚的胸襟和通达的评诗态度。评陆游《陈阜卿先生……》诗云:“虽见宋派,却能以古人语为己用者,不愧坡公。”[2]1605流露出对陆游和苏轼诗歌的赞许。他认为宋人唐庚《正月晦日儿曹送穷以诗留之》诗“事佳而诗复有名”,于眉批中将此诗整首补入:“世中贫富两浮云,已着居陶比在陈。就使真能去穷鬼,自量无以致钱神。柳车作别非吾意,竹马论交只汝亲。前此半痴今五十,欲将知命付何人?”[1]这也是何氏唯一整首补入的诗歌,从中可以看出何氏对宋诗佳作的赞赏。对宋诗创作的高明之处,何氏亦予以点明,不因其为宋诗而废其巧。其评苏轼《次韵孔常父送张天觉河东提刑》诗云:“‘典裘’只以起‘千钟洗愁’兼趁韵耳,此宋人辞贵处。”[1]
合选唐宋诗而又主“江西”的《瀛奎律髓》本来就是明清唐宋诗论争的大舞台。明末清初的二冯囿于“主西昆而排江西”的门户之见,评点重门派,充满负气诟争之词,大失平正公允之心。与之相比,何焯以平常心论诗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乾隆年间的沈廷瑛即感叹道:“秋田师云义门评诗专在知人论世,能揭作者苦心,诠解出人意表,非仅如两冯公之但论源流法律也。兹阅朱笔所志,信然。敢不秘之,为枕中鸿宝?”(沈抄本题识)
四、明确的诗论理念:重本质功用,轻形式技法
明清之际,在经世致用精神和尊经复古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儒家诗学的政教精神得以复兴。受此时代思潮之熏染,何焯笃好儒学,读书以经史为主,著文以穷究《四书》精蕴为根本。其研读经书,非以饾饤文字、鸟兽虫鱼为务,而旨在经世致用:“论经时大略者,必本其国势民俗,以悉其利病。……才气豪迈,而心细虑周,每读书论古,辄思为用天下之具。”所评点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诸书价值颇高,“超轶数百年评者之林”[3]1277。
影响到《瀛奎律髓》评点,何焯每以儒家诗教精神评论诗歌,重视诗歌美刺比兴的讽谏功能,并主张诗歌应具有“主文谲谏”“温柔敦厚”的含蓄蕴藉之美。
1.重视美刺比兴的讽谏功能。何氏评韦应物《送溧水唐明府》诗云:“落句推其贤,叹其屈,勉其终,无不包蕴风雅之旨。”[2]1048以包含“风雅之旨”、有所寄托作为论诗之准绳。他指出梅尧臣《古塚》诗“结是讽刺”[1],更赞叹罗隐《黄河》“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句为“好讽刺”[2]121。以此论诗,他往往能体味到隐含在文字之下的深层内蕴。如评杜甫《杜位宅守岁》云:“后半并非叹老嗟卑,盖实有不堪于身世者,于时兴叹,不觉流露言外。”[1]挖掘出了隐含于杜诗之中一饭不曾忘君的忧国情怀。评韩偓《春尽》诗:“以春尽比国亡,王室鼎迁,天涯逃死,毕生所望,于此日已矣。元遗山尝借次联而续以‘惟余韩偓伤心句,留与累臣一断魂’,盖以第三比叛臣事敌,第四比弱主之迁国也。”[2]365此评结合韩偓所处的时代背景,揭示出诗人慨叹国家败亡、弱主播迁,痛恨叛臣事敌的无限悲慨,颇有识见。
2.提倡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在审美风格上,何焯主张含蓄蕴藉,反对直露,这也和儒家诗教传统“发乎情,止乎礼义”“哀而不伤”“主文谲谏”“温柔敦厚”等主张相一致。他对合乎此种风味的诗歌赞誉有加,评崔涂《过陶征君旧居》诗“后半欲从执鞭之意,妙在隐约不露”[2]86,认为岑参《初至犍为作》“草生公府静,花落讼庭闲”二句“已极貌荒远,非两省重臣所堪处也,却不露,便纡余有味”[2]235-236。又赞李白《宫中行乐词》(其五)“得主文谲谏之妙”云:“未央,正皇后所居,归之于正,且并讽之视朝于前殿也,却仍以‘游’字结,不脱行乐,得主文谲谏之妙。”[2]207对岑参《送杨中丞和蕃》诗结二句刺而不露的追求亦颇加赞许,认为其“妙有余味”[1]。相反,对于一些表达过于直露的诗歌,则深致不满。如梅尧臣《较艺和王禹玉内翰》诗,何焯评其“力槌顽石方逢玉,尽拨寒沙始见金”[2]74二句云:“是黜刘几而取苏、曾之用心。嫌其太露,遂为怨毒所归。”[1]
正是从儒家诗教传统出发,何焯反对在诗歌技巧上花费太多功夫。对于方回着眼于李商隐《井络》诗对仗工巧的评论,何氏批评道:“义山诗如此工致,却非补纫,其佳处在议论感慨。专以对仗求之,只是‘昆体’诸公面目耳。”[2]104因此,对用韵、对偶、用字、用事等有关诗格方面的问题,何焯虽有谈及,却用力不多。
何焯一生著述颇丰,仅评点前贤著作即多达数百种*许抄本正文前许士模题识云:“(何焯)生平手不释卷,丹黄点勘不下数百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其诗文及评本大多散佚,诗歌创作成就和学术观念难以得到全面展现,遂使后人产生“诗非先生所致意,亦不足名家”的偏见,其学术也“每为通人所诮”[6]265。就何氏评点而言,虽有其后人及后学相继辑得评点五十八卷镂板刊刻,即今所见之《义门读书记》,但是,此书之缺失亦甚为明显。仅以杜甫和李商隐诗歌评点为例,这些评语非一时、一地,亦非为一书而发,所辑既难以求全,又不注明辑录出处,难免会造成何氏曾有意识地选评杜、李之诗的误解*朱秋娟《何焯诗歌评点之学刍议——以何评义山诗为例》以此立论:“何评义山诗是一部选评本,其对义山诗的选择即表明了一种诗学倾向,……义山诗有600余之多,何焯只选评了250余首,其所选之作绝大部分是咏史、感怀之作,少量艳情诗得以入选是为了辨明其并无寄讬。”(见《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21页。),从而影响对其诗学观念的正确认识。借助稀见许抄本、沈抄本,我们得见何评《瀛奎律髓》之大致样貌,这也是现今可见何焯少数的诗歌专书评点之一。对其加以钩沉,其意义不仅在于促进何氏评点《瀛奎律髓》研究的深入,还在于 它将有助于全面深入研究何焯的诗学思想,正确理解和评价其诗歌评点成就及其在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 田金霞.《瀛奎律髓汇评》失收何焯评点辑补[J].待刊稿.
[2]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 何焯.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任渊,等,注,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 莫砺锋.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宋诗观[J].文艺理论研究,1995(3):71.
[6] 何焯.义门先生集[M].续修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20.
责任编辑:刘海宁
I207.22
A
1007-8444(2015)06-0776-05
2015-05-15
田金霞(1980-),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