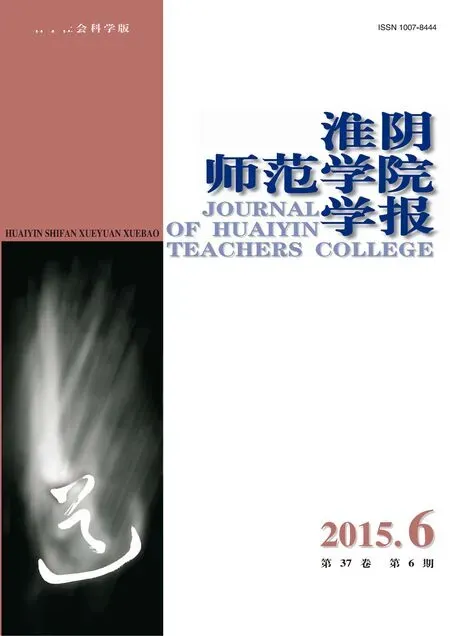仪式原型与革命叙事:《青春之歌》中的成年礼
苏永前, 陈晓璐
(1.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2.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文艺学】
仪式原型与革命叙事:《青春之歌》中的成年礼
苏永前1, 陈晓璐2
(1.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2.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在《青春之歌》的革命叙事背后,潜隐着成年礼这一古老的仪式原型。林道静面对接踵而来的人生挫折,最初茫然不知所措,后来在江华等的引导下经历了“死亡”与“再生”的考验,最终获得了身份的终极转换,由一位“知识青年”成长为一位“共产党员”。这种生命历程,正是古老的成年仪式在当代的置换变形。对《青春之歌》成年礼原型的揭示,有助于从文化层面深化对这部小说的认识。
杨沫;《青春之歌》;成年礼;仪式原型
作为诞生于“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青春之歌》自问世之日起即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许多研究者或立足于话语分析,或着眼于形象诠释,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极富启发性的探讨。与上述思路不同的是,本文拟从文学人类学角度出发,就这部小说与成年礼之间的隐性关联作一考察。小说主人公林道静面对接踵而来的人生挫折,最初茫然不知所措,后来在江华、卢嘉川、林红等的引导下经历了“死亡”与“再生”的考验,最终获得了身份的终极转换,由一位“知识青年”成长为一位“共产党员”。这种生命历程,正是古老的成年仪式在当代的置换变形。原型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曾指出:“一如我们所见,原始的程式在最伟大的经典作品中一再重现;事实上,就伟大的经典作品而言,它们似乎本来就存在一种回归到原始程式的普遍倾向。”[1]23-24《青春之歌》是否称得上“伟大的经典”自然值得商榷,但“回归原始程式”这一趋向在小说中却有迹可循。
一
人类学资料表明,许多部落社会中均存在“成年礼”这一仪式行为。成年礼的受礼者一般是即将步入社会的青春期成员,此时这些成员的生理已发育成熟,但心理尚处在前成熟状态,相应的社会地位也未获得。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一书中强调:“生理成熟期与社会成熟期是有本质差异的两个问题,它们只是极偶尔重合。”[2]51正因为此,许多族群需要通过特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成年礼仪,来彰显青春期成员社会地位的转换。比如,汤姆森印第安人为男孩所举行的成年礼,依据其所被指定的行业分工(狩猎、斗士等)而定,每个男孩在到达青春期时举行此仪式,有时是在12岁至16岁之间,标志性时刻是他第一次梦见箭头、独木舟或女人。[2]53-54与此类似,西南非洲几内亚湾埃利玛人在男孩5岁时便为他举行第一次仪式,第二次在10岁,第三次更晚,通过这些仪式,男孩成为战士并可结婚。[2]54针对成年礼中通常进行的“割礼”仪式,范热内普指出:“施行割礼的年龄变化本身说明这是具有社会意义而非生理意义之行为。在许多民族中,举行割礼仪式的时间不等,如每两年、三年、四年或五年,以便性发育程度不同的孩子可同时参加。”[2]55这些民族的成年礼在其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经历了这一仪式过程,个体的心理才会真正成熟,社会才会赋予个体以成年人的合法地位。
从人类学视角来看,《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正是一位即将步入社会的受礼者。林道静出生于地主家庭,但生母却是被父亲用暴力手段霸占的贫民子女,因而其身上同时流淌着贫农的血液。血统的复杂性,无形中造成了林道静的身份焦虑。林道静此后的人生道路,正是背离父系血统而走向母系血统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身份焦虑恰恰是许多部落社会成年礼受礼者的典型特征,此时他们处于成年与未成年之间的过渡阶段,而成年礼仪式的功能,就是使他们顺利跨入成人的行列,同时赋予他们相应的社会权利及义务。
林道静自小失去母爱,在生父与继母的虐待下艰难成长。长大后,继母发现林道静长得漂亮,因而把她送入学校读书,以此作为面向将来的一种“投资”。后来父亲破产,继母逼迫她嫁给三十多岁的胡局长,林道静的生活彻底陷入困境。作为一位接受了多年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一方面以自身微弱的力量进行反抗,另一方面努力考取师范大学,希望能够摆脱封建家庭的控制,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不过,即便此时,生活中的磨难也并未使她失去童心:
她除了喜欢文学也很喜欢音乐。此刻放了假,她雇了洋车从学校向城里拉去时,车上还带了一堆乐器——笙、笛、箫、月琴、二胡,她那最宝贵的蝴蝶牌口琴就放在口袋里。无论走到哪儿,她总是随身带着这一堆东西。因此同学们给她取了两个外号:好听的叫做“洞箫仙子”;不好听的叫做“乐器铺”。下课之后,她常常一个人吹着、弹着,这时候看见她的人,都有些惊讶她那双忧郁的眼睛忽然流露出喜悦的光芒,也只有这时候,她那过于沉重的神情才显出了孩子般的稚气。[3]13
这便是小说中旁观者眼中的林道静,一个看似成熟、却依然固守孩童天性的“青春期成员”。不仅如此,当她面对继母的阴谋时,依然抱着几分侥幸心理:“道静想:‘妈妈也许不逼我嫁人了,也许还能供给我念书?’于是,她向客人们微微鞠了一躬——过去她是非常讨厌家里的赌客、烟客的,今天却仿佛看他们顺眼一些,竟站在牌桌旁,对他们羞涩地笑了笑。”[3]14显然,面对黑暗的社会和复杂的人心,林道静的想法过于幼稚。由于继母仍然逼迫她嫁给胡局长,万般无奈之下,她唯有选择离家投奔远方的表兄。由前文分析不难发现,此时的林道静内心并未成熟,她依然是一个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孩子。
林道静在爱情上选择余永泽,也是心理尚未成熟的一种体现。余永泽出现在林道静人生最低落的时期,“他留着短分头,穿着黄色卡叽布学生制服,眼睛虽然不大,却亮亮的显着灵活和聪慧。这样的人在农村里是少见的。道静不由得对他注意起来”。[3]28-29正是这种学生般的外表和共同的爱好,吸引了林道静对他的关注。此后,当林道静因走投无路跳海自尽时,余永泽挺身相助。这种“英雄救美”的行为,使得余永泽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林道静的芳心。不过,林道静显然对余永泽缺乏深入了解,并未考虑余永泽能否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只是凭感觉将对方幻化为“多情的骑士”与“有才学的青年”,这才导致了日后的焦虑、矛盾与彷徨。林道静遇见余永泽时的内心波动及嗣后作出的选择,均体现出其心理的“前成熟”状态。
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看,成年礼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存在于每个时代,虽然人们对此无法自觉感知,它却可以置换为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而加以呈现。由前文分析可见,在《青春之歌》中,涉世之初的林道静依然是一个心理稚嫩的“未成年者”,她即将面对人生中的种种磨砺并真正长大成人,这些都使她完全符合成年礼中受礼者的特征。我国学者施春华在《心灵本体的探索:神秘的原型》一书中,曾对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思想进行了总结,其中的一点,就是“它是个体始终意识不到的心理内容”[4]60。杨沫虽然并未有意识地将林道静塑造成一位“成年礼”中的受礼者形象,不过,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成年礼中的“受礼者”原型仍然借助林道静的形象得以显现。
二
在人类文明早期,成年礼通常在一种相对隔绝的环境中举行,从而形成分隔与聚合礼仪。澳大利亚若干部落的仪式,是先将新成员从之前的环境(即女人与儿童世界)分离出来;新成员被隔离在丛林中某个特别的地点或茅屋内,同时还伴有各种生活方面的禁忌。[2]58这种相对隔绝的环境是为了使受礼者与之前的生活环境分离,在接受了严格的成年仪式之后,开始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生活,因而被赋予全新的社会意义。
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年仪式正是在这种相对隔绝的环境中进行的。由于受到继母的逼婚,林道静不得不离开家庭投奔远在北戴河的表兄,从此开始一段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历程,体现了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中所要面对的陌生和恐惧。而在此过程中她所遭遇到的人和事,同样体现了成年仪式所需的特有环境。首先在生活上,林道静投奔表兄张文清未果,生活上的无所依归使她形成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和漂泊感;其次在情感方面,林道静过分依赖余永泽,听从余永泽的劝告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做一个家庭主妇。虽然在意识上林道静也有抵触,却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其原因正是缺乏外在力量的援助,于是只能在矛盾与挣扎中孤独前行。最后,在事业上,林道静仰慕、依赖卢嘉川,但在卢嘉川失去消息后,仿佛失去了人生的指引:“整天整天她就那么呆呆地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翠绿色的孤单的小枣树。她觉得世界忽然变了色,她觉得她刚刚敲开的幸福的大门,在她刚要迈进的时候,却突然紧紧地关闭了。”[3]179于是林道静只有在彷徨无措中独自摸索前行的道路。
成年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作为现代文明“他者”的各个前现代社会中十分普遍,但在现代人眼中不但陌生,而且有些悖于常理。因而只有正确理解成年礼,才能以之作为一种原型模式来解读《青春之歌》。从原型的角度来看,成年礼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早已成为人类一种无意识的共同经验,是历代祖先在漫长的岁月中传承下来的。虽然古老氏族所选择的成年礼环境以及分隔与聚合礼仪所需要的条件在今人看来难以理解,但它已成为一种潜在的模式,在经历了久远的积淀之后融汇于我们的无意识深层。在原型批评家弗莱看来,文学发展遵循着原型“置换变形”的规律,“随着抽象理性的崛起,人的愿望幻想渐渐受到压制,神话趋于消亡,但变形为世俗文学渐渐发展”[1]132。将成年礼作为一种原型来解读林道静的成长之路,正是因为原型的“置换变形”已经演化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原动力。透过它,既能看到远古成年仪式的象征性意义,又能够理解杨沫赋予林道静成长历程的文化含义。
从来自世界许多地方的民族志来看,成年礼通常由部落中的长老或有威望的人主持。他们之所以被赋予这种资格,是因为在精神领域享有特殊地位。他们能够以一种精神与象征的力量引领受礼者接受社会考验,以达到身份的终极转换。虽然成年礼常常通过一些具体的仪规来昭示社会新成员的加入,但作为一种仪式,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精神内涵。这一点可以从对成年礼主持者的选择上看出。例如,肯尼亚的马赛人只有在父亲进行了叫做“逾越栅栏”的仪式后,男孩和女孩才可举行割礼。父亲所行的礼表明他接受他已是“老人”的地位[2]65。与此相似的还有伊鲁西斯的成人礼仪,新成员被带到一起,圣师(主要的巫师)被用禁令(禁忌)与那些手不洁净和说话不清楚的人隔开[2]69。这些案例表明仪式主持者对于成年礼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受礼者的深刻影响。
在林道静的人生旅程中,亦出现成年礼的主持者(精神导师)的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是卢嘉川。自离家出走之后,林道静的思想始终处于一种矛盾、彷徨状态,她只是模糊地明白自己应当过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却迟迟未付诸行动,这显然是一种“前成年”状态的体现。正在此时,卢嘉川走进了林道静的生活。作为一位理想化的共产党员形像,他曾组织、领导过许多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思想成熟而稳重大方。对林道静而言,卢嘉川无疑是一位精神导师,“只不过短短十多分钟的谈话,可是他好像使道静顿开茅塞似的,忽然知道了好多事情”[3]49。正是在卢嘉川的引导下,林道静实现了身份的终极转换,从一位富有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
卢嘉川给她的仅仅是四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写成的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道静一个人藏在屋子里专心致志地读了五天。可是想不到这五天对于她的一生却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这里,她看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从这里,她看见了真理的光芒和她个人所应走的道路;从这里,她明白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原因,明白了她妈因为什么而死去。……于是,她常常感受的那种绝望的看不见光明的悲观情绪突然消逝了;于是,在她心里开始升腾起一种渴望前进的、澎湃的革命热情。[3]106
杨沫在小说中正是通过林道静思想的转变,突显了卢嘉川之于她的精神意义。如果说,此前的林道静尚处于思想、身份的“前阈限”状态,经历此一事件之后,林道静终于跨越了生命的“阈限”阶段,彻底实现了“旧我”向“新我”的飞跃,从而进入了新的生命状态,与此相应,也获得了全新的社会身份。
三
在成年仪式中,受礼者不仅需要接受氏族首领和长老的训导,而且要经受严酷的身心考验,以完成一次象征性的“死亡”与“再生”过程。在澳大利亚的巫术活动中,乌拉尔—阿尔泰的萨满必须避居于森林、荒野或寒漠,经受贫困所带来的心理和神经后果[2]81;在加勒比的皮埃人中,受礼者被年长的皮埃成员隔离在茅屋里,遭受鞭打,直至昏倒;新员还被洒上黑蚁血,被迫喝烟叶汁而“发疯”[2]82。此种施加于身心的磨砺在许多原住民社会均有所发现。对于这种习俗,现代思维自然难以理解。不过在部落社会,它作为成员进入社会的一种必经形式和过程,则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形式有所差异而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成年礼中的这种“考验礼”,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已转化为一种原型,在不同作者的笔下反复再现。从成年仪式中“考验礼”的角度来观照《青春之歌》,林道静成长中所经历的磨难可以视为其社会层面成熟的必要条件。
在《尼伯龙根之歌》《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等众多中外英雄史诗中,主人公自幼失怙,成长的道路充满种种磨难。与这些史诗中的英雄主角一样,林道静的成长之路同样充满坎坷与艰辛。一岁的时候,生母被林伯唐逐出家门,不久投河自杀。从此,林道静在继母严父的淫威下生活。此种经历,不仅成为林道静人生中的第一课,而且预示了她此后将面对的一系列人生磨难。不过对林道静来说,更严酷的考验尚在其后。具体而言,便是从幼年步入成年的人生转折阶段。
中学即将毕业,继母便因一己私欲,强迫林道静嫁给阔佬胡局长。如同我们在许多现代家庭小说中所看到的,此时“离家出走”成为林道静唯一的选择。所不同的是,对林道静来说,“离家”仅仅是嗣后一系列人生考验的开始。更准确地说,从离家那一刻起,林道静真正开始了其成年礼中的诸种“考验仪式”。首先是赴北戴河投奔表兄张文清非但未果,反而险些落入小学校长设置的圈套。小说中的环境描写尤具象征意味:“雨下得越发大了,闪电在黑暗的空中刚刚划过,沉重的雷声便跟着发出惊人的巨响。”[3]33仅仅是逃离家门后的第一站,林道静已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此种环境与遭际,恰与受礼者的考验仪式相契合。
绝望之下,林道静选择了投海自尽,危急时刻却被在北平读大学的余永泽相救。至此,林道静的人生似乎出现了转机,可事实上,这不过是她即将面对的第二重考验的开始。因为余永泽的出现而带来的感情上的波折,同样给林道静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使她不得不在爱情和事业中作出抉择,而这才是她自我意识觉醒且付诸行动的关键选择。从最初对余永泽的感激到最终试图摆脱余永泽为她设定的人生轨迹,从起初的一味逃避到后来压抑自己盲目跟随他人的想法,林道静在这一系列的磨难中逐渐成长。最明显的就是她选择追随卢嘉川的革命事业,驳斥余永泽的考据学,即使是在感情上遭遇了挫折,她依然能够痛定思痛,坚定自己的信仰。在意识到自己的妥协与不反抗只会加深磨难而无其他益处时,磨难的真正意义就在此体现了出来。
无论是在家庭中所受到的虐待、轻视,还是在社会上所遭遇的阴谋、险恶,抑或是情感与事业的冲突、矛盾,这些都属于林道静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磨难与挫折,这也正是成年礼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正如申荷永在《荣格与分析心理学》中所说:“集体无意识中包含着人类进化过程中整个精神性的遗传,注入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5]44林道静自身并未意识到她所遭遇的磨难其实是通往成人的必经之路,如果单从磨难的层面来看,也许它只是让身体有所损伤,但实际上这些磨难的真正意义在于磨砺了人的内心,使受礼者的心灵由天真、幼稚逐步走向成熟。因此,我们必须从心灵成长的角度来看待林道静所遭遇的这些“苦难仪式”。
所谓象征性的“死亡”和“再生”,与伊鲁西斯和澳大利亚的阿切凌喀仪式中向祖先敬献的行为完全对应。第一部分几乎是普遍存在的:从世俗世界死去的新员通过冥府(或冥王海德斯)获得再生,然后进入到神圣世界。[2]70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中还提到:“这同样的进程中包括对新员死亡和再生的戏剧化,在对狄俄尼索斯、(波斯太阳神)米特拉斯(通过阶段行动加入礼仪)、阿蒂斯、阿多尼斯、爱希斯等的崇拜,以及加入俄耳甫斯教和塞拉斯宗教组织的仪式中也同样存在。”[2]70此外,“从阿蒂斯的死到再生,人们相信其加入礼仪也会使其未来信仰者从死亡得到再生:1)通过斋戒,他将世俗不洁之物从身体排除;2)使用圣物(如鼓和锣)饮食;3)他蹲在土坑里,以便牺牲之牛血倒在他全身上;然后从坑里出来,从头到脚都是血;4)几天之内他只得到牛奶喝,犹如新生儿”[2]71。从以上所举诸例不难看出,受礼者所经受的象征性“死亡”和“再生”,正是分隔礼仪和聚合礼仪的深入表现。只有在经历了这些象征性的仪式后,受礼者才算真正的浴火重生。
与上述死亡与再生仪式一样,杨沫在《青春之歌》中也为林道静设置了这种象征性的仪式,让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心灵的蜕变:
一间阴森森的大屋子里,地下、墙上全摆列着各式各样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奇怪的东西——刑具。几个穿黑衣服的彪形大汉凶恶地盯着她,好像怕这个犯人逃遁似的。道静被卫兵推搡着,来到这间屋子里。她站在地上,觉得浑身疲乏,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她挺着,挺着,挺着。杠子,一壶、两壶的辣椒水……她的嘴唇都咬得出血了,昏过去又醒过来了,但她仍然不声不响。最后一条红红的火箸真的向她的大腿吱的一下烫来时,她才大叫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3]348-349
林道静被捕入狱之后,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残酷刑罚。这些刑罚对于她来说有如一次“死亡”,不仅身体濒临崩溃的边缘,心灵也深受煎熬。经此一役,她才真正从过去懵懂、幼稚的状态中走了出来,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对革命的坚定信念。这就是林道静在成人礼中象征性的“死亡”。而所谓的“重生”,要数林红在狱中给予她的光明和希望,让她相信自己也能成为像卢嘉川、江华、林红这样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并且为更多正在经受苦难的人带去希望,以此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道静贪婪地听着郑瑾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周身的血液突然在血管里奔流起来、沸腾起来了。她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还会碰到这样坚强的老布尔什维克——像卢嘉川、像江华、像她梦想中的伟大英雄人物。看,她受刑多重,而且有病,可是她却这样愉快、这样充满了生活的信心,这样用尽她所有生命的力量在启发她们、教育她们。”[3]355重生需要的不仅是生理上的条件,更重要的是相信自身的价值所在,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心理意义上的“重生”。至此,林道静已经从象征性的“死亡”中“重生”了,由一位稚嫩的知识女性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经历了此番生死考验,林道静的成年仪式也真正宣告完成。
综上所述,成年礼作为一种古老的仪式传统,一些具体行为和象征意义也许不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但作为人类的一种原初经验,其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以各种方式“置换变形”于文学作品之中。就原型批评的层面而言,成年礼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原型程式,为人们探究文学作品增添了一条新的途径。因而,从成年礼角度解读《青春之歌》不仅可行,而且有助于我们从文化层面更新对这部小说的认识。
[1] 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2] 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M].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 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 施春华.心灵本体的探索:神秘的原型[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5] 申荷永.荣格与分析心理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刘海宁
I207.425
A
1007-8444(2015)06-0763-05
2015-05-2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10&ZD100);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人类学实践研究”(14JK1589)。
苏永前(1978-),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
——以林道静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