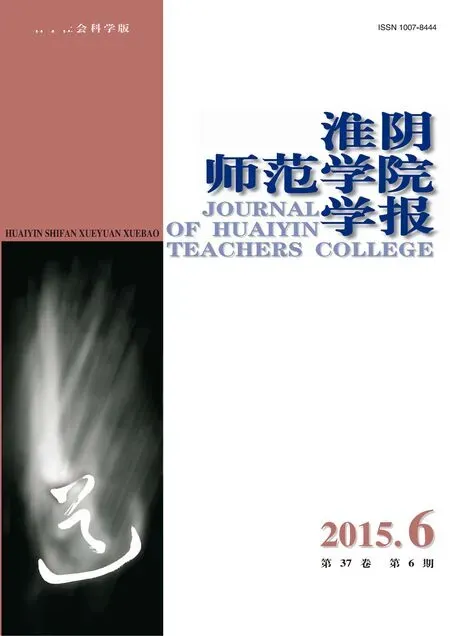电影对小说叙述时长的表现方式
贾 佳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电影对小说叙述时长的表现方式
贾 佳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电影作为时空艺术的代表,时素的调控是其得以形成叙述的关键。对小说文本时素的讨论已经有了颇多成果,而对电影叙述中时间因素的讨论,尤其是电影对小说文本改编过程中时长的表现还没有相关研究,本论文着眼于电影对小说叙述改编中“时长”问题的分析,主要从时长角度,涉及电影文本对小说文本省略、缩写、场景和延长与停顿的改编,以及电影艺术音乐和色彩的运用在时素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时分析时间变形的速度,时长变化对电影情节节奏、人物心理表现,以及观者接受等所产生的影响。
电影;叙述;时间
从人类诞生那时起,叙述就作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存在,正如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所论述:“以这些几乎无限的形式出现的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有了人类历史本身,就有了叙事。”[1]2而电影作为现代大众消遣的主要方式之一,同小说一样是虚构和真实的产物,但在虚构中建构真实有其特有的时间规律,时间艺术的形变是决定一个文本好坏的关键。
主要小说作为叙事话语的形式,它的基本结构呈现出一种线性历时状态。“叙事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质”[1]6,从语言学角度,“句子”存在于语言双轴操作逻辑的线性选择。线性的顺序性特点决定了“时间”在小说叙述中基本要素的地位。相比其他艺术形式,小说在时间运用上有更多选择,对“时素”的分析是研究小说叙述的关键所在。而电影艺术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双重特性,也因此它被称为“时空艺术”。马塞尔在《电影语言》中认为“电影首先是一种时间的艺术”。电影理论的先驱,意大利电影家奇奥托·卡努杜将电影看作是“动与静、时间与空间、造型与节奏”相互融合的艺术形式。因为“时空艺术”的特质,节奏在电影文本叙述过程中起到了行动素的推动作用,与小说文本同样的情节,在不同的节奏推动下在电影文本中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和感官感受。
托多罗夫将叙事分为三个范畴,其中时间范畴的作用就在于“表现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的关系”,“故事时间”就是所谓的“被叙述时间”(narrated time),“指被叙述出来的文本内以各种符号标明的时间,并不是指事件在‘在现实中’发生的时间”[2]147。“话语时间”指“叙述行为时间”(narration time),“叙述文本占用的时间”[2]150。在《叙事话语》中,热奈特将叙述时间问题分为“顺序”“时距”和“频率”三个部分[3],“顺序”指叙述的述本对底本故事时序上所作出的调整;“频率”指“叙事与故事间的频率关系”,即“重复”程度;“时距”所指的是叙述行为时间对被叙述时间所造成的时间长度变形,恰特曼将其具体表现分为:省略(ellipsis)、缩写(summary)、场景(scene)、延长(stretch)、停顿(pause)等。“时间变形是叙述文本得以形成的必然条件。”[4]本论文着眼于电影对小说叙述改编中“时长”问题的分析,主要是从时距(时长)角度,讨论时间变形的速度,时长变化对电影情节节奏、人物心理表现,以及观者接受等所产生的影响。
一、省略
叙述文本中的“省略”是指述本时间在文本叙述中为零,或因叙述时间受限对述本进行有目的地删减。可以说,“电影是省略法的艺术”[5]53。艺术活动的存在必然以选择作为手段,“没有省略,就不可能有叙述,因为选择性是叙述加工中最基本的一环”[6]。“电影工作者就像戏剧家一样,是能够对有意义的元素进行选择,然后去安排成一部作品的。”[5]53热奈特将小说文本中的省略分为明省略和暗省略,电影文本对小说文本省略的展现同样可以分为明省略和暗省略。
明省略是指叙述文本中明确的时间空白,比如“几年之后”,叙述直接省去了“几年”的底本时间,为主要情节的发展提供时间背景。电影文本中对此种省略的展现更多是用文字进行暂时的叙述时间填充,或许镜头仅仅显示“几年之后”几个字作为切换镜头,电影《山楂树之恋》(2010)对明省略的运用尤为突出。因为作者在小说文本中涉及了很多时间元素,也由于故事时间跨度的问题,导演多次采用了明省略,采用电影文本和小说文字文本相结合的方式解决时间跨度问题。比如小说结尾处:
十年后,静秋考上L大英文系的硕士研究生。
二十年后,静秋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三十年后,静秋已经任教于美国的一所大学。今年,她会带着女儿飞回那棵山楂树下,看望老三。
她会对女儿说:“这里长眠着我爱的人。”
电影文本采用了字幕形式,将省略的时间在短时间进行呈现,造成世事变迁,恍如隔世的历史感。
暗省略指“文本中没有声明其存在、读者只能通过某个年代空白或叙述中断推论出来的省略”[3]69。小说文本及电影中的暗省略可以仅仅通过一个场景来省略并暗示文本需要表达的意义。《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陌生女人含泪再次离开了作家的寓所,撞见了老管家,茨威格并没有明说老管家认出了陌生女人,而是转而描写“他的眼睛突然一亮”[7],电影(2005)中镜头定格在噙着泪的管家身上,也没有明说“他认出了她”。电影用特定场景来暗示无法言说的可能,调动了接收者的逻辑思维,人类的思维需要时间进行线性拼贴,进而组成逻辑线条供读者理解文本,这种迂回的传达和接收方式让文本的意义呈现更加富有张力。
小说中的暗省略在电影中也可通过快速运动的画面进行表现,从而体现时间如梭的历史感。《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陌生女人因为家庭变故离开了作家两年,在电影文本中叙述者通过展现从火车看车窗外运动的景物来诉说自己在山东六年的生活,六年的时间就在火车车窗场景的运动中一晃而过。
《拉奥孔》对时空艺术关系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这个概念也同样适用于电影文本中的“省略”,“这一顷刻既包含过去,也暗示未来,所以让想象有自由发挥的余地”[8]。省略的运用增加了接收者参与文本建构的可能,可以说省略在电影文本中起到了指示符号的作用,“让接收者能想到其对象,指示符号的作用,就是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到对象上”[9]。尽管电影是事先已录制好的,但其艺术效果又可以让接收者有“在现场”的感觉,正如拉费所承认的,“电影中的一切始终处于现在时”[10]134。省略带来了欲言又止的效果,而安德烈·埃尔博也说:“一个‘好的读者’应该能够从当前呈现的视觉性内容中提炼出信息内部的无形数据。”[11]电影叙述同观影者的互动推动了电影情节的进一步发展,而非等时效果所带来的平铺直叙,让文本的呈现更加富有张力和戏剧性。此外,省略能够艺术化地对小说文本的内容进行含蓄表达,避开某些色情或是血腥的镜头,从而增加电影文本的艺术美感。
二、缩写
缩写与省略对时间的完全忽略相区别,是指文本述本时间明显小于底本时间的情况。这种时间形态在叙述文本中用来呈现具有前后衔接性但又无太多用处的时间,这也是麦茨所说的“插曲段落”和“普通段落”之间的地带。虽然缩写看似无足轻重,但完全省去缩写之后,叙述文本会出现断层,接收者对文本的理解也会受限。
表现在电影文本中,快镜头是其缩写的主要手段,它可以捕捉到缓慢的运动所带来的节奏感,比如花朵从生长到开花的过程,人们就可以在快镜头的帮助下对其进行感知。同时,画外音在电影文本中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缩写”的作用,将各个主要场景进行拼接,使叙述文本前后连贯。
同省略相同,在电影文本中运用缩写有时也是为了避免某些暴力或是情色场景的叙述,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对其进行简单叙述加工,既不省略情节,同时又交代了故事的发展方向。张爱玲的小说《色戒》中,王佳芝为了完成任务不得已需要和梁润生行男女之事,因为涉及敏感的话题,叙述者只用短短一句隐晦的话就将其交代给读者:“今天晚上,浴在舞台照明的余晖里,连梁润生都不十分讨厌了。大家仿佛看出来,一个个都溜了,就剩下梁润生。于是戏继续演下去。”此部分情节在电影(2007)中也同样采用了缩写的手法,点到为止。
三、场景
场景是指述本时间等于底本时间的叙述情况。相比电影文本,小说文本的时间概念的划分并不清晰,只能通过叙述文本篇幅所占空间的多少来判断叙述时间的长短。电影艺术由于其文本的时空特性,其叙述对时间的呈现比较明晰,所以电影述本中的场景可以完全等同于底本中的场景再现。所以在小说文本中符合“场景”叙述主要是对话场面,“是客体中心词,是角色的直接话语”[12]223。电影文本一方面可以完全忠实于底本时间,对情节进行客观再现,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小说文本对话场景的改编加入人物的心理色彩进行主观呈现。
“叙事的时间等于故事的时间,属于这种情况的镜头始终遵守所展现行动的计时的完整性,既不加快也不放慢。”[10]160这也是电影文本最擅长的叙述手法,最经典的电影文本就是改编自理查德·林克莱特的同名小说《爱在黎明破晓前》(Before Sunrise),小说文本发生在午后的餐车上,杰西邂逅赛琳并开始两个人的对话,电影文本(1995)忠实于小说,采用大篇幅对话,对底本进行了完全的叙述还原。正因为生活化的完全展现,大篇幅场景的运用会削减文本所带来的跌宕起伏的效果,事实上,任何小说都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将生活完全搬入文本,有选择地对事件进行叙述是决定一部作品好坏的关键。电影作为新的叙述形式,同样不可能将生活完全搬上荧幕(不否定现代少数纪录片似的“先锋电影”,这里所讨论的是非完全等时的、通常意义上的电影),所以叙述文本中所呈现的场景是选择的产物,或是人物之间相遇的关键时刻,或是推动叙述发展或是转折的场景,抑或体现人物某些品质和性格的运用等。
电影文本对小说场景的表现可以通过叙述转换使场景加入人物的色彩。电影艺术的本质是否在于表现情节曾经一度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随着各种“先锋电影”的诞生,“情节”的作用受到了颠覆。事实上,电影文本中所呈现出的场景画面并非简单地对小说文本的完全再现,而是暗含了角心人物的视角范围以及角心人物的心理等元素。比如小说文本《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始描述了“我”到布坎南夫妇家做客一起用餐的场景,小说述本忠实于底本,用大量直接引语呈现了用餐人之间的对话,而与之相比,在电影文本中黛西、卡罗维、乔丹三个人交谈甚欢,此时电影镜头采用了快闪,语句也是只呈现部分,并不完整,画面始终在三个人物以及餐桌上进行拼贴,直到布坎农开始长篇大论:“文明就要崩溃了,你有没有读过《有色帝国的兴起》……”[13]16这个时候镜头才恢复常速。之前快速镜头在对话人物之间的切换,以及对话的不完整性的呈现反映了布坎农对其他三人的对话并无兴趣,此时电影文本的叙述是站在布坎农的心理视角进行的场景再现,而非从小说文本中叙述者“我”的视角对宴会场景进行表达。小说人物的色彩在电影文本中通过对场景时间呈现的调整得到新展现。
四、延长与停顿
延长是述本时间长于底本时间的文本状态,而停顿(pause)是延长的一种极端状态,指叙述文本着重表现底本的一个时间点所发生的故事,底本时间为零,所以述本时间远远大于低本时间。热奈特认为小说的叙述时间只能是人们“根据行数或页数,以近似的方式计算行动的速度”[10]158。可以说叙述时间只是人们对生活感知的一种相对经验值,而非绝对值。
因为延长或停顿是时间的非合理性存在,在底本中是完全不符合时间规律的,而在述本中叙述者叙述选择的不同会涉及不同的角心人物进行跳角,所谓的“跳角”赵毅衡的解释是:“‘人物视角叙述’(POV narrative)中出现的不规则变异,是对人物视角整齐性的违反。在人物视角叙述作品中,叙述者原本坚守集焦(focalization),即坚持同一人物视角,以达到叙述经验自限的效果。”[14]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出延长和停顿效果的产生是叙述转换,角心人物参与叙述活动的选择,而这往往涉及人物的心理活动,反映在电影文本中就是通过特效让接收者体验角心人物内心的惊喜(电影中往往表现为画面静止)、纠结。小说文本中时间的延长和停顿在电影中可以通过“动”与“静”两个呈现方式进行表达。
“动”主要表现在电影镜头运动的切换中。这种切换还可以分为“想象”与“当下”两个模式。所谓的“想象模式”是通过缓慢的蒙太奇场景的连续性变换,展现人物内心的意识的流动,“蒙太奇是最能有效地使人感到时间停滞不前,感到延续时间的方法,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使人产生这种感觉的”[5]194。涉及的镜头自然是人物受某点刺激后引发其思潮涌动所联想到的涉及过去或者未来想象的场景。这种情形在小说叙述中经常存在,比如《失恋33天》中前一段叙述中王小贱还在为黄小仙摇晃隔板而同其争论,后一段叙述就引入叙述者对王小贱的介绍。电影则通过场景和叙述者自述将这种运动中的回忆表现得淋漓尽致,底本中本来只是一瞬的回忆,因为角心人物意识的参与,述本时间被无意识地拉长。“当下模式”则在于从角心人物视角捕捉人物当下见到的场景,主要通过慢镜头来表现人物心理。电影文本通过慢镜头对小说文本时素延长进行呈现。《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陌生女人见到了作家考究的家具以及丰富的藏书,按照底本这部分本来是一瞥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的内容,小说文本用了大量篇幅进行叙述,叙述时间明显长于底本时间。同样,在电影文本中对此部分情节的呈现使用了慢镜头,尤其是当主人公看到满院子的藏书,视角通过角心人物发出,对书进行缓慢地扫视。在电影文本中通过慢镜头对小说文本的时间延长进行了很好的诠释。
“静”在电影镜头中通过镜头的停顿性持续来展现,这也是表现小说文本停顿的主要手段。最经典的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对盖茨比微笑的叙述:“他善解人意地笑了笑——还不仅仅是善解人意。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微笑,带有一种让你无比放心的感觉,这种笑容……并且让你相信他对你的印象不多不少正是你处在最佳状态时留给比人的印象。”[13]59-60电影中采用了时间定格,聚焦盖茨比的微笑。在进行中的电影中采用这种暂时静止的策略,夸张地表现了尼克被盖茨比迷人微笑所征服时的惊叹状。
五、音乐与色彩
从某种程度上说,“问题不在于探究叙述对读者产生的影响,而在于描写叙事作品本身过程中叙述者和读者得以获取意义的代码。初看起来,叙述者的符号似乎要比读者符号更为明显,数量更多。实际上,读者符号比叙述者符号更为复杂罢了”[1]28。“读者”对电影文本的建构作用不容小觑,“对于叙述行为,叙述的主体强调他者,叙述是建构在与他者的关系之上的”[12]224。所以,针对电影作为“读者”参与的文本,电影文本的时间应当分为“放映时间”和“观赏时间”,所谓的放映时间是指影片放映的客观时间,这个时间是科学精确的;而观赏时间则是接收者的感受时间,这个时间是接收者对影片客观时间的反应,具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电影文本明显的优势在于,其在感受时间上和对时间艺术的塑造上,除了以上列出的几种情形外,还可以通过声音与光线的变化对时间的节奏产生影响。快节奏的或者骤停的背景音乐会使文本时间更加急促紧凑。相反,舒缓的背景音乐会产生延长叙述时间的效果。比如:在电影《海上钢琴师》中,前一段叙述是1900坐在游轮的吊床里,背景音乐是欢快的,突然音乐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重重的吊钩将1900的养父丹尼砸伤。欢快音乐的骤停暗示了接下来不祥事情的发生,叙述时间也随着音乐的暂停变得紧凑。同样,在电影《勇敢的心》中当Wallace和Murron这对恋人在山岗上眺望远方落日时,时间随着悠长婉转的背景音乐而被拉长,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见证这对恋人的浪漫爱情。
画面不同色彩的呈现对时间也有暗示的作用。色彩的微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产生时间变换的效果。从色彩丰富的画面渐变为黑白或是暗色调,是电影中涉及回忆情节时常用的手法,时间就自然地从当下转为过去。王家卫《花样年华》采用的是暗黄色的色调,整体表现出一种历史感,给人以回忆,时间也在这种浓重的氛围中变得厚重。电影《菊次郎的夏天》中则采用了对比鲜明的色彩,电影的节奏也随之变得明快。
小说作为最传统的文本,不仅为电影艺术提供了主要的情节,
而且在时素运用上启发了电影更多的艺术手法的诞生。小说文本中的“时长”元素在电影艺术的加工下表现更加自然,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此外,电影文本也为接收者参与叙述文本提供可能。如果说小说文本通过时间的线性逻辑使读者将虚构的文本世界同真实的现实相联系,模拟一个“第三世界”;那么电影就是多维艺术,时空结合,在调动了观者视听官能的同时,更能诱发其充分的想象空间,从而在真实世界之外塑造一个复杂的多维世界,而观者也从一维向多维获得全方位的体验。
[1] 罗兰·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M]//张寅德.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3]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103.
[5] 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M].何振淦,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
[6] 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126.
[7] 斯台芬·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M].张玉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337.
[8] 莱辛.拉奥孔[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91.
[9] 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83.
[10] 安德烈·戈德罗弗朗索瓦.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1] 安德烈·埃尔博.阅读表演艺术——提炼在场主题[M].吴雷,译.成都:符号与传媒(第7辑),2013:165.
[12] 茱莉娅·克里斯蒂娃.词语、对话与小说[M].张颖,译.成都:符号与传媒(第3辑),2011.
[13] F.S.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刘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14] 赵毅衡.论叙述中的“跳角”[M].重庆: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3).
责任编辑:刘海宁
J904
A
1007-8444(2015)06-0759-04
2015-08-20
贾佳(1990-),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主要从事身体妆饰符号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