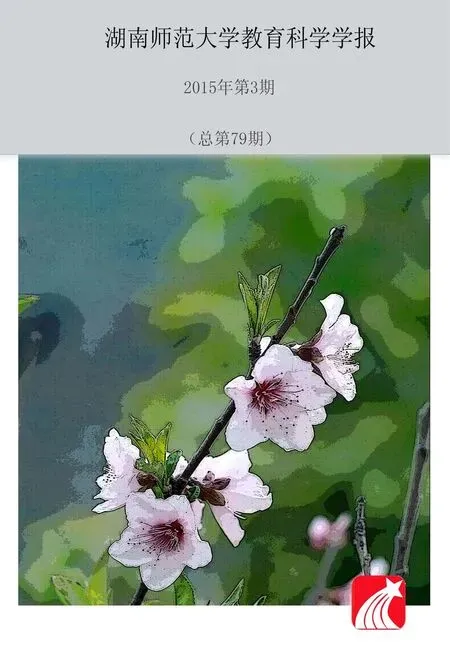道德教育的生活本义及其回归路向
曹 辉
(江苏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深刻地批判了现代性引发了人类科学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认为现代科学把客观世界作为了“研究对象”,忘掉了那是我们生存的家园这一基本的事实,因此主张科学理性要“重返源初的生活世界”,并且响亮地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1]。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也曾经说道,所有的科学和工具理性必须以“开放的世界”为前提。这一“世界”是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视域和场所,它向一切事物和工具开放,但它本身却不是某种工具,更不会屈从于某种人为的目的,而是我们人类一切有目的的活动的家园[2]。然而在教育领域,受工具性价值理性的影响,道德教育长期以来被作为社会或个体工具使用,在本质上日益远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以至于在现当代出现了全球性的道德教育危机。这一状况迫使人们不停地追问,工具性的道德教育价值几何?对于儿童的道德成长有怎样的局限与危害?实际上,儿童的道德发展,正如美国学者麦克唐纳所说,“促使我们价值选择和道德生成的原动力不是那些从外部强加的东西,它更应当是一种生存的状态和生活的过程”[3]。因此,德育必须在学生和教师、时间和空间、意义和情景、过去和未来之间建立扎根生活的、生动的联系,找到其生活的本义,回归生活,才能使道德教育拥有真正的生命与活力之源。
一、道德教育与生活隔离的现实与弊端
1.学生道德发展的主动性日益被消解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科学技术发展迅猛,技术强势日益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社会生活也越来越强化道德教育的工具价值,把道德教育打造成了能够“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伦理、思想孵化器”。学校德育开始不以生活为基础、不把生活作目的,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分离出来、孤立起来。这种工具价值被强化到了极端的程度,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直接在方法上把儿童看做是等待填充的美德容器,把道德条目和礼仪规范强行灌输,如同是一条精心设计的“流水作业生产线”。这种极有“效率”道德教育方式,如果教授的内容是不可靠的信条或真理性无法证实的时候,其传播的对象更广,危害的范围可能性更大;即便其内容是长期以来被社会公众认可的美德,但是,简单粗暴地通过说服、规劝、奖惩、教学、考试的形式让学生理解并记诵,使学生无条件地接受和服从,显然剥夺了怀疑、思考和判断的权利,限制了儿童自我发展与教育的空间,违背了儿童道德发生和发展的规律。这种封闭式、机械化的德育方法使学生在人格上与教师的平等成为一种根本难以实现的奢望和空谈。学生被试图通过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措施接受来自不容置疑的、道德“权威”教条,自身作为道德发展与实践主体的能动性被置之不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生活交往”与“教育交往”关系几近沦落为纯粹的主客体关系,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主体性交往也因为工具性道德教育的预设和干涉而失去其生动性。
2.“知性”道德教育的盛行
以认知为单一模式的道德教育是道德教育与生活隔离弊端的又一显现。20世纪中叶,新科技革命、信息化的新时代使人类对知识倍加推崇。然而,尊重知识经济是人类的进步,而把道德学习看做纯粹知识学习的知性德育却远离了品德发展的自然轨迹。“知性德育”认为,学校应当采用知识教学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品德。这样的教育理念把道德知识的获得等同于道德品质的养成,幻想着通过德育课程考试,以分数来评判促进学生全面的道德发展,完全忽视了情感、意志在学生道德发展中的作用。然而“知性”道德教育的产生并非偶然。海德格尔说,现代性的所有问题是“存在与人的互属关系”被颠倒了[2]。人类对知识的推崇,以及知识化社会、信息化社会的实存使得人们易于把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世界”以及所有的生活都看成是一种知识而加以“研究”,从而陷入了现代科学理性传统思维模式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德教育追求“科学化”,演变成纯粹的知识的教育,将道德的知识从人的完整生活中抽取出来,作为一个纯粹理性的学术研究领域,把道德教育缩减为纯知性的构成,必然远离了作为意义和价值源泉的人们的具体感性生活。当然,不可否认,道德知识在个体品德结构中是最为重要的基础性要素,但是,如果崇尚单纯的“知识中心主义”,脱离学生丰富多彩的生活,就必然不能培养出真正的生活主体和道德主体,从而使道德教育在失去具体生活情境的同时也丧失了其自身固有的生命关怀意蕴和生活关怀取向。
3.受教育者道德主体地位遭遇漠视
近现代科学以主客二体方法论为哲学基础指导人们的社会生产实践,把人作为主体,自然界作为客体,通过人对自然界的探究来发现规律。在这种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作为客体,为人类这一“主体”而存在,因此人类可以随性对客体进行把持、控制和改造。同样,在传统教育中,作为教育对象的活生生的人时常被认为是教育劳动的客体,人的自主发展被沦落为物的可改造性。现代德育受近现代科学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蜕变成了一种“技术”德育而非主体性德育。其典型的后果是直接导致了受教育者主体意识的缺失。在“技术”德育的理念作用下,道德教育开始远离了“做人”、“交往”、“对话”、“价值商谈”与“生活”这些核心话题,在教育方法的选择上,无视学生的人格、尊严、个性与权利,漠视学生道德发展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使得受教育者作为社会主体的意识和作为道德生活主体的意识被逐渐消解与淡化。作为价值建构的道德教育放弃了发生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的道德感悟和体验,试图借助于各种现代科技手段,要求受教育者行为的外显化,用数理方法测定德育的实效,隔离了人的心灵,违背了德育的规律,使德育过程技术化、程式化、模式化、数字化,在根本上,泯灭了道德教育生动的主体性。
二、道德教育与生活的内在必然联系
1.道德教育的生活源泉
人类的道德自发地形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于人们物质生活过程中的社会交往活动中,因此,原初的道德教育其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形态,与生活融为一体。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可以分为心智和德性两个方面,心智以知识的形态为存在,是可以教授的;但德性方面的习惯只能在生活中形成。因此生活本身是个体道德生命成长的沃土和田园。个人在生活中享受着生命的愉悦,完成富有意义的价值追寻。因此道德教育必须与摒弃唯科学化的倾向,摒弃无视对人的生命、生活的机械运作,以生命、生活为基点,关注学生个体生命世界,关注学生道德生命的自然成长,促进受教育者人格的完满发展,使学校德育发生在儿童鲜活的生活世界中。强调道德教育的生活性,是对人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手段”的充分肯定,是对道德教育工具性价值的深刻反思。道德教育的本义,不仅是要教给学生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生存,如何与他人交往,如何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相互理解、相互沟通,从而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创造。
2.道德教育旨在创造“可能的生活”
在规范伦理学的视域中,人们的生活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具体生活,另一种是抽象生活。具体生活又称感性生活,是一种与生命个体相关的衣食住行等日常感性交往活动,具有经验性、重复性等特征;抽象生活又称理性生活,是具体生活的“抽象化”与“理性化”,是对具体生活的抽象和创造性变革,具有理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的特点。对于我们每个生命个体而言,我们的生活习惯于徜徉在重复性的感性生活之中,偶尔也会“升华”到理性生活中实现超越与提升。对受教育者的道德成长与发展而言,这两种状态都是必要的。道德教育既要提升人们的感性生活水平,又要关注理性生活的质量,使人们在理性生活上不断超越。道德教育不仅应当使人们认识到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然”,更应当使他们明晰人们道德生活的“应然”。这种“应然”的“可能”的生活映射了人们的生活理想,彰显了人们对精神家园的道德诉求。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创造条件,使人们不断接近可能的、超越现实的生活。
3.德育的“生活性”体现了对儿童发展主体性的尊重
由于科学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所以以此为基础的德育时常局限于知识的学习,并且使教育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人的精神世界被化简为工具理性而导致人性的疏离和人生意义的悬置。而随着人的物化的加深,他可能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却越来越不知道如何规划自我的形象,如何善待自己的心灵。因此,以胡塞尔为代表的一大批现代思想家大力呼吁“理性向生活世界回归”,希望借此探寻那些对人生至关重要的生存问题、意义问题和心灵问题。而以生活为基础和目的的德育理念主张,教育世界不是一个纯粹“物”的客观世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在这里,有心灵的震颤和受教育者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因此,不能采用实证的工具理性方法,否则,必然因为“物性”的泛滥而导致“人性”的窒息。生活德育把生活主体的培养放在了首位,体现了对受教育者情感、意志等自我品质的关注,是对学生道德发展主体地位的尊重,诠释了德育的生活本真内涵,因而是一种超越工具理性的主体性德育。
三、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基本路向
1.重新审视道德教育的工具性价值
不可否认,道德教育在维护人类生活有序、安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满足了人们政治、经济、文化、个体身心发展、享受生活的多种需要。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强化道德教育的工具性价值,使之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文化的维护者、经济的扬声器,这就违背了道德教育的本义,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道德教育的本真属性。道德教育是人类特殊的实践活动,这种特定的实践活动及其主体既具有工具性价值,又具有主体性价值,即创造上述多种价值的价值,并且主体性价值是内在价值,是工具性价值的源泉。道德教育的主体性价值是其存在的根本。否认了道德教育的主体性价值,必然易于导致把道德教育作为消极的、被动的、任人使用的客体,由此而发挥的工具性价值也必然被严重扭曲,使其陷入全方位的消极与被动。重新审视道德教育的工具性价值,意味着德育要放弃工具理性的核心价值观,不把工具价值认同为德育的唯一价值。德育在本质上不是任何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它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形态。道德教育只有认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地位,才能够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并且为在实践上的创新与发展开拓空间。
2.在生活中实现价值商谈与对话
道德教育研究普遍公认“教育性活动与交往是德育过程的基础”。然而这种教育性活动与交往应当在人们的生活中实现。这是由于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往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念的沟通与交流。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实现相互理解、相互认识、平等对话、展开价值商谈,表明相同的理解或不同的观点,促进彼此的理解与沟通。道德教育应当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在保证人格的独立与平等的基础上,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往、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往真正定位为主体间的民主交往关系。道德教育选择了价值商谈与对话的方式,这在理论上深刻表明,学生只有作为发展主体主动参与社会生活才是道德发展的真正前提,道德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无条件地接受和服从规则,教师的责任不是强制灌输,而是价值引导,是要鼓励学生理智和思维的参与,通过自己的实践、判断和选择,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生活。当然,鼓励学生的道德发展在生活中以交往、价值商谈与对话的方式实现,并不意味着德育“德性培养”的自然职能被消解,相反,这对德育本身的价值引导提出更高的要求。学校德育必须精心、细致地设计和组织适合德育对象品德成长的价值环境和生活环境,才能够有效促进受教育者在道德认知、情感和实践能力等方面不断建构和得到提升。
3.营造批判与反思的理性生活情境
道德教育尽管鼓励儿童的道德成长在生活情境中完成,但是由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存在零散性和随意性的特点,因此道德教育必须有目的、有序地对受教育者的生活情境进行价值设计,营造有利于儿童的道德认识、道德判断和道德实践能力发展的“有意义的生活情境”,以抽象的批判与反思的理性生活为支撑,创设道德理性水平较高的、具有批判和反思情境的教育生活。道德教育向生活世界回归、现代性的批判与重构,培养个体具有反思的道德生活主体意识,真正在理念和实践上提升道德教育的实效,在当前道德教育陷入困境的现实背景下,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4.尊重受教育者道德成长的生活背景差异
学校道德教育倡导学生作为生活主体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建构,在客观上要求德育必须重视受教育者个人生活情境的差异性。因此,德育必须从学生生活情境的个别差异出发,尊重有个别差异的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说,社会交往行为为人们积极习得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系统”铺平了道路[4]。因此,必须破除道德教育中的“流水作业”生产线模式,克服把多种多样的个人心灵抽象、压缩为单一的心灵,针对受教育者生活情境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参与儿童道德人格的形成与完善,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你自己”。回归生活的道德教育更应当放飞儿童的个性,奠定良好的道德人格生成的基础,植根于个体鲜活、生动的现实生活之中。
[1][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二版)[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2]佘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3][美]帕特里克·斯莱特里.后现代时期的课程发展[M].徐文彬,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二版)[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