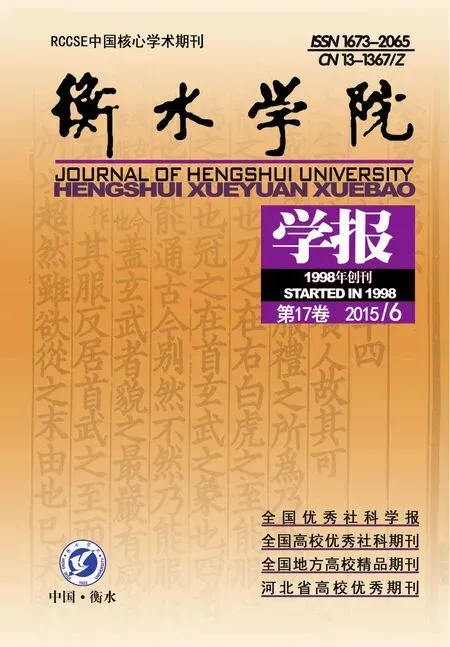周桂钿先生之“董仲舒研究”及现代价值
常 会 营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研究部,北京 100007)
周桂钿先生之“董仲舒研究”及现代价值
常 会 营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研究部,北京 100007)
周桂钿先生是秦汉思想史及董仲舒哲学研究的大家,在学术界、思想界和社会科学界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其潜心学术、孜孜不倦的学术态度及哲学精神令人钦敬。周先生在董仲舒研究的历程中,对董仲舒哲学进行了三次定性。学术范式对董仲舒历史地位及评价影响巨大。周先生对董仲舒的理论贡献归纳、总结为大一统论、天人感应、独尊儒术。由孔子“富而后教”出发,结合新中国历史,周先生总结了“国家发展三阶段论”。周先生提出的“汉代新儒学”基本等同于“董学”。
周桂钿;董仲舒;学术范式;历史地位;理论贡献;现代价值
周桂钿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秦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国传统科学等方面,先后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400多篇,出版个人著作20余种、合著多种,主要著作有《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对中国哲学尤其是秦汉哲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周先生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组织创建哲学系的元老之一,并连任两届哲学系系主任(1994—2000),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创立和发展繁荣,为国家哲学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弘扬和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周桂钿先生之董仲舒研究历程
如果说《王充哲学思想新探》是周桂钿先生的学术生涯开山之作的话,《董学探微》则是周先生学术生涯的扛鼎之作,亦是其学术生涯中最具代表性且最有影响力的著作。
周先生经过综合各种史料,详细缜密考证,认为董仲舒应该生于公元前198年,即高祖九年;卒于公元前107年到104年之间,寿曰93岁。这是其对东汉桓谭、清代苏舆以及近现代学者吴海林编的《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考》及章权才《董仲舒生卒年考》之说很好的驳正①。
周先生在《董仲舒研究》一书的《自序》中提及,其在董仲舒研究历程中,曾经三次定性董学。他认为“定性的变化,说明研究的深入,思想的提高”[1]2。第一次定性,是在研究王充哲学时,给董仲舒哲学定性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研究乃至文史哲各方面学术研究的公认的学术范式,所谓的两个对子,两条路线。周先生第一阶段的学术研究,亦是受此范式影响的。他所言的当时学界关于王充与董仲舒关系的论著,往往认为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王充反对天人感应,因此他们是针锋相对的,皆是在此时代和思想背景下的对学术研究的简单化、形式化、一刀切。周先生从其具体学术研究出发,认为这多是人云亦云,没有仔细读原著,没有全面深入研究二者思想,并指出了具体的例证。
但是,学术范式对于一个人的思想影响实在太大了,故周先生说自己在研究王充的时候,还是时常将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作为王充反对天人感应说的对立面。周先生总结认为“根据王充《论衡》中62次提到董仲舒,看不出王充与董仲舒针锋相对,却看到王充对董仲舒的高度赞扬,即使是批评,也是比较客气的”,这其实是对他早期董仲舒研究的一个思想驳正,亦体现其实事求是的严谨学术作风。
周先生对董仲舒的第二次定性,是在早期董仲舒研究定位的基础上,对董仲舒哲学研究的再定位。他在获得美国王安研究院汉学奖助金后,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又用两年的时间专心研究董仲舒思想。通过通读《春秋繁露》,翻阅过去发表的关于董仲舒的论文,复印查找相关资料,“最后在综合古今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的方法,分析研究,写成《董学探微》”[1]2。本书对董仲舒生平事迹做一考证,主要考证他的出生之年和故里、对策之年与任相经历。周先生指出:“董仲舒哲学是从当时社会现实出发,最后还是归结到社会现实。他的哲学体系用天人感应形式来论述,内容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服务的,有明确的针对性。因此,我用了‘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唯物的’来定性董仲舒哲学”[1]3。
由此来看,周先生在此阶段通过对董仲舒生平事迹及对策和任职经历,对于董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审视,从“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唯物的”这一定位可以看出,他对董仲舒哲学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从唯心主义的整体评价到“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唯物的”,这应该说是认识上的一次大的转变和飞跃。尽管如此,其学术研究依然没有摆脱唯物唯心二分法的范式影响,如他自己所评价的“虽然仍然肯定董仲舒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也像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那样,肯定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唯物主义的成分和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但还是没有脱离用两个对子来研究中国哲学的旧理路,尽管在研究中尽量使用中国哲学原有的概念和范畴”[1]2。
周先生总结指出:“《董学探微》认为,董仲舒哲学是以‘大一统论’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独尊儒术’为重要两翼,充分肯定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辩证法思想,不赞成根据‘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句话就将它定性为‘形而上学’。”这其实也是他在唯物唯心、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个对子一统天下的学术范式框架内,对于董仲舒哲学思想所做的力所能及的“拨乱反正”。
周先生对董仲舒的第三次定性,是在他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以后,发现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政治哲学,董仲舒哲学就是其典型代表②。周先生受徐复观先生《中国艺术精神》认为庄子的道就是中国艺术精神启发,认为王充是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者,是求真的科学哲学;庄子是求美的艺术哲学,那么董仲舒与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这些主流派哲学家,就都是求善的政治之学。这样,他就把哲学分为三大类,即求真的科学哲学、求善的政治哲学与求美的艺术哲学③。这是周先生第三次对董仲舒哲学的定位,即求善的政治哲学。周先生认为:“科学哲学探讨宇宙本原,因此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政治哲学家探讨的是社会治乱问题,只有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开放与封闭的区别,不存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董仲舒哲学是求善的政治哲学,因此不能用唯心主义来定性。”[1]4
应该说,周先生对于董仲舒哲学的第三次定性,是在前两次定性基础上对于董仲舒哲学的进一步全新认识。在此阶段,他完全摆脱了之前的唯物、唯心两个对子的束缚,使得自己对于董仲舒哲学的研究在思想上提高到哲学的新高度。他的这一定性尽管如其所言,主要是受徐复观先生《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扩展。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在研究董仲舒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并没有被之前的学术范式所束缚,并且根据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不断发展,勇于突破原有既定学术研究范式和思维范式的束缚,创新学术研究方法,更新研究思路,从而将学术研究提高到全新的水平。
笔者认为,其对哲学的三分法即求真哲学、求善哲学、求美哲学,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定义为灵感突发或者触类旁通,而是首先基于他的思想是活的,是不断发展、更新和完善的,是与时偕行的。另外,他的求真、求善、求美哲学的哲学三分法,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哲学价值观的终极追求,即真、善、美以及三者的和谐统一,它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也是人类从事实践活动的根本要求。由此来看,周先生的求真哲学、求善哲学、求美哲学的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善、美的价值观和终极追求,无疑也是其思想资源之一。只是,周先生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对于真、善、美之人类永恒追求,依据中国哲学家自身的思想特点,做了全新的诠释和阐发。
周先生进而从历史的角度对董仲舒哲学进行了再评价,并针对过去学界对于董仲舒哲学的批评提出了质疑。“秦汉时代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封建制度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制度,地主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董仲舒哲学代表地主阶级,为封建制度服务,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过去对董仲舒哲学的批评,多是由于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缺乏历史辩证法的思维能力”[1]3。
他的这一评价无疑是中肯的,既对董仲舒哲学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正确评价,肯定其积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对学界过去对于董仲舒批评的原因进行了准确总结,特别是从辩证法的思维能力角度进行了客观分析,可谓切中肯綮。
此外,我们也不能不佩服周先生这种敢于修正自己学术观点的勇气和魄力。我们不由联想到冯友兰先生三次重写《中国哲学史》。作为学者,我们不能保证自己学术观点百分之百正确,但我们至少可以随着历史的发展,学术的进步,思想的革新,不断修正自己之前的学术观点。“蘧瑗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淮南子·原道训》),朱熹于《论语集注》赞曰:“庄周称‘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盖其进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践履笃实,光辉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牟宗三先生亦是如此,早在1949年,他便已经撰成大部头的《认识心之批判》一书,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作了深入的探讨。但在此书绝版多年之后,于1990年由台湾学生书局重印时,牟先生在《重印志言》中对此书表示了不满,认为:“最大的失误乃在吾那时只能了解知性之逻辑性格,并不能了解康德之‘知性之存有论的性格’之系统。”[2]由此看来,真的有德行有学问的学者,概莫不如此也。
正如周先生自己所言,他从1979年开始研究董仲舒,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感想非常多。“第一,我将董仲舒与孔子、朱熹并列为中国历史上对全社会影响最大的三大思想家。孔子是儒学创始人,董仲舒是经学大师、汉代新儒学的代表,朱熹是理学大师、宋代新儒学的代表。……第二,董仲舒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项:‘大一统’论、‘天人感应’说与‘独尊儒术’。……第三,哲学按三类方法,董仲舒哲学属于求善的政治哲学。……他借用《春秋》与阴阳五行理论,阐发自己的政治哲学。同时也融汇先秦诸子百家的优秀成果,根据汉代的社会实际,构建适应汉代社会的儒学体系。因此,董仲舒的哲学体系具有综合创新的意义。……第四,研究董仲舒思想要摆脱疑古思潮的影响。……我们读经典著作的时候,要怀着崇敬的心态,同情的理解,采取学习的态度,而不是轻蔑的心态,挑刺的眼光,否定的观念。……轻蔑古籍的人都在历史中被淘汰了,古籍仍然不断流传下去。谈儒色变,是从五四到‘文化大革命’批儒积弊的后遗症。……第五,富而后教正当时。”[1]5-7
从以上周先生关于自己30年研究董仲舒哲学的感想来看,其实他自己已经对自己学术研究的对象历史地位及评价、理论贡献、哲学类属、历史贡献乃至学者对于古代典籍之应有学术态度等,不厌其烦,条分缕析地做了简明扼要的归纳总结和论述。这充分说明,周先生对于其学术研究是有充分的自觉性的。笔者想结合周先生以上论述中最有代表性和现代价值的几点进行探讨。
二、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及评价
《史记·儒林列传》曰:“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王充《论衡·别通》赞曰:“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又《论衡·超奇》赞曰:“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张岱年先生认为:“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家、哲学家。《汉书》云:‘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可以说他是汉代儒者的领袖。他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尤其深远。”[3]1周先生亦将董仲舒与孔子、朱熹并列为中国历史上对全社会影响最大的三大思想家。他认为,孔子是儒学创始人,董仲舒是经学大师、汉代新儒学的代表,朱熹是理学大师、宋代新儒学的代表。以后虽然也还有一些大师如元代的吴澄,明代的王阳明、黄宗羲、王船山等,影响都不及前三者久远广大。
这里就牵扯到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及评价问题。如周先生之前所言的,“学术界关于王充与董仲舒关系的论著,都是说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王充反对天人感应,因此,他们是针锋相对的”[1]2。这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对于董仲舒的历史定性,即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属于唯心主义哲学,受到当时学界的一致批判。由周先生对董仲舒哲学的三次定性来看,即便是1985年之后,他作为一名敢于突破既有僵化学术范式束缚的学者,也至多能做出“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唯物的”这一历史定性和评价(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了),且仍未摆脱唯物唯心两个对子的学术思维模式。比较而言,这一评价至少在内容上肯定了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贡献。而在周先生约在世纪之交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从而进一步将董仲舒哲学定性为求善的政治哲学之时,应该说此时的中国哲学研究大致摆脱了之前唯物唯心两个对子的束缚,开始走上用中国哲学自身的语言叙事之路。
由此看来,学术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历史人物特别是古代哲学家的历史地位定位及学术评价。这是作为学者,应该特别值得警惕和注意的。而一种学术范式的形成,又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正如周先生在讲董仲舒的人性论时所言:“过去有人认为‘圣人之性’是指不需要教化就是‘善’的统治者,‘斗筲之性’是生来就恶,经教化也不会变‘善’的奴隶。那么‘中民之性’就是指各级官员和贵族。实际上,这种理解受到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不符合董仲舒的思想。董仲舒不认为所有统治者都是性善的,他对历史上许多统治者持批评的态度。孔子和董仲舒所讲的‘斗筲之性’都说的是大坏蛋,不是一般平民。平民哪有资格当大坏蛋?不能全面体会古代社会,只从自己的角度,没有同情地理解、评估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很容易出现这种误解与曲解,妨碍我们正确认识古代思想的合理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一味批判传统文化,很少注意研究其中的科学性。”[1]56-57他正确指出:“董仲舒的人性论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代有广泛的影响。董仲舒说:‘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里的上中下开了后代性三品说的先河,后经王充、荀悦,到韩愈,形成完整的、系统的性三品说。董仲舒讲:‘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个‘天性’,在张载那里就演化成‘天地之性’。董仲舒的‘仁贪二气,两在于身’演化成‘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后来就变成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董仲舒所为身有性情,‘谓性已善,奈其情何’和‘损其欲而辍其情’(《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唐代李翱提出‘性善情恶,复性灭情’。本性是天理,人情是人欲,于是,宋明理学家就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也可以说受到董仲舒人性论的影响。学界多讨论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少讨论董仲舒的人性论,或者简单地将董仲舒人性论概括为‘性三品说’。经过深入研究,董仲舒的人性论以‘性未善论’来概括,可能更确当些。”[1]57-58
清末民国以降,西学东渐,西风尽吹,并借坚船利炮、科技、政治、法律、学术、文化诸方面,涌入日本乃至中国,西风压倒东风。志士仁人皆以救亡图存为急务,遂东学日本,西学法、德、美、俄,一力挽狂澜于未倒,扶大厦之将倾。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如欧洲14至16世纪之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而又有救亡图存之急务,故其势更为迅猛。故有只手打倒孔家店者,有批判吃人之礼教者,有清扫经学马厩者。而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先行者,其对经学儒学孔子之态度反倒更显温和,足以发人深思。而在民国时期,无论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除1927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之年,对儒家孔子稍显冷淡外,从1935年起,蒋介石政府便封衍圣公孔德成先生为奉祀官,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每年隆重庆祝,推崇备至,大陆一直持续至1948年为止④。
由历史来看,自民初经学废,儒学便由经学复归于学术之一家。或曰中国之学术,由经学时代,又返归先秦诸子时代,如老子所言“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然此时中国之学术又引入西方诸多研究方法,如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直觉主义(柏格森)⑤、历史唯物主义⑥,一直到现代的精神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等。这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方法,对于将中国古代学术引入现代语境,是有划时代之意义的,即实现其与世界接轨,与时代接轨。然因20世纪救亡图存为第一要务,故引进时未免囫囵吞枣,甚至燕语郢说,故亦有诸多与中国古代学术历史相龃龉处。如西方现代之解释学消释主客之对立,并以偏见亦是一种理解等,对于我们传统的训诂、考据、义理、辞章之解释方式,冲击是很大的,有其可取之处,如拓宽视域,增进理解等,但又不可因此置传统研究方式于度外,两者实可兼采之,互相补充。
三、董仲舒的理论贡献及历史价值
周先生对于董仲舒的理论贡献,归纳总结为三项:大一统论、天人感应说与“独尊儒术”。
周先生的这一总结是有所本的,如他在研究董仲舒对策之后所言:“三对策所反映的思想,是董仲舒思想的精华,《春秋繁露》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展开、丰富、发展,形成完整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有三要素:大一统论、天人感应、独尊儒术,在三对策中都有。注重天人感应,则称此为‘天人三策’。”[1]16其实,从学界的研究及周先生的论著中,还可以看出,董仲舒的理论中,还应包括政治上的三纲、经济上“调均”以及关乎修齐治平的“中和”。大一统论、三纲和天人感应论应属政治思想,“调均”则属于经济思想,独尊儒术应属于文化思想,而“中和”则是哲学思想。周先生研究认为:“圣人所定的原则多得很,在汉代社会条件下,有两条最重要,那就是中和与大一统。中和是普遍规律,无所不包,天地有中和,社会有中和,人体有中和,人的思想情绪也要中和,以中和治天下,也以中和养身。整个社会是大一统的,思想也要大一统。天下人的思想都要统一于天子,天子要统一于天意。就是说,天下只能有一个思想中心,这样才能使人民‘知所守’‘知所从’。”[3]2
周先生对董仲舒理论贡献的归纳总结,是在其30年系统梳理和研究董仲舒哲学基础上做出的。通过《董学探微》《董仲舒研究》《中国儒学讲稿》等书籍,我们亦可以看出他对董仲舒这几方面理论贡献的特别关注和重视。而他对大一统论、天人感应说与独尊儒术的历史梳理,以及对三者之间内在关系的探讨阐发,更让我们对于董仲舒的理论贡献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和把握。
对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在科学范式占主导的现代社会,似乎持否定态度者较多。周先生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他研究认为:“所谓‘天人感应’‘灾异谴告’,只是他用来推行自己理论的工具,并为后代儒者提供一种向集权者皇帝进谏的手段或方式。在缺乏民权的专制时代,实践证明,这还是可行的方式。历史事实也说明它在许多时候还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说三纲是束缚人民思想的三条绳索,那么,天人感应论则是专为皇帝特制的精神枷锁。”[3]2-3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正如其所言:“董仲舒的学说在这么大的国家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中国传统观念与董仲舒的学说有很密切的关系,传统观念的积弊和优点,大部分与它有关。但是,应该指出,现在成为思想包袱的一些传统观念,在过去却曾起过进步的作用,而且一些传统观念似乎是应该彻底抛弃的东西,但只要换一个角度,却可以看到它的合理性,因此,略加改造,在现代社会却也能‘化腐朽为神奇’,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3]4
在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论进行论述以及比较了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之后,周先生在论述“董仲舒独尊儒术”一章中对董仲舒的三大理论贡献及价值再次进行了阐发:“董仲舒的著作主要有《贤良三对策》与《春秋繁露》。主要思想是大一统论、天人感应说与独尊儒术。董仲舒这三方面的理论价值,可以说立了万世之功。大一统论,强调‘屈民而伸君’,全国统一于皇帝,保证了全国政治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维护了新创造的中央集权制度,使中国形成民族复杂、人口众多的大国。天人感应说限制了皇帝个人的私欲,达到‘屈君而伸天’的作用,协调了君民之间的矛盾,调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使矛盾尽量缓和,不使激化。在没有民权的时代,这是存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方式,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西方的民主观念传入中国以后,许多学者都极力批判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但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建立与维护中央集权制度,代表着最先进的文化,也是最文明的意识形态。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国的富强无不与此相联系。独尊儒术,屈君而伸天,天又是由儒者按照儒学来解释,已暗含独尊儒术的意思。汉代独尊儒术奠定了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民族魂。董仲舒为政治服务,不是简单地为当时的政策做论证,而是为整个民族的兴盛与发展、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做宏观长远的设计。”
正是在此基础上,周先生更进一步指出董仲舒哲学的巨大历史贡献:“从这种意义上说,孔子创立了儒学,而董仲舒以儒学奠定了中国魂。思想统一和政治统一是一致的,都统一于儒学。这是董学对儒学的贡献,也是董学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简单地说,董学的历史地位,董学使儒学从诸子升为独尊角色起了关键作用,使儒学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做了奠基工程。”[1]218
周先生对于董仲舒的三大理论贡献及价值的评价是非常客观公允的。大一统论强调“屈民而伸君”,这里有必要做一解释。此处的民,根据周先生的研究分析,主要不是指老百姓,而是指拥有地方势力的诸侯国君。他指出:“理由很简单,老百姓没有权力,无法与封建统治实力对抗,只有那些地方诸侯国君有实力与中央政权对抗。董仲舒曾经亲见景帝时代的吴楚‘七国之乱’,‘屈民而伸君’可能就是从这一事实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屈民而伸君’实际上是为了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而提出的口号。这一口号对于中国长期维持统一大国的政治局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63在比较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一讲中,他再次指出:“屈民伸君,主要是限制诸侯,树立天子的权威,巩固中央集权制度。”[1]79他的这一论断,从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有其独特的历史意蕴。
四、富而后教正当时——孔子“国家发展三阶段论”
“富而后教”语出《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周先生指出:“‘富而后教’,这是孔子儒学的重要思想。富以后,如果不进行教育,那就会堕落、腐败。君子富起来后,不能骄傲,‘富而后教’还要‘富而好礼’。如果富裕了,不能及时给予教育,新富起来而又缺乏教育的人容易骄横为暴,严重危害社会。按孟子的说法,这种人就跟禽兽差不多:‘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1]8
紧接着,周先生结合汉初60年的历史,指出“其正好是孔子所说的三个阶段,即先建立健全的社会秩序,人口增加,安居乐业;让人民富起来;对他们进行教育。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提高文化。”[1]8
关于富然后教,徐复观先生在其《释论语“民无信不立”》一文中也曾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言论,从修己和治人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层面进行了解读,他说:“孔孟乃至先秦儒家,在修己方面所提出的标准,亦即在学术上所立的标准,和在治人方面所提出的标准,亦即在政治上的标准,显然是不同的。修己的学术上的标准,总是将自然生命不断地要德性上提,决不在自然生命上立足,决不在自然生命的要求上安设价值。治人的政治上的标准,当然还是承认德性的标准;但这只是居于第二的地位,而必以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居于第一的地位。治人的政治上的价值,首先是安设在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之上;其他价值,必附丽于此一价值而始有其价值。”[4]
“国家发展三阶段论”应该说是孔子最先提出来的(当然孔子在言此的时候,可能并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这主要是由其一贯的为政治国理念所决定的),是先秦儒家仁政学说的重要体现。而孔子的这一思想,却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相契合。由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来看,也确是如此。周先生依据汉初发展的历史现实,指出其理论的合理性。此外,他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的社会发展,总体也是按照这一三阶段的发展模式行进的,从而进一步肯定了这一“国家发展三阶段论”。
由此“国家发展三阶段论”出发,我们便可以参照汉初60年历史,对于今日中国历史发展做一客观认识和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60年,基本上也走过了稳定政权、发展经济和文化复兴三个历史阶段。作为一历史发展规律来说,它是不以人之意志为转移的。而从新中国成立发展60年历史来看,也确是如此。稳定政权是第一步,这一阶段基本上是从1949年国家成立开始,通过“三反”“五反”,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等的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基本上由新民主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而后,又经历了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代,经历了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才基本上实现了国家政权、政局的稳定。此后,在邓小平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恢复经济,发展生产,逐步全面对外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30年后,中国已经由之前的积贫积弱跃居为世界瞩目的第二大经济体。这便是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第二阶段——发展经济。而在国家经济逐步繁荣的今天⑦,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决策者也审时度势,将文化复兴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正如许嘉璐先生评价习近平主席视察曲阜,认为其历史意义等同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其意在为儒家正名,平反昭雪。而习近平主席亲自出席参加于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则等同于向全国乃至世界宣布,中央政府正式为儒家正名,为其平反昭雪,还其本来的真实面目和历史地位,并进而追溯其历史发展流变,肯定其思想价值和历史贡献。毫无疑问,一个重视、研究、传播、弘扬和借鉴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时代已然来临,中华民族正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和姿态,走在文化复兴的开阔大路上。
五、结语
此外,在论述董仲舒哲学的过程中,周先生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汉代新儒学”。从周先生的叙述中,它基本等同于“董学”,或者说“董学”集其大成。我们都知道,“新儒学”是近现代学者对宋明以来程朱、陆王等创立的理学、心学之称谓,意即宋明理学、心学以天理、天命、心性、道器等阐释和发展儒学,开创了儒学的崭新格局风貌。而在对董仲舒哲学的研究中,周先生用“汉代新儒学”来指称“董学”,这真是别开生面的。
周先生对于“汉代新儒学”给予了历史的总结和论证:“汉代开始兴起儒学。汉代独尊儒术,实际上独尊的是汉代的新儒学,是已经融会众家思想,经过综合创新的新儒学。陆贾在刘邦面前提倡《诗》《书》,提倡儒学,后来,叔孙通与其弟子制定朝廷礼仪,贾谊、晁错都在朝廷上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受到迫害。辕固生、胡勿子都、公孙弘等也都为儒学复兴作出过贡献,而董仲舒从理论上做了集大成的工作。从以后的情况来看,当时独尊儒术,主要是独尊了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是唯一明于公羊学的学者,因此说到底,独尊的是董仲舒哲学,是董学。”“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先秦的各种思想,按照自己的思想体系进行组织,自成一家之言。这一家可以成为新儒家。他的这个新儒家,比先秦原始儒家增加了很多思想内容,其中有墨家的兼爱思想,也有阴阳家的阴阳五行思想,还有道家、法家、名家等各种思想。各家思想都有一方面的真理性,都是整个社会所需要的,所以才在激烈竞争中得以保存下来,而没有被淘汰。它们都在复杂的政治活动中起一定的作用,也都是不可或缺的。治理天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许多思想。没有综合性的思想,只靠一家的思想,对于治理天下来说,显然是不够的。”[1]102-103
周先生指出:“当时独尊儒术,主要是独尊了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是唯一明于公羊学的学者,因此说到底,独尊的是董仲舒哲学,是董学。”这是一个极具创新性的论断,从而将人们对于“独尊儒术”的理解和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周先生对于“汉代新儒学”的定义和阐发,不同于学界对“新儒学”的理解,但却有很深刻的理论启发意义。若从理论综合创新角度来定义“新儒学”,那么新儒家便不能仅仅限于宋明新儒学。周先生通过研究秦汉思想史,研究董仲舒哲学,提出了“汉代新儒学”。笔者以此类推,汉代以后还有“魏晋新儒学”“南北朝新儒学”“隋唐新儒学”,然后才是“宋明新儒学”,直至“现代(当代)新儒学”。这一推论应该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
在《董仲舒研究》“汉代新儒学的启示”一节中,他指出:“汉代新儒学得以独尊,而坚持先秦的儒学却一再受到打击。这是变与不变的命运。时代变了,理论不变,必然凝固、僵化,被淘汰;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有活力,有长久的生命力。”[1]110这些都是对于儒学在不同时代发展创新,并保持其顽强生命力的辨证认识,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是对董仲舒集其大成的“汉代新儒学”(董学)的高度赞誉。
作为周先生的学生,笔者从周先生身上所学到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学术的极度专注与认真执着,我们可以从周先生的《六十自述》中窥其端倪。无论是参加何等的学术团体成立大会,各种类型的学术交流研讨会,周先生都会做详细的记录,时间、地点、人物、研讨内容、讲话发言、个人心得,事无巨细,详实丰富,面面俱到,为我们保存下如此众多的场景史料。周先生说:“我们对于资料先认定是真实可靠的,尽可能不将某一资料否定掉,经过详细研究,作出各种可能的解释,选择最合理的说法。对于古籍的解读,必须有训诂的根据,不能根据现代人的理解,望文生义,而产生曲解,误解。主要有三条原则;一是资料尽可能收集全面;二是要正确解读;三是将各种资料联系起来考察,反复推敲,努力达到完满、圆融。”[1]10二是他对人类、国家、社会、生活、自然乃至宇宙的持续不断的思考和判断分析,以及所形成的诸多极富创见的学术观点和历史评价。这些都内化成其学术研究的宝贵精神财富。
注释:
① 参周桂钿《董仲舒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4-7页。
② 周桂钿先生于1994年第3期的《福建论坛》上发表文章《董仲舒哲学与西汉政治》,认为董仲舒哲学与当时政治关系密切,是政治哲学,属第二层次,其核心是大一统论,天人感应是其理论形式。他在1998年第2期的《船山学刊》上发表《独尊儒术,奠定汉魏——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在题目上明确标出“政治哲学”,并给董仲舒定性为“政治哲学家”。
③ 但周先生在2008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董学探微·再版序言》中提到,他是受胡适关于哲学定义的启发,又提出哲学可以分为三大类:求真哲学、求善哲学、求美哲学。也即是说,他的哲学三大分类说可能既受到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一书影响,也受到胡适关于哲学的定义启发。
④ 关于民国年间的祭孔讲学活动,笔者于2010年立项的北京市课题“续修国子监志”《新编国子监志》一书中有专门章节论述,该课题已于2013年底结项,拟于2015年底正式出版。
⑤ 现代新儒家之张君劢先生便受其影响较深,并作专文对其向国内学界进行推介。
⑥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学术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故历史唯物主义一直盛行于世。
⑦ “调均”一词的提出来源于西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是其针对当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而提出的治国经济方略。具体参周桂钿《董仲舒研究》,第二讲“董仲舒对策的主要内容”,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22-23页。
[1] 周桂钿.董仲舒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刘明辉.当代儒学的自我转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0.
[3] 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0:299.
Mr. Zhou Guidian’s “Research on Dong Zhongshu” and Its Modern Value
CHANG Huiying
(Department of Research, Confucius Temple and Imperial College Museum, Beijing 100007, China)
Mr. Zhou Guidian, a master of the studies on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holds an important academic position and influence in the field of academic, ide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and his great devotion and assiduous attitude to academic together with his philosophical spirit is looked up to. In the course of his study on Dong Zhongshu, Mr. Zhou defines Dong Zhongshu’s philosophy for three times. Academic paradigm has great influences on Dong Zhongshu’s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evaluation. Mr. Zhou summarizes Dong Zhongshu’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s the great unification, the telepath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nd honouring Confucianism alone. Based on Confucius’s “education after wealth” and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he puts forwards “the theory of the three phase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His “New Confucianism in the Han Dynasty” is basically equal to “Dong Zhongshu’s Theory”.
Zhou Guidian; Dong Zhongshu; academic paradigm; historical positio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modern value
B234.5
A
1673-2065(2015)06-0024-08
10.3969/j.issn.1673-2065.2015.06.005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2015-06-05
常会营(1980-),男,山东寿光人,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研究部副研究员,哲学博士,衡水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