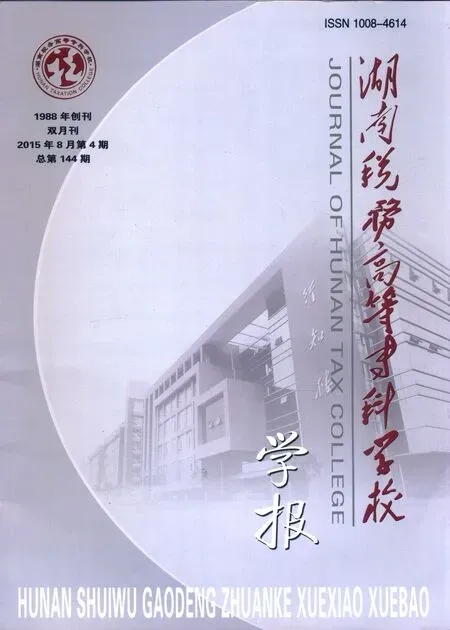从《家》中“鸣凤之死”论现代女性文学*
□郑晓宁
(福建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福建福安355000)
从《家》中“鸣凤之死”论现代女性文学*
□郑晓宁
(福建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福建福安355000)
女性文学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文学中的显学,但是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却也免不了误解与错解,以女性文学的内涵为切入点,探讨什么才是女性文学的问题,并以巴金先生现实主义著作《家》中鸣凤之死的有关情节加以佐证,挖掘出超越男性惯常理解与期待的女性视野与女性经验,以帮助构造形成完整化的女性文学经验世界。
现代女性文学;《家》;鸣凤
《家》中鸣凤这一人物是个非常感人的艺术形象,国外甚至有评论者认为鸣凤的既文雅且让人感伤的形象是中国女性的代表,她的爱、她的死都是极具现实表现性的。这种说法有过于吹捧之嫌,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巴老对于鸣凤的描写,是对鸣凤的赞歌,是站在女性视角写出一个人及一个时代的悲剧。
一、女性文学的内涵
女性文学这一概念虽然早有提出,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直到上世纪90年代,它才逐渐变为中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伴随女性意识从哲学领域的扩散,也伴随着整体人本主义文学的解体,女性文学变成文学理论中的全新审视范畴。这一概念强调了性别因素对于文学作品与文学影响力的作用,它不但强调了一种对于确实存在的文学形式的命名心理,也强调了这种文学形式界限的厘定原则。应当说,女性文学是和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等政治概念有较紧密联系的,女性文学毕竟应当以女性所著文学作品为大宗。[1]但是我们也应该了解,女性文学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普遍性的肯定,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说女性文学是一个外延并不明确的内涵也并非无稽之谈,一些对于女性文学的质疑与追问会将矛头指向下述几个观点。第一,很多文学理论研究者谈到女性文学时都特别随意,直指作品本身,而轻轻带出女性文学的概念又不深究其内涵。这种随意性的态度可以应用于文学作品,却不能应用于文学理论,因为每一个新概念的形成,都是要有严格的界定的,否则它便无法从旧概念中完全剥离出来。比如本文所要论述的《家》,是否属于女性文学,不同的标准就会产生不同的结论。第二,女性思想如果进入到特定历史语境中,就会得到文学表达的机会,然而这是从传统文学中“逃逸”出来的作品,具有叛逆性与“多余性”,所以很多人都将之视为男性主体出于礼貌而给出的多余席位。[2]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文学越分越细,即使男性文学占据绝大多数席位,但女性文学并非附庸。女性作家本身的女性文学暂不必提。就是一些男性作家(关于男性作家以女性视角所著文学作品是否为女性文学,属于另外一个课题,本文不以性别分类,而只以作品视角分类,允其置于女性文学之中)所写的妇女题材,创造的人物形象特别真实、丰满,成为文学中的经典,比如曹雪芹创造的金陵十二钗,鲁迅先生创造的子君与祥林嫂,茅盾先生笔下的一些时代女性,曹禺所创造的繁漪等;再比如国外莎士比亚所创造的克里奥皮特拉,雨果所创造的爱丝美拉达,左拉所创造的娜娜以及托尔斯泰所创造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些经典人物形象极深入地达到了历史与社会环境下的女性经验最深处,站在女性视角表达出女性的痛快与欢愉,寂寞与欲望等。而巴金所著《家》中鸣凤这一艺术形象,典型性与女性思想深度尤为突出。应当说,女性作品并非全如有些论者所指称的那样难以窥见,它也并非可以被随意操作,女性作家能够窥见其中奥秘,男性作家同样也可以,起码就现在看来,文学依然是没有性别之分的,男性作家的作品,当然可以显现女性世界的丰富与柔弱、美好与忧伤,亦可以从独特的视角折射出时代的发展与变迁。
二、女性视角的鸣凤之死
长篇现实主义著作《家》,是巴金先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这部小说自从20世纪30年代出版以后,长期受到众多读者的热爱,文学研究者也站在多个角度对其加以评析与研讨。这部小说的悲剧色彩很浓厚,特别是小说里面的女性人物形象,尤其以鸣凤最为特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力,看出其对于女性主义的深度赞许及将女性主义应用于文学作品上的表达热情。巴金所塑造的鸣凤这一人物,以其独特的性格特点而留名后世,闪耀着无穷的艺术光芒。特别是在写到鸣凤之死时,可以说凄惨难以卒读,伤情使人落泪。作者在《关于〈家〉》中写道:这并非小说作者代鸣凤出主意,要她走那条路,而是性格,教养与环境逼着她(或者引诱她)在湖水中找到归宿。[3]也就是说,鸣凤之死,与客观环境相逼迫有关,也与她本质上的性格特点有关,是这样的性格才会必然走向这样的结局。毕竟,因为教养与性格的迥然不同,即使是同样的客观环境,鸣凤是自杀而死,婉儿则是忍辱吞声。当然,对于这部作品来说,造成鸣凤之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巴老自身的叙事立场和结构构思。而无论哪一种原因,对于鸣凤之死这个情节来说,都无碍于其作为女性文学的典范地位。
(一)社会原因与鸣凤之死——旧时代下层女性的外部束缚
普遍的观点认为,封建社会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森严的等级制度与严酷的封建礼教。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开始产生一种倡导民主科学的思潮,这种闪烁着人道主义光芒的思潮促进了社会向前发展,对于封建家长制度是一股极大的摧毁力量。但是同时这种民主科学思潮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并非能够立刻将旧的思想与制度完全颠覆掉。《家》里面的觉慧就是一个有志于新思想的青年,他不走老路,敢于向老太爷反抗,并积极参与到社会斗争中去,也敢于和下层的小丫头鸣凤表白自己的爱情。但是觉慧的思想革命并不彻底,是他成全了鸣凤,也造成了鸣凤最终的悲剧产生。[4]在小说里面,三少爷觉慧和鸣凤是真心相爱的,但是高老太爷却把鸣凤送给了冯乐山,鸣凤没有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而是以投湖的办法来保存自己生命的清白。如果只考虑故事情节,则鸣凤完全可以不死,至少她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委曲求全而嫁给冯乐山,二是坚决地反抗下去。我们不妨试想,觉慧对鸣凤之死是什么感受,鸣凤死了,觉慧肯定非常痛苦。可是如果鸣凤一直为了爱情与幸福进行奋斗与反抗呢?觉慧又会是什么态度?如果鸣凤反抗了、奋斗了,那么觉慧反而会觉得很为难。因为如果这样,必然也会把觉慧牵涉其中,但是觉慧此时是不想反抗,也不能反抗的。在经过一夜深刻的思索以后,他是将要把这个少女放弃了,他可以忍受放弃鸣凤的痛苦。他所做的这种决定是有其深刻环境根源的,那就是小资产阶级所谓的自尊心与此一时代年轻人的献身热诚,觉慧将自己的责任夸大了,虽然明确方向的奋斗目标还没有找到。这正像哈代在其作品《德伯家的苔丝》里面所说的那样:这位青年(哈代指的是克莱),是有进步的思想与善良的心灵的,是这个时代所能产生的典型人物,但是事出非常之际,他还是会按照童年时所接受的教育那样,成为世俗观点的仆从。[5]觉慧与克莱是有相似之处的,《家》这部作品也正是用鸣凤的死来体现悲剧产生的直接社会原因。同时向我们预示了悲剧发展到最后必然带来的阶级反抗。按照作者的观点也正是这样:如果她们(指鸣凤这样的下层女性)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中,她们的青春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她们的才能也才有得到发展的机会。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做下人的生命信条就是好好侍侯主人,自己的命运同样是掌握在主人手中的。当时民主与科学观念的产生虽然也对下层女性造成了一定影响,使其中一部分人明确反对照办主人意思的观点,但传统束缚的影响是深重的,毕竟并非所有人都能有此觉悟,如鸣凤等人是难以有勇气与力量对旧制度提出挑战的,她们所面对的只能是无意识地进行反抗却没有结果同反抗之后不理想的结果,最终产生自虐行为。思想上有进步,但是出路依然渺茫,最终酿成了一个人乃至整个时代的悲剧,这就是巴金笔下鸣凤这样的女性悲剧的真实写照。
(二)心理原因与鸣凤之死——旧时代下层女性的内部束缚
旧时代下层女性的内部束缚强调的是文化与心理因素对于下层女性悲剧形成的作用: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是培植不出女性自由主义的。那种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道德,对于女性是一种强大的外在约束,但是时日既久,外在约束开始向内化的道德标准转化,深深植根于女性意识之中,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强大外部束缚,使得将爱情视为达到她们所有愿望目标唯一路径的女性感觉到极为寂寞乃至自卑与绝望,这是自虐行为产生的主观心理原因,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有一部分女子将所有的精神生活全都集中到寻找爱情与推广爱情中去。鸣凤正是这样的女性,她被压制在高家小社会的最底层,处在受奴役与压迫的位置,因为一直以来都受到根深蒂固封建礼教的残害,她有寻找爱情幸福的心理,却始终无法真正得到这样的幸福,自卑心理让她产生了胆怯心理,正是胆怯心理的作用使她不由自主地拒绝了觉慧对她的爱情表白。在得知自己要被送给冯乐山时,她能做的只有哀求:只要不把我送到冯家,你打我、骂我都可以……但是她的命运何曾有过丝毫转变,小说里面有这样一段:在鸣凤自杀之前,她去找过觉慧,在他的窗外徘徊许久,直至鸣凤进屋,读者可能会以为鸣凤要向觉慧诉说自己的真实想法了,想要说说自己是如何痛苦与无助了,可她最终还是没有说,不说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她将觉慧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认为自己不能对他产生妨碍。这种本质上不平等的爱让鸣凤最终放弃了诉说。[6]还有一个原因是鸣凤清楚自己即便说了也于事无补。鸣凤在绝望之中产生了自虐心理,而自杀正是自虐的终极表现。在动乱的年代,只有出现社会性的强烈失败、绝望、耻辱等情绪才会造成自杀现象的产生,若鸣凤不选择自杀,她的未来能否避免悲剧的发生,答案是否定的,还有另外一种悲剧的结局在等待着她,那就是做冯乐山的小妾。在此事件里面,高老太爷的位置高高在上,即使像正房太太也是毫无自由,只能对高老太爷惟命是从,并且还说服他人也要顺从。女性社会地位本已低下,更何况身处下位却仍然操纵较之更下者的命运,这是鸣凤之死最大的悲剧引线。而这些,都和文化氛围对女性心理造成的影响有关,如果不是深谙女性心理,并积极站在女性角度考虑问题,巴金不会写出这么深刻的故事来。
(三)作者影响与鸣凤之死——男性作家的女性视角
在《家》里面,觉慧这个人物的立场同作者的立场有相似之处,这使得作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处处站在觉慧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鸣凤最终的结局是投湖自杀,但是作家却将之写为现代文学史中诗意美感十分突出的女性,这显然就是男性视角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家》不完全是女性文学,鸣凤之死的有关情节,也不能完全归入女性文学,这是需要注意的。另外,在上文曾经指出过,鸣凤若是不死,还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跟随觉慧,另一条路跟随婉儿。但是对于一个小说作者来说,不太可能在一部小说里故意创作两个同样性格的人物,走其他人物已经走过的路,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鸣凤只有自尽才是最合理的构思,当然,无论男性作者还是女性作者,在艺术构思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别。再者,在这部小说里面,女性的独立性体现得不强,几乎所有女性都保持着和其有关男性相同的立场,而小说整体叙事过程中,将很多女性塑造成为性格温驯、美丽纯洁视爱情为生命的形象,这是站在男性思维角度而出现的必然结果,这样一来,所谓男性作家创作的女性文学,多多少少有一股不纯粹的意味。[7]但无论如何,在《家》里面,女性用受难甚至死亡的办法,起到了控诉男性主体罪恶的作用,鸣凤之死悲剧尤其体现出觉慧在封建阵营里面失去所爱之人的心灵创痛,觉慧也正是在失去亲人与爱人的过程中体会到死亡带给他的恐惧感,最终选择大胆的反抗:是鸣凤等女性的死,成就了觉慧等人的生。看来,女性文学与传统文学的离与合,真的不是很容易说清,最起码我们是可以用不同视角审视同一部作品的。
二十世纪我国女性文学,产生于悲壮的历史环境之中,并且经历了坎坷的发展历程。我国现代女性文学与中国的美学尺度与价值取向有密切关系,其中《家》中的某些章节特别是关于鸣凤之死的情节,以女性视角再现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可以说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文学现象。
[1]王新玲.《家》的人物形象系列[J].上海戏剧,2012(7):33-34.
[2]张乐涵.巴金理想与现实中的女性[J].神州,2013(1):12.
[3]张乐涵.巴金与夏目漱石小说中婚恋观比较研究[D].辽宁大学,2013.
[4]徐慧娟.试论鸣凤悲剧处理艺术[J].株洲工学院学报,2002 (12):37-38.
I206.6
:A
:1008-4614-(2015)04-0047-03
2015-6-15
郑晓宁(1978—),女,福建福安人,文学硕士,福建宁德职业技术学院语文教研组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