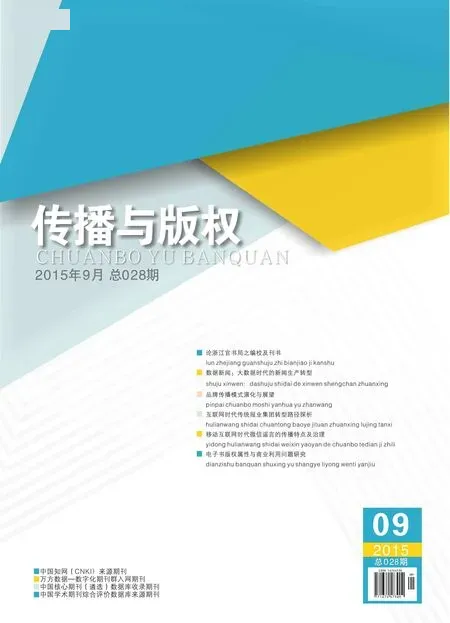唐宋小说中狐精形象研究
袁中华
唐宋小说中狐精形象研究
袁中华
唐朝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流光溢彩的朝代。它的壮阔胸襟正是来自于自身的实力,广阔的领土、强大的军事实力、繁荣的经济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经过隋唐之前长达四百年的民族融合而来的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出现在唐代小说传奇中的狐妖的形象越来越偏向于女性化,人性化色彩渐浓,也进入了普通的家庭生活秩序中。
唐宋小说;狐狸精;形象研究;女性化;人性化
[作 者]袁中华,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生活在唐朝的人们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而自豪,同时也有更充足的理由为身为人类社会的一员而自豪。“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人们将代表着死亡与绝望的沙漠纳入了自己的审美视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怎样强大的自信才能将“骏马西风冀北”描绘出“小桥流水江南”的风韵;“落花踏遍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骄傲的大唐人,充满活力,对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那么,出现在唐代小说传奇中的狐妖的形象又有新特点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一、狐妖偏向于女性化
唐初小说《古镜记》是较早提到狐妖的唐代传奇,其中有一只老狐妖化为人形,在人间却颠沛流离、多历艰难,后来遇到传世宝镜,化出原形而死。故事中的狐妖化为婢女,寄身一户人家,被识破后却并不见惊慌畏缩,它言语从容地叙述自己来历,大醉尽欢后,长歌一曲,从容赴死。“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而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1]。这里的狐妖没有外貌、性格等的描写,但从它与人的对话中,可看出它颇有看透生死的淡定从容,仅这一点就能让人们对其留下些不同的印象。《广异记》是中唐时期的志怪小说集,专述狐精的就有33篇。《崔昌》《李元恭》中的狐精化为男身,其特性、遭遇与前代基本相同,而化身为女性的狐精形象却鲜明了起来。《李黁》中的狐精与人结婚生子,不但与丈夫感情非常好(其夫不但在其生前对其眷恋宠爱,在其死后还念念不忘),对自己的孩子也充满了爱怜,对自己的被侮辱也感到委屈。《贺兰进明》与《冯玠》故事中仍是狐精与人相配,但一个被逼离去时泣涕不舍,一个婉转殷勤地讨好丈夫甚至于仆佣,可以明显看出,作家在创作狐精的女性的形象时投入了更多的心力与想法。
看来,唐代之人不仅认为自身有实力引出狐妖的真心喜爱,还很有兴趣去探索狐的感情。人们在生活中喜爱那些“通人性”的动物,仔细想想,所谓“通人性”就是能跟人做一定的交流。唐人已经把狐看作是可以交流的,那么有喜爱之情也就不奇怪了。在一个男权的社会中,狐精被喜爱,它们形象上偏重于女性的东西便逐渐凸显了出来。狐是狡猾的,又是诡秘的,狐的形象在人们心里一直是偏于阴柔的,狐妖就渐渐流向了女性化的狐精。
这时的小说创作,其手法也明显地提高了,不再是平铺直叙,而有了比较曲折的故事情节,小说的语言明显是经过雕饰的,确实是“有意为小说”[2]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虽然在向狐精靠近,但仍然保持着戒心与警惕。看下面几段摘录:“旧说,野狐名紫狐,夜击尾火出,将为怪,必戴髑髅拜北斗,髑髅不坠,则化为人矣”[3],“忽有妖狐踉跄而至。初不虞晏通在树影也,乃取髑髅安于其首,遂摇动之,倘振落者,即不再顾,因别选焉。不四五,遂得其一,岌然而缀。乃褰撷木叶草花,障蔽形体,随其顾盼,即成衣服。须臾,化作妇人,绰约而去”[3]。月夜,妖狐头戴骷髅拜北斗,化身为美女,听起来就叫人觉得毛骨悚然。可以看出,狐精在人们心里仍属于异类。当然,也不能否认,这里面还糅合了一些“红颜祸水”的传统思想,正所谓,“红粉骷髅”销魂蚀骨,在这里狐妖害人的观念已经偏向狐妖化为美女,诱惑男性伺机加害。也可以看作是狐妖偏女性化的一个表现。
二、狐女的人性化色彩渐浓
人们的注意力被狐精的人的外表吸引了过去,开始着意于发掘它们的人性化的方面,而动物性、妖性的一面被人们有意地忽略。《广异记》就有几个狐精颇有人的性格。如《李氏》中描写了一对争风吃醋的狐狸精兄弟,听其言,观其行,只觉得既天真、又狡黠,还带了几分恶作剧的调皮,使人好像亲眼见了小狐狸戏弄哥哥后的得意。而几个狐精女性的对爱人孩子的深厚的感情,则更能表现出它们的人性。狐精形象中注入了感情,犹如花瓣上缀了露水,瞬间生动了起来。“性欲成为爱情,自然的感官成为审美的感官,人的情欲成为美的感情”[4],“动物只有性,没有爱,由性变为爱却是人独有的”[5]。
狐精,原本就有蛊惑害人的一面,既然唐人眼中的狐精偏向于女子的形象,那蛊惑自然就转成了女子的婉娈柔媚,狐女在与人的相处中人性化的一面也就越发的明显。
《任氏传》是唐传奇中极为出色的一篇,故事塑造了一个十分可爱的狐女形象。任氏是个狐女,美丽温柔、聪慧柔顺,人们大都喜欢她。有研究者从各个方面分析任氏的形象,有人认为任氏是身上有娼妓的特点,放诞风流,有人认为她妩媚柔顺,是士人心中理想化的红颜知己,还有人认为任氏的表现过于柔弱而与妖精的实质不符。
如果从作者写小说迎合当时读者的口味的一方面来看,则可进行如下分析。故事的一开始就交代说“任氏,女妖也”[6],此后文中多次明示暗示任氏的身份,说是狐女,实际上无异于妓女。因此任氏不同于人世间的良家女子,她极富于女性的魅力,也极善于施展、表现出这种魅力。唐代贞操观念不强,作为娼妓更是不必有任何顾虑,但非常奇怪的一点是,任氏与郑六的结合非常轻易,而后来面对无论是品貌、家世都强过郑六的韦崟的求爱时却宁死不从,不仅反抗十分激烈,而且在绝望时抱有巨大的痛苦和悲愤,十分类似于明清时代的贞妇烈女。这明显是一位男性作者严格按照男性的审美观塑造出来的形象,或者说是男人理想的伴侣形象。在对待丈夫时尽可能的风流妩媚,创造夫妻间的乐趣,而在面对丈夫之外的男性尤其是有威胁的男性是则一定要坚持立场,捍卫贞操,替丈夫守护他的私有财产。像郑六那样的情况更需如此,郑六虽是世家子弟,但是已经败落,他并没有经济来源,要靠韦崟来接济,仰他人鼻息而活,自然更不能庇护家眷,只能由任氏来“宁死不屈”。作家按照理想标准来塑造自己的主人公,一方面是狐女进入了作家审美创造的范围,同时显然也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狐女不再被当作有害的妖精,而是一种有趣新鲜的存在,人们与她们保持者距离,小心翼翼又充满兴味地观察着。即使是这样,狐女也越来越有了人类的气息,他们有了人类的感情,会为了离别而黯然销魂。
《任氏传》的末尾有这样一段话“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6]。作者感慨狐女之一往情深,甚至认为人间的女子不如狐女。他叹息这样多情的狐女却所遇非人,郑生只喜欢她的容貌而不能体会她的深情,不能体贴她的感觉而真正建立心灵上的沟通。这实在是一种很“超前”的认识,几百年后的一部奇书《红楼梦》中对此作了深刻的描述,认为“皮肤淫滥之蠢物”不及“意淫”。
三、狐女进入普通家庭生活
就像人们对狐的畏惧一样,人们一旦对狐女产生了好感,这种好感就会凭借着想象的力量开始扩大。人们尽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去尽情幻想狐女的美丽慧黠、活泼温柔,狐女的形象得到进一步丰富。
宋代刘斧编撰了一部文言小说集《青琐高议》,包括杂事、传奇、志怪在内,其中有四篇是写狐精的传奇小说,《小莲记》《西湖游春》和《张华相公》等。几篇故事都写得比较精彩,而且可以明显看出受了《任氏传》的影响。《西湖游春》是一个传统的始乱终弃的故事模型,只不过女主角换成了狐女。穷书生侯生遇到了美丽的狐女独孤氏,一时间不仅有了美丽的妻子,还借助独孤氏的钱财做官高升。但独孤氏的狐女身份给了侯生薄情的借口,他并没有尊重独孤氏的感情,没有把她当作人来尊重。而独孤氏也同样因着狐女的身份超脱于贞洁观念之外,不但洒脱改嫁也惩罚了侯生。宋人尊崇义理,诗文小说中多带有说理的成分。《西湖游春》中引入了佛家的因果善恶报应的观念,非人类的狐女被辜负、被侮辱,而饱读圣贤书作为国家栋梁的书生成了反面。一方面,再次提出了人不如狐的观念,而且被比较的不再是女子的温柔贤惠,而是狐女与书生之间的人格、品德上的较量,也可以说,狐女的地位被提高了。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城市渐渐扩张繁荣,开始出现市民阶层,相应的市民文学也渐兴起佛教的循环报应思想一向在平民百姓中极有市场,它几乎就是朴素的市民观念的基础,狐精故事中掺入这样的思想,易被平民读者接受,也即世俗化了。狐女由之前文人公子案头的理想中的艳遇美梦中款款而来,慢慢向寻常百姓的家门靠近。
还有一篇故事《小莲记》,其中的狐女名叫小莲(不知是不是要谐音“小怜”)是一户人家买来的女奴,因为美貌聪明而被主人所宠爱,她的遭遇十分可怜,不仅被主人逼迫还因犯律被鞭打。狐女小莲没有任何的妖邪之处,她不仅不能危害主人,反而甘心承受着主人的欺凌,她甚至不能像独孤氏那样自由离开,更遑论保护自己。但即使如此,小莲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狐女,因为她进入了人类的家庭,成为家族生活的一员。
在《西湖游春》中,独孤氏的一片心意最终没有被珍惜,侯生在道义上对她的亏欠以丢官穷困作为代价,而感情上的亏欠却是无法弥补的了。而小莲则更为可怜,她的身份尴尬,是半婢半妾,更没有真情可言。相比之下,另一位狐女宋媛则幸福的多了,其实,但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宋媛的情况比之她的前辈要好多了。魏晋六朝时的狐妖承袭的是上古淫妇的名字“阿紫”,任氏与独孤氏则只知其姓氏、排行,小莲是个婢女,只有一个使唤用的小名,而狐女宋媛却是有名有姓。宋媛是另一部文集《云斋广录》中《西蜀异遇》中主人公,她的故事比较有浪漫意味。宋媛与书生李达道在花园相遇,以诗传情,李达道因为宋媛的才情而对她产生了爱情,后来经过一番波折,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李达道与宋媛花园相遇传诗定情的经历颇似《西厢记》,李达道最初爱上了宋媛的才华,是“爱其才而复思其色”[7],宋媛作为一个狐女,终于不再是狐媚惑人的形象,而以自身的气质、修养来吸引异性,李达道也不再是只贪恋美色、渴思艳遇的书生,而是一个有品格、有思想的正人君子。最为可贵的是,是李达道所说的“吾生之前,死之后,安知其不为异类”[7],人类与狐交往的种种情态,畏惧、新奇、不尊重或蔑视等,都是因为狐为异类,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李达道却认为物种都是天造,应该是平等的,就像文中之辞说的“万物盈于天地兮,莫知去来之因。谓大钧之可度兮,局变化之无垠。形非可以长久兮,造物与之而栖。周旋上下无不知兮,乃独栖此而不去者,盖以吾之有身。孕阴阳而更寒暑兮,是未离乎死生之津。凡物随缘而异观兮,然自宇宙言之,不含乎泰山之与微尘。彼动植与飞走兮,忽而化而为人。安知人之去世兮,不为木石之类、鸟兽之群?眷兹理之固然兮,则又何戚而何欣”[7]。好一篇众生平等的宣言,看来主人公李达道的名字确是名副其实,同时,这大概也是作者的想法。有了这样的创作意图,宋媛获得了在人间居住的合法身份与权利,以一个普通女人的身份生活着,侍奉公婆,伺候丈夫。但是书中极力渲染宋媛才情,她的诗作也没有一点淫邪之意,她就像一个标准的大家闺秀,进退有矩,而失去了狐女的活泼与生命力,就像野兽被豢养后没了野性一样。她最后的离去也比较突兀,竟是凭空不见了,她的离开就像出现一样离奇。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71.
[2]王立兴,等.唐传奇英华[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3.
[3]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35.
[5]李泽厚.美学三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99.
[6]林骅,等.唐传奇新选[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7]胡大雷,等.唐宋小说选[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