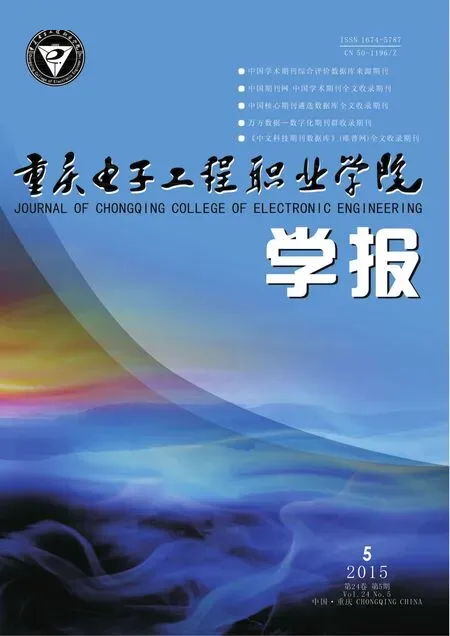香港电影中的“追寻”与“迷失”主题浅析
崔 颖
(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100875)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很长时期内,作为通商港口的香港只是一个拥有数百常住人口的小村庄,在行政体制上接受广东的管辖。1842 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给了英国。1898 年,中英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新界、新九龙被英国租借99 年,香港从此开始了近百年的殖民历史。
长期被英国统治的香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与祖国大陆在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上的区隔日渐明显,香港人对炎黄子孙的身份认同也受到了极大挑战。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香港成为了一座政治和文化上的“孤岛”。这种特殊的境遇造就了香港特殊的“无根”身份,“无根”也成为了香港独有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气质。在香港电影中,这种“无根”身份以充满悲情色彩的“追寻”与“迷失”的主题呈现出来。
1 “追寻”的主题表达
关于“追寻”的主题显现,可以追溯到香港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期——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变革,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社会文化开始出现明显的分野: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台湾则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偏安王朝”;而香港则开始从战乱中恢复元气,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此时的香港,由于作为“生母”的祖国大陆江山易主,变了颜色,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对立导致其与内地曾经紧密的联系被迫中断,其命运多舛的“无根”身份更加凸显出来,对自我身份、地位、角色的追寻也显得更为迫切。
在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中,出现不少以“寻亲”为主题的影片,这些影片充分显现出香港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心理。在胡鹏导演的《万劫孤儿》,珠玑导演的《孤星血泪》和《万里寻亲记》,卢雨歧导演的《苦海亲情》等影片中,主人公大多是背井离乡、流浪四方的孤儿,这些孤儿在对“母亲”或是“父亲”的苦苦追寻中慢慢长大。在这些“寻亲”主题的影片中,孤儿们都能够最终找到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家人得以团聚,对于自己身份的“追寻”问题似乎得以解决。但在现实生活中,尴尬的香港仍然没有找寻到自己的身份定位,“追寻”的主题也仍然继续在香港电影中得以延续。
这种延续在20 世纪70 年代后新时期的香港电影中以新的意象呈现出来,许鞍华电影便是个中代表。作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许鞍华不再以“寻亲”作为对自我身份追寻的意象,而是以“失母”构建起身份追寻的悲情故事。在她的影片中,母亲角色大多是缺场的:《疯劫》结尾处号哭的婴儿,联系着母亲的死亡;《女人,四十》开篇,疼爱女主人公阿娥、懂得人情世故的婆婆病逝,全家人于是面临着严峻的生活考验;在《客途秋恨》中,晓恩的母亲虽然健在,但她无法与母亲沟通,实际上她也是“失母”的。“失母”意味着母体的丧失,意味着身份的不确立,也意味着“无根”的飘离。
对身份的“追寻”伴随着香港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直到1997 年,回归大陆的香港才终于有了久违的归属感,当然,这种归属同时也伴随着阵阵的伤痛和迷茫。
2 “迷失”的主题表达
对身份的“追寻”源于自我的迷失。在漫长的殖民历史中,“迷失”成为香港“无根”文化的重要呈现。对“迷失”这一主题的显现仍然可以追溯到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黄金时期。在吴回的《败家仔》、李铁的《危楼春晓》以及楚原的《问君能有几多愁》等影片中,可以看到许多“迷失”意象的显影。
《败家仔》中,主人公邝世昌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世家子弟,整日无所事事,游走于舞厅、赌场,最后被父亲赶出家门,流离失所、穷困潦倒。影片中,邝世昌在复杂堕落的环境中迷失了自己,他所处的香港社会也同样在迷乱心性、迷失方向。《危楼春晓》则更具象征意义,影片以一座“危楼”以及楼中所住房客的命运,暗喻香港风雨缥缈、不知所去的迷茫现实。在《问君能有几多愁》中,影片则以斑驳陆离、迷离恍惚的香港图景,给人一种冷漠、无奈和迷茫的感受,喻示香港的迷失状态。
“迷失”的意象在许鞍华电影中同样明显。在《胡越的故事》的结尾处,胡越用船载着香消玉陨的沈青飘荡在海面上,茫然不知何去何从。《投奔怒海》最后,琴娘只身带着幼小的弟弟逃离祖国,黑夜中漂流在一望无边的大海上,不知所终。《极道追踪》的最后一个画面,呈现的是茫茫无际的大海中,一艘小船在蜡黄的天空下缓慢行进,渲染出一种强烈的“迷失”感。
在香港历史上,最具“迷失”色彩的时期是1984 年至1997 年的13 年间。1984 年,中英两国政府达成协议,英国在1997 年租借期满之后,把香港的主权归还给中国政府。在“母亲”身边漂泊了一个世纪的香港终于要回到以大陆为母体的中国大家庭。“回归”似乎意味着“无根时代”的结束,但是,长期的分离和阻隔,使得香港和大陆之间产生了诸多的分歧甚至对立。特别是香港在经济上的优越地位以及对政治上的迷茫,更是使得一部分香港人无法正视自己的“回归”。1997 年因此被这些香港人视为“九七大限”“世纪末日”,“末日心态”“没有未来”成为其主流心态,数十万港人移居他乡便是这种心态的典型体现。
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香港的“无根”身份和“迷失”心态不但没有因为回归的来临而消退,反而随之日益加剧,而无所不在的“末世情结”也成为香港文化的显要特征。这些“没有将来”的“末世情结”和“迷失”心态,在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特别是王家卫电影表现尤为明显。
王家卫崛起于20 世纪80 年代末,比徐克、许鞍华、严浩等“新浪潮电影”的领军人物出道晚了将近十年。不过,这并不妨碍王家卫的电影大师之路。从1988 年的处女作《旺角卡门》到2013 年的《一代宗师》,25 年里王家卫虽然只拍摄了十部影片,但几乎每一部影片都被奉为经典,被无数的影迷顶礼膜拜。在王家卫的十部电影中,《旺角卡门》(1988)《阿飞正传》(1990)《重庆森林》(1994)《东邪西毒》(1994)以及《堕落天使》(1995)拍摄于香港回归前,五部影片充满了身份、历史的迷失和末日的悲情,折射出香港独特的“九七”心态。
《旺角卡门》讲述的是黑道分子华和乌蝇在香港旺角终日过着打打杀杀的生活,后来华的表妹阿娥从大屿山出来治病,华和阿娥渐生情愫,但华为了帮助乌蝇刺杀证人,最后不得不走上败亡的结局。《阿飞正传》的故事背景是20 世纪60年代,讲述旭仔、苏丽珍、咪咪、歪仔、超等人之间的爱情或偶遇的关系,电影以旭仔前往菲律宾寻母失败而结束。《重庆森林》讲述的是两段不同的爱情故事:电影的上半部讲述当警察的何志武邂逅走私毒品的金发女郎,下半部则以一个警察为主线,讲述阿菲如何介入他的日常生活。《重庆森林》以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为蓝本,讲述东邪与西毒各自纠缠不清的爱情瓜葛。《堕落天使》则呈现的是几个杀手之间细微而又复杂的关系。
在这五部影片中,封闭的空间、充满压抑和忧郁情绪的暗蓝或灰绿色彩是它们在影调上的共同特点,这种封闭、压抑的影调营造出含糊的、不确定的氛围,透视出一种末世的、没有出路的景观。“末世”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这些影片中,时间、记忆成为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象。《阿飞正传》的开始,旭仔要苏丽珍永远记住“1960 年4 月16日下午3 点前的一分钟”,要她记住他,而他便可以让自己因为这一分钟的存在而永远停留在苏丽珍的记忆里,这和“九七大限”之前的港人心态正好吻合。
在《东邪西毒》中,时间与记忆更富象征意味。故事的人物都活在“记忆”的痛苦之中,而时间却无法把记忆抹去。影片中,张国荣不时的独白,看似简单的计时与计事,但其实却别有寓意:
——今年五黄临太岁,到处旱灾。
——初六日,惊蛰,每年这个时候,黄药师总会来找我饮酒。
——去年立春后,我一直没有买卖。
——初四,立春,那天黄历写着,东风解冻,说是一个新的开始……
——初十日,立秋,晴,凉风至,宜远行、会友,忌新船下水。
——十五,有雨,土黄用时,曲星,宜沐浴,忌出行。
——他走的那天,风是向南吹的,他故意逆风而行,我记得那天是十五,黄历上写着:失星当值,大利北方。
——立春之后,很快到了惊蛰,每年这个时候总有一位朋友来探望我,但他今年没有来。①
这些独白表面上是流水帐式的记录,但其中却包含着宿命的论调,因为他在记录人和事的同时,还特地强调了每个日子的吉凶。宿命的东西是无法逃避的,正如“九七”的到来无法逃避一样。
以时间概念凸显“末日情结”还在《重庆森林》里有突出体现。影片中,何志武失恋,女友拒绝与他见面,于是他便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要在5 月1 日自己的生日之前忘掉失恋的痛苦,为了记着这个日子,他每天都买一听5 月1 日过期的罐头。所谓“过期的罐头”,其实就是“到期的香港”,“九七”便是香港的到期时间,便是“终止”“结束”。在《阿飞正传》中,主人公旭仔最喜欢讲述一个无足鸟的故事:“听说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只可以一直飞啊的飞,飞得倦了,便在风里睡觉,它一生只可停一次,那就是它死亡的时候了。”“我以为有一种鸟生下来便没有脚的,一生只能在天空飞,其实这种鸟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因为它从开始便已经死了。”这种带有“顿悟”色彩的旁白既是对旭仔自我身份和命运的概括,也是王家卫对香港身份和命运的总结。在王家卫眼里,“末日”的香港就像无足的鸟一样,命运注定是悲情的。
陈果是另外一位记录香港“九七”心态和“末日情怀”的导演,与王家卫虚幻的“自我”表达不同的是,陈果把目光转向了现实香港的下层社会,在穷街陋巷中,展现香港人迷茫不知所措的末日心态和群体意识。
拍摄于1997 年的《香港制造》是陈果的成名作品,这部独立制作的影片几乎耗尽了陈果所有的财产,在刘德华的资助下,影片才最终得以完成。《香港制造》借两个生活在贫民窟的边缘青年男女,反映出他们无助的生命状态。主人公阿秋先后被父母抛弃,随着女友和好友的死去,找不到出路的阿秋开始以暴力发泄内心的不满,最后,阿秋死在女友的墓边,了结了年轻的一生。阿秋的悲观、游离和找寻不到出路,折射的正是回归前夕港人的迷失状态。
1998 年的《去年烟花特别多》表现的是回归之后,英国驻港部队解散,吴家贤等华籍军人退伍回家后,无法适应新的生活,在无奈、困惑和焦虑中,他们选择了犯罪的道路,最终以悲剧收场。影片的英文名为“The Longest Summer”,反映出港人面对回归度日如年的焦虑而复杂的心态。正如陈果自己所说那样:“这群华籍英兵的心态便正是香港人的心态。”②
除王家卫和陈果之外,“九七”带来的迷失心态在杜琪峰、韦家辉等人的作品中也时有显现。其中,“杜韦组合”(以杜琪峰、韦家辉为核心的电影创作小组)的作品尤为突出。在1997、1998 年两年间,杜韦组合拍摄了《一个字头的诞生》《两人只能活一个》《暗花》等影片。这些影片充满了不可抵抗的宿命色彩,悲观情绪随处可见,没有生机的灰暗影调也贯穿始终。同时,在这些影片中,时钟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反复出现,时间的限制和存在被刻意强调,“九七大限”之前后的焦躁和不安显露无遗。
3 结 语
因回归而带来的“九七阴影”曾伴随香港度过了近十年的时光,它给香港人造成的心理阵痛也许身处内地的同胞永远无法体会。但这种集体的恐惧和焦虑却对香港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回归十多年后,曾经的“九七大限”“世纪末日”已经烟消云散,内地与香港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紧密往来,“无根”的香港也开始向“有根”身份转变。尤其是2004 年内地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之后,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不论是资金、人才还是市场都已经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大部分香港电影人的事业重心都已北移。许鞍华拍摄了内地题材的《玉观音》《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以及话题作品《黄金时代》;陈果在《榴莲飘飘》中,也开始把故事延伸到内地的吉林,主人公阿燕在香港飘零许久之后,终于回到东北的老家;杜韦组合也开始摒弃了以往的阴冷、灰暗和不安,影调开始变得明快和乐观,《暗战》《枪火》《孤男寡女》《瘦身男女》《单身男女》等均是如此,杜琪峰2014年的内地题材作品《毒战》更是把华语警匪片的创作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只有王家卫仍然在《花样年华》《2046》和《一代宗师》里,在过去和未来的穿梭中进行着喃喃自语的追问和寻找。
总之,无论曾经有过怎样的迷失,香港终究要寻回历史,要从“无根”的追寻过渡到“有根”的成长,外出的儿子也终究要真正回到“生母”的怀抱。而香港电影,也会在不断的追寻中找到自己的归途。
注释:
①潘毅,余丽文.书写城市:香港的身份与文化[M].香港:牛津出版社,2003.
②孙慰川.论90 年代香港电影导演[J].当代电影,2002(2):68-76
[1]张江艺,吴木坤.映画神州:中国电影地域纷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李欧梵.寻回香港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王岳川.香港文化的后殖民身份[J].文学自由谈,1999(2).
[4]徐勇.移民电影与香港的身份表达及其困境[J].电影艺术,2010(4).
[5]艾晓明.后殖民处境与香港身分辨析[J].当代港澳,1996(1).
[6]陈向阳.后殖民时期再论香港身份[J].电影艺术,1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