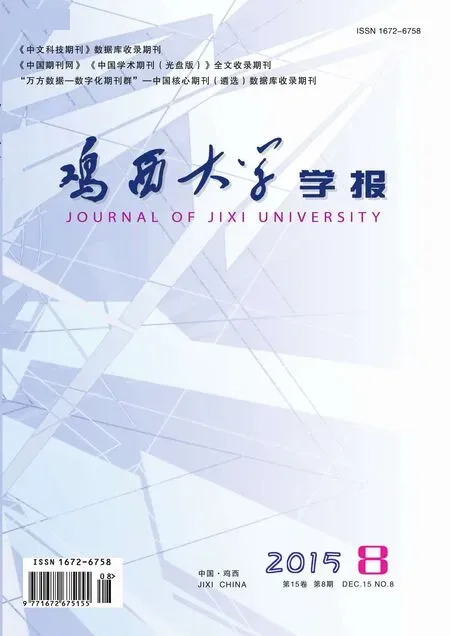《红高粱家族》英译伦理评析
董国俊
(甘肃农业大学外语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红高粱家族》英译伦理评析
董国俊
(甘肃农业大学外语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依凭对“高密东北乡”的独特叙事,莫言不仅获得了国内文坛主流作家的崇高地位,也赢得了国际文坛重要作家的充分认同。在葛浩文已译介的20多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近50部作品中,莫言的小说翻译最多。《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标识性小说,其英文版充分表征了葛浩文以“直译式意译”或“异化式归化”为原则的翻译伦理。
《红高粱家族》;葛浩文;翻译伦理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文坛,《红高粱家族》都是莫言的标识性小说,它在莫言的小说创作和国际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红高粱家族》初版于1987年,是由《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和《奇死》五个中篇小说组成的一部准长篇小说。该小说虽然在“结构上乏善可陈”,[1]但总体上有一个连贯的故事逻辑。其英文版由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并初版于1993年,是莫言在英语世界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本文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在词汇、语句、语段等方面的翻译策略为例,对葛浩文的翻译伦理做出评析。
一 “异质”词汇的翻译策略
所谓“异质”词汇,主要指中国文化中特有的那些文化意象与物象。葛浩文在翻译《红高粱家族》时,采用了以下几种基本的翻译策略。
1.直译法。直译法能够尽可能多地保留源语文化的特征,也能开阔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视野,从而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例1: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面看水面。(莫言,2007:6;下文出自该文献时只标识页码)①
译文:If not for the sake of the monk,stay for the Buddha.If not for the sake of the fish,stay for the water.(Mo Yan,1993:9;下文出自该文献时只标识页码)②
这是《红高粱》中“我奶奶”为了挽留罗汉大爷而说的话。“僧”与“佛”属于中国文化,但无需加注英语读者也能明白其中的涵义。
例2:(你简直是)鲁班门前抡大斧,关爷面前耍大刀,孔夫子门前背《三字经》,李时珍耳边念《药性赋》。(107)
译文:(like someone)wielding an ax at the door of master carpenter Lu Ban,or waving his sword at the door of the swordsman Lord Guan,or reciting 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at the door of the wise Confucius,or whispering the‘Rhapsody on the Nature of Medicine’in the ear of the physician Li Shizhen.(122-123)
葛浩文没有对“鲁班”“关爷”“孔夫子”“李时珍”这些中国文化名人做出过多注解,英语读者也能凭上下文猜测其义。这说明直译法不是显得过于生硬的话,既能传达丰富的含义,也能被异域读者所接受。
2.转换法。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使得他们在生活中所倚重的东西也不会一致。转换法能够把源语中带有深厚文化色彩的词语转换成译入语中带有同等文化色彩的词语。
例3:买卖不成仁义在嘛!(23)
译文:Even if you can’t agree,you mustn’t abandon justice and honor.(27)
我们生活在讲“仁”谈“义”、说友情道交情的文化语境中,而西方文化却注重社会生活中个体的“正义和荣誉”。但在《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另一处,葛浩文则把“咱们是买卖不成仁义在”(179)进行了意译——“we can’t make a deal doesn’t mean we’re not on the same side”(199)。笔者以为,对“仁”和“义”的英译,转换法比意译法更加确切。
3.译注法。译注法是通过增词或注释的方式进行语言转换,这既能保留源语中特有的一些事件、人物、典故等所携带的文化色彩,也能降低异域读者对原文的理解难度。
例4:那天是清明节。(34)
译文:It is Qingming,the day set aside to attend ancestral graves.(39)
例5:这条公路,是日本人和他们的走狗用皮鞭和刺刀催逼着老百姓修成的。(7)
译文:Japanese and their running dogs,Chinese collaborators,had built the highway with the forced labor of local conscripts.(10)
例6:但这些人住在村里时,搅得鸡飞狗跳。(9)
译文:But when they were quartered in the village,they had stirred things up so much,with chickens squawking and dogs yelping.(12)
如果把中国人祭祀祖先的传统节日“清明节”音译出来,就需要加注。“走狗”在百年中国屈辱史中已沉淀为妇孺皆知的“汉奸”之意,但如果没有“Chinese collaborators”的注释,西方读者恐怕只能把“running dogs”认为是“奔跑的狗”。同理,如果没有“they had stirred things up so much”一句,英语读者也不会明白“这些人”干嘛与鸡狗过不去。
4.意译法。在用转换法和译注法无法传达源语的文化意义或者在译入语中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词语来翻译源语时,译者就会选择意译法。
例7:奶奶在三天之中参透了人生禅机。(62)
译文:Grandma unlocked the mysteries of life in three days.(70)
例8:你打开天窗说亮话。(178)
译文:Let’s open the skylight and let the sun shine in.(198)
再如把“曹青天”(100)译为“Upright Magistrate”,(115)“不惑之年”(149)译为“an age of confidence”(169)等,这虽然造成了源语文化意象的某种缺损,但也是不可为而为之的一种译法。总体来讲,《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以直译法为主,意译法的运用并不多。
5.音译法。译者面对文化“空白”或“空缺”,采用音译法既能保存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也能丰富译入语语言文化。
例9:我奶奶是否爱过他,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都与伦理无关。(10)
译文:Whether my grandma ever loved him or whether he ever lay down beside her on the kang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orality.(14)
此译文中“kang”与kowtow、kongfu等词语一样,已广泛存在于英语文献中。
6.造词法。由于“英语是欧洲语言中变化最大,词汇成分最复杂,词汇量最丰富的一种语言”,[2]所以在其15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广泛吸纳了其他语言中的大量词汇,这当中自然包括汉语词汇。葛浩文在翻译《红高粱家族》时也自造了新词。
例10:哑巴是余司令的老朋友,一同在高粱地里吃过‘拤饼’的草莽英雄。(8)
译文:Mute was one of Commander Yu’s old bandit friends,a greenwood hero who had eaten fistcakes in the sorghum fields.(11)
“拤饼”是山东方言,原文中的“擀拤饼”意为做一种食物,而“吃拤饼”则为当土匪。这样,葛浩文面对“拤饼”的“不可译”,便选择了自造新词“fistcakes”。
7.混合法。如果以上几种翻译策略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译者就会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法进行翻译。《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也表现出这一特点。比如,“观音”(75)译为“Guanyin bodhisattva”,(86)这是音译与译注的结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75)译为“Marry a chicken and share the cop,marry a dog and share the kennel”,(87)这是直译与译注的结合。另外,《红高粱家族》中某些人名的翻译也具有混合法的特点,比如“刘罗汉大爷”(Uncle Arhat Liu)、“曹梦九”(Nine Dreams Cao)、“江小脚”(Little Foot Jiang)等等。
二 语句的增删与改写
莫言小说的“感觉化”特征异常突出,其词类的活用、反常的搭配、修辞的陌生化以及语言的写意化、图像化、幻觉化、通感化等现象也新鲜饱满。这一切在英译本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然而,“莫言先生是个细腻美、粗犷美、朴素美并存的作家”,[3]其小说在语言上的刻意、勉强、多余等病灶也显而易见。葛浩文凭借其深厚的文学修养,在《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增加了个别词句,也省略了部分语句,还改写了一些语句,从而使译文在语言上具有再创作的特色。
1.词句的增加。葛浩文的译文以严谨而讲究著称于国际翻译界,他在翻译《红高粱家族》时增词添句的现象不多,但有一处增词翻译显得非常精准。
例11:我们村里一个九十二岁的老太太对我说: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余司令,阵前战,一举手炮声连环。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9)
译文:An old woman of ninety-two sang to me,to the accompaniment of bamboo clappers:Northeast Gaomi Township,so many men;at Black Water River the battle began;Commander Yu raised his hand,cannon fire to heaven;Jap souls scattered across the plain,ne’er to rise again;the beautiful champion of woman,Dai Fenglian,ordered rakes for a barrier,the Jap attack broken.(13)
这是在《红高粱》第二节中,“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本句被省译),“我”在村里进行调查时,碰到的一个老太太对“我”说的话。而这个老太太押韵(韵母为an、ian、uan)的话却明显是一段说唱词。译文中增加了“to the accompaniment of bamboo clappers”这个有趣的分句,“说唱词”也以/n/为韵进行翻译,这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手持竹板进行说唱表演的民间老艺人的深刻印象。
2.语句的删减。《红高粱家族》英译本删除了原文中的部分句子,而这种删减又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冗余信息”,它在汉语系统中并非多余但在英语系统中显得累赘,这种删除在《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多处可见。第二种是纯粹与上文重复的内容,比如在《红高粱》第四节中有这么一句——“我家在抗战前种植的罂粟花用蟹酱喂过,花朵肥大,色彩斑斓,香气扑鼻。”(20)它与第一节中的相关叙述是重复的,因而被合理地省译。第三种是读者意识的需要,中国先锋小说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喜欢在文本中站出来说话,对故事情节做一补充或评论,而那些补充或评论属于小说技法范围,多数时候对文本的故事情节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为了追求译文的精炼,葛浩文省略了一些语句,比如《高粱酒》第四节中有一段交待余占鳌“迟迟未入绿林”(90-91)的原因、第五节中有几句补叙了曹梦九与其他官员的“名声勋业”、(98)第六节中有一段“作者”对“我奶奶”的性格与命运进行了评价,(116)这些都在译文中被省略。
另外,与西方读者的意识形态有明显冲突的叙述,也在译本中被省略和省译。比如,“她就是造物主”(116)一句被省略;“父亲对我说过,任副官八成是个共产党,除了共产党里,很难找到这样的纯种好汉”(52)一句,只是被省译为“Father told me that Adjutant Ren was a rarity,a true hero.”(59)。
3.语句的改写。许钧曾对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说:“一个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4]那么,莫言遇上葛浩文就是名副其实的“一场艳遇”。也就是说,莫言在海外的知名度离不开葛浩文这位译评家精湛的翻译以及他的激赏与推介。例如,《红高粱》原文中有一句是:“奶奶右眼看着吃拤饼的人,左眼看着轿夫和吹鼓手。”(41)这种描写并不符合人的生理常态。因此,葛浩文把它改译为“Her gaze traveled from the man to the bearers and musicians.”(48)但是,百密难免一漏,葛浩文也有疏漏之处,比如“汗滴禾下土,心中好痛苦”(11)一句,被错译成了“(that)soaked up their sweat and filled their hearts with contentment.”(15)这使文意发生了根本改变。笔者以为,可把“contentment”一词替换为“torment”或其他词语。
三 语段的重新划分与融段
《红高粱家族》是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在叙述话语上,文本时间(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之间出现了大错位,包括预叙、倒叙、插叙、补叙等时序关系尽情涌现,叙述的步速(时距)被有意加快或放慢,叙述频率也得到了格外的重视。特别是叙述视角的转换、叙述者的更换以及多层次叙述者的设立,更是中国先锋小说惯用的技法。这满足了先锋作家从多个角度表现人物、试图把一个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展示在读者面前的需要。
然而,中国先锋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西方读者的关注和文学界的肯定,并非是由于其小说技巧而是源于其小说的内容和主题。因此,《红高粱家族》中的预叙、倒叙、插叙、补叙等叙事手法在其英文版中得到了一定的调整。比如,《红高粱》第四节讲罗汉大爷和两头骡子一起被鬼子和伪军捉走,当晚平明时分,枪声从东南方向传来。原文接下来先是一部分环境描写,接着叙述了父亲和我奶奶听到枪声不久被日本兵驱赶到河南岸路西边。但在译文中,把父亲和我奶奶被驱赶到路西边的情节放在了那段环境描写之前。再如,在《红高粱》第五节的译文中,把原文第三自然段拆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移到了原文第二自然段之前,而后一部分放在了原文第二自然段之后。这种为了情节的连贯性而重新做出的分段与融段,能够让英语读者获得一种比较清晰的故事线索,但也不会影响原文的艺术效果。
葛浩文在接受一次访谈时说,国外编辑在接到一部译稿之后,最喜欢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对译稿的删减;二是对小说结构的调整。[5]由此可见,一部翻译小说的最终形成,在文本内部就暗藏了作者、译者和编辑之间的争议、协商与妥协。由此看来,虽然翻译文学的主体是译者,但是翻译文学的最终形成并非全由译者所操控。有意味的是,以莫言、余华、苏童等为代表的中国先锋作家,曾经正是以小说的“非线性叙事”“非稳定结构”“非逻辑表达”等形式技巧赢得了国内文坛普遍的赞誉,也给中国小说创作注入了并非原创的“创造性”特质。而在葛浩文的译本中,那些形式技巧又被部分地打回了原形,这也许是西方文学界并没有多少充足的理由而看着中国小说形式技巧的模仿、借鉴或探索的原因所致。
四 结语
文学翻译是一片广阔的文化生产场域,“原文中心”“译文中心”或者“译者主体”的翻译理论,表征着这片文化生产场域的复杂性。“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以及它们在汉译英或英译汉过程中的复杂缠绕,似乎表明了文学翻译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慢慢长路。从上文《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具体的翻译策略来看,葛浩文的翻译伦理表现为词汇省略、结构调整、删除议论、改变节奏等特质。这是一种“直译式意译”或“异化式归化”的翻译原则,一方面尽可能多地保留了源语中的异质元素,另一方面又最大限度地遵守了译入语的文化规范。
注释
①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②Mo Yan.Red Sorghum:a Family Saga[M].Tr.Howard Goldblatt.NY:Viking Penguin,1993.
[1]莫言.小说的气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155.
[2]陈安定.英汉比较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1.
[3]黄惟群.中国当代文学鼎盛期再望[J].南方文坛,2008(5).
[4]高方,毕飞宇.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家毕飞宇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2(3).
[5]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2(1).
Translation Ethics of Red Sorghum by Howard Goldblatt
Dong Guo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Lanzhou,Gansu 730000,China)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narrative of Northeast Gaomi Township,MoYan has become a prominent writer at home and abroad.Among nearly 50 translation works of Howard Goldblatt’s,MoYan’s novels are the most translated in more than 20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Red Sorghum,as a representative novella,is fully characterized in Goldblatt’s translation ethics of literal liberalness or foreignizing domestication.
Red Sorghum;Howard Goldblatt;translation ethics
H315.9
A
1672-6758(2015)08-0090-4
(责任编辑:蔡雪岚)
董国俊,博士,讲师,甘肃农业大学外语学院。研究方向:翻译文学与比较文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小说英译及接受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C751015)阶段性成果。
Class No.:H315.9 Document Mar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