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古藏文文献若干问题释难
——访藏族著名学者卡岗·扎西才让
拉毛太多杰
(①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②青海省果洛州民族师范专科学校 青海果洛 810500)
吐蕃古藏文文献若干问题释难
——访藏族著名学者卡岗·扎西才让
拉毛太①多杰②
(①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②青海省果洛州民族师范专科学校 青海果洛 810500)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从事古藏文文献、吐蕃史、梵文等藏学研究工作二十余年,尤其古藏文文献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在国内外藏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文章以古藏文文献为主线,结合运用藏文和梵文中词语的演变规则,着重探讨了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方法,以及敦煌文献对于研究古代藏族历史文化和西域民族历史文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通过对古藏文文献进行探讨认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藏族历史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论证。
古藏文文献;文献价值;研究方法
卡岗·扎西才让是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授课的同时,利用闲暇时间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曾多次参加国内外藏学研讨会,尤其在吐蕃古藏文与于阗关系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部分学术论文得到国内外相关同仁的肯定,其学术成果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笔者依照其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中阐述的学术观点,围绕吐蕃古藏文文献的研究成果,对他本人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访谈。
笔者:教授,您好!这些年您在授课的同时,撰写了很多有关古藏文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同。我们曾几次想请教您有关吐蕃古藏文文献方面的疑难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如愿。今天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给我们这次访谈机会。首先,我们想知道您是何时涉足藏学研究领域的?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上世纪80年代藏文化各领域开始复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建立后不久,《中国藏学》杂志问世。1990年,我的拙作《“安多”等地名考释》一文在此刊上首次发表,从此我便开始了藏学研究工作。
笔者:我们阅读了您的很多论文,如《热萨和拉萨地名初探》、《论公元7~8世纪吐蕃和于阗之友好关系》、《与藏王赤松德赞登基相关的若干历史问题考释》、《敦煌文献P.T849——莲花生大师传记研究》、《敦煌文献P.T849——行大乘佛法之赞普称谓研究》、《敦煌文献中“马重”和“集巴城”等地名与安多卡岗地区地名比较研究》及《昌珠寺寺钟铭文及达扎鲁恭碑文中的部分误抄内容补正》等,您的大多数学术论文都与古藏文文献紧密结合。目前,藏学界很多人在研究古藏文文献时,对于“古文”(和“古词”()二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老师您是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和区别的?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古文的来源从大的方面而言,是指未经后人改动的古代文献,主要集中在吐蕃时期至11世纪期间。譬如敦煌写卷、金石铭文、摩崖石刻、木简等。从西藏各地和阿里托林寺等地发现的古藏文写本经卷分析,敦煌出土的写卷属于吐蕃当时的通用写本,代表了这一时期内的藏文字历史进程。这些文献虽与后期的佛经文书相比数量较少,但从古文献本身而言,其学术价值无法估量。这些写卷体现了古藏文文法和语法结构的特征,部分词和词汇在现有的各种词典上无法查找,对于考证其内涵和外延带来一定难度。因此,当时从事研究这些写卷的研究者对其称为“古文”和“古词”,两词交替使用,所指一致,特指这些古文献。藏语口语中有很多古词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但在书面语中较少使用。就分裂割据之后的文献及近代著作中出现的一些古词来说,“古文”中势必包含有“古词”,但很显然“古词”并非都是“古文”。我经常将敦煌写卷和古代碑文等统称为“古文”。现在,很多学者根据古文的不同特点称其为“古词”、“古文”、“写卷”、“摩崖石刻”、“碑文”和“吐蕃文献”等,这些称呼均特指古代文献。
笔者:据我们所知,您曾在北京参与编辑《敦煌古藏文藏汉双解词典》时,有机会与王尧教授等学者研习古藏文,期间接触了很多古藏文文献。我们在阅读您的作品时发现您很重视敦煌古藏文文献,尤其对P.T960文献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您可否依照自己的研究成果简要阐述一下P.T960写卷?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写卷P.T960共有114行,其主要内容是于阗兴佛和灭佛的历史事实。写卷中载:“佛法伊始至一千七百三十年,自萨诺王()至于阗王赞列()之间,共传五十六代王”;在《丹珠尔》中的《于阗授记》中则记载为“萨诺王最初登基执政于阗至于阗王赞桑赞()期间,共传五十六代王及其一个摄政王”。以上两种文献中除了于阗王“赞列”和“赞桑赞”的名称及“一个摄政王”的记述稍有不同外,其余内容基本一致。又如《阿罗汉根敦群培于阗授记》中记载有“于阗王赞列时期聚集于阗的堪布们”的字样也可知最后一位王的记述与以上文献一致。因此,不难发现,敦煌出土的写卷P.T960和《丹珠尔》中的记述,其来源基本一致,源自同一母体。
写卷P.T960中的“佛法伊始至一千七百三十年”的记载对于佛法何时始传于阗的年代及考证方面造成了混乱。但在敦煌P.T45v中的第216行“義་和P.T41v中的20行“”,P.T38v中的14行“”之等都是“”的写法和读法。根据纳唐梵文读法,在印度东部“纈羋”读成克什米尔的“繳繸纈”音可知,敦煌写卷采用了克什米尔的读法和写法。另在阿里发现的手写残片中所载的”等字样也与敦煌写卷中的梵文书写方式近似。依据后弘期大译师仁钦桑布和俄·勒贝西绕等前往克什米尔学经取法及12世纪至西藏的上座部学者班智达释迦室利等可知,敦煌写卷P.T960的年代计算方法符合班智达释迦室利的上座部计算法。根据上座部计法,释迦牟尼佛诞生于公元前624年,三十六岁始转四谛法轮。如依照这一计法,授记中“佛法伊始至一千七百三十年”则指的是公元1145年,也即公元1145年佛法始兴于于阗。又据《弟吴宗教源流》记载于阗的诸多堪布们将于阗王赞列登基之年确认为兔年,而兔年则为公元1147年,此推算与P.T960写卷的记载仅相差2年。因其故,敦煌写卷P.T960内容中对佛祖的诞辰和圆寂,始传佛教的年代等问题的考证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笔者:我们都知道您撰写的《藏族古文献所载有关于阗地区的历史资料解析》一文获得了2010年的珠峰奖,此文主要依据《于阗授记》和敦煌写卷P.T960两个文献进行了论证,该文章主要解决了哪些学术问题?以上两个文献之间有何关联?

笔者:除敦煌写卷P.T960外,我们发现您的文章经常引用敦煌写卷P.T.849文献。敦煌写卷P.T.849的主要内容可分为梵文和藏文对照词汇,梵文的元音和辅音,吐蕃部分赞普及印度等国国王修持大乘佛教成为法王,历史人物传记四个方面。因此,以往的研究者把此卷视为梵文和藏文的对照词典,认为《翻译名义大集》是在此卷的基础上产生,成为公元8至9世纪藏地已有梵文和藏文对照词典的文献来源。老师您对此卷的研究中主要论述了哪些问题?


笔者:藏文文献中词的演变,对于藏学研究的各领域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老师您具有深厚的藏文和梵文基础,而且撰写了很多梵文演变藏文的文章,您对于梵文在藏地的兴盛持有什么样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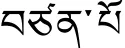
笔者:您在多年的古文献研究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论证问题时,经常从文献、逻辑、例证三方面进行考证说明,而且把实地考察视为首要,能否扼要说明实地考察的重要性?

笔者:老师您在研究过程中把实地考察作为重中之重,不管路途艰辛,遵循史料线索前往考察,这种执着的学术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听说2011年您曾前往阿里实地考察,在阿里考察期间您有哪些学术收获?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以前由于阿里交通不便,很多文化遗迹点不通车,但现在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建设得也比较好,有利于实地考察。阿里对藏族历史文化而言,犹如第二个敦煌。一则此地是佛教后弘期学者聚集地;二则岩洞文化从印度犍驮罗兴起后传至新疆、敦煌及阿里地区。从现有阿里的大小石窟及大量壁画唐卡艺术分析,不逊于敦煌石窟文化。阿里有些寺院的佛经藏书也很可观,我们在托林寺转经路上发现了几个早期梵文写卷,这些文献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如果不实地考察阿里,不仅与这些佛经写卷无缘,对其研究也只会停留在文本研究层面上。从古格和科加寺的历史人物分析,后弘期的很多高僧大德都到过此地习法传佛,譬如译师仁钦桑布、拉喇嘛意希沃、绛曲沃、俄·洛丹喜绕、阿底峡大师、纳措粗墀杰哇、仲敦巴等。因此,此地不仅遗留有诸多写本,而且学术价值极高。譬如出现在吐蕃时期桑耶寺碑文中的热萨()一词,后期的很多史册中都认为该词的涵义指以山羊驮土填卧塘湖而得名,且此说法至今广为流传。从阿里古格遗址中找到的因明著作残卷中有“”的记载可知,“热萨”一词演变为“拉萨”一词的过程。另外,梵语“”早期被读作“”,萨班在《音韵组合()》里指出“”应读作“”。阿里科加寺的一张残片上记载为“”,由此可知,在阿里“”写作“”,敦煌文献中也有“”的写法。在安多牧区将父亲称为“”,或在农区将哥哥称为“”。因此,从一词多义的用法分析,梵文“”的读法遍及藏区,词义也是指善或好之意。卫藏语“”的含义与“”的意译一致,安多语“”也被认为是梵文“”的变音。现在安多语中“”一词被视为方言而未列入书面语,既然有词源就应该归入到书面语。通过对阿里的实地考察发现敦煌和藏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在同一平行线上,安多口语中“”在卫藏方言中意为“取胜”的“”,纳唐言中的“”在词语前或尾出现时应与藏文读法一致。竹巴·白玛嘎布的《竹巴教法史》中记载了“”在不同的地域和时间都有所演变,表明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相似或相等特征。如“”都是“”的演变,源自于梵文的“”一词,“”意为王。以前的有些史册中记有“”,古藏文中也有“”的记载,前者是“”加了上加字而形成,后者是“”中的“”演变为“”,加人称格构成“”一词。后来逐渐演变为饰有前加字和上加字的写法,譬如“”等等。如此通过实地考察,在比较研究分析基础上,方能解决藏语言及文字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笔者:在论证自己观点的过程中,老师您提到文献的真假需谨慎引用。据我们所知,藏学界中有些学者不太认可敦煌文献和木简等文献,老师您对此有何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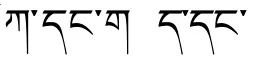
简而言之,质疑是研究者寻找真理的伴侣。敦煌文献的时间段被认为是11世纪左右,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可信度,但对于聂赤赞普至松赞干布等的历史记载不一定完全无误。如果唯独以敦煌文献中的记载为真实的历史,把同一时期或后期著作中与敦煌文献记载不一致的地方认为是虚假文献,极易导致偏见。参考文献的真假需从多方面进行甄别研究,我虽然很重视敦煌文献的价值,但在研究过程中对很多文献的内容产生过质疑,尤其对后辈研究这些文献而得出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产生过质疑。由于文献历史悠久,词和词汇的用法有很大的演变,而且还有很多词和词汇在各种著作和词典中很难查找。但是,也不能因为敦煌文献中的部分旧词而对文献本身产生质疑。完全否认文献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且容易误导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大多数藏文历史文献中提到了吐蕃时期的年代和社会现象,但都不如敦煌文献P.T.1288写卷,这份写卷中详细记载了每年发生的大事。这些文献如此宝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撰写于一千年前左右,后人没有篡改,属极其难得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具有一定时期的文字特点,与一般文献相比其文献价值极高。
笔者:现阶段,藏文化研究者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建立了很多藏学研究机构。研究领域和水平也在不断扩大和提高,开始向纵深研究发展。老师您对藏族历史的研究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在古藏文研究方面。您认为藏学界在古藏文研究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仍有哪些不足之处和需要注意的方面?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对我而言,古藏文研究领域内还未取得较好的成果,但在研究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和研究方法。首先,在研究古藏文时,需认真搜集论据,谨慎研究相关文献,挖掘新文献或根据现有的历史文献寻找质疑点。很多学者对敦煌文献做过研究,但至今仍有一些写卷的内容不够清晰。作为研究者,一定要理解文献及史料研究价值,掌握文献价值需要一定的实践过程。初次接触文献时要了悟文献内容、思考文献价值,通过反复思考研究后对文献进行深入理解,对于疑点要进行再三反思和分析。同时,需反复查阅相关文献对疑点进行论证阐述。作为研究者,当我们初次看到文献时总有想写这样或那样一篇文章的冲动,这仅仅是一种感性认识而非理性认识,一篇好的文章需要多年的研究准备。对于问题要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思考,解开疑虑后仍要对论点和论证进行不断思考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方可写作。写作过程中同样会遇到很多问题,需进行反复查阅文献和多次修改,这也是深入理解文献的一种过程。有些人对文章不进行修改,甚至忽略年代和随意使用新名词,尤其在汉藏翻译中随意性不能太强,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影响文化的发展的。因此,热爱和学习一种文化时,要将研究和讨论相结合,通过讨论研究,就能及时发现自己的观点是否成立。以往的学者们给我们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理解消化这些文化遗产的第一步是要懂得语言。如果不懂语言和文化习俗,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无法进行深层了解的。在熟知语言文字基础上进行写作,且语言文字得符合语法规则和历史事实。其次,藏学研究过程中需要对研究课题是否具有学术价值要准确判断,很多人对研究现状不闻不顾,容易步入重复研究之路。如康嘎·次成格桑在1985年发表的史册《前宏期宗教辨析明镜》中引用了敦煌文献中“马年赞普赤松德赞生于扎玛,母后芒在蒙之薨,是为一年”的记载,此文否定和论证了藏文史册中赤松德赞为金城公主所生的说法,但后来的很多学者做了重复研究。我认为学术论文和编书是有区别的,编书可以将相同主题的诸多作品合编,但学术论文表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通过参考文献表述观点,以一门学科方式表述前人未提及或未解决的突出问题。以论点为基础表达不同的观点,没有观点和论点则不成论文。论文的另一个特点是注解,即注解疑难问题及标注引用文献。1950年之前的很多藏族学者的著作都无注解,这是一种旧的惯例,就像佛教理论著作中普遍引用的是《五部大论》,虽无注释可读者能知晓。但今非昔比,现在的学术著作需要参考和引用各种文献,有些文献闻所未闻。因此,需要用注解来说明,如果没有注解就不能有效地支持文献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笔者:谢谢!老师您在古藏文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也是藏学界取得的学术成果。最后我们想知道,您在今后的藏学研究过程中将会注重哪些研究方向?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我的研究方向不是很固定,在学习和工作环境中会产生一些灵感,随兴趣而定,但大致还是在古藏文研究方面。通过查阅古藏文文献能使人见多识广,能发掘到很多新文献及思路,文献指引新的研究内容,碰到什么样的文献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研究兴趣,因而无法中断研究工作。我的很多研究构思都是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产生的。
笔者:老师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非常感谢!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顺心,扎西德勒!
On the Ancient Tibetan Literatures of the Period of Tubo-An interview of with Kagang·Tashi Tsering,a famous Tibetan scholar
Lhamo Tai①Dorje②
(①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②Guoluo Ethnic Teacher School,Guoluo,Qinghai 810500)
Professor Kagang·Tashi Tsering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ancient Tibetan literatures,the history of Tubo,Sanskrit and so on for more than 20 years,and his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Tibetan literatures have a certain influence in Tibetan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and Sanskrit words,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cademic value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Dunhuang literatures,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Dunhuang literatures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 western ethnic nations’.Moreover,the value system of the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in China,a multi-ethnic country,is studied and demonstrated through ancient Tibetan literature research.
ancient Tibetan literatures;literature value;research methods
10.16249/j.cnki.1005-5738.2015.01.008
G256.1
A
:1005-5738(2015)01-053-08
[责任编辑:拉巴次仁]
2014-08-11
拉毛太,女,藏族,青海海南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经济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