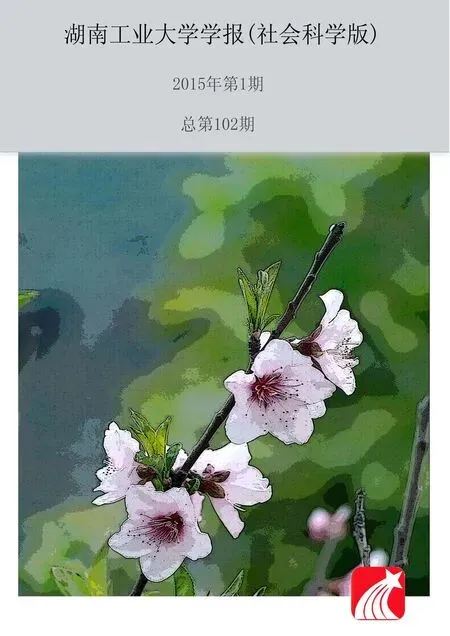论严羽的诗学体系*
——回归《沧浪诗话》的文本
李三达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08)
论严羽的诗学体系*
——回归《沧浪诗话》的文本
李三达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08)
严羽《沧浪诗话》以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尤其是禅宗理论为基础,对一系列诗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继承并发展了“以禅喻诗”的理论模式,并在此之上建构了一个涵盖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鉴赏论的诗学体系,对后世王士祯等人的诗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诗缘情;兴趣说;妙悟说
严羽的《沧浪诗话》不仅仅只是一本诗话,书中真正意义上的诗话部分(即其中诗评的部分)并不占重要地位。严羽的独创性集中于开篇的《诗辨》中,内含许多诗学理论。对于其中的观点是否真如严羽所说“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余唾得来者”(《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以及他是否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学界已有诸多定论。无可置疑的是,严羽所拈出的“妙悟”说、“以禅喻诗”说都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诗歌批评家和创作者,这也形成了后世学者不从文本出发而以神韵、格调、性灵理解严羽的基本论调。由于中国缺乏西方体系化论著的学术氛围,因此《沧浪诗话》也如溪水中的沙金一般,只有在仔细的检验后才能发现其内在的闪光点,而西方已建构的逻辑体系则正如显微镜一般有助于我们的仔细观察。
一 诗学本体论
西方哲学中无论是本体论或是存在论,所关注的都是外在于主体的世界,而对于这个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being-in-the-world),主体没有丝毫改变的能力,从出生的那一刻起,甚至在人类出现之前,这就是一个既有的事实。同样地,严羽所关注的并不是在现存的诗歌中总结出诗之所以为诗的本体,而是在于通过古诗去述说诗所应是,而这一述说的根据来自于他的审美经验和判断立场,众所周知,这一立场在相当程度上即是江西诗派的反面。所以,严羽要述说的是:在他的审美判断下如何才是“理想的诗歌”。
(一)“诗缘情”——诗学本体论的继承
严羽通过回归诗歌的“情性”传统来批驳江西诗派的互文性游戏。《诗辨》云:“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别材、别趣之说道尽了严羽眼中的诗何以为诗。严羽此处是就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而言,总结起来江西诗派主张“取陈言入翰墨”“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也就是注重将前人的文本化用、推陈出新,这无疑是一种很朴素的互文性(intertexuality)思想,尽管这种思想在当时语境下不大可能发展出作者之死这一必然的结论。诗歌的创作沦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呼应,由于脱离了客观世界引发的感性生命,所以诗歌也变得更关注对于同样沉溺在文本海洋中的“理”的阐发,因此“书”之为“材”促成了“理”之为“趣”,两者相辅相成完成了文本间性的游戏。严羽认为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而这些诗歌“虽极天下之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这说明严羽希望通过溯源诗在源初状态中的存在方式来逃离互文性游戏。
在他看来,“诗者,吟咏情性也”,诗之“别材”应继承传统的儒家诗学主张。这一点前人已有阐发,如张宗泰谓:“余则以严氏所谓别材别趣者,正谓真性情所寄也。试观古往今来文人学士,往往有鸿才,博通坟典,而于吟咏之事,概乎无一字之见后,所性不存故也。”[1]36这种情性不是在文本之间游戏,而是面对客观世界的生命感发。但是,严羽并不是简单地继承“诗言志”的说法,而是对“诗言志”进行了阐发,他认为“兴趣”才是诗歌的本质。
(二)“兴趣”——诗学本体论的深化
在一定程度上,严羽所谓的“情性”,其实就是后文“兴趣”的本质,而以“兴趣”说为核心的诗学就是严羽所发展的诗歌本体论,他的这一提法是对儒家传统的阐发。宇文所安认为:“从读者的角度谈文本的特质就是‘兴趣’:它是一种感染力,它激活了文本,同时抓住了读者。”[2]440这是对严羽的严重误读,而且是典型地重造了一个虚幻的意图谬误。因为《诗辨》中云:“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果严羽将兴趣归为读者,那严羽为何会指明兴趣的发出者是“盛唐诸人”?实际上,严羽关注的是作者从周围世界感发兴趣,并将这种“兴趣”融入文本的过程,而不是读者反应的过程。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赋、比、兴”传统来看,“兴”者诚如《诗集传》所言:“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而对于“趣”,则可参照叶适《水心集·跋刘克逊诗》:“怪伟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言语之外。”[3]另外,与严羽交好的戴复古在《赠二严诗》中的《论诗十绝》谓:“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这都说明,“趣”指向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才会说:“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许印芳《沧浪诗话跋》云:“严氏虽知以识为主,犹病识量不足,僻见未化,名为学盛唐,准李杜,实则偏嗜王孟冲淡空灵一派,故论诗唯在兴趣,于古人通讽谏、尽忠孝、因美刺、寓劝惩之本意全不理会。”显然许所以为的“趣”则全然是禅趣,所以才会指责严羽于美刺、劝惩无所理会,殊不知倘若此处趣即是禅趣,那后文“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也是禅趣么?因此,此所谓趣乃是指读诗反复终篇,知道“着到何处”,并且又并非直陈其着落处而应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兴”是指具体客观的事物指向物象以外的抽象所在,这种所在即是人的情性,“趣”则是对这种情况的描摹。这种情性的流露并不是粘滞的,如果直白地通过语言来陈述自己的情性并不能成为诗,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谈到:“王济有言:‘文生于情。’然而情非文也。性情可以为诗,而非诗也。诗者,艺也。艺有规则禁忌,故曰‘持’也。‘持其情志’,可以为诗;而未必成诗也。”[4]107所以,严羽认为“兴趣”的关键在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正意味着不显露地从具象指引到抽象,因此隐藏在诗歌语言中的不只是具象还有不着痕迹的抽象的意和性情。这一点已经非常接近象征主义了,这也是钱钟书先生不断在《谈艺录》中将严羽与白瑞蒙(Henri Bremont)以及瓦莱里(Valeri)相比较的原因。
(三)郭绍虞对“兴趣”的误读
从这个角度看来,郭绍虞对严羽的批评也是脚跟未点着地的。他首先引朱庭珍《筱园诗话》指责严羽:“挟枯寂之胸,求渺冥之悟,流连光景,半吐半吞,自矜高格远韵,以为超超玄著矣,不知其无物,转坠肤廓空滑恶习,终无可医也。”并且认为这句话“正指出了这种脱离现实的妙悟,必然会造成这种的诗风。”[1]43实际上,如朱熹所揭示的“兴”的意义中就明确指出“先言他物”,也就是包含了引发情感的事物。因此,郭绍虞指责严羽脱离现实是武断的,是将“兴”的含义单独地囿于情性这一“兴”的结果,这也是性灵派、神韵派的滥觞。郭绍虞认为:“从兴比言诗,而有所悟入,所以孔子称商赐可与言诗;从兴比评诗而体会入微,所以议论道理全是活句,指陈发露仍合诗教。以此言悟,悟原不离于现实。若从兴趣言诗,则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尽管说得头头是道,总不免英雄欺人,因为这种讲法,是教人不可捉摸,无从下手的。”[1]43郭绍虞在此逻辑不甚清楚,如何“兴比”之“兴”就是“不离于现实”而“兴趣”之“兴”则是“英雄欺人”?其实,他忽略了“兴趣”之“兴”而单论其“趣”,那结果自然如吴乔《围炉诗话》云:“作玄妙恍惚语,说诗说禅说教俱无本据。”可是,严羽对于“兴”的关注并不只有这一处,后文还有曰:“且多务使事,不问兴致”,同样是强调“兴”,这说明了“兴”在严羽诗论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兴趣”和“兴比”于其同处看都强调由具体事物感发而产生“情”和“意”,而于其不同处看,“兴趣”强调在诗歌的语言中并不直接体现“兴”的结果,而是注重“言外之意”。从《沧浪诗话》的文本出发也同样可以得到证明,《诗评·九》云:“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可见与词和理相对的就是“意兴”,“趣”只是兴的效果:不粘滞,不着相,超脱于语言文字之外。“词”指的就是诗歌的语言;“理”指的是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义理,这种义理直白而缺乏蕴藉;“意兴”之意既可以是理也可以是情而非如郭绍虞强言“意”便是“理”,这在《沧浪诗话》原文中可对证,“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诗评·四五》)这里的“意”显然不是指的理而言。
(四)刘若愚“入神”说——形上本体论的谬误
《诗辨》云:“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对此处理解最为精到的当属钱钟书先生,他在《谈艺录》中谓:“可见神韵非诗品中之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选色有环肥燕瘦之殊观,神譬则貌之美而玩赏不足也;品庖有蜀腻浙清之异法;神譬则味之甘而余回不尽也。必备五法而后可以列品,必列九品而后可以入神。”[4]109入神的境界仿佛《庄子》中所谓庖丁解牛、佝偻者承蜩、梓庆削木一般,是对诗歌进入极致的描述。如果将之与“兴趣”说联系起来看则是不论诗歌风格是“优游不迫”或“沉着痛快”,也不论诗歌居于“九品”中的任何一品,只要达到词、理、意兴相融洽而且能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般有透彻之悟便是入神。如郭绍虞所言:“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云云,即是入神的境界”[5],明显有误,因为此句上半句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指的是一种在盛唐诸人中普遍的现象。入神之境界则唯李杜二人得之,且若承蜩者、庖丁一般技通于神而得道,其他人虽有佳篇入于神,然就诗人整体而论终未入神也。刘若愚认为:“可是不管将‘神’解释为物之‘spirit’(精神)或‘essence’(本质),或者’divine’(神圣)和’god-like’(如神),入神包含超越或透过物质世界的意思,而且,严羽既然认为这是诗之极致,他对诗的概念至少有一部分是形上的。”[6]56刘若愚提出了严羽诗学的另一种本体论即形上本体论,这同样是削足适履,为了迎合自己的理论体系所加入的臆断。
二 诗学认识论
严羽《沧浪诗话》不但提出了诗歌本体论问题,而且以对传统儒家理论的诠释和阐发重新作出了回答。但是这一理论问题并不是在著作发端提出的,作为发端的则是严羽诗学的认识论。所谓认识论即是对如何认识本体的回答,受时代所限,严羽在这条路上最终走入了直觉主义,他提出以“识”和“妙悟”来通达诗之本体,它们又分属鉴赏论和创作论。在严羽看来,鉴赏论应当在创作论之前,只有具有“正法眼”方能作出好诗。对于严羽诗论中的两种倾向,郭绍虞是有所察觉的,他认为:“即就沧浪所谓妙悟而言,所悟的可不止一端,因此即以诗禅相喻,亦可生出种种歧义。不仅如此,即就沧浪所谓妙悟而言,亦可别为二义。一是第一义之悟,即沧浪所谓:‘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之说。又一是透彻之悟,即沧浪所谓‘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之说。”[1]20但是他的理解仍不透彻,如果从认识主体的区别来看则能看出两种悟之区别。吴调公《读<沧浪诗话>诗札》说妙悟有两义:“一指创作而言,偏于‘灵感’;一指鉴赏而言,体会古人。”[7]虽然此处着眼于“悟”之主体,但是都没有深刻把握住“识”与“悟”的微妙关系。
(一)《沧浪诗话》的鉴赏论
严羽《沧浪诗话》的鉴赏论统观之当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对“识”的继承,另一个则是对“悟”的运用,两者相辅相成,不可脱离而论,如果采用现代的说法,“识”是一种能力,并且是“悟”这一行为的结果。而这里所谓的“悟”即是指郭绍虞所谓的“第一义之悟”而不是“妙悟”,“妙悟”则将在创作论中讨论。
1.“识”与“悟”的关系。《沧浪诗话》是以创作诗歌为基石来探讨诗话的,对于这一点,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有更深刻的感触,如宇文所安就将严羽所谓须熟读讽咏的作品称之为“诗歌课程”(poetic curriculum)[2]430,刘若愚也同样认为:“严羽所谈论的主要是关于如何写诗以及如何评诗”[6]55因此,严羽才会在开篇第一句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他的逻辑自然是只有在知道什么是好诗之后才能创作出好诗。“识”的出处据郭绍虞考证也非严羽“实证实悟”得来,而是他拾江西诗派余唾得来,范温《潜溪诗眼》引黄庭坚:“故学诗要先以识为主,如禅家所谓正法眼者。直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严羽这一对批驳对象的化用也颇遭人诟病。严羽又云:“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这里的“悟”等同于“学者须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中的“悟”,而这些都只是“悟”而并非“妙悟”。(对于这一点郭绍虞在早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措辞颇为注意,但在《<沧浪诗话>校释》中则一概而论之则谬也)这里可以看出“识”应当是“悟”的结果,但是并非只是靠“悟”还需要“学”才行,这种“识”就通于康德所谓的审美判断力。
2.“识”的对象与“悟”的对象。严羽有言:“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这就是严羽所谓识最主要的“对象”,其余诗之“九品”“用工”“大概”都是细分或者从不同角度来看的“识”之具体内容。陶明濬《诗说杂记》卷七:“体制如人之体干,必须佼壮;格力如人之筋骨,必须劲健;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须活泼;音节如人之言语,必须清朗。”[7]这种说法颇多附会之疑,严羽本身的阐发也颇多语焉不详处,但是可以看出来的是陶明濬发现兴趣与其余各部分的关系仿佛是精神与肉体之关系,这也说明“识”的对象应当包括本体和现象两个部分,但是限于时代原因,严羽还未能作出如此细致的区分。
这种区分在《诗法》《诗评》中颇多印证。如论体制则有:“辩家数如辩苍白,方可言诗。荆公评文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诗法·十八》),论气象则有:“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诗评·五》),又有:“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论兴趣则有:“诗有词理意兴”(《诗评·九》),“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诗评·四十五》)论音节则有:“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诗评·四十三》)因此,虽然严羽的诗论看上去散乱,但是实际上却是有法可循的,但是唯独对“格力”严羽语焉不详。
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提到:“至他所谓‘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与‘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云云,是以禅喻诗。”[8]这里的第一义只是比喻,其所指则与大乘、正道、最上乘相同。也就是指最好的诗歌,而其悟的结果则是“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的确,这也就是后世格调派的滥觞。后世学者指出他这样做是嚼饭与人,实际上,他是在提出所悟之结果,而这一结果当是由学诗者学习并且在自己的悟入中验证的。虽然他比较武断地说:“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这种论调真如宇文所安所言:“如果与他意见相左,他就用羞辱来惩罚你”,也就是说“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这就用一种非理性的手段维护了自己的理论。
3.叶燮对严羽的错误批评。叶燮《原诗》:“夫羽言学诗须识,是矣。既有识,则当以汉、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诗,悉陈于前,彼必自能知所抉择,知所依归,所谓信手拈来,无不是道。若云汉、魏、盛唐,则五尺童子,三家村塾师之学诗者,亦熟于听闻,得于授受久矣。此如康庄之路,众所群趋,即瞽者亦能相随而行,何待有识而方知乎?吾以为若无识则一一步趋汉、魏、盛唐而无处不是诗魔;苟有识,即不趋汉、魏、盛唐而诗魔悉是智慧,仍不害汉、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谬戾而意且矛盾也!”此言初看在理,但是细究则是对严羽的歪曲。第一,严羽此处讨论的归向是“学诗者”而并非叶燮这类已然具“识”之人。第二,既有识,自然可以抉择而并不必听信于严羽,又何必一一读将下来不知依归呢?这是叶燮误解了严羽,因为严羽所谓“学诗者以识为主”当是指的以追求识为主而不是以拥有识为主。第三,叶燮说汉魏盛唐之诗是众所群趋的康庄之路,这是完全不顾历史,盛唐诗的经典化是在严羽推尊之后在历史中形成的,叶燮站在自己时代的状况揣测则又是误读。况且严羽对此做过说明:“近世赵紫芝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唐宗……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耶!”可见叶燮对严羽批评流于表面,并未细究文本。
(二)《沧浪诗话》创作论
“识”不但是《沧浪诗话》鉴赏论的核心,还是其创作论的基础。严羽所认为的诗歌创作应当是以“识”为基础,以“妙悟”为核心,以“学”为辅助,以盛唐为法,以“古人之诗”为归宿。而其中妙悟说虽非他独创,但是却由他发扬光大,并且直接导致了后世神韵说的滥觞,也正是从这一点考量,严羽是向直觉主义倾斜的。
1.妙悟说。《诗辨》云:“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这说明,第一,所谓当行本色正是说明在源初状态的诗之所是,也就意味着妙悟所通达的正是诗歌的本体——兴趣。王士禛谓:“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无言尤近之……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带经堂诗话》卷三)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士禛所谓的“深契其说”恰恰是对严羽的严重误读,并且将严羽所兴之内容限制在非常狭小的禅理之中。这种错误非常普遍,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云:“诗教自尼父论定,何缘堕入佛事?”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也说:“诗乃人生日用中事,禅何为者?”这种论调都以为诗不当与禅相合,可是严羽之所以说“喻”,也本无相合之意,这也是认为严羽混李杜为王孟的根本原因。其实,从《诗法》《诗评》大量篇幅讨论李杜便能清楚看到严羽对“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贯彻。第二,妙悟的结果并不只有兴趣,还需要包括语言与兴趣融合的混合体,也就是言象意或者“词理意兴”的混沌不可分割之诗,这是严羽与其他以禅喻诗者大异其趣的地方。吴可《学诗》诗云:“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韩驹《赠赵伯鱼》诗云:“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便超然。”似乎在悟得诗之所是之后便可随手作诗,实际上诚如钱钟书所言:“诗家有篇什,故于理会法则意外,触景生情,即事漫兴,有所作必随时有所感,发大判断外,尚须有小结裹。”[4]249这说明仍然需要学识、语言等相辅助才能成诗,而并非“一悟便了”。第三,“妙悟”的效果应当透彻。所谓透彻应从“透彻玲珑,不可凑泊”之意,陆游《跋吕成尗<和东坡尖义韵雪诗>》云:“字字工妙,无牵强凑泊之病。”这里可见凑泊指的是牵强散漫地聚合在一起,也就是拼凑的意思,所以透彻玲珑强调的正是指“无迹可求”的聚合在一起,这正说明了妙处与诗歌妙合无垠。另一方面,透彻亦可在后文中得到诠释,如“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挠痒;语贵洒脱,不可拖泥带水”(《诗法·九》),揣度此处严羽的意思当是指意义必须深刻、清晰而不肤浅、模糊,《诗法·十一》有言:“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与此可相互印证,互为补充。
2.“妙悟”与“读书”“穷理”之关系。严羽又云:“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一说法最遭后人诟病。黄道周《书双荷庵诗后》谓:“此道关才关识,才识又生于学,而严沧浪以为诗有别才非关学也,此真瞽说以欺诳天下后生,归于白战打油钉铰而已。”(《漳浦集》二十三)又汪师韩《诗学纂闻》云:“我生古人之后,古人则有格有律矣,敢曰不学而能乎?”再有朱竹坨诗曰:“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别材非关学,严叟不晓事。”关于此,崔旭《念堂诗话》已作说明:“竹坨但摘上二语讥之,徒欲自畅其说,则厚诬古人矣。”此说已经道出前诗问题所自,虽然诚如郭绍虞所言以上称引的“非关学”乃是“非关书”之误,但是此语虽能暂避问题,而并未真正刺着痛处。因为无论是“读书”“穷理”都可以看作学,所以非读书、穷理与言“非关学”说法实际上是一致的。也有人对严说持赞同意见,张宗泰谓:“余则以严氏所谓别才别趣者,正谓真性情所寄也。试观古今来文人学士,往往有鸿才硕学,博通坟典,而于吟咏之事,概乎无一字之见于后,所性不存故也。”又有凌扬藻《蠡勺编》谓:“亦有不读书而能诗者,北齐斛律金不解押名,而敕勒歌乃为诗一时乐府之冠。”这些说法虽然替严羽辩护,但终究是隔靴挠痒,只可论证严羽诗学中的本体论部分而已。实际上此处严羽所意欲表达的是:第一,诗歌之本体才关于诗之所是着落在何处,而不是像江西诗派那样掉书袋“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因此对于诗之本体的把握才可以使你所作称其为诗。第二,严羽还强调了如果要创作出诗之极致也就是说要创作出好诗来则“非多读书,多穷理不能极其致。”所以,对于“妙悟”“读书”和“穷理”之间的关系,严羽是非常明晰的,以妙悟为主,仍需“读书穷理”。
3.“妙悟”与“学”之关系说。为了替严羽申辩,后世学者也有从“禅”与“悟”之关系入手的,其中钱钟书先生的论述最为充分和确凿,他在《谈艺录》中说:“沧浪《诗辨》曰:‘诗有别才非书,别学非理,而非多读书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曰‘别才’,则宿世渐熏而今生顿见之解悟也;曰‘读书穷理以极其至’,则因悟而修,以修承悟也。可见诗中‘解悟’,已不能舍思学而不顾;至于‘证悟’,正自思学中来,下学以臻上达,超思与学而不能捐思废学。”[4]236钱钟书此处着意在从唐代圭峰之论断来引申补充严羽之说,但恐怕只是凑巧,因为如钱振鍠所言:严羽并不知禅,否则也不至于犯“第二义”与“声闻辟支”“临济”与“曹洞”之误而贻笑大方。但是,这仍然可以认为是对《沧浪诗话》这一文本的完善。
4.诗歌创作最高标准的确立与复古。严羽之所以要确立诗歌最高标准的原因同样是基于《沧浪诗话》的原旨是对诗歌创作有所借鉴,也许诚如宇文所安所言:“宋代的诗学越来越关心如何创作伟大的诗歌。兴趣的转移大概说明了自信心的丧失。”[2]432严羽推崇盛唐之诗,号称“以盛唐为法”,并标举“汉魏晋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而“独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诗辨·五》)所以可见后世认为严羽有复古之意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严羽之所以希望不断熟参古诗,原因并非为复古而复古:第一,熟读前人作品是为自己创作做准备。《西京杂记》就曾引扬雄言;“读千首赋,乃能做赋。”杜甫也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换句话说,学习前人的诗歌乃是学习、体验其技巧和规则以及体制。第二,严羽以其独到的眼光发现,诗歌在源初语境下可以生发出更多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他强调“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的原因,这一点在《沧浪诗话》中可以得到印证,《诗评·四七》云:“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一连六句,皆用叠字,今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叠字的运用在诗歌产生的源初状态中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后世逐渐稀少,郭绍虞谓:“可知中国口头语和书面语发生距离之后,修辞标准,即不相一致。顾炎武以为‘河水洋洋’、青青河畔草诸例,连用叠字,复而不厌,后世无人可继,其原因正于此。”[1]201从语言来分析并没有错,但是终究应该从文化层面上来考虑,由于正统文化以文言作为载体排斥口语的介入,诗歌在进入正统文化的中心之后无法再回归到源初语境,诗歌形式的可能性逐渐萎缩而显得逼仄,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力量才得到释放,叠字的使用也得到回归。由此也生发出严羽的致命弱点,本来这种对于可能性的追溯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他将盛唐诗歌设立为判断的唯一标准,而盛唐诗歌仍然属于正统文化,所以他所谓“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则明显是借由传统来判断诗歌之好坏,这一点正是他弱点所在,即排除了诗歌创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落入为复古而复古的窠臼中去了。故冯班《纠缪》谓:“沧浪之论,惟此一节最为误人”则是矣。钱振鍠《谪星诗说》谓:“我诗有我在,何必与古人争似。如其言,何不直抄古诗之为愈乎?”这一评价虽然对,但显得不是太理性。
总而言之,严羽本来已经触摸到诗歌可能性与文化传统的辩证关系,但终究由于无法脱离自己塑造的盛唐诗歌之典范而与其失之交臂。但是,在一定范围内,严羽设定的诗歌标准仍然能够起到鉴别诗歌好坏的作用(尤其是从严羽的语气来看《沧浪诗话》很大程度上在教育初涉诗歌的人就不难理解这种化约的手段了),但是严羽却永远逃不掉“屋下架屋,愈见其小”的弊病。但是,严羽诗学的体系性是不言而喻的,每一章节的安排都颇费心机,虽然也许严羽并没有严格的创作主体与鉴赏主体相区分的意识,但是潜移默化之中其文本所表现之思路是相当明晰和透彻的,虽然最终严羽并没有探入语言论的领域,但终究是完成了对诗学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的回答。这也说明了他之所以能在袭用时人话头且并不知禅的情况下能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后人或者指出严羽于禅无所知,只是袭用话头,但又有人指出他以禅喻诗是对正统儒家诗教的颠覆,最后以至于以为严羽所谓悟之结果就是禅,可是细究下来,倘若严羽并不知禅,又如何能以禅理来推翻儒家诗教呢?无论如何,严羽毕竟使得“以禅喻诗最终走向圆融即最后完成”,在他之后,“以禅喻诗也成为重要的批评模式”[9],他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抹杀的。
[1]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李锐清.《沧浪诗话》的诗歌理论研究[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197.
[4]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7.
[6]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M].杜国清,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7]吴调公.读《沧浪诗话》诗札[M]//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87-99.
[8]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75.
[9]田 琼.走向圆融:“以禅喻诗”的演进历程[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1(2):100-103.
责任编辑:黄声波
On Yan Yu's Poetic System——A Return to the Text of Cang Lang’s Notes on Poetics
LISand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08 China)
Yan Yu’s famous workCang Lang’s Notes on Poetics,which tak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especially the theory of Zen,a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investigates into a whole series of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poetic theory,and develops the theoreticalmode of“taking Zen as ametaphor”,upon which a whole poetic system consisting in various aspects of ontology,creation theory,text theory and appreciation theory aswell,and from which results a wide range of influence on the following poetry critics such asWang Shizhen.
Yan Yu;Cang Lang’s Notes on Poetics;taking Zen as a metaphor;poetry deriving from emotion; Xingqu theory;Miaowu theory;
I207.2
A
1674-117X(2015)01-0096-06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1.019
2014-10-14
李三达(1986-),男,湖南衡阳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