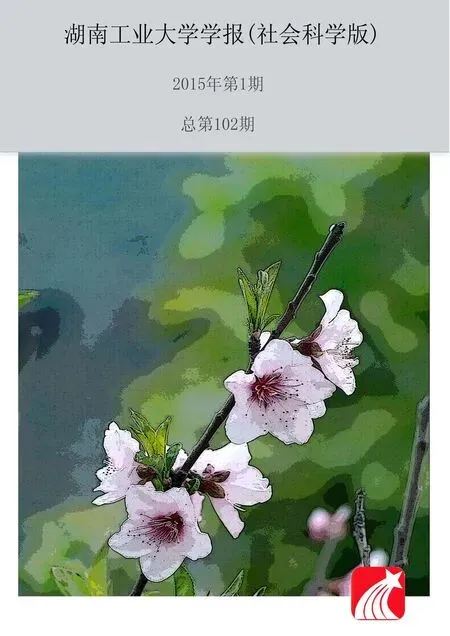电影《罗生门》的存在主义解读
丁瑜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株洲412007)
电影《罗生门》的存在主义解读
丁瑜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株洲412007)
电影《罗生门》中的强盗、武士、武士的妻子在极限的境遇中选择自私、狭隘,以至沦入痛苦的地狱,无法获得自由。樵夫虽然犯了错,但是他用自己积极的行动改正错误,使自己超越了地狱,获得自由。黑泽明希望观众通过他的影片,学会如何在一个充满荒诞和非理性的世界中去面对人类的不幸和克服人性的弱点。
《罗生门》;黑泽明;他人就是地狱;存在主义
电影《罗生门》一开始就为观众呈现出一副地狱般的场景:阴沉的天空、倾盆的大雨、破败的罗生门城楼、表情阴郁的人物……愁眉紧锁的行脚僧悲天悯人地嘟囔:“什么兵荒咧,地震咧,风暴咧,火灾咧,荒年咧,疫病咧,……连年灾难不断。再加上那成群结伙的强盗,没有一天晚上不像海啸一般地到处骚扰。我实在记不清,亲眼看到多少人就像虫子一般地死了,或被惨杀了。”然而更可怕的是人性的自私和谎言,正如行脚僧所说:“世道人心,实在是没法叫人相信了。这可比什么强盗,什么疫病,什么荒年、火灾、兵灾都更加可怕。”影片接下来演绎了同一个案件的四个不同版本。每个版本的陈述者都编造了一套漂亮的陈词,把自己塑造成完满的形象。真相到底是什么?影片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行脚僧再次发出感慨:“这真是可怕的事了。要是任何人都不能相信,那么,这个世界就成了地狱了。”杂役则肯定地回答:“一点不错。这世界压根就是个地狱。”是什么导致信任的缺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恶化到如此的地步?他人真的就是地狱吗?
一
电影《罗生门》讲述的故事起初是一起很简单的奸污案,强盗多襄丸强奸了武士的妻子真砂,后来却演变成一场杀人案。强盗强暴真砂后,本来想从此拥有这个女人,未料他发现女人的丈夫已经嫌弃这被糟蹋过的女人。丈夫的说法是,“在两个男人的面前丢丑,为什么不自裁呢?你这可憎的女人!”“这样的贱人还要她干嘛?你要就给你好了。事到如今,这样的女人,还不如抢走我那匹桃花马来得伤心呢。”强盗竟然也因此嫌弃这个女人。女人羞辱悲愤之余,说出“谁是强者我跟谁!”挑起两个男人开始竞争。打斗过程中两人都充满恐慌与惧怕,仓皇中,强盗无意间杀死了武士。一起奸污案为什么会演变成杀人案?武士因为贪心上了强盗的当,导致自己的妻子被奸污,为什么却要嫌弃受到伤害的妻子甚至希望自己的妻子自杀?武士的妻子为什么要两个男人决斗?决斗能使她恢复贞洁吗?这些思想与行为基本上是不可思议的,可是产生这种结果的背后在日本有一套坚不可摧的说辞,那就是日本的传统伦理道德,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菊与刀》的作者在第八章“洗刷污名”中这样分析日本人,“在日本,持之以恒的目标是荣誉,”[1]140“清除自己美誉上的污点是一种美德,”“为了‘荣誉’,一个人会献出财产、家庭和生命,献出多少,他的美德就有多高。”[1]119事实上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重视名誉,但是对于名誉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而为了名誉做出极端的事情,在日本表现得极其特别,它导致的一个可怕后果就是极端的自私自利,武士与妻子以及其它的种种人物都是这样。武士的污名是保护不了妻子和妻子被强暴,为了洗刷污名,他没有追究自己的失职,却责问妻子为什么不自杀,希望以妻子的自杀来为自己洗刷这种奇耻大辱。武士的妻子遭受到强盗的凌辱后又遭到丈夫的羞辱,污名无以复加,但是她没有检视自己也存在的错误,而是想办法要消灭这一耻辱的见证者:强盗或丈夫,所以她挑起了两个男人的决斗。他们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名誉以及如何消除这种耻辱感,使自己在道德上得救,而没有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和利益,他们的自私、狭隘导致大家一起沉没。
人总是处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之中,完全与世隔绝的个体是不可能生存的。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之中,如果只顾及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择手段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么你就把他人推进了地狱。而他人的生活其实都是在自己的生活中的投影,最后,害人者必害己。影片中的强盗多襄丸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强奸了武士的妻子,使得武士和他的妻子蒙羞,并导致他们夫妻反目,自己最终也被官府所抓,等待自己的是断头台。武士在自己的妻子受辱后,没有安慰、同情妻子,而是嫌弃妻子,致使妻子挑起本不想杀人的强盗和自己决斗,最终屈辱地被强盗杀死。武士的妻子本来可以选择依附强盗或者丈夫,可她偏要挑起两个男人的决斗,导致最后自己身无所依,只能托身尼姑庵。由此可见,凡是“地狱”,都是从自私的选择开始,祸及他人,然后殃及自身,最后是大家都生活在“谁也好不了”的地狱之中。
正如电影所表现的,我们人类的生活从来都是与错误、罪恶相伴随的,那么,拯救的方法是什么呢?西方人提供了一条通道,那就是忏悔和赎罪,即宗教的救赎。在欧美的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社会道德的绝对标准,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他们相信这种罪恶感可以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得到解脱。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在罪感文化下,常见的社会现象是人们习惯于忏悔。忏悔是向他人坦白自己的过错,以求得他人的宽恕和容忍,是彻底、完全和自愿地改正过错的心灵基础,是对过错发自内心深处的自我惩戒。人们通过忏悔来获取灵魂上的罪恶感的解脱,进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与此相对应,在罪感文化中,人们也赞赏勇于承认错误、公开道歉和真诚悔过的行为。很明显,《罗生门》当中的种种人物都不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生活在日本,在日本没有这种基督教的文化基础,日本是耻感文化。“在以羞耻为主要制裁手段的地方,当一个人向别人甚至向神甫坦白他的错误时,他体会不到这种痛苦的缓和。只要他的不良行为没有暴露给世人,他就不需要自寻烦恼,在他看来,忏悔只会招致麻烦。因此,羞耻文化没有忏悔,甚至对上帝也没有。他们有表示好运的仪式,却没有赎罪的仪式。”[1]180-181
羞耻是对他人的批评、嘲笑的反应,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也是人类共有的心理,与西方不同的是,在日本不是通过忏悔来取得内心的净化与平和,而是想方设法要使自己的“不良行为没有暴露给世人”,因为日本人觉得如果没有外人的存在,也就没有了耻辱感,这就是电影当中人物各种不可思议的自私自利行为的黑暗动机。“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羞耻是首先要考虑的,这意味着,任何人做任何事,都要看公众对自己的评价。”[1]182换一句话说,日本人过于依赖他人的目光而不是自己的行动来确定自己,这样看来,自私自利不但可以消除耻辱,而且可以让自己的形象变得完美。
影片《罗生门》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自私自利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他们都在撒谎,撒谎的目的就是要塑造公众认可的完美的自我形象。
多襄丸的谎言有意将自己塑造成人们心目中剽悍勇武的一代枭雄。首先,他将犯罪的原因归咎于那阵凉爽的风。是风吹起了武士妻子的面纱,让他看到了武士妻子的美貌,勾起了他的淫欲,他才开始谋划邪恶的阴谋。在他与武士妻子发生性关系时,武士妻子并没有强烈反抗,后来甚至还伸出手来抱住了他,可见是自己的魅力征服了她,那么自己的行为就不能算是强奸。最后,他并没有打算杀死武士,只是想向他的妻子泄欲,是武士的妻子求他杀死武士的,而且他还松了武士的绑,与武士公平决斗,足足斗了二十三个回合,他是通过公平决斗杀死武士的,要怪只能怪武士自己技不如人,不能完全怪他。由此,多襄丸将强奸罪、杀人罪洗刷得一干二净,反而成了一个应被尊敬的侠士。他勇敢地承认自己杀死了武士,甚至宣称早就知道自己的脑袋总有一天会挂在高杆上示众。这是何等的豪迈!
真砂的谎言将自己打扮成被强盗欺凌后又被丈夫侮辱的悲惨而可怜的女性。她在遭受强盗凌辱以后来到丈夫身边,希望从丈夫那里得到安慰,然而丈夫给予她的却是冷酷的眼神。丈夫的鄙视让她觉得比死还可怕。她把短刀递给丈夫,请求丈夫杀了自己,但是丈夫仍然不理她。得不到丈夫原谅的她悲痛过分以至晕倒,醒来后,发现丈夫被杀死,胸口插着短刀。后来,她想过很多法子自杀,都没死得成。这样一个女性俨然就是日本最标准的妇女典范:柔弱,虽然反抗不了强暴,但是心里却是坚贞不渝的;顺从丈夫,没有自我,永远跟在丈夫的身后;知耻,多次想以死来洗刷自己的耻辱,以保住自己的声名。
武士鬼魂的叙述是要将自己塑造成清高刚直、不辱精神的武士。武士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妻子的身上。他反复强调妻子的美,因为她的美貌引来了强盗,真是红颜祸水。妻子还被强盗的花言巧语所打动,愿意跟随强盗逃走。更为可恨的是,妻子竟然要求强盗在逃走之前杀了自己,这真是不可饶恕。强盗没有理睬妻子的要求,反而踢倒妻子,把妻子交给武士处置。武士因此饶恕了强盗的过错。最后武士用自杀来保住了自己的名节。
这三个人始终关注的是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公众的认可成为制约他们行动的强大的外在力量,这种力量紧紧地束缚着他们,压迫着他们。一个人如果过于依赖他人对自己的判断,一味地追求他人的认可和赞美,甚至不得不通过谎言与损人利己来达到这一目的,结果必定陷于精神地狱之中。萨特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同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变了质,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我同他人的关系之所以很坏,是因为我完全依赖于他人,这样我当然就像在地狱里一样。世上有许多人处在这种地狱般的境况中,因为他们太依赖于他人对自己的判断。”[2]95-96多襄丸、武弘、真砂为了迎合世人对自己的期望,不惜伤害他人的利益,还要挖空心思编造谎言,他们无疑都生活在精神的地狱中。
二
相对于耻感文化而言,罪感文化有一定的解脱途径,那就是向上帝忏悔,通过忏悔洗刷心灵的尘埃,并用实际行动为自己赎罪。而耻感文化下的人毫无解脱的途径,重要的是避免被别人嘲笑。这样就产生了两个犯罪陷阱,一个是人们可以存着做错事而不被发现的侥幸心理去犯罪,另一个是,在人们已经犯罪的情况下,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罪行而进一步的犯罪。罪感文化则不存在这些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罪感文化在塑造人的道德品质的途径上比耻感文化的积极作用要大得多。
影片中的三个主要涉案人员在罪恶面前,首先想到的是逃脱别人的嘲笑,逃脱不了就用谎言来掩饰、辩护,他们找不到解脱的途径,最后陷入地狱一般的境遇。从小就热爱西方文学、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黑泽明清楚地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别具匠心地将这种西方通行的忏悔意识和赎罪意识赋予了影片中的另一个人物:樵夫。通过樵夫从而为人们安排了一条解脱之路。
在原小说中,樵夫作为发现尸体的报案人出场,与案件本身并无直接关系。而在电影中,樵夫不仅是报案人,还是案件的目击者,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与其他三个主要涉案人员一样,他也犯了错。他的错误在于将贵重的短刀据为己有,而且为了掩盖这一个错误他又犯了另外一个错误:撒谎。这与其他几个剧中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黑泽明的安排下,樵夫最后却展现出了强烈的道德自我反省意识。
悲剧已经发生,痛苦、焦虑的樵夫目光发直,不停地喃喃自语:“不懂,简直不懂!”他不懂的是人为什么如此善于撒谎,不论是强盗还是武士,男人还是女人,甚至死者都在掩盖真相。同时他也为自己把短刀据为己有而痛苦,以至于在庭审时没能说出全部真相,也无法指证和揭露他们的谎言。他的痛苦有着自我谴责的因素,是自我反省意识的表现,同时也是一个人良知未泯的证据。他在人性的不道德面前表现出来的这种震惊、痛苦、自责的心理状态,是黑泽明铺设的一条伏线,为他后来的忏悔和赎罪预先做了逻辑上的铺垫。
然而,樵夫的忏悔、赎罪之路走得艰难而曲折。他目睹了杀人案的全过程,拿走了遗落在现场的短刀,然后及时报了案。由于他及时报案,衙役迅速抓获强盗和武士的妻子。他虽然拿走了短刀,但是还是本着自己的良心及时报了案,而不是一走了之。在庭审现场,他亲眼目睹了涉案三人的丑恶嘴脸。案件的真相在他们的层层谎言中被遮蔽、扭曲,直至彻底消失。他被人性的丑恶所震惊,也被自己的良心所折磨,跌入精神的地狱,不得安宁。如果没有弃婴的出现,没有杂役对自己谎言的揭露,樵夫可能永远陷入精神的地狱,无法得救。弃婴情节的设置体现了黑泽明编剧的高明,人性软弱且不敢直面自身,需要外力的推动才能弃恶从善。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黑泽明在樵夫的身上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性意义。樵夫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既善良又摆脱不了人性固有的各种弱点(贪小便宜、撒谎、胆小怕事)。他虽然撒了谎,却天真地对其他三人的撒谎表示了极大的不理解和愤慨。这反而是他善良的体现,因为善良的人总是更容易相信人性,对人性的恶也有更敏锐的痛感。与他相比,杂役对人性恶的反应就非常平淡,显得习以为常。他拿走了那把贵重的短刀,是因为他要在兵荒马乱中养活六个孩子,也许这把刀能暂解家中的燃眉之急。他在官府没有完全说出他所看到的真实细节是因为怕被卷进官司。因为他上有老,下有小,一家老小眼巴巴等着他上山砍柴,卖钱糊口。他崇尚道德,渴望社会秩序。当杂役剥去婴儿衣服的时候,他愤怒地出面制止杂役的不道德行为,骂他是“恶鬼”。然而,杂役的反驳和质问让他哑口无言。“难道你就不是那号人吗?……纠察使署的官们,也许叫你糊弄得过去。可我呀,你可糊弄不了。”“我问你,那把女人的短刀哪去了?……难道落在草里就没有了吗?不是你掖起来了,还有谁呀?”这一质问揭示了樵夫一直隐藏、不愿面对的真相,终于逼迫樵夫直面自己内心的恶。为了不再经受良心的折磨,樵夫选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忏悔、赎罪——收养弃婴,尽管家里已有六个孩子。樵夫用自己的行动把自己从精神的地狱中拯救了出来。
樵夫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普通人的代表。是凡人就难免犯错。犯错后,人们往往喜欢去找社会原因、客观原因、他人的原因,而看不到自己的原因。或者即使看到自身的弱点,却不敢去面对,选择逃避。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面对自己,那么自己也就成了自己的地狱。
萨特认为世界和人生虽然荒诞,但是人生的意义在于选择。人要通过自己的道德选择来塑造自己,实现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而且要对整个世界负责,人在选择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就选择了别人的自由,所以应该做出积极的、进步的选择。电影《罗生门》中的多襄丸、武士及其妻子的自我选择体现出一种道德上的卑劣性,因而他们的本质是低劣的,也因此他们的境遇才显得那么的难堪,以至于别人像地狱一样使得自己难以忍受,无法获得自由。萨特把这种卑劣而低下的人际关系提炼为著名的论断:他人就是地狱。萨特把人生看成是一系列自由选择的总和,他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人生来没有什么本质可言,只是在存在的过程中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塑造自我,才逐渐造就了自己的本质。樵夫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是他能用自己积极的行动改正错误,做出迥异于前的选择,从而改变了自己的本质,使自己超越了地狱,获得自由。
黑泽明是一位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的导演,他清楚地看到了日本耻感文化的最大劣根性——过分驯服的性格,他认为这种奴隶性的怯懦导致日本人没有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他说:“我们接受了以看重自我为恶行、以抛弃自我为良知的教育,习惯于接受这种教育,甚至还不怀疑。我想,没有自我完善,那就永远也不会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3]211黑泽明认为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是改变日本的民族劣根性,推动日本社会前进的武器。这里提到的自我完善,指的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内在的自我完善。而西方社会由罪感文化形成的忏悔意识、赎罪意识正好可以帮助日本人实现自我完善。这就是黑泽明赋予樵夫这一形象忏悔意识、赎罪意识的用意所在。
在存在主义看来,“世界是毫无理由的荒诞,人生是毫无内容的虚无,但反过来,正因为世界荒诞,才显出人直面荒诞而活下去的勇气和伟大,正因为人生虚无,才需要人以自己的顽强追求去充实,从而以自己的活动赋予人生以意义。”[4]174“对黑泽明来说,揭露世间的凄惨是作家的职责,只有让人类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愚行,才有可能促使他们重新依靠信仰、理性与良知的力量战胜绝望,这是一种敢于正视现实的人生态度。”[5]105-106黑泽明希望观众通过他的影片,学会如何在一个充满荒诞和非理性的世界中去面对人类的不幸和克服人性的弱点。而《罗生门》这部影片告诉观众的是:世界是荒诞的、非理性的,到处都充满了罪恶,但是我们不能效仿罪恶,更不能以恶对恶。在生活的苦难面前,应该学会宽容,而不是怨恨。选择自私、狭隘,就会连自己也无处藏身,只能沦入痛苦的地狱。选择宽容,不只宽容了别人的过错,也相对净化了自己,由此带来的将会是没有任何不安和痛苦的天堂般的心境。人应该直面自身的弱点,勇敢地承认错误,用行动改正错误。只有选择忏悔和赎罪才能获得拯救。
[1]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塔,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2]萨特.萨特思想小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3]黑泽明.蛤蟆的油[M].李正伦,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
[4]刘象愚.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刘 佳.解读黑泽明[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李 珂
Existential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lm Rashomon
DING Y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Hunan 412007,China)
Being self and narrow,the characters who are the robber,the worrior and his wife in the film Rashomon have lead to miserable hell and couldn’t acquired freedom in spirit.Although the woodcutter had mistake,he could corrected the error by active behavior so that his spirit could surpass the Hell and get freedom.Akira Kurosawa hoped his audiencesmight studied how to confront human’s suffers and conquer human’s weakness in absurd and non-rationable world by watching his films.
Rashomon;Akira Kurosawa;hell is other people;Existentialism
G206.2
A
1674-117X(2015)01-0109-05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1.022
2014-09-01
丁 瑜(1971-),女,湖南醴陵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学、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