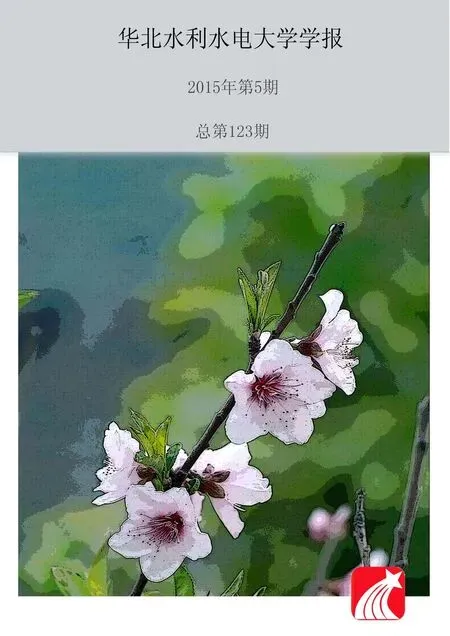论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的正当性
黄华生,李文吉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论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的正当性
黄华生,李文吉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是一项正当合理的法律制度。《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实行从严限制的修改方案,实无必要。
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刑法修正案(九)
我国现行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规定就是本文所称的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目前面临着立法修改的挑战,正在研议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将现行刑法第390条第2款修改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检举揭发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免除处罚。”也就是说,研议中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从严限定对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的条件,因为根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规定,即使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其行贿犯罪行为的,一般也只可以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只有行贿人犯罪较轻并且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才可以对其免除处罚。
然而,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的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本身是一项正当合理的法律制度,并无修改和从严限制的必要。具体阐述如下。
一、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兼具自首与立功双重性质
关于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性质,我国法学界一般将其定性为刑法中自首的一种,是刑法分则规定的特别自首。例如赵秉志教授、于志刚教授即持这种观点[1]。
然而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不够准确和全面。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其行贿事实的行为,除了是一种特殊的自首之外,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立功,它兼具自首与立功的双重性质,属于自首与立功的结合。这是因为:一方面,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其行贿事实的行为,属于自动投案并且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如实交代,因而构成自首;另一方面,由于行贿与受贿的对合性特征,行贿人在如实交代自己行贿罪行的同时,也就如实地检举揭发了受贿人的受贿犯罪,经查证属实后,又构成立功。当然,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上,司法机关对于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其行贿行为的案件,应当按照法条竞合的适用规则来处理,选择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这一特别条款,而不再适用刑法总则规定的自首和立功制度一般条款。
行贿人检举揭发受贿人的受贿罪行构成立功的观点,实际上也可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相关表述中得到印证。《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将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改为“……检举揭发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这一修改方案的表述说明,最高立法机关也持行贿人检举揭发受贿人的受贿罪行构成立功的观点。如果将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仅仅看作一种自首,则会导致忽视行贿人检举揭发受贿犯罪这一立功表现,实际上未能充分认识和评价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其行贿行为的双重法律意义,容易导致对行贿人的不公正处罚。
正是因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兼具自首与立功双重性质,刑法就有必要对其规定比单纯的自首或者单纯的立功更加宽大的法律后果。相较于我国刑法关于自首从宽和立功从宽的规定,我国现行刑法第390条第2款关于“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并不存在立法上不当放纵行贿罪的问题。
二、行贿人在行贿与受贿的互动关系中属于罪责较轻的一方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之所以提出严格限制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修改方案,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受贿与行贿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伴生、相互依存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受贿是由行贿引发的,因而主张加大对行贿行为的处罚力度,将行贿与受贿一并严厉处罚。例如,有学者提出:“行贿与受贿是一种对合性犯罪,二者之间具有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密切联系。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行贿就没有受贿,并且是先有行贿而后有受贿……为了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犯罪,有必要重新评价行贿行为的危害性。”[2]最高人民法院的李少平副院长也指出:“今后,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原则,修正行贿犯罪的刑法规范,并努力提升查办贿赂犯罪的执法能力,切实遏制行贿犯罪。”[3]
然而笔者认为,行贿引发受贿,行贿与受贿的危害性基本相当的观点值得商榷。从实践情况来看,大多数贿赂犯罪案件确实表现为行贿人主动向官员行贿,也就是官员“被动收受”贿赂的情况是常态,“主动索取”贿赂的情况较少见。但是,这仅仅是贿赂犯罪的表面现象,呈现的仅仅是行贿与受贿关系的“局部截图”,而忽略了贿赂犯罪的主导因素和深层机理。笔者认为,在行贿人与受贿人的互动关系中,受贿人才是真正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的一方,行贿人其实是处于从属和劣势地位的一方。受贿人手中掌握的职权是一种稀缺的“重要资源”,只要他有了以权谋私的意愿,他完全没有必要去“主动寻求”他人行贿,而是只需“待价而沽”即可,自然会有行贿人“主动出价”。而行贿人之所以宁愿“牺牲”自己的钱财去讨好受贿人,是因为他有求于受贿人,需要寻求受贿人给予“恩赐”。简言之,如果把行贿与受贿之间的“权钱交易”看做一个市场,那么它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卖方市场”,真正的市场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受贿人手中。由此看来,在贿赂犯罪的实施过程中,受贿人才是真正的主导人和关键角色,行贿人处于从属和次要的地位。既然如此,对于行贿人与受贿人的共犯关系,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行贿人和受贿人双方的刑事责任大小。在刑罚后果上应当区别对待,将受贿罪作为惩治的重点,对行贿罪适当地宽大处理。
三、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有利于贿赂犯罪的侦破
我国刑法上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的正当性,除了可以从法律意义上予以阐明之外,还可以从刑事政策角度来加以阐释。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有利于司法机关收集相关证据,侦破贿赂犯罪,从而有效地惩治贿赂犯罪。
众所周知,在现实中贿赂犯罪黑数很高,司法机关侦破该类犯罪的难度特别大。贿赂犯罪案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并因此决定了该类犯罪比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更加难以侦破,司法机关需要借力于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来解决侦破难的问题。
第一,贿赂犯罪的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一般不存在“加害与被害”的利益侵害关系,双方之间是一种各取所需的“共犯关系”,缺少直接被害人。现实中的绝大多数贿赂犯罪表现为受贿人“收受”贿赂而不是“索取”贿赂,因此缺少直接被害人。正因为如此,贿赂犯罪不像普通刑事犯罪诸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盗窃等犯罪案件那样有直接被害人来积极地检举、控告、证实犯罪,不存在“被害人陈述”这种天然容易获得来证实犯罪的重要证据,这就加大了司法机关查处贿赂犯罪案件的难度。面对这一难题,司法机关的一个重要侦查策略就是设法瓦解行贿人与受贿人的“同盟关系”,从犯罪人的内部“攻破堡垒”。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正是司法机关对贿赂犯罪实施分化瓦解的一个重要抓手,在解决贿赂犯罪侦破难的问题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贿赂犯罪往往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一对一”地进行,很少留下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通常没有目击证人在场,因而具有高度的秘密性。司法机关侦破和认定贿赂犯罪,不可避免地高度依赖行贿人与受贿人的口供。在法律上保留对行贿人的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有利于鼓励行贿人如实供述其罪行,推进贿赂犯罪案件的侦破。
第三,受贿人一般是文化程度和智力水平较高的官员,案发前心理准备通常也比较充分,具有较强的反侦察能力。因此,司法机关通常需要借力于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从行贿人一方率先打开缺口,取得受贿人收受贿赂的相关证据,继而步步紧逼攻破受贿人的心理防线,促使受贿人如实供述其受贿事实。
第四,受贿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比例
较高。司法机关如果没有较大力度的“优惠政策”来稳住行贿人的口供,往往容易造成行贿人与受贿人双方事后双双翻供,从而使案件的诉讼陷入僵局。
四、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有利于有效预防和公正惩罚贿赂犯罪
贿赂犯罪发案率高的原因之一,就是该类犯罪难以被发现,行贿人和受贿人都比较自信地认为犯罪后不会被发现。行贿和受贿在刑法上都是构成犯罪的行为,既然如此,行贿人和受贿人都天然地希望他们的罪恶勾当不被发现,这就使得行贿人与受贿人双方之间很容易一拍即合地建立一种共同保守犯罪秘密的“同盟关系”和“互信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导致已经发生的贿赂犯罪案件难以侦破,另一方面导致贿赂犯罪人更加放心大胆地实施更多的贿赂犯罪,导致贿赂犯罪陷入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之中。
采取有效的立法和司法措施来打破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共同保守犯罪秘密的“同盟关系”和“互信关系”,斩断贿赂犯罪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关系,可以说是有效预防贿赂犯罪的关键策略。我国现行刑法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有利于降低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的“互信关系”,受贿人担心行贿人主动如实交待行贿事实而有所顾忌,有利于遏制贿赂犯罪。司法机关借助于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促使行贿人如实交代贿赂犯罪,有利于降低贿赂犯罪黑数,有效打击和遏制贿赂犯罪。贿赂犯罪被发现、被追诉的比例越高,就越有利于预防和减少贿赂犯罪;反之,如果贿赂犯罪被发现、被追诉的比例很低,则会导致事实上助长贿赂犯罪。
在惩治贿赂犯罪问题上,有效侦破犯罪比公正惩罚犯罪更加重要。我国目前贿赂犯罪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在于破案率低、犯罪黑数高,而不在于刑罚的严厉性不足。实证研究资料表明,“无论是惩罚的确定性还是严厉性均对总犯罪率、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产生了显著的威慑作用。其中破案率的威慑力最强”[4]。因此,国家应当把惩治贿赂犯罪的着力点放在提高破案率而不是加大刑罚力度方面。有了尽可能地侦破贿赂犯罪,对罪责相对较轻的一方——行贿人——给予较大力度的宽大处理,虽然从局部而言稍失公正,但这是为了换取侦破案件效果而不得已付出的一种“必要代价”。如果脱离贿赂犯罪的有效侦破问题来要求对贿赂犯罪的公正处罚,这只是一种“纯理念上的公正惩罚”,其实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况且,有效侦破贿赂犯罪是公正惩罚贿赂犯罪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贿赂犯罪案件的侦破率太低,则会导致大量的贿赂犯罪逃脱法网,导致从整体上来看刑罚更加不公正。
五、类似的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如何有效地侦破和认定犯罪案件,是世界各国的刑事司法机关面临的共同难题。为了解决破案难的问题,各国刑法都普遍规定了自首、坦白、立功等针对犯罪人的“刑罚优惠”政策,意在鼓励犯罪人配合侦查,提高破案效率。特别是贿赂犯罪、有组织犯罪和共同犯罪等侦破难度大的案件,各国刑法一般规定了较大的“刑罚优惠”力度来鼓励犯罪人配合侦查机关破案。
对主动如实交代贿赂犯罪事实的行贿人给予宽大处理,是多数国家的共同做法。一些国家的刑法对于主动交代行贿事实的行贿人甚至明确规定“免除刑事责任”或者“免除处罚”,比我国刑法规定从宽力度更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91条规定:“……行贿人主动向有权提起刑事案件的机关坦白行贿事实的,行贿人可以免除刑事责任。”[5]《克罗地亚刑法典》第348条规定:“……(三)因公职人员索要贿赂而犯本条第一、二款规定之罪,并且在该行为被发现之前,或者其察觉该行为被发现之前主动向有关机关进行报告的,应当免予处罚。”[6]
为了解决一些犯罪案件调查取证难的问题,美国联邦议会于1857年制定了《联邦刑事免责法》(于1868年、1893年和1970年作了修改),规定了“刑事免责”制度。按照美国《联邦刑事免责法》中的规定,考虑到侦破案件的需要,作为刑事追诉主体的警官和检察官,可以向联邦法院提出免除共同犯罪案件中的某个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的申请,前提条件是该犯罪嫌疑人承认其犯罪事实并揭发了同案犯的犯罪事实或者提供了侦破犯罪的证据。这一“刑事免责”制度是美国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的方式之一,旨在鼓励共同犯罪案件的被追诉人承认犯罪并配合警方揭发同案犯的犯罪行为。美国的“刑事免责”制度经常适用于有组织犯罪案件、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其他警方运用一般调查方法难以侦破的案件[7]。
我国刑法除了在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了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之外,还在第164条第3款和第392条第2款分别规定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的特别从宽处罚制度,以鼓励行为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其犯罪行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2014年11月通过的《反间谍法》规定了对间谍犯罪的特别宽大和奖励制度。该法第
27条第2款规定:“实施间谍行为,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给予奖励。”这一从宽和奖励制度,同样是为了应对间谍犯罪的高度隐蔽性和侦查机关破案难问题而作出的策略性规定。
六、行贿罪的追诉数量不应简单攀比受贿罪的追诉数量
有学者从行贿罪与受贿罪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数差异出发,试图揭示大量行贿人逃脱法律制裁的事实,进而论证从立法上提高对行贿罪处罚力度的必要性。该学者指出,从行贿罪与受贿罪的追诉比例来看,行贿罪的追诉数量明显低于受贿罪的追诉数量,二者比例严重失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资料表明,全国检察机关在2004年至2008年期间立案侦查的受贿犯罪案件总数为45046件47297人,而同期立案侦查的行贿犯罪案件总数仅为10201件11699人,立案侦查的行贿犯罪案件总数仅约为立案侦查的受贿犯罪案件总数的27%,二者差额巨大,表明有大量行贿犯罪案件未被立案查处。在提起公诉数据方面,在2004年至2008年期间,全国检察机关共对受贿犯罪提起公诉38587人,而对行贿犯罪提起公诉的仅为5809人,约为被提起公诉的受贿犯罪人数的15%,二者之间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也就是说,即使一些行贿案件被立案侦查,也只有更少一部分行贿人被提起公诉,相当一部分行贿人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究其原因,立法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刑法对受贿与行贿采取了差异性处罚的立法方式。因此,应当从立法上修改行贿罪的刑罚规定,使行贿罪与受贿罪同等处罚[8]。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过于简单化和过于激进之嫌。我国现行刑法对行贿罪与受贿罪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罪状要求、构罪标准和刑罚后果,总体上是科学合理的。应该说,与受贿罪相比,行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必要性都明显更小。对行贿罪与受贿罪规定差异化的构罪标准和刑罚后果,正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也是刑罚正义的必然要求。既然如此,就不宜简单地比较行贿罪与受贿罪的追诉人数,不能简单地要求行贿罪的定罪人数要达到与受贿罪定罪人数相近的程度,更不能为此而激进地将刑法对行贿罪的刑罚处罚提高到与受贿罪同等的程度。
七、立法修改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无助于纠正实践中的执法偏差
从我国打击贿赂犯罪的实践情况来看,过度宽宥行贿人的现象比较常见,一些本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贿人逃脱了刑法的制裁。例如,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受贿、滥用职权一案中,郑筱萸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8家医药企业的负责人给予的贿赂财物合计人民币649万余元,郑筱萸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是作为行贿方的该8家企业及其负责人无一被追究刑事责任。又如,在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受贿一案中,许迈永利用职务之便收受14名企业负责人给予的贿赂财物合计人民币1.45亿余元,许迈永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是多个行贿金额高达数千万元的企业及其负责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再如,在湖南省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一案中,曾锦春因受贿3151万余元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是向曾锦春行贿次数多达16次,金额合计多达240余万元的某位行贿人最终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此类案件不胜枚举[9]。
正是因为实践中存在对行贿人过度宽大的问题,近来很多人提出要修改现行刑法中的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严格限制对行贿罪的从宽处罚,以便加大对行贿罪的惩罚力度,纠正“重打击受贿,轻打击行贿”的倾向,甚至有人提出了对受贿和行贿同等处罚的激进倡议。
笔者认为,实践中过度宽宥行贿人的现象固然应当纠正,但是导致过度宽宥行贿人的原因不在于现行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的特别从宽处罚制度,而在于办案机关对该条规定的理解不当和执法偏差。应当准确理解、正确适用我国现行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规定。需要特别澄清的几个认知是:对于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其行贿犯罪的行贿人,刑法条文规定的是“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而不是“应当”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司法机关适用该条文的正确做法应当是在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二者之间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其一”,而非都是“免除处罚”“免除处罚”的实现方式包括“定罪免刑”“相对不起诉”和不予刑事立案三种情况,而非都是“不予刑事立案”“免除处罚”不等于“免除刑事责任”。遗憾的是,实践中一些办案机关片面理解和不当适用了我国现行刑法第390条第2款,导致一些本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贿人被过度宽宥。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属于执法上的偏差,并非立法上的缺陷。也就是说,现行刑法规定的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本身是科学合理的,今后要注意纠正的是实践中的执法偏差,而纠正执法偏差的要领应当是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刑法的规定,而不应将执法偏差推脱给立法,否则未能“对症下药”,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1]赵秉志,于志刚.论我国刑法分则中的特别自首制度[J].人民检察,2000(3):18.
[2]张智辉.受贿罪立法问题研究[J].法学研究,2009 (5):170.
[3]李少平.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J].中国法学,2015 (1):6.
[4]陈屹立,张卫国.惩罚对犯罪的威慑效应: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方经济,2010(8):41.
[5]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下册)[Z].黄道秀,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6]克罗地亚刑法典[Z].王立志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
[7]周国均.借鉴“刑事免责”制度和“证据强制”规则之构想[J].中国法学,2003(5):153-156.
[8]肖洁.行贿犯罪查处的困境与解决途径[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8):95-96.
[9]李少平.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J].中国法学,2015 (1):6.
(责任编辑:袁宏山)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Especial Lenient Punishment System of Bribery Crime
HUANG Huasheng,LI Wenji
(Law School,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The especial lenient punishment system of bribery crime in our present criminal law is legitimate.The Modification plan in the ninth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Draft)which strictly limits the special lenient punishment of bribery crime is in fact not needed.
bribery crime;especially lenient punishment;ninth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D924.392
A
1008—4444(2015)05—0064—04
2015-01-28
黄华生(1969—),男,汉族,江西宁都人,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挂职担任九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以106份刑事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
——兼论《刑法修正案九》行贿罪新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