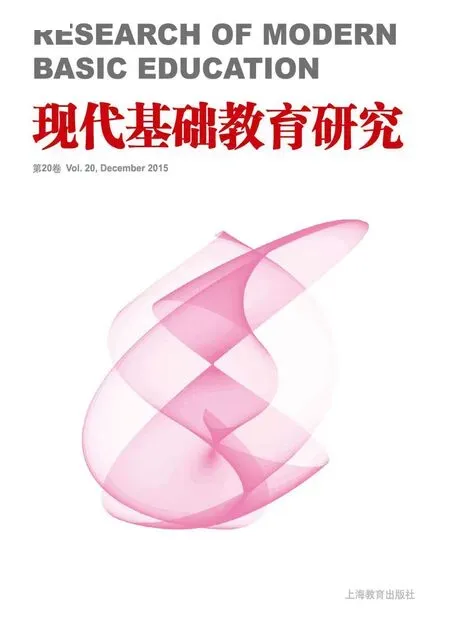论家庭治疗在学校心理咨询中的适用性
李正云,徐欣颖
(上海师范大学 心理咨询与发展中心,上海200234)
一、家庭治疗及其应用进展
家庭治疗是一种从家庭视角来审视来访者的心理问题,并经由任何形式的语言、互动等治疗行动而促使家庭有所改变的治疗体系,其目的在于消除心理疾患,使家庭成员更加分化、更加自由地完成个人及家庭整体发展的阶段性任务。
家庭治疗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Christian Midefort和Nathan Ackerman分别出版的《心理治疗中的家庭》和《家庭生活的心理动力学》为标志。在家庭治疗实践者们的努力下,家庭治疗已成为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内继精神动力学、认知行为主义、人本主义之后崛起的“第四势力”。家庭治疗已发展出多种模型,基本模型有:心理动力模型、经验模型、代际模型、结构模型、策略模型、米兰系统模型和认知行为模型。随后现代思潮而兴起的新模型有:叙事模型和心理教育模型(I-rene,G.,& Herbert,G.,2005)。
家庭治疗于20世纪80年代末传入我国以来,已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并应用。刘晓敏、曹玉萍、施琪嘉等人(2013)采用多级分层方式抽样,在中国内地6个行政区选取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的从业者1232名,包括教育、医疗和其他从业系统,以及经济发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城市。使用《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人员现状调查问卷》中的“疗法和疗效”部分,调查从业者的常用疗法和首选疗法。结果发现,常用疗法为家庭治疗的从业者,教育系统占9.6%,医疗系统占23.5%,其他系统占15.9%,在53种疗法中排列第4。目前家庭治疗在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神经症、物质滥用、网络成瘾、儿童或青少年情绪行为障碍及心身疾病中均有临床应用(杨建中,赵旭东,康传媛,2002)。
纵观目前国内外有关家庭治疗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报告,多集中在专业的精神科医疗及社会机构中,而家庭治疗在学校心理咨询中的研究报告却相对较少,并且还主要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可见,家庭治疗在学校心理咨询工作中的应用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一项对74所高校心理咨询机构的调查显示,开展个体咨询的学校占81%,开展团体咨询的占35%,家庭治疗未进入调查范围(鞠丹,2006)。
二、家庭和家庭关系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和家庭关系,特别是母亲抑郁和父母化对儿童青少年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有重大影响。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母亲抑郁对青少年的精神疾病都是严重的风险因素(Hirshfeld-Becker et al.,2008;Kim-Cohen,Moffitt,Taylor,Pawlby,&Caspi,2005)。抑郁的母亲更可能认为自己是糟糕的家长,对孩子的成长与发展几乎没有掌控力。母亲的抑郁也影响其有效监控孩子、适当给予惩戒和提供温暖与支持的能力(Goodman,2007)。国外的临床研究综述表明,与治疗有关的母亲抑郁的降低和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的改善之间是有关联的(Gunlicks & Weissman,2008)。相反,治疗中若无法降低母亲的抑郁,孩子的行为表现也会很糟糕(Weissman et al.,2006)。
所谓父母化(Parentification),就是父母与孩子的角色倒转,是一种并不成熟的对父母期待与需要的认同,其代价就是童真的缺失。Wells和Jones(2000)对197名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童年期的父母化和成人期的害羞倾向是关联的,父母化通常会让孩子因为真正的自我未获报偿而感到羞愧。咨询师需要帮助父母化的大学生梳理家庭结构带来的冲击,提升自我价值感。Katz等人(2009)对163名来自完整家庭的女大学生所作的回顾性问卷调查研究发现,与母亲之间的角色倒转能够预测女儿的抑郁状态,并且导致当下过度的保障寻求(Excessive Reassurance-Seeking,ERS),即询问别人是否真正关注自己的倾向。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角色倒转增加了今后人际关系困难的风险,这可能是来源于心灵深处的(如焦虑型依恋),也可能产生于真正的人际压力(如ERS)。研究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帮助来访者以非评判的方式重新评估曾经分裂的家庭层级,对该类型青春期女孩的治疗应鼓励并强调家长的参与,以家庭治疗的方式进行。
在中国文化中,孩子是家庭的核心,家庭特别关注甚至是过度关注子女的成长。Sze、Hou、Lan和Fang(2011)调查了北京一所家庭治疗中心的612例个案,包括其人口统计学数据和所呈现出的问题。研究发现,与西方文化的经验不同,该中心的个案主要都是关于家庭中孩子和青少年的问题。较为典型的是关系问题,主要表现在将与子女的关系凌驾于夫妻关系之上,夫妻关系在三种家庭关系(母子、父子和夫妻关系)中的地位最低,过度关注孩子的问题,研究结果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研究者同时强调,孩子的学业问题很可能只是表象,不要错过或否认其他重要的问题,比如抑郁和焦虑。
有研究者在家庭治疗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家庭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强调避免人际冲突,培养人际和谐,这在功能良好的西方家庭中并不显著。Shek(2000)在香港地区所作的一项历时2年的调查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品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预测性是不同的。尽管父亲通常和孩子的距离更远,但来自父亲的影响比来自母亲的影响更会影响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因此,在中国人家庭的家庭治疗中,一定要重视不同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作用。
三、家庭治疗对青少年学生个案的有效性研究
1.有关大学生适应障碍的家庭治疗研究
有一例结合大学生适应障碍的个案治疗,尝试展现系统家庭治疗灵活而有效的实务操作,同时对出现精神病性倾向家庭成员的家庭关系进行了探索性的理论讨论(张捷,陈向一,邓云龙,徐赟,2011)。该研究认为,大学生适应障碍不仅是家庭中孩子出现的问题,而且与家庭因素紧密相连,其家庭还恰好处于转换期。在共计6次的家庭治疗中,咨询师通过中立和共情建立与家庭的治疗联盟,帮助家庭成员表达情感。在第2次到第5次的工作阶段,咨询师运用差异性提问、循环提问等技术采集有关家庭的新信息,并基于新的信息修正原来对家庭的假设。然后以证伪的取向保持中立与共情验证假设的正误,在这个过程中关注关系、互动和系统的资源,这不仅巩固了治疗联盟,同时获得了新的家庭信息。通过6次家庭治疗,家庭的交流模式得到改善,父亲、母亲和孩子(大学生)之间的边界进行了重建,家庭氛围也得到了改善。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咨询师常常带领家庭在关注问题的时候不时看看家庭的力量,在感受家庭力量时回望家庭目前的困扰。对家庭资源的关注不仅体现在找到家庭的力量,还体现在提升家庭的控制感、营建轻松的治疗氛围上。
武志伟(2012)用系统式家庭治疗的方法为一位厌学并且家庭关系不良的青少年提供个案服务,最终让个案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点融化的迹象。
可见,大学生适应障碍可能源于家庭关系、家庭互动和家庭教养方式等方面,家庭治疗可以改善家庭关系和互动。
2.有关青少年进食障碍的家庭治疗研究
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AN)是一种常见的身心综合征,是以病人自己有意地严格限制进食、体重下降至明显低于正常标准或严重的营养不良,伴有恐惧发胖或拒绝正常进食为主要特征的一种进食障碍(史靖宇,赵旭东,缪绍疆,2008)。神经性厌食症主要见于13~20岁之间的年轻女性,其中,17~20岁的发病高峰正处于大学阶段(另一个发病高峰是13~14岁)。
我国学者梅竹和孟馥(2003)应用结构式家庭治疗理论,采用参与、重新框架、行动促发等技巧,通过按摩问题、维持问题、改变问题等方式对1例神经性厌食症患者(18岁)进行共计10次、为期3个月的家庭治疗。通过治疗,患者体重上升6公斤,抑郁症状得到改善。在3个月的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努力改变家庭关系结构:拉开母女距离,鼓励夫妻多沟通,修正夫妻子系统缺失功能部分,协助家庭发展更清晰的界限,学习以协商来达到所希望的改变,使本来无助的患者学会怎样和父母做正常的交流,学会正视母亲对她的控制,不再需要以绝食抗议。研究者总结到,神经性厌食症的病因之一在于错误的家庭结构,改变家庭结构有助于消除相应的症状。因此,对神经性厌食症患者予以结构式家庭治疗,可增进疗效、改善预后。
陈志青等人(2008)对12例门诊神经性厌食症患者采用与患者一起绘制家谱图的形式,以结构式家庭治疗理论对家谱图进行解释与分析,结果表明,家谱图在神经性厌食症的治疗中,对于揭示家庭结构和功能的不良、规划治疗的方向、评价治疗的效果以及激发患者和家庭的内省等方面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可见,家庭治疗现已成为我国精神科医师治疗青少年进食障碍的常用治疗方式,大量个案研究结果对其在高校心理咨询中的应用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3.有关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家庭治疗研究
网络成瘾综合征(IAD,简称网瘾)是指在无成瘾物质的作用下的上网行为冲动失控,表现为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的学业失败、工作绩效变差、人际关系不和谐等一系列的社会、心理功能损害,网瘾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卢言慧,杨永信,慕江兵,魏秋香和孙振晓,2013)。
卢言慧等(2013)将120例网瘾患者随机平均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临沂市精神卫生网络成瘾综合征(IAD)戒治中心常规的综合干预,试验组还进行萨提亚家庭治疗,依据萨提亚家庭治疗基本内核:(1)“我自己”,内在和谐、做自己的主人;(2)“我”与“另一个人”,关系和睦;(3)“我”所处的人际系统(家庭或组织),社会和谐、家庭或组织成员之间和谐、协作、有凝聚力等。治疗结束后,采用网瘾自测量表和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分别对两组研究对象作干预前和干预后5个月情况的测查,结果发现,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较常规的综合干预,更能提高网络成瘾患者家庭的亲密度和适应性,有效改善亲子关系,对IAD的戒治有积极作用。
刘学兰等人(2011)认为,家庭治疗在网络成瘾干预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有利于改善家庭环境和家庭功能;(2)有利于完善青少年的人格及社交技能;(3)能够满足青少年的情感需求和沟通需要。
4.有关抑郁和自杀个体的家庭治疗研究
Harrington等人(1998)的研究发现,对故意服药但并非抑郁的青少年实行简短的、基于家庭的干预,在降低其自杀念头方面,比常规看护更为有效。该研究的基本原理在于,青少年服药与家庭功能失调紧密关联,那么,改善家庭功能就应该能够减少青少年的自杀倾向,并降低他们在家里所感受到的压力。该干预项目有5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青少年从过量用药中苏醒过来之后马上开始,在医院或家里都可进行,其余4个阶段在家里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评估会谈,用以解释干预项目及确定目标;第二阶段是讨论干预项目本身;第三阶段聚焦于沟通;第四阶段是问题解决;最后阶段是一些有关青少年的发展问题及其对家庭的影响。干预过程鼓励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参加,但只要青少年当事人和至少一位家长参与就可视为一次干预。
Huey等人(2004)随机分配精神科急诊的年轻患者接受多系统家庭治疗(Multi Systemic Therapy,MST)或住院治疗。在治疗前评估病人的自杀企图、自杀意念、抑郁情绪和父母亲的控制,并在治疗结束后4个月和1年时进行回访研究。结果表明,根据患者1年后回访的报告,多系统家庭治疗比住院治疗在降低自杀企图的比率上更加有效,但在自杀意念、抑郁情绪或无望感方面未见显著差异,这恰恰佐证了家庭在自杀危机干预上的重要作用。
Diamond等人(2013)对有自杀倾向的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Lesbian,Gay,and Bisexual,LGB)青少年采用以依恋为基础的家庭治疗(Attachment-Based Family Therapy,ABFT),并在对这一群体进行治疗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上获得了初步的数据。在治疗的第一阶段,该治疗发展小组修改了ABFT以满足LGB自杀倾向青少年的需要:(1)用更多的个别治疗时间处理家长对孩子非主流性倾向的失望、痛苦、愤怒和恐惧;(2)提出接受的意义暗示和处理;(3)让父母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应对孩子性倾向时所表现出的不露声色但仍显强势的否定态度。第二阶段,有10位对象接受了为期12周的特定ABFT治疗。在治疗前、治疗进行到第6周时和第12周时分别评估自杀念头、抑郁症状和与母亲依恋相关的焦虑及回避。第二阶段的治疗结果表明,治疗效果得以保持,自杀想法、抑郁症状和与母亲依恋相关的焦虑及回避都显著降低,这些都是对该群体青少年可有效实行家庭治疗的证据。
可见,抑郁个体的家庭治疗在降低自杀企图、缓解家长焦虑和调整家庭认知等方面都有较好的成效。
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对家庭治疗的需求调查
随着时代的变革,经济的发展,现如今的90后大学生,他们的家庭结构与成长环境差别很大。父子的争锋相对、母女的过分纠缠、父母的冲突爆发等问题都极可能影响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而以人际关系、学业压力、网络成瘾、恋爱情感等看似单一的心理困惑表现出来。从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个案梳理情况看,来访学生中家庭关系及亲子冲突问题不少,再加上学生学业、就业、恋爱、人际关系问题的处理多与家庭关系有关,上海师范大学在此前对咨询师队伍进行系列家庭治疗专业培训的基础上,已经开展和应用家庭治疗于学生个案中。相关个案的治疗进展也支持家庭治疗的必要、可行及有效。
笔者所在课题组向上海10所高校的心理咨询师及辅导员发放自编问卷调查表,分别从咨询师和辅导员的角度调查心理咨询工作和学生思政工作中家庭治疗的适用性以及家校联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接受本次调查的心理咨询师为上海地区的部属重点高校、市属重点高校及本专科院校,共计20人,平均年龄35岁,平均工作年限为7年;接受本次调查的高校思政辅导员共计42人,平均年龄30岁,平均工作年限为5年。
参加问卷调查的20位心理咨询师中,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请学生家长一起参与咨询,因为家庭的高期望是造成学生心理困扰的重要原因,有11位咨询师详细阐述了家庭对来访大学生主诉问题的影响。他们认为存在人际困扰的来访学生,往往与父母或其他家庭主要成员的关系不佳;在帮助学生走出与家庭有关的困惑的过程中,70%的咨询师希望整个家庭一起介入,40%的被调查者并不赞同“家丑不可外扬”这一传统观念;与此同时,55%的咨询师参加过以家庭治疗为主题的专业培训。可见家庭治疗在高校的运用已有一定的专业基础。
对于高校实施家庭治疗的困难所在,75%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客观原因导致,比如父母在外地,不太可能来学校;45%认为父母不愿参与会导致家庭治疗在高校无法实施;认为目前尚缺乏家庭治疗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咨询师分别占30%和45%,这一结果提示家庭治疗在高校的运用需要从专业指导、实践操作和家庭实际三方面综合考虑,需要逐步推进。
42位参与调查的辅导员中,超过四成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学生工作中,主动与家长联系非常必要,说明辅导员工作普遍重视家校联系,重视家庭情况对学生大学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在辅导员的工作实践中,45.2%的被调查者发现,对于人际交往方面出现问题的学生,与其家长沟通通常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另一方面,超过半数的辅导员认为,在学校人际关系糟糕的学生,其与家长的相处也不融洽;7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家庭的高期望是造成学生心理困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帮助学生走出困惑的过程中,他们希望整个家庭一起介入;在与家长沟通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现家长与学生之间沟通方式的相似性;对于人际交往方面出现问题的学生,可以邀请家长定期到校参与学生问题的讨论,或是与学校定期电话联系,与学校一起帮助学生走出困境。
从咨询师和辅导员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家庭治疗对高校心理咨询师并不陌生,既有共识又有专业实践探索。而家庭关系也是高校辅导员在了解大学生生活、学习状况时重点参考的内容之一,并且家校联动已经在辅导员工作实践中广泛涉及。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需要家庭治疗的介入,家庭治疗在高校心理咨询中的适用有基础、有共识、有依据。
五、关于家庭治疗的应用及思考
1.拓展“一个人的家庭治疗”
家庭治疗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强调以家庭系统和家庭关系为视角,将个案学生的问题置于家庭背景下审视,从而达到家庭系统和功能更健康、个体分化更好以及家庭沟通更清晰的目标。但是家长来校困难重重(主观不愿意或客观上时空不允许),尤其是大学生通常来自全国各地,有时迫于现实困难,即便最适合做家庭治疗的学生,也很可能无法要求其家庭成员一次次到校参与咨询。在由于地理距离等因素导致学生家长无法到校的情况下,可通过电话等远程方式灵活开展家庭治疗。同时家庭治疗的后期发展更是提出了“一个人的家庭治疗”概念,使得家庭治疗的形式更加灵活,尤其对处于青春期的学生而言,客观上远离家庭对他们是非常好的自我分化契机,而这更是给一个人的家庭治疗提供了有力支持。
McGoldrick和Carter(2001)详细论述了一个人的家庭治疗由至少5部分的重叠过程组成,包括:(1)与来访者的约定,通过在不同家庭系统层面(如父母层面、亲子层面等)询问来访者相同的问题,鼓励其拓展看待自己当下问题或主要关系的视角,由此展开三角关系和自动化反应的过程等系统化概念的讨论;(2)了解家庭系统和个人自身的任务,通过通俗而轻松的提问方式帮助来访者深入了解其家庭关系的基调与历史,包括其所卷入的三角关系等,根据家谱图讨论将来访者置于更为客观的“研究者”的位置来看待自己的家庭,而不是一直被内疚与抱怨淹没;(3)再次介入,鼓励来访者发展与每一位家庭成员之间富有情绪性连接的关系,改变过往反复出现的、功能失调的情绪形式;(4)强调改变,帮助来访者澄清自己在言行上究竟哪些方面是需要改变的,继而帮助来访者在家庭中表现出更符合自身信念的行为;(5)坚持到底,随着咨询的推进,一些来访者会感受到各种领悟或改变的困难。咨询的时间间隔经常会因为来访者需要从学习与计划转向付诸行动而被延长。一个系统式的治疗师几乎不会在与来访者共同决定结束工作之前就终止个案,而是会逐渐延长咨询间隔,用以讨论来访者做出改变后可能面临的困境甚至是危机,也可能一、两年后,来访者因曾经的家庭问题继续求询。
2.将家庭治疗理念技术融入学生思政工作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家庭治疗不仅仅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治疗体系,其系统论视角以及对单一因果的摒弃和对循环因果的强调也同时为学校的学生工作,尤其是家校互动形成家校合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创造性地运用家庭治疗的理念和方法,以系统视角和循环因果思维对学生和家长的问题和需求进行分析,将其置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层级系统中,探讨系统中各人的位置、动力、变化和角色功能,从而达成工作共识,形成工作合力。笔者咨询的一个辅导员和家长个案即是如此。
一个周五中午,某大三辅导员赶到咨询中心求助:他所带的大三学生小芳周四买票离校后没有回家,不知去向,家长和辅导员心急不已。该生和父母关系多年以来非常紧张,其父母出于无奈求助于辅导员做工作。学生出于报复父母,也不满意于辅导员替父母说话而出走,辅导员工作陷于被动。咨询师在协助找到学生后,决定邀请学生家长和辅导员来校心理咨询中心,以家庭治疗的系统视角和循环因果观协助辅导员和家长认识到他们在学生、家长和辅导员(包括咨询师)大系统中各自合适的角色和功能。咨询中,咨询师邀请父母各自审视他们不同的功能,领悟其间的差异,调动这一对父母的合力。之后,以团体雕塑的方式,现场呈现当父母困于亲子冲突而求助于辅导员时,辅导员与父母的不当结盟将破坏辅导员与学生的良好联盟。同理,咨询师与父母的不当结盟将破坏他与学生的良好联盟,其结果是导致学生对辅导员和咨询师的拒绝,使学校对学生的支持和帮助系统中断,学生彻底失控和失管,而这是辅导员不愿看到和难以承受的,继而家庭的压力放大,而这也不是家长愿意看到和承受的。通过咨询,辅导员认识到在三方系统中,师生联盟是首要基础,其次才是与家长联盟。家长学习的是父母联手共同应对亲子冲突,对辅导员和咨询师的求助以不破坏师生联盟为前提。
可见,家庭治疗的系统观不仅可以帮助专职咨询师拓展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服务范畴,而且可以帮助、融入和拓展学生辅导员的家校工作。基于家庭治疗的系统性、多方参与、注重关系等理念,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从中借力。
3.加强家庭治疗的专题培训
一种治疗体系的推广和应用,队伍是关键。为了推广应用家庭治疗,自2012年始,借助上海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区域示范中心这个平台,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与发展中心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每年定期举办为期5天的“结构式家庭治疗现场示范课程”,主要面向上海市高校心理咨询中心的近30名专职咨询师。课后收获及满意度问卷评价表明,学员对培训内容、效果及对工作的指导性等满意度达99%,具体体现在家庭治疗理论和技术的掌握,以及学生辅导和团训工作能力的提升。连续4年的培训和跟进的相关督导,为家庭治疗在上海高校的推广应用培养了骨干队伍。
六、结论
家庭治疗引入学校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必要且可行有效;家庭治疗在学校心理咨询中可以以家庭为单位,也可以重点拓展一个人的家庭治疗;家庭治疗的系统观可以帮助、融入和拓展学生辅导员的家校工作;加强专业人员的家庭治疗培训是家庭治疗应用于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关键条件。
[1] Diamond,G.M.,Diamond,G.S.,Levy,S.,Closs,C.,Ladipo,T.,&Siqueland,L.(2013).Attachment-Based Family Therapy for Suicidal Lesbian,Gay,and Bisexual Adolescents:A Treatment Development Study and Open Trial With Preliminary Findings[J].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1(s),91-100.
[2] Goodman,S.H.(2007).Depression in mothers[J].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3),107-135.
[3] Granic,I.,Otten,R.,Blokland,K.,Solomon,T.,Engels,R.C.M.E.,&Ferguson,B.(2012).Maternal Depression Mediates the Link Between Therapeutic Alliance and Improvements in Adolescent Externalizing Behavior[J].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6(26),880-885.
[4] Gunlicks,M.L.,& Weissman,M.M.(2008).Change in child psychopathology with improvement in parental depression:A systematic review[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47(4),379-389.
[5] Harrington,R.,Kerfoot,M.,Dyer,E.,McNiven,F.,Gill,J.,& Harrington,V.,et al.(1998).Randomized trial of a home-based family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who have deliberately poisoned themselve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37(5),512-518.
[6] Hirshfeld-Becker,D.R.,Petty,C.,Micco,J.A.,Henin,A.,Park,J.,&Beilin,A.,et al.(2008).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s in offspring of par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associations with parental behavior disorders[J].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11(2),176-184.
[7] Huey,S.J.,Henggeler,S.W.,Rowland,M.D.,Halliday-Boykins,C.A.,Cunningham,P.B.,&Pickrel,S.G.(2004).Multisystemic therapy effects on attempted suicide by youths presenting psychiatric emergencie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dolescent Psychiatry,43(2),183-190.
[8] Katz,J.,Petracca,M.,& Rabinowitz,J.(2009).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Daughters’Emotional Role Reversal with Parents,Attachment Anxiety,Excessive Reassurance-Seeking,and Depressive Symptoms[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37(3),185-195.
[9] Kim-Cohen,J.,Moffitt,T.E.,Taylor,A.,Pawlby,S.J.,&Caspi,A.(2005).Maternal depression and children’s antisocial behavior:Nature and nurture effects[J].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62,173-181.
[10]McGoldrick,M.,&Carter,B.(2001).Advances in coaching-family therapy with one person[J].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27(3),281-300.
[11]Nichols,M.P.,&Schwartz,R.C.家庭治疗——理论与方法[M].王曦影,胡亦怡,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12]Shek,D.T.L.(2000).Parental marital quality and well-being,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and Chinese-adolescent adjustment.the American[J].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2(28),147-162.
[13]Sze,Y.T.,Hou,J.,Lan,J.,&Fang,X.(2011).Brief Report:Profiling Family Therapy Users of a Therapy Center in Beijing[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39,299-306.
[14]Weissman,M.M.,Pilowsky,D.J.,Wickramaratne,P.J.,Talati,A.,Wisniewski,S.R.,&Fava,M.,et al.(2006).Remissions in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Child Psychopathology[J].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295(12),1389-1398.
[15]Wells,M.,&Jones,R.(2000).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and Shame-Proneness:A Preliminary Study.(28),19-27.
[16]H.Goldenberg &I·Irene Goldenberg.家庭治疗概论 (第六版)[M].李正云,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7]陈志青,陆新茹,华芳,杜亚松.家谱图在神经性厌食症患者治疗中的应用[J].上海精神医学,2008,(3).
[18]刘学兰,李丽珍,黄雪梅.家庭治疗在青少年 网络成瘾干预中的应用[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19]卢言慧,杨永信,慕江兵,魏秋香,孙振晓.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对网络成瘾患者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的影响[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3,(5).
[20]梅竹,孟馥.1例神经性厌食患者的结构式家庭治疗[J].上海精神医学,2003.
[21]钱玲,胡伟.家庭治疗的理念及应用简述[J].时代教育:教育教学刊,2012,(19).
[22]史靖宇,赵旭东,缪绍疆.青少年神经性厌食症的家庭治疗[J].上海精神医学,2008,(2).
[23]武志伟.系统家庭治疗模式在个别化青少年中的应用——基于一项个案的研究[J].社会工作,2012,(5).
[24]张捷,陈向一,邓云龙,徐赟.大学生适应障碍的系统家庭治疗个案报告[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12).
[25]赵旭东,宣煦.“资源取向”家庭治疗的操作技术[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9,(2).
[26]朱新,张晨.神经性厌食症的心理治疗[J].精神医学杂志,2011,(3).
[27]鞠丹.我国高校心理咨询及其发展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28]刘晓敏,曹玉萍,施琪嘉等.不同从业系统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的理论取向[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3,(8).
[29]杨建中,赵旭东,康传媛.家庭治疗在精神障碍治疗中的应用[J].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