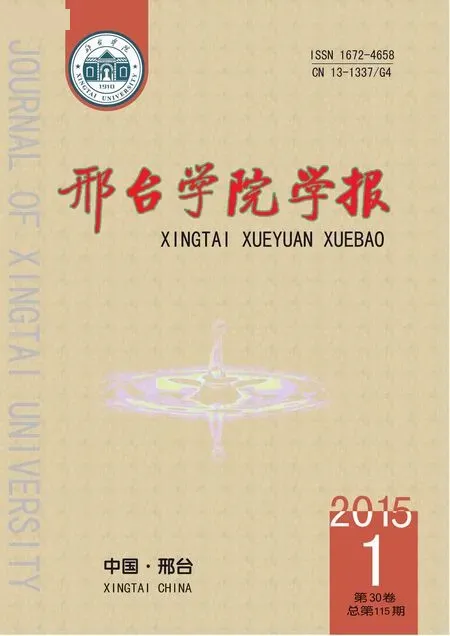玄学对魏晋南北朝审美意识的影响
张健旺
玄学对魏晋南北朝审美意识的影响
张健旺
(河北美术学院文化艺术教研室,河北新乐 050700)
魏晋玄学就是本体论哲学。本体论哲学是很高妙的抽象思辨,也可以说是纯粹理论思辨。魏晋士人对这种纯理论思辨的兴趣,更换了他们思维的帽子,对他们的审美意识有巨大的影响。无论是艺术本体论、艺术风格论、艺术批评论、艺术创作论、艺术素养论、艺术介质论、艺术发展观、艺术价值论,还是艺术意象论,魏晋南北朝人和先秦两汉人都不一样,可以说先秦两汉人的艺术理论兴趣思考的焦点是艺术的社会性,而魏晋南北朝人的艺术理论兴趣的焦点是艺术的艺术性。
玄学;审美意识;艺术
玄学是魏晋时代的哲学,玄谈是魏晋时代的风尚。庄子、老子、易经是他们玄谈的资源,被称为“三玄”,而“三玄”的核心范畴是“道”,而“道”是闻不到其声,看不见其形的,是我们感官无法把握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玄”,“玄”就是远的意思。例如“有无之辩”就是当时玄学的中心命题之一。 “有”可以说是对在具体时空中可以被感官把握的现象世界的抽象概括,“无”可以说是“有”的最终依据,除了这一点以外,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就是“无”的特性,语言是无法直接传达“无”的,只能在思辨中体味,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无”,他们认为是“有”的“本”,“有”是“无”的“末”,故要“崇本息末”或“举本统末”。我们可以用西方哲学词汇说“有”或“末”就是“存在”,而“无”或“本”就是“存在的本体”,那么魏晋玄学就是本体论哲学。本体论哲学是很高妙的抽象思辨,也可以说是纯粹理论思辨。魏晋士人对这种纯理论思辨的兴趣,更换了他们思维的帽子,对他们的审美意识有巨大的影响。先秦两汉的审美意识集中在艺术的实用功能上,而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审美意识集中在艺术本身。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里就明确地肯定音乐的美就在于音乐的和谐的形式美,也就是其“自然之和”,这是音乐的自然属性,与政治治乱和人心哀乐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可见嵇康“声无哀乐论”是对音乐艺术本身特征的把握,这种把握体现了玄学本体论的精神即“本末体用”。 音乐和谐的形式美即“自然之和”是自然之“本”的表现,而人心哀乐就是对这自认之“本”的用。故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本体论音乐美学。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明确地提出了“文本同而末异”论。这是对文学艺术本体的沉思。曹丕用“本”“末”思辨的玄学方法高屋建瓴地深思繁华多样的各类文体,突出了文的共同性,也突出了文的差异性。这种认识就具有辩证智慧的高度和深度。顾恺之的“传神”论,也渗透玄学的精神。“神”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的“本”或“体”“,形”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的“末”或“用”,而绘画的最高境界就是超“形”而“传神”,这和玄学的“崇本息末”或“举本统末”息息相关。这种对艺术本体的追问,是魏晋南北朝士人在玄学影响下开辟的新的问题域之一,可以概括为本体论审美意识的觉醒。
魏晋南北朝士人在玄学影响下开辟的新的问题域之二是艺术风格也成为他们理论兴趣的关注点。不同的艺术家用不同的艺术样式反映不同的内容,充满了差异,他们有没有共同点,如果有,它是什么。艺术品与艺术家到底有什么关系,这还是玄学对“本”的追问精神的体现。艺术的“本”就是艺术家,所以魏晋士人特别关注人的胸襟气象,他们品藻人常常说什么“风神”、“风韵”、“风姿”、“神彩”、“神骏”、“神貌”、“神味”、“神明”、“神隽”、“神怀”、“神气”等等词汇;他们品藻人物也常常说什么“清畅”、“高清”、“清新”、“清允”、“清识”、“清便”、“清鉴”、“清真”、“清淳”、“清蔚”、“清竦”等等词汇,其实这些词汇说的就是一个人的个性或生活情调,也可以说是对一个人生活风格的赞叹,而一个人的生活风格影响他的艺术风格。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说“文以气为主”,而“气之清浊有体”,也就是文章中的“气”是由艺术家不同的个性所形成,这就非常明确地肯定了艺术风格与生活风格的联系。其实魏晋艺术之所以精彩绝伦,主要是他们有鲜明而特异的生活风格,他们的艺术就是他们生活风格的传达和再现。例如,我们常常说王羲之的书法风格是飘逸,其实王羲之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飘逸风格的人,《世说新语》里就说他“飘如游云”。 这不就是对他飘逸个性的生动描述吗?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就专门讨论艺术风格与艺术家才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把文学艺术的风格概括为八种类型: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这充分体现了玄学思维的“以一统多”或以“一治多”的精神,把千变万化的艺术高屋建瓴地归纳为八种基本类型,就是玄学方法的灵活运用。这些可以概括为艺术风格审美意识的觉醒。
魏晋南北朝士人在玄学影响下开辟的新的问题域之三是艺术批评标准也成为他们理论兴趣的关注点。艺术品或艺术创作有没有自身的“本”,如果有它是什么。这还是玄学对“本”的追问精神的体现。顾恺之的“传神”论,其实也是人物画的批评准则。人物画的好不好,就看艺术家画的“传神”不“传神”,这完全是艺术的标准,不是伦理的标准,也非实用的标准。《世说新语》记载顾恺之画裴叔则,在他的面颊上加了“三毛”,看画者就认为十分的传神。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认为“五声有善恶”的区别,即好听不好听的区别,而与人心的哀乐、政治的治乱没有关系。他的结论是:“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这也完全是艺术的标准,不是伦理的标准,也非实用的标准。曹丕的“诗赋欲丽”的标准,也是完全艺术的标准,不是实用的标准,且曹丕非常明确地划分出不同文体的不同准则,实用的“奏议”“宜雅”,实用的“书论”“宜理”。用今天的文体划分来说,“奏议”、“书论”是应用文,而“诗赋”则是文学艺术。刘劭在《飞白书势》说“飞白之丽,貌艳势珍”也是用“丽”、“艳”来判断书法的审美价值。这些都可以概括为纯艺术批评的觉醒。
魏晋南北朝士人在玄学影响下开辟的新的问题域之四是艺术家的艺术构思也成为他们理论兴趣的关注点。在绘画领域体现在顾恺之的“迁想妙得”论。“迁想”就是要积极充分地发挥艺术家的艺术想象,而“妙得”就是在艺术想象里扑捉能体现人精神品质的风神或神韵。在书法领域里体现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提出的“凝神静思”和“贵乎沉静”论。这是对书法创作心态的思考。在文学领域体现在陆机《文赋》里。《文赋》是有名的系统论述文学创作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陆机提出了“玄览”,即强调艺术家创作前必须具有虚静的境界,精神专一,思虑清明,才能烛照万有,心物合一。陆机对艺术想象的认识十分深刻精辟:“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艺术想象不受空间的阻隔;“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艺术想象也不受时间的限制;“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艺术想象又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艺术形象就孕育而呈现在如此丰富的艺术想象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里提出的“神与物游”论,也是对艺术创作的探索。 这些都可以概括为艺术创作论的觉醒。
魏晋南北朝士人在玄学影响下开辟的新的问题域之五是艺术家的艺术素养也成为他们理论兴趣的关注点。大名士嵇康有《养身论》,宗炳在《明佛论》里明确说“若老子、庄周之道,松乔列真之术,信可以洗心养身”,陆机在《文赋》里也积极提倡艺术家要“颐情志于《典》《坟》”,也就是艺术家要用传统经典涵养自己的性情。刘勰《文心雕龙》则专门有“养气”一篇论述艺术家素养,可以说是对魏晋南北朝这一问题的理论总结和提高。这些可以概括为艺术素养论的觉醒。
魏晋南北朝士人在玄学影响下开辟的新的问题域之六是对艺术介质也成为他们理论兴趣的关注点。玄学中的“言意之辩”更新了魏晋南北朝士人对语言文学性的高度重视。他们认识到了作为抒情达志的语言介质,是粗糙的工具,即“言”不能尽“意”是文学必须接受的事实。陆机《文赋》集中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就是“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那么,如何使语言在传情达意上生出细致而非粗糙的艺术效果,魏晋士人热情地思考了这一问题。他们积极倡导要“巧言”,要“巧思”,要“巧喻”,要“巧构”,也就是说要恰如其分地发挥语言介质的功能。这些可以概括为艺术介质论的觉醒。
魏晋南北朝士人在玄学影响下开辟的新的问题域之七是艺术发展也成为他们理论兴趣的关注点。在书法领域,虞龢认为钟繇、张芝与王羲之、王献之相比,钟繇、张芝的书法古质,而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艳美,也就是他说的“古质今艳”。虞龢认为形成钟繇、张芝的书法古质,而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艳美的原因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就是他说的“数之常也”。 虞龢的结论是钟繇、张芝,还是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都是“独绝”,都是“楷式”。在文学领域里,刘勰有《通变》篇。他积极肯定了“通则不乏”的文学发展观,且倡导文学家即要“参古定法”,又要“望今制奇”,才能是文学健康发展,而避免陷入繁华损枝的歧途。可见他们不是用僵死的观点看问题,而是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体现了辩证智慧。
魏晋南北朝士人在玄学影响下开辟的新的问题域之八是对艺术价值的重新思考。先秦两汉人对艺术的价值的理论兴趣集中在伦理道德的实用范围内,而魏晋士人由于受玄学的影响,更换了思维的帽子,在旧的问题领域里也发现完全不同的景观。宗炳在《山水画序》里就非常明确地说山水画的功能就是“畅神”,即精神舒畅愉快,这是纯粹的审美,这就不是所谓的“比德”,即用山水的特新类比道德伦理,充满了实践功利的羁绊。魏晋士人的“以玄对山水”也是对山水的纯粹美的欣赏与陶醉,荡尽了世俗的尘埃,使山水成为他们一往情深的知己,充满媚态,可亲可狎。陆机在《文赋》里把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明确规定在“兹事可乐”,即在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的欣赏活动中,人能获得最充分的精神快乐和精神慰藉。这也是对传统文学狭隘实用价值观的突破。这些可以概括为纯艺术价值观的觉醒。
魏晋南北朝士人在玄学影响下对艺术“意象”的发现和思考。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里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这里的意象,完全就是审美意象,不是玄学的“意”,也不是玄学的“象”,而是刘勰的独创,显然受到玄学的“言意之辩”的智慧启迪。谢赫在《古画品录》里说绘画“若取之象外”,才“方厌膏腴”,即韵味无穷,才“可谓微妙也”。如果把意象理解为所以艺术品的艺术本质,那么魏晋南北朝士人在玄学影响下对艺术“意象”的认识就是理论上一次质的飞跃,如果把“意象”理解为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典型,那么魏晋南北朝士人在玄学影响下对艺术“意象”的认识就是一次巨大的理论贡献。
总之,无论是艺术本体论、艺术风格论、艺术批评论、艺术创作论、艺术素养论、艺术介质论、艺术发展观、艺术价值论,还是艺术意象论,魏晋南北朝人和先秦两汉人都不一样,可以说先秦两汉人的艺术理论兴趣思考的焦点是艺术的社会性,而魏晋南北朝人的艺术理论兴趣的焦点是艺术的艺术性。东晋道教徒葛洪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畅玄》,“畅玄”就是哲学的纯粹理性愉悦,“畅神”就是艺术的纯粹迷醉。“畅玄”给他们的“畅神”一种纯度,洗尽了尘滓,独流一份神明;“畅玄”给他们的“畅神”一种高度,远离了质实,独留一份空灵;“畅玄”给他们的“畅神”一种深度,远离了枯淡,独留一份“深味”。
总之,魏晋玄学是一种本体论哲学,有很强的思辨哲学的特征,他们思辨的“本”与“末”,“有”与“无”,“言”与“意”,“一”与“众”“静”与“动”,“明教”与“自然”等等话题都是对事物的两面,而不是一面的探讨。这种哲学思辨,极大地刺激了士人对艺术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探讨,故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审美意识具有思辨哲学的精神。这是玄学的积极作用和积极的贡献,是主要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玄学带给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并不全是艺术的福音。黑暗和光明是事物的两面,光明放大的同时,黑暗面也在悄然延伸。他们同时代的钟嵘在《诗品》就大胆而深刻地批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现象。顾恺之的“传神”论有重“神”遗“形”之危险,特别是当“传神”成为所有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时,成为艺术批评的金科玉律时,艺术家和批评家时时流露轻视艺术写实的冲动,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潜在伤害,特别是在那些所谓追求写意的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品里这种伤害是很明显的。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存在割裂音乐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总之,魏晋士人在“明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们的口号是“越明教而任自然”,轻视“明教”而重“自然”,他们的人生观是放任自由。这种人生观虽然给他们带来了思想的解放,精神的自由,但是他们思想的解放,精神的自由的却是信仰破坏后的沉沦,人之为人尊严和价值的丧失。在那样一个政治龌龊黑暗的时代,不需要他们拥有济世志,没有人理解他们,没有人尊重他们,他们动不动就被杀,就被宰。他们“任自然”的人生观里埋藏着他们的理想毁灭的痛苦,流露为人尊严丧失的悲痛。再说,有些士人在“任自然”生活风尚的影响下,“溲便于人前”,完全沉沦为禽兽,羞耻心丧失殆尽。即使象嵇康这样的大名士,也说自己“不喜俗人”,而“轻肆直言”被杀,故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审美意识缺乏广阔的同情心,浩博的社会关怀。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张少康.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叶朗.中国历代美学文库[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014-09-18
张健旺(1976-),男,宁夏海原人,陕西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河北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美学.
I01
A
1672-4658(2015)01-01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