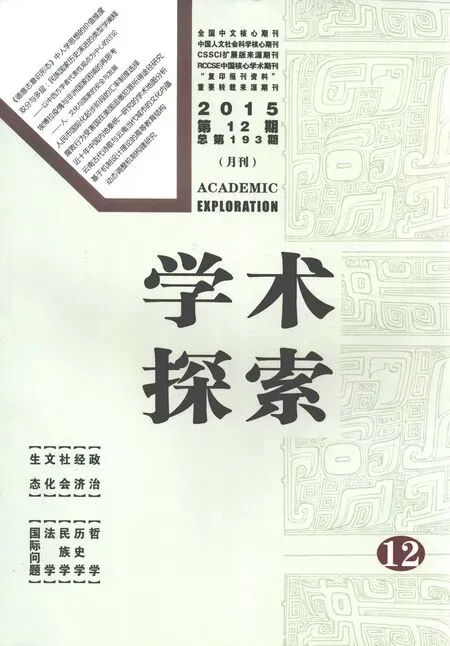无心而顺性即是独化
——郭象玄学意义上的“心性论”刍议
刘 晨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无心而顺性即是独化
——郭象玄学意义上的“心性论”刍议
刘 晨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在郭象的玄学体系中,独化论是基础,在此基础上郭象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道家的自然相结合,形成了玄学意义上的人性论。郭象并不否认“仁”为人性,而是以自然来解释人性,将“仁”释作人性的自然,并以“无心”作为实现自然人性的途径。这样的心性论是以实现人个体生命的自我安顿为目标的,并期望以此来实现由一个个适性独化的个体所构成的和谐的社会整体。由无心而顺性,无心而体化,正是郭象玄学意义的心性论的体现。
心性论;无心;人性;独化
魏晋玄学的发展过程中,郭象的独化自生说无疑是独具特色的,他既否定了能生成万物的造物主的存在,又否定了超越于万物存在之上的道的存在,把万物的存在归结于存在自身。在郭象看来,天道即是万物独化之道,而人不过是“万化之一遇耳”(《庄子·大宗师注》),作为“万化之一遇”的人存在于世间,当然也就要遵循万物独化之道了,这样要使人道合乎天道就是要实现人的“独化”,而人的“独化”的就是人的理想的存在方式的实现。正是在强调人的独化的实现过程中,郭象将“无心”“顺性”和“独化”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玄学意义上的心性论。这样的心性论是以独化自生为基础,以实现人的独化为目标的。以下,我们就试图从“无心”的含义、“无心”而顺“性”、“无心”而体“化”三个方面来看看郭象的玄学意义上的心性论,亦即如何通过无心之法来实现“人之独化”。
一、“既遣是非,又遣其遣”的无心
在郭象那里,“独化”就是事物的存在的状态和方式,事物无识无知,一切变化皆是无目的、依性而自化的、自然而然的,而人则不同,人有识、有知、有思虑,其行为往往是有计划的、带有某种目的的、对结果患得患失的,在这样的思虑作用下的行为当然是失之自然的。显然,要使人达到“独化”的状态,就要断绝人的思虑,而“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所以人的独化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实现心的独化。在郭象看来,要做到心的独化就是要做到“无心”,但“无心”并非不要心,更非死心,而是一种发乎自性、与变化合一、与物同在的状态。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无心”呢?又如何才能做到“无心”呢?郭象说:
“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则彼指于我指独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复以彼指还喻我指,则我指于彼指复为非指矣。此(亦)〔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将明无是无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则彼之与我,既同于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则天下无是;同于自是,则天下无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则天下不得复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则亦不得复有是之者也。今是非无主,纷然淆乱,明此区区者各信其偏见而同于一致耳。仰观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故浩然大宁,而天地万物各当其分,同于自得,而无是无非也。”(《庄子·齐物论注》)
“今以言无是非,则不知其与言有者类乎不类乎?欲谓之类,则我以无为是,而彼以无为非,斯不类矣。然此虽是非不同,亦固未免于有是非也,则与彼类矣。故曰类与不类又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也。然则将大不类,莫若无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于无遣,然后无遣无不遣,而是非自去矣。”(《庄子·齐物论注》)
人有别于动物在于人有识有知、有思虑,而思虑正是人的“心”的功能,这样一种思虑的作用即是人对事物的认知,而如何来实现认知并以此来指导人的行为就成了实现人的独化的关键了。这里,郭象并没有从“无心”的结构来说明什么是“无心”,而是从人以获得“是非”的判断为目的的认知活动的弊端出发,来说明人达到“无心”后所呈现出来的状态,这就是郭象的“双遣”。在郭象看来,这样的是非判断并不是从对象本身出发,而是从主体出发,是失去了统一的判断标准的,因而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其所形成的是非的认识也是不尽相同的,对“我”而言“彼指于我指独为非指矣”,对“彼”而言则“我指于彼指复为非指矣”,其结果是“今是非无主,纷然淆乱,明此区区者各信其偏见而同于一致耳”。显然,从主体自身出发,执着于是非之别的认知方法是不能实现对事物的真正的认识的,依此认知而进行的人的行为更无法使人实现人的“独化”,那么如何来实现人的认识使人实现“独化”呢?郭象的方法即是“无心”,“然则将大不类,莫若无心”,而如何实现“无心”呢?则要去掉“是非”,又要去掉“去‘是非’之念”,这就是“既遣是非,又遣其遣”的双遣之法。[1]依郭象的独化论来看,天地万物都是依自性而自生、自化的,这种自生自化是无目的的、自然而然的,物与物之间的关联不过是万物各自独化之至的结果,同样是无目的的、自然而然的。物与物之间的关联是如此,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联亦是如此。显然,依照这样的独化论的观点,如果人执着于自身的是非认知,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当然是不可能达到自身的独化状态的,只有既遣掉“是非”,又遣掉“遣‘是非’之遣”,让心处于一种“无是无非”“无遣无不遣”的状态,才能达到和物一样的独化。实际上,郭象的“双遣”之法的关键并非在“遣是非”本身,而是要去掉物我两分的认识架构,从而彻底地消解掉基于主客二分的“是非”判断,从而使心达到一种“无遣无不遣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显然不是通过言语或逻辑的推演本身所能解释清楚的,这样的状态是一种直觉的体悟所达到的精神的境界和存在的状态,而当心执着于“遣”或“不遣”本身之时,恰恰丢掉了“双遣”的实质,显然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的。这种境界抑或状态类似于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所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那种“欲说还休”的状态,是经历后所达到的境界和感悟,而不是逻辑分析的结果。这个境界或者状态在郭象看来就是“无心”,就是“心之独化”,也就是“人之独化”。
从以上我们对郭象的“双遣”之法的分析不难看出,郭象对于“人之独化”的认识实际上是暗含了两个既区别又统一的层面的,一是人自身独化的层面,一是人对独化自身的体悟的层面,而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之独化”,也是真正实现前者的关键,体悟了独化自身也就能自然而然地实现“人之独化”。天是万物之总名,天道也就是万物存在之道,人道要同于天道,也就是人的存在要符合万物的存在之道,即是独化之道。但人毕竟不同于无识无知的自然之物,虽然人也不过是“万化之一遇耳”,但人有心,从而有识有知可利用万物,因而人的独化不单单是一种发自本性的自然而然的存在,更是出于对万物(包括人自身)的存在之道的体悟而实现的独化。这样的区别类似于张祥龙先生所说的“生存于世间”与“生存于对此世间的领会之中”的区别。[2](P356)万事万物(包括人)都是存在于此世间的,但唯有人可以体悟到存在本身,也唯有人会把存在自身作为一个问题来思考,无识无知之物当然是不会去思考什么存在和存在自身的问题的,它只是一个存在者。当然,思不思考关于存在的问题并不影响事物作为一个存在者而存在,无识无知的事物正是在这样的无识无知的状态中存在的,但对于人来说却会影响人的存在方式和状态——人生的苦恼恰恰就是根源于对存在自身以及自身存在的不体悟。对于郭象而言,“独化”是人应然的存在方式,但人的有识有知往往使人不能体悟自身的“独化”,从而不能实现“独化”,人生的种种烦恼和不如意,人世间的种种苦难和不和谐都是因此而生。有识有知是人用心的结果,识和知使人背离自然而然的独化之道,但同时对独化的体悟也恰恰是心的作用的结果,如彻底无心,人岂不是成了物,又何谈体悟?显然实现“人之独化”的关键在于“无心”,而“无心”的实质不在于有没有心,而在于如何用心!郭象说:
“物来以鉴,见不以心,故虽天下之广,而无劳神之累。”(《庄子·逍遥游注》)
“鉴,镜也。鉴物无私,故人美之。夫鉴者,岂知鉴而鉴邪?生而可鉴,则人谓之鉴耳。若人不相告,则莫知其美于人。譬之圣人,人与之名也。鉴之可喜,由于无情,不问知与不知,闻与不闻,来即鉴之,故终无已。若鉴由闻知,则有时而废也。”(《庄子·则阳注》)
“至人之心若镜,座而不藏,故旷然无盈虚之变。”(《庄子·齐物论注》)
“吾丧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识哉!故都忘内外,然后超然俱得。”(《庄子·齐物论注》)
如果从认知的角度来看郭象以上的言论显然是不可理喻的,人对事物的认知怎么能像镜子照物一样呢?物立于镜子之前,则镜中有物之影,物不立于镜子之前,则影不现于镜子之中。如果人的认知也是如此,这样一种完全被动而又不留任何“闻”“见”的认知又有何意义?显然,郭象这里并不是从获得一般意义的知识的认知角度来讲,而是以镜子照物来说明如何用心,亦即如何体悟“独化”从而实现“独化”。就万物的存在而言,万物皆是自生、自尔、依性而自化,即独化着存在的;就镜子照物而言,镜子之所以能够照物亦是其自性使然,物未置于镜子之前时,镜子没有丝毫对物的“知”“闻”,当物置于镜子之前时,则自然而然有物之影现于镜子之内,非镜子有意而为之,镜子的照物之能是自性之自然,也是镜子独化自在的结果。镜子照物的过程是“无私”“无情”的,而人的认知活动往往出于主体自身的需要,对认知的对象进行了改造,这便有了“私”,有了“情”。这样的认知不仅不能体悟事物的存在,反倒成了体悟事物独化之道的障碍。因而,人要体悟独化从而实现自身的独化就要剔除一切“知”“闻”,使心处于一种无私、无我宛若明镜一般的状态,一切言、行、思全然由“性”而发,这样就能“旷然无盈虚之变”,就能“超然俱得”,这就是“无心”,亦就是心之独化、人之独化。
“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庄子·齐物论注》)
“夫我之生也,非我之生也,则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动静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庄子·德充符注》)
依郭象的独化论来看,人的独化在本质上是和物的独化相一致的,这也是天道在人道上的体现,要实现人的独化就是要使人道合乎天道,正如物之独化是依性而自生、自化,因独化之至而相因,人的独化也就是要做到依性而为、体化而与化一体,从而实现物物而不累于物的玄冥之境,而做到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无心”。从这个角度讲,“无心”既是人之独化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亦是实现人之独化的途径,即郭象的人性论的精神追求实现的途径。
二、“无心”而“顺性”
那么“无心”如何来“顺性”呢?“心”和“性”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在儒家那里“心既是能思能知的器官,又是人身的主宰和万物的根据,性是天赋的、在一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本性”[3](P19),心性的最终指向是至善这一价值目标。郭象的心性论显然是不同于此的:就“性”而言,郭象的“性”就是自然;就“心”而言,“心”的思虑之能不但不能成就自然之性,反而是其最大的阻碍,“无心”而独化的逍遥境界才是其心性论的精神追求。显然理解郭象的“性”,也就成了理解郭象心性论的关键了。
在对人之性的认识上,郭象将儒家的道德仁义融入到了人性之自然之中,以自然之人性改造了儒家道德之人性,把人性、人性之善都看作是自然自生的。郭象说:
“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庄子·胼拇注》)
“恐仁义非人情而忧之者,真可谓多忧也。”(《庄子·胼拇注》)
“夫仁义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横共器器,弃情逐迹,如将不及,不亦多忧乎!”(《庄子·胼拇注》)
“夫仁义者,人之性也。人性有变,古今不同也。故游寄而过去则冥,若滞而系于一方则见。见则伪生,伪生而责多矣。”(《庄子·天运注》)
乍一看,这里郭象以“仁”为人之性,似乎和儒家的仁没有太大的分别,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不妨多引几句郭象的言论:
“夫至仁者,无爱而直前也。”(《庄子·天运注》)
“谓仁义为善,则损身以殉之,此于性命还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于己,彼我同于自得,斯可谓善也。”(《庄子·胼拇注》)
“夫知礼意者,必游外以经内,守母以存子,称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声,牵乎形制,则孝不任情,慈不任实,父子兄弟,怀情相欺,岂礼之大意哉!”(《庄子·大宗师注》)
显然,郭象虽然讲“夫仁义者,人之性也”,但他的“仁义”的内涵及实现的途径已和儒家的“仁义”已大相径庭,其“仁义”是玄学化了的“仁义”。郭象并不否认人之所以为人、人和动物区别就在于人有能“仁”之性,“仁义”是人性所具备的,“恐仁义非人情而忧之者,真可谓多忧也”,人之所以能行“仁义”是因人有能“仁”之性,从这一点上说,郭象和孟子是相通的。[1](P117)但就“仁义”自身而言,郭象的“仁义”和儒家的“仁义”明显不同,这一不同主要体现在对“仁”根源的认识上,在儒家看来“仁”本自“天”,是道德之“天”在人性上的体现;而在郭象看来“仁”就是人性本身,人自身的存在就是人性,“仁义”本身并不在人的存在之外,是和人的存在一体同在的,人依性而独化的存在过程就是人性的自我打开、自我彰显的过程。基于此,郭象把儒家所讲的“仁义”看成是“然”、是“迹”,这样的仁义是固定的,不变的,以这样的“仁义”来求“仁义”就是以“然”求“然”、以“迹”求“迹”,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离真正的“仁义”越来越远。而真正的“仁义”是“人性”的体现,这个“人性”是具体的、个体性的“人性”,人存在是本身,是因时、因个体的不同而变化着的,“人性有变,古今不同也”。所以儒家讲“仁者爱人”,以具体的行为来规范人性,郭象则讲“至仁无爱”,以人之存在的境界和状态来彰显人性;儒家讲“杀身成仁”,郭象则以此为“不仁”,讲“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于己,彼我同于自得,斯可谓善也”;儒家以忠、义、孝、悌为礼,强调外在的行为的约束,以此来达到内在的“仁”的要求,而郭象则以此为虚妄,强调“守母以存子,称情而直往也”的内在的依性而自为。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性”在郭象那里绝不是可以通过认知的方式来认识的,“性”是和人与物的自身的存在相一致的。显然,存在着的事物是各不相同的,事物所呈现出来的“性”自然是无法从认知的角度以抽象的方法来给它下一个统一的定义的。人也好,物也罢,都是自身存在和本质的统一体,存在着的万物本就各不相同,而万物存在的过程本身就是其“性”的彰显。这样来看郭象的“人性”和“仁”的关系也就很明确了:“仁”即是人性,也是人的存在本身,人只要“顺性”而为就自然能行“仁义”之事。这样如何实现“仁”的问题到郭象这里也就变成了如何来“依性而为”的问题,那么怎样做才能顺性而成仁呢?郭象说:
“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顺公乃全也。”(《庄子·应帝王注》)
这里,郭象以“无私”来解释“爱人”,反对“推己及人”的主张,认为这样一种推己及人实质上是以爱己为先,爱人为后,爱人之目的在于爱己,是“私”而非“公”。至于何为“公”、何为“私”,郭象进一步以任性为“公”,心欲为“私”,任性自为就是“公”,存心而为就是“私”,而只要任性而为就自然会存仁义,“守母以存子,称情而直往也”(《庄子·大宗师注》),存心而为则会离仁义越来越远。显然,这里的“人性”和“仁”的关系和郭象所述的“双遣”“无心”是一致的:就“双遣”而言,所要遣掉的并非是非本身,而是之所以形成是非之别的主客二分的认识构架,要遣掉这一构架的关键就在于要做到“无心”,使心处于镜子照物般的“无私”“无情”,全然由性而自发的状态之中,只有这样,人性之应然的“仁”才能得以实现,也唯有这样所实现的“仁”才是真正的“仁”。反过来,为求仁义而行仁义之事,就是在行为之前先有了是非之别,而这个是非之别是建立在“知”“闻”之上的,非本于“性”,是以己为是,以彼为非,因而是“私”而非“公”,是用心的结果,这样做看似是行仁义之事,实是对“性”的背离,所得的也并非真正的仁。这样“顺性”的问题实质上就变成了“无心”的问题了,“顺性”即是要无心,亦唯有“无心”才能“顺性”,而“顺性而为”则自然“得仁”。通过这样的方式,郭象将“性”“心”“仁”统一了起来:人要实现其自身的应然的存在状态就要“无心”而“顺性”,而“仁”是人性之应然,只要人能“无心”而“顺性”,自然就能行仁义之事,这样的无心而顺性、顺性而得仁就是人应然的存在状态,亦就是人的独化。
“无心”就是要“顺性”,“顺性”就是要在性分之内而为。在郭象看来,物皆有性,且一旦化定成形则“性”不可变,人的能力的大小,人生命运的顺与不顺、遇与不遇,都是由“天性”所定,是无法凭借人自身的意愿改变的,“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庄子·养生主注》) 。有心之为就是超出了“性分”的范围而强力为之,而人往往容易用心去追求性分之外的东西,这样做不能改变人生之命运,只能是离性越来越远,平添人生的痛苦而已,“若乃开希辛之路,以下冒上,物丧其真,人亡其本,则毁誉之间,俯仰失措也”(《庄子·齐物论注》)。若是安于性分之内,依性而为,虽然不能改变性分之大小,命运之变化,却也能做到安居乐业,“凡得真性,任其自为者,虽复皂隶,尤不顾毁誉而自安其业,故知与不知,皆自若也 ”(《庄子·养生主注》)。
值得一提的是,郭象在肯定“性”之不可变的同时,并不否认后天的努力对“性”的作用,这就是郭象的“习以成性”说。在郭象看来,“性”是不可变的,“性”的不可变也决定了人的能力的大小和类型的确定性,能够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多大的能力,这是后天的努力所无法改变的,但性分之内的能力的显现却不是当然的,这需要后天的“习”,以使“性”中本有的、尚未彰显出来的“能”转变为现实的“能”。换句话说,“性”中所定的能力的大小和类型是潜在的、可能的,而要把这样的能力转化为当下的、现实的,就必须通过“习”,以成就“性”。郭象说:
“言物虽有性,亦须数习而后能耳。”(《庄子·达生注》)
“习以成性,遂若自然。”(《庄子·达生注》)
基于以上原理,研发团队研制了直线电机下沉分析、预测的数学模型及相关软件,并采用大量的历史数据和实际案例进行仿真分析,其分析结果与实际案例完全一致。
“此言物各有性,教学之无益也。”(《天道注》)
“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须冶锻而为器者耳。”(《大宗师注》) “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虽希翼凤,拟规日月,此愈近彼,
愈远实,学弥得而性弥失。”(《齐物论注》)
“夫积习之功为报,报其性,不报其为也。然则学习之功,成性而已,岂为之哉!”(《列御寇注》)
不难看出,郭象既坚持“性分”的确定性和不变性,同时又肯定了后天的“习”的必要性,并将“习”和“学”做了严格的区分,强调“习以成性”,反对“假学以成性”。在郭象看来,“能”是“性”的外在的表现,是由“性”所确定的,对于这一点人是无法改变的,但内定于“性”的能力的彰显却需要后天的“习”才能凸现出来,“自然之理,亦有须冶锻而为器者耳”,这里的“自然之理”就是受之于自然的“性”,“性”之能的彰显需要经过冶炼锻造才能成之为有用之器,其能才能显现出来,正如钢铁要打造成器物才能彰显其性,牛马虽有供人骑乘之性,但也得经过训练才能供人骑乘一样。“习”是通过反复的练习,将“性”中原本就具有的、潜在的能一步一步地彰显出来的过程,也是排除物我两分、以意代性的过程,其实质就是通过反复的练习使人达到“无心”的状态,成就人的独化的过程。就“无心”而言,是实现人的独化的途径,所谓“无心”也并非是指不要人的思虑,只是指排除主客二分的认识架构,全然由性出发,依性而自为的状态,而如何来实现这样一种状态却是难之又难的,执着于排除主客二分,又何尝不是执着于是非之别,强调依性自为的同时,又何尝不是一种以我之意愿指导我之行为?基于此,郭象对“习”和“学”做了严格的区分,指出“习”和“学”的区别不在于为或不为而在于是否依性而为。正是在这样的区别之上,郭象看到了通过不断地反复练习,人可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人可以一步步地实现“无心”的状态,从而实现人的“独化”。
可以说,“无心”是实现人之“独化”的途径,同时也是人实现“独化”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或境界,但更多的时候这样一种实现“独化”的途径却很难被人所把握,人只能从无心所体现出来的状态上去体悟,而“习”正是实现这一状态的现实的方法,这也就是郭象所谓的“习以成性”,即通过不断的练习使人实现其本应呈现的存在的状态——独化。
三、无心而体化
就无心而顺性而言,郭象的性是要引起“化”的,就物的存在而言是“独”与“化”的统一,“独”在于物之“性分”,“化”在于物之“足性”,对于人而言,顺性一方面要依性而为,另一方面也是要安于性之化,即要安于命,也就是说,仅仅认识到“性分”而依性而为是不足以体悟独化本身的,还要进一步体悟到“化”,且顺性而化。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郭象的“性”并非是对事物的某种规定性的认识,而是事物的存在自身,这样的一种存在只能从其存在的状态来理解,而要揭示事物的存在状态亦只能从事物自身的“有——无”统一性的内在结构来解释其存在。虽然郭象并未明确地揭示,当然也不可能明确地以现象学的方式来揭示事物的“有——无”统一性的结构,但其对“独”与“化”的统一性的描述正可以以此结构来进一步加以解释和引申,事实上,这种“独”与“化”的统一正是其“足性”的含义所在,也正是事物自身的“独”与“化”的统一才使得事物得以存在和生生不息。就事物的存在自身来看,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人作为存在之一当然也不例外,而人生的生老病死、遇与不遇即是人生之化,是人生之必然,也是人的存在的组成部分,人只有体悟此,且安于此,才能实现人的独化。那么,人又要如何来体悟人之“化”呢?
人生的遇与不遇、变化变迁是人生的必然,非个人的意志所能改变:
“而区区者各有所遇,而不知命之自尔。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为巧,欣然多己,及至不免,则自恨其谬而志伤神辱,斯未能达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则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动静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而横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
(《庄子·德充符注》)
“死生犹昼夜耳,未足为远也。时当死,亦非所禁,而横有不听之心,适足悍逆于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于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谓死耳;在生,故以死为彼。”(《庄子·大宗师注》)
“突然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忽然自死,吾不能违。”(《庄子·则阳注》)
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但这样的行为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的目的却往往不遂人意,在郭象看来人生的动静趣舍、情性知能、拥有的、失去的、所为的、所遇的都是不由自我的意愿所决定的,是人生变化的自然,也是必然,亦是人的存在的应然,人只能顺应之而不能改变之。就人生的大变化生死而言,它同样也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就像昼夜的自然更替一样,也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郭象进一步说:
“故人之生也,非误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虽大,万物虽多,然吾之所遇适在于是,则虽天地神明,国家圣贤,绝力至知而弗能违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为,弗能为也,其所为,弗能不为也。故付之而自当矣。”(《庄子·德充符注》)
人的生死、能力的大小虽是自然而生,自然而有,但并非妄生妄有,“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庄子·大宗师注》),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依自性而独化的结果,其存在本身就是必然和本质一体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因而对待人生变化的态度应当是“付之自当”,那么如何来“付之自当”呢?郭象说:
“以化为命,而无乖迕。” (《庄子·德充符注》)
“命非己制,故无所用其心也。”(《庄子·秋水注》)
“以变化为形之骇动耳,故不以死生损累其心。”“以形骸之变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为死。”(《庄子·大宗师注》)
“体夫极数之妙心,故能无物而不同,无物而不同,则死生变化,无往而非我矣。故生为我时,死为我顺;时为我聚,顺为我散。聚散虽异,而我皆我之。故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丧。(《庄子·德充符注》)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为我载,生为我劳,老为我佚,死为我息。四者虽变,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死与生,皆命也。无善则死,在善则生,不独善也。故若以吾生为善乎?则吾死亦善。” (《庄子·德充符注》)
“死生觉梦,未知所在,当其所遇,无不自得,何为在此而忧彼哉!”(《庄子·大宗师注》)
“夫死生变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忧哉!”(《庄子·大宗师注》)
在郭象看来,要做到“付之而自当”即是要依性而体化,“无心”而与“化”一体。一方面,既然生命的变化无常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是人生之存在的自然亦是应然,那就不能以人的自我的意愿来试图改变它,这样的努力也是徒劳无功的,人只能顺应生命而变化,“以化为命,而无乖迕”(《庄子·德充符注》);另一方面,要减少人生的痛苦,即要体悟人生的变化,做到与化一体,这样才不会患得患失,才能以生死皆为自得,遇与不遇都是我之变化,无所谓得失。有意思的是如果将“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则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动静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故生为我时,死为我顺;时为我聚,顺为我散。聚散虽异,而我皆我之”与“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为我载,生为我劳,老为我佚,死为我息。四者虽变,未始非我,我奚惜哉”三段文字放在一处,郭象的表述似乎就有了一些矛盾:一方面说“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皆非我也”,另一方面又说“故生为我时,死为我顺;时为我聚,顺为我散。聚散虽异,而我皆我之”,“四者虽变,未始非我”,一会说“非我”,一会又说“皆我”“未始非我”,其意似乎截然相反。其实不然,这里虽然都是说“我”,但“非我”之“我”和“皆我”之“我”却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讲“非我”是从“化”的根据上讲,人的生死变化是“理自尔耳”,是自然而然的,是不受人的意愿的支配的,生老病死、遇与不遇,这都是人生的自然,也是应然,既不是由“我”的意愿所决定,也不是“我”的意愿所能改变的,所以说“皆非我也”;讲“皆我也”,则是从“化”的承担者的角度来讲,生老病死、遇与不遇这些人生的种种变化,都是作为主体的“我”的存在的状态,无论如何变化,都是作为主体的“我”的变化,所以说“皆我也”。事实上,无论是“非我”还是“皆我”都是人的独化的一部分,讲“非我”即是从“性”上说“化”,讲“皆我”即是要体悟人生之“化”,从而与“化”一体。从“性”上说化,即是要体悟“性”之自然,顺“性”而为,亦是要排除主体意愿的干扰,打破主客二分的认识架构,即要做到“无心”。而要体悟人生之“化”,做到与“化”一体,亦是在“无心”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郭象讲“知以无涯伤性,心以欲恶荡真”(《庄子·人间世注》),说的亦是这个道理,基于主客二分的认识架构而形成的对知识的无限的追求,是心之欲望作用的结果,这样做只会离“性”愈来越远,背离事物存在的本来状态,从而使人生陷入无穷无尽的苦恼之中。而只有摆脱了心之欲望,打破主客二分的认识架构,体悟到人生诸多变化的必然和应然,把生老病死、遇与不遇当作人生的本然,且与之同化,才能真正地实现人生的逍遥,这便是齐生死、安于生死的无心而逍遥,“所谓齐者,生时安生,死时安死,生死之情既齐,则无为当生而忧死耳”(《庄子·至乐注》)。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生死贵贱,只要能做到适性而为、安于性命,人生就自然得到了安顿,“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鸟兽万物,各足于所受;帝尧许由,各近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实也。各得其实,又何所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尧许之行虽异,其于逍遥一也。” (《庄子·逍遥游注》)
不难看出,郭象的无心而体化体现的正是他的玄学意义上的心性论的现实和精神的双重追求,这样的无心而体化是以实现个体生命的安顿为目标的。当然,郭象的独化说并没有把个体的存在看作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恰恰相反,郭象从自生、自化的内因性出发,强调了万物之间的关联性,使得适性独化的个体能够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从而为他的民皆独化而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提供了理论支持。
这样,通过对“无心”“性”的重新界定,以“独化自生”之说来融合儒道,郭象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心性论。一方面,他并不否定儒家的伦理道德,把仁义看作是自然之人性;另一方面,他以个体的独化自生为人性的基础,以无心顺性为实现人的独化的途径,在强调个体生命的安顿的同时,以期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与安定,这也正是郭象心性论的特色和贡献之所在。但客观地讲,郭象的“无心”是对心的认知的排斥,其人性虽然以自然融合了儒家的伦理道德,但以自然来讲人性却容易使得内在的自我超越沦为任意恣为的自我堕落。在现实的践行过程中,试图融合儒道的结果往往是既丧失了道家不系于外物的对精神绝对自由的追求,又拒绝了儒家由心到性的道德自我超越方式,这恐怕也是后世诟病于郭象的独化之说的原因之一。
[1]康中乾.从庄子到郭象——《庄子》与《庄子注》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3]张立文.圣境——儒学与中国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李 官〕
Self-transformation: Being Inadvertently Compliant——Discussion of Guoxiang′s Mind-nature Theory in the Metaphysical Sense
LIU Che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In Guoxiang′s metaphysics,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was developed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Confucian ethics and Taoist nature on the basis of self-transformation. Guo did not deny humanity as human nature, but interpreted it as natural humanity with being inadvertent as the way to realize it. The goal of this theory was to achieve a self-settled life as well as a harmonious society composed of self-transformed individuals. In brief, Guoxiang′s mind-nature theory can be summarized as being inadvertently compliant and integrated.
the mind-nature theory; inadvertently; human nature; self-transformation
刘 晨,男,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B235.6
A
1006-723X(2015)12-0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