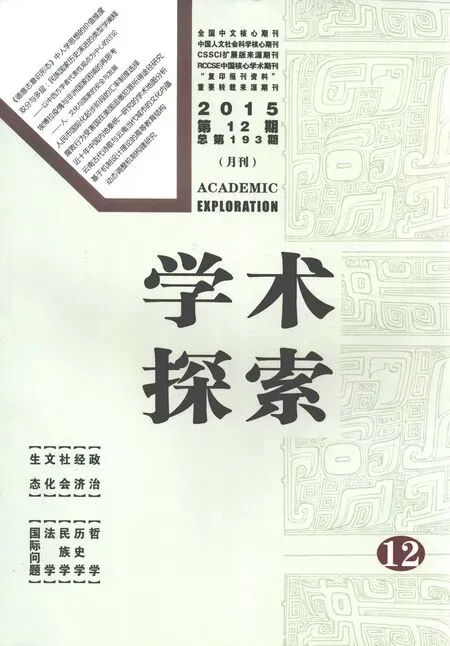双分与多层: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类型学阐释
——以中西方学者代表性观点为中心的讨论
于春洋
(复旦大学 民族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双分与多层: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类型学阐释
——以中西方学者代表性观点为中心的讨论
于春洋
(复旦大学 民族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基于类型学的视角回顾中西方学者有关民族国家历史演进问题的讨论可以发现,“双分”和“多层”是学者讨论该问题时采取的两种重要分类体系。“多层”是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历史叙事,梳理民族国家演进历程并进行阶段划分,其代表学者是迈克尔·曼和吉尔·德拉诺瓦;“双分”则认为民族国家全球扩展的真相并不蕴含在历史演进本身,主张用更为深刻和内隐的标准来划分民族国家类型,其代表学者是安东尼·史密斯、菲利克斯·格罗斯和马戎。而史密斯和格罗斯的观点有很多内在关联与照应,值得深入讨论;另有学者从“双分”与“多层”相交织的立场,立体而全景式地呈现了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其代表学者是宁骚和贾英健。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其实就是民族国家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那里被持续建构的历史。基于类型学阐释展开对中西方学者有关民族国家历史演进问题讨论的评析,能够为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未来建构提供有益启发。
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类型学阐释;民族国家建构
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嬗变进程中出现的普适类型,民族国家初创于近代的西欧,之后历经北美洲和大洋洲的衍生性建构,及至20世纪中叶获得了全球性扩展——那些并不具备西欧原生民族国家建构条件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纷纷模仿这一建构方式,最终发展成为现今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体系的基本分析单位。民族国家的演进是一个历时性过程,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并且可以据此而对其演进过程做出类型学划分:处于大致相同的民族国家演进阶段,其民族国家建构的路径带有某些共性特征,反之亦然。回顾中西方学者的相关讨论可以发现,尽管大家在关注点、表述方式和研究领域上存在诸多差异,但确有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且就此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与讨论。我认为,中西方学者的这些分析与讨论为目前中外学界有关民族国家及其建构这一热点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和文献准备。受本文篇幅和研究主旨的限制,这里仅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观点进行评介性讨论。
一、对于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多层”叙述
回顾中外学界有关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和类型划分的讨论可以发现,很多学者愿意以时间为线索进行线性叙事,历时性地梳理民族国家从初创、衍生到全球扩展的历史演进历程。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和吉尔·德拉诺瓦(Gil Delannoi)。
(一)迈克尔·曼:社会权力话语中的民族国家历史演进
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尝试用权力关系来阐析自人类诞生以来的世界文明史,站在社会权力的山巅,纵观人类文明的起源和世界历史的起落。在他的四卷本巨著《社会权力的来源》①该书目前已经出版了两卷,第一卷1986年出版,内容主要包含了从新石器时代到1760年这段历史时期,副标题为“一部权力的历史:从开端至1760年”;第二卷1993年出版,内容紧密衔接第一卷,主要讲述从1760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历史,副标题为“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崛起:1760-1914”。无论是从篇幅、涵盖内容还是从信息容量上看,《社会权力的来源》都堪称鸿篇巨制。这两部书稿的中译本分别于2002年和2007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曼“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对人类文明史做经验性的梳耙,并按极富建设性的理论架构逻辑对这一史实进行系统取舍和整理”,[1](P85)其核心观点主要包括: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权力的历史”;权力分为四种,即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基于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具体构型”(Configuration)而相互作用、此消彼长的历史;等等。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的第二卷中“关注阶级斗争并以此批判马克思的相关理论,系统展现了欧洲工业社会的权力史,之后用他自己的权力理论对于一战爆发的原因做出了对应性分析。”[1](P86)在这卷著作中,曼将自己研究的中心聚焦于民族—国家问题,在对民族和阶级产生的过程进行了系统阐释和阶段划分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在它们的交织、共存和促发下形成民族—国家的历史——也就是在这里,曼系统考察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问题。
曼愿意把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同时也着意强调民族国家创建的历时性特征:16世纪第一阶段开始,意识形态权力开始发挥支配性作用,天主教改革和新教运动促进了新的精英文化网络的建构,教会传播推动了广义的社会认同并且逐渐导致了权力的集中,促生了早期民族;1700年第二阶段开始,近代国家与商业资本主义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两者的混合与传播之下,更具普遍意义的民族认同得以形成,而在第一阶段形成的较为有限的共同体意识变得愈发浓厚。该阶段属于商业—国家主义阶段;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792年第三阶段开始,由于在这一阶段,更为广泛的认同与民族国家一道被军事权力关系向前推进,因此可以把这一阶段称之为军事阶段。而且在这一阶段,“跨阶级的民族”在军国主义的推动之下最终得以形成;及至19世纪晚期第四阶段开始,该阶段被曼称之为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相互作用的频繁程度因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而增加了,也让政府变得更为同质化、更为代议制化,也就更为民族化。在这里曼着重指出,这一阶段的跨阶级民族已经包含着公民权利的概念了,开始关注国家和民族是否应该中央集权化,关注“代表制度”与民族事务,同时也让上述变化更具挑衅性。曼分析认为,这种挑衅更多是由近代国家的持续军事化带来的,也包括国家与家庭更为紧密的结合的因素。[2](P236~270)
(二)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主义浪潮与民族国家历史演进
吉尔·德拉诺瓦在自己的专著《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中,以“民族主义浪潮”为视角回顾了民族国家的全球扩展,进而以时间为线索,以“民族主义浪潮”的性质及其表现形式的不同为标准,把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区分为五个阶段。
德拉诺瓦指出,以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作为发端,旨在摆脱宗主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浪潮在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普遍兴起,这是“民族主义的第一个浪潮:共和主义的浪潮”。与此相联系的是民族国家历史建构的第一个阶段。他表示,“自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开始,都是在民族原则的名义下人民才获得了解放”。法国在这一点上走得显然更为彻底,因为法国“不但……从专制制度之中解放出来,而且还宣称要将其他人民从专制制度之中解放出来”。德拉诺瓦认为,这一民族国家建构阶段的显著特征在于“民族与革命交织在一起;”[3](P12)民族国家历史建构的第二个阶段是以法国民族国家建构模式“作为参照或衬托”而建立的“民族认同民族国家”,这一民族主义浪潮被德拉诺瓦称作“浪漫主义”浪潮。[3](P12)在他看来,法国出色地输出了自己的民族感情,并且倡导和呼唤全人类紧跟带有普适意义的法国模式,而无论是拿破仑的帝国主义、保守派的复辟还是共和国的殖民等等,也都把基于法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而形成的法国模式作为自己的参照或衬托;以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以及爱尔兰和波兰的独立作为标志,民族国家历史建构的第三个阶段到来了,德拉诺瓦将与此相对应的民族主义浪潮称之为“政治独立的浪潮”。他指出,及至19世纪末期,虽然共和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原则和影响仍然生机勃勃,但是,“最早建成的欧洲民族—国家已变成了殖民帝国和帝国主义列强”。[3](P12~13)这就使得其他一些地区想要模仿它们的愿望,“不再仅仅是思想性的,而且是战略性的”。在这一背景之下,一些城邦、公国、小王国在国家的形式下结为一体或建立起来(德国和意大利),而长期被占领的领土则开始为寻求独立而进行努力(爱尔兰和波兰);随后,德拉诺瓦所宣称的民族主义的第四次浪潮到来了,这次浪潮是以中国、印度和非洲为典型的“尽管有过殖民化,现在又重新获得独立和昔日的边界”的“非殖民化的浪潮”。伴随这次民族主义浪潮到来,开启了民族国家历史建构的第四个阶段。他指出,“受到削弱和不被尊重的欧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走了出来,立即又面临着非殖民化的浪潮。”[3](P13)在这次“非殖民化的浪潮”中获得民族独立的既包括中国和印度,也包括很多非洲国家——只是在非洲创建的这些新兴民族国家是保留了非常随意形成的领土,并使之成为新的国家、新的民族;最后,德拉诺瓦将发生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的,以“共产主义的突然坍塌”为标志性事件的民族主义浪潮称之为“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新浪潮。[3](P13)这一浪潮致使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走向解体和分裂,并因此产生了一系列民族国家,这是民族国家历史建构的第五个阶段。在德拉诺瓦看来,这一浪潮是同时发生的,拥有前所未有的“同时性”,而其独特的冷战结束和“后共产主义的背景”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讨论的最后,德拉诺瓦总结到:尽管存在着众多的不同,但这些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潮流都具有热烈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自豪的因素,有时也与追求强大和独特性相始终。“现代政治看起来似乎总是回到民族的形式上。解放与关闭,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在这些持续的浪潮中,经常结伴而行。”[3](P13~14)这里剩下的唯一问题在于:“此潮流还要持续多长时间呢?”[3](P14)显然,这是被德拉诺瓦提出的,也是现时代留给我们的对于民族国家未来发展前景的最大疑问。
二、对于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双分”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在把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加以现象观察和特质梳理时,有些学者并不打算停留和满足于历史叙述本身,而是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指向更为深刻而内隐的因素。在他们看来,对于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线性描述仅仅是为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历史背景,而民族国家全球扩展的真相并不蕴含在历史演进本身。而且颇为有趣的是,秉持这种研究取向的学者大多倾向于对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依照某种标准加以“双分”,并且着力将研究重点放在“双分”之后的不同民族国家类型的关系探讨上。
(一)史密斯与格罗斯的“双分”及其观点比较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和菲利克斯·格罗斯(Feliks Gross)都倾向于对民族国家的建构类型进行“双分”,而且在他们两人的观点之中存有很多一致或者相似的地方,这种共性促使我们希望把他们两人的观点放在一起加以说明。
根据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产生机制和社会基础的差异,英国学者史密斯将民族国家的建构模式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公民的‘民族’模式”(a civic model of the nation),该模式以西欧为典型,其特点在于:其一,历史上形成的领土疆域;其二,达成法律与政治上的共同体;其三,全体成员在法律和政治上拥有平等权利;其四,共同的文化以及被普遍认可的意识形态。在史密斯看来,这四个方面的特点也恰好构成了西方话语之中的“民族”(nation)的关键条件。[4](P11)另一类是“族群的‘民族’模式”(an ethnic model of the nation),该模式以东欧和亚洲为典型,其特点在于:其一,对血统与亲缘谱系的认同程度超越了对于领土疆域的认同;其二,基于强烈的群体归属感而产生出稳定的内在感召力量与外在动员效果(popular mobilization);其三,对于法律的尊重让位于对于本土文化和地方传统(语言、习俗和价值观等)的尊重。史密斯认为,上述特点在东欧和亚洲地区的“民族”(nation)建构进程之中体现得非常清楚。[4](P11)
与此相对应,美国学者菲利克斯·格罗斯在描述民族国家形态的历史演进时,给出了另外一对相互对应的概念,即“公民国家”与“部族国家”。而且分析表明,格罗斯所提出的这组概念与史密斯归纳出来的两种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在其实质内容上拥有相互重叠的边界。在提出公民国家与部族国家的概念之后,格罗斯描述了它们的主要特征:“自由公民的联合体构成公民国家,因此,不管出身、族群(ethnicity)、宗教以及文化背景怎样,在同一地域内生活的全部具备资格的居民,都是国家的成员;”[5](P11)“……公民国家的核心制度是公民权,它建立在政治纽带之上,并诉诸于政治纽带;”[6](P26)“公民国家……提供了一种把政治认同从亲族认同转化为政治地域关系的途径,一种把同国家相联系的政治认同(国家民族)与种族上的亲族认同(文化民族)相互区分的方法。”[6](P32)而与构成现代“公民国家”的这些基本理念和主要特征产生鲜明反差的是,“部族国家普遍把血缘、族群(ethnicity)、宗教、历史记忆和政治制度混同在一起。所以,它是一种难以容忍少数群体(minorities)存在,甚至也与平等权利无关的具有高度排他性的制度。”[5](P6)格罗斯强调,“……部族国家是一种与现代社会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产生持久冲突和永恒张力的制度安排;”[6](P37)“部族国家天然地将种族起源和种族身份与政治认同关联在一起。”[6](P26)
经由上述分析,我们愿意把“公民国家”大致等同于依照史密斯的“公民的‘民族’模式”建构起来的民族国家来看待,而将“部族国家”大致等同于史密斯的依照“族群的‘民族’模式”建构起来的民族国家。而且,基于历史发展的巨大惯性,在“部族国家”以“民族国家”作为目标所进行的嬗变中,也很容易形成事实上的“族群的‘民族’模式”。根据格罗斯的分析,“部族国家”与“公民国家”是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前者拥有传统的内部政治关系,后者则拥有现代的内部政治关系,而处于不同国家形态中的国民也基于这些巨大的反差而表现出大相径庭的效忠形态。在现代“公民国家”之中,国家成员都是公民,宪法赋予每位公民在法律及政治上平等的权利。作为国家公民经由合法程序集体选举而产生的执政代表,政府首脑及其委任的各级各类公职人员没有任何特权,更何况公民对于政府首脑还享有罢免权。总之,公民国家中的政府首脑、各级各类公职人员和全体公民都效忠于国家宪法,服从国家的法律。而在存在多族群的部族国家*按照我们的理解,现实中的部族国家往往会拥有多个族群,是由多个族群共同构成的民族国家。这种理解在格罗斯有关“部族国家”的阐述中也能找到充分的理由。之中,民众分属于不同的族群,他们效忠的对象首先是本族群的首领,而每一族群的首领则主要围绕和依照本族群的利害得失来判定是否要对部族国家的统治者——皇帝宣誓效忠。在这种效忠形态之下,某一族群的首领一旦“倒戈”,就势必引发该族群对部族国家统治者的“背叛”。并且,传统部族国家内部的每一个族群单位都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权力,而有相当多的部族国家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这一政治统一体的内部组织结构就是以族群作为基础的。
依照史密斯的两类民族国家建构模式的观点加以分析,在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在亚非拉各国中普遍存在着的“族群的‘民族’模式”势必要逐渐过渡和转变为“公民的‘民族’模式”,这一内容其实已经构成了这些国家发展历程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线索。而这一过程,同时也是由格罗斯的传统“部族国家”朝向现代“公民国家”的过渡和转变过程。对此,如果我们从“时间”的维度介入进行分析,史密斯与格罗斯的两组不同分析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就会显得更为清晰:作为历史发展的大势,经由“部族国家”而向着“公民国家”进行过渡是一切国家迟早都要完成的转变。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内部不同区域在转变的形式与速度上会出现不同步、不平衡的现象,这一现象在那些族群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里表现尤其明显。因此,在最终完成这种转变之前,这些国家中的已经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特征的整体政治框架与仍旧保持着传统中的“部族集合体”特征的某些族群政治生态之间,肯定会产生持续不断的矛盾。因此,在传统中的“部族集合体”特征彻底消失以前的并不算短的历史时期里,各国政府都有责任在尊重本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致力于通过必要的制度调整和政策探索来协调处理这些矛盾,以确保“部族国家”向“公民国家”的过渡和转变能够顺利完成。
(二)马戎的“双分”民族国家:原生型与被动型
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7](P1~6)中也涉及了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马戎将西欧最早建成的一批民族国家称之为“原生型民族国家”,而把在“西欧民族国家向东欧以及其他大陆的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7](P1)促使当地建构出的民族国家称之为被动型(或后发型)民族国家。他指出,西欧的“民族主义”运动与“民族”理念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也使得西欧之外的其他国家普遍以西欧作为参照,依托自身原有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生活基础而不断致力于成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马戎认为,可以把这些民族国家命名为“被动型”或“后发型”的民族国家。[7](P1)
在进行上述一般性的讨论之后,马戎就“一个传统的多部族帝国”建构民族国家的“类型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马戎认为,在向“民族国家”进行转型时,传统的多部族帝国大致能够做出的选择有两种。一种可能的选择是以建立一个“多族群的民族国家”为目标,努力打造统一的“国家民族”,并用它来引导国内各种少数群体和各个部族发展成为国家民族内部的“文化族群”。同时,国家把国内少数族群的文化权利当作一项非常重要的公民权利来看待,在全体国家公民之中推行统一的行政、法律与政策,进而在宪法和“公民权”的框架和价值目标之内去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扶助弱势群体;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是以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为目标,亦即将国家内部存在的各个传统部族作为“民族”(nationality)来看待,让这些“民族”拥有相对独立的政治身份、享有特殊的政策待遇。之后,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或者“民族联邦”这样一种行政体制安排去协调这些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而,马戎以“中国的清朝和辛亥革命的中华民国政府”和沙皇俄国为例指出,“这两种选择所带来的社会发展后果完全不同”。[7](P3)
而且在马戎看来,即使传统的部族国家被建构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即马戎所说的第二种选择),“倘若这一选择的未来发展的方向仍然是向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迈进,那就势必要用统一、平等的公民权去替代各个‘民族’的自治权,努力强化公民意识和公民权,淡化和祛除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7](P4)这一迈进的实质也就是引导现有的“多民族国家”进行第二次转型,用文化色彩为主的“族群”(ethnic group)去替代政治色彩强烈的“民族”(nationality),即转变成为一个“多族群的民族国家”。马戎指出,倘若“多民族国家”不努力进行“第二次转型”以便发展成为“公民国家”,将始终面临国家分裂的潜在风险。可以看出,马戎的观点依然延续着他在2004年年底提出的民族关系“去政治化”[8]的思路,在他看来,“多民族国家”是未完成的国家,实现“多民族国家”向“多族群国家”的“第二次转型”,对于国家的存续至关重要。
三、“双分”与“多层”的交织:国内两位学者的讨论
在对中外学界有关民族国家历史演进问题的讨论进行梳理时,一种与上述分类存在较大差异的划分方式逐渐进入到了我们的视线——国内有两位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采取了“双分”视角与“多层”叙述相交织的立场。两位学者的讨论对我们理解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提供了更为立体和全景的说明。
(一)宁骚:民族国家的历时类型与共时类型
北京大学的宁骚教授在其50万字的学术专著《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1995)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9](P281~317)*宁骚在该书的第五章“民族国家辨析”中,专门列出一个标题来深入分析“民族国家的历时类型与共时类型”问题。,以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的历史演进作为线索,详细分析了民族国家的“历时类型”与“共时类型”。这是国内学界对此问题所展开的最早的、最权威的,同时也是最为细致的讨论。
宁骚指出,“当代世界的民族国家是在世界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形成的。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民族的外观。”[9](P282)在此基础上,宁骚对民族国家的“历时类型”进行了深入的说明。他指出,“第一批民族国家兴起于从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下半叶的西欧”。经过“这个时期,王权得到了普遍地加强,它为建立民族国家提供了现成的国家机器”。[9](P283)但是宁骚认为,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民族国家尚未发展成熟为现代民族国家,因为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都不是现代形态的。而只有当“民主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成为民族国家正常的国家政权形式,国家主权从君主的手里全部或者部分地转移到了国民议会的手中,而这个国民议会不仅在形式上可以代表全民族,在实质上也的确归由民族统治阶级掌控”[9](P284)的时候,民族国家建构的任务才会真正得以完成。于是,在此后的接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初创的民族国家陆续完成了“资本主义改造”,到17世纪上半叶,这些国家最终得到了巩固;此后,“崛起于新大陆的那些民族国家”开启了民族国家建构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宁骚认为,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虽然具有刻意仿效西欧范式的痕迹,但是这些国家在现实的发展进程之中,还是逐渐形成了带有自身特点的民族国家建构方式”。[9](P292)在此基础上宁骚指出,“这些特点在拉丁美洲表现为民族国家缔造者们的政治思想在实践中被粉碎和被扭曲,而在美国那里则集中体现为民族国家的缔造者群体把他们独特的政治理想付诸于现实实践。”[9](P292)在这个意义上看,美国的民族国家缔造者们要远比他们在拉丁美洲的同行更为幸运。民族国家建构的第三个阶段,是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地利帝国的纷纷解体而开启的民族国家建构浪潮。在这一阶段出现的民族国家多达30多个;此后,“与帝国主义这一特殊历史时代相联系,民族国家形成的最后一个高潮得以出现。伴随广袤的亚洲和非洲大陆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的主要矛盾则变为那些生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广大民众要求摆脱帝国主义桎梏,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问题;”[9](P300~301)最后,随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这三个民族联邦制国家的解体,”[9](P301)又一批民族国家得以建立。
而在分析民族国家的“共时类型”时,宁骚注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当代各个民族国家的成熟程度来说,存在着发达的民族国家、中等发达的民族国家、发展中民族国家的区别。”[9](P314)需要注意的是,宁骚在这里提出了“无产阶级民族国家”的问题。他指出,“当我们把研究的视角从纵向的历时分析转为横向的共时比较时,当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形态之中的一个全新类型——无产阶级民族国家及其特征问题就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9](P314)进而,宁骚对于无产阶级民族国家类型及其特征进行了分析——“从历时的比较来看,无产阶级民族国家属于新兴的民族国家”;而从共性的角度加以分析,这一类型的民族国家“属于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其原因在于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国家还只是初步具备了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经济物质条件和文化基础”。[9](P314~316)必须承认,这种来自“横截面”上的共时性思考对于我们辩证看待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是极富启发的,因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方式与共性特征,并不能抹杀不同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事实差距。
在对“民族国家的历时类型与共时类型”进行分析讨论的最后,宁骚极具洞见地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民族国家”的方法论问题:“在对民族国家的历时类型与共时类型进行研究时,我们一方面必须要充分重视民族国家的崛起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对于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又不能像黑格尔那样崇拜和迷信民族国家。必须时刻清醒地注意到,不管是哪一类型的民族国家,那些可以维系它存在的因素,同时也都能转化为瓦解它的因素。”[9](P316)
(二)贾英健:民族国家的建构方式与历史演进
贾英健教授在自己的专著《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2005)中,也不乏对于民族国家建构类型及阶段划分的讨论。民族国家的建构被贾英健区分为“否定性建构”和“肯定性建构”两种理想类型。在他看来,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在“否定”和“肯定”两个向度上展开的,前者是“在对原来存在的国家形式进行否定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后者是“在肯定原来存在的国家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对于旧有国家形式的改造而建构”。[10](P76)而决定一个民族国家究竟是要进行“否定性建构”还是“肯定性建构”,主要是看“旧有国家形式的合法性”。而对于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贾英健认为,“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最为根本的判断标准就是国家是否符合本民族的利益和要求。”[10](P76)如果旧有国家符合本民族的利益和要求,就能够通过“肯定性建构”而成长为民族国家;而一旦国家无法做到这一点,就会出现认同危机,从而只能通过“否定性建构”而建立民族国家。
进而,贾英健把民族国家建构的具体形态从“从历史的角度”区别为“原生形态的欧洲民族国家”“衍生形态的主要由欧洲移民组成的民族国家”和“传统社会根基深厚,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建立起的民族国家”这样三种类型。[10](P78~81)他指出,对于第一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建构,即“原生形态的欧洲民族国家”来讲,“这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是西欧历史上的第一批具有明显近代色彩的主权国家。其民族国家建构主要是通过争取民族独立,肃清封建割据势力及其影响,反抗和打击外来压迫势力,进行宗教改革、纳教于国等等长期的斗争和努力而展开的”,[10](P79)其典型性国家主要有法兰西、英国和西班牙等等。而在这些国家的形成过程之中,原来那些在意识形态上“不知有国,只知有教”、在政治上以各自的封建领主作为权力中心的小居民群体也开始逐渐实现了以国家作为标识的聚合;对于第二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建构,即作为民族国家衍生形态的那些“主要由欧洲移民组成的民族国家”(主要包括那些北美洲、大洋洲的殖民地经由民族独立努力而建立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来讲,这一类型国家的主要成员(欧洲移民)陆续从欧洲大陆来到了美洲,由于他们经历过资本主义文明的洗礼,因此也将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关系带给了这片新大陆。而且,正是“由于这些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也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因此,当这些移民与自己母国的附属关系被切断之后,民族国家很快就会随着殖民地的独立而得以建立。”[10](P80)毋庸讳言,这一类型的民族国家多是目前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而对于第三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建构类型(主要是二战之后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拉国家)来讲,“由于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封建主义根基往往较为深厚的存在于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继而,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又在这些国家里不同程度地实施过。”[10](P80~81)基于这样一种经济基础与社会发展现实,当这些国家获得民族独立之后,还面临着非常繁重的民族国家建构任务。
四、总 结
我认为,上述中西方学者对于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类型划分的讨论,会为目前学界民族国家及其建构这一热点问题的研究提供宝贵文献准备和理论参照。而在这种类型学阐释的视角之下,隐匿在两三百年世界近代历史之中的民族国家全球扩展的线索和逻辑,也得以呈现出了自己的原貌。今天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在于:无论是否愿意,赞成或者反对,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关系体系之中。而随着全球化带给民族国家的冲击和挑战的不断加剧,怎样通过民族国家建构来让这种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高层次和最具普适性质的国家形态适应全球化的发展,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做出回答的问题。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经极富洞见地指出,“要谈论民族国家的未来,就必须先回顾其过去。因为,如果不了解民族国家在过去200多年里的演进,就很难理解民族国家这一全球性制度(global institution)在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11](P188)吉登斯在这里所提供的是一个寻求答案的时间维度:为了回答上面提到的问题,应该系统回顾民族国家是如何被创建的,又是如何在美洲和大洋洲的早期殖民地那里实现了成功的“自我复制”,及至后来,又是怎样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伴随沙皇俄国、奥斯曼土耳其和奥匈三大帝国的解体、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东欧剧变,促生了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和置身其中的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关系体系。因为在相当程度上,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其实也就是民族国家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那里被不断建构的历史。希望本文这种基于类型学阐释而展开的对于中西方学者有关民族国家历史演进问题讨论的评析,能够为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未来建构提供有益的启发。
[1]姚朋.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史及权力史观述评[J].史学月刊,2003,(7).
[2]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M].陈海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M].郑文彬,洪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4]Smith, Anthony D.,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5]Gross, Feliks. The Civic and the Tribal State: The State, Ethnicity, and the Multiethnic State[M].Westport: Greenwood Press,1998.
[6]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M].王建娥,魏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7]马戎.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和国家形态的演进[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
[8]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9]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0]贾英健.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1]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M].郭忠华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左安嵩〕
Dichotomy and Multi-layers: Types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Nation State: A Discuss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Viewpoin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YU Chun-yang
(Center for National Minorities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ypology, this paper makes a review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nation states by Chinese and West scholars. It is foundthatdichotomyandmulti-layersare the two important classification systems to study the problem.Multi-layers, whose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are Michal Mann and Gil Delannoi, takes the time as a clu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to sort out the nation-state evolution and divide the stages.Dichotomy, with Anthony Smith, Feliks gross and Ma Rong as its representatives, believes that the truth of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the nation states is not i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itself, and advocates the use of a more profound and implicit criteria to divide the type of state nations. Other scholars, such as Ning Sao and Jia Yingjian, have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nation state from the standpoint ofDichotomyandMulti-layers.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abou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nation stat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ypology can provide useful inspiration for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nation-stat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nation state; historical evolution; typology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state construction
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3FMZ00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批面上一等资助项目(2015M580280)
于春洋,男(蒙古族),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后,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D031
A
1006-723X(2015)12-002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