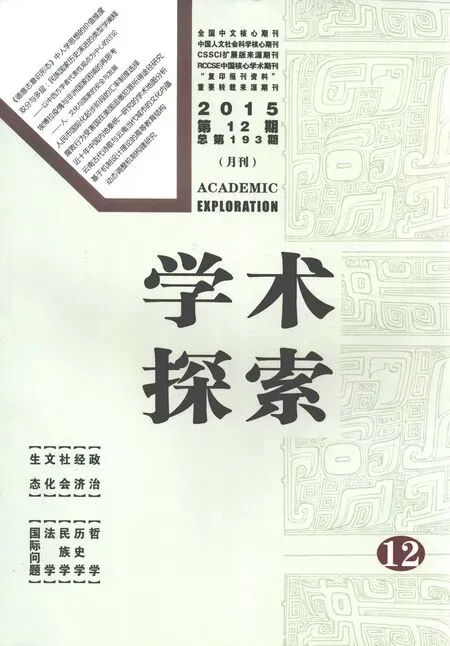边境民族地区宗教治理法治化研究
佴 澎,高崇慧,陈肖龙
(云南财经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021)
边境民族地区宗教治理法治化研究
佴 澎,高崇慧,陈肖龙
(云南财经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021)
宗教工作应当正视宗教的社会价值,以法治路径解决好政教关系,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注重综合治理,加强宗教社团制度建设、自我管理与政府监督。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存在境外僧人主持部分寺院活动,基督教发展迅速,境外渗透活动加剧,宗教工作部门弱化,发展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等情况。边境民族地区的宗教治理,应变“行政管理”为“综合治理”,立足实际,与“一带一路”战略相结合,进行跨领域综合构建。
边境民族地区;宗教;社会治理;法治创新
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法治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初步形成时期(1931年《宪法大纲》至1949年《共同纲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发展时期(1954年《宪法》第八十六条、八十八条①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到1978年《宪法》第四十六条②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法治思维形成与贯彻落实时期(1982年《宪法》第三十六条③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1]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宗教工作进行系统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有关宗教事务的论述可概括为: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加强对宗教的积极引导、精心做好宗教工作,[2]其中强调:“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3]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宗教工作进行了全面论述:“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4]然而,现有的宗教事务管理体制法治化水平不高,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实践中法治弱化,在边境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与坚持中国化的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维护民族团结的使命尚有较大差距。
一、宗教治理法治化
宗教治理法治化,要求改革目前的宗教管理“法制—行政”二元化体制,[5]使之沿着法治轨道前进。破除对宗教的偏见与“隐形歧视”,甚至某时期某些领域的“片面维稳”做法。由过于倚重行政管理转向综合治理,改变目前以“宗教场所”为中心的行政管理模式,[6]改变目前宗教人员服务同信教群众需求脱节的弊端,精心做好宗教工作、使中国化方向真正深入人心、赢得话语权。探索宗教法人制度,完善相关行政执法程序,使宗教团体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与宗教管理部门监督有机结合,积极促进宗教团体通过慈善事业、社区服务、文化交流等形式融入社会主义建设,助力中国梦。
(一)宗教治理法治化,须正视宗教的社会文化价值,从宪法法律层面落实好政教关系、宗教信仰自由
政教关系是一国宗教法律制度的出发点。世界政教关系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政教合一模式;二是政教分离模式,设立国教,世俗社会的治理由政府负责,但是对确立为国教的宗教会给予政府层面的优先权利,国教与非国教宗教间为非平等关系;三是政教分离、禁立国教模式。禁立国教模式肇始于美国,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由“禁止立教条款”(establishment clause)、“宗教自由条款”(free exercise clause)和“宗教检验”(religious test)所构成的宪法宗教制度。*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首先,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宗教”概念的认知大体可以概括为“严格—宽泛—适度限缩”三个阶段;其次,实践中“establishment clause”与“free exercise clause”常有矛盾(比如,政府出资对某些宗教建筑进行修复),布莱克法官在Everson v. Board of Education,330 U.S.1(1947)一案中提出了分离主义(“Separatism”,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主导理论),严格隔离政府与宗教;Rehnquist大法官在Wallace v. Jaffree,472 U.S.38(1985)一案判决中的异议意见提出“Nonpreferentialism”,政府的中立仅适用于各宗教间,而不是宗教与非宗教间。[7]日本战后的《日本国宪法》第20条、第89条规定了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两大原则。其第20条第1款前段、第2款规定了信教自由原则,具体而言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内心层面的宗教信仰自由;第二,宗教行为的自由;第三,宗教结社自由。《日本国宪法》第20条第1款后段、第3款和第89条基于战前神道教参与政治而严重损害宗教自由的教训,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禁止赋予宗教团体特权、禁止宗教团体行使政治权力、禁止国家进行宗教活动等。[8]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就政教关系而言,宪法并未做出明确规定,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八条中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于教育领域明确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此外,198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就我国政教关系做了详细论述。*“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当然决不能被用来推行某种宗教,也不能被用来禁止某种宗教……”“决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但是,此原则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导致政教界限不清,进而产生矛盾,且司法救济途径缺失。如少林寺上市问题,当地县政府和旅游管理部门希望上市,而少林寺方面却不同意,双方长时间发生龃龉。一些地方政府借宗教之名发展旅游业,与政教分离原则扦格。因法律对政教界限的规定模糊,极可能导致政府权力滥用,政教间对“宗教平等”或“宗教内部事务”的认知产生分歧,或某些宗教组织以政教分离为理由不服从政府的管理。[9]此外,依据政教分离原则,教规不能与国法相违背,但也要正视宗教的独特社会价值,精心做好宗教工作,积极引导教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衔接。从法社会学角度看,教规作为一种调整教徒行为的社会规范、实际中的“软法”,对于民族性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软法”不是国家制定并以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法规,可其既有行为的软约束力,更有思想上、心理上的硬约束力。[10]
《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确立了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然而,任何权利都有其边界,故宪法亦规定:“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依据法理,附加义务系权利之当然限制。在宗教事务领域,宗教行为的否定或限制应基于两类情况: 1.其非为宗教自由权利之范畴,故无权利请求排除对其之干涉。例如邪教非为宪法意义上之宗教,故不得享有相关自由之权利;2.虽为宗教自由之行为,然其损害其他的合法正当之权利,依据权利冲突的法理,侵害正当权利的行为须对其他权利让步。故对宗教自由的限制需要对《宪法》的抽象规定进一步细化,目前相关事务主要由2004年制定的《宗教事务条例》调整。政教关系、宗教自由与限制,是宗教法律制度在宪法层面上原点性的原则,仅由行政法规进行规制,于法理扦格。在具体实施环节,对法律条文内涵和外延的理解,特别是对具有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办法性质的行政规章中的限制性规范的理解,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11]这也导致宗教自由与限制问题的处理,在实践中更依赖于政策,司法救济途径弱化。然而,无救济则无权利这一古老法谚告诉我们,这样做必然会在工作中“输理”。其实,近年来日本宗教法的实践可以为我国提供一些借鉴。日本政府在宗教事务的治理中以法律为主导,在处置“东京地铁沙林毒气”这一高度敏感突发事件时,并未贸然采取法律以外的维稳手段,而是立即启动相关的法律应对机制,迅速出台《沙林防止法》《团体规制法》《奥姆特例法》《奥姆财产特别措施法》一系列专门法律,以处理奥姆真理教问题。[12]
(二)由行政管理转变为综合治理,由以宗教场所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宗教团体自我管理与政府监督相结合的治理模式
宗教治理法治化,需要破除过分依赖于行政管理,甚至演变为“行政管制”的窠臼。完善宗教团体、宗教场所的准入、监督制度,使宗教团体自治与政府监管、事前准入与事后监督、宗教与相关的民族、经济文化等世俗问题有机结合,构建法治综合治理机制。
2004年《宗教事务条例》施行以来,我国宗教法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绩,构建了由登记管理和年度检查制度构成的基本制度。登记管理制度要求,由民政部门统一登记,实行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并按活动地域分级登记管理,即“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年度检查制度规定,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宗教管理部门和民政部门对已登记的宗教团体执行法律、法规、政策的情况依法监督检查,以确认社会团体是否具有进行开展活动的资格。
在此基础上,我国制定了大量保护宗教自由与宗教管理的法律规范。例如,宗教场所法律制度就有:(1)主体制度(全国性宗教团体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申办)和设立审批主体(国家宗教事务局有设立审批权,省级宗教事务部门对本省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申请设立宗教院校有初审权)。(2)管理体制(国家宗教事务局是宗教院校的行政主管部门)。(3)教职人员管理制度(认定、备案。宗教团体对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后,须报相关宗教事务部门备案)。(4)宗教财产管理制度,《宗教事务条例》明确规定宗教财务受法律保护,包括三方面的规定:宗教财产管理应当执行国家的财务、会计制度,宗教活动场所属于民间非营利组织,必须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财务收支情况监督管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财务收支情况和接受、使用捐赠情况,既应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告,又要以适当方式向信教群众公开;依法纳税和依法享受减免税优惠。(5)重大事项许可制度(大型宗教活动管理制度、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管理制度、宗教出版物管理制度)。(6)宗教涉外事务制度(宗教院校的涉外事务规定、邀请境外宗教团组来访及国内宗教团组出访的规定)。[13]
由于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宗教法治建设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14]究其原因,“大多是管理不当激化出来的,用通俗的话说,都是管出来的问题”。[15]此外,我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宗教领域也表现出一些“新常态”:第一,信教人数不断增长,信教群众结构呈现年轻化,宗教的渗透多发,宗教的经济利益矛盾纠纷日趋复杂。第二,依赖行政管理宗教事务的模式离精心做好宗教工作的要求差距较大,如行政管理模式导致宗教团体的机关化倾向,与教众脱离;部分宗教教职人员教风不正,戒律松弛。第三,一些基层宗教工作机构人员与经费不足,基层工作弱化,难以适应日趋纷繁复杂的宗教工作,于边境民族地区尤其严重。第四,互联网的发展,使宗教传播的物理界限被打破,宗教传播呈现多样化姿态,并因互联网拉平了各领域间距离,使得宗教与金融、文化产业进一步结合,甚至极端宗教势力利用网络平台传播极端思想、融资洗钱,一时间泥沙俱下。[16]破解上述问题,需要将行政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将“宗教场所中心主义”转变为现代社团制度。
宗教事务管理去行政化需要实行宗教领域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因宗教工作的敏感性、复杂性、民族性、国际性、群众性,个别地区宗教领域行政权力出于“片面维稳”思维而异化为“行政管制”。宗教治理,须对宗教领域行政权力“脱敏”,将其纳入法治轨道,规范行政权力运作形式。具体而言,要严格行政审批“准入制”,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审批项目应予取消,防止以行政手段来干预合法宗教活动。要标准化审批流程,完善宗教事务行政审批工作机制。要建立宗教事务权力清单。“法无禁止即自由,法无授权即禁止”“明确政府权力边界”。[17]要转变政府在宗教事务中的角色,由宗教事务的管理转向服务与管理并重。2015年7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27号)就体现了简政放权,职能转变的思路。其中涉及国家宗教事务局审批职责的共有4项:“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审批”、“全国性宗教团体接受国(境)外捐赠宗教书刊音像制品审批”和“全国性宗教团体接受国(境)外捐款审批”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取消“印刷、出口、发行《圣经》审批”,待下一步研究、清理和规范。
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的建立,是保护宗教界合法权益的要求,也是宗教法治化、实现综合治理模式的必然要求。宗教财产主体地位不明确,容易造成宗教财产被侵占、被无权处分,造成宗教财产流失。因此,应当赋予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地位,宗教活动场所财产同僧尼等宗教教职人员的个人财产、捐助人财产及宗教团体财产相区分,确立宗教教职人员对宗教财产的使用权和管理权,确立信徒等捐赠者的知情权、国家的监督权。[1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对宗教法人制度给予了正面回应。其中,第84条规定:“财团法人,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助的财产,以从事慈善、社会福利、教育、科学研究、文化、医疗、宗教等特定公益事业为目的,依照法律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本法所称财团法人,包括基金会社会团体法人、宗教团体法人等。”[19]第85条至90条就宗教法人的登记核准、法人的机关、捐助章程、捐助财产归属、捐助人的权利试做了规定,是我国立法的一大进步。根据民法基本理论,法人资格的实质要件为:一、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二、独立财产;三、团体章程。实行宗教团体法人制度后,相关宗教团体对宗教财产有独立所有权,可负独立责任,有利于实现宗教团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将行政化宗教管理转变成为综合治理,以实现社会组织与社会团体管理。立足于宗教法人基础上的宗教团体,能够进一步在宗教组织内部实现有效的民主管理,民主选举各个宗教团体的负责人,进而将宗教法人的自治与宗教事务部门的事后监督有机结合,将《宪法》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于宗教相关公共事务的法治治理中,最终实现信仰无限制而宗教行动有法治约束的宗教自治目标。这无疑也能最大限度地消除目前宗教事务工作与信教群众需求脱节等问题,真正把宗教工作做好,牢牢把握宗教治理中的话语权,使中国化内化于具体工作中。当然,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的建立,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我国各地宗教活动的发展情况不尽相同,法人登记也需要遵循自愿原则,循序渐进地展开。
二、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宗教治理存在的问题
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笔者深入云南边境地区的6个州市(德宏州、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文山州、西双版纳州)进行田野调查,发现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宗教治理与法治化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一)境外僧人主持部分南传佛教寺院活动
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5个边境州市。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寺院的功能已经从单纯的宗教活动场所演变成为村民聚会、传承民族习俗、举行婚丧嫁娶仪式的中心。一些村寨无力负担僧人的费用,有寺无僧的现象突出。佛学修养较高的僧人相对缺乏,导致寺院管理不规范,难以满足信教群众需要。与此相反,毗邻的缅甸、老挝则注重佛教人才培养,僧侣素质较高,在边境地区上座部信众中影响很大。有寺无僧导致的“缅僧入境”把国外的宗教观念、思想意识、管理模式,甚至宗教生活方式带入国内,对我国边境群众尤其是跨境民族的宗教认同感、宗教工作的中国化方向带来一定影响。
此问题在西双版纳州最为突出。西双版纳州与老挝、缅甸接壤,相同的民族、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为宗教界的来往提供了方便。近年来,傣族地区有寺无僧现象日趋严重,佛寺的数量不断增加而僧人数量却逐年减少。据调查,目前全州有几十座“空壳佛寺”。由于本地住持宗教活动的僧人数量不足,不能满足傣族信教群众正常宗教生活的需求,故每当各村寨举行宗教活动,尤其是关门节、开门节、泼水节三大节日时,信教群众就到缅甸、老挝邀请外国僧人到境内村寨主持佛寺活动。这些外国僧人入境时多未办理出入境手续,在我国主持佛寺活动属违法行为。
(二)边境地区基督教发展迅速,境外渗透活动加剧
据调查,在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发展过快、过热,有个别县基督教信徒已占到总人口的一半。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播,呈现出由传统活动的地区向原来没有的地区发展、从低层次低收入人群向高层次高收入人群蔓延、由妇女老人向青少年扩张的趋势。边境地区基督教私设聚会点问题严重。其中农村私设聚会点较城市严重。这些私设聚会点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宗教活动场所安排不合理,信教群众为方便宗教生活自行形成的,但也有不少是非法宗教组织和境外渗透组织的活动点。云南边境地区基督教与境外联系比较紧密,有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人士还曾接受过境外资助,甚至受境外控制,已影响到边境地区基督教领域的和谐稳定。
(三)边境地区宗教工作部门弱化,宗教生态脆弱
云南边境地区教派全、信众多、宗教活动场所点多面广,宗教工作十分繁重。与此相对,云南边境地区的宗教工作机构却处于弱化状态。全省从事宗教工作的专兼职干部人数严重不足,在保山、普洱、西双版纳等这些有着数十万信教群众的地区,此问题显得尤其突出。边境地区宗教工作部门的现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做好宗教工作的需要,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心做好宗教工作还有较大差距。
例如在德宏州,边境乡镇信教群众分散,并且缺乏高素质的宗教教职人员,自传工作压力大,导致各教派都存在着自传困难的问题,与独立自主自办宗教的精神相悖。边境乡镇宗教工作经费不足、工作人员少,导致宗教事务管理滞后。各乡镇虽然都配备了民宗助理员、有分管领导,但由于乡镇人员变动大,且为兼职人员,大多缺乏宗教管理方面的知识,对宗教政策认识不够,难以适应宗教工作需要。
再如在普洱市,宗教工作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需要,一些县(区)、乡(镇)、村民委员会(社区)领导干部对宗教问题认识不清,处理不当,部分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对党的宗教政策不熟,情况不明,对宗教“不会管、不敢管、不愿管”的现象普遍存在。
(四)发展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
云南边境地区多为贫瘠山地,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人民群众收入较低。边境乡镇经济发展滞后,信教群众自养能力较弱、受教育程度低,境外宗教渗透势力以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文化普及为手段进行渗透。例如,德宏州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的1.7%,为全省倒数第3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是全省平均水平的67%、全国的37%;贫困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35.6%。在边境沿线的高寒山区等生存条件恶劣地区,主要居住着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景颇族、傈僳族群众,他们还肩负着固边守土的任务,不宜于搬迁。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县乡财政困难,信教群众自养能力较弱,难以抵制境外敌对宗教势力的渗透。
三、边境民族地区宗教法治治理路径
在四个全面伟大战略的时代背景下,要以法治为指导,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和统战工作方针、规制宗教团体与宗教活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维护好各民族团结进而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具体到边境民族地区,还必须解决好民族性、边境性、经济社会与宗教问题相交织的问题,保护合法、打击非法,形成强大的中国化的宗教文化生态以抵制敌对势力的渗透。
(一)以法治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树立法治思维,依据宪法、法律处理好政教关系、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运用法治思维,以法治手段保障宗教治理的长效机制。在遏制渗透、打击犯罪的同时,注重保护合法宗教,积极改善宗教工作。
(二)构建宗教法治化综合治理模式
边境民族地区经济较为落后,信教群众受教育程度低,其获得正确的宗教知识教育的权利难以保障,相关教职人员的培养也难以到位,形成了巨大的空缺,使得境外宗教势力以经济刺激为手段的宗教渗透极为便利。须将发展问题与宗教问题通盘考虑,加大边境地区的扶贫力度,提高边境地区受教育水平。积极引导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宗教团体对边境地区进行扶贫、支教等慈善活动,防止境外敌对势力以扶贫、支教的形式进行宗教渗透。要努力造就一支政治上坚定、学识渊博、品德服众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确保宗教事务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要引导社会信众资金参与宗教学校建设,培养更多可靠的高素质宗教人才。例如,建设巴利语系高级佛学院,可以解决境外僧人当家住持南传佛教寺院的问题。要充分贯彻落实国家宗教局、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卫生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妥善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意见》,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安心为广大信众服务。
(三)转行政管理为综合治理
边境地区经济较为落后,财政资金有限,如果继续延续固有的行政管理模式,甚至“行政管制”模式,必然会力不从心,宗教事务工作必然弱化。所以,必须转宗教事务行政管理为综合治理,改变传统的宗教场所中心主义为宗教团体和宗教场所法人化,依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在宗教团体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政府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事前准入的审批,对宗教行为而非宗教信仰本身进行监管,以更有利于改善宗教工作、服务好信教群众,将中国化的方向内化于信众内心,形成强大的宗教文化生态以抵御宗教渗透。
(四)将边境地区宗教法治建设与 “一带一路”战略相结合
由于边境地区比较贫困,修缮重点宗教活动场所工作不到位,给境外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特别是地处边境地区的宗教活动场所破旧不堪,成为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目标。加强边境地区和宗教重点地区宗教活动场所修缮工作,不仅是为信教群众提供良好宗教活动场所的需要,也是让各民族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分享改革开放成果,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凝聚群众的现实要求;不仅是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宗教渗透的需要,也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保护合法宗教活动,精心做好宗教工作的现实要求;不仅是保护重点宗教文物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挖掘和弘扬重点宗教文物文化内涵的现实要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安排专项资金,在少数民族信教群众聚居的自然村,修复或重建一批具有“标志性”“窗口性”以及对外影响力的“宗教培训中心”和宗教活动场所,以开展宗教对外友好交往,提升对外文化交流的基础能力和条件,增强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渗透的“软实力”。
总之,边境民族地区治理法治化要贯彻中央依法治国方略,努力揭示宗教法治治理的内在规律,反思现行机制的得失,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扶正祛邪,探索边境民族地区宗教法治新路径,必将对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全局性战略构想做出应有贡献。
[1]何虎生,王超.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形成过程中的法治思维——从1931年《宪法大纲》到1982年《宪法》[J].中国宗教,2015,(5).
[2]郭玉华.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统一战线新思想新观点[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
[3]习近平.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N].人民日报,2014-5-30.
[4]习近平.科学把握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N].人民日报,2015-5-23.
[5]高全喜.试论中国当前宗教管理法制化二元模式[J].中国法律发展评论,2009,(3).
[6]李向平.“场所”为中心的“宗教活动空间”——变迁中的中国“宗教制度”[J].宗教社会学研究,2007(26).
[7]Kent Greenawalt. religion and the constitution,vol2,establishment and fairness[on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Available from: www.columbia.edu. 2008.
[8]冯玉军. 日本宗教法治体系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
[9]陈林林.宗教法治的三个基本问题[J].浙江社会科学,2014,(8).
[10]冯玉军.我看国法和教规的关系[N].中国民族报,2015-8-24.
[11]陈欣新.法治与宗教信仰自由[J].中国宗教,2015,(7).
[12]冯玉军.日本宗教法律的实施及对我国的启示[J].学术交流,2014,(8).
[13]刘金光.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成就、挑战与展望[J].中国宗教,2013,(1).
[14]刘会会,马帅.现阶段我国宗教法制建设概况[J].中国科技投资,2013,(11).
[15]李向平.“社团”与“法人”的双重建构——当代中国宗教政策与管理制度改革路线图[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16]徐晓光.新常态下推进宗教法治工作的思考[J].中国宗教,2015,(3).
[17]张勇,胡卓.规范宗教领域行政执法行为路径探究——以江西省为例[J].中国宗教,2015,(6).
[18]董慧凝.解决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保护宗教界合法权益[J].中国宗教,2014,(11).
[1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EB/OL]. 中国民商法网http://www.civillaw.com.cn/zt/t/?29169#_Toc416624039.2015-8-1.
〔责任编辑:左安嵩〕
Innovation Study of The Rule by Law of Religious Affairs in Frontier Minority Areas
NIE Peng, GAO Chong-hui, CHEN Xiao-long
(Law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Kunming,650221,Yunnan, China)
To do well in religious work, we must fac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s of religion; pay more attentions to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lawful 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bal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government and supervision. These problems are serious in Yunnan frontier minority areas.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rule by law, we must transform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into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Furthermore, construction of rule by law of religious affairs must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cal actual situations in frontier minority area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ntier minority areas; religion; social governance;innovation of the rule by law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3XFX025);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YB2014045)
佴 澎,男,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群体性事件研究; 高崇慧,女,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行政法研究; 陈肖龙,男,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宗教法研究。
D693.739
A
1006-723X(2015)12-003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