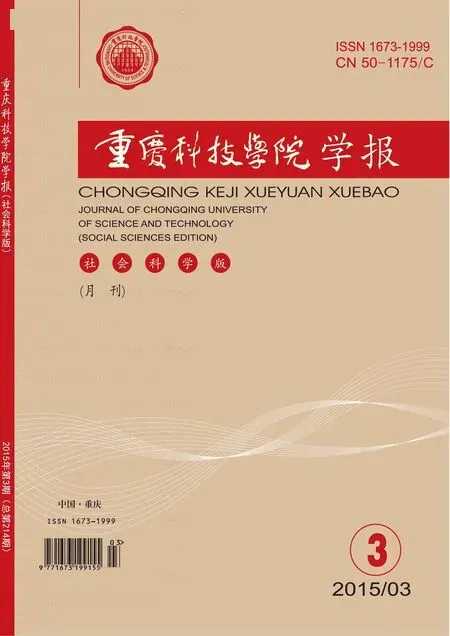从常用范式看新历史主义主体观
邵榕榕
新历史主义代表著作《新历史主义》一书的编者H·A·威瑟把新历史主义评价为 “一个没有确切指涉的措辞”[1]。新历史主义的诸位代表人物也一直努力避免体制化,反对学界对新历史主义僵化的理解,并努力消除学科理论边界。新历史主义的领军人物格林布拉特曾经否认有新历史主义这门学科,更质疑有新历史主义的专门从业人员。然而通过阅读大量的新历史主义著作,笔者归纳整理了新历史主义的建构模式,由此窥测其主体观。
一、新历史主义常用范式
1.“自我塑型”
西方文学史及哲学史很早就开始了对 “自我形象”母题的研究,新历史主义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阐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自我”是快速理解新历史主义的着手点。
19世纪末语言的再发现是学术界的巨大突破。人类惊觉“自我”是深陷在语言之中的历史存在,离开语言人类无法在社会中生存。语言制约并塑造了人。工业、战争、环境在20世纪逐渐强大并扩大其影响,唤醒了新的“自我意识”,人类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世界和他人、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人们试图重构并完善自我。新历史主义理论家在研究此现象的过程中,发现作为主体的人在社会中受到了权力归置和深度解构,并由此建立了新历史主义的重要理论——“自我塑型”。
以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为例,他的“自我塑型”理论始于博士论文《沃尔特·罗利爵士:文艺复兴时期的男子和他所扮演的角色》。沃尔特·罗利爵士(1552-1618)是文艺复兴时期自我形象极为突出的人物。他是政客、冒险家,又是诗人、史学家,他的一生大起大落令人惊叹。罗利在权力斗争、探险战争等等社会操作之间,将现实中的冲突张力放在书信、诗歌、游记等文本的书写当中使之得以疏解。格林布拉特认为,罗利通过诗歌的创作宣泄情感、塑造自我、将自我加以戏剧化,更借此拉近与女王的关系。罗利爵士一生跌宕起伏,主要原因是他被卷进了政治和权力斗争中,这也使得他不得不将“自我塑型”内在化。
罗利曾在其著名的诗作《生活》当中写道:“什么是生活?生活是一幕情感剧,我们随着音乐的节拍欢笑哭泣。母亲的子宫是那疲倦的小屋,我们在那里为着短暂的表演而装扮自己。上帝是那目光犀利的观众,坐在那里记录着个人所犯的错误。夕阳掩映下的坟墓,好像一场即将落幕的戏。我们演着演着,直到最后一次休息。只有死亡千真万确,绝不要以玩笑对之。”罗利借这首诗清晰地表达了自我戏剧化的感慨和人生的诗性内涵。
格林布拉特通过对罗利爵士一生经历的研究,以及对其作品诗性的解读,逐步把“自我塑型”这种研究模式广泛应用到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作品的阐释当中。他的代表作《文艺复兴的自我塑型》详述了自我塑型理论,这一理论为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该书分析了托马斯·莫尔、莎士比亚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在其戏剧性的人生中所进行的自我塑型,并由此发现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人物事件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必然联系,历史、文学和文化的多项反应机制应运而生。
格林布拉特于2004年推出新书《尘世中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新传》,书中汇集了大量边缘化的社会资料,包括私人档案、政治禁忌、警局案件、民间臆想等等。格林布拉特通过这些资料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进行了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向人们展现了莎士比亚独特的自我塑型的过程:这个无权无势无高等教育背景的普通人,凭借创作戏剧与社会展开对话,进行“协商”与“交流”,以其伟大的作品穿越时间和空间,成为戏剧巨匠。
2.“戏剧性”
史蒂芬·奥格尔曾在他的文章 《权利的幻象: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剧院》[2]和《皇家剧院与国王的角色》[3]当中重建了1635年查理一世在皇家剧院观看戏剧表演的场景:查理一世稳坐观众正中,观众如众星捧月般三面环绕着他。英尼格·约翰(Inigo Jone当时一位著名演员)的舞台仅仅是个载体,查理一世的目光可以由此延伸到全英国的大街小巷中去,就仿佛整个英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着。而国王坐在台前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尽在掌握。国王和他无所不在的视线代表着宇宙统治就在皇室中间。新历史主义的主要范式——戏剧性通过这幕场景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了。
有趣的是玛丽·海伦娜·怀特在审判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资料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戏剧性:1793年路易十六被审判时,座位的安排与查理一世看戏时的座次是惊人的相似:路易十六居于中心,那些曾经听命于他如今却能置他于死地的臣子包围着他。看似完全相同的场景,一个是加冕,一个却是罢黜。
新历史主义在对文艺复兴研究当中发现,戏剧性不是始于文学作品,而是始于现实中的剧场,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文化的主要转喻形式。新历史主义理论家认为,戏剧性范式是用来说明“权力”的主要模式。权力本质上是社会、个人和产生单一文化制度的社会之间的协商。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纷乱的社会现实与内部协调一致的状态是相距甚远的,实际上社会生活每个层面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其内部力量自我紧张相互争竞,形成生机勃勃的活力,使得该社会层面得以继续存在。而权力就是从这种充满活力的斗争中产生的。新历史主义所研究的就是具体考察并把握这种权力对于人文表述和主体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因素能够将结构当中的多元性凝聚在一起,戏剧性这种范式就是建立在多元性之上微弱的文化控制。孟酬士曾在《塑造幻想:伊丽莎白时期文化中的性别和权力比喻》一文中,讨论过伊丽莎白女王在自身地位并不巩固、手中权力还不强大时,使用这样的戏剧范式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也就是权力关系)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调节,从而树立了自身的权威,巩固了统治。
3.“凝视——全景监控”
唐·E·韦恩在《潘赫斯特:地域符号学和历史诗学》当中详细描述了一座14世纪的贵族宅邸,从花园的观赏塔可以看到从大门、小路转角,甚至佣人通道,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尽收眼底[4]。这样的描述为的是带领读者越过时间的阻隔,通过全景监控对整个宅邸全盘掌控。约翰·班德在他的著作《想象的监狱:十八世纪英格兰小说及建筑》当中也曾大量使用“凝视——全景监控”范式[5]。班德描述了杰瑞米·班瑟姆(Jeremy Bentham)监狱中央设置的瞭望塔,从这个瞭望塔可以对牢房里的每个犯人进行全视角的监控,而囚犯却对此一无所知。在新历史主义作品中,理论家甚至在自然风景当中也找到了这样的监控点。新历史主义理论家对华兹华斯的作品《夜晚散步》进行了类似的解读,文学作品中风景描述也存在政治性:罗尔·瑞德瀑布(Lower Rydal Fall)自然而然成为了观察者眼中的中心点,从而对周围的自然风景以及风景中的游客起到了监督、规训和统治的作用。
从人类日常生活的居所到囚犯所处的监狱,甚至是旅游胜地,在新历史主义的解读下,都发现了全景监控的中心点,及随之而来的 “自动而匿名的权力”(边沁)。
二、新历史主义常用范式分析及其主体观
新历史主义的自我概念是:长期存在的对个人秩序的感受;个人借以向世界言说的方式;私人欲望被加以约束的一种结构;某种对个性(identity)形成与表述一直发挥着审慎造型作用的因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概念中主要体现的是自我表现力、自我约束力和他人的制约三种因素。自我问题究其实质是人的主体性问题,对意识形态抑制以及他异因素的揭示和彰显只是一种文本阐释的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6]。新历史主义研究自我塑型的根本原因在于探讨并进一步指出自我塑型在历史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性。
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首次确认了文学史是统一结构与多元插曲的结合。他认为历史是具体的、零散的,与充满着偶然性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因此历史代表着文化多元性。文学则被作家提炼加工为更接近普遍真理的作品,从而能够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统一体。而主体所要做的就是在多元性的历史事件中识别并提炼出文学统一体。
在新历史主义常用范式中,无论是自我塑型还是戏剧性、凝视——全景监控范式都包含着统一和多元这对辩证关系。新历史主义大量使用这些范式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揭示两者之间的联系。这样的范式提出了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联系是什么?”也就是说把多元性控制在统一性之中的正式原则是什么。此外,是什么将多元的历史与统一的文学文本联系起来——是什么把国王和戏剧、风景和统治,联系在统一的文化作品之中?
新历史主义研究“联系是什么”,从而引出“文学史的主体是什么”。“主体”这个概念在新历史主义文艺复兴研究的作品比比皆是,例如:格林布拉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型》和《心理治疗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孟酬士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主体和斯宾塞体》,多里摩尔的《激进的悲剧》,亨格森的《自我加冕的桂冠诗人》,凯瑟琳·贝瑟的《悲剧的主体》。另外,部分新历史主义关于浪漫主义的研究作品当中主体性的核心地位也一再被论述。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不仅是福柯似的批评主体——“人性”,更主要的是搜寻主体,任何可以告诉我们它是什么的概念,如权威、作者、身份、意识形态、意识、人性。因为主体把多元性与统一性、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联系起来了。新历史主义的核心问题是“谁拥有权力?”例如,当研究身份的历史塑型时,新历史主义反对对于自我和主体性过于限定的现代概念。在超越个人身份的领域——法庭、王室、工作场所、乡村、教区、班级、国家等等,新历史主义假定在这些权力场所里权力授予的过程中自我塑型随处可见。解释性导向的历史学家迪尔第认为,历史的理解从根本上取决于对权力主体的理解。因为权力的主体是理解错综复杂历史现实与和谐统一的文学文本的最佳着眼点。
新历史主义与传统的历史主义不同,它经由多种范式追问“权力”和“主体”的问题。其中自我塑型概念体现出主体形成过程中与权力的矛盾争斗。在被权力压抑和颠覆的过程中塑造出了自我。新历史主义者研究了众多文艺复兴作家的生平经历、创作思想、社会背景和文化生产,新历史主义的历史主体性视角被得以强调,文化诗学的文化建构实质也浮出水面。作为一种权力结构的政治充当新历史主义意义系统的核心,其主体性问题可以由历史、政治、权力来阐释。
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学生激进的政治主张之中包括了明确的学术改革诉求,他们明确要求大学的课程设置不能回避政治、权力及社会重大问题,同时教师在教授这些课程的过程中需要有鲜明的政治主张,不能一味地保持“学术中立”。新历史主义理论家大多在60年代走入大学课堂接受学术培训,他们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年代独特的政治视角。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批理论家开始学术生涯的时候,他们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把自己的激进思想转化为学术理论,期待通过学术研究处理真实世界的问题。与此同时,新历史主义理论家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使用话语不仅获得教职,取得学术地位,还坚持了自己的理念,对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新历史主义理论家身体力行,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社会“交流”、“协商”,同时也进行自我塑型,成为社会的精英人群。
1968年世界范围内的学生运动轰轰烈烈,昙花一现。这引起了知识界的反思:适逢解构和重建的年代,我们不能只在文学文本中解读文学性。批评家对政治、权力等意识形态问题的缄口不言阻碍了具有政治历史意义的学术研究,对传统的反抗与颠覆在学术界蔓延。时代的变革呼唤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建立,后者充分尊重主体的能动性,重新定位主体,使得人的主体性作用跳出文学领域的藩篱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开拓了理论研究的视野。
[1]Vesser H A.The New Historicism[M].New York: Routledge,1989:9.
[2]Stephen Orgel.The Illusion of Power:Political Theater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27-36.
[3]Guy Fitch Lytle,Stephen Orgel.Patronage in the Renaissance[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266.
[4]Wayne D E.Penshurst:The Semiotics of Place and the Poetics of History[M].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84:81-115.
[5]John Bender.Imagining the Penitentiary:Fiction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Mind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6]傅洁琳.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