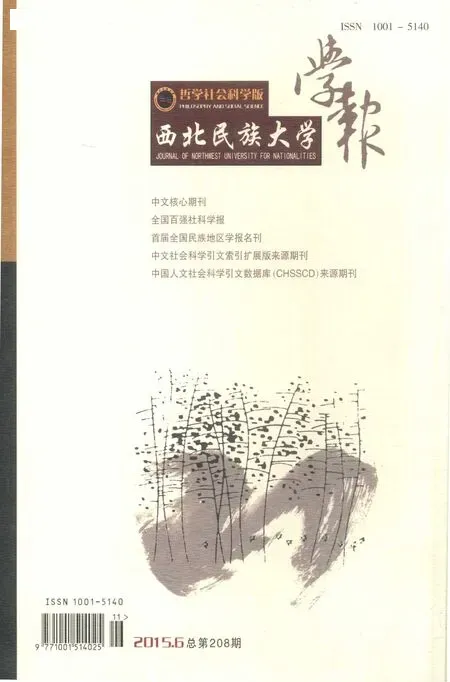从《坛经》看中国佛教的特点
晋 甜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211102)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就不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碰撞,实际上,佛教与中华文化之间的矛盾,时常表现在儒、释、道三教哲学思想的论辩上。有趣的是,长时间的论辩极大地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发展。隋唐时期,佛经的翻译已大致完备,随即出现了开宗立派的辉煌时期,法华宗、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先后成立。特别是禅宗因吸收了儒、道两家思想之长,而广泛被人们接受,可以说,此时期禅宗是融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最成功的佛教宗派,其影响程度使其日益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这也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主要标志,而禅宗的经典《坛经》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总结。《坛经》是出自禅宗六祖惠能之口,经由弟子记录整理而成,是佛教典籍中第一部以“经”命名的中国僧人的著作。《坛经》记载了惠能一生“悟道扬宗”的事迹和开示弟子的言教,文字通俗易懂,内容丰富生动,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它对佛教文化的传播及中国文化的影响都是极其重要的。《坛经》由于历代修订转抄,因而版本繁多,内容详略有别。现存有代表性的《坛经》有敦煌本、唐代惠昕本、宋初契嵩本、元代宗宝本四种版本,其中以敦煌本成书最早。《坛经》的整个哲学体系都是围绕着识心见性而展开的,主要阐述心性论,主张心就是佛,成佛不必外求;针对佛教繁芜的修行仪轨,提出顿悟即可见性的命题的方便法门;惠能所主张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注重现实的特点,为中国化佛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信仰基础。下面笔者拟从分析《坛经》的思想入手来探讨中国佛教的特点。
一、重视心性
《坛经》一书的内容主要阐述心性论,心性论可以说是《坛经》思想的核心,是禅宗修行成佛的理论基础。惠能十分强调“本心”的重要性,他认为人心的本来状态是清净无染的,只要认识了本心,还原了本心,就能见性成佛。他说:“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1]惠能认为,“自性”中本具有般若智慧,只要向内心观照,便有顿见真如本性的可能性,又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2]这样,心性的迷悟成为众生成佛的关键,惠能把抽象的佛性与具体的人心结合起来,他认为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要想悟证佛法,不必外求,只要认识本心,呈现真如本性即可。《坛经》说:“见自本性,即得出世。”[3]及“自性本净”[4];“本性自有般若之智”[5];又谓:“般若常在,不离自性。”[6]也就是说众生本来就具有清净的自性,自性是具有大智慧的,众生若呈现自己的本性,就可以求得解脱,证见佛果。从《坛经》的思想内容来看,心与性的关系常常是统一的。《坛经》说:“识心见性,自成佛道。”[7]可见,识心见性是成佛的途经和方法,觉知自心具有的自性,才是成佛的内在根据。
佛教自传人中国后,就不断吸收儒家思想中重视人本、重视心性的观念。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8]心在具体的修养过程中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儒家提倡“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自察精神,当遇到困难和挫折,当愿望不能达成的时候,要懂得反躬自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从而修正自己的言行举止,不断进步提升。禅宗的创建,《坛经》的问世,正是中国佛教重视明心见性、关注人生解脱的充分体现。《坛经》的心性论思想在禅宗以及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心性合一说”提高了人的生命主体的地位。《坛经》的思想成为唐以后中国禅宗发展主流的基本框架,把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禅宗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从此,禅门多关心内在的解脱和心性的开悟,以《坛经》为理论结晶的中国佛教在心性问题上大有超出儒家的高明之处,这也因此启发了宋明理学心性本体论的建立,为宋明理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为了以更好的状态来维护和加强专制的统治秩序,儒学家们假借反佛、道之名,常常出入佛老,借鉴其高明详尽之义理,为儒学增长元气,以求得两全其美之法。因此,代表官方正统哲学思想的理学应运而生,这无疑是三教思想融合的最终结果。随着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儒、释、道三教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导,以佛、道为辅翼的组合形式,影响千年之久。毋庸置疑,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存并发展下去,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固有的儒、道文化需要吸收、借鉴佛教的心性论来完善、丰富自己的哲学体系。因此说,心性论是中国佛教哲学的核心,重视心性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特点。
二、重视顿悟
关于“顿悟”成佛还是“渐悟”成佛的问题,在中国佛教历史进程中有过长久的争辩。“顿悟”说并不是惠能首创,早在东晋时竺道生便提出这一命题,但惠能的“自性顿悟”与竺道生的“渐修顿悟”在内涵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坛经》提出“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9]的命题,是说顿悟的方法是于自心上实现觉悟。《坛经》把“真如”视为最高的世界本原,惠能曰:“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10]这是说众生本具有圆满的佛性,但有的人愚笨,有的人聪明,愚笨的人执迷不悟,聪明的人迷途知返。惠能认为众生与佛的区别仅在于“迷”与“悟”的差别,那么迷是什么?悟又是什么呢?惠能说:“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11]也就是说,迷是不识本心,悟是自觉本性。惠能还说:“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迷即渐契,悟人顿修。自识本心,自见本性。”[12]在悟的过程中,人之所以有快慢渐顿的区别,是由人的根器不同决定的,利根觉悟较快,钝根相对较慢。又云:“不悟即是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13]又谓:“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14]这是说凡夫与成佛之间只是一念之差,众生本具有成佛的般若智慧,观念的转化是悟道成佛的根本,所谓:“迷人口念,智者心行。”[15]若不觉悟,即便整天念经、拜佛都无济于事,可见,认识本心是成佛的根本条件,“顿悟”是成佛的根本方法。“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16]由此可见,惠能的顿悟说具有“刹那”的特点,因为人人先天具有可以成佛的般若智慧,只要一念相应,让本来存在的心性,自然地呈现出来,就可以刹那间求得解脱。惠能针对其顿悟成佛的命题,提出了坐禅的方法,他说:“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17]惠能特别强调自性不乱的重要性,他认为禅修应该从无念着手,一切智慧都以自性而生。
总之,顿悟是惠能禅宗修持的根本法门,与同门神秀一系主张“渐修渐悟”的法门相对立。《坛经》“顿悟见性”的修行观,把佛从遥远的彼岸世界拉回人间,使人们把寻求解脱的希望从佛国落实到自身。在新的宗教旗帜下,顿悟见性让人们在佛门中找到了自己,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才是成佛的无价之宝。这种创造性的修行观与印度禅注重渐修的方式已有显著的区别,这也是惠能将南宗禅推向中国化的标志。“顿悟成佛”的思想,把佛教从繁冗的清规戒律和经义名理中解脱出来,不但迎合了上层阶级的需要,而且也为下层普通百姓学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种思想对禅宗以及整个佛教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并影响了唐代以后佛教的修持方式,这也是禅宗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广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不讲累世修行、注重顿悟的方便法门,顺应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并成为中国化佛教的显著特点之一。
三、重视现实
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出世、寻求精神解脱的宗教,其宗旨是去除贪、嗔、痴等烦恼,使人们从生、老、病、死等现实诸苦中解脱出来,摆脱生死轮回,永生极乐世界。但这种关心彼岸世界的宗教并非不关心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佛陀创教的本怀正是基于他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眷注。《坛经》虽产生于中国,但在思想上继承了佛陀的大乘精神,同时也吸收了中国儒家重视孝亲伦理与道家重视自然的文化思想。毋庸置疑,中国化佛教重视现实,重视入世的特点在禅宗中的表现最为突出,这种出世不离入世的思想在禅宗之经典《坛经》中有着充分的表现。比如,惠能的顿悟体验并不是在打坐禅修时发生的,他说:“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行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18]可见他提倡注重现实的修行观,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19]他认为,学佛悟道不能脱离现实的人世间,脱离现实人生去寻求佛法与菩提是不可能实现的,又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20]认为在家同样可以修行,不一定非要出家在寺院里进行。《坛经》为了调和佛教出家与儒家伦理纲常之矛盾,提出:“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21]惠能认为清净心即佛心,佛教的神秘化被淡化,修行重在行孝道、行仁义,行为正直、心中无私才是修行的根本法则,修行不能脱离现实人间,而惠能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坛经》辑录,惠能在离家求道之前,“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令充老母衣粮”;“惠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22]可见惠能是安排好母亲的生活以后,才安心前往黄梅拜师学道的。惠能的孝心和出家学佛并不冲突,而是把佛学灵活地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而且惠能还努力使佛教平民化、大众化,他说:“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23]这种思想更加适应下层平民百姓的精神需求,为禅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观念使佛教进一步面向社会、注重现世,重视此岸世界,注重生活修行,即运水搬柴,无非妙道,培育出中国佛教的现实品格。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惠能清醒地认识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统治阶级的接纳和认可,也离不开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即儒、道二家的文化,只有和儒家、道教建立关系,才能保护佛教的顺利发展。惠能虽不识字,但作为中国人无疑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因此,惠能把儒、道二家文化圆融地吸收到佛教之中,特别是在处理孝亲问题上是非常成功的。这种重视现实社会和人生的特点,改变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这无疑也是中国化佛教的一大特色。
总之,禅宗的盛演,与《坛经》的问世密切相关。《坛经》无疑是佛教中国化的思想集结。《坛经》将出世与入世智慧圆融地结合了起来,表现出重视现实、重视人生、强调佛教平民化、关注人们当下解脱的特色,更好地适应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精神需要,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兴盛与发展。惠能大师创新性地将佛陀的本怀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使佛法变得大众化、通俗化,他不愧是人生佛教的先行者,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助缘。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条大河的话,其上游有儒道两个支流,中游有佛教支流汇入,三种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互相激荡,奔向远方[24]。禅宗以其重视现实的精神开创了中国佛教的新纪元,使中国佛教走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即“既在红尘浪里,又在孤峰顶上。”
结 语
唐宋以降,中国佛教以禅宗为主导的发展趋势,正是基于《坛经》重视心性、重视顿悟、重视现实品格的完美演绎,这也构成了中国化佛教的主要特点。当今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科学技术的空前进步,物质文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也不难发现,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价值危机问题严重,社会乱相丛生。侵害弱者、拐卖儿童、吸毒、假丐帮等恶性事件常见诸报端,许多人感到在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情境中惝恍迷离,无所适从。佛教无疑为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因缘。中国化佛教所展示的肯定自性、树立自信、真空妙有、即心即佛、顿悟见性、重视现实的解脱观、修行观,恰似给紧张、焦虑的人们指引了一盏道德的明灯,它让人们相信,人人都有清净圆满的佛性,外在的欲望执著是人生痛苦的根源,在红尘中,保护心灵的清净无染才是得到幸福的真谛。中国化佛教中的禅思可以赋予现代人启迪生命智慧的钥匙,寻回精神的家园,重新认识迷失的自我。近现代佛教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都是中国佛教所透露出的注重现实人生、心性特点的最好说明。
[1][2][3][4][5][6][7][9][11][12][13][14][15][17][18][20][23]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敦煌本坛经(第2卷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15,7,22,10,15,14,15,15,14,9,15,14,13,10,16,19,5.
[8](战国)孟轲著,王常则译注.孟子[M].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207.
[10][16][19][21][22]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宗宝本坛经(第2卷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36,39,41,43,31.
[24]方立天.中国佛教散论[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242-243.
——从体、相、用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