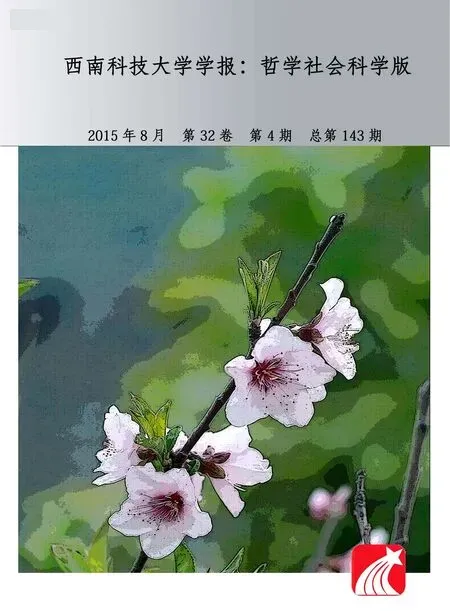取径自然,崇尚天成,回归本色
——论刘克庄诗学的创作论和批评论
何忠盛
(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 四川绵阳 621000)
取径自然,崇尚天成,回归本色
——论刘克庄诗学的创作论和批评论
何忠盛
(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 四川绵阳 621000)
刘克庄是南宋后期文坛的领袖,他受道家美学的影响,形成了取径自然、崇尚天成、回归本色的诗学思想。刘克庄在创作论上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反对堆垛典故和雕章琢句,主张随物赋形,提出“不求工而自工”的理念。刘克庄还把自然美学和本色诗论用于批判宋诗流弊、得出了一些中肯的结论。
刘克庄;道家美学;自然;天成;本色
宋诗到南宋宁宗、度宗朝,发展和演进几近完成。刘克庄和严羽等人一起,完成了对宋代诗歌和诗学进行反思和总结的历史任务。刘克庄没有《沧浪诗话》那样的论诗专著,诗学理论散见于其《后村先生大全集》(后文简称《大全集》)中的论诗诗、序、跋、记、诗话等作品中,但其诗学自身不乏系统性,在理论建构上取得了较大成绩。严羽和刘克庄诗学的论诗范式和理论内核有很大区别,严羽以禅喻诗,重“饱参”,重“妙悟”,重点研究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刘克庄论诗取径道家,以自然美学为理论圭臬,重点研究是什么样的诗歌才是最好的诗歌,诗人怎样才能写出最好的诗歌。取道自然,回归本色,居于刘克庄诗学的核心位置,此前学界并未予以足够重视,本文拟对此进行深入讨论,以期进一步推动刘克庄诗学的研究。
一、静定闻天籁罔象拾遗珠——刘克庄诗学的美学内核
宋代思想文化多元发展,三教合流成为学术文化的主流,士人对儒释道多有濡染,这种取向也表现在宋代诗学上。宋代以禅喻诗成为风尚,如吴可、赵蕃等人“学诗浑似学参禅”的绝句,几乎成为宋人论诗的口头禅。以禅喻诗,以禅宗的智慧来言说诗歌艺术的隐秘和深刻,丰富了中国诗歌理论的话语系统,确有独到之处。但严羽等人认为,惟有以禅喻诗,方能说得透彻,这未免有些过头。所谓“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例如严羽主张从“饱参”到“悟入”,便是借助了禅家从渐修到顿悟的修行范式。刘克庄把诗人从生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比作道教徒从“重浊”到“清轻”的脱胎换骨的修炼过程,又云“余以其说推之于诗,凡大家数擅名今古,大丹之成者也;小家数各鸣所长,内丹之成者也”[1]2471,亦见刘克庄论诗借鉴了道教的修仙范式。
刘克庄出生理学世家,传统儒学和理学修养深厚,其母笃信佛教,受家庭影响,刘克庄对佛学亦有涉猎。他与家乡福建的道士多有交往,对道教和道家的思想有较深入的研究。刘克庄诗学可取资的理论资源是很丰富的,其论诗的理论范式也有多种选择,但刘克庄构建诗学,主要还是取径道家。道家的自然美学主要有两点主张,一是把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纳入审美的视野;二是要求维持世间万物包括人类自身的本真状态。《庄子·骈拇》云:“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2]142。庄子认为,不论“合者”、“枝者”、“长者”、“短者”都是最自然、最美好的存在,人类的任何改变都是徒劳无益、画蛇添足;所谓“不失其性命之情”,就是不让事物失去其本真,人类不能按自己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念去品评事物的美丑善恶。道家自然美学深刻影响了刘克庄诗学的诗人论、作品论和创作论。他认为,诗人只有做自然之子、自然之人,才能作自然之文、自然之诗;只有自然天成、不烦绳削的诗歌才是最地道、最本色的诗歌。
诗人的美学观对其艺术观具有统摄和指导作用。那么在刘克庄的诗学里,什么样的美才是最真实、最自然、最至高无上的美?诗人要保有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才能感知这些美?《大全集》卷88《听雨堂记》云:
天下之至音非静者不能闻,至乐非定者不能知也。风之翏然也,水之淙然也,啸之 然也,入于耳同也;然南郭子綦以为天籁,元结以为全声,阮籍以为鼓吹、为凤音,得于心异也。 昔之人有以丝竹陶写为乐者,有以朋友切偲为乐者。丝竹托于物之声也,人也;雨自然之声也,天也。 今夫大衾长枕,短檠细字,漏断人寂,埙唱箎和,当此之时,溜于檐、滴于阶者,如奏箫韶,如鼓云和,静者闻躁者不闻也,定者知动者不知也[1]2278。
刘克庄把最自然、最真实、最美好的声音称之为“至音”、“至乐”,而如风声、水声、啸声这些“至音”、“至乐”并不神秘,它们广泛地、毫无隐藏地存在于自然界。前代学者对这种“至音”、“至乐”做了理论上的阐释和概括,庄子称之为“天籁”;玄学家阮籍称之为“鼓吹”、“凤音”;文学家元结称之为“全声”。虽异名而同实。《庄子·齐物论》首先提出“天籁”的概念,玄学家郭象对其进行了阐释:“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 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2]24郭象认为“天籁”的特质就是自然而非人为,即所谓“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刘克庄云“丝竹,托于物之声也,人也;雨,自然之声也,天也”,他认为丝竹之声是靠乐器演奏出来的,这样的声音和音乐只不过是“人籁”,而自然界的风声、雨声没有任何人为的痕迹,因而是最真、最美的“天籁”。要感知这些“天籁”,必须保持“静定”的审美心态,所谓“静者闻躁者不闻也,定者知动者不知也”。“溜于檐、滴于阶”的雨声,听起来近乎单调乏味,但在夜深人寂,过滤掉所有的欲望和浮躁后,人们就能欣赏到它“如奏箫韶,如鼓云和”的境界,刘克庄的自然美学观于此也昭然彰显。
诗人要具备怎样的心灵、质素和思维方式,才能捕捉和固化事物的审美特征?诗人要具备怎样的天赋、才学和艺术技巧,方能把事物的审美特征毫发毕现、得心应手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困扰了不知道多少代诗人和文艺理论家的问题,也是刘克庄诗学要回答的问题。《大全集》卷94《竹溪诗序》云:
乾(道)、淳(熙)间,艾轩先生始好深湛之思,加锻炼之功,有经岁累月缮一章未就者。 三传为竹溪,诗比其师,枯干中含华滋,萧散中藏严密,窘狭中见纡余。当其拈须搔首也,搜索如象罔之求珠,断削如巨灵之施凿,经纬如鲛人之织绡。及乎得手应心也,简者如虫鱼小篆之古,协者如韶钧广乐之奏,偶者如雌雄二剑之合[1]2438。
“竹溪”即林希逸,为刘克庄好友。林希逸的诗歌具有“枯干中含华滋,萧散中藏严密,窘狭中见纡余”的特质,接近于刘克庄的“本色”标准和理想,得到刘氏的赞许。对于林希逸的创作经验,刘克庄总结为“搜索如象罔之求珠,断削如巨灵之施凿,经纬如鲛人之织绡”。“罔象求珠”这一寓言出自《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罔象,罔象得之。”[3]217在这则寓言中“玄珠”喻“道”,拾珠喻“求道”;4种求道方式中,“知”同“智”,此指人类的智慧;“离朱”,传说中的明察秋毫者,此指人类的各种感官;“吃诟”,此指能言善辩;“罔象”的意思“无心之谓”,即所谓“象则非无,罔则非有”。善于思考的智者、感官极好的超人和能言的辩士都不能得道,只有若有形、若无形、似无心的“罔象”得道了。刘克庄以罔象求珠的寓言来比喻审美实践和文学创作,意即作家应以自己的心灵去感知和把握若有若无、昏昧不清、处于混沌状态的美;“断削如巨灵施凿、经纬如鲛人织绡”,就是要求诗歌创作不能有任何斧凿的痕迹,诗人应该用最自然的方式把审美的成果表现出来。
二、崇尚天成,追求自工——刘克庄诗学的创作论
刘克庄从道家的自然美学中获取理论资源建构自己的诗学理论,决定了其诗学崇尚自然天成,主张“不求工而自工”的艺术取向。刘克庄诗学在创作论上,反对呕心沥血,戛戛独造。他认为不饰雕琢、得自然之趣的作品才是最好的作品。刘克庄在《大全集》中反复阐述了这一创作思想:
(赵孟侒)卷中佳句清拔流丽,他人掐擢胸肾、呕出心肝形容不得者,君独等闲片语道尽。夫非穷而工,未老而就,不思索而高深,不锻炼而精粹者,天成也。或以人力为之,勉强而不近矣[1]2751。
惟太渊诗文设的于心,发无虚弦,具稿于腹,成不加点。读之尽卷,不见其辞穷义堕处,然犹未尽见其俪语也。 太渊所作剪截冗长,划去繁芜,如以凤胶续断、獭髓灭瘢。人见其粹美无暇,意脉相贯,孰知良工之心苦焉[1]2527-2528。
赵孟侒、林太渊都是江湖诗人,二人的诗歌粹美无瑕,获得刘氏首肯。很多江湖派诗人由于社会阅历、学问才力有限,创作时“掐擢胸肾、呕出心肝”,可谓煞费苦心,结果还是“形容不得”。而赵孟侒能用“等闲片语道尽”所要表现的对象,创出“清拔流丽”之作,刘克庄认为这种不假思索、不经锻炼的创作方式,体现了自然天成的要旨。林太渊创作时“设的于心”、“具稿于腹”,胸有成竹,如同宿构,未遇捉襟见肘、词穷理屈的尴尬,作品亦无苦心经营的痕迹。所谓“凤胶续断、獭髓灭瘢”,传说以为凤胶可以将断裂的物体粘连缝合,獭髓可以去除各种瘢痕,刘克庄以此表彰林太渊通过“剪截冗长,划去繁芜”的不懈努力,收获了“粹美无暇,意脉相贯”的本色作品。赵孟侒和林太渊的创作实践,无疑体现了刘克庄追求自然天成的诗学思想。
刘克庄也认识到,自然美和艺术美是有很大差别的,自然美是客观存在的,只待发现美的眼睛和心灵,艺术美却必须是体验到美的人的提炼和创造。以诗歌创作为例,作家要把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剪裁成诗,则必须借助艺术功力和艺术创作经验。所以“天成”、“本色”对于艺术和诗歌来说是一种理想追求,实践中殊为不易,因此,刘克庄又提出了“不求工而自工”的理论:
周情孔思,既非浅见所能测,湘弦泗磬,又非俚耳所习闻,然平生好之笃如得之艰,颇略知古今作者旨趣。大率有意于求工者率不能工,惟不求工而自工者为不可及。求工不能工者滔滔皆是,不求工而自工者,非有大气魄、大力量不能[1]3441。
引文中的“周情孔思”代表深刻的儒家思想;“湘弦泗磬”代表精湛的音乐艺术,只有笃志好学、孜孜以求的人,才有可能领会其精髓和美感。作家的审美和创作也是如此,要做到“不求工而自工”,诗人必须要有生活基础和艺术功底,刻意求工,结果只会适得其反。那么,要做到“不求工而自工”,刘克庄认为作家必须首先具备“大气魄、大力量”,韩愈、苏轼就是这方面的表率:“坡诗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典丽者,有简澹者,翕张开阖,千变万态,盖自以其气魄力量为之。”[4]25总之,要做到“不求工而自工”,就应该“贯穿融液,夺胎换骨,不师一家;简缛浓淡,随物赋形,不主一体”[1]2498,也就是作家有了深厚的生活底蕴,具备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熟悉诗歌的各种题材和体式,创作起来就会水到渠成,不见斧凿锤炼痕迹,作品才显成熟老道。
三、回归本色,反对雕琢——刘克庄诗学的批评论
“本色”,原是宋代工商业的行话,后来逐渐转换成诗学用语。但理解“本色”的内涵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刘克庄诗学中的本色,要求好诗应该“幽闲澹泊,如不设色之画,不糁之羹,有自然色味”[1]2811,反映的是仍然是道家的自然美学观。道家主张“顺物自然”[2]49,“既雕既琢,复归于朴”[2]124,庄子还说过“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2]82。取道自然,回归本色,自然就要反对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流弊,反对堆砌典故和雕章琢句。
宋代诗人在艺术上不蹈袭唐人,求新求变的愿望非常强烈,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江西诗派及其末流却走上了“搜猎奇书,穿穴异闻”的邪路,写作成为一种文字游戏,诗歌失去了应有的生动形象和情感内涵。刘克庄非常希望纠正宋诗的这种偏颇和失误,《大全集》卷94《竹溪诗序》云: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自二三钜儒及十数大作家,俱未免此病[1]2438。
宋代士人的学问普遍比唐人渊博,表现在创作上就是好逞才使气,好掉书袋,诗歌应有的灵动和生气被完全窒息。刘克庄对此非常不满,讽其不过是“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很多宋诗的大家“俱未免此病”,这和刘克庄追求的“本色”和“天成”的诗学理想完全背道而驰。刘克庄认为,宋诗的这种习气和流弊,深受宋代科举考试的影响:“自先朝设词科而文字日趋于工,譬锦工之机锦,玉人之攻玉,极天下之组丽瑰美,国家大典册必属笔于其人焉。然杂博伤正气,絺绘损自然,其病乃在于太工。”[1]2428-2429很多宋代诗人都有科举考试的经历,诗赋和经义又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长期的科场功夫使他们的思维和创作模式化、刻板化,这些士人不管是否登第入仕,都积习难改,作起诗文来,少不了引经据典,少不了空发议论,这样离本色的要求就越来越远。
刘克庄认为,雕琢是末世文学和台阁文学的通病,历代的宫廷诗人,他们满腹经纶,写起诗来堆砌典故、卖弄学问。宋初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为首的一批学者,受命编纂《历代君臣事迹》等典籍,闲暇之余,写诗唱和,宗法晚唐诗人李商隐,他们的作品后来结集为《西昆酬唱集》。杨亿《西昆酬唱集序》云:“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他们把作诗变成一种拼凑典故、摭拾前人名句的体力活。刘克庄对此痛下针砭,批评西昆体云:“昆体过于雕琢,去性情寖远,至欧、梅始以开拓变拘狭,平澹易纤巧。”[1]2849昆体作家囿于台阁,疏离生活,喜欢雕章镂句,诗歌纤巧拘狭,自然情性被完全窒息,和刘克庄回归本色的主张南辕北撤。
刘克庄指出,诗歌要保持本色,回归本真,而雕章琢句,堆垛典故,割裂诗歌的情感脉络,破坏诗歌整体的美感,就和自然天成、回归本色的理想格格不入。他在《大全集》中结合前代文学,反复阐述这一诗学思想:“真妍非粉黛,至巧谢雕镌”[1]174,“早知粉黛非真色,晚觉雕镌损自然。”[1]496刘克庄对南朝文学和晚唐诗坛颇多非议:“南朝有脂粉气,唐季誇锦绣堆”[1]671,他认为南朝、晚唐那些写富贵闲愁、声色犬马、轻歌曼舞的诗歌,思想上丧失风雅传统,艺术上有失清新自然,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批判。
在文学史上,还有另一类诗人值得注意,这些人生活圈子狭小,思想浅薄,感情苍白,艺术功力不够深厚,永嘉四灵和江湖诗人大多如此。他们足不出乡县,识见有限,创作诗歌往往抓住零星琐碎的情景和感受反复雕琢,意图以苦吟掩盖生活的不足:
古人之诗大篇短章皆工,后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联一句擅名。顷赵紫芝诸人尤尚五言律体,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其精苦如此[1]2431。
虽郊、岛才思拘狭,或安一字而断数髭,或先得上句,经岁始足下句,其用心之苦如此,未可以唐风少之。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惟永嘉四灵复为言,苦吟过于郊岛,篇帙少而警策多,今皆亡矣[1]2540。
以上两则材料,一则说永嘉四灵诗歌的促狭和窘迫;一则说永嘉四灵敝帚自珍,苦吟甚于贾岛。晚宋永嘉四灵和江湖诗人苦吟成风,严羽亦云:“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5]24刘克庄认为永嘉四灵和江湖诗人走肤浅、圆滑、熟烂的路子是不行的,即便是诗人的生活积累不够厚重,社会阅历不够广博,只要创作时做到“简而远,近而深,有味外之味”[1]2429,离本色的要求也就不远了。
总之,刘克庄诗学以道家的自然美学为理论内核,向往天籁之音,主张诗人用独特的心灵去感知和把握事物的审美特征;创作上崇尚自然天成,反对逞才使气,追求“不求工而自工”的艺术境界。刘克庄还以自然美学和本色诗论,对宋诗和前代文学的流弊进行了较为中肯的批评,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1]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2] 郭庆藩.诸子集成本·庄子集释[M].上海:上海书店,1986.
[3] 杨柳桥.庄子译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 刘克庄.后村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Approach Nature,Advocating Tiancheng,Returning Plain——A Study of Theory of Creation and Criticism in LIU Ke-zhuang’s Poetics
HE Zhong-s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Mianyang 621000,Sichuan,China)
LIU Ke-zhuang is the leader of the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literature.He was influenced by the Taoistaesthetics,formed the poetics thoughtof approach nature,advocating tiancheng and returning plain.LIU Ke-zhuang opposed writing poems with the allusion,knowledge and reasoning,and refused stacking allusions and writing in an ornate style.He claimed describing objectively,proposed the concept of“not for the pursuit of exquisite but natural exquisite”.LIU Ke-zhuang criticized the abuses of 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natural aesthetics and plain poetics,and draw some relevant conclusions.
LIU Ke-zhuang;The Taoist aesthetics;Nature;Tiancheng;Plain
I207.22
A
1672-4860(2015)04-0015-05
2015-02-05
何忠盛(1970-),男,四川资中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本文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改革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团队项目成果,项目编号为:Sc-mnu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