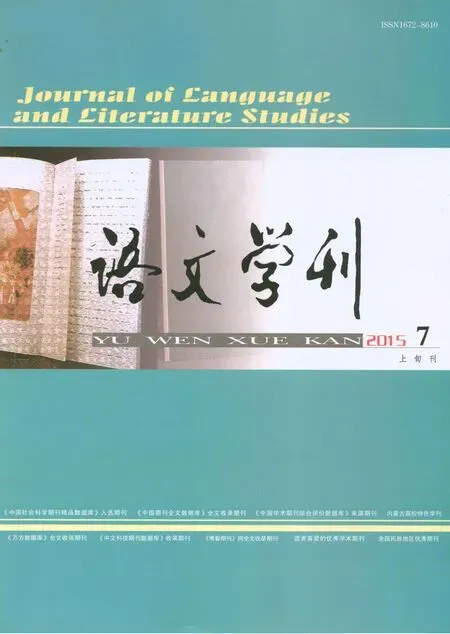破绽与困境的极荒地
——析《荒原》诗学的美学现代性及其悖论
○ 刘一轲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破绽与困境的极荒地
——析《荒原》诗学的美学现代性及其悖论
○ 刘一轲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荒原》作为现代诗歌至尊的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是美学的,因为它将不断更新的隐喻和象征毫无保留地砸到读者面前,从而代替了阅读中传统的“清醒、平庸但朴实的精神”。但诗作百年,“解读”业已前赴后继,艾略特的原始意图虽不可测,但文本却已经承受了来自后来者、尤其是后现代诸流派的理论淬炼和批判攻势,并亲历了自身美学系统的摇摇欲坠、气息奄奄。颇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艾略特再也没能用荒原的手法创作后来的诗歌;但恰恰是这首他自己口中的“个人的、完全无足轻重的对生活不满的发泄”“通篇只是有节奏的牢骚”的发泄之作、这一在批评家口诛笔伐中陷入“形式上的混乱”“模仿性形式谬见”的结构欠缺、语言残缺的争议之作,竟然获得了比其他的语言寻常正规又无比精确的作品(如《四首四重奏》)更恒久的生命力。现代主义在艾略特的身上遗留下的最璀璨的胜果就是《荒原》,现在看来,竟也不知幸或不幸。
象征; 意象; 结构; 二元对立
托·斯·艾略特(T·S·Eliot,1888~1965)这位早已在现代诗歌的“横空出世史”中奠定了宗师地位的“天才人物”,不同于只随时代而变化的感受性相对钝感的普通作者,这些人的出现并不会在语言和诗行的铺行中掀起多大的涟漪;艾略特是一位改变了那一代人表现方式的天才人物[1]1,因此他强烈地感到了与前代人的不同,至少是因为感觉的不同而导致必须使用不同的词汇,所谓“一剑西来,搅乱数池春水”,对于古旧诗歌创作的反叛意图在意象的大胆尝试中昭然若揭。而作为批判者的艾略特,其视角则陡然不同,正如钱锺书在评论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时所说的,“复古未必就是逆流或退化”,艾略特本人在诗歌创作和批评的理论建构中表现出浓烈的古典主义风格:他主张“去个人化”的创作倾向和理性的无往不利,以此来反对浪漫主义过分夸大的个人色彩和无逻辑的感受表达;同时,作为有历史传统意识的批评家,他了解“过去的现在性”,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他指出“历史意识迫使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认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2]3艾略特本人想借助17世纪以前的英国诗歌传统的古典倾向来实现诗学领域的“变革”,这是创新性的另一重话语内旨:复兴,复古以兴,而非复兴古典,或者说以“传统”来“创新”。关于他本人的创作实践和批评观点之间的诸种二元关系,学生在下面将借《荒原》之东风来一窥面目,此处不赘。
然而,比《荒原》文本本身更加棘手的,并不是艾略特的创作和批评是否总是处在同一维度、是否进行同质性的诠释、是否走在平行而有条不紊的方向上这一充满了辩证意味的话题,而是作为现代主义先锋主将的艾略特,是怎样最终坠入“现代性”的极荒之地、面临着大举的溃败,并在理论和创作双方面都被后现代等后来者篡夺城池,至于诗作本身依旧迷雾重重、理论疏漏星罗棋布、争议非难无孔不入的境地的。这样颇带有点悲剧意味的谢幕正是现代派注定要立足的“荒原”。因此,学生这篇论文无意于关注繁缛的象征及其诸种意象本身(也即传统评论中“荒原怎样象征现代文明的没落”等等),而在于关照和考量“象征”之意象成诗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现代性自相矛盾的悖论;同时,既然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派主张“诗学独立”“审美至上”这样有关诗的效果、诗作本身的语境内的问题,那么我们也便从这样的角度切入,以文本作基、以美学形式分析为凭由,再次审视艾略特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进入那“远离人寰”的幽寂荒原。
一、象征的入侵与崩散
我被那缭绕着、紧抱着
这些意象的幻想感动,
一种无穷地温柔的
无穷地痛苦的事物的概念。
——《序曲·第四节》[3]
艾略特的“新史诗”尝试(与庞德不无关系)或者新古典倾向的复苏意图,体现在他本人的创作实践中,是试图使诗成为一种整体的形式,也就是使诗成为关于一切而不是只是某种特别事物的主张,使各种经验在一个整体内各得其所,也就是詹姆逊笔下的“努力协调文化过程的语言概念与越来越看得见的经验资料”[4]23,这就是新史诗的使命(意图);因此在随之而来的论述中,抵制诗作本身的特定主题和应运而生的隐喻带来的特定意义是一切认知的大前提。这可以为艾略特在《荒原》中如此密集地采取象征的态度张本:“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无所不包、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5]18艾略特认为世界本来就是无序的,语言也就不必考虑是否规范,因为“秩序”的概念本就不存在,这也是维姆萨特所说的“以无序的语言模仿无序”①。在艾略特的《荒原》中,读者最直观的印象便是其晦涩难解的诸多意象,其实这种状态更多地来自他诗作中谋划得当的思想脉络的缺席;也正因为此,在剥解掉核心的意义时,读者才会感到作品中并不存在的“细节意义”颇费脑筋,也才会为了寻找晦涩背后的内涵而大费周章。
但是,这恰恰是艾略特所强烈批判的效果!他并不希望读者在面对类似《荒原》这样晦涩的诗歌时表现出“怯场”的状态;在他的设想里,使用的象征意象及混乱化的手法愈多,读者收获的鉴赏感受应当愈好,因为诗歌创作中应当有不同于经验世界熟悉的秩序和逻辑的“想象的秩序”“想象的逻辑”,其特点就是省略了起连接作用的环节、而将纯粹的形式和艺术感觉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应当听任诗中的意象而自行进入那处于敏感状态的记忆之中,却并不必考察这些意象是否使用得当,最终自然会收到最好的鉴赏效果。这一逻辑本是那样的迷人而惊艳,以至于后来居上的现代派们都乐意以这样“为艺术而艺术”的姿态进行诗歌创作;他们推崇将诗歌本体视作自足的艺术系统,而其自身的演进、诗行的延展是“个性消灭的过程”,正如艾略特在那篇经典的论文中所说的那样,“诗人的头脑实际上是一个捕捉和贮存无数的感受、短语、意象的容器……重要的不是那些感情或组成部分的伟大和强烈,而是艺术创作过程的强烈……”②诗作是最终形成的所有要素结合而成的完美化合物,而作者本人在这一过程中只是“媒介”、是将个人化感受全部抛弃、将经验和印象在某一气氛中综合加工起来的中转站而已。艾略特在《荒原》中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信马由缰地驾驭意象、纵横奔肆地使用象征,以期能助推“伟大化合”的水落石出。
然而,艾略特无比歆羡而委以重任的象征性诗学,其核心就在于对艺术技巧和手法的无限推衍,以此来达成对古典文类体系在新时期被破坏掉的统一性的补偿,以便使分散时间在思想里重新汇聚在一起,最终带来统一、整饬而严肃的效果。可惜这其中悖论的出现太过急促,留给《荒原》来消化的时机尚不足余,就被过于浓重的技巧色彩而遮蔽了内旨。原作中这样的诗行:
我想咱们是住在耗子的洞穴里
死人连他们的尸骨都丢失了。
——《荒原·第二节·弈棋》
白色的尸体赤裸在低洼潮湿的地上
尸骨却被扔在一座低矮而干燥的小阁楼里,
年复一年只是给耗子踩得咯咯作响。
——《荒原·第三节·火诫》
这一派腐烂破败、老鼠爬行的景象,加之弥漫在字里行间的百无聊赖的感觉,都在夺目的“尸体”“白骨”的死亡意象中生发,这本是艾略特由对特定意象的迷恋而折射出个人境遇中的挫折和诞生其上的绝望动机,而这种感受本来是贯穿在文本始终的、是理应完整的时间维度,我们也依然有理由相信,艾略特原本的意图绝对不是以技巧来使经验混乱、零碎、破裂,以致出现断片的阅读感受;然而,艾略特忽略了一组微妙的二元对立:即整体和部分的调和度。技巧无论如何都是碎片化的,这是令《荒原》的象征手法始料未及的一点。艾略特本想让思想成为人们可以同时占有的独特客体,但作品的思想和潜在概念都被技巧而四分五裂,占据了作者或者是知识分子活动的不同空间,并脱离了完全是时间延续的事实。换句话说,“作品的纯粹时间或维度都与思想无关,它不再是思想的实现,而仿佛是后者的标志。”[4]38如果到这一层面,我们尚且还可以为艾略特辩白,说这只是艾略特对于审美形式的创新,是惊世骇俗的思想乱流、是转瞬即逝却独一无二的感觉,并把它看做艾略特“纯粹为诗的效果”的本位性坚守,那么下一重的推断则无论如何都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恒河沉落了,蔫蔫的草叶
等待着沐雨,但乌云
集合在远方,在喜马拉雅山巅之上。
丛林默默地匍匐,隆起。
——《荒原·第五节·雷霆的话》
我们看到一个自我批判的意象主义出现了,而最完美的意象(如一颗“草叶”)与生态语境的分离被主题化了,也就是随着技巧悄然变化,“分离”的概念改弦更张成了主旨,而“结合”成为它相对立的概念。与生态语境的分离,也即与真实事物的分离,这里面包含了“象征”概念的原初意义,而蛀洞出现在具体的操作阶段。詹姆逊认为,在科学的时代,象征的投入必然降到看上去最少投入的物质本身,降到最缺少概念内容的东西,也就是“自然的元素”[4]58;在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之下,人们期望把一切观念的事物蔑视为非科学的和迷信的,由此来证明事物及其经验永远比纯粹的观念更值得相信(因为观念总是成为绝对意见和纯意识形态的所在,这样或许还会导致个体化的反动!)。因为这样的思想源流,作为象征主体的意象被迫在具体事物里寻求必要的抽象距离,这本是无可厚非。事实本身虽然不能破坏鉴赏力,但鉴赏的对象却会一定限度上稀释事实的浓度、甚至削弱它的臂展。
关键在于,以上诗句内“恒河”“喜马拉雅”“丛林”和“乌云”的意象,即可以看做是生命的象征,也可以看成是抽象的力量臻于衰落的古老寓言,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因此具有抽象的意义;用黑格尔的观点来衡量,它们每一个都是“既表示意义有同时是象征的类型”③,因此不会融合成总的观念。但诗作又明明把各种现象的不同方面结合在一起,这些现象本身是特定的、实在的事实,却又具有内在本质的联系,这一点显得非常奇怪。这样既独立又相融合的象征范型,最终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被迫表示自己,因为在刚才的论证中我们发现,它们已经不能表示意义。
因此,当象征与事物的这对二元对立产生并被意识到,艾略特所能做的一点,就是在文本中消解意义,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荒原》成稿中所表现出的混乱无序的表象。可是,意义的消解必然借助形式的抽象(像诗中展现的那样),而且需要同时采取多重形式的禁忌:如主题、伟大的风格或连贯叙事本身。然而艾略特对于形式的重视,这个文学性无论多么理想,都是现代主义者的乌托邦构想,实际并不存在。因为这种文学理想需要空间上足够的关注,而读者不可能只关注消解意义的隐喻和意象,在诗行的阅读过程中,对时间和诗体的注意无疑会取代对隐喻和意象相对更多的空间的注意,而隐喻和意象是否就有了退化为相对空洞的“视觉形式主义”的危险呢?至于最决绝的做法:杀死意义和象征带来的隐喻,则更是不可行,因为一旦这样,思想本身压根不会存在;而语言本身就是对于现存事物的隐喻,因此无论如何也不会采取自杀式的“内爆”。这是在现代性美学层面上对于现代性悖论无可奈何的切点:我们只能两手空空地运用象征,它于是成了鸡肋。如若不然,象征就只能承受着“分离”的荼毒,而这种主题的意义无疑是扩展性、污染性的,并且会逐渐扩展到包括诗歌本身的结构;结构若死,则荒原崩散,无所遁形亦无处容身。
“这些意象构成了你的灵魂/这些意象在天花板上隐现/当人世生活全都重新回来。”[3]
艾略特将文本前进的活动性固定于单一的修辞方式的企图,虽然叛离了传统现代性对于修辞的认知,然而偏执于一种“彻底象征化”的模式对于艾略特本人所推崇的整体性审美的损害不言而喻。艾略特在形式的圈套里将自己困入了“荒芜而空寂”④的原野、或者,悬崖。
二、传统干涸与指涉偏误
记忆将一大堆扭曲的事物
高高抛起、晒干;
沙滩上一根扭曲的树枝,
让海水冲洗得平整、光滑,
仿佛这个世界吐出了
它骷髅一般的秘密,
又硬,又白。
——《大风夜狂想曲》
艾略特始终宣称自己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可是在他对技巧的偏向力背后,对于诗歌内容和风格化的辩白则是绵软而零散的,正想现代主义所践行的结果那样,他们没办法给诸种鲜明的二元对立以令人信服的解释:整体与部分、个人与传统、普遍与风格。在这里当我们面对那个并不急需获得回答的问题,即“艾略特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实践是一致的吗?”,必须要接受一个思路,原型是文学的或诗的作品,不一定再是古典意义上的史诗;尽管艾略特的努力正在于此,但却未必很好地吐出了世界秘密的真相,这种不协调性至少在《荒原》中可见一斑。诗作中“报时的钟敲着缅怀往昔的钟声/还有从空虚的水池和枯竭的井底唱出的歌”⑤很像艾略特对于古早生活秩序的追怀和叹息,但是即使感喟若此:
在山岭上那座崩裂了又重建/却又在紫色的天空中突然爆炸的是什么城市/高塔纷纷倒坍/耶路撒冷 雅典 亚历山大/维也纳 伦敦/一切化为虚幻。
——《荒原·第五节·雷霆的话》
也难以逃离虚幻的崩裂在诗行间弥漫的无可为的境地;这样指向性强的字码越多,越在读者眼前展现了一副古典沉沦的悲情画卷。艾略特本人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曾提出较为新颖的传统观,“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自然是不足称道的……”“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整个的体系必须有所修改……于是个体艺术品和整个体系的关系、比例、价值得到了重新的调整……”,[6]从这个角度看甚至可以说,《荒原》从本质上就是将一种真正创新的尝试融入“理想秩序”的实践;由于共时性的传统在不断产生新的组合,那么以不断变化的传统观念驾驭新的创作以吸纳并改变现存的秩序就很可行,尽管《荒原》文本本身的结构是无秩序的。艾略特认为,这就是文本要去个人化的宗旨,也是解决文本对于世界的答案的最好办法。《荒原》是无比焦急的,恰恰在于它太想给现存的事物一个满意的回应,而不只是成为镜像。
但是这真的能实现吗?方才对于《荒原》文本中象征的批判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性谜团的突破口,而之后,又提到了“结构死亡”的可能性,下一步就必然要直面艾略特的设问,他煞有介事的做派之下,关于文本中强烈的“自我指涉性”与去个人化的冲突锋芒毕露,根本没办法被我们绕开。当结构的整体性被破坏,风格就会凸显,也就是他本人极力回避的“感情的放纵”“个性的表现”,也就是作为“起改造作用的催化剂的元素”的个体经验和感情感受。这些也就是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极力关注的“伟大的个人风格”,它会使个体文本失去直接性而变成想象本质的某种实例;所以作者天然的反应就是拼命摆脱“成为典型事例”的死路,转而寻找新的生机,艾略特于是选择了一种更直接也更非个人的东西。然而风格本身就是令人绝望的存在,根本不可能真正通过非个人化来摆脱它,因为充分而确定的实现必然意味着事业的失败;因为在象征出现的一刻,系统成功地变成了冻结的风格,其中体现的各种流动的、无形的互文性和意图,并不会使文本远离自我指涉,反而会以更加自我欺骗性的方式维持着自己计划的自负。也许感受着的人和创造的心灵并不像他所设想的那样容易分离,这也就是批评家所指出的“不是逃避个性,而是更深地进入个性或‘黑暗的胚胎’”。没有非个性的禀赋就没有事物之诗本身,所以艾略特斗争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在对象中消失,把个人的、私自的痛苦转化为更丰富、不平凡的东西,这是普遍而超越的时代能力;但艾略特的失败是注定的,《荒原》里自我指涉的矛盾不可避免。
我坐在岸边
垂钓,身后是干旱荒芜的平原
我是否应该至少把我的国家整顿好?
伦敦桥倒坍了 倒坍了 倒坍了
Poi s'ascose nel foco che gli affina(于是他隐入精炼他们的烈火之中)
Quando fiam ceu chelidon(何时我才能像一只燕子)
——啊,燕子,燕子,燕子
Le Prince d'Aquitaine à la tour abolie(阿基坦王子来到毁圮的高塔)
这些就是我用来支撑自己以免毁灭的零星断片
嗨 我会使你中意的。希罗尼摩又发疯了。
Datta. Dayadhvam. Damyata.
Shantih shantih shantih”
——《荒原·第五节·雷霆的话》结局⑥
平原是最静止的东西,同时又是一切张力和对立的惊人所在,一个持续斗争的地方,充满了鸿沟和断裂。世界和土地似乎要互相撕碎,形式在曾经静止的地方活跃起来。重复的坠落和倒坍,毫无意义却凛冽浮夸,这似乎是所有维度的“降落”,是拯救的失败也是诗歌最终的失败,是作者已死的陈述也是情感的、历史的、甚至是比喻的沦丧。艾略特无处可去,因为他已来到命定失意的极荒地,诗歌的收束是果敢的尽忠,荒原上万籁俱寂、实落材亡。
三、结 语
博尔赫斯说,“西方文学的第一座丰碑《伊利亚特》写作于三千年前……在如此长的时期内所有内在的、必要的相关词都曾被涉及和写作过,但这不意味着隐喻的数量趋于尽头,指出或暗示秘密的方式永无止境。”[7]73在这样漫长的流动中,语言的变化会抹去次要的意义和微末的色彩,修辞学(象征学)隐蔽的真谛是现代文学永恒的主题,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不可知的始作俑者。艾略特很想了解通过了符咒和幻觉的灵魂是否依然从属于这个时空,或许他根本上还是想以这样打破主语和谓词局限的否定者身份,接近非个人式的无限回归,那将是从分裂成相互仇恨的遥远的人类处归来,走在属连的土地上进行似是而非的衔接过程。
然而,荒原的本质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因此普遍的、传统的证实只能成为虚无的寓言,毕竟未来之花比梦中之花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说我们可以大胆设想,《荒原》美学所构想的乌托邦终究实现,那将不可抗拒地使所有人向往它的背面,而最终必将大获全胜。而现在,艾略特吞咽注定失败的果子,其形式,正是荒原的沉堕和降落。
【 注 释 】
①(美)维姆萨特:《语象》,第116页。
②(英)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本文引用此论文有两个译本,一是李赋宁译本,一是卞之琳译本,撷取各自特征引用,以下所有为卞本。
③该论述引自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著作《美学》和《精神现象学》
④引自艾略特组诗《荒原》第42行,属于第一节《死者的葬礼》,汤永宽译。
⑤引自艾略特组诗《荒原》第383行,属于第五节《雷霆的话》,汤永宽译;本文中《荒原》译本有两个来源,一是汤永宽译本,一是卞之琳译本,撷取各自特征引用,以下所有诗句引自卞本。
⑥引自艾略特组诗《荒原》第423行起,属第五节《雷霆的话》,卞之琳译,此段为荒原最后一段。
[1]陆建德.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2](英)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M].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3](英)托·斯·艾略特.序曲[C]//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4](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总体性诗学[C]//论现代主义文学.苏仲乐,陈广鑫,王逢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英)托·斯·艾略特.玄学派诗人(1921)[M].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6](英)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M].卞之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7](阿)博尔赫斯.隐喻.王永年,译[C]//博尔赫斯谈艺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8]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9](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10](阿)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艺录[M].王永年,徐鹤林,黄锦炎,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11](德)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13.
[12](德)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
[13](英)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刘一轲,男,湖北武汉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I106.2
A
1672-8610(2015)07-0003-04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