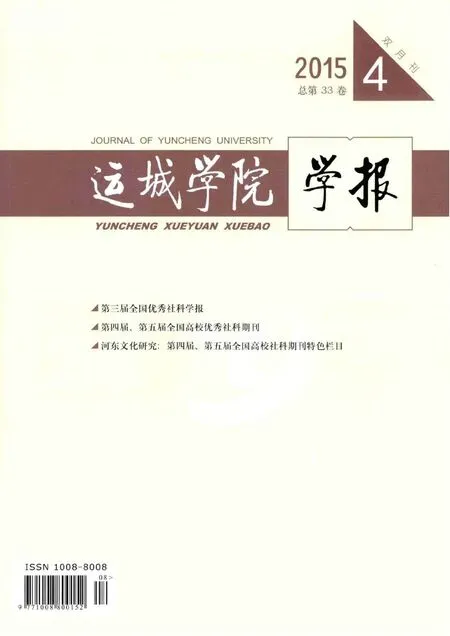辩护律师获取证据制度的完善
——以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为分析背景
王 晓 红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辩护律师获取证据制度的完善
——以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为分析背景
王 晓 红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为使律师辩护达到实质效果,保障辩护律师获取有利于被追诉者的证据和充分知悉控诉证据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面临结构性障碍,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间接保障律师知悉或获取证据,保障辩护律师申请调查取证以及申请调取证据权的实现;充分保障辩护律师与被追诉者的会见交流权;保障律师阅卷的全面性;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审判机关应予以满足;增加规定辩护律师申请证据保全的权利;并对剥夺辩护律师获取证据权利的,确立程序性制裁。以上措施的完善可以有效弥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能力的不足,实现律师辩护的实质化。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申请调查取证;申请调取证据;证据保全
一、引言
刑事诉讼的发展史即是辩护制度的发展史,辩护制度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志。辩护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专门维护者,在参与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充分知悉有利于被追诉者和不利于被追诉者的证据材料是进行有效辩护的前提。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改,为了保障辩护律师获取充分的证据,新增辩护律师有权申请调取证据,即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同时恢复全案卷宗移送制度,进而扩大了辩护律师审前阅卷的范围,使辩护律师通过审前阅卷可以充分知悉控方的证据材料。为了防止辩护律师因为调查取证受到报复性追诉,新《刑诉法》第42条第2款规定,追诉律师伪证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审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与此同时,增加对辩护律师的权利救济,辩护律师行使辩护职能受到阻碍的,有权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或控告,检察机关有救济义务。不可否认以上制度设计对于辩护律师获取证据的能力有所提升,但新《刑诉法》对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本身并无实质性突破,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依旧无完善的制度保障,《刑法》第306条依然是阻碍律师调查取证的达摩克斯之剑。同时,辩护律师申请调查取证面临的困境也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律师申请检察机关调查取证与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能发生直接冲突,尤其在自侦案件中更是如此。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无阅卷权,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律师会见嫌疑人还面临障碍。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不管是辩护律师还是被追诉者均无权申请保全证据。办案机关侵犯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不需承担任何不利后果。
辩护律师充分获取证据是保障律师实质性参与刑事诉讼并进行有效辩护的基石,也是落实“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必要制度设计,更是实现刑事诉讼控辩平等的必然要求。而律师获取证据能力的欠缺可能导致新《刑诉法》旨在加强辩护律师有效参与刑事诉讼的各项制度设计落空,造成辩护律师无论是进行程序性辩护还是实体性辩护均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在我国当前的法治环境下,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有效保障辩护律师获取充分的证据是我们应予以认真思考的问题。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框架内,就获取证据的手段而言,为了达到理想的辩护效果,辩护律师是应该自行调查取证,还是可借助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力量获取证据,抑或应更加注重通过阅卷来发现控方证据的漏洞进而对控方证据提出质疑以减少自行调查取证带来的执业风险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辩护律师获取证据的文本解读
为了保障辩护律师充分获取证据,新《刑诉法》首先赋予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权。除此之外,为了弥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能力的不足,同时赋予其申请调查取证和申请调取证据权。为保障辩护律师充分获取证据,新《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对辩护律师会见权、通信权、阅卷权、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权、申请重新鉴定、核实证据权等权利的保障。
(一)自行调查取证
新《刑诉法》及司法解释对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权进行规范,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对象包括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掌握实物证据的有关单位和个人。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相比,新《刑诉法》对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并无新的规定。新《律师法》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并未特别强调调查取证需经被调查者的同意和许可,旨在减少律师调查取证的阻力,遗憾的是新《刑诉法》并未吸收此规定,而依然延续1996年刑诉法的规定,即辩护律师在征得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向其收集证据材料;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证据材料时,需经其同意,同时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否则不得向其收集证据材料。与侦查机关取证的强制力不同,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以对方的同意和配合为前提,如果对方不愿提供证据,可以任何理由拒绝辩护律师的要求,造成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权利落空。
新《刑诉法》明确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完善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权利,但是对于侦查阶段律师是否有权调查取证并未明确规定,其后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依然语焉不详,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认识上的分歧以及实务操作标准不一。由于所持的诉讼立场不同,辩护律师和办案机关对律师在侦查阶段是否有权调查取证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办案机关尤其是侦查机关对此大多持反对态度,其理由是刑诉法未明确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刑诉法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列举并未包括调查取证,法律没有明确赋予的权利辩护律师就不应享有。而且从办案的角度考虑,如果允许律师侦查阶段调查取证,可能会给侦查工作带来障碍,尤其是对于主要依据言词证据定案的贿赂犯罪案件更是如此。相反,学界和律师界对辩护律师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持支持态度。其理由为:根据新《刑诉法》第40条的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如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能调查取证,何来将以上证据告知给负责侦查的公安机关一说?新《刑诉法》已经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而调查取证是辩护人基本权利的应有之义,承认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就应承认其调查取证权。法律条文并非孤立存在并发挥作用,法条的确切涵义有时必须联系前后相关法条的语境才能确定,尤其是同一部法律前后法条之间不能出现矛盾和冲突。[1]从体系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来理解,新《刑诉法》关于辩护律师权利的一系列规定均表现出赋予其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意图。
对于以上对立的观点,笔者认为侦查是收集、固定以及保全证据的关键阶段,实物证据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会面临毁损、灭失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进言词证据可能会改变,证人的记忆会逐渐模糊,侦查阶段不但是获取指控证据的黄金时间,也是辩方收集对被追诉者有利证据的关键环节,因此为了实现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有效辩护,充分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为了实现实体公正和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均应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调查取证权。
(二)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查取证
由于辩护律师无强制取证权,取证成功与否取决于对方的配合程度,在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还较为淡薄的状况下,律师自行调查取证面临不少障碍。为了弥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能力和手段的不足,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规定了辩护律师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收集和调取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规定:“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时,因对方不同意,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或者申请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辩护律师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向证人或者有关单位、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且不宜或不能由辩护律师收集调取的,应当同意。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材料时,辩护律师可以在场。收集调取证据材料后,应及时通知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并告知人民检察院。辩护律师的申请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说明理由,写明需要收集、调取证据材料的内容或者需要调查问题的提纲。对辩护律师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在5日内做出是否准许、同意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法院不准许、不同意的,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高检规则》)对此作了大致相同的解释,只是审查时间规定为7天。
以上司法解释规定的辩护律师申请调查取证的理由可以是“由于对方不同意”,也可以“基于其他原因”而申请调查取证;律师提出申请的方式应是书面而非口头方式,而且只有被申请的检察院或法院认为确有必要时,才会准许。由于检察院和法院对申请的审查标准语焉不详,如果申请被拒绝,律师如何寻求救济也不明确。在我国现行诉讼环境下,检察机关承担追诉职能,有很强的追诉倾向,而申请检察机关调查取证与其追诉职能相悖,成功的概率可想而知。行使审判权的法院虽然在刑事诉讼中地位中立,但法官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较重的审判任务,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可行性也令人生疑。
(三)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证据
为了保障辩护律师获取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新《刑诉法》增加辩护律师申请调取证据权。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高法解释》进一步规定申请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提供线索或材料,人民检察院移送相关证据材料后,人民法院应及时通知辩护人。《高检规则》规定,案件移送审查逮捕或者审查起诉后,辩护人认为在侦查期间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申请人民检察院调取的,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应及时将申请材料送侦监或公诉部门办理。经审查,认为辩护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已收集并且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应当予以调取,认为申请调取的证据未收集或者与案件事实无联系的,应决定不予调取并向辩护人说明理由。公安机关移送证据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在3日以内告知辩护人。从以上规定分析,在侦查和审查起诉期间,辩护人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调取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而到了审判阶段,辩护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向检察机关调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
(四)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
《高法解释》第182条规定,申请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应当列明有关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证人是否出庭由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决定,允许控辩双方在参加庭前会议时对出庭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名单提出异议。对于不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辩方只能在法庭审判开始之后的庭审过程中,才能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第302条规定,控辩双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出示证据,应当说明证据的名称、来源和拟证明的事实。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准许;对方提出异议,认为有关证据与案件无关或者明显重复、不必要,法庭经审查异议成立的,可以不予准许。
人民法院对是否通知证人出庭的衡量标准是,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同时人民法院认为有作证必要的,证人才应出庭。由于证人出庭可能会给庭审结果带来不确定性,尤其是在证人证言属于关键性证据的案件中更是如此,因此为避免证人出庭后改变证言带来的败诉风险,公诉方一般不希望证人出庭。对庭审法官而言,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对质可能使庭审过程充满变数,使法官难以掌控庭审,而且证人出庭也面临着延长审理时间,降低庭审效率的弊端,目前法官普遍面临极大的办案压力,因此对证人出庭也无很大的积极性。新《刑诉法》实施后证人出庭率并无实质性突破。海南省H市2013年以来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情况统计显示:出庭公诉案件总数1582件,其中证人出庭案件5件7人,证人出庭率0.3%。值得注意的是,5个案件中控方证人出庭案件4件5人,证言均被法庭采信,辩方证人1件2人,证言未被法庭采信。[2]如此低的证人出庭率显然与我国对抗制的刑事庭审制度改革的初衷相悖。
(五)辩护律师通过行使会见、通信和阅卷权等方式知悉相关证据
除了自行调查取证、申请调查取证以及申请调取证据外,辩护律师通过与被追诉人的会见、与被追诉者通信以及阅卷等方式可以知悉相应的证据。会见与通信是辩护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重要活动,通过与嫌疑人的交流,辩护律师不但可以为其提供法律咨询,而且可以充分知悉被追诉者是否实施犯罪行为以及掌握有利于嫌疑人的相关证据。有效辩护的实现除了需要积极收集有利于被追诉者的证据之外,对不利于被追诉者的控诉证据辩方也应充分知悉,唯此,辩方才能有针对性地展开辩护,找出控方证据存在的漏洞,达到理想的辩护效果。
辩护律师通过会见嫌疑人、被告人获取对其有利的证据是辩护律师享有的基本权利。但侦查人员普遍反映,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会见嫌疑人后,嫌疑人翻供率较高,如果在嫌疑人供述前辩护律师会见,则以后可能很难获得有罪供述,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更是如此,因此新《刑诉法》实施两年来,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律师的会见权依然受到一定的限制。
(六)辩护律师向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
新《刑诉法》赋予辩护律师核实证据的权利,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向犯罪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通过阅卷获得的证据绝大多数属于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控方案卷中的证据可能由于提取、保管、收集方式不当等原因导致证据的虚假或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因此,向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是辩护律师与嫌疑人、被告人商讨合理的辩护策略以及进行有效辩护的基础。新《刑诉法》的这一规定值得肯定,但其对辩护律师核实证据的具体方式并无进一步的规定,究竟是律师仅能就了解到的证据不明确的部分向嫌疑人口头核实,还是辩护律师可向嫌疑人出示摘抄或复制的证据材料,司法实务界存在分歧。实务部门主流观点认为,辩护律师核实证据并不等于向嫌疑人直接出示证据材料,其理由是如果允许律师将证据材料展示给嫌疑人,极有可能导致嫌疑人进行串供或翻供,在共同犯罪案件中更是如此。而且如果证人的信息被嫌疑人知悉,可能会导致证人被报复的现象,客观上加剧证人不出庭的状况。笔者认为以上理由过于牵强,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核实证据的阶段为审查起诉阶段,根据侦查规律,在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的证据已经固定,而且除了嫌疑人口供之外,还存在着其他证明嫌疑人有罪的各种证据,即使嫌疑人翻供,如果其他证据确实充分,尤其是相关的实物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依然可以实现追诉的成功,并不会给侦查造成障碍。至于办案机关所担心的证人受到报复的问题,应从加强对证人的保护方面做文章,而非片面限制嫌疑人对证人证言的知悉权。
(七)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
勘验犯罪现场是侦查机关实施的专门侦查行为,辩护律师无权参与,如果辩护律师对侦查人员的勘验过程及结果有异议,可视诉讼的不同阶段向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提出重新勘验的申请。根据我国刑事诉讼鉴定体制,辩方无权自行鉴定或直接申请办案机关鉴定,对于办案机关出具的鉴定意见辩方如果有异议,只能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申请重新鉴定的时间一直延续到开庭审理阶段。辩护律师通过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可能会获得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信息,尤其是当重新勘验和鉴定的结论与原结论完全相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从以上关于辩护律师获取和知悉证据的法规范分析,刑诉法对辩护律师获取和知悉证据的权利从以下三方面予以保障。其一,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此为辩护律师获取证据最为简单直接的方式,但其效果取决于证人的配合程度,实践中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根据实证调研的结果,新刑诉法实施以来,“实践中调查取证依然是律师的红线,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刑网。调查取证从目前来讲,一点进步都没有,就是不能去触碰的高压线。”其二,通过向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公权力机关申请调查取证或申请调取证据。检察机关负有客观义务,对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或调取证据的申请,应积极给予回应和帮助,但此义务与检察机关承担的控诉职能直接冲突,一般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审判人员承担繁重的审判任务,实践中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或调取证据申请,一般也不会予以积极回应。第三,通过对辩护律师阅卷、会见被追诉者、与被追诉者通信、申请证人出庭、申请重新鉴定等权利的保障来实现其知悉证据的目的。在以上各种途径中,辩护律师知悉控方证据最直接的方式即是查阅控方的案卷尤其是证据卷,从而获得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证据。
三、域外辩护律师获取证据的方式及启示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
由于诉讼模式不同,两大法系国家辩护律师获取证据的方式存在根本差异。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法律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行为并无禁止性的规定。在侦查阶段,实行双轨制侦查,辩方拥有与侦查机关平行的证据收集权,除自行调查取证外,辩护律师亦可通过私人侦探等专业机构调查取证。为实现有效辩护,保障辩护律师与嫌疑人进行充分交流,侦查阶段即允许辩护律师与在押的嫌疑人自由会见和通信;警察实施强制侦查行为时,辩护律师有权在场。简而言之,作为一项普遍规则,每一个被告人都具有与他的律师探讨涉及案件事实的侦查、辩护准备和辩护行为方式的所有问题的宪法性权利。[3]135与此同时,为了防止侦查机关的非法或不当的调查取证行为造成对被追诉者宪法性权利的损害,英美法系国家要求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的正当程序,否则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可能面临被排除的危险。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平等,保障辩护律师对控方证据充分的知悉权,英美法系国家要求控方将所有的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都开示给辩方,而辩方向控方开示的证据范围则极为有限,一般仅限于能证明嫌疑人无罪的证据,比如无作案时间,不在犯罪现场等。
(二)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的侦查模式为弹劾式,侦查活动由代表国家的检察官主导,实行单轨制侦查,检察官同时负有客观真实的法律义务,收集证据应全面客观。法律不鼓励辩护律师进行事实调查,也不允许辩护律师与控方证人接触,否则一旦被发现,将会削弱证人证言的可信度。[4]258审问式侦查认为,辩护律师一旦介入侦查,侦查工作就有先入困境的危险,因为通过与律师的会见,犯罪嫌疑人极易增强抗拒侦查的信心和勇气,对侦查人员的讯问不予合作的情况也会急剧增多。[5]29需要注意的是,大陆法系国家通常认为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的规定只是为了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对辩方并不适用,“私人非法获得的证据,原则上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6]242
为保障辩方在法庭上拥有提出证据并对控方证据充分质证的机会,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构建了保障辩方获取证据的制度。以德国《刑事诉讼法》为例,被告人获取证据的途径除了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自行收集证据之外,主要通过三种具体方式来实现:首先是被告人的案件知悉权;其次是提出证据权;最后是对质询问权。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47条规定,辩护人有权查阅移送法院的或者在提起公诉时应当移送法院的案卷,有权查阅官方保管的证据。在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允许拒绝辩护人查阅对被告人的讯问笔录,查阅准许他或者提出要求时必须准许他在场的法院调查活动笔录,查阅鉴定人鉴定。第165条规定,被法官讯问时,被指控人申请收集对他有利的一定证据,如果证据有丧失之虞,或者收集证据能使被指控人得以释放的,法官应当收集他认为重要的证据。在实质真实理念的指导下,大陆法系国家的审判法庭负责收集所有必要的证据来对案件做出裁决,但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有权自由参与对相关证据的调查、有权独立收集并在法庭上提出相关证据、有权同法院解除并要求其调查额外的证据;甚至有权审查法院提出的证据以及违背法庭意愿提出相关证据。[7]167
(三)对我国的启示
从两大法系国家刑事辩护制度的规定来看,虽然诉讼模式不同导致对辩护律师获取证据的权利保障存在差异,但是各国均在积极通过各种制度设计来保障辩护律师最大限度获取证据。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双轨制侦查,律师拥有较为广泛的侦查权,并且以传闻证据规则来保障辩护律师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权。而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实行单轨制侦查,侦查由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主导,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规定并不明确,但如此并不代表律师获取证据能力的欠缺。为了保障辩护律师充分获取相关证据,保持基本的控辩平等对抗,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规定辩方有权申请证据保全,以免造成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毁损、灭失而带来给被告人错误定罪的风险。同时,大陆法系国家确立的检察官应承担客观真实义务以及检察引导侦查的体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证据收集的全面性和合法性。需要强调的是,基于律师自行调查取证存在困难及风险,大陆法系国家更加致力于通过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会见交流权、申请调查取证权、证据保全等制度来间接达到使辩方充分获取证据的目的。另外,两大法系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是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方式不属于该规则的规制范围。
与大陆法系的侦查体制类似,我国实行单轨制侦查,侦查权被侦查机关垄断,辩护律师无权参与,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辩护律师获取证据的时间较为滞后,并且辩护律师的取证手段有限。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的诉讼制度和司法环境下,除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外,应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制度设计,即不必过于纠结如何保障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而应从国家专门机关对辩护律师证据获取权的保障和救济等角度进行制度设计。因此,笔者认为:为了保障辩护律师充分获取证据,实现有效辩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确立证据保全制度;保障律师全面阅卷,尤其是补充侦查获取的证据应保障律师能够查阅。为了保障辩护律师对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对质询问权,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证人、鉴定人出庭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审判机关应予以支持和满足。
四、辩护律师获取证据的制度完善
(一)吸收《律师法》关于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规定
无可否认,自行调查取证依然是辩护律师获取证据的最有效方式。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对于知悉案件情况的证人,无论是对国家机关还是辩护律师,只要符合作证条件,均有作证的义务,立法应鼓励有关单位、个人向律师提供证据。因此应吸收新《律师法》的规定,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时,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取消“需经对方同意”的规定。当然如此规定并不代表律师拥有强制取证权,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权利属性依然为“私权利”而非“公权力”,但至少可以淡化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抵触情绪,便于律师收集证据。另外,实践证明,刑法第306条已然成为律师调查取证的最大阻力,此条文在实践运用中针对性极强。据全国律协的有关调查显示,1997年至2007年的10年间,已经掌握的因刑法第306条被追诉的律师多达140多人,但该调查尚有很多遗漏,实际数字更高,而最终被判定有罪的只有32起。正是这一条加剧了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职业报复,也加剧了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难度。因此,为了保障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顺利进行,应考虑废除该条。
(二)确立程序性制裁
程序性制裁与实体性制裁相对应,不是制裁违法办案机关或办案人员本身,而是“以毒攻毒”,一旦确认程序违法行为成立,即宣布由此获得的诉讼利益无效或不发生预期的诉讼效果。[8]535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救济的最后保障措施,为保障辩护律师获取证据权的实现,对于检察机关、人民法院随意拒绝辩护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或申请调取证据的,应给予相应的程序性制裁。《刑诉法》确立了辩护律师的权利救济制度,第47条规定:“辩护律师认为公、检、法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和控告应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专门机关阻碍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既包括积极阻碍也包括对请求的消极回应,《高检规则》对阻碍行为进一步解释为:“没有正当理由不同意辩护律师提出的收集、调取证据或者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或者不答复、不说明理由的;未依法提交证明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的。以及违法不允许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的;违法限制辩护律师同在押、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的;未依法告知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的。”以上对于辩护律师权利救济的制度设计应予肯定,但值得思考的是,如果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被办案机关无理拒绝后,发生证据毁损甚至灭失的情况,此种情形下通过检察机关的事后救济,根本无法达到法定的效果。因此,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对辩护律师的救济条款,但就调查取证而言,显然必须同时确立程序性制裁,才能真正将救济条款落到实处。程序性制裁意味着违法者违反程序法的规定即应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对于辩护律师申请调查取证、申请调取证据的,如果由于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怠于履行职责,致使证据毁损、灭失的,应该做出不利于控方的推断。
(三)赋予辩方申请证据保全的权利
证据保全制度是指证据在后续程序中存在灭失、伪造、变造、藏匿或其他难以取得的情形时,由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向专门机关提出申请后所采取的预防性保全措施。[9]我国民事诉讼以及行政诉讼中均规定有证据保全制度,《民事诉讼法》第74条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加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证据保全的条件是有保全的紧迫性,对证据如果不予保全,将导致证据永远无法取得等后果发生。与民事诉讼相比,刑事诉讼结果涉及对被追诉人的人身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的剥夺,因此更应赋予嫌疑人、被告人申请证据保全的诉讼权利。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是收集和保全证据的关键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遗留的证据可能面临着毁损、灭失的风险,证据的性质和状态也会发生某种改变,如果不及时进行证据保全,可能面临由于证据毁损灭失而错误追诉的危险,因此侦查应是证据保全的关键环节。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均规定了侦查环节的证据保全制度,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台湾地区2003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专门增设了证据保全制度,第219-1条规定:“告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或辩护人于证据有湮灭、伪造、变造、隐匿或碍难使用之虞时,侦查中得申请检察官为搜索、扣押、鉴定、勘验、讯问证人或其他必要之保全处分。检察官受理前项声请,除认为其不合法或无理由予以驳回者外,应予五日内保全之处分。”[10]553通过上述对证据保全的规定可见,证据保全是一种特殊的措施,其采取的前提除了证据可能灭失这一典型情形外,还包括证据可能会被伪造、变造、藏匿等情形,即证据可能永远无法取得或性状发生根本性改变时,应采取证据保全。证据保全的申请主体有当事人、辩护人以及诉讼代理人,当事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必然的利害关系,因此拥有申请保全的权利自不待言,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分别是被追诉者和被害人合法权利的专门维护者,为了维护其利益和弥补其法律知识和诉讼能力的缺陷,亦应被赋予申请的权利。
我国证据保全的义务主体可确定为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审前充当准司法官的角色,与审判阶段相比,较易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可以进行以下制度设计,嫌疑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在侦查阶段或者审查起诉阶段,申请检察院保全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辩护律师或者代理律师也可以代为提出保全证据的申请;对此,除确无必要或者明显是为了故意拖延诉讼的以外,检察院不得拒绝;检察院应当及时把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等的申请收集调取的证据告知申请人, 必要时可以通知申请人或者其律师到场。[11]
(四)明确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检、法应当同意的理由
依据刑诉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目前律师申请调查取证的,能够获得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认可的理由为“认为确有必要”,这一标准过于主观化,等于没有任何标准,因此对其应予以明确。笔者认为可借鉴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律师申请调查取证的前提是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需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辩方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辩方申请调查取证的前提是辩方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调查证据,即只要辩护律师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案件的定罪量刑有关联,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律师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调查取证的,并且律师申请的目的不是为了故意拖延诉讼,即应获得准许。
申请调查取证应以书面形式提出,书面申请的内容包括拟申请调查的证据名称、申请原因、与待证事实的关系、申请通知出庭的证人、鉴定人的姓名、住址等。审查的标准以及驳回申请的情形可列举为:不能调取的;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的事实;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性;待证事实已有相关证据证明,无再调查的必要;申请的目的旨在拖延诉讼时间的。对于拒绝申请的情形应尽量明确列举,减少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空间,保障辩护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权的有效运行。
(五)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保障机制
1. 保障律师的会见权
辩护律师与嫌疑人、被告人自由会见与交流是律师知悉案件事实并获取证据的重要制度保障。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基本解决了辩护律师会见难的问题,一般案件律师仅凭三证即可会见,并且会见时不被监听。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过侦查机关许可。辩护律师普遍反映职务犯罪案件的会见依然面临一定的障碍,因此为了保障职务犯罪案件律师的会见权,笔者认为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应作限缩解释,即嫌疑人必须同时具备涉嫌犯罪数额在50万元以上和犯罪情节恶劣两大条件,同时50万犯罪数额的确定应以有证据证明且已经查证属实的犯罪数额为准,不得以初步调查的犯罪数额来考量,另外此类案件人民检察院应保证在侦查终结前许可辩护律师见到犯罪嫌疑人。
2. 确保律师阅卷的全面性
新《刑诉法》要求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较原刑诉法而言,新法扩大了辩护人的阅卷范围,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不再限于“诉讼性文书及技术性鉴定材料”,而是将各种由侦查机关装卷成册的证据材料也纳入其中。因此,根据以上规定,如果律师通过阅卷掌握案情以及了解所有的证据,包括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那“将会减少律师调查取证的需求和冲动,进而也会缓解调查取证难的主观感受和实际困难。”[12]290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大陆法系国家,律师在审前则很少调查取证,而是通过对案卷的查阅来达到与调查取证相同的目的。我国的侦查模式与英美法系国家迥异,而更接近于大陆法系国家,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受到诸多限制并无切实的保障,为了实现控辩双方获取证据信息的对等,实现控辩平等对抗,达到庭审实质化的效果,办案机关应确保律师阅卷的全面性,尤其不得隐藏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信息。
3. 申请证人出庭的权利保障
控辩双方有异议的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是保障案件事实真相得以查明的重要方式,亦是辩方质证权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鉴于新《刑诉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率并无根本改观的现状,笔者认为应改变证人出庭的条件,即对于控辩双方有异议的并且对案件的处理有重大影响的证人均应出庭。考虑到控辩双方掌握的证据数量的不对等性,司法实践中存在更多的是辩方对控方的证人证言提出异议。因此,应更多考虑对辩方申请证人出庭权利的保障,辩方申请证人出庭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对控方提供的证人证言有异议,另一种是由于己方的证人证言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有关键作用,要求法院通知辩方证人出庭。笔者认为对于控方提供的证人证言,辩护律师如果有异议,固然应通知证人出庭接受质证,但更重要的是对于辩方提供的新证人,如果对案件的处理有重大影响的,更应通知其出庭。唯此,才能有效保障被追诉者辩护权,最终保障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
五、结语
辩护律师充分获取证据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并进行有效辩护的前提。从新《刑诉法》实施近两年的情况来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不管是自行调查取证还是申请调查取证抑或申请调取证据,均面临难以实施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法治环境以及刑事诉讼模式下,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面临诸多障碍,因此应将目光转向通过其他制度设计保障辩护律师充分获取办案机关收集的各种证据,以最大限度实现辩护的实质性效果。
[1] 万毅.曲意释法现象批判——以辩护制度为中心的分析[J].政法论坛,2013(2).
[2] 李雪峰.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相关问题探讨[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2).
[3] James J Tomkovicz.The Right to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M].Greenwood Press,2002.
[4] [美]米尔吉安 R 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M].吴宏耀,魏晓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5] 左卫民,周长军.刑事诉讼的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 [德]克劳斯.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 王天民.实质真实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8] 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9] 张泽涛.我国刑诉法应增设证据保全制度[J].法学研究,2012(3).
[10] 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M].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
[11] 吴建雄.检察官客观义务的错案预防价值[J].法学评论,2011(1).
[12] 顾永忠等著.刑事辩护——国际标准与中国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杨 强】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of Defenders’ Obtainment of Evidence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It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WANG Xiao-hong
(SchoolofCriminalJustice,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Beijing,100088)
To guarantee the substantial effects of lawyers’ defense, it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protect the defenders’ right of obtaining the evidence in favor of the prosecuted and fully knowing evidence for the prosecution in the criminal system of defense. Considering the structural obstacles the defenders has been confronting in investigation and obtaining evidence by themselves, solution lies in protecting the defenders’ right of knowing and obtaining the evidence indirectly, the right of applying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obtaining the evidence, the right of meeting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rosecuted, the right of going over the records comprehensively, meeting requirements of the witness appearing in the court conforming to the legal standards, adding to the right of applying for preserving evidence, and establishing procedural sanction in the case of depriving the defenders of obtaining the evidence. Such solution above-mentioned can effectively compensate deficiency of the defenders’ ability of investigating and obtaining the evidence.
Defenders; Investigating and Obtaining Evidence; Apply for Investigating and Obtaining Evidence; Apply for Investigating and Taking Evidence; Preserving the Evidence
2015-05-11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2014BSCX25)
王晓红(1978-),女,山西临猗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
D915.3
A
1008-8008(2015)04-006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