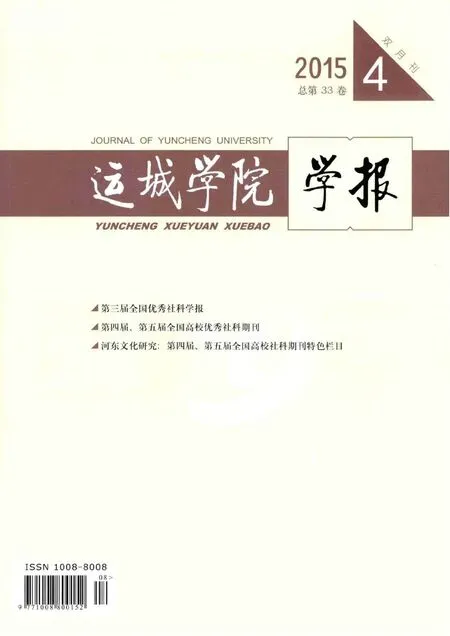隋代河东史家王劭的文学成就和意义
李德辉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湘潭411201)
古史上颇有一些杰出人士,虽然著书多种,但在当今的文学史研究中并不被视为文学家,然而却又对当时文学实实在在地做出了重要贡献。生活于周隋间的山西籍史学家王劭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此人历来被视为史家,但在文学方面亦卓有建树。只因著述散佚不传,成就不为今人所知。细心爬梳史料可知,此人籍贯山西晋阳,系出太原王氏,开皇、大业中长期在秘书省担任著作郎,在隋代著作局任职近二十年,专典国史,深受帝王信任,留有多种著述。只因史学观念多与时流不合,便长期遭受贬抑,《隋书》《北史》本传将其人其书丑化。由此之故,他留给后人的多是负面印象。由于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以致其书虽然品格不凡,但均不传,只能在唐宋史传、书目中觅得一二踪迹。其中《俗语难字》《隋开皇二十年书目》《读书记》三书不在文学范围,编年体史书《齐志》、纪传体断代史《齐书纪传》及《隋书》(未完稿)、杂史《尔朱氏家传》四书则程度不同地带有文学性,志怪小说《舍利感应记》《皇隋灵感志》二书更是文学之书。这些书中有诸多不合时流的地方,包含有丰富的文学性:
其一,鲜明突出的实录精神。王劭编著史书,不像当时文士,把文学性放在首位,“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而是严守史学本位,追求记载的真实性,有鲜明的实录精神。以《史通》所载为例,这种精神,具体表现在史书的体例和“书法”方面,不虚美,不隐恶,如实记载,态度客观公正,可以取信于人。《史通》卷五《载文》云:先秦史册,文字可以察兴亡,其用颇大,“至于近代则不然,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之英伟则臣皆二八。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眦而称感致百灵。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惟王劭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1]91-92卷七《直书》:“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欤。”《曲笔》:“如王劭之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寻此论之作,盖由君懋书法不隐,取咎当时。”[1]144卷一八《杂说下》:“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记也,喜论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讦以为直,吾无取焉。”[1]388以上引文,都谈到王劭著书不畏权贵、直书无隐的特点,最后一则还谈到王劭直书“丝毫必录,琐细无遗”,“喜论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的不足,这又从反面彰显了其史书直书的独特性:为了追求真实,甚至连君王“帷薄不修,言貌鄙事”也写进去,有伤大雅。王劭本人也正是因为这些地方而招致时人诋毁。《史通》就此析曰:“近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而世人议者皆雷同,誉裴而共诋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且几原务饰虚辞,君懋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1]卷六《叙事》,120-121指出南朝学者修史,以文学为本、辞采为贵,不在乎事实之真伪、记载之可信,唯有王劭以史学为本、文学为用,保持周秦汉魏风格。由于史观不同,故遭诋毁。而从文学角度看,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也正是秦汉以来史传文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东汉学者王充就特别痛恨虚妄,提倡真美,反对有文无实的华伪之文,自觉地将真实作为一种美感来追求[3]。王劭受此观点影响,也是如此。所著《齐志》、《隋书》语言质朴,文字明白,所记之事经得起核实。作为一种带有文性的史传文学,能够反映客观生活的真实,表明他是有意识地将真实作为一种美来追求。刘知几云:“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1]119“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1]122真实既是史学著作的灵魂,也是纪实文学的基石,因此叙事真实,记载可信也可以视为其史书叙事的文学成就。
其二,与众不同的文体文风。或许是出于天性,或者是因为文学观念不同,王劭著书作文,不像当时士人那样“尤工复语”、“雅好丽词”,而是多采俗语,多用散体,自由行文,多用生活化的通俗语言,甚至采用北朝地方土话入史,有北朝民间风格,叙事方式、文献解读和历史评价都有趋俗好奇特征,可以视为隋代通俗史学的代表。《隋书》本传说他“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湮没无闻。初撰《齐志》,为编年体二十卷。复为《齐书纪传》一百卷,及《平贼记》三卷,或文词鄙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识所嗤鄙”[2]1609又谓其所撰《皇隋灵感志》三十卷亦多采民间歌谣,广引佛经图谶,也有较强的趋俗倾向。这些唐初史臣给出的否定性评价,正是王劭史书用语上的一大特色和成就。《史通》卷六《言语》就其这一特点继续申述曰:“唯王(劭)、宋(孝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1]109-110同卷《叙事》:“案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受纥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彦銮撰以新史,重规删其旧录,乃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王劭《齐志》载谣云:‘貛貛头团圞,河中狗子破尔菀’也。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后。”[1]130-131卷一八《杂说下》:“案王劭《齐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汉儿。’夫以献武音词,未变胡俗。王、宋所载,其鄙甚多……牛弘、王劭,并掌策书。其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其载周言也,则文雅若此,何哉?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1]373-375指出对语俪辞经过文人加工,脱离生活实际。王劭掌国史,载齐国方言,虽然土俗,但有生活气息,能反映生活实况,亦是一得。卷一七《杂说中》:“或问曰: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为是乎?为非乎?对曰:古往今来,名目各异。区分壤隔,称谓不同……多必寻其本源,莫详所出。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录,其为弘益弥多矣,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另一处又提到王劭《隋书》有意效仿《尚书》,措辞宪章虞夏,而所述则接近《孔子家语》和《世说新语》,有六朝小说家风。《史通通释》就此指出,这是因为王劭著书有尚古好奇的倾向,又往往以俗为美,对于以骈俪为特征的雅文学颇为不以为然。而刘知几论史亦“有质癖”,“黜饰崇真,偏于里音,不惜纸费”,见唯王劭能存质语,故深许之。可见在史书中载录民间口语、俗语,乃是王劭史书载言的一大特色。这么做能增强史传的生动性、记事的真实度,读之情态毕现,较之文雅规范的书面语别具一种美感。而从写人的角度看,这些东西的加入,也有助于凸显故事主人公的多面性,增强传记的趣味性。尤其是对于多民族聚居、言语混杂的北朝社会,这样做更能反映民族大融合的社会面貌。用刘知几的话说,就是有助于“寻其本源”,可令学者“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所以王劭这么做,反而是基于当时社会现实而做出的合理选择。而且,按照刘知几的理解,多载口语和史书存实还有因果关系,多录委巷之言、不经之语,能够反映南北东西不同地域世态人情的不同,有益于考见南北分裂所造成的地域分隔,为益甚多。所以无论从史学还是文学角度看,王劭此举都应大力肯定。其著书取材也不是仅依官方档案簿录,而是博采民间杂说私记、佛书道典,多语怪力乱神。这种独异时流的观念、风格和做法使得此书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众作,看上去不太像正史。虽然不够严肃,却有异端色彩。行文上以散句为主又不失文学语言的美感,这样就和当时主流文风接近起来。不仅将正史、编年史文学化,还撰有更具文性、本在文学范围的《舍利感应记》、《皇隋灵感志》之类“偏记杂说、小卷短书”,在著述部类上丰富了隋代文学品类。
其三,独特的史书编纂体例。表现之一是私撰正史而采用类书编纂之法,编录材料,竟然以类相从,各为题目。《史通》卷一《六家·尚书家》:“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1]4“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即是说的王劭《隋书》著书体例。隋代秘书省特别重视文学文献史料建设,在类书的编纂上投入很大,长年不断,共计主编过十多种类书,成就斐然。王劭身为其中要员,经常参与其事,熟知类书的编纂体例。修史之时,出于习惯,沿用其法,亦在情理之中。表现之二是身为史臣,所撰史书往往杂采他书,自我作注,自我作古,做法类似六朝注释学新体裁——合本子注。《史通》卷五《补注》就此论曰:“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注列行中,如子从母。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1]95指出作者官居史职而著为杂录,又复自我加注,注书不释文义,重在博采史料,补充正文叙事之疏漏。只因无删述之才,导致材料贪多,事止罗列,编次失当。尽管如此,从文学角度说,这么做却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主要依靠编次类书之法来辑集史料,这样做就保存了更多的材料。因为多照录原文,未加删改,其所辑集的材料也更为接近原貌,更可凭信。在得书不易、赋诗作文依赖类书文集的隋唐,这样做对于创作尤有促进作用,可以视为他对文学史料学所做出的贡献,不能不提。
其四,善于叙事,有《左传》之风。王劭《齐志》从语言文字到编排体例都有《左传》之风,妙于形容,多有情节,《史通》据此将其列入“左传家”,并就其叙事文学成就多有揭示。卷八《摸拟》:“夫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睠言……至王劭《齐志》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占者曰:‘其为幽州乎?’秋七月,拜为幽州刺史。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1]161“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夫不言奋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1]161卷一七《杂说中·北齐诸史》:“王劭国史,至于论战争,述纷扰,贾其余勇,弥见所长。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禅,二王杀杨、燕以废乾明,虽《左氏》载季氏逐昭公,秦伯纳重耳,栾盈起于曲沃,楚灵败于乾溪,殆可连类也。又叙高祖破宇文于邙山,周武自晋阳而平邺,虽《左氏》书城濮之役、鄢陵之战,齐败于鞌,吴师入郢亦不是过也。”浦起龙释曰:“此所论载四事,非止述事,乃论文也。”[1]361-362所谓“论文”主要就是论《齐志》在记载事件、描写人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从《史通》所述及保存在《法苑珠林》和宋明类书中的残文来看,王劭《齐志》长于通过语言、外貌、动作、神态描写等写作手段来塑造人物,记述事件,借此来表达自己的史观,这样就能反映社会生活,展现人物风貌,兼具史的品格和文的色彩。特别长于摹写战争,记述内乱,读之情态毕现,在这方面尤有心得,特色鲜明。《左传》本是叙事文学的典范,王劭刻意模仿,辅之以个人创造,因此形成了其《齐志》善记战争、长于摹写的特色。而且使用散体,“广以异闻”,中多奇事,其文学性却因此又添一层。
综上,王劭史书在叙事写人、体例材料、语言文风方面都是带有文学性的,将其所撰《齐志》《隋书》视为隋代史传文学著作,将其人视为文学家,并不为过。尽管记事乖滥踳驳,但在取材用语都与众不同,因此而取窘流俗,见嗤朋党。其时“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2]1544受此风尚影响,著作局中亦复如是。“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1]卷9《核才》,179一代文风如此,想要独立不迁,又何其难也。由此看来,王劭史书的文学意义之一在于标志了隋代史传文学的另类风格、另一侧面。以往论史传文学,止于《史记》、《汉书》,很少到魏晋以下,更不曾把王劭作为善于叙事的史传文学典范、风格独特的通俗史家来加以标举,本文的研究则表明,史传文学亦是隋代有成就的文学门类之一,王劭即是这种文学的重要传人,且是其中比较另类的一家。他的存在表明,史书编撰中的《左传》家风代有传人,只因史料堙沉,不为人知。史传文学研究本来就是隋代文学研究的缺项,王劭则是冷门中的冷门,即使作为史家,亦只有少数几部中国史学史和中国通史略加提及,写法就是一笔带过,不曾顾及其和隋代文学的关系。作为文学家的王劭更是无人论及,原因主要就在于他的文学成就是寓史于文,以史存文,即通过史学撰述和子书小说来展现其学术著述的文学性,其本位还是史学著作或者子书杂著。不像一般文士那样创作诗文辞赋,有名篇佳作流传,有文集传世。其文学并不以优美抒情为特征,而以叙事为职守,不在纯文学的范围,所以不可能进入以纯文学为研究对象和材料取舍范围的现当代人编撰的文学史。本文人弃我取,从史传文学的角度和广义的文学角度来考论他的文学成就,这就从视域上拓展了隋代文学研究的探索面,能够使人们看到更多的东西。再则从史传文学角度来论述王劭史书的文学性,也是对于隋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局部的深入。须知“史者当时之文”,隋代毕竟时属中古,一般的史书,总是带有程度不同的文学性。我们讨论隋代文学,还是要从当时实际出发去探求真相。今人论隋代文学,往往只提及薛道衡、卢思道等人之诗,很少提及其他文人和其他文体。本文的研究则表明,隋代文学创作实况要比当今文学史描述的复杂得多,其种类之繁复、内涵之丰富、创造性之强,都要远超今人预想,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其中隋代史家对史传文学和散文创作的贡献就是很值一提的,理应加以关注投入。而且这么做也要更加贴近隋代文学的实际。今人研究古代文学,往往从纯文学观念出发,考察集部范围的文学家,一般不研究史学家。研究古代文学,总是习惯于从文体出发,讨论诗文、戏曲、小说,而不是从古人的大文学观念出发,本着史中有文、以史存文的认识去对待古代文学。许多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文学现象,只因古今文学观念不同,常常就与我们失之交臂,毕竟可惜,需要更新观念,转换手法,重新考量。本文的研究意义,或者亦在于此。
[1]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魏徵等.隋书(卷 69)[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谌兆麟.中国古代文论概要[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