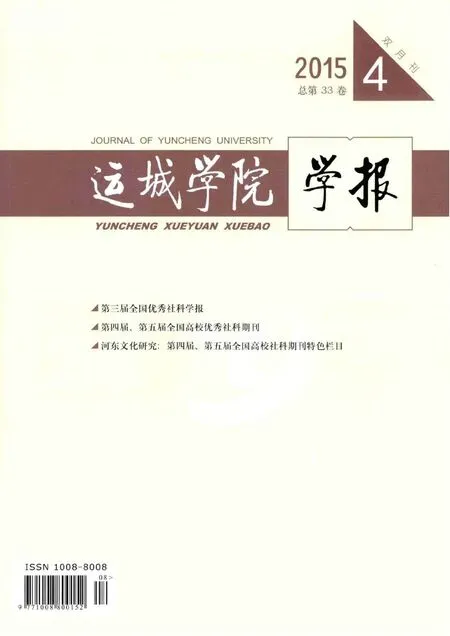独化思想视阈下的王维山水田园诗
张 佳 玉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独化思想视阈下的王维山水田园诗
张 佳 玉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郭象的独化思想已经深入王维的骨髓中,进而影响到其山水田园诗写作。王维以山水为其思想载体,以“独”为基本生发点,道法自然任山水万物随运而化,回归自我本性,进入独我、任我的自由境界。“独”是其创作思想的内核,亦是诗人的精神追求,在由“独”到“独”的过程中,诗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自得而逍遥,主体精神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独化;王维;山水田园诗;自得
王维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现存诗歌374首,其中山水田园诗占的比重最大。现在对王维山水田园诗歌的研究,多集中于“诗中有画”特点、空灵意境、佛教思想对其诗歌及思想的影响等方面,而对王维与道家思想的研究,则相对冷清。二十世纪以来,一些学者注意到了道家思想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且取得了一定成,但多以道家“坐忘”、“自然”、“虚静”等思想分析其山水田园诗创作。这些思想虽对王维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却并非其根本,因而在论及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时仍觉有未达之感。实际上,“独化”思想才是王维诗歌创作的主导思想,他以“独”为内核,道法自然,肯定山水自性,以无心顺应万物,任运而化,回归自我本性,真正实现个体精神的自得逍遥。在由“独”到“独”变化中,诗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主体精神实现了绝对自由。
一、独,万物自生
独化是郭象哲学的核心范畴。汤一介先生曾指出:“如果说‘有’是郭象哲学体系中最普遍的概念,那么‘独化’则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上述概念最终都是为了证成‘独化’这个范畴的。所谓‘独化’,从事物存在方面说,是说任何事物都是独立自足的生生化化,而且此独立自足的生生化化是绝对的,无条件的。”[1]113“独”指一切万事万物的个体自存、自足、自立、自由、自生、自己的存在状态。“化”就是形容这种活动的变化。“独化”即指万物皆独立自然生成,不需要任何条件,也无需遵循任何规律。它的生成既不依赖他物,也不因自我意愿而生,“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大宗师注》)[2]251这种无条件的自生现象方是天地之正。
万物独立自生,皆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在不知所以生、也不知所以得的状态下,神秘且突然地生成。在其生成背后,郭象并不认为存在有意志的上帝,或者本体,也就是老庄所说的“无”或“道”。他说:“世或谓罔两待景(影),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2]111郭象否不仅认了形体由造物者产生的观念,也否定了“有生于无”的观点。他指出如果造物者无形,那就是空无,空无如何能产生万有?如果有形,它便只是一个特殊的东西,又怎能产生多种形状的万物?而且,既然已经是“无”,便不可能对事物产生任何作用和影响。此外,“无”不仅不能生“有”,“有”无论经历怎样的发展变化,也不能彻底消释为“无”,“夫有不得变而为无,故一受形,则化尽无期也。”(《田子方》注)[2]708因而,万物的背后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主宰者和支配者,事物的发展和推行都是“自行”的结果。
万物皆神秘而独立生成,无需凭借外面的资助,只需各自“自足其性”即可。如《辛夷坞》中的芙蓉花,“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3]425你无法详细考证寂寂空山之中的这朵芙蓉花从何而来,在诗人到来之前似乎已经存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凭依着本性自由绽放、自由凋零。而这一生命历程始终独立自足的生生化化,即使诗人走后也依旧会长久存在,完全不需依赖外界力量。它开花,不因人觉其美;凋零,不为无人欣赏。在这一极其幽静的自然环境中,它始终在尽力实现着自己的本然之性,“自尽为极”罢了。诗人并没有干预这一自然演化进程,而是肯定芙蓉的自性,让它们无碍自发的显现。
二、性,自生之理
万物独立自生后不断发展变化,而“性”是其存在发展的必然依据,为万物固有。它不可逃,也不可加,始终贯穿于万物存在的始终,中途没有改易的可能。“物各有其性,性各有其极”,(《逍遥游》注)[2]11即各自有各自的自性,而每个独立存在的事物的自性也各自有各自的原则,万物皆依自性自行其是、不断发展,如辛夷坞的芙蓉花、欹湖的青山白云、鹿柴的青苔等等,共同构成了这个形形色色、姿态万千的现象世界,人当然也是这个大千世界的一部分。以观物的视域来看依据自性独立自生的万物,它们无疑具有多样的形态,但如果将多样的形态理解为彼此差异,则容易陷入物我之辨、是非之争中。若执着于此,便脱离了自身本然之性,也不利于本性充分而完整地实现。因为,性皆在自身,是事物自身最根本的存在,犹如虚空,无边无际,无法逾越,“万法尽是自性。是一切人及非人,恶之与善,恶法善法,尽皆不舍,不可染著,自如虚空,名之为大。”[3]810“不舍”指万物皆由性所生,不能脱离自性。所谓的大小、好坏、是非、美丑等差异本来是没有的,皆是脱离自身本性跂尚外物的结果。因此,万物之间从来不存在比较的意义,无需执着外物或外在环境,只要满足自身本性,“于心不舍,不执著于万法,不为万法所垢”,[3]810便可见性成圣、成佛。一旦自性满足,泰山和秋毫又有什么区别,甚至天地万物和人也无所谓内外彼此。
事物发展始终以自性为本,只有“自足其性”,方能“乘化用常,于百法而无得,周万物而不殆”,[3]807真正进入“离寂不动”的大道之域,即“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但然寂静”。[3]808“无静”指人的见闻知觉;“无动”指人的本性不动。于大千世界中,寂然独生、独在,不执著于万相,不为万法所染,始终保持本心不动。本心即本性,指万物本身固有之自性,或曰真如、或曰道心。本心不动就是去除人为主观思虑、意图,顺应事物必然之性,“无心而应,其应自来,则无往而不可也。”(《人间世注》)[2]137“无心而应”指于一切事物上“念念不住”,即不执著,不著于一切,方能常保自性之清净,因此可以在一切处中来往自由,“随所住处常安乐”,实现诗意地栖居,自得而逍遥。如《酬张少府》[3]476。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王维少年天才,能诗会画又精通音律,二十一岁即中进士,任大乐丞,后因受伶人舞黄狮牵连被贬,直到开元二十三年,受到宰相张九龄的提拔才重新回到长安。然而,第二年即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即被罢相,这也代表着玄宗开明政治的终结。这对踌躇满志,拥有满腔抱负的王维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一方面一直坚持的政治理想破灭,另一方面以李林甫为主的奸党大量不断排除异己、打击忠贞正直之士,这都使得王维对朝政十分失望,内心也极为痛苦,从此开始半官半隐的生活,以期获得精神的解脱。这首诗即是反映他的这种精神状态。
尘世浮沉数十载,几多酸楚与感慨,人至晚年方悟得一切的痛苦皆源于自己的跂尚之“心”,陷入俗世是非、穷通中不可自拔,从而伤害了自己的性命之全。一切外在的现实,无论自我的政治理想,还是残酷的政治斗争,皆是放任人的主观意欲妄作妄为的结果。假若人人都能回归自我本性,自足其性,方知名利、穷通皆是空,又何来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想要消除这一切,唯有返归“旧林”。诗人将自己化入空山之中,迎着松林吹来的清风解带敞怀,在山间明月的伴照下独坐弹琴,自我身心极大地解放,自性得到充分舒展。明白自己曾经在意的事物以及汲汲追求的穷通之道,皆是脱离自我本性的主观妄为。万物皆依据自性自然存在,无需动心体认,正如山间青松、明月一样。它们自由、自足、自立的存于此间,生生化化,不会因我,亦不会因你而改变生存轨迹。
三、独,复性于内
自性皆依自性自然而然生成,“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既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齐物论》注)[2]112万物的变化发展皆以实现自性为本,只需“各反所宗于体中”,无需外求。而外在所谓的“分”与“别”(有封)之物,于我而言皆是不同现象的外在形态,是主观意志的人为规定,脱离了自我本性。关注外在,同时容易使人心受束缚,从而形成思维定势,即“成心”,这也是人们容易惑乱迷失的根源。与反对“攖人心”相联系,庄子提出“解心释神”主张,而郭象提出“独化”思想,皆旨在引导万物各复其根。一旦万物皆回归自我本性,各为其极,外在各种所谓的差异、竞争和纷扰就自然消失了,万物在天地宇宙中皆可“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3]827于天地间内外不住,来去自由,通达无碍,是为“独”。“独”强调的是以自我本性为主体实现的精神领域的逍遥,庄子将能做到“独”的人,视为“至贵”,极为赞赏个体精神层面的自由。
王维在把握和应付世界的自然过程中,将“独”作为内在的视域融入自己的“在世过程”(日用常行或者生活实践),从而在日用常行中实现了主体精神的回归与超越,获得了内心的自得逍遥。如《竹里馆》[3]424: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首诗作于诗人晚年隐居辋川时期,描写隐居山林的情趣,表现了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意境清幽。
全诗重在一个“独”字,既点明诗人是独自一人,又暗示诗人此时的精神境界也是“独”。开头两句写诗人独坐于清幽的竹林里,悠然弹着古琴,琴声悠扬,和着琴声,不禁发出长长的啸声,一切都是那么惬意。“独”点明了诗人和周围的幽篁皆是独立自生、自由、自足地存在这一方天地中。二者只是静静共存,各自舒展着自己的本性,彼此自为,不存在并非创生和被生的关系,也不是依赖和被依赖的联系。后两句写深林之中没有人与我做伴,只有明月照耀着大地。虽没有人做伴,但也不会感到孤单。因为,在这里我可以随意而为,肆意地实现自我,不受束缚,兴之所至就坐在月下弹琴长啸,此时如何弹,如何唱都已不重要,自己尽兴即可,无需考虑任何外界因素,没有逢迎,亦没有委曲求全,只为我自己,我的本性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外界的幽篁也好,明月也罢,此时于我而言皆是空,它们无法融入我的本性中,自然也不会对我的本性产生任何影响。因而,再没有可以阻碍“我”的事物,“我”的主体精神可以“出入六合,游乎九州”,于整个天地间自由翱翔,“独与天地之精神相往来”。“天地之精神”指天地本源,即自性,“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则指诗人个体精神进入郭象所言“独”的状态,内外不住,来去自由。因而,世间一切事物于诗人而言,都成为可有可无的存在。既然毫不相关,那么任何地方、任何事物都没有差别,我都“独”存其间,从此任何地方即是幽篁。
又如《山居秋暝》[3]451: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此诗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山村的美丽风景,表现了诗人对山水田园以及隐居生活的喜爱心情,寄托着自身的高洁情怀和对隐居生活的追求。诗人将空山秋雨、松间明月、清泉声、浣女嬉笑声等融合在一起,动静结合,自然和谐。
一场秋雨过后,山里多了些凉意,傍晚时分,几缕月光从树叶间洒落,林间清泉淙淙流过,一切都是那么清幽宁静,而且自然。这些都是自然运化的结果,它们依据自己的本性自然地存在于此,无需外物夹杂渗入。处于其间,诗人的心也变得越来越平和恬静,因而能够注意到竹林喧声,以及莲叶摇动,接着才发现归来的浣女和莲舟。自然独化的空山、无忧无虑的山民,都让诗人无比轻松惬意,心中的烦恼、忧愁逐渐消散,同时体悟到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快乐,正是因为它们皆以自性为本,满足于自身本性,不假外求、无所待,“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既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齐物论》注)[2]112既然都不外求,“反所宗于体中”,各种无谓的竞争和纷扰也就自然消失了。“反所宗于体中”即是回归自我本性,进入“独”的状态,此时外界自然万物于我本性而言都属于“无待”的范畴,没有区别,属于不相关的存在,因此王孙可以“随意春芳歇”。“王孙”这里当然指诗人自己,“随意歇”则是说假如保持自性,不假外求,随处即是风景,“随所住处常安乐”,于一切处中皆可自得,无需苛求外在环境,正如并非只有隐于深山之人才可称为隐士,保持自性之人,即使处于闹市中,又何尝不是隐士!
当不能在现实世界中获得自由时,只能向内寻求,本性的保存、物我的观照相忘都使得我们的心灵和精神获得自由和解放。辛夷坞的芙蓉花、欹湖的青山白云,鹿柴的青苔等等,使诗人明白世间一切事物形式方面虽纷繁多样,于本质而言却都是从“独”而来,又各自独立尘世间,自生自化,人亦是如此。本然之性皆存于自身之中,不需外求,如此便可无所待,那么各种所谓的竞争、烦恼、纷扰也就无法存滞于心间。只要心间不滞,无念无住,世间一切事物将皆如一,即于己而言皆是无差别的存在,心灵方能超脱外在形象的桎梏,回到混沌初立的“独”的状态,真正游心于天地之间,独与天地之精神相往来,超然自得。如此随处将都是美景,皆可从中获得内心的自得,实现诗意的栖居,正如诗人所言的“随意春芳歇”。正因诗人能够做到“独”,保持自己的本然之性,才能不受外在事物的影响,从任意事物中皆可发现美、欣赏美,获得心灵的、精神的愉悦与自得。
[1] 杨立华.郭象《庄子注》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责任编辑 马重阳】
2015-01-28
张佳玉(1990-),女,河南新乡人,广西民族大学2013级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先秦两汉文学。
I207
A
1008-8008(2015)04-0012-03
——从体、相、用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