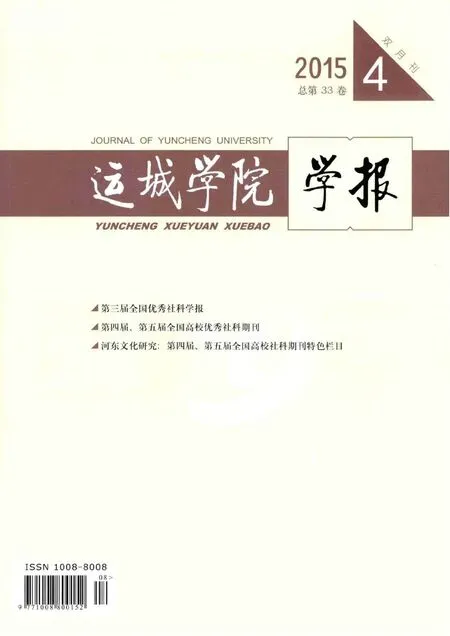王通与“三教可一”论
李 海 燕
(北方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144)
王通与“三教可一”论
李 海 燕
(北方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144)
隋末大儒王通于大业年间在河汾仿孔子续《六经》,聚徒授学,其弟子门人多为当时的一些豪杰之士和隋唐名臣,其学说被称为“河汾道统”。王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儒家学者的身份提出了“三教可一”的命题,对于中国的政治、哲学、宗教等思想文化形态以及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融合精神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通;三教可一;儒家思想
王通(584-617),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大儒,教育家。卒后弟子门人谥曰“文中子”。
王通二十岁时,曾西游长安,向隋文帝献上《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帝大悦。”(《中说·关朗篇》)然因公卿阻拦,“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同上)隋炀帝大业年间,王通隐居龙门白牛溪,著书授徒,朝廷数征而不至。*《文中子世家》:大业十年,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并不至。据杜淹《文中子世家》:“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这些门人包括一些豪杰之士及隋唐名臣,“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和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颖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另外,还有杜如晦、王珪等。据《文中子世家》:“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薛收《文中子碣铭》载:“渊源所渐,著录逾于三千,堂奥所容,达者几乎七十。”“盛德大业,至矣哉。道风扇而方远,元猷陟而愈密,可以比姑射于尼岫,拟河汾于洙泗矣。”(《全唐文》卷一三三)杜淹曾云:“隋季文中子之教兴河汾,雍雍如也。”(《文中子世家》)著书讲学的情形,在隋季可谓盛况矣。王绩《游北山赋》及注亦云:“山似尼丘,泉疑洙泗”,“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溪。”此种讲学盛况及其文化传承后世称之为“河汾道统”或“河汾之学”。
以“河汾道统”和“河汾之学”体现出的王通的“王道”思想、“仁政”主张、“天人”观念、“穷理尽性”理论等等,都是王通的重要政治、哲学思想。*参见尹协理、魏明《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然而笔者以为,王通思想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是其以儒家学者身份提出的儒释道可以相容的主张:“子读《洪范谠议》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与“三教可一”“三教同源”相似的理论早已出现,如东汉末的牟子,在《牟子理惑》中提出了“人道法五常(仁、义、礼、智、信)”以五常作为佛道修行的方式和方法。三国孙吴僧人康僧会(?—280)亦注重佛儒的融合,以儒家的仁义之道为佛教修养的方法。东晋孙绰《喻道论》指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南齐的顾欢,倡导儒、佛、道一致。并认为佛教可用来教化人民。王褒、宗炳、释慧灵、张融、北周道安等大批隐士或僧人都认为儒、释、道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但这些人多是佛道信徒或学者。《洪范谠议》即王通祖父安康献公所撰之《皇极谠议》。可见王通“三教可一”思想的提出,是继承发扬其祖之说,但其何以从祖父的著述中得出“三教可一”的主张,已不得而知。(《中说·问易篇》)这就是所谓的“三教可一”论。
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理论,无疑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隋朝建立后,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必须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以精神的统一保障政治的一统。然而长期以来,儒释道却在鼎立的状态下相互斗争,无法真正满足统一的封建国家对思想文化整体性的要求。故而王通认为,三教之间相互攻讦,就像政出多门一样,是非常不利于政治统治的。“程元问:‘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中说·问易篇》)因此可以说,正是为了改变这种“政恶多门”,三教相互斗争的状况,王通才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
事实上,作为一个以当世孔子自居的儒家学者,王通认为佛、道二教虽有其长,但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缺陷。《中说·周公篇》载:“或问佛子。曰:‘圣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可见在王通看来,佛教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同时他对道教也多有批评,《中说·礼乐篇》载:“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在王通看来,长生之说纯属虚妄之谈,是世人贪得无厌的表现,若无仁义、孝悌等儒家伦理道德的修立,所谓的长生是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的。可见王通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佛、道二教是持批判态度的。
然而与许多儒家学者不同的是,王通决不主张对于释、老之学采取暴力手段强硬废除,《中说·问易篇》载:“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太平真君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年号(公元440—451年),建德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年号(公元572—578年)。上述两位皇帝都曾用暴力手段灭佛,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已有众多的僧众与信徒。因此若用暴力强硬消灭之,是很困难的,故而王通认为暴力废佛之举,实是“推波助澜,纵风止燎”的愚蠢行为。既然佛教在当时已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取其长而用之了。正是吸取了历史上的教训,结合儒释道当时的发展状况,王通才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认为三教应相互接近,相互吸收,取长补短。而作为以儒家正统自居的学者,他当然更希望通过吸收佛、道两家之长,进一步充实儒家的内容,从而提高儒家的地位。这就把儒学变成了一个开放的体系,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种意义上的“三教可一”便既不会像“三教并行”那样使人们无所适从;又不会遭遇强行消灭而引起的“纵风止燎”之负面效应,既利于政治统治,又能够“使民不倦”。
不仅如此,王通还提出了“共言九流”、“共叙九畴”的观点,《中说·周公篇》载:“史谈(司马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在王通看来,不仅三教各有利弊,不可偏废,其它的思想流派也同样如此。只要善于通变,善取其长,则天下没有什么弊漏之“法”,从这种意义上说,“共言九流”,也就是“九流可一”。在此基础上,统治者便可以“九畴”之法治理国家。可见王通以极其开放的心态,对于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存在的思想和治国方略,都采取辩证的态度,希望能够兼采众长,扬长避短。
应该说,王通的“三教可一”理论,既是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的带有创新性的政治、哲学命题,又是对前代思想的总结。我们纵观历史,就会发现,王通继承发扬其祖之说提出的“三教可一”的理论,乃是政治思想史发展到隋唐之必然产物。自东汉明帝佛教思想传入中国后,儒、释、道三家并存,从此便开始了融合与斗争的过程。作为中国本土之外的异教,佛教的诸多教义,可以说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背道而驰,因而想在中国扎根,必须依托于中国固有的儒道文化,对自己进行改造以宣传其教义,因而从其传入中国,就开始了与中国文化融合的过程。魏晋以来,玄学大兴,佛教思想也日渐繁荣,使得儒学与汉代“独尊”的地位相比,出现了式微的状况,甚至被认为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三教斗争与三教融合一直在继续。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三教各自以己为本、他教为末来会通三教。比如葛洪《抱朴子·朔本》谓:“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是站在“道”的角度以“道”为本进行的融合;《高僧传·慧严传》载:“范泰、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是以佛教为本的融合思想。
而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的需要而进行的提倡与实践,对于三教的融合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汉桓帝曾将黄老、浮屠、孔子并祀;降至魏晋南北朝,许多帝王为了扩大势力,巩固地位,也都采取并重三教的政策,如曾经四次舍身佛寺的梁武帝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梁书·武帝纪》载其不仅着《周易讲疏》《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儒学著作,而且写《涅磐》《大品》《净名》等佛教典籍,还有《老子讲疏》一类道家著作。参见《梁书·武帝纪》。即使是上文提到的北周武帝在下诏废除二教之前,仍不免要召集群臣商讨三教优劣,如此又使三教在辩论中得到了交流,加快了融合的步伐。
这种三教融合的趋势使很多人在思想和行为上往往集三教于一身。如张融在其《遗令》中嘱托自己入殓时要左手执《孝经》《庄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南齐书·张融传》)道士陶宏景遗令其尸要冠巾法服,左肘录铃,右肘药铃,佩符络左腋下,绕腰穿环结于前,钗符于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手足,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燃灯,旦常香火。(《南史·陶宏景传》)这种汇集三教的丧葬方式,竟让时人纷纷仿效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虽然历史上在三教并存的情况下,曾发生过灭佛废道等斗争,甚至是流血事件,但其融合的趋势也是显而易见的。王通不失时机地提出“三教可一”的命题,足可见其对时代精神把握之精当。哲学在本质上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从这一角度讲,王通当不愧为哲学家之称号,故而他能有这样的认识:“诗书盛而秦世灭,非孔子之罪也。玄虚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中说·天地篇》)而此种包容精神,正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盖此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当是呼之欲出的。因而笔者以为,王通的这种关于“三教可一”的主张,乃是顺应时代思潮的发展而提出的,是一种建设性的理论并为以后的儒学思想发展开辟了道路。“王通的出现及其‘三教可一’主张的提出,似乎是为了预示中国古代思想在隋唐时代及其以后的发展趋向,”此一主张,使王通“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为不可忽视的人物。”[1]127
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对后世帝王的统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在唐初,佛教的发展更是广泛,傅奕为太史令时,于武徳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给唐高祖的奏疏《上废省佛僧表》中有:“缙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浪语。”(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一)可见其在士大夫中已被广泛传播并影响极深,因而废除佛教几乎已成为不可能的事了。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导利用,如唐太宗李世民曾云:“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学,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而三教虽异,善归一揆。”(《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其《大兴善寺钟铭序》曰:“皇帝道叶金轮,示居黄屋,覆焘万方,舟航三界,欲使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随梵音而俱远。”(《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上)体现了其利用三教加强统治的目的。初唐还在政府的支持资助下,整理了三教的文化典籍,包括佛经翻译,道教经典的整理等*据《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统计,自汉乞唐,翻译大小乘经论典籍和传记等,已有三千六百六十部,计八千六百四十一卷(还不包括当时入藏的经卷)。675年将所有的道教经书抄录为7300卷。武则天时期还编辑了1300卷的《三教珠英》。。唐代的其他帝王也纷纷采取措施来积极贯彻实施三教并举的政策。如高宗时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老子》。玄宗常集儒、道、佛各教代表于一室,讨论三教异同,声称要会三归一。*开元十年(722)唐玄宗颁布《孝经注》,认为,“孝者德之本”,只有“孝”可以教育人民,“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共称,如此则秩序可以重建,道德可以恢复。开元二十至二十一年(732-733)唐玄宗又完成《道德经御注》引入佛理,讨论“性”与“情”、“心”与“境”的问题,以此哲理的讨论,为秩序确立一种人性与道德的基础。开元二十二年(734)又颁布了其注释的《金刚经》,认为“不坏之法,真常之性,实在此经。”并与《道德经》《孝经》并称。参阅《旧唐书》。可以说整个唐代,只有武宗时有过短暂的毁佛事件,但其结果却促成了中国化的禅宗的进一步盛行。随后的宋代帝王更是积极贯彻三教并举政策以加强其政治统治,兹不赘述。总之,三教合流的情形正如鲁迅先生在《吃教》所说的中国晋以来的名流,每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儿,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而且常常作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这正是魏晋以来三教融合的生动写照。
王通站在儒家立场上提出的“三教可一”思想,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智慧。它极大地促进了思想的融合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王通的身后,屹立着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繁荣、开放的唐朝,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王通的思想密不可分。司空图在《文中子碑》中认为王通与孔、孟、荀一样,受命于天而启汉唐盛世之不朽功业: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圣哲之生受任于天,不可斫之以就其时。仲尼不用于战国,致其道于孟荀而传焉,得于汉成四百年之祚。五胡继乱极于周齐,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圣人之用,得众贤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魏数公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跻贞观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司空表圣文集》卷五)
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以其极大的包容精神和开放的理论特色,对中国文化及其士大夫的心态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融合智慧,可以说在王通那儿,就已经走向成熟了。
[1] 张成权.道家与中国哲学(隋唐五代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马重阳】
2014-12-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ZW023);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李海燕(1972-),女,山东五莲人,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B241
A
1008-8008(2015)04-0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