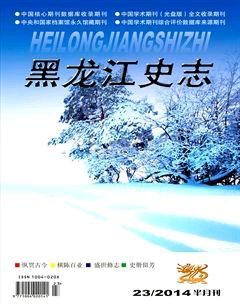从尊情视角考证龚自珍的诗歌创作渊源
[摘 要]龚自珍在清代堪称文史大家。其诗歌创作充分体现了尊情主张。无论从诗学主张比对,还是从诗歌风格考量,龚自珍的诗歌和袁枚的诗歌具有诸多共通之处。从“宥情”到“尊情”的升华使得诗歌的感情境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加之龚自珍和性灵派诗人的交际人脉,足证性灵诗派和龚自珍诗歌创作的渊源关系。
[关键词]龚自珍;诗歌创作;感情色彩;渊源探究
在清代诗坛上,袁枚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在当时诗坛颇具影响。他在诗歌创作上,继明代“公安派”、“竟陵派”而持“性灵说”。《随园诗话》及《补遗》《续诗品》是他诗论的主要著作。与龚自珍一样,袁枚的诗学主张同样具有反道学、反传统的特点,他指出诗并非说教的手段,而要抒写性灵。他认为:“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1]他强调作诗要本乎自己的真性情,要写出自己的个性,抒发真实情感;创作时要独出新意,作品既要新鲜,同时又要自然有趣。袁枚的这些诗歌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时间出现了“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的局面,而作为清代大家的龚自珍亦颇受其影响。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证:
第一,诗学主张见源流。朱杰勤就曾说过:“定庵之诗,拟求之于西洋则浪漫主义文艺,拜伦之俦也。拟求之于中国,则性灵派一流”。[2]这句话就准确点出了龚自珍在诗歌创作上与性灵派的渊源,甚至可以归划到性灵诗派中。其实,龚自珍的诗歌中情感激荡,也很得益于性灵派的熏陶。他曾言:“席中亦复无知音,谁是乾隆全盛人?君言请读乾隆诗,卅年逸事吾能知。江南花月娇良夜,海内文章盛大师。■山罗绮高无价,仓山楼阁明如画。”(《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赋诗》),足以看出他对这位同乡前辈十分敬仰,用“海内大师”盛赞袁枚,并用“仓山楼阁明如画”句来塑造袁枚的文学巨匠形象,并在诗中标注:“■山谓毕尚书沅,仓山谓袁大令枚”。可见诗人心目中,毕尚书和袁大令都是不同时期的流派宗师,值得效仿研究。身为同乡翘楚之才的龚自珍,具有汲取他人素养的博大胸怀。他将性灵派主真性情的观点予以提炼加工,提出了“尊情”、“主逆”、“真风骨”的诗学主张,并在此基础上身体力行地坚持了下来。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不仅仅针对“性灵派”的诗学精华予以部分性地继承,而是对于晚明以来包括性灵派思想在内所有有益思想的一种认同。“提笔先须问性情”和“诗贵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就是袁枚早期提出的集中观点,他强调从事诗歌创作必须先灌注炽烈的感情,情在笔先、以笔驭情,其情要有孩童般的纯真(即赤子之心),要有真情亦即纯粹的创作之情,将诗文创作与“情”统一起来。而龚自珍提出的“宥情论”也明确主张诗“陶写性灵”。[3]这和性灵说所提倡的经典说法殊无二致。宥情论在强调人的真情实感是创作基础的同时,在哲学上反对宋明理学禁欲主义,在文学上反对复古主义、形式主义。此观点也出现在了龚自珍的《宥情》一文之中。他借助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辩论点出人与物态的区别来,人主要在于有七情六欲,“能言哀乐”。他把情欲列为人的第一等需要,这是经常会“阴气沉沉而来袭心”的,而“自求病于其心,心有脉,脉有见童年”[4]对诗文创作是最重要的。从这些表达可以看出,龚自珍所说的情即为“童真之情”,在感性和纯洁方面具有终极意义。
第二,“宥情”“尊情”再升华。龚自珍在《长短言自序》中有“情之为物……宥之不已,而反尊之”[5]的表达,这表明他已经对宥情学说有了创新与升华。在袁枚看来,要达到有“情”的地步,关键是要突出“真”,即通过“真”来达到文学作品“含情”的目的,“以真达情”。而龚自珍也吟道:“少年哀乐过于人,歌哭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感动人,关键在于“尊情”。他所强调实际上就是在从事文学创作时突出个人情感,与“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中的情、意是相通的,即“性情”与“情”应当同义理解,这与袁枚的延展性认识也具有同向性。在其诗歌创作中主要体现为忧时愤世的情感,实际上是集个人朴素情感、创作诗情和社会情感的一种统一。也有学者将袁枚的创作风格归结为四点,即:发自童真的渊源启发、“性情”与“情”的同义理解、以“真”达“情”的别样意境、以情驭诗的客观评价。[6]仔细品味,从中就可以分别出袁、龚二人诗学主张的异同来。
第三,袁、龚诗风多相近。认真比较龚自珍和袁枚的诗歌,就会发现其风格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往往信手出笔,无拘无束,率性而为,例灵活多变,不事雕琢,深得“诗主性灵”之妙。文学观与审美取向的高度契合,成就了二人如臂使指的诗句,甚至有化用之嫌。在此试举几例,如《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何日冥鸿踪迹遂,美人经卷葬年华”与袁枚《题永竹岩〈双美读书图〉》中“供得年华消得恨,美人颜色古人书”就很相像;《投宋于庭》“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与袁枚《少年行》的“与余握手铜龙楼,衣香一过三年留”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己亥杂诗》其一零六“寄语瞿塘滩上贾,收帆好趁顺风时”与袁枚《示儿》“骑马莫轻平地上,收帆好趁顺风时”几为活脱的两个版本。还有《己亥杂诗》其一二六:“别有狂言谢时望,东山妓即是苍生”句与袁枚《谢太傅祠》中“一笑翩然载酒行,东山女妓亦苍生”真可谓一脉同源,渊源匪浅。
第四,龚氏人脉多性灵。龚自珍曾与随园女弟子归懋仪多有诗歌唱和,而他与年长自己三十二岁的王昙结为忘年之谊更为时人所称道。陈文述在《王仲瞿墓志》中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王昙的性格特点:“性慷慨,好奇计,每发一论,出人意表”;“好谈经济,尤喜论兵”;“性豪逸,尝于除夕携眷属泛舟,皋亭梅花下度岁”等莫不如是。王昙十分欣赏龚自珍遒劲纵横的卓绝才气,龚自珍亦心折于王昙独特的思想性格,两人的友情佳话竟贯穿终生。由于王昙不合纲常,习惯于特立独行,导致自己逐渐与社会隔绝孤立起来,生活境况颇为潦倒,以致身后事都是龚自珍参与料理。由于二人年齿悬殊,王昙阅历、学识、人格、品德均为龚自珍赏识,半师半友的关系亦对其产生了一定影响。
参考文献:
[1]袁枚.笺注随园诗话补遗卷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2]朱杰勤.龚定庵研究[J].现代史学,1935(4).
[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537.
[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89.
[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232.
[6]高云亮.情到真处方成诗——浅析袁枚诗歌的创作风格[J].甘肃高师学报,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