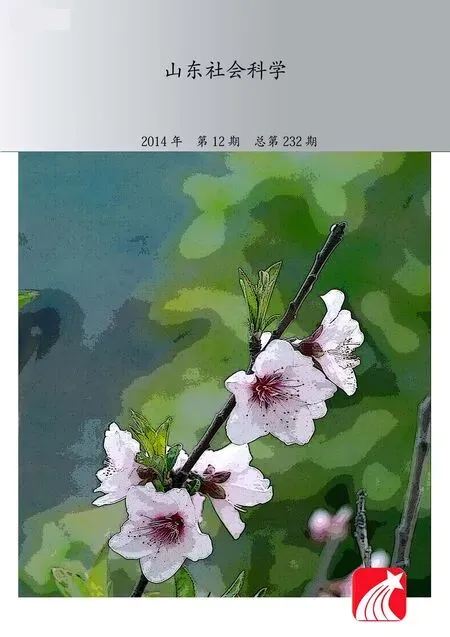大江健三郎《晚年样式集》中的鲁迅《孤独者》映像
陈世华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
大江健三郎在1955年进入东京大学法语专业后,受导师渡边一夫的影响,开始接触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思想和东方主义文学思想,而这直接反映在了其作品的创作上,大江是一位互文性意识非常强的作家,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特点更加凸显。许金龙基于多年对大江文学作品的研究,认为大江健三郎“常常在小说中引用或参考其他作家、诗人的作品或自己的作品,这从他的处女作《巧妙的工作》(1957)中便可见一斑;到了他的晚年作品,这种互文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被偷换的孩子》(2000)与莫里斯·森达克的绘本《外头那边》、《愁容童子》(2002)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别了,我的书!》(2005)与瓦尔特·本雅明的《论历史哲学纲要》、《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2007)与埃德加·爱伦·坡《安娜贝尔·李》等等”*许金龙:《〈水死〉的“穴居人”母题及其文化内涵》,《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许金龙进一步指出,大江的长篇小说《水死》(2009)同样具有很强的互文性。可见,进入21世纪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晚年的工作”系列作品,比以前的创作表现出更加强烈的互文性。
连载在2012年1月号到2013年7月号的《群像》杂志上的大江“晚年的工作”系列作品的集大成之作《晚年样式集》,宣告大江“小说的工作基本结束”*大江健三郎、古井由吉:《迷茫于浩瀚语言,超越混乱的现实》,《新潮》2014年第6期。。小说的大部分内容围绕“女子三人组”对“我”和“我”过去创作的作品的批判展开。这种作品构造自然决定了要引用自己以前创作的作品内容,同时也不断出现了以前创作的作品中的出场人物和故事,可以说该作品是到现在为止互文性最强的作品。该作品的互文性特点还体现在对鲁迅《孤独者》创作结构、修辞方法以及创作主题的接受上。
大江健三郎在本世纪初声称,虽然他“十分尊敬鲁迅”,但他的“小说创作没有受到鲁迅的直接影响”*王新新、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心中的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2期。。大江认为,“鲁迅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伟大的鲁迅,他饱尝痛苦和艰辛,时常觉得自己软弱无助,他是经过一生的时间,才不断成熟,最后使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去战斗的文学家的。一个最初软弱、历经苦难甚至受到压制的人,能不断革新自己、战胜自己,的确了不起。也许我成不了这样的人,但我想成为这样的人。作为一个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而奋斗的斗士终此一生,是我作为文学者的理想。我正是想在这一点上靠近鲁迅”*王新新、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心中的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2期。。这看似矛盾的说法,实际上表达了大江对鲁迅一种“望尘莫及”的敬仰之情。从早期的创作开始,大江作品中就一直有鲁迅影响的影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大江的处女作《奇妙的工作》(1957)开始,直至最近刚刚发表的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2013),在这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鲁迅文学一直是大江健三郎创作小说的重要资源”[注]许金龙:《大江健三郎小说研究在中国》,《中华读书报》2014年4月16日,第13版。。王新新甚至认为在处女作《奇妙的工作》发表之前,大江“就曾援引鲁迅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注]王新新、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心中的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2期。。除此之外,在《别了,我的书!》(2005)日文版原著封面红色腰封上,意味深长地用醒目白色大字为我们表明了该书的主旨:“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这句话也立刻让我们联想到了鲁迅在《希望》中写下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由此看来,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尤其是在后期作品中,大都有鲁迅作品的影子。在《晚年样式集》开头,小说主人公长江,在3·11东日本大地震第一百天,和往常一样看电视到深夜,而内容一直是有关福岛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扩散引起污染问题的特集,看完后“在上二楼时,止步于楼梯半道平台上的我,像儿时通过翻译的鲁迅短篇记住的那样,‘呜呜的哭起来’”[注]大江健三郎:《晚年样式集》,讲谈社2013年版,第14页。以下简称《晚》,只随正文夹注页码。,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呜呜的哭起来”的描写多次出现,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再次表明这“呜呜的哭起来”是“注释为通过鲁迅的日译本记住的说法”(《晚》,第288页),这就首尾照应地说明了大江在创作该作品时,始终没有脱离鲁迅小说的影响。早在1932年,日本改造社就出版了由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虽然这个时候的《鲁迅全集》并没有收录鲁迅的所有作品,却收录了《呐喊》和《彷徨》的内容,可以说,大江健三郎应该在年轻时候就充分接触到了鲁迅的作品。而“呜呜的哭起来”这种表达,正是出现在鲁迅作品《孤独者》中。
在叙事艺术、修辞艺术和创作主题上,《晚年样式集》都受到了鲁迅《孤独者》的影响,尤其是在创作主题上,鲁迅对大江的影响已经上升到雷同社会背景下的精神层面。
一、叙事艺术:边缘人物叙事策略和转述叙事
在《孤独者》中,“我”和魏连殳除了直接接触外,“我”对魏连殳的了解,则多是通过第三者——边缘化人物的叙事来实现的,而这些边缘化的人物几乎都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作品开始就描写了自己和连殳的相识,“是以送殓始”[注]鲁迅:《孤独者》,载《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以下简称《孤》,只随正文夹注页码。,连殳送殓的不是别人,而是祖母。而“这祖母,是我父亲的继母;他的生母,他三岁时候就死去了”(《孤》,第96页)。虽然连殳“爱这‘自己的祖母’”(《孤》,第97页),但在连殳心中,这不过是爱着“盛装的画像”(《孤》,第96页),因为他对真正的祖母并没有任何印象,他真正爱着的是那善讲故事、会做针线活但却少见笑容的这父亲的继母,这“管理我,也爱护我”(《孤》,第97页)的祖母。这些由送殓引起的话题,从侧面反映了连殳性格的形成,正是受到了“父亲的继母”这祖母的影响,“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命运”(《孤》,第96页)。作品无论是送殓时候的情景还是“我”和魏连殳关于祖母的话题,都用大篇幅进行了描写,这实际上是为描写连殳的性格埋下了伏笔,“在‘魏连殳’的意识当中,祖母在自己家族中的处境,和他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整个中国社会中的处境,不仅具有外在形式上的形似,而且具有内在的精神意蕴和精神价值上的深刻联系”[注]李林荣:《〈孤独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期。,因此,其后故事的展开,都离不开连殳接受教育和影响的背景,以及连殳自己所处的特殊社会背景。对连殳性格造成影响的是另一类边缘化的人物,那就是他的堂兄和堂兄的小儿子,为了争夺祖母的一套房子,对连殳用尽了威逼利诱的各种手段,而越是争夺,连殳就越不留下任何财产。在连殳眼里,自己周边人物对财产的争夺,是一种世俗的表现,他“将所有的器具大半烧给了他祖母,余下的便分赠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并且连房屋也要无期地借给她居住了”(《孤》,第88页)。这一方面表现了连殳的爱心,另一方面表现出了连殳对世俗的叛逆性格。
在《晚年样式集》中,主人公“我”,也就是“长江”先生,是一位获得世界级文学奖的日本著名作家,在3·11东日本大地震和核泄露事件发生后,“我”对自己写到一半的小说失去了兴趣,转而创作高龄老人在大灾难时代正视自我的文章。“我”的妹妹亚沙、妻子千樫和女儿真木则结成“女子三人组”,专写反驳“我”到现在为止创作的小说内容的文章,甚至连“我”残疾的儿子也对“我”的文章进行了反论,“我”将这些反驳文章和自己的文章合在一起,做成了一本私人出版的杂志《晚年样式集+α》,故事就是围绕着家人对“我”的文章的反论和批判展开的。“女子三人组”对“我”进行批判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你用片面的写法在小说中被描写而抱有不满”(《晚》,第10页)。“女子三人组”和儿子阿亮对“我”和“我”创作的作品进行批判后,女儿真木和儿子阿亮表现出了对我的反抗,并最终决定移居四国的森林,这既是一种反抗,也是一种从压抑的父权中逃离的表现,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改变,而是对自己从事的反核反战的游行以及演说继续一意孤行,并一边进行着反抗残酷现实和社会的创作。最终,边缘化人物对“我”的批判和“我”的主张成为了平行线。但这种平行线式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反映了边缘化人物对“我”家长制权威的消解,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对自己消解政府右倾化权威的坚持。
两部作品中对主人公的另一种描写手法,是通过转述叙事方式实现的。在《孤独者》中,大良的祖母在连殳死后,对连殳做官后的样子、病状、生前时的情景进行了详细描写和转述,“你可知道魏大人自从交运之后,人就和先前两样了,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对人也不再先前那么迂。你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个哑子,见我是叫老太太的吗?后来就叫‘老家伙’。……要是你早来一个月,还赶得上看这里的热闹,三日两头的猜拳行令……他用各种方法逗着玩;要他买东西,他就要孩子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他就不肯积蓄一点,水似得化钱。”(《孤》,第106—107页)。大良祖母的转述,详细刻画了孤独者连殳发达之后的样子,同时也描写了大良祖母这个边缘化人物的心理状态。但无论是孤独者连殳,还是边缘化的人物,他们“都与社会生存环境处于对立状态”[注]宋寒冰、杨东霞:《彷徨着的“孤独者”与野草丛中的“过客”》,《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对连殳发达后状况的转述,何尝不是鲁迅对自己的审视。
在《晚年样式集》中,女儿真木和儿子阿亮对“我”的态度,也是通过亚沙和妻子转述出来的。关于真木对于父亲的态度,“我”的妹妹亚沙转述道,“如果用真木的说法的话,我听说是希望从爸爸的压抑中摆脱出来自由生活”(《晚》,第74页),千樫面对长江,也说出了孩子们的不满,“真木实际上也对你关于阿亮最近经常说的阿归的事情,没有认真领会而不满”(《晚》,第83页)。长江的妹妹亚沙将从真木那里听到的阿亮对长江不满的话告诉长江,千樫告诉长江的孩子们的话,同样是从真木那里听到的,而真木告诉千樫的话,除了自己的想法外,很多是阿亮直接告诉真木的。这种转述叙事,在反映了孩子们真实想法的同时,也多向度反映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和创作特点,通过这种转述叙事,使作品中的“我”更能达到一种自我审视的效果。
无论鲁迅还是大江,都是用一种边缘化人物的语言或者反抗,还有一种转述的叙事方式,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这种反思,虽然表现为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的一种坚持,但这恰恰印证了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的灵魂所在。在这一点上,大江明显受到了鲁迅的影响,“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大江总是下意识地站在边缘角度,开始用审视甚至批判的目光注视着权力和中心,越来越靠近作家鲁迅所坚持的批判立场”[注]许金龙:《“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鲁迅影响之初探》,《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1期。。在两部作品中,通过这些籍籍无名的边缘化人物的描写,发挥着对世俗和权威解体的作用。通过转述叙事,实现了作者化身的主人公“我”的自我审视。虽说两人所处年代不同,但社会背景却类似,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孤独者》中的边缘化人物叙事和转述叙事是对世俗的映衬和讽刺,而《晚年样式集》中则是用这些叙事方式,暗示着对家长制权威和右倾化政府权威的解体。
二、修辞方法:对白、幽默和反讽
在两部作品中,对白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孤独者》中,魏连殳命运的呈现与叙述者“我”和魏连殳的对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魏连殳的命运发展过程中,对白提炼和概括出了几个彼此相关的形而上主题,进行交流和争论。这几个形而上的主题,是通过“我”和魏连殳的三次辩论开始的,三次辩论讨论了三个主题。第一次辩论是从孩子说起的。魏连殳非常喜欢孩子,虽然作品中的大良、二良是极其调皮、极其讨厌的两个小孩,而且他们的祖母也是个极其讨厌的小市民,但魏连殳非常喜欢这两个小孩。有一次,“我”和魏连殳就如何看待孩子的问题进行了一场争论:魏连殳认为“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而“我”却认为“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孤》,第91页)从表面上看,这是讨论孩子问题,而实际上两人讨论的是“人的生存希望”在哪里的问题。两种观点没有结论,但却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矛盾。第二次辩论围绕“孤独”问题展开。有一天,“我”看到魏连殳的样子,“忽而感到一种淡漠的孤寂和悲哀”(《孤》,第95页),于是,“我”强装着微笑,说:“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你看的人间太坏……”,“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孤》,第96页)在“我”看来,魏连殳的这种孤独处境是自己造成的,因此也可以用自我调整的方式改变。这个时候,魏连殳却说起了祖母,他虽然和祖母没有血缘关系,但当看到祖母的孤独时,自己觉得“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孤》,第96页)。也就是说,在魏连殳看来,自己的这种孤独状况,不是由心境带来的,而是命运造成、注定如此的,而且会代代传下去。这次争论是一种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追问,即争论了人的生存状态是可以改变的,还是无可改变的宿命的问题这个矛盾主题。第三个问题则探讨了更加深刻的主题。第三次对白是在魏连殳来求“我”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我还得活几天!”(《孤》,第100页)当连殳走了之后,这句话却像火一样烙在“我”的心上。而这次真正的对白却是通过连殳给“我”的信,信的第一句话就说:“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在这里,连殳提出了“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从信中内容来看,连殳结合自己的经历,回答了为自己活,即为自己某种追求、理想、信仰而活的问题,当理想破灭后,他又提出了为爱我者活的问题,当爱我者也不希望我活下去的时候,自己只能为那些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活着,即为敌人而活着,这是对命运的残酷抗争。这些对白描写是“对魏连殳的命运的重新思考和审视”[注]薛毅、钱理群:《〈孤独者〉细读》,《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7期。,更是作者鲁迅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警戒。
在《晚年样式集》中,“女子三人组”同样通过对白的方式和“我”讨论了三个问题,一个是居伊兄之死。亚沙指出杀死居伊兄的是“我”,让“我”陷入了恐慌之中。第二个问题是塙吾良之死。亚沙怀疑吾良在自杀之前,古义人可以采取某种方式阻止,却没有去阻止。第三个问题是古义人被指责虽然将自己患有智障的儿子放在了自己创作的作品中,但却对自己的儿子没有表现出充分的敬意,而是将自己儿子表达的真意进行了歪曲。作品中,“我”在创作的阿亮的台词是“不要紧,不要紧,因为阿归会救我的”(《晚》,第131页),但阿亮却反驳道,“长江总是用错误的语言在说。我说的事情全然不听”(《晚》,第285页),阿亮真正说的是“阿亮来救”。无论是居伊兄之死,还是塙吾良之死,都是面对残酷现实作出的挣扎和选择,而儿子由于先天性的智障,也在自己的世界里痛苦挣扎。而“我”面对这些,同时面对的也是一种心灵的煎熬和自我的反思,面对残酷的家庭现实和社会现实,“我”矛盾于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
无论是在《孤独者》还是在《晚年样式集》中,都是通过“我”和连殳、“我”和“女子三人组”对白的互相对峙、互相辩驳,写出了鲁迅和大江内心深处的困惑。两部作品都通过对历史和现实命运的考察,在更深层面上展开关于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价值和人的生存希望的思辨。同时,两部作品的故事,都是在意识到“死”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孤独者》中,连殳的死带有极为悲观和无奈的特点,但在《晚年样式集》中,亚沙却不准“我”死,“如果我不拉住露出的细脚踝的话,哥哥就那样水死了吧”(《晚》,第48页),因为在亚沙看来,自己不允许长江死去,一方面表达了大家从现实中逃离到四国森林中去的坚强决心,一方面对长江也提出了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问题。
在两部作品中,还同时使用了幽默讽刺的手法,《孤独者》中魏连殳的桀骜不驯、愤世嫉俗、飞黄腾达后家人对自己的态度变化等,无不用幽默的方式反讽这社会现实,“《孤独者》所探讨的,并不侧重在魏连殳的新思想、新观念以及他有什么政治、宗教、社会的改革主张,而主要是揭示他在走投无路之际以灵魂的自我毁灭来嘲弄社会的情形”[注]李允经:《向旧我告别——〈孤独者〉新说》,《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6期。,作品通过一个知识分子的遭遇,反讽了当时现实的社会。在《晚年样式集》中,“我”面对“女子三人组”的批判,陷入了孤立的境地。而在残酷的现实社会中,尤其是残酷的核泄漏现实面前,几乎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地方,只能躲到四国的森林边缘。如果说到现在为止,大江对四国森林的描写是“把森林看做摆脱生存困境、灵魂再生的精神家园,是理想之国‘乌托邦’,同时又是核时代的‘隐蔽所’和充满不安与困惑的地方”[注]王玲:《大江健三郎及其作品与日本森林文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0期。的话,那么在核泄漏的现实面前,在日本各地被核电站包围着的现实面前,安全“乌托邦”不复存在,到四国森林的举动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更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讽刺。
三、创作主题:残酷现实面前的“绝望”和对未来的“希望”
在两部作品中,都探讨了“生”和“死”的问题。《孤独者》中“我”和魏连殳讨论的三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在面对命运和社会现实时,“我”和连殳对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的探寻。整篇作品透露着对个人命运的无奈和对现实社会的失望。而在《晚年样式集》中探讨的三个问题,是对日本战前天皇制集权制度对人性迫害的失望,以及如何保护智障儿子这个残酷个人命运的讨论。如果说对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感到无奈的话,那战后非战非核的民主精神还些许让“我”或者“我”们得到安慰。遗憾的是,为追求高度增长的经济效益,日本政府一意孤行发展核电,在面对3·11东日本大地震造成的核泄漏时,政府和东京电力都束手无策。更让人失望的是,面对核泄露造成的巨大灾难,在灾区复兴停滞不前、治理泄露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又极力推进其他核电站重启,并加速将日本核电技术出口到印度的进程。与此同时,伴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日本政府急剧右倾,加速制定对外侵略、对内专制的各种法案和法律。残酷的现实面前,鲁迅和大江都表现出对现实的极度失望。
同时,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作为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作品传达的并不仅仅是失望,同样要传达积极的力量,为人们带来希望。[注]参见张福贵:《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孤独者》中“我”和连殳的讨论首先是从孩子的问题开始的,魏连殳认为中国的希望只在孩子,孩子们在本性上是好的,只是后天的环境造成了人的坏,既然是环境造成的,就有改造的可能性。而“我”认为不是环境造成的,是人的“根苗”就是坏的,无法改造,也就没有希望。这里实际上是从人的本性这个根本上来辩论人的生存有无希望的问题。“我”和连殳的相互质疑一直处在两条平行线上,未分伯仲。虽然作品中的“我”对未来抱有悲观态度,但在鲁迅的作品中,“鲁迅一旦意识到自己笔下已流露出过于浓重的黑暗时,便又有意生造出一丝光明来”[注]程桂婷:《疾病与疗救:鲁迅小说中的矛盾内涵》,《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5期。,这也切合着鲁迅心灵中关于生存希望的主题。作品最后,送完“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孤》,第107页)的连殳后,“我”的灵魂的忍受程度也达到了极限,于是“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深夜在旷野里发出的长嗥,夹杂着“我”和连殳的愤怒和悲哀,同时也可以说是作者的心声。但当“我”的绝望与痛苦达到极限时,“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地路上走,月光底下”(《孤》,第108页),在“我”重新上路的最后画面中,“夜色与月光,‘我’忽而轻松起来的心态以及坦然的步履,与潮湿凝滞的石路,以对立的情状,预示了‘我’与‘我’未来的处境之间并不乐观但决不会因‘我’的妥协而流于松懈的紧张关系”[注]李林荣:《〈孤独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期。。也就是这个时候的“我”,由极度的痛苦恢复到平静,把这种痛苦真正内化在心灵最深处,开始新的挣扎和努力,开始创造新的希望,开始了更深远的思索。鲁迅的创作,“在强烈地表达孤独者的绝境、自我毁灭之必然和死之阴影、死之虚无的包围的同时,又表达着一种对另外的、超出其经验范围的,未曾发现、未曾证实的可能性的期待”[注]薛毅、钱理群:《〈孤独者〉细读》,《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7期。。
《晚年样式集》的构成看似是对过去小说的再解释和过去自我的再解释,但其中也只是讨论了过去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即居伊兄之死、塙吾良之死和在作品中对智障儿子真意的歪曲问题。前两个问题,是试图“斩杀给日本带来巨大灾难的王/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注]许金龙:《“杀王”: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对决——试析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追求的时代精神》,《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也就是在面对残酷的战前绝对天皇制社会给东亚人民以及日本人民带来的战争灾难时,以及战后美军进驻日本带来的恐慌时,“我”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失望以及对决。这种与旧体制对决的典型现实也表现在冲绳集体自杀诉讼案中,自己床边放着的笔记上,记录着“这六年间,关于与此相关的日本军强制冲绳庆良间诸岛六百余名岛民的集体自杀的审判。我们受到两个岛的守备队长(一人是本人,另一人是家属)名誉损毁控告,但在最高法院,我们被告方全面胜诉”(《晚》,第13页),虽然由于自己揭露事实而惹上了官司,但正义还是站在了自己一方。但面对3·11之后政府继续重启核电的计划,面对政府积极出口核电的计划,面对急剧右倾的政府强制推行《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并意欲强行通过《行使集体自卫权法案》和修改日本和平宪法,这些对“战后精神”和战后民主全面否定的做法,“我”在表示失望的同时,作出了“必须打破那种体制”(《晚》,第187页)的决心,这是维护“战后精神”的决心,也是为了人类将来的光明。当然,除了自己与右倾化政府权威的抗争,对未来的希望也寄托在孩子身上。作品最后,同样一转阴暗的氛围,用长江在70岁迎来第一个孙子时写的诗歌《遗物之歌》,将故事推向了高潮。诗歌既简短地回顾了作者的一生,又对下一代寄寓了嘱托,“我不能重生。但,我们能够重生”(《晚》,第331页)。大江将小说用如此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的诗篇结尾,“是意欲从痛苦的窘境中摆脱出来,走向祈祷,走向无垢”[注]野崎欢:《走向祈祷,走向无垢》,《群像》2013年第12期。。这种对未来的希望和意志,源于一种对家庭的爱,也源于一种对家庭、国家和人类的责任,同时也“暗示了借助超越世代和民族的集团想象力,靠共同拥有面向未来的意志,在悲惨的结局后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注]武田将明:《献给不能命名的人们》,《群像》2013年第12期。。可以说,作品的大部分内容,是“女子三人组”对长江作品的批判,对到现在为止创作的作品的疑问、重读、再解释、阐明和细说,这种形式的小说,从侧面反映了长江现实生活和创作中的烦恼。作品真正的目的却是探讨在这种灾难和烦恼的阴影下人类的希望和未来。
两部作品都是对自我生命的体认与超越、自我意识的剖析,同时也是鲁迅和大江的自我投射。两部作品都提出了对残酷现实的失望,同时又提出了无论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脱离现实便只有灭亡,因此不得不面对现实,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主题。这种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的主题表达方式,大江明显受到了鲁迅的影响。
四、结语:类似社会背景下的精神影响
鲁迅对大江文学的影响,在文本表现上看是创作结构、修辞方法和创作主题的影响,但实际上更多的是在类似社会背景下对社会现实的绝望,以及对未来的希望这种世界观层面。虽然二者所处的年代不同,但二者所处的社会背景都是国家和民族处在水深火热的危机之中。大江认为,“在社会的危机中,鲁迅总是全力以赴、认真应对,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使自己成熟”[注]王新新、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心中的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2期。,而大江在自己将心中对日本社会的苦闷一吐为快的过程中,“广岛问题、冲绳问题、核武器问题,还有残疾儿童问题成为我关注的中心”[注]王新新、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心中的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2期。。也就是说,二者都是在面对类似的残酷社会现实时,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中,体现出了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大江看来,二人所处的时代,有极为类似的特点,“在我看来,中国的改变始自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日本的改变应该始自战败,辛亥革命和战败在这一点上应该具有相同的意义”[注]王新新、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心中的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2期。。在五四时期,“鲁迅作品的显层主题虽然是‘改造国民性’,但‘国民’始终是‘他者’。‘他者’是外在的,无法取代内在的‘自我’。‘自我’虽然被悬置了,但总会利用有限的时空顽强地展示自己的形象、发出自己的声音”[注]罗晓静:《“孤独”的个人与鲁迅作品的自省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5期。,同样,大江也是面对残酷现实时用有限的时空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读鲁迅和大江健三郎的小说,要深切地贴近作者,贴近那个时代,尤其是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也是大江的创作深受鲁迅影响的文化根源。
鲁迅作品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否定、对现实社会的失望以及对未来的希望描写,都深深影响着大江,这种影响,已经超越了创作形式和修辞手法的层次,而是上升到了对创作主体的精神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成为日本知识界自我否定的内在契机,以及借以反省侵略战争和日本近代化、拯救自我、重建主体性的重要媒介和思想资源”[注]刘伟:《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的影响问题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在《晚年样式集》中,这种影响还表现为萨特存在主义和鲁迅文学思想的融合,日本战后进入民主国家,天皇也仅仅是个象征,日本人在民主主义的影响下取得了自由,行动也相对自由。在这种民主自由的背景下,人们发挥自己的想象,指导自己创建了核电站。但现在核泄漏的严重事故发生了,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萨特的“自由选择”思想。“萨特的自由选择和鲁迅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有关探索,其实都与人道主义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注]许金龙:《大江健三郎小说研究在中国》,《中华读书报》2014年4月16日,第13版。。鲁迅对大江的影响,在精神层面表现在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对未来希望的描写上。
在希望描写方面,大江同样接受了鲁迅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一方面是面对急剧右倾化的日本社会,自己坚定了与残酷的社会现实对抗的决心和信心,就如其对中日关系的寄语中所说:“安倍政权是靠各种牺牲支撑的,他们意欲用非民主主义的方法将我们坚守了67年的时代精神破坏。为了守卫下一代的和平和民主主义,我们能够做的是游行和这些集会。”[注]大江健三郎:《中日关系一句话》,《人民中国》2014年第6期。
——以大江健三郎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