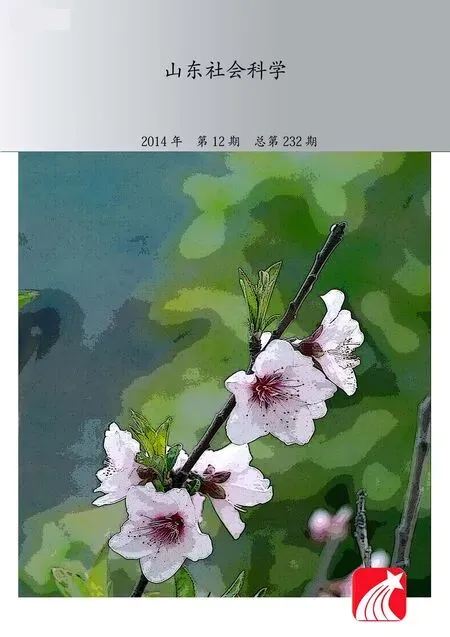民国时期乡村精英与权力结构
——华北村落特质的一个侧面
韩朝建 赵彦民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山东大学 文化遗产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中,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组织东京大学的学者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其原始资料结集为《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以下简称《惯行调查》)。这批资料为学者研究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文献,学界亦借此展开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讨论。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日本学者的观点出现了分歧,即以平野义太郎为代表的“村落共同体”肯定论派和以戒能通孝为代表的否定论派。平野主张村落生活中的耕作、治安联防、祭祀信仰、娱乐、婚葬以及农民意识道德中的共同规范等方面具有共同体意义,农村社会是以寺庙祭祀为中心形成的共同体生活组织。*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论战”为核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第200页。与此相对,戒能在论证中国农村社会土地所有权问题的同时,指出中国的封建制度或村落秩序不具有像西欧或日本社会那样的自律性共同结合关系,*[日]戒能通孝:《支那土地法惯行序说》,载《法律社会学の诸问题》,日本评论社1943年版,第85-176页。强调中国的村落集团不是共同社会而是利益社会。*[日]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理论》,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14、249页。平野和戒能将学界的注意力聚焦到村落社会结构的层面,具有开拓性的时代意义,但他们强调的只是村落特质的不同侧面,两方面的观点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此后研究村落性质的学者在“村落共同体”理论的基础上,逐渐转向了“村落—国家”的视角,比如旗田巍强调了村落内在传统与国家新政的关系,他指出村落行政组织不是国家随意设定的,而是以村落的传统自治组织为基础建立的,通过传统的村落自治组织与行政组织的结合,才能实现村落行政职能的作用。*[日]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理论》,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14、249页。黄宗智也持类似观点,指出村落“内生的权力结构”的顽固性。*[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7-250页。笔者亦曾通过山东冷水沟村信仰空间的探讨,认为乡村宗教活动被纳入村政的范围,文化网络并没有脱离村政,它仍然强化了村落政权的合法性。*赵彦民、韩朝建:《村落行政变迁下的信仰空间——以民国时期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村为个案》,《文化遗产》2013年第6期。
杜赞奇则更强调国家政权建设对乡村权力结构的冲击,他认为19世纪末,以治安为目的的保甲制和以征税为目的的里甲制已名存实亡,清朝政府只能通过中间人即“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至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使得经纪体制从原来的县衙延伸到区和村庄,这些基层的国家经纪在征收和解交各种摊款及其他捐税过程中上下其手,以饱私囊,谓之“营利型经纪”。[注][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149、66-68页。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村公职不再是炫耀领导才华和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追求,相反,村公职被视为同衙役胥吏、包税人、营利型经纪一样,充任公职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149、66-68页。。因此,公职更加被社会精英鄙夷,同时,随着摊款压力增加,村落精英出于自保的目的,纷纷退出公职,结果导致规利之徒即“营利型经纪”控制乡村政权。由于他们“窃取”公职的目的是为了中饱私囊,导致征收的税收无法强化国家权力;同时他们的存在降低了国家的威信,这两个因素体现了所谓“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149、66-68页。
近代化过程中,国家政权建设给村落造成的压力是毋庸置疑的,阶级分化导致的村落凝聚力的丧失也有一定的道理[注]黄宗智其实从农民分化的角度认为沙井村的村落共同体走向解体,“易受外来压力的欺压摆布”。参见[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3-279页。,但如果过于强调民国时期村落社会断裂性的话,就会忽视华北村落政权连续性的方面[注]实际上已经有若干学者强调村落权力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连贯性,除了前文提到的旗田巍,近年来还有内山雅生,参见《現代中国农村と「共同体」——转换期中国华北农村における社会构造と农民》,御茶の水书房2003年版;另外张思的文章也关注了自治组织的渊源及适应性,参见张思:《近世以来华北农村青苗会组织的成长与村民自治》,载唐力行编:《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1-162页。,从而造成很多理论上的混淆,比如,所谓“精英退出政权”究竟是怎么回事?村落中的“营利型经纪”究竟是国家改造基层政权的产物,还是更多导源于村落内部?等等。鉴于这些重要的讨论都是以《惯行调查》为资料基础,笔者亦利用这批文献[注]对满铁调查村落进行回访和后续研究的成果很多,具体成果见顾琳的总结,Linda Grove, “Revisiting the Kanko Chosa Villages: A Review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Studies of North China Rural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1.1(2014), pp.77-98.,通过分析村落精英的构成与村落权力结构的变与不变,来重新审视近代华北村落的特质。本文将首先以顺义县沙井村、石门村为例,分析地方精英的构成及其对村落政权的支配;其次通过梳理两村庙产之争,说明精英分化及其与村落权力结构的问题;最后将考察对象扩大到其它满铁调查的村落,并对杜赞奇“营利型经纪”的概念及村落特质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
二、地方精英与村落政权的支配
根据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的定义,精英是指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取最多的人,这些价值包括尊重、收入、安全等。[注][美]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页。当然根据其活动的范围和影响力,精英可以分为多个层次,在中国乡村的层级,精英究竟指哪些人呢?社会学家王汉生曾分析过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根据精英影响力来源的不同,分为党政精英、经济精英与社会精英,在村落环境下这些身份往往重合,精英往往兼具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影响力。[注]王汉生:《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秋季卷。类似分法同样适用于民国时期的华北村落,彼时担任村公职者往往是土地众多者,这些人既是政治精英也是经济精英,他们通常称作会首,是村落内生的领袖。当然,这种情况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与清末民国村政权的出现密不可分,并经受住了民国政府对基层政权的改造而延续下来。
(一)村公会的出现
近代华北村落政权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村公会的出现,而它又与青苗会有直接的渊源关系。青苗会产生于清末,成立的目的除了看青之外,还负责征收其它费用作为村费。沙井村会首杨润称:“那时候为什么出现青苗会呢?以前只向县里交纳田赋(钱粮),民国以后产生了副税,为了交副税而成立了青苗会。”[注]关于青苗会何时建立,沙井村的会首们分别有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以及民国成立以后等多种看法,参见[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72页、175页、204页。在另外一次场合,被问及青苗会成立的缘由,杨润称:“以前,没有特别的费用。民国成立,省政府发通告到县政府,让成立青苗会,据此学、警两款全部让村里出。”[注][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72页。换言之,青苗会其实与村费的建立是同一个过程,由于村费不是都解运到上级政府,它也可以用于本村各项事业中,它使得村落能够建立自己的预算,因此可以说,青苗会更多的是一种村落财政制度。
青苗会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看青,并由此产生了“青圈”即看青的边界。这个边界在最终确立的过程中产生过纠纷,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以前,青苗钱基本上是交给耕种者居住的村庄的,但同时土地所在的村庄也要征收青苗钱,所以就导致了诉讼,结果当年顺义县安知县出台了“死圈”的命令,通过这一命令,每个村落看青的范围固定化了[注][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204-205、98、172、175、172、174、172、181-182、97、116、122、100页。。青圈的固定化,使得村落形成了自己的地理边界,因此村落在地理意义上形成了更紧密的一个整体。
随着村财政的建立、村落边界的固定化,村庄已不再是单纯的地理单位,而是独立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因此青苗会成为实际的村政权,“相当于民国的村公所”*[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204-205、98、172、175、172、174、172、181-182、97、116、122、100页。。而青苗会的权力扩大化之后,自然演变为村公会(村公所)。这个时间点大约在1900年之后。[注]关于村公会成立的年代,杜赞奇引用甘布尔研究的B村的事例,认为大概是1900年之后,根据县衙成立村公会的命令,青苗会改为村公会,会首成为村长副,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9页。根据满铁调查人员对沙井村会首李濡源、杨润的采访,该村青苗会是村公会的一部分,它的首领和村公会的首领是相同的。*[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204-205、98、172、175、172、174、172、181-182、97、116、122、100页。
根据杨润的说法,村公会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是办“善会”,由于每年举行五次,所以也叫“五会”。这个“会”就是村公会产生之前的村落自治组织,是它的另一个制度源头。村公会成立后,办善会被纳入村公会的行政范围,“是村公会的一部分”*[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204-205、98、172、175、172、174、172、181-182、97、116、122、100页。。 “青苗会成立以后,香头变成了会首。”*[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204-205、98、172、175、172、174、172、181-182、97、116、122、100页。。根据杨润提供的当年庆祝正月十五的“善会单”,彼时17位善会香头中有10人兼任青苗会与村公会的会首*[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204-205、98、172、175、172、174、172、181-182、97、116、122、100页。。有了这样高比例的重合,也难怪村民会认为香头、会首是同一批人。石门村与沙井村的情况一样,香头也是青苗会和村公会的会首*[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204-205、98、172、175、172、174、172、181-182、97、116、122、100页。。
村公会的制度源头之一是带有宗教性质的善会,村公会成立后,接管了善会,并将其活动被纳入村政的范围,这一点正是满铁调查村落的共同特点。[注]赵彦民、韩朝建:《村落行政变迁下的信仰空间——以民国时期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村为个案》,《文化遗产》2013年第6期;林聚任也注意到 “宗教财产及机构被纳入公共政治范围内”,参见林聚任、解玉喜、杨善民:《一个北方村落的百年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页。村公会的产生、演变之所以顺利,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无论是五会还是青苗会都是有产者主导的组织,当村公会成立的时候,有产者转而成为村公会的会首,其职责范围也从宗教、看青扩大到所有的村政,享有了更广泛的权力。由于村公会的产生根植于村落传统,以至于旗田巍称之为中国农村“自生的自治组织”,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后来政府强力推行的大乡制和保甲制,并没有改变村公会主导村政的格局。[注][日]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理论》,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250-252页。
(二)会首的责任与利益
在满铁调查时的沙井村和石门村,村落领袖分为两类,一类是选举产生的村庄领袖,比如村长、乡长,“村长是选出来的,能处理公私事情的,识字的,不限财产多少。”[注]当时主村、副村合成一乡,主村的村长即乡长,副村的村长即副乡长。石门村是主村,因此村长即是乡长,参见[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97页。村长需要县里的任命,其责任包括村里的所有事务,比较重要的如筹措摊款、学校经费、处理纠纷、修桥铺路等。*[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204-205、98、172、175、172、174、172、181-182、97、116、122、100页。尽管村长责任重大,但村务繁杂,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那么村长如何有能力处理村政呢?答案是他依赖另一类的村落领袖即会首。会首(村民更习惯称之为“在会的人”)名义上是村长任命的,但村长既不出具任命书,也不向县里汇报,因此所谓村长任命不过徒具形式而已。实际上,多数情况下,会首的概念是包含村长的,会首是村公会的主要成员和决策者。
那么什么人能成为会首呢?采访时,沙井村一共有十位会首,分别是赵廷魁、李濡源、张永仁、杨泽、杨正、杨润、李秀芳、杨源、张瑞、杜祥。其中几位会首是世代相承的,比如受访者赵廷奎的祖父、父亲、自己三代都是会首*[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204-205、98、172、175、172、174、172、181-182、97、116、122、100页。,家里是“村里有名望的家庭”。[注]此名单与1942年3月11日李濡元、杨润提供的名单稍有出入,参见[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98页。杨润、杨源的父亲都是会首,杨源不仅继续担任会首,而且曾替他叔父杨斌代理村副之职,他有如此之能力,很重要的一点是土地多*[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204-205、98、172、175、172、174、172、181-182、97、116、122、100页。。其他会首的情况类似,他们的政治资本和土地,显然主要来自继承,当然也有很多会首是自己发家之后才成为会首的。也就是说,除了家庭名望、能力之外,成为会首最重要的条件是土地和财富,而这些可以继承,所以会首的职位实际上也继承了下来。
会首由有产者担任有其必要性,因为会首们的责任重大,需要有相当的财产作为支撑。会首的责任包括:选举村长、接受村长转达的命令、与村长协商处理摊款、治安等村落事务、代替村长承担接待任务等[注][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97-98、102、177、201、217页。。另有村民称,会首负责修庙修路的公共事务、决定雇佣看青之人、决定会产的租佃等各类事情。种种村政,出钱出力处甚多,非有产者无以胜任。据统计,沙井村9个会首平均占有土地50亩,远远高于全村户均面积数(15亩),其中村副张瑞的土地高达130亩。杜赞奇据此认为“沙井村的领导权掌握在占总户数15%的富有人家手中”,“拥有财富是进入乡村领导层的关键”。[注][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151页。关于沙井村会首占有土地面积,马若孟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附录整理的结果与杜赞其有出入,不过他同样认为“村公会成员属于该村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参见[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杜赞奇同时也指出,村庄领袖除了富有之外,还必须担当起社会责任。[注][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会首制度其实是村落内部的自治传统,会首的经济和家世背景,为一般村民所熟知,这是其权威形成的自然基础。新政权建设运动产生的村长、乡长等新制度,不过是在会首制度之上进行叠加而已。名义上,会首由村长任命,实际上,因为会首是村里有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人物,其影响力并不因村长换届而发生变化,因此即使换了村长,只要会首自己愿意,一般都会连任。实际上,村长、村副、乡长、乡副等通过选举产生的公职,很多情况下也由会首担任。换言之,村长、乡长等村落上层职位的存在,并没有改变会首主导村政的势力格局,会首制度其实是村落权力结构的核心。
基层政权的正规化和官僚化,对会首制度产生多大影响呢?以保甲制为例,根据制度规定,保甲是按照地域来划分的,十家为一甲,甲长的选任与辞退都需要村长实施并向上级报告,但实际执行中,并不会按此官僚程序办理,比如,沙井村就是先确定甲长再安排相应的甲,而甲长通常从会首中产生。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村政的内容没变化,甲长和会首的职责没有分别,这使得有产者成为担任甲长的自然人选。在访谈中,受访者经常将“甲长”与“会首”这两个概念混用,也就是说,甲长不过是会首的变相而已。实际上,沙井村的六位甲长,有四位是会首,另一位是善会的香头。*[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97-98、102、177、201、217页。石门村前任村长樊宝山曾明确指出:公会的会首即甲长、保长。也就是说,保甲制改变的仅仅是村落精英(甲长)任命的程序和他们的法律地位,并未真正改变村内的权力结构。
在权力集中于会首的情况下,就必然出现权力寻租的空间。比如在采访樊宝山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对话*[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97-98、102、177、201、217页。:
调查员:李恩是有力者吗?
樊宝山:现在是最有力的。
调查员:土地呢?
樊宝山:大约三十亩。
调查员:为何会有力?
樊宝山:儿子做保长。
调查员:何时变得有力的?
樊宝山:从去年正月儿子成为保长时开始。
调查员:村里的人很听他的话吗?
樊宝山:因为他儿子是保长,所以很听。
这段材料说明两个问题,首先,李恩之子成为保长即会首,其有产者的身份十分关键。其次,成为保长即可变得有力,在村内讲话变得有分量。也就是说,有产者获得公职,可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甚至包括牟取私利,下文将会提到,樊宝山指责李恩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李恩从庙地上取土造瓦盖房。权力寻租之普遍,亦由原沙井村司房杜祥的话得以确认,他说因为有财产的人希望神明保佑,所以很多人希望当“香头”,当香头的目的不是为村,也不是为了宗族,而是为了自己*[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97-98、102、177、201、217页。。香头即会首,只是不同概念的转化而已。杜祥的话说明村落精英其实并不回避而是积极追求公职。以上两个事例表明,公职带来的诸多利益包括经济与威望方面,不仅是普通村民的认知,而且亦为会首们所承认。事实上,杜赞奇也注意到,精英阶层控制村政,虽然有繁重的摊款和垫款的压力,但同时可以借助公职渔利和转嫁负担。在村公会权力越来越大且缺少监管的年代,会首们尤其是村长谋取私利是再方便不过的了,并由此出现了若干村落精英的贪污事件。[注][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208页。
需要说明的是,大多数情况下,会首们通过公职获得的利益是不易被一般村民察觉的,明目张胆的贪腐行为应该只限于个别人,而不能夸大为整个会首精英群体的行为。过度追求私利损害的不仅是普通村民的利益,还包括精英的群体利益,因此往往会遭到反抗。这种矛盾统一的现象其实揭示了华北村落政权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村落实行精英集体领导制;另一方面,精英会进行权力寻租,精英内部会分化。这两个因素相互影响,构成了村落权力结构的基本面相。正确理解华北村落的这两个特征,不仅有助于解读所谓的贪腐现象,而且有助于理解许多重要的学术问题,比如“村落共同体”、“国家经纪”等。
三、庙产之争:精英的分化与村落权力结构
旗田巍在梳理沙井村村公会的构成时发现,民国时期的村落政权内生于村落传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新的行政制度、赋税制度只有通过它才能得到落实。受此启发,笔者认为唯有探明村落内部的权力结构,才能真正理解村落的特质。本部分通过石门村庙产之争的个案来考察这一事件中村政权受到的挑战、精英个人立场的变化、村落精英的分化等内容,动态地展示村落权力结构实现和展开的过程。笔者选取这个个案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即它是杜赞奇、黄宗智等学者借以立论的一个重要根据,但却存在不少误读,如果不将其仔细梳理,恐难真正明白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问题。
(一) 庙产问题的产生
满铁调查员入村调查之时,围绕石门村三教寺的香火地的所有权问题,村公会与城隍庙的和尚照辉产生了纠纷,石门村村长刘万祥恳请满铁调查人员帮助解决争端。因为石门村香火地的归属问题直接影响沙井村的香火地的归属,甚至会波及当时顺义县下各村的香火地走向。另外,满铁调查人员在沙井村调查时,得到了村民的协助,相互关系极其融洽。基于上述理由,满铁调查员旗田巍等人赴沙井村,走访了相关村民,确认了石门村香火地的始末、香火地与寺庙间的关系、和尚及其合作者樊宝山的意向,并最终迫使和尚与樊宝山放弃其占有企图,香火地作为重要财源依旧归村公会管控。[注][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94-195、195、195、195、199、196页。。
该地归石门村三教寺所有,一部分在石门村内,有五块,面积分别为5亩、3亩、6亩、5亩、4亩;另一部分在沙井村内,有三块,面积分别为12亩、5亩、3亩;总计八块,都是下等地,作为“香火地”用来维持寺庙的修缮及其它活动,亦被称为“公会地”*[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94-195、195、195、195、199、196页。。民国四年(1915年)以前,此地为“黑地”,未曾纳税;民国四年土地清查后登记入册,土地执照上所有者是三教寺。税单上显示纳税人亦是三教寺。此后,这八块地的纳税及摊款未曾中断过,纳税需要保长与甲长的联名*[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94-195、195、195、195、199、196页。。
耕种这些土地的佃农都是石门村本村的村民,至于把这些土地租种给谁,通常是在保长与甲长的监督下投票决定。八块土地分别由七位佃农打理,佃农们每年向村公会缴纳地租。佃农缴纳的地租作为村公共财政来源之一,与其它收入一并记入村公所办公帐,由保长和会首管理和支配。这些收入主要用于修庙、上供烧香、沙井村学校的修缮及看青等费用*[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94-195、195、195、195、199、196页。。由此可以看出,民国四年以后,石门村三教寺的八块香火地在名义上虽然属于三教寺,但管理及纳税一直由村公会来承担,其记账方式和支出方式表明庙地是村财政的组成部分,所以村公会主张该地为本村公有财产。
与此相对,城隍庙的僧人照辉则主张,沙井村的观音寺和石门村的三教寺归县城内的城隍庙管辖,香火地应为己有*[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94-195、195、195、195、199、196页。。城隍庙与三教寺发生关系是因为清光绪后期,村里请和尚宣涵来打理寺院,但彼时宣涵未入住三教寺,而是居住在城内的城隍庙。至宣统元年(1909年)修庙为止,香火地的地租都是由宣涵收取。而当年石门村借口修庙,收回了香火地的收租权。每年由会首和乡长选定佃户、收取地租,每年向宣涵说明土地的租赁及收支情况,并将地租的一部分支付给宣涵。宣涵死后,其弟子圆洞、照辉仍继续收取部分地租。受访者称,当年石门村将庙委托给宣涵是因为其势力较大,杀过同门,无恶不作,而且与官府同流合污,村里迫于其威势不得不委托给他*[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94-195、195、195、195、199、196页。。而现今城隍庙住持照辉也是一个吸食鸦片、与女子厮混生子、打架斗殴、做尽坏事的和尚[注][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97、197、199、198页。。他和“无赖”樊宝山相互勾结,试图霸占村内的庙地。
由此,整个事件有了截然对立的双方,一方面是村公会,其代表是保甲长也即是众会首;另一方面则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和尚照辉与“无赖”樊宝山,他们要夺取村公会的土地。表面上看,事件的是非曲直是如此的分明,以至于学者往往也受到误导,将樊宝山视为民国时期村落无赖的典型。实际上如果追溯庙地产权的话,正是村公会成立后需要建立自己的财源,所以才一步步将该地收归村集体所有,并通过纳税等方式获得合法性。而樊宝山之所以卷入进来,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他与村公会会首们的关系恶化并最终被逐出村落的领导集团,换言之,村落内部的权力关系是决定事件走向和事件定性的关键因素。
(二)樊宝山与精英群体的矛盾
樊宝山祖父樊天顺、父亲樊喜都担任过会首。祖父在世时家境较殷实,有一顷多土地。至父亲樊喜这一代,因为分家,变卖了一些土地,不过他在城内开店,仍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樊宝山在民国28—29年(1939年—1940年)做过两年乡长。因此从会首的家世背景、土地数量、身居乡长之职来看,樊宝山本来都是石门村精英阶层的一份子。他之所以成为村民及其他精英的对立面,是因为在乡长任期内,利用职位之便做了很多坏事,与村民及会首们结怨已深。
在满铁人员听取樊宝山与村民交恶的经过时,现任乡长刘万祥首先讲述了樊宝山诬陷村民杨玉田的过程。杨玉田在石门村以做豆腐营生,为人耿直,不满樊宝山的不正当行为,因此遭到樊宝山怨恨。在宝山与玉田矛盾关系之间,还媒介另一村妇李刘氏。李刘氏借钱给宝山,催其还款,反遭宝山殴打,她于是哭着去县城告状,宝山在追赶时,看到玉田正在地里干活,于是让玉田拉住李刘氏,玉田未听从。为此,宝山开始诬陷玉田和李刘氏,他状告玉田是匪贼,但因为村民做证而没有得逞。后来宝山偷了枕木栽赃给李刘氏,被查出后判处6年徒刑,在北京的监狱服刑2年*[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97、197、199、198页。。宝山回乡后,以4、5亩土地为生,经济地位下降颇多。此前他做乡长时最多种过18亩庙地, 甚至退任后的1941年也租种过12亩庙地,但到1942年村公会开始投票决定庙地由谁来耕种时,宝山未被入选,反而是其对手杨玉田佃种最多,所以宝山对村公会的决定不满,开始与城隍庙的和尚勾结,欲霸占庙地*[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97、197、199、198页。。可以说,樊宝山走上与村公会对立的道路,其实是肇始于与普通村民的恩怨,连续的诉讼与牢狱之灾,使得他已经不能获得村公会精英群体的信任了,所以他们对他投了反对票,当然,樊宝山也不甘失去种种利益。
民国32年(1943年)11月29日,樊宝山带领城隍庙和尚照辉及雇工来到村内,欲在土地边上埋石头作标记。会首们集合与宝山及照辉进行了交涉,双方就土地所有权进行了激烈争论。由于村民与会首的强烈反对,樊宝山及照辉等人未能如愿以偿。第二天宝山从石门村雇用了二人,偷偷地埋了界石。村里叫来了警察,并向爱护村事务所和分所提出了状告。
根据调查员对石门村乡长刘万祥的访谈,樊宝山“有手段,谁也不是他对手。平时打架的时候,他都会站在中间把事情闹大,有从两边获取钱财的毛病”,仅满铁人员采访时的1943年,他已经在村里惹了四、五起事件了,刘万祥举了其中一个事例,村里有曹氏兄弟分家,都主张院子中间的篱笆是自己的,争执不下,“保长和甲长在中间调解也未解决,最后决定以保长“二人平分”的意见来解决。”偏偏樊宝山建议双方诉诸公堂,刘万祥调解未果,而樊宝山则通过代理诉讼获利。在这个事件中,保甲长、村长等人调解无效,颜面尽失,也因此加深了与樊宝山的矛盾。在刘万祥讲述宝山这些恶行时,流露出仅他一个人不愿意说的态度,他让保长李有功也来讲述。在满铁调查人员的劝说下,李有功讲述了当年宝山恶行的两件事:一件是唆使村民诬告某甲长;另一件事是宝山以居中调停为手段骗取村民钱财*[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97、197、199、198页。:
本村杜忠有6亩土地,与本村的李荫村伙种,商定每亩4斗收成交杜。但到了交租的时候,杜说大斗,李说小斗(新斗),二者产生分歧。宝山和杜是亲戚,进来调解。另外杜还委托了车站工务段的刘殿升。在纠缠不清时找保长、甲长调解,在保长、甲长的调解下,最后双方以每亩3大斗达成协议。此前因为李荫村已经按每亩交租两大斗,剩下共每亩一大斗,所以还应该再交6大斗。但是,李荫村说生活困难请求只交5斗,杜和刘殿升也同意了。但是唯有宝山坚决主张把剩下的一斗也交上。另外,杜说借给李130元钱,李说没有借。最终,李拿出130元钱交给了宝山。宝山拿到钱后,全部用光,还说要告李荫村一大斗粮租未交。保长丢了面子,对宝山说:“要告的话,不要告李,你就告我吧”。后来,刘殿升在宝山和保长间调解,让宝山停止了上告。但那130元钱就这样被宝山拿了。
在这件事情上,保甲长是被请来调解矛盾的,而且成功地使纠纷双方达成了减免佃租的协议。但宝山对这一结果不承认,坚持要求李某补交佃租,他损害的不仅是村民的利益,而且完全不顾及保长、甲长的情面,甚至连他们也告上法庭,从而与大多数社首对峙起来。从时间上判断,宝山的行为如此乖张,当是源自1942年村公会决定不再把庙地租给他之后,因此才处处与诸会首为敌。经过这样几件事情之后,樊宝山差不多得罪了本村所有的精英,从而与精英控制的村公会站到了对立面。
(三)樊宝山的立场及问题之解决
鉴于樊宝山与本村精英结怨已深,庙地之争已无和解的可能,于是村民们在11月30日午后开会,推举乡长刘万祥和会首杨永芳为代表,来到沙井村向满铁调查人员寻求帮助。满铁人员委托县顾问通过第一分所,把和尚照辉叫到县公署,询问了庙地与城隍庙的渊源、城隍庙争取庙地的理由等[注][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98、201、201、202-203、203、210页。。另外,满铁人员还听取了宝山的意见,以及他与保长李有功的父亲李恩的过结*[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98、201、201、202-203、203、210页。:
樊宝山:李恩在村里有权势,和他打官司,我一定成为坏人。庙地是上等地还能收获庄稼,但他仍在庙地取土烧瓦。李恩也挖,大家也挖。我并不想要,但是庙地被毁坏让人困惑。
调查员:你和李恩关系不好吧?
樊宝山:过去挺好,我从开始公会的工作后,关系不好了。我父亲也是会首,我也是会首。所以不做乡长后也有保护庙产的义务。从我阻止李恩取土开始,我们的关系不好了。
调查员:今后再不打算与这件事牵连在一起了吧?
樊宝山:无论是和尚管理还是公会管理,不在庙地取土就行。过去我状告李恩,因为没钱进行民事诉讼,我完全是为了村里着想。
调查员:那时候村民为什么未站在你这一边?
樊宝山:村里人都利己心很强,李恩胜了,可以自由取土。土可以当肥料和炼瓦。我不从庙地挖土,是因为良心过意不去。即使不用庙地的土,在别处有官土坑,可以在那取土。
樊宝山的话其实揭示了村落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村公会土地获益的不仅是他自己,还包括他的反对者即其他村落领袖,换言之,是否牟利并不是樊宝山的真正问题。樊宝山以其祖父曾集资修庙、购地为由,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祖上留下的土地”。满铁调查人员确认了宝山的意图后,劝他说:“你还在缓刑释放期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对你不利,你还是停手吧!”*[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98、201、201、202-203、203、210页。。在满铁人员的规劝下,宝山决定退出庙地的纷争。而对于照辉展示的石门村和沙井村的“请帐”,满铁调查人员就此向县顾问进行了说明,县顾问建议满铁调查人员请教承审员张家宝,张家宝就两村的请帐问题做了答复,他认为“请帐”因为没有获得县里的行政许可,所以不能成为证据;和尚如果每年继续接受三十元,则不能借此寻衅、讹诈;同时村里若要终止委托关系,也必须向县里申请*[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98、201、201、202-203、203、210页。。承审员的意见反馈到县顾问后,县顾问对照辉进行了斥责并威胁要将其赶出本县。最终,照辉放弃了对石门村土地的主张,县顾问让其出具誓约书,承认“该庙之土地,本石门村公会之产业,向与城隍庙无涉,今已悔悟,此后决不参与,任凭石门村会首等如何处置该地,自己决不干涉”*[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98、201、201、202-203、203、210页。。
对于这个案例的误读存在若干方面,首先,杜赞奇说是“村中恶霸与衙门营利型经纪勾结起来将其魔爪深入村庄权力结构之后,围绕文化网络而建立的村庄权力体系则显得何等的无能为力。”而案例中,村庄权力体系并非无能无力,会首们在处理村民纠纷、代表村民诉讼、保护公共土地上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村政权并没有失去其权威。实际上,村公会对土地的控制,其实得到了政府、法律专家、满铁、本村居民等各方的支持。而樊宝山此时是一个被村政权排斥的人,并且也无意再竞选公职,因此并无所谓“将其魔爪深入权力结构”的问题。
其次,杜赞奇认为樊宝山与衙门营利型经纪勾结,他多次提到这一点:“村民不愿将此争端告到县衙,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那些地痞恶棍们的对手”;“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开辟利源,使国家政权进一步深入乡村,它必然会加速村中土豪与衙门恶役的联合”;“大部分新领导还是依靠与县、区的国家经纪的联系来获得权威的”,并举樊宝山与衙役勾结为例*[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198、201、201、202-203、203、210页。。可实际上,民国时被边缘化的城隍庙僧人根本不能算是衙门营利型经纪。樊宝山之前屡次唆讼无非是利用了村民害怕诉讼的心理,并不能说明他在衙门中有后台,所谓“衙门恶役”所指显然不实,没有证据显示他曾受到任何国家经纪的帮助。类似地,黄宗智认为沙井村内部分化导致村落共同体解体之后,“易受外来势力的欺压摆布”并以樊宝山为例,但很明显樊宝山并不是“外来势力”。[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7-278、277-278页。
再次,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案例中看不到明显的国家政权建设带来的影响,黄宗智在解释这件事的时候认为,由于日本当局企图通过保甲制、大乡制控制自然村,“沙井原有的首事,没有一个出任新乡长之职”,结果使得“流氓”樊宝山窃取了乡长一职。*[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7-278、277-278页。实际上这一点并无资料佐证,樊宝山与村民及其他精英的纠纷,全部是因为私人恩怨、处事不周、故意为难或其它经济上的矛盾,并非出于樊宝山侵吞公款、转嫁税收等这些“政权建设”带来的问题;而他对庙产的主张,也只是想夺取佃种权而已,而且当时已经没有公职,与利用公职中饱私囊有根本区别。因此把樊宝山作为“营利型经纪”的案例,模糊了他与村民和村公会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有偷换概念之嫌;而用这一案例进一步证明“国家政权建设”对村落权力结构带来的冲击,则完全是过度解读,缺乏证据支持。
石门村的个案具有学术对话的意义,它表明村公会成立并形成自己的财产,而村落精英是一个以村公会为中心的群体,有其自身的整体利益;而作为村落精英一份子的樊宝山,经过一系列的事件,逐渐走上与整个精英群体对立的道路,并最终被排斥出村政权。在村庄权力关系的游戏中,樊宝山是个失败者。换言之,村落内部的权力关系(而不是外在的因素)是导致受排斥的“营利型经纪”存在的主要原因。
四、其它满铁村落的国家经纪问题
满铁调查的村落分布在河北和山东等省,这些村落的社会结构、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面临的摊款压力都不一样,因此读者完全有理由质疑个案研究的有效性与结论的普遍性。杜赞奇为了证明1930年代开始“营利型经纪”占据村政权,对这几个村落逐一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比对。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就满铁调查诸村的基本情况进行逐一检视,以扩大本文的证据基础。我们所用的方法与前文一样,即坚持村落“精英”概念的一贯性,并对精英与村政、公职的关系进行严格审视。
河北栾城县寺北柴村从清代到1938年一直有内生的行政机构“董事会”,后来的闾邻制和保甲制,不过是在董事会的基础上增加成员而已;董事们土地众多,又会读书写字,决定村庄事务并挑选村长。[注][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担任村长长达14年的张乐卿,非常富有,本来有80多亩地,虽然后来出于垫付摊款、以及为兄弟的饭馆填补亏空等原因抵押出去48亩,但与一般村民比较,仍占有很多土地,他一直担任村长到1930年代末。[注][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4、166-167、164-166页。显然,寺北柴的村政仍然是村落精英控制的。
至于山东平原县后夏寨,1922—1937年间,先后由富户李仆与最大的地主王保垣担任庄长,1937年之后,由于摊款频繁,无人愿意充任此职,所以4年之间换了6任庄长。杜赞奇没告诉我们这些短暂接替的庄长是否是富户,假如是,则不能证明精英退出政权。除了庄长之外的公职人员,比如牌长和首事则全是村中最富有的人家;取而代之的甲长,杜赞奇说“由于资料不足,无法断定这些甲长是来自村中的上层还是下层人家”。*[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4、166-167、164-166页。笔者完全认可村落精英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但这两个案例既不能证明村落精英退出村落政权,也不能证明公职为营利型经纪所占有。
河北良乡的吴店村,因为受到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的影响,军队勒索严重,富裕的村落精英逃离了农村。1940年代前后,赵风林、张启伦先后担任村长,二人都因贪污亩捐被拘留,传讯到县,他交还赃款后,继续担任村长。*[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4、166-167、164-166页。这条资料虽然可以作为存在营利型经纪的证据,但是疑问仍然存在:第一,赵、张二人的土地多不多?假如土地多,那么他们就属于精英阶层,则所谓精英阶层退出政权就有问题;第二,吴店村的其他有公职的人,比如那些保甲长,是否为土地众多者?假如土地多,那么也不能证明精英阶层退出政权。因为逃离村落的不可能是所有的村落精英,一定会有很多精英留下来担任公职。如果这两点都得到确认的话,那么杜赞奇的观点不能成立。
山东历城县冷水沟在1928年之前,担任八段首事的人都非常富有,土地在20—80亩之间,人均52.5亩。1929—1939年之间,此前的8位首事人皆不再担任闾长,而新任的14位闾长的平均财富减少为人均24.1亩,一是因为与其它村落相比,冷水沟是相对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平均土地数字不高,而人数的增加也会拉低平均数,即便是这个数字,仍然比全村户均11.2亩要高出一倍以上,毕竟当时2/3的村民只有不超过10亩的土地。[注][日]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四卷,岩波书店1955年版,第1、6页。因此大部分担任公职的人仍然属于相对富裕的人群。在一个相对平均的社会里,普通村民担任公职的可能性会稍大,冷水沟村就有两位闾邻长的土地低于10亩。与此同时,1928年普通村民杜凤山担任村长,积极替村民办好事,赢得村民信任。杜赞奇认为这是“乡村精英‘隐退’之后,普通村民可以利用“公职”来提高自己在村中的地位”,并认为这种情况很少,必须视为例外。这个例子对杜赞奇不利的地方是,首先,在冷水沟担任大部分公职的仍然是相对富裕的精英群体,他们并未退出村政,并没有“隐退”;其次,占据庄长之位的杜凤山虽然不属于精英阶层,但他并不是营利型经纪。
河北蓟县侯家营的情况则更为明显,1914—1942年历任村长、村副的资料显示,他们的土地并未减少,土地皆在60—170亩之间,而1928—1929年的几位会首,土地最少的也有20亩,多者50—100亩。杜赞奇因此说:“可以说在民国时大部分‘精英’以会头或村长副身份参与村政。与其它村庄不同,侯家营的‘精英’们尚无意从村政中退出。”也就是说,在侯家营,地方精英自始至终都是村政的直接控制者。侯家营精英对村政的主导的另一个表现是精英集体领导体制的强大。1930年代初,有80亩土地的侯大生任村长,他蔑视村会头的决定,滥用存款,结果村中10个有影响力的人联名到县衙告他,侯大生被迫辞职。被问到这10人是否有地位,回答者说“他们土地多,是村中有才能有势力的人。由于他们地多,所以,不论村中有什么开销,他们都得拿大头。他们对此十分反感,所以要告倒侯大生。”反对者中包括两次担任村长的刘子馨(有土地170亩)。“刘的继任者也非常富有,但在老会头们看来,他只是大乡乡长的‘走狗’而已”。[注][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207-208页。无论是村长侯大生,还是刘子馨的继任者,他们是营利型经纪,但同时也都是村落的精英,他们追求公职的目的本来就是为自己打算。但是他们过分追求私利的结果,损害了精英群体的整体利益,以至于遭到精英们的激烈反对。
通过沙井村、石门村的个案,以及对河北、山东的五个村庄资料的分析,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这些村落都是精英的集体领导制,因此,在分析乡村政权由谁“控制”的时候,不能仅仅考虑某个职位(比如村长),而应该将会首等人也纳入考量。杜赞奇注意到了会首或保甲长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他们是村政权的重要部分,不过在论述过程中,却又有意无意地淡化其角色,比如在侯家营的事例中,他虽然强调了村长的贪污行径,以作为“营利型经纪”控制村政的例证,但事实上不是整个村公职群体都沦为“营利型经纪”,村长的逐利行为受到其它决策层的反对。而本文研究的石门村的例子,肆无忌惮的乡长樊宝山更是身陷囹圄,这也说明庄长并不能完全主导村政。
第二,大多数有公职的人一直都是村落的精英,最主要是有产者,他们从清末到满铁调查的1940年代初,不仅没有退出权力架构,反而一直都在控制着村政。在村政权形成、演变的过程中,以有产者为代表的精英阶层一直都扮演着领袖作用,随着村政权的职责范围越来越广,他们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杜赞奇在证明精英阶层退出村政权的时候,其所用的事例往往是1930年代末个别富户不愿意担当公职或迁出村落,但是他忽略的是:填补职位空缺的,仍然是村里的有产者,尽管不一定是最富裕的家户。在满铁调查的村落中,只有冷水沟庄长杜凤山是“普通村民”,其它各村并没有这样的现象,同时冷水沟村的其他保甲长仍然是村里的富户。事实上,杜赞奇也注意到,精英阶层控制村政,虽然有繁重的摊款和垫款的压力,但同时可以借助公职谋取私利,转嫁负担。*[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207-208页。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不一定需要躲避公职。
第三,营利型经纪和精英阶层不是对立的概念。因为精英阶层追求公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自然也会从村政中谋取私利;而一旦出现损害利益者,他们会团结起来将其驱逐出权力架构。在利益调整的过程中,村庄领袖由于利益分歧而分裂,“保护型经纪”与“营利型经纪”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从村落获得经济利益,而是在于他们与村民及其他村落领袖的关系相处得如何,那些与村民交恶的领袖——尤其是在此过程中,得罪了其他精英的——被排斥出村政权,而各种关系处理比较妥当的则会继续留在村政权之内。因为“营利型经纪”在大多数时候来源于精英阶层,因此杜赞奇采用的“土豪”、“地痞”、“恶棍”、“无赖”、“走狗”等词语,可能模糊了“营利型经纪”的阶层属性以及这个概念的真正问题。[注]村落权力斗争中,双方使用这些污名化的标签,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利用国民党打击土豪劣绅的政治话语,参考李怀印对获鹿县上庄的研究,参见[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晴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69-273页。
五、结语
村政权的出现是清末民国以来中国基层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它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各种税收、摊款的压力。它往往从民间的宗教组织发展而来,并进而整合了村庄的其它职能,比如看青和其它公共事务,从而成为具有各种职能和资源的政治组织。随着其职能范围的扩大,村政权的权力也越来越大。近代的村政权虽然受到邻闾制、保甲制、大乡制的影响,但实际发挥影响力的,仍然是根植于村落传统的村公会(或“董事会”,甚至更简单的“会”),村公会负责协调村落内部的利益关系,并因地制宜地执行各种新政,它的相对独立性减弱了外部严峻的环境对村庄的冲击。[注]比如,摊派的对象往往是村落,它使得普通村民不必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参见[日]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理论》,第249-262页;关于民国的乡村精英和市镇精英对各种捐税差徭的抗拒,参见[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晴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30-245页。它使得村落具有了古代没有的那种团体性质,如果没有它的出现与演变,“村落共同体”也就无从产生,更无从发展出成员意识了。
与村公会的地位相对应,主导村政权的是一个以有产者为主的精英群体即“会首”(或“董事”、“会头”、“在会的人”),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来自于家庭声望以及更重要的土地财产,他们是村落内生的领导群体。当然,受到新政改造基层行政组织的影响,村落精英又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职位类型,比如选举出的乡长、乡副、村长、村副,比如以户为基础的闾邻长和保甲长等。而实际上,他们是同一个阶层即有产者,这群精英阶层共同主导村政,实行集体领导制。当然精英阶层会分化,权力斗争在所难免,不过,个别“营利型经纪”的存在,丝毫无损根深蒂固的村落精英政治。这种精英政治伴随着村政权的出现而出现,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
民国时期的华北村落政权包含一定的民主因素,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基层民主。它的民主仅局限于精英阶层内部,而并不包含普通村民。在某些情况下,村民虽然享有一定范围的选举权,但具体的行政过程完全与他们无关,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小圈子决策的结果。鉴于此,如果内生的村落政权继续维持它的超强适应性,如果基于土地占有的精英政治得不到改变,那么不仅各种新政的实施要大打折扣,而且下层村民参政议政的可能性也难以得到拓展。也因此,1949年以后共产党在农村推行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才具有如此巨大的颠覆性。土改改变了村落内部的资源分配,土改后,“广大贫下中农不仅是经济上的获利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得权者……国家治理村庄的重要社会基础得以形成。”[注]林聚任、解玉喜、杨善民等著:《一个北方村落的百年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228页。华北的乡村社会也由此得到了根本的改造。
——基于FPS游戏《穿越火线》战队公会的网络诈骗行为研究
——以FPS游戏《穿越火线》战队公会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