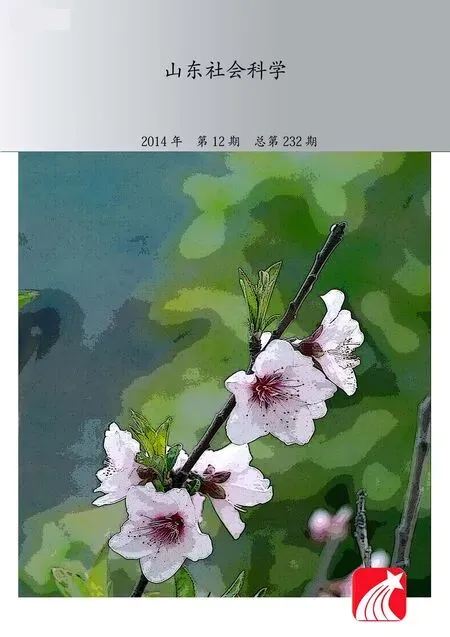如何营救丁玲:跨国文学史的个案研究
苏真撰 熊鹰译
(芝加哥大学,美国 芝加哥 60637 ;柏林自由大学,德国 柏林 D-14195)
本文旨在再现一段1930年代初国民党囚禁丁玲的历史。丁玲的被捕成为国民党镇压上海左翼人士即“白色恐怖”的转折点,中美的许多学者都已谈到了丁玲被捕以及这段白色恐怖的历史。这些研究指出,丁玲的被捕引发了中国左翼人士的抗议和愤怒,也打破了中国公众的沉默。*英语相关的研究有 T.A. Hsia, Enigma of the Five Martyrs: A Study of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1962) 和 Charles Albert, Enduring the Revolution: Ding Ling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 in Guomindang China (Praeger, Westport CT: 2002).丁玲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她的被捕也因此在作家和普通民众中唤起了强烈的同情。大家认为她是国民党全面控制下的一个牺牲品,丁玲也因此成为左翼人士反对政治迫害所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中的政治标杆。同时,丁玲与包括茅盾和鲁迅在内的知名作家的个人交往也使得她的被捕在左翼知识分子对抗国民党政府的运动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丁玲的被捕以及与之相关的公众舆论在30年代中期上海所涌现的左翼政治与文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上的叙述已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历史研究者所熟知,而我想提供的却是另一个不同的叙述:我将丁玲的被捕看作一个全球或“跨国”事件,它所具有的深刻国际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中国。下文我会证明,丁玲事件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它还波及了包括苏联、西欧和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通过当时的美国记者及小说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丁玲的近况尤其引起了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关心。我认为丁玲的被捕是一个国内事件,也是一个国际事件;国内和国际层面间展开了重要的对话,它们互为支持。美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对上海的左翼联盟感到震惊并为之感动,他们也全情投入了为争取丁玲释放所展开的抗争。就这样,丁玲事件变成了一个超越文化边界的国际“诉讼案”。
本文希望通过丁玲的例子探讨30年代“跨太平洋”文化战线( “trans-Pacific” Cultural Front)这个想法。丁玲的被捕激发了中国与美国左翼作家间的一系列合作,他们致力于在30年代初中国的实现“言论自由”、“民权”和“民主”。这是一段重要的历史,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一段中美文化敌对之前的历史:在冷战开始前、在“民主美国”与“共产中国”的对立开始前,曾有那么一段短暂的友好交往。美国和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放宽了“民主”的边界,他们看到了能在他们各自文化间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实现“人类平等”这一共同目标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可以自由交换思想的中美文学公共空间。更重要的是,中美左翼知识分子间的这些合作促生了对“民主”这一政治文化概念的跨国反思。尽管我们今天常常将“民主”看作一种西方的范畴,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都要吸收和学习这一西方范畴,当时的史沫特莱和宋庆龄却大胆地尝试在跨文化交流中重新思考这一概念。“民主”并不一定非是一个从西方引介到东方的“西方概念”。简而言之,30年代初期见证了中美政治和文化交往中从未有过的激动人心的时刻,而丁玲事件为此作出了最好的诠证。
同时,本文还提出一个方法论上的尝试,即用文学与历史的“跨国”视角来叙述丁玲在全球范围内的接受历史。这就意味着我要使用英语和中文的材料、美国和中国的不同档案,并且要将它们重新组合。尽管,作为事件中心人物的中国作家居住在中国,为了描述这段历史我所参阅的大部分档案却都在美国。我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方法论方面,有些看起来是地方的或者中国的事件其实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们对一些看起来很遥远的地方,例如纽约或者华盛顿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在中国以外的档案中努力寻找历史的踪迹,我们才能重新发现许多中国历史文化事件的全球重要性。因此,在我叙述这段历史的同时,我也想仔细地描述我所寻访过的各种档案材料(大部分在美国)。这样一来,有兴趣的学者可以知道它们的存在,并在他们未来的研究中更好地使用这些档案资料。
一、白色恐怖在美国的反响
美国的知识界对中国左翼政治和文化的关心可以追溯到20年代中期。例如,著名的杂志《劳工保卫者》(TheLaborDefender)在1927年发表了3篇有关中国的文章,1928年又发表了9篇。与中国相关的文章与日俱增,1932和1933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9篇,达到了一个发表的高潮。[注]The Labor Defender: “China in Revolt,” 1927年3月,第38页;“China Surges Forward,” 1927年5月,第68页; “Hands of China,” 1927年7月,第103页。30年代初期,以中国为焦点的文章也出现在《新共和国》(TheNewRepublic)这样的主流期刊上。[注]例如 Agnes Smedley, “Shanghai Episode,” The New Republic, 1934年6月13日。
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上海以及中国南部的劳工问题和左翼抗争上。例如,1930年史沫特莱为《新共和国》撰写的文章题为《中国的农民和地主》。该文仔细描述了长江沿岸出现的“土地左翼”(agrarian-leftist)社会运动。史沫特莱认为,这一运动的出现预示着一种更广泛的反对国民统治的运动。[注]Agnes Smedley, “Peasants and Lords in China,” in Th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3, 1930), pp. 69-71.随着30年代的推进,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美国杂志对中国劳工政治问题日益增加的兴趣。中国开始“热”起来了。上海的劳工积极分子,例如30年代末被国民政府处决的黄平,成为美国迈克·高德(Mike Gold,1894—1967)和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1901—1982)等左翼知识分子的英雄偶像。或许,美国支持中国劳工激进分子最令人吃惊的例子便是,1931年的纽约,西奥多·德莱赛 (Theodore Dresier,1871—1945) 等一大群美国工人和作家走上街头抗议国民党杀害6位中国作家。[注]这一事件在1931年8月的《新大众》(The New Masses)上进行了报道。 联盟在7月15日组织抗议活动。
美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为什么对中国如此感兴趣?作家们,例如迈克·高德, 在中国似乎看到了美国政治和经济继续恶化后可能出现的样子。在美国,劳工运动和左翼的反对声音早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伊始就出现了。股票市场于1929年崩溃,并引发经济大萧条,这一切又在1931年的美国政治和文化中激发了大规模的左翼和社会主义力量。这场运动最有力的表率便是30年代的“文化战线”了。“文化战线”不分性别、不分种族地凝结了所有想要通过劳工平等和重新分配财富来改造美国社会的工人、职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都坚信文化的力量,坚信文化运动可以帮助他们实现目标。尽管这一社会运动一部分是因为受到了苏联国际主义的启发,美国的学者认为文化战线运动主要是吸收了美国当地的思想资源。[注]更多有关美国文化战线运动的研究, 参见 Alan Wald, Exiles from a Future Time: the Forging of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Literary Left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2003) 以及Michael Denning, The Cultural Front (Verso, London: 1997).美国历史将铭记30年代,因为它是第一次——可能也是仅有的一次——社会主义占据美国社会的主流。
虽然美国的激进分子面临着严酷的政治打击和各种困难,但是中国的“白色恐怖”更为惨烈。美国左翼所担心的那可能在美国发生的一切,例如对激进思想和言论的暴力镇压,已经变成了上海活生生的现实。《新大众》的编辑每周都能读到有关中国作家被国民党杀害的报道。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写作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美国的情况虽然不好,但远不及上海恶劣。因此德莱赛和史沫特莱等美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案例,可以借此探讨世界范围内的左翼和劳工运动。 一方面,上海的政治迫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另一方面,对政治迫害的反抗也达到了顶点。美国的激进分子们为鲁迅、丁玲、茅盾以及其他众多挺身而出面对暴力政府的中国作家所打动,也想在中国的左翼抵抗经验中吸取经验。
我们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寄给美国左翼领军杂志《新大众》的一系列信件为例。1931年1月,左翼作家联盟寄出了一份“来自中国作家的通信”,该信作为社论刊登。在这封信中,中国作家告诉美国左翼知识分子中国正在经历的政治危机以及正在大行其道的“白色恐怖”:“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正在使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革命文化运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希望揭露国民党的暴行能够激发美国左翼人士的同情,并在他们那儿寻得援助。信中说,“我们需要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支持。我们呼吁世界各地的同仁给予我们任何可能的帮助,公开中国的革命斗争,和我们一起反抗那些支持中国反动势力的帝国主义力量,迫使他们从中国撤走。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支持,面对革命工人和农民的抵抗,国民党连一个月也抗不住。”[注]“From the Writers of China”, The New Masses (January 1931).1931年6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又寄去一封信,再次作为《新大众》的社论刊出。该信唤起了美国读者对发生在上海的“白色恐怖”的记忆。信里说“白色恐怖”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越演越烈。左翼作家联盟还仔细描述了国民政府如何处决了几位成员,“白色恐怖已经影响了中国革命的文化领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已经失去了许多成员。许多作家被判三到七年的监禁,狱中的情况极差,他们往往在狱中囚禁几个月后就牺牲了。他们身受镣铐,在中国黑暗封建的监狱里等死,或是在外国租借的审讯房里倍受折磨。”[注]“A Letter to the World: An Appeal from the Writers of China” , The New Masses (June 1931).《新大众》的编辑们配合着照片刊出了被国民党杀害的“五烈士”的生平介绍。
到30年代中期,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寄来的报道已经在《新大众》、《新共和国》和《工人日报》(TheDailyWorker)等报纸期刊上司空见惯了。从谈论中国文学到中国政治和社会,许多文章在这些拥有广大读者且代表美国智识中心的杂志上定期刊登。美国的读者,尤其是那些隶属于左翼的读者,非常了解中国以及中国的政治危机。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主要由伊罗生(Harold Isaacs,1910—1986)、史沫特莱和斯诺(Edgar Snow,1905—1972)等20年代就移居中国且对中国左翼运动报以同情的美国国际主义者在其中穿针引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形式的中美文化交流和以前的诸种交流不同:以前的交流往往更多地在农业发展领域,或者是留学交换,而如今的交流却在和自由相关的言论空间中展开。比如说,20年代中期,许多美国的农业学家到南京,和当地的中国工人一起组队,意图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赛珍珠就是当时的随行团员之一)。又例如,许多中国留学生利用庚子赔款远赴哈佛和哥伦比亚求学,膜拜实用主义等美国政治和社会理想。[注]详情参见 Randall Stross, The Stubborn Earth: 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 1898—193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1986); James Thomson Jr.,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69). 有关庚子赔款和中国留学生参见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1986); Jerome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70).与此不同,我们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新大众》的交往中看到的是一种独特的中美左翼文学的交流与接触。
在接下去的篇幅里,我会讨论这种中美交流或“跨太平洋文化战线”的主要思想和文本。我的主要论点是:这种交流非常特殊且重要,因为我们习惯性地以“苏联国际主义”来理解30年代美国和中国的激进主义,而它却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虽然在美国和中国,左翼运动的兴起是由于苏联的组织和动员,但是在中美激进分子接触以后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自主的国际主义左翼思想。我认为有许多思想并非仅仅来源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有着更丰富的形成历史。中国和美国在30年代都处于苏联和欧洲政治文化思想传统影响的边缘,因此,他们可以创造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概念的新谱系。也正因为如此,跨太平洋联系尤其吸引人。中美的左翼知识分子找到了共识,发现了一个既可行又具有创造性的综合思考模式。
二、如何营救丁玲:一场政治考验
在这一节中,我将要着眼于跨太平洋文化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具体例子:丁玲的被捕以及中美知识分子为了公开其被国民党囚禁的事实所做的种种努力。我认为这一案例促进了中美左翼知识分子一系列交流活动的展开。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它加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新大众》间的合作 。丁玲事件成了一个关键点,它使得跨太平洋文化战线得以组织起来。
当时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小说家及新闻记者史沫特莱成了中美左翼交流的主要组织者。在美国的文学和历史上,史沫特莱因其小说《大地的女儿》而广为人知。该小说描写了她如何在美国中西部长大,如何在1910年代后期迁往纽约,并在20年代后期成为一个政治激进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该小说被认为是美国普罗文学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在纽约,史沫特莱和诸如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1879—1966) 、德莱赛等许多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积极分子成为朋友。她还成了一个全职的记者,为《新共和国》和《新大众》等杂志写稿。她是20年代后期美国左翼政治和早期普罗运动中(proletarian movement)的关键人物,还参与了南亚企图推翻印度的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加达运动(Ghadar movement)。在德国短居以后,1929年史沫特莱决定前往上海亲身体验一下中国左翼运动,希望吸收东方和西方的经验以加深自己对左翼政治的理解。[注]有关史沫特莱生平,参见J.R. and S.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Virago, London: 1988) 以及 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5)
史沫特莱1930年初到达上海后很快就投身于中国蓬勃发展的左翼文学运动。通过美国朋友伊罗生的帮助她接触到了鲁迅、丁玲和茅盾等中国知识分子,并和他们成为好朋友。鲁迅曾阅读过史沫特莱的小说《大地的女儿》的中文译本,十分欣赏。尽管史沫特莱不能说中文,她仍然以非正式的“外国”成员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也很尊敬她。在茅盾的帮助下,史沫特莱曾在1931年的上海筹办过鲁迅50岁的生日寿宴。1931年,“白色恐怖”业已吞噬上海。由于史沫特莱本人曾饱受美国政府打压言论自由之苦(1910年,她曾因煽动言论罪在纽约被捕),她对左翼作家联盟抵抗国民政府的运动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1931年7月,当白莽、柔石、冯铿、李伟森、胡也频五位左翼作家被国民党逮捕并杀害时(这五位作家被左翼作家联盟追认为“五烈士”,上海的公众也开始表达对左翼知识界的同情),史沫特莱非常难过,她通过她的朋友丁玲认识了胡也频,而柔石又是鲁迅的学生。[注]更多细节见 T.A. Hsia, Enigma of the Five Martyrs: A Study of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史沫特莱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反抗白色恐怖的努力在丁玲1932年5月14日被上海警察秘密绑架和逮捕后真正显示出了成效, 因为她将丁玲视为挚友。[注]更多详情参见Tani Barlow, “Introduction,” in I Myself an Woman: 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edited by Barlow (Beacon Press, Boston MA: 1989).史沫特莱很快在这次危机中看到了机会。尽管“五烈士”的被杀是民族悲剧,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仍是新兴的年轻作家,不十分熟悉。相反,丁玲却已经是知名的作家,拥有众多读者,她在美国和苏联也都建立起了国际声望。正如1931年初由中国作家寄送《新大众》的各种信件所表明的那样,“五烈士”被杀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确吸引了一些国际注意。但是,这还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舆论力量迫使国民政府释放丁玲。作为一个受人爱戴的作家、一个富有魅力的女性,丁玲会在国内外的读者中赢得广泛的支持和同情。事实上,“五烈士”证明中国能在公民自由问题上获得国际援助。但是史沫特莱认为,这一运动能够通过丁玲的被捕获到更好的效果,这能更有效地打击国民党的势力。在美国期间,史沫特莱就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网络,她立刻通过该网络向美国的朋友们公布了丁玲被捕的消息。
接下来,我要谈一下史沫特莱如何说服美国的左翼人士,特别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来反对国民党囚禁丁玲并要求立即释放。史沫特莱首先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发去电报通告了丁玲的被捕,并要求自由联盟公开谴责国民党践踏公民权利的行径。她的一个潜在论点是“公民自由”代表了一项基本的人权,自由联盟的职责便是要捍卫美国以至全世界的公民权。史沫特莱的努力很快就遭遇了挫折。虽然自由联盟的许多著名成员,例如弗兰克(Waldo Frank,1889—1967)很同情史沫特莱,但是整体而言,由于许多实际的和理念的因素,自由联盟对介入国际事务持保留态度。例如,著名的律师和自由言论倡导者哈普古德 (Norman Hapgood,1868—1937)就拒绝在鲍德温(Roger Baldwin,1884—1981)牵头的公开请愿书上签名,他说他不想把“公民权利”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强加给中国。尽管鲍德温反驳道:“对中国左翼的迫害是如此的明白,从我们反对压制公民权利的基本立场而言,这个迫害发生在哪里并不重要”, 哈普古德和其他的一些成员仍未被说服。[注]“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Political Prisoners, Records: 1918—1942,” at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Manuscripts Divisions. New York City, NY. Box 2, Folder 4. 哈普古德1933年3月致鲍德温的信。史沫特莱对此的回复使得争论更为激烈。哈普古德完全没有能力招架这么一位坚定的辩论者。史沫特莱回复说:
尽管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是一个美国的组织,我们面对的事件却具有国际影响力,因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完全应该干涉。那些曾经参与在中国建立外国租借的美国人要为中国今天的白色恐怖以及逮捕、囚禁和杀害成千上万的中国政治犯负直接责任。上海的国际租借是由各国势力共同管辖的,而其中便有美国。美国官员在上海市政府和国民党特务一起携手制造了白色恐怖,美国的商人和银行家们也同意让主要针对中国普通大众的国民党军队进入上海。 美国的保卫公民自由运动无论如何都不能仅仅局限于美国,它必须深入中国的心脏。由于中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支持南京政府的正是华盛顿的美国政府、资本家和银行家,将活动延伸到中国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使命所在。[注]“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Political Prisoners, Records: 1918—1942,” at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Manuscripts Divisions. New York City, NY. Box 2, Folder 4. 史沫特莱1934年5月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信。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声明。和当今的政治情况正好相反,史沫特莱认为政治要紧跟着经济,而不是如我们今天所设想的那样经济要追随政治。上海乃至于中国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她被包括德国和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势力瓜分,不幸沦为半殖民地。美国在中国虽没有正式的殖民地,但支持在中国获取经济利益,施行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政策,用外国资本重塑当地市场。史沫特莱指出了这个将美国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市场的存在。正因为这种联系的存在,美国有义务要促进——而不是扰乱——诸如民主这种由经济发展引发的新型政府管理形式。资本主义将美国卷入了一张包携上海的网络,美国不能中途放弃她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民权和民主的坚持。因而,这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对中国应尽的义务。
史沫特莱向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发出呼吁时正值联盟的转变时期。在经历了近10年的节节后退之后,自由联盟取得了包括猴子公案(Scopes Monkey Trial)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案件的胜利,终于在30年代初期开始蓬勃发展。[注]Samuel Walker, In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Carbondale, IL: 1990), pp. 103-104.像节育运动等美国社会的变化以及美国文化中的一些新变化都使得美国能更宽容地对待言论自由权。正如Judy Kutulas所写的那样,公民权利突然就流行起来了。[注]Judy Kutulas,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eralism, 1930-1960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NC: 2006), p. 3.舆论的胜利必定意味着政治权利中心的变化:曾经对政府持敌对态度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突然在罗斯福新政中找到了战友。联盟号召内部统一,集中精力于一系列如个人政治自由、个人经济抉择和有限的代议政府等概念,它们互不相关但却与30年代日趋流行的主流自由观有关。[注]David Plotke, Building a Democratic Political Order: Reshaping American Liber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1996), p. 20.让鲍德温本人失望的是,他的一些得意项目,尤其是那些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项目很快就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议程中消失了,因此自由联盟强烈反对史沫特莱的提议也就不足为奇了。她的提议涉及的是真正的左翼分子,它的范围超出了美国,倡导的也不是传统的民权观念。
尽管如此,鲍德温和他的追随者们仍不顾董事会的反对,支持史沫特莱的呼吁。鲍德温正需要这么一个案例。当时,鲍德温的一个重要项目是国际政治犯联合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Political Prisoners)。这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下属的一个致力于保护集权政权下政治犯的民权的组织。这个项目对董事会而言太棘手:偏右的成员不想参与有关苏联的事务,而偏左的成员不想公开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注]Samuel Walker, In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Carbondale, IL: 1990), pp. 86.而丁玲的案例正好给鲍德温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它代表的仍然是委员会的核心问题,然而它却避开了不为大众所接受的“苏联共产主义”。鲍德温与在中国国内公布丁玲被捕消息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联手,在美国发起了一场公共舆论运动。他们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领导者宋庆龄那里得到消息,并在华盛顿的中国代表那里提出要求;他们向美国公众散发由美国著名作家签名的请愿书;鲍德温还向身在上海的史沫特莱送去大笔的资金,让她在上海印刷反对国民党的宣传材料。
指导这场运动的是一个有争议的论点,即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具有在国外(比如说中国)开展运动的合法性。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史沫特莱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回复意见,但是鲍德温的观点更好地处理了史沫特莱观点中所隐含的普世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紧张关系。一方面,鲍德温将中国看作一个测试美国自由主义的好地方,去除狭隘性以后公民权利的概念可以得到加强和完善。上海和美国的斯科茨伯勒(Scottsboro)很相像,那里有威胁到公民权利的具体危机,它需要美国自由主义的解救,是一个有问题的“外部”存在。正如鲍德温所说:“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遭受着政治压迫,公开它们是必要的。”[注]鲍德温1934年12月6日写给 Arthur Garfield Hays的信。同时,鲍德温在处理丁玲事件时使用了很强的普世主义话语,他借用像伸张个人权利等自由主义变通的话语来使丁玲事件进入美国的关注视野。[注]David Plotke, Building a Democratic Political Order, p. 23.鲍德温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拥有一整套普世概念,因此自由主义必须能够在各个地方捍卫其概念固有的普世性。他说:“尽管我知道从美国这里的义务看起来很遥远,但是美国是唯一一个能向公民自由权利受到威胁的绝境提供援助的国家。”[注]鲍德温写给Hays的信。
鲍德温用30年代已为人接受的自由主义言论对运动进行改头换面,使之能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同仁所理解。但鲍德温的论点和中国历史语境相关。该运动首先由上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起。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等一群志同道合的改革者们共同创建了这一同盟,以反对国民党镇压政治异见者。他们有三个主要的目标:为释放国内政治犯与废除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而斗争; 给予政治犯法律及其他援助;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 。[注]Maria Svensson, Debating Human Rights in China: A Concep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Rowan and Littlefield, Oxford, UK: 2002), pp. 170-171.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很快注意到了丁玲的被捕,并通过大量的民众请愿要求政府当局释放丁玲。慢慢地,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该运动也波及了美国的大众。
鲍德温和宋庆龄之间的友好沟通意味着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间有基本的对等性。说到底,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为参照的。但是,尽管他们都致力于同一个目标,这两个组织对于“民权”的不同理解使得他们有所区别。蔡元培在中国古典传统中搜索本土的民权概念,他上溯到孟子的儒学传统,认为中国自古就有个人权利观念。尽管蔡元培对民权的理解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一样,都认为公民权超越国家及政党的限制,但他是要从中国的思想资源内部寻找一种普世主义。也就是说,当蔡元培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那里吸取自由观点时,他是通过中国文本消化那些表面上的西方概念。[注]Maria Svensson, Debating Human Rights in China: A Concep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Rowan and Littlefield, Oxford, UK: 2002), p. 172.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不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简单复制。同盟还曾将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胡适驱逐出同盟,因为他过于听命于美国的自由传统。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维,崇尚比较简单的法律意义上的民权。因此他认为同盟的职责只是保护囚犯的权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而同盟,尤其是宋庆龄,却持有更激进的观点,他们将争取公民权利看作挑战国民政府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因此,宋庆龄所做的远不止于把美国价值简单地引进中国,她把当时的危机看作一次在殖民地和非西方的语境内重新建构和定义民权概念的机会。她认为美国的民权观念已经被资本主义腐蚀,美国对于个人主义的过分重视已经使得对民权的保护沦为对那些企图通过剥削大众获得个人经济利益的个人的保护。在中国,有机会可以在人民而不是经济利益获得者中重新塑造民权观念。宋庆龄和蔡元培都认为民主只是一种随着内容变化的形式,而非受缚于单一的定义。[注]宋庆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章程》,载《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她甚至认为完全照搬美国的民权观念是一种幻想。[注]宋庆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章程》,载《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宋庆龄的言论凸显的是30年代美国和中国对于民权观念的根本差异。对中国人而言,它只是在面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国民政府的集权压迫等一系列政治危机时的实际解决措施。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宣言里,有关民权的措辞明显含糊其词,可以应对各种诘难。它是对西方概念的一种批评。对于这种西方的民权观念,聪明的思想家如宋庆龄很清楚它在中国社会和政治格局中的复杂牵连。中国式的解读是不断变化着的美国民权话语的一种突变,它甚至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为了和罗斯福政府的自由主义“公民权利”相协调,鲍德温停止了任何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余味的项目。30年代早期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采取的是高度规范的自由政治立场,例如支持保护个人权利和个人经济抉择权;和中国相反,在国家、帝国或者阶级的借口下,它拒绝对其自身进行反思和批评。
丁玲的例子表明的不仅仅是从美国输送公民权利的观念到上海。像宋庆龄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迫使美国知识分子——如史沫特莱和鲍德温——重新思考公民权利的实质及其在美国之外的适用性。通过这些,我们看到这个典型的西方民权概念转变的过程,以及新的、混杂的平等与民主观念的出现。我们开始觉察到中美政治概念在跨文化接触与交流中的共同演变。为了解救丁玲,在国际社会中倡导公民权利, 势必会发生这些概念的变化。中美的知识分子都没有选择简单地将西方的民主观念单向传播到中国。
在进入下一节之前,我希望简单地谈一下我所使用的一处档案。纽约公共图书馆藏有大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相关的档案,以及许多国际政治犯联合委员会相关的档案,而国际政治犯联合委员会负责了丁玲案在美的游说活动。有关丁玲案的大部分英文资料我是在这个档案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档案馆中找到的。[注]读者可以通过国际政治犯联合委员会的网站http://archives.nypl.org/mss/1515 了解情况。我所使用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小部分档案可以通过以下的网站查阅http://findingaids.princeton.edu/collections/MC001.03.这些资料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它们为一个中国政治事件提供了一个完全非中国的视点;同时,还为研究者们大量使用的中国民权同盟的中文材料提供了补充。和原先的材料一起,它们使得我们对那一段历史有一个更完整、更全面的看法。有关营救丁玲的档案是一个既在中国又超越中国的跨国档案。
三、丁玲是如何获救的:文学的功劳
代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鲍德温和代表中国民权同盟的宋庆龄就中国的民权概念有激烈的争论,但是,大多数时候这些争论只是象征性的。作为一个在华的外国团体,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不能雇佣律师也不能提起法律诉讼,它的诉讼权非常有限。因此,它的主要工作是在公众中发动舆论攻势。只有如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中国民权同盟才能迫使国民党释放丁玲。在这一节中,我要讨论释放丁玲的过程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即如何利用文学的舆论宣传功能在国内外为丁玲赢得同情和支持。
从一开始,中国民权同盟就希望他们的运动是一个速战速决的舆论运动。为此,同盟使用了当时日趋流行的“公电”来公布丁玲被捕的消息。正如周永明所指出的那样,电报在20世纪初期有关国家政治的辩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一直持续到二三十年代。争取释放丁玲的运动具有电报抗议的所有基本特征。[注]Zhou Yongming,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lo Alto, CA: 2006).他们使用大量的公电来公布丁玲被捕的消息,来抗议国民党对她的逮捕;他们在中国电报新闻和抗议集会的中心——上海从事这些电报抗议;在像《申报》这样适合此类消息的报纸上发表这些公电。[注]参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中收集了大量诸如此类的电报。这些都满足了一种新的电报活动的基本标准,成为中国民权同盟此次运动的核心手段。
活动伊始,同盟便知道他们要报道的不是一般的不公正,要唤起民众同情的也不是一般的烈士,而是丁玲——一位拥有大量知名文学作品的著名小说家。宋庆龄很快就巧妙地把丁玲的作品融进了他们正式的抗议材料中。这些作品变成了丁玲不再场的声音,用以代替丁玲事实上已经被捕的个体存在。到1933年为止,中国左翼人士已经出版了两本丁玲的作品集:《丁玲选集》和《丁玲女士》。它们的出版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读者熟悉作为作家和个人的丁玲,并引发同情;继而,通过散发丁玲被捕的消息让大众支持同盟抗议国民党的运动。这一切在选集的编排上可见一斑。首先,两本作品集都刊载了丁玲的生平介绍,告诉读者丁玲的文学地位。之后又介绍了丁玲的轶事,传递出丁玲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的信息。例如,题为《我们的朋友丁玲》的短文描写了一个令人喜爱的、踏实的丁玲形象。[注]蓬子:《我们的朋友丁玲》,载《丁玲选集》,天马书店1933年版,第1-42页。值得注意的是,选集中的作者都有意把丁玲和他们所写的文本联系起来,就好像丁玲自己在诉说。在这两本选集中还刊有许多正式的抗议材料,例如宋庆龄的电报和丁玲被捕的事件回顾。这两本选集担当了重要的宣传职责。[注]更多关于1933年1934年间丁玲小说的重印以及有关丁玲被捕消息的公之于众请参见Charles Albert, Enduring the Revolution, p.97;更多关于丁玲的作品在史沫特莱的组织下翻译成英语的内容参见 Tani Barlow, “Introduction” in I Myself am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p. 34.
这些故事成功地向国内的读者传递了丁玲的近况。它们对中国民权同盟的工作贡献巨大,使同盟能更好地宣传丁玲的被捕并迫使国民党释放丁玲。史沫特莱很快就看到了一个不仅在国内读者中,甚至在国际读者间宣传丁玲被捕消息的机会。因为当时美国和英国的读者常认为中国人缺少个性,因此丁玲的故事可以用以证明她的个人主义和个体的声音。仅仅使用政治性的电报来勾起全球读者对丁玲的同情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方式,但是,发行她的小说就不同了。这些小说赋予丁玲鲜活的脸孔和个性。新闻报道和抗议材料缺少人性色彩,而文学恰恰写出了人生的喜怒哀乐,具有新闻报道所不具有的亲和力。同时,因为丁玲的小说大部分都使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这也让美国公众更好地理解了她的处境。因为,现实主义是30年代美国和欧洲文学的主流。
在丁玲被绑架6个月之后,史沫特莱召集了一群中国学者将丁玲最著名的一些短篇小说翻译成英语,发表在《亚洲和美洲》(AsiaandtheAmericas)等美国著名的杂志上,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将中国作家的主体存在“翻译”成美国读者所熟悉的模式,使得她对人性和民权的诉求更易理解。史沫特莱、鲍德温以及美国现实主义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1968 )比较了丁玲的文学和美国民权保护运动的政治相似性,认为丁玲能够用写实主义作品表现自己的主张,其作用相当于美国的民权保护运动。
史沫特莱集中精力翻译、出版了丁玲的短篇小说,强调丁玲对人性和民权的诉求。这些短篇中的两篇——《某夜》和《水》——在国际左翼刊物中刊载最为频繁。《某夜》被翻译成了“Night of Death, Dawn of Freedom” (译者注:死亡的夜晚,自由的黎明), 而《水》则被翻译成了“The Flood”(译者注:洪水),这两篇都是丁玲创作于30年代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们虽各不相同,却有着相似之处:首先,它们都通过现实主义追求一种即个体又普遍的身份;其次,它们都描写了统一、团结和集体的形象。例如,以白色恐怖为题材的《某夜》描写的就是5位年轻人在被国民党处决前的最后时刻,尽管饱受折磨和凌辱,他们仍忠实于自己的政治使命,英勇就义。故事是以一个在临死前开始摇摆不定的年轻人的视角讲述的,但是在同志的帮助下,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懦弱,并与朋友们手拉手唱着《国际歌》坦然面对处决。丁玲严格遵守了现实主义的法则,通过她从辛克莱那里学到的一系列自由间接引语塑造了一个受苦的形象。当然,史沫特莱之所以选择这篇小说是出于内容上的考虑,因为小说描写了5位年轻作家的遇害,主人公的遭遇正好道出了丁玲当时的处境。史沫特莱对小说的形式也很感兴趣,尤其是小说的自由间接引语。小说的中文原文使用这一写法是为了能够在5位主人公中自由地转换,使得5个人能够分别讲述故事。而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的效果创造出一种单个主人公和全体主人公同时受苦的强烈感觉,读者们也能通过主人公的遭遇感受到人类的苦难。 把小说翻译成英语使得这种效果进一步加强。史沫特莱在几处关键的地方对原作进行了细微的处理,在英语翻译中增加了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例如,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她故意改换了小说的叙述方式。原作:
夜是沉默着,肃静,压严,飘着大块的雪团和细碎的雨点。 冬夜的狂风叫着飞去,又叫着飞来。雪块积到那垂着的头上,但风又把它吹走了。每个人都无言的,平静的被缚在那里。在一些地方,一个,二个,三个地方流出一些血来了,滴在黑暗里的雪上面。天不知什么时候才会亮。
史沫特莱的翻译是:
The night was ugly and forbidding. The huge snowflakes and the fine sleet drifted through. The wild wind of winter roared by only to come roaring back again. The snow piled upon the hanging hands to be blown off again by the gale. They were all dumb and motionless, fasted there. In some spots - in one, in two, in three spots - the blood trickled down and mottled in the snow in the darkness. Will the sky ever grow light?[注]Ding Ling, “Night of Death, Dawn of Freedom,” in Short Stories From China (Martin Lawrence, London, UK: 1935), p.73. 小说集的介绍部分是由史沫特莱执笔的,她也协助了翻译;翻译工作是由 Cze Ming- Ling完成的。 中文引文部分引自《丁玲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8-363页。(译者注:天会亮吗?)
最后的这句翻译很重要。尽管史沫特莱在小说的其他部分都直接遵从中文原文,但是最后这一句却通过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而加强了小说的力度。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It is not known when the sky will finally grow light”。史沫特莱的改动很小却很重要。从陈述句到疑问句,史沫特莱让这句话首先成为死去的主人公的疑问,其次是读者的疑问。这样就让主人公和读者的意识合二为一了,而不是仅仅将它翻译成主人公对客观世界的观察。这样才能影响读者,进入主人公的内心。
对《水》的翻译是为了让丁玲的小说和国际读者联系在一起,但它没有为了感动西方读者而调整原文,而是强调了一个在不同文化和语言中都会出现的比喻(tropes), 比如说“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 和平民主义(populism)。 Marston Anderson在其研究中国现实主义的著作中指出,《水》要描写的是一种新的“集体身份”,一个散播进集体的主体概念。[注]Marston Anderson, 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1990), p. 180. 他对《水》的阅读参见第180-190页。由于在作品中呈现了总体和社会行动概念的复杂性,也即Marston Anderson所说的 “有意识的增加”(a consciousness of increase),小说经由卢卡奇发展出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批判现实主义。史沫特莱很快就发觉了“洪水”这一形象的力量。在中国语境中那慢慢起来抵抗的农民集体以及如洪水一般汹涌的抵抗意志与活动在一个更广阔的的国际语境中可以解读成国际抵抗力量的形成。洪水这一个形象或象征已经超越了文化差异,号召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读者加入人类愤怒的汹涌大潮中。在《亚洲和美洲》上发表的《水》的英文翻译《洪水》将原本30页的中文原文紧缩到8页,主要翻译的是奔腾的洪水和处于急剧运动中的人的身体。比如说以下的段落:
The dong, dong, rolled across the fields from the direction of the dikes, a confused clamorous note shaking the people out of their houses, rousing all the animals and fowls, startling even the roosting birds. The whole village burst into life. The universe itself seemed to have been strung on a line, ready to break at this touch of sound. One of the women dashed from the house, and then everyone emptied from it, streaming towards the cinnamon, everyone ...[注]“The Flood” by Ting Ling [sic] in Asia Magazine, October 1935, p. 634.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1932年中文原文的标题是《水》。该小说非常有名,见于大多数的丁玲选集和读本。
翻译之所以选择这一场景是因为它创作了一个社会生活中丰富且完整的图景,中美文化里都有。这图景就是普通老百姓和“整个村庄”都突然爆发;动物、每个人,以及整个宇宙都一起突然爆发。史沫特莱的目的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一图景。在公布丁玲被捕消息的同时,倡导一种肯定世界内部关联性,并以此解决文化差异的文学样式。世界各国所共有的图景便是大众集体和人类生活无穷尽的“洪水”。
30年代,国内的研究者们很快就认识到《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价值。同时,国内的评论家们也注意到了国际社会对它的喜爱。[注]参见张惟夫编辑:《关于丁玲女士》,立达书局1933年版,第24页。小说仿佛是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和社会革命的象征,它也因此在国内外都能找到读者。史沫特莱和国内的批评者们都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她特地在翻译小说的时候将标题更改为“洪水”,使它能够融入美国左翼圈中有关群众力量的话语,也使小说能配合美国对中西部地区相似天灾的关注。从内容上而言,《洪水》和当时美国的文学潮流是相容的。Barbara Foley发现美国30年代左翼小说中也在差不多时间出现过一个类似的“集体形象”(collective subject)。[注]Barbara Foley, Radical Representations: Politics and Form in U.S. Proletarian Fiction, 1929-1944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NC: 1993), pp. 398-441.和中国的作家相似,美国的左翼作家深感批判现实主义的局限性,转而投向于以群众为焦点形象的、更为有力的社会现实主义。美国的集体形象小说常在结尾处描写罢工场面,而《洪水》则在小说的最后提供了相似的农民一起反抗国民党的场景。
总而言之,丁玲小说的翻译和传播使得美国的读者能够阅读到一个令人同情的、似曾相识的丁玲;同时也证明丁玲能够如美国人一样有深厚的感情和鲜明的个性。这些翻译将中美左翼文学连接起来,指出他们都拥有像“洪水”和群众形象等共同的比喻和想法。至于这群众是一群中国农民还是美国中西部的农民已经无关紧要了。这些都使得美国左翼人士关注起中国的政治危机,使他们更愿意加入营救丁玲的活动。文学就这样成为一种沟通的工具。它促进那些看起来根本不同的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和中国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正遭受苦难的工人和左翼知识分子,看起来是如此的相似,且有着同样的愿望。
这里我想介绍另一个对理解丁玲被捕事件至关重要的档案,那就是丁玲作品的英语翻译以及它们在中国之外的地区和国家的流通,对理解丁玲被捕事件也至关重要。我们常常把翻译看作文学作品的后续生命,并且认为翻译对理解原作发表之初的意义并不重要。但是,正如我所谈到的那样,丁玲作品在美国的解读和它们发表之初在中国语境中的原始解读关系密切。为了更完整地理解丁玲的作品,这二者的情况我们都需要了解。我认为他们中的任意一方都对另一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中文的原文影响到了作品的翻译和接受;同时,作品的翻译和流通也决定了原始作品的意义和解读。翻译不仅仅是原作的后续生命。我在本文中所举的例子只是我所使用的档案的一部分,另有许多仍未被处理。它们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三四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
四、结语
1936年9月18日丁玲再一次在上海出现。她完全自由了。在过去的一年中,国民党慢慢地释放了她。一方面是史沫特莱和宋庆龄反对国民党的民主运动的功劳;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注意到国民党对丁玲事件所激起的国际关注感到吃惊,在压力下不得不释放丁玲以免遭受更多国际谴责。[注]更多的请参见 Charles Albert, Enduring the Revolution, p. 94.无论从文化还是政治角度来看,解救丁玲的运动都非常成功,达到了预期目标。
在此,我想向中国学者介绍英语文献和美国档案馆中的一大批政治和文学文本,我认为他们对研究像丁玲被捕这样的现代中国历史事件非常有用。我是在写作我的书稿RepublicofMind:Democracy,Communication,andtheRiseandFallofaU.S.-ChinaLiteraryNetwork, 1925-1955时找到这些档案的。[注]该书将于2015年由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项有关两次大战间中美文学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它研究民主和技术沟通等概念对创造中美文学空间的重要作用。我惊叹于丁玲例子所展现出的强大全球效果。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在中国和美国找到了大量散落的档案材料。[注]有兴趣了解这些档案的读者可以通过邮件 richardjeanso@uchicago.edu 和我联系。我将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我发现她的例子代表的是一段典型的“跨国界文学史”(transnational literary history),看起来是中国国内的事件和文本却隐含着国际的关联,而地方和全球的交互关系又使得这些事件和文本呈现出完整的意义。我认为把中国的资料和美国、欧洲、拉丁美洲以及俄罗斯的档案资料联系起来解读将有利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以及其他民国时期的文本和事件的研究。只看其中的部分,我们无法了解它们发生之初的真正意义,因为中国的左翼作家并非只在狭隘的视野里考虑他们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