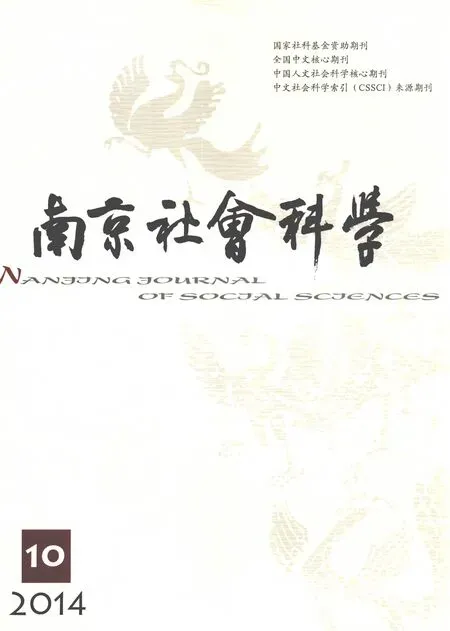生产与合谋:当代青年的视觉文本转换
董小玉 严 亚
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微小叙事、新媒介、城市话语在青年亚文化中得以统合,并迸发出视觉建构的强大力量。当代青年以日常生活叙事为内容、以新媒介为手段、以城市为空间载体,利用另类符号使抵抗性、风格化、边缘性的亚文化特性解构消费者、服务者、普通人的现实形象,询唤着超现实、去政治化、自我主体化的视觉形象。时尚表现者作为当代青年着力建构的当代视觉形象,充分诠释了作为符号的时尚元素被其赋予意义的过程;作为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也积极地争夺文本编码权。在后亚文化中,当代青年与商品和媒介合谋、“相互剥削”:商品为他们提供娱乐、消费和表演的实在意义,并与媒介一道成为“符号资源”供其创造性地生产自我主体性及其物化体现——新媒介文本。新媒介文本对现实文本的观照与对传统大众媒介的邀约,创设了值得深思的视觉文本场域。
一、视觉文本场域的逻辑
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视觉文本场域意指视觉文本形态,即现实文本、新媒介文本、舆论文本之间意义生产与增值过程或关系的一组网络或构型。在这个场域中,文本生产者与阅读者、意义制造者与意义消费者、符号资本占有者与符号资本附属者因其地位的对抗性向合谋性的连续性递变,导致文本及其意义的生产与创造逐渐由单向度的霸权/对抗的关系转向共谋与相互剥削。实现这种转变的内生机制,在于视觉文本间发生的转换允许生产者/符号资本占有者与消费者/符号资本附属者身份产生互转,由此推动能指与所指的固有关系被颠覆。能指与所指之间发生断裂和错位接合,使得视觉文本形态间的转换制造出新的意义,并在新的语境中实现意义增值。菲斯克对此的判断是“打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社会控制的另一种断裂,因为它瓦解了符号,而符号就是文化,所指是它的含义……”①。实际上不仅是通过所指创造意义,文本形态之间的转换也创造意义,只不过是在能指与所指的断裂语境中生产、增值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视觉文本场域充满着张力,从对所指/文化意义的对抗到对能指/自然的转移,再到所指的重构,时尚的符号指涉在当代青年中逐渐依靠文本的转换而形成快乐原则。
在媒介社会和商业消费主义时代,规避和抵制在青年与媒介和商品的合谋中让位于相互剥削、彼此利用,这种合谋关系让时尚的视觉文本及其形态转换脱离抵抗话语而进入到意义生产主体性话语中,意义增值也在其间发生。在这里,视觉文本转换承载着时尚的能指/所指的断裂与错位接合,意义的生产与增值冲动得到释放。与大众文化观点不同的是,后亚文化认为青年人在媒介消费和商业消费文化中并非是愚昧的、消极的,而是积极地“盗用”市场中获取的媒介产品和商业制品,以规避或抵制支配性权力统治体系的方式重新语境化进而转换其意义。在保罗·威利斯看来,青年人的商品消费行为和媒介使用都是积极的符号创造实践,意义生产逻辑就是其消费方式体现了“关于认同、空间、文化形式的自我创造,拥有自我的文化授权”②。这种文化授权行为充分赋权于青年人去“盗用”、重释媒介文本意义,从而使得其消费实践拥有创造力和识别力。在这里,媒介资源和商品资源不仅是单纯的剥削资本,还被当代青年用来生产主体性的意义,而这些意义是被抽取了曾附着于其上的所指含义并被置换出的全新意指。基于此,视觉文本场域的逻辑既不是“限定的生产场域”的“是非”逻辑,也非“大规模的生产场域”的“敌友”逻辑,而是能指和所指的“断裂”逻辑与当代语境中的“合谋”逻辑。这种逻辑充分赋权于年轻人去解构附着于时尚上的固化意义,而在“意义的漂浮”中用自身独特的编码与解码方式重新建构出青年亚文化的所指。
二、从现实到超现实:视觉文本的转换
约翰·菲斯克对媒介文本中“受众对媒介做了什么”的研究路径,为意义生产及其影响过程提供了符号学研究框架,更为生产者式文本及其形态转换构建了分析路径。时尚现象是当代青年主动构建的视觉文本,意在通过与媒介和商品的合谋实现对符号意义的再造。这种视觉文本呈现出不同形态并经历动态转换,形成视觉文本场域。菲斯克在分析麦当娜形象及其粉丝的自我授权行为时,用初级文本、次级文本和第三级文本来说明大众文本的构成形式。这个三级文本结构为视觉文本场域分析提供了方法论,但遗憾的是该结构较少触及文本形态间的动态转换及其社会逻辑。
1.现实文本
现实生活中的时尚现象只有进入到人们主动或者被动解读的范畴才能作为文本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文本意指等待读者去解读的,年轻人用以建构其自身、社会和信念的意义的时尚现象或行为,通常表现为客观存在的生活片段、事件、过程等。以自发性为表征,现实文本以衣着、言行、休闲、娱乐为表征符号,通过原创性、原生态的形式悄然存在于大众的身边。因其出现伊始只存在“新族群”式圈子里,以“内行人”所引领的流行行话和打扮为表征,时尚现象的现实文本并不为父辈文化、大众媒介、社会公众所重视。相较菲斯克的初级文本概念,即原初的文化商品,如麦当娜本人或一条牛仔裤,现实文本则更强调时尚现象为青年们提供的意义生产权的潜在性。时尚在这里体现为他们所能拥有的亚文化资本,。它在萨拉·桑顿那里,则是他们“为了权力而寻求意义”③的方式——“流行的区隔”,即与其所不喜欢和不属于它的东西区分开来制造差异。按照索绪尔的理论,“意义”依赖于对立者的差异。进一步用人类学观点观照,如果事物出现在错误的类别或不属于任何类别时,即菲斯克所谓的“异类”,这种“不在其位的事物”会搅乱文化秩序。在此,时尚符号恰恰作为“异类”来实现目的:他们凭借以时尚为表征的亚文化资本透过与主流文化的差异来生产意义,并用“异类”或“不在其位”、跨越符号边界的现实文本来寻求意义。正是因为被禁止、属禁忌,对文化秩序造成威胁,与主流文化的差异,时尚符号才显得强大,才形成奇怪的吸引力。巴布科克对此的论断是“在社会上处于边缘的,通常在符号上是处于中心的”④。青年人利用这些符号来表达他们与主流文化的距离,甚至“从休闲中获得自尊”⑤。现实文本所建构的差异或对符号边界的嘲弄以“震惊”式的视觉感受呈现出来,以获得娱乐的快乐和快感。青年亚文化所形成的社会氛围导致两种话语的分离和张力:“一方面,娱乐化的诉求把政治挤压到了很小的空间里,造成了娱乐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分离运作。另一方面,少谈政治的倾向又日益淡化了受众通过大众文化来参与社会公共政治的意愿和冲动”⑥。社会权力、意义生产、符号戏虐,似乎都指涉当代青年的娱乐诉求,快乐和快感成为他们的意义生产指向。例如,当代社会,经典国货即以位处艰苦奋斗的革命岁月与最新流行趋势间的“异类”符号出现。原本市场上难觅踪影的经典国货,成为当下年轻人寻求快乐、制造快感的亚文化资本。这样的亚文化资本符号是对当下商业消费主义和媒介议程设置等支配性话语的某种规避和抵制,其背后却隐含着对严肃话语、生存压力、身份危机的反讽与嘲笑。凭借其跨越时空、跨越符号边界的审美反逆,国货新时尚这一现象凸显于现实生活,被成功地制作为供人解读、与现有文化秩序存在明显差异的现实文本。
与“策略性攻击”和“游击式袭击”都不同的是,青年人在后亚文化中的意义生产不再是越轨式解决方案和仪式抵抗,而是与媒介和商品的相互剥削,即盗用、改变、在新的语境中制作媒介文本和创造商品意义,尽管总是在商业利益限定的范围内运作。以cosplay为例,这种集体认同以虚拟角色扮演为表征,充分揭示了当代青年时尚表现者的视觉建构机制。一方面,他们的自我潜隐于他者中。作为被规训的对象或客体,青年群体选择了差异化他者——动漫作品人物来进行意义生产权的争夺。动漫作品的故事情节演绎着勇气、不羁、挑战、反叛、蔑视等情感,父辈或长辈在叙事中缺席或沦为配角,都与当下年轻人的自我认知或者向往境界相符。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群体放弃面临现实矛盾、对社会冲突无所适从的自我,转而将自我他者化——也就是说,年轻人为了规避现实矛盾、逃离社会冲突,将自我设想成动漫人物。而动漫虚拟人物的各色装扮则成为抵抗现实话语、塑造理想自我的载体。简单地说,这种潜隐就是要实现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断裂”:播放着的动漫画面、现实生活中的cosers、互联网络中的cos攻略、同伴间的热情推荐,都在邀约他们利用夸张的服装、饰品、道具和妆容进入他人的凝视中去规避父辈规范、主流价值、规训话语,实现自我消解并转化为理想“他者”。另一方面,他者被内化而成为自我的组成部分。他者意指差异,动漫人物的完美人格物化为外在形象,建构出理想的他者,与现实中的冲突自我形成鲜明差异。当代青年的现实自我被虚拟他者消解了,消解的结果却是他者客观化、对象化,他者转化为自我的统一化身份。青年对动漫作品的消费,并非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在消费角色的过程中生产出自己的意义和隐喻,“阐释、符号行为及创造性是消费的组成部分”⑦。根据费斯克的“影子文化经济”理论,进一步来解读cosplay“易装”和“易性”,可以发现其在异装癖、同性恋这类官方媒介产业之外的创造性文本意义:“易”表达着“他者”性别身份的认同,意味着对传统社会男女二元对立结构的打破,隐喻着对身体政治的某种反讽。cosplay活动的匿名性使虚拟角色扮演在一个超现实语境中发生,角色与情节和环境的结合消隐了扮演者的现实自我,易装或易性后的角色则更直接地载入了其对异性角色的性幻想和情感体验,表明对完美的理想气质的追求,建构出“被授权的社会行为”并允许他们参与媒介文本的生产加工。这个过程模糊了现实社会性别制度和身份规范,“易”使他者成为自我认同的载体,内化于自我的现实需求。Cosplay的他者成为一个被收藏、赏玩和消费的意义生产对象。
2.新媒介文本
从存在形态分析,只有被新媒介及其技术所观照的现实文本才能称为新媒介文本。新媒介及其技术为新媒介文本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和社会氛围。基于此,新媒介文本界定为利用新媒介进行视觉呈现,具有较强相关性并充分互动的时尚现象。与约翰·菲斯克的文本等级概念相似,新媒介文本类似于次级文本,如广告、媒体故事和评论,所不同的是它更强调新媒介及其技术对现实文本的意义生产功能和所指含义置换功能。
新媒介及其技术为现实文本提供了事件选取和意义再造机制。构架模式理论揭示新闻事件以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为依据的选择机制,即“通过选择某些故事而舍弃其他故事而进行的……”⑧。新闻机构对新闻事件和内容的选择拥有决定权,仅仅选择性地对现实社会进行镜子式的再现。与此相反,新媒介文本赋权于当代青年,使其作为意义生产和传播主体进行事件选择,他们作为文本的观视者、转换者和发布者利用新媒介及其技术在分解专业精英的职责。与霸权新闻原则不同,当代青年对新媒介文本的选取着力于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即“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制约”⑨。这种相关性可以视作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体现。就在与自身生活联系紧密的现实文本中,青年对社会生活、娱乐休闲、生活空间的强调决定了他们对现实文本的“技术性观视”(瓦尔特·本雅明)。现实文本一经新媒介的“技术性观视”所观照和聚焦,即被选取为新媒介文本,并为意义生产提供内在逻辑:主体性生产和意义再造。新媒介的“赋权”功能提供自治空间,使他们依据相关性去搜寻有利于建构主体性的现实文本。在时尚表征领域,任何具有意义再造潜在性的符号或形象,在新媒介技术性观视中都能成为其可利用的符号资源,用于主体性地生产自身话语。这种主体性是对“物役”的某种反讽,是对自主性、能动性、自我中心性的回归。在主体性被异化的阶段,自我主体性依赖于由他人和他物构建的他者主体性。当新媒介使年轻人成为信息编码和解码的主/客体,物质世界容易被把握为或原创、或改编、或戏谑的图像符号。由此看来,与其说新媒介生产信息,倒不如说生产青年的主体性。在主体性回归语境中,时尚符号的意义生产也形成有利于青年的主体性导向。在生产者式文本概念中,意义建构与阐释之间的抗争揭橥着文本读者对意义生产的民主力量:生产者式文本允许读者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利用文本创制出符合其利益的意义。“年轻人创造性地把互联网作为文化参与的一种手段,可以产生各种带有自我建构和自反性色彩的‘亚文化’身份认同形式”⑩。班尼特所关注到的青年人在虚拟世界中的文化参与,正是当代青年在互联网络中主体生产性的物质体现,也是意义生产的虚拟空间再现。主体性的回归,让年轻人在虚拟世界中开创出新的意义框架。“相关性因受众的积极参与和主动介入而非中产阶级的‘距离’式审美和静观,产生出一种‘意识形态的暂时丧失’和逃避宰制力量的快感,大众主体就像一个在意义超市中挑拣商品的‘商品盗猎者’一样,从原初的文化资源中挖掘出关联自身个性、富有创造性、吻合相关性的意义、快感和权力来”⑪。在新媒介文本中,这种文本“盗猎”行为就是新媒介提供符号资源给当代青年,鼓励他们产生社会感受并由此建立主体性身份。互联网络上流行的一张图片(电影男星奥兰多·布鲁姆穿着一双飞跃运动鞋坐在公园里的照片),让“技术性观视”移向经典国货的现实文本,推动现实文本向新媒介文本的转换。由此开始,飞跃、回力、海魂衫、梅花运动服、军用挎包等国货新时尚受到新媒介的极大关注。在以互联网络、移动互联网络为表征的新媒介空间里,这种新时尚的再现、创新使国货俨然成为青年群体的自我主体性标志物。在这股浪潮中,国货为青年群体生产主体性并为再生产所指。青年群体不仅通过新媒介将自己定义为国货新时尚的创造主体、消费主体、传播主体,更是为国货再生产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拼搏精神、团结奋斗精神与抵制国外奢侈品牌、反对经济帝国主义的符号意义。其间,隐藏着这个群体推翻主流话语霸权、嘲笑所指的快乐和快感。在此,青年群体“盗猎”了国货的本原意义,而将其与当下浮夸、享乐、媚外的消费风格形成明显区隔,国货的时尚与爱国意指从固定时空场域中成功地挪用和消费为用于建构自身视觉形象的亚文化资本。
必须指出的是,新媒介及其技术以能指与所指间的断裂与媒介和商品的合谋为着力点。一方面,符号能指与所指的断裂被利用来生产意义。在菲斯克那里,能指与所指间关系的破裂意味着对霸权的抵制。“打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社会控制的另一种断裂……所指是文化,但能指却是自然,是知觉”⑫。能指是客观的,所指却是社会文化与社会互动所赋予的。,在伯明翰学派那里,其意义潜隐着支配性权力结构对从属群体的文化政治关系;而在后亚文化中,所指却来自年轻人与媒介和商品共谋对能指进行的符号资源再利用。作为能指,国货以亚文化资本的形态被年轻人建构所指、实现文化参与的目的。亚文化资本是由媒介主导的,“因为在亚文化资本中,媒介……是一个对定义和传播文化知识至关重要的网络”⑬。媒介覆盖、创设、揭露的程度与时尚和落伍的人们间的区别、亚文化资本富有和贫瘠间的区别有着直接联系,可以说媒介就是当代青年制造差异、生产意义的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商品及其消费成为其创造意义的符号资源。在让亚文化资本收获效益的社会环境里,“圈子”或新族群却是“依据各式各样的、变动的,经常是转瞬即逝的消费方式”⑭而建构的。在马菲索利那里,商品及其消费方式建构出圈里人相互认同的标准,为亚文化成员提供了集体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感。媒介和商品的合谋对国货的所指内生出某种标准,霍金森用“商业和媒介特意建构并促成了哥特景象”⑮的结论来强调合谋的强大力量。就在媒介和商品的合谋力量中,年轻人验证着符号资源的创造能力,尝试为国货赋予时尚的所指,试图“剥削”时尚的符号魅力、“盗猎”固化的所指意义。在视觉符号的互动沟通中,青年亚文化与时尚流行文化彼此渗透、相互指涉,国货的现实价值在新媒介中逐步瓦解,其所指也在虚拟空间以青年亚文化的形式所逐步改变和重写。在青年亚文化中,拼贴和同构为国货所指的意义再造提供了路径。各种国货及其新媒介文本被年轻人吸收和重新语境化后,其意义被转化。例如,飞跃运动鞋拥有了时尚的魅力和抵制国外品牌的民族自豪感,海魂衫被嵌入儿时梦幻般的完美记忆,军用挎包则被意指为英雄情结与男性气质的再现。拼贴让国货成为风格和快乐的符号,而同构则使混搭在一起的风格元素形成有凝聚力的亚文化群体认同的象征性表达:音乐、服装、休闲活动等被结合在一起,以迪克·赫伯迪格式的“符号的游击战”方式把日常的文化制成品及其新媒介文本的自然化意义转变为新语境化的、在消费中制造快乐和创造意义的所指。国货的能指被嵌入新的所指,更关键的是这种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置换发生着快速的变化。所指意义的生产权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青年所掌握和把持。
3.舆论文本
新媒介文本在赛博空间中引发的争论与争议,在现实生活中引发大众传媒的广泛关注。除了议程设置之外,商业市场的利润追逐也推动舆论文本在更广阔的范围中产生影响。在此,舆论文本定义为新媒介文本中拥有引发社会意义争议的价值而进入传统媒介视野的时尚现象或事件。
新媒介文本在虚拟空间中的激情表现,越来越受到传统媒介的关注和重视,二者甚至建构出前者制造主题,后者验证、强调、论争并复又返回赛博空间继续发酵的关系。新媒介文本的技术特性为青年群体生产主体性,使其成为自身文本的制作者、传播者、阅读者提供了路径。这种主体性激发当代青年通过文本的生产和改造去追求快乐的渴望。在菲斯克看来,这种快乐源自对支配性权力结构的逃避;而在后亚文化中,却是在商品和媒介的消费中创造性地生产意义而获得的快感。新媒介文本将注意力引向年轻人,其中的时尚符号和行为将他们自己建构为供人解读的符号,在这些时尚符号中,能指尽情嘲弄着所指,“快乐,因其对能指的强调及对所指的否定,就成了意识形态的抵制的一种方式”⑯。青年群体不仅成功抵制了意识形态政治学,还通过把自己建构为符号,实现了利用能指去再造所指,让所指服务于能指,从而收获快乐和快感的目的。所指来自于固有的文化解释,以实现“意义的滑动”的固定,“解释成了意义被给予和获得过程的一个根本方面”⑰。按照斯图亚特·霍尔的观点,被编入意义的能指必须由接受者从意义上加以阐释和解码,读者在生产意义这个方面与作者同等重要。新媒介文本赋权于青年群体破坏固有的解码方式,甚至赋予他们编码的权力。在固有文化中,对能指的编码是支配性权力结构的特权,规训式解释则是读者作为从属群体的受限义务。新媒介文本改变了这种关系,他们获准利用其技术特性将自己裹挟于能指中创建新的编码关系,邀约传统媒介进行解码。新媒介文本引发传统媒介,对其进行社会生活、道德伦理、规训与抵制的解读和评判,其实质是编码权的倒置。正是这种编码权的置换,当代青年逐渐建构出对自己形象、认同、地位、归属的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粉丝文化揭橥了读者利用媒介文本创造文本意义的实质。粉丝比普通受众更具创造性和积极性,他们表达了将媒介消费经验转化为新文本制作的参与热情。约翰·菲斯克用“影子文化经济”来揭示粉丝巧妙地利用商品市场中可以获得的文化形式以创造性方式消费并制造媒介文本的意义。在麦当娜的例子中,他关注“被授权的社会行为”,认为粉丝通过自我授权能够去创造新的文本意义。其观点直指文本意义生产与文本编码的内生联系,新媒介文本用全新技术机制鼓励青年群体利用文本意义的生产过程去获取文本编码权。国货新时尚如此,跑酷、极限运动、cosplay、拍客、快闪等流行现象亦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时尚现象可视作粉丝文化的同质化体现。时尚能指的出现为所指的再生产提供了契机,在新媒介文本中,青年群体对这些时尚进行编码,即进行文本意义的再生产。比如,国货被视作经济帝国主义的解构和对国际时尚趋势的民族化抵制;跑酷和极限运动被用来表达对城市空间桎梏的嘲笑;cosplay是对现实社会角色的脱逃和反叛,其中的“易性”、“易装”行为建构出“他者”的幻想;拍客和快闪打破看与被看的固定关系,建构出观视的自反性和反观性,将“我”主动建构自己注视的对象。就在能指与所指的断裂与重构中,就在意义产生与文本编码权的移交中,拥有自我主体性的当代青年在新媒介中尽情生产、纵情编码,拼贴与同构为笔,挪用和消费当墨,以文本制作彰显主体性和自我认同、社会认知的主动地位。正是这种文本生产和意义编码,撩动着传统媒介的新闻价值神经,舆论文本用“新”、“奇”、“特”视角观照着新媒介文本。舆论文本的呈现,在这里体现为对新媒介文本的解码和阐释,以议程设置的方式引发青年亚文化群体之外的广泛读者的关注。舆论文本与菲斯克提出的阶梯形文本结构中的第三级文本,即持续存在于日常生活过程中的文本形态相类似,但前者更强调其本身对新媒介文本的解码和阐释,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附属性和补充性。新媒介文本与舆论文本间的转换关系揭示出意义生产权的逐步移交与文本编码权的悄然转向,当代青年的自我主体性渐渐明晰。舆论文本喻示着作为控制方的主流文化与作为接受方的从属文化之间的霸权关系被解构,青年群体利用媒介和商品的符号资源为自己争夺到参与和自我控制的权力。
当代青年通过新媒介文本主动邀约大众媒介的介入,他们成为实质上的内容生产者。时尚符号首先表征为一种亚文化资本,它允许该群体以社会生活中的“内行人”引领时尚风向、把握风格趋势,生产对内认同、对外区隔的“流行的区隔”。这种资本是一种知识和能力,在萨拉·桑顿看来,其与文化资本的区别主要是媒介的主导作用和无阶级的幻想。“媒介……是一个对定义和传播文化知识至关重要的网络”⑱。在桑顿看来,亚文化就是年轻人与大众媒介结成的动态的、高度自反性的关系的产物,因为“媒体和其他文化工业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并发挥作用”⑲。大众媒介视觉的、意识形态的资源,为青年亚文化的构建提供了丰富内容。大众媒介的动机,如同“电视不生产节目,电视生产观众”⑳的论断一样,在于生产观众/听众/读者和使广告商成为消费者,以实现媒介自身的盈利目的,这是与大众媒介社会功能并行的经济功能的体现。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大众媒介主动与新媒介合作,甚至渗透至新媒介领域以全媒体的形式出现,以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在消费社会和景观社会中,所有的一切都以消费品和视觉奇观的方式呈现,如媒介接触也转变为媒介消费行为,足以说明商业消费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对后亚文化颇有研究的安迪·贝内特建议将亚文化改称为“新族群”,因为现在,集体认同的表达依据的是各种各样、变动不居的消费方式,甚至有学者建议用“生活方式”来取代亚文化的提法。生活方式强调消费者的创造力,承认商品作为文化资源在“基础性美学”和“影子文化经济”层面发挥作用。当时尚作为一种后亚文化时代的文化资本出现,就会产生相应的生活方式和场景,媒介的舆论引导和商品营销的完美配合,甚至以社会道德伦理的形式教化年轻人:消费建构主体,商品赋予身份。cosplay、跑酷、极限运动等时尚现象一旦呈现为新媒介文本,传统媒介立即进行流行预测、模仿攻略、购买途径、身份匹配方面的详细解读,商品营销同时展开攻势,媒介与消费如影随形、相互验证,为时尚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三、生产与增值:当代青年视觉形象的自我定制
在视觉文本场域中,文本形态的转换实现了文本意义的生产功能和增值效应,由此也使青年群体获允发挥其自我主体性以定制其视觉形象。文本形态转换,在斯图亚特·霍尔那里体现为文本间性,约翰·菲斯克则称其为互文关系。文本间性概念强调差异,“这一形象是通过标志出‘差异’来运作的”[21],文本间差异是意义的来源。在霍尔那里,文本多指图片文本,也更侧重于种族差异的意义制造,但他没有观照不同媒介文本间的差异及其意义生产机制。互文关系则更关注联系,认为意义是在某文本与整个其他媒介文本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菲斯克的阶梯形文本结构意识到了文本转换的动态关系,甚至认为意义从中产生,但却未将消费社会和媒介社会的快速变迁置于这个语境中体现,更未将青年群体的主体性建构意图、媒介和商品的利益冲动结合起来考虑。在媒介和商品成为符号资源的语境中,当代青年挣脱以往颓废的、被动的从属式的社会认识,而将媒介和商品作为一种可加利用和“剥削”的符号资源,主动、积极地打破这些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固化关系,重构所指意义,逐步恢复他们对自身形象和社会认同的主体性地位。现实文本是自为之物,能指和所指隐含主流意识形态的固化关系,而新媒介文本则为他们利用新媒介及其技术主动打破这种自为状态和固化关系提供了方便。青年将自身的主体性建构诉求、社会权力争夺欲望、快乐话语操纵渴望寄托于新媒介的数字化和互动性,跨越“界面”促成现实虚拟化、虚拟现实化的社会关注。在此,意义生产既非单纯来自差异,也不仅源自互文性,其关键在于视觉符号的生产与传播。Ipad、数码相机、智能手机等硬件产品,微博、微信、陌陌等自媒体手段,优酷、56、新浪、雅虎等视频网站,以及各类论坛、贴吧等社交网站,整合成为覆盖面和深度极大的虚拟空间。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这个空间允许任何人作为符号制作者和传播者上传信息、建构意义。当代青年作为社会交往中的活跃者、困惑者,甚至叛逆者,充当了这个虚拟空间的舆论领袖。他们关注身边的时尚流行细节,并即时上传至虚拟空间,主动地将个人信息转化为公共信息,推动现实文本转化为新媒介文本。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独特的阐释使视觉符号“漂浮的意义”固定下来,拼贴和同构也好,挪用和消费也罢,不过成为他们生产意义的语义机制。时尚符号的所指在这个生产过程中被重构为他们自我主体性的视觉象征。虚拟空间的互动功能不仅将他们看与被看的政治关系被打破,也使二者统一:他们既是观视自己的主体,也是观视反观性的客体。恶搞、自拍、文身、cosplay等时尚符号在此发挥验证功能。如果仅仅将虚拟空间中时尚符号视为新族群或圈子内部的基于认同而形成的意义生产行为,那么舆论文本对新媒介文本的观照则使意义生产过程进入增值阶段。传统媒介从社会伦理道德和交往规范的显性动机与生产观众/听众/读者来吸引广告商的隐性动机来透视新媒介文本,从中挑拣具有较高新闻价值的细节来引发圈子或新族群以外受众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圈子内的亚文化资本,经过大众媒介的聚焦和阐释,而成为超越阶层、跨越地域、模糊等级的公共领域式的文化资本。亚文化资本回归为文化资本,将小众资本提升为大众趣味,时尚的领先性被趣味的大众性所取代。
必须指出的是,在从现实文本到舆论文本的转换过程中,当代青年把握自身主体性的权力在增加,对时尚现象及其文本的编码控制在增强。青年自我主体性的增强,体现为对自我形象,尤其是视觉形象控制力的极大提升。作为中间形态的文本,新媒介文本从现实文本中挑选素材,按照自身价值观念进行虚拟化和数字化加工并即刻传播至赛博空间,其间的社会逻辑是他们作为编码者将其自身信息编码为视觉符号,邀请大众媒介进行解码,并由此介入社会生活。这是一种反规训的信息传播活动,打破了信息传播中的专业主义、精英主义及其话语霸权。这是一种时空的断裂,正是这种断裂诱惑着当代青年从中找到快乐,发现快感。视觉符号的所指被能指嘲弄着,所指被他们操纵着,“符号的游击战”的胜利归属于他们。
注:
①⑫⑯【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金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8、68页。
②⑦Paul Willis.Common Culture:Symbolic Work at Play in the Everyday Cultures of the Young.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90,p.82,p.21.
③⑤⑬⑱萨拉·桑顿:《亚文化资本的社会逻辑》,陶东风、胡疆锋主编:《亚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8、363、360、360 页。
④B.巴布科克:《可颠倒的世界:艺术与社会职能的符号性倒置》,(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页。
⑥周宪:《当代视觉文化与公民的视觉建构》,《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
⑧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⑨【美】约翰·菲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钰、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⑩【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译.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⑪陆道夫:《试论约翰·菲斯克的媒介文本理论》,《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
⑭比尔·奥斯歌伯:《青年亚文化与媒介》,陶东风、胡疆锋主编:《亚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1页。
⑮Paul Hodkinson.Goth:Identity,Style and Subculture.Oxford:Berg,2002:p.109.
⑰【英】斯图亚特·霍尔:《表征的运作》,【英】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页。
⑲S.Thornton.Club cultures:Music,Media and Subcultural Capital.Cambridge:Policy Press,1995:p.117.
⑳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3页。
[21]【英】斯图亚特·霍尔:《“他者”的景观》,【英】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