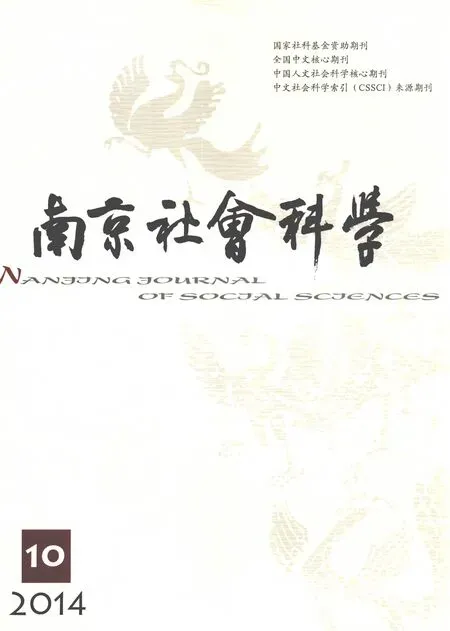超越精神分析:家庭系统心理学与文学批评*
顾 悦
超越精神分析:家庭系统心理学与文学批评*
顾 悦
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对心理学的理解片面局限于精神分析,忽略了这一学科近数十年的发展。家庭系统文学批评正缘起于对这种状况的不满。作为一种心理学范式转换,家庭系统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与情感必须放在家庭的语境中方能得到解读。波恩、萨提亚、米奴欣等人的理论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家庭系统文学批评打破了精神分析的垄断地位,为心理学视角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家庭系统;心理学文学批评
一
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学科与文学的交融、互动、互释。用不同的理论视角审视、解读文学文本,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与影响力。心理学便是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丰富互动的学科,对更好地理解作者、读者、文学人物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理论思路。心理学与文学密不可分,二者都关注人的生活与内心世界,使得二者之间有本质的亲缘性。然而尽管心理学是20世纪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但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对心理学的理解往往局限于精神分析(以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拉康等学说为代表),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当作心理学(psychology)之同义词。事实上,精神分析只是心理学的一种流派,远非心理学之全部。传统精神分析中诸多业已被心理学界扬弃的观点依然被文学批评所使用,而心理学界近一个世纪的理论发展并没有得到文学研究界的足够重视。弗洛伊德理论诞生已一百多年,临床治疗实践早已不会套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弗氏的许多观点被质疑、被修正,然而文学批评界却依然抱守精神分析,对于心理学的发展及各种新学说新流派几乎持着“井底之蛙”的态度,弗洛伊德及“法国的弗洛伊德”①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成为心理学视角的文学批评中的垄断性声音。文学批评家对于精神分析之外的心理学或是知之甚少,或是基本忽略。
此种现状终于在20世纪末引起一些文学批评家的担忧与不满;他们也恰切地指出,文学批评界对心理学的狭隘认识亟待修正。对这一问题提出最尖锐批评的当属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英文系教授约翰·纳普(John Knapp)。纳普一再强调,精神分析批评方法(无论是基于弗洛伊德的还是拉康的理论)倾向于聚焦单个人物的内心,孤立看待个体,并没有将人物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呈现与理解,尤其是忽略了人的社会性。他认为,以心理学视角研究文学的学者应当在弗洛伊德之外寻找心理学的理论依据。纳普同时也质疑了拉康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他指出,拉康的理论是基于传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概念(如压抑、俄狄浦斯情结等),更多的是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的“拓展而非革命”②。同时,文学批评家由于无法有精力投入系统学习心理学(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纳普本人在从教三十年之后又去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因此“图方便”地固守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③。
在阿布拉姆斯的《文学理论术语手册》中,“心理学与精神分析批评”是同一个词条,释文中只提到了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荣格、拉康三位心理学家的理论④。事实上,大量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著作都将“精神分析批评”(psychoanalytic criticism)与“心理学文学批评”(psychological criticism)视为等价,或是只提前者不提后者。为何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的理论垄断了心理学视角的文学批评?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纳普认为是文学批评家对权威的习惯性崇拜使然⑤——文学批评家常年习惯于拜倒在莎士比亚、但丁、荷马等文学巨擘面前,对于权威有一种渴望;他们需要心理学上也有一位类似于莎士比亚的“不是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时代”的权威,因此他们选取了弗洛伊德(后来又选择了拉康作为衣钵继承者)。纳普的观点很有见地,但其实弗洛伊德成为文学批评界的超越时代的“心理学代言人”的原因不仅如此。例如,同样在心理学史上地位显赫的皮亚杰、马斯洛等人为何没有获得文学批评家的青睐?这与弗洛伊德本人与文学艺术的紧密的关系息息相关。与其他很多心理学家相比,弗洛伊德的理论具有很强的人文性,也更容易吸引人文学者。弗洛伊德对文学艺术非常热爱,经典文学作品是其灵感与学说的重要来源,他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以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人物命名,其精神分析著作中也大量探讨了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弗洛伊德的著作也具有很强的文学价值,如哈罗德·布鲁姆就将弗洛伊德视为一位经典文学家,一位“散文化了的莎士比亚”⑥,并认为“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消亡之后仍会作为一个作家而长存于世”⑦。文学批评界对弗洛伊德的非正常偏爱大抵与这些原因有关。
“言必称弗洛伊德”的局限性让一些当代学者寻找精神分析之外的心理学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新工具。约翰·纳普以及葆拉·科恩(Paula Cohen)、杰罗姆·邦普(Jerome Bump)等美国学者开始用在心理学界影响日渐增长的家庭系统理论解读文学作品,这也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精神分析一般被认为是现代心理学的“第一波”,随后的行为主义、人本主义分别是“第二波”与“第三波”。作为一种崭新的心理学流派的“家庭系统理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被认为是20世纪心理学发展的“第四波”⑧。二战之后,受到系统论、控制论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心理治疗(特别是对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临床实践的启发,一些心理治疗师开始将家庭当作有机的情感整体,不再仅仅关注单个“病人”的“疾病”,而是更多关注家庭整体的情感状况与关系模式,“家庭治疗”(family therapy)及“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由此诞生。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有机的情绪整体,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的行为都会影响系统中的其他成员,一个人的行为与情感必须放在家庭的语境中方能得到解读;家庭又是社会的子系统,家庭与社会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家庭治疗秉持系统性的思维方法,不将单个个人当作孤立的存在,而是认为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是理解个体的必要条件。家庭系统理论堪称心理学的一场范式转换。它将家庭当作一个“情感场域”⑨,场域中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其中的每个成员。在家庭系统理论看来,出现精神障碍或是行为异常的人并不是“病人”或是“坏人”,而是不健康家庭的带症者,承担了“替罪羊”的角色;只有改变整个家庭关系模式,才能疗愈症状。
精神分析主要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而家庭系统理论则更多聚焦于关系。家庭系统视文学批评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家庭,将个人当作家庭系统的子系统,认为文学再现的不仅是人物,而是人物所在的系统;在文学作品只有理解了人物所在的家庭系统,方能真正理解人物。这并不意味着家庭系统文学批评忽略人物的内心,而是将人物的内心放在与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关系中进行理解。家庭系统文学批评在一定的语境中探讨人物及其行为,将人物与情节、背景更紧密地连结,更能够通过解读文学叙事中的关系模式,探讨个体心理、家庭关系、社会结构、历史变迁、文化演变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联系。
二
家庭系统理论作为心理学的“第四波”,自有其理论体系与内在机理,这是习惯了“第一波”精神分析的文学研究者需要了解的。家庭系统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半世纪,形成诸多流派;倘若加以梳理,其中最主要的三大流派是以莫里·波恩(Murray Bowen)为代表的历史派、维吉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为代表的经验派和以萨尔瓦多·米奴欣(Salvador Minuchin)为代表的结构派。三个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理论对家庭系统文学批评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莫里·波恩(一译鲍文)是家庭系统理论的最重要奠基人之一;从他的理论转向中我们看到,家庭系统理论的诞生与对精神分析的修正与超越密不可分——这也与家庭系统文学批评的发端十分相似。波恩最初是精神分析治疗师;20世纪50年代他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时发现,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多代过程(multigenerational process),通过家庭中的三代人甚至更多代人发展而来,这样的家庭有特定的关系模式,精神分裂症并不是患病个体的问题,乃是家庭的问题。波恩因此拒绝给患者贴上“精神分裂”的标签,而是认为他们是家庭问题的替罪羊,是不健康家庭关系的症状携带者。波恩进而发展出了一系列家庭系统理论,其核心是著名的“波恩八个概念”(eight concepts of Bowen theory):自我分化、三角关系、核心家庭情感过程、家庭投射过程、多代传递过程、同胞位置、情感决裂(隔离)、社会情感过程。“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the self)是波恩理论的基石,意指一个人成为情感、思想、行为上独立自主个体,同时依然与他人保持连结。完成自我分化,需要“脱离与原生家庭的过度情感依恋”⑩,这也是健康心理的要求。波恩强调家庭中的问题是通过数代人产生的,因此会追溯数代人的关系模式。波恩理论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非常有帮助,尤其适合于解读描写数代人故事的作品,例如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谭恩美的《喜福会》中大量出现的代际关系、自我分化不完全问题等。
“联合家庭疗法”创始人萨提亚的理论带着很强的存在—人本主义色彩。萨提亚受到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马丁·布伯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影响,相信“人类能够展示出积极的生命力量”。萨提亚的理论也体现了对精神分析的超越;与弗洛伊德一味强调性不同,萨提亚认为“维护自尊”才是一个人最本质的动力,性只是其表达方式或从属。“自尊”在萨提亚的定义中指一个人“珍视自我,以尊严、爱和真实对待自己的能力”。一个人的自尊水平主要是在家庭中形成的,来源于早期和父母的互动。自尊水平高的人对于自身价值非常确定,因而能够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做出恰当而有爱的行为,而自尊水平低下的人则过度依赖他人对自己的认可。萨提亚对人际沟通深入研究,发现自尊低下的人往往会采取言语信息与非言语信息矛盾的“不一致沟通”,并且将不一致沟通总结为讨好、指责、超理智、打岔四种模式,这些模式是他们的“生存姿态”与防御机制。萨提亚理论对于分析小说戏剧中的人物很有帮助,例如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中的悲剧可以看作威利及家人自我价值感低下的结果。
以米奴欣为代表的结构派认为,不健康的家庭是因为家庭结构不健康。一个家庭系统中包含诸多子系统,如夫妻系统、亲子系统、同胞系统等,不同子系统之间应当有清晰的心理界限(boundaries),例如夫妻与子女之间需要有明确的界限,清楚彼此属于不同的子系统。倘若子女和父母中的一方“结盟”对抗另一方,就严重的破坏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必然造成家庭问题。米奴欣将家庭称为“身份母体”(matrix of identity),个体的身份认同最主要是在家庭中建立,家庭赋予一个人关于自身、关于世界的基本信念。家庭作为系统,既会影响其所在系统,也会受所在系统的影响;家庭是社会的子系统,社会文化环境是“与家庭系统有同样的特质、遵循同样规律的系统”。比如,一个社会文化系统中暴力充斥,则家庭中往往也充满暴力;如果家庭中常常出现暴力,社会中往往也如此。结构派观点对于文学作品的语境化研究非常有启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人物行为与其社会历史环境之间的联系。
除了这三种主要流派,家庭系统理论的另一些流派也值得文学批评界关注。麦克·怀特创始的“叙事疗法”(narrative therapy)受到建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带有很强的后现代色彩,认为人类对生活的理解源于叙事,故事构建了我们的生活。叙事疗法不去评判、诊断,而是通过与来访者对话,让他们改变自身的叙事,用新的故事代替源有的问题故事,为生命经验赋予新的意义。客体关系理论(object relations theory)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当代发展,同时也是家庭系统理论的一支,是家庭系统理论与精神分析的交界,也是弥合二者的分歧与差异的方式。这些理论取向都值得文学研究界进一步挖掘。
三
反思精神分析及其在文学批评中对心理学话语的垄断地位,促使了家庭系统文学批评的兴起;二者几乎是在同一过程中发生。家庭系统文学批评从诞生至今二十余年,对这一领域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正是邦普、科恩、纳普三位美国学者。三位学者承担了不同的角色。葆拉·科恩堪称家庭系统文学批评实践的先驱。1991年科恩出版了《女儿的两难:十九世纪家庭小说中的家庭问题》一书,以家庭系统的视角探讨了19世纪小说中的家庭,第一次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该书探讨了理查德森的《克拉丽莎》(Clarissa)、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f the Floss)以及亨利·詹姆斯的《尴尬年月》(The Awkward Age)等小说中的家庭关系模式,聚焦于小说中有神经官能症的女儿们,分析她们作为病态家庭系统的带症者的角色,以及其症状作为维系家庭系统的功能。本书以神经性厌食为切入点,而神经性厌食本来是家庭治疗关注的重要问题。科恩通过对19世纪家庭小说(domestic novel)的文学批评,试图“书写一部女儿在家庭中角色的社会史”。这部书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开创了家庭系统文学批评的先河,是极为大胆的尝试与开拓。精神分析统治多年、文学批评界从未有过家庭系统理论的在场,《女儿的两难》一书让这一心理学新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首次产生碰撞,意义重大。
几乎是巧合一般,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杰罗姆·邦普在科恩出版《女儿的两难》的同一年发表了第一篇以家庭系统理论研究文学作品的学术论文。二者可以说在各自独立的学术思考中找到了相同的问题。而邦普的研究实践又有他的个人特色;作为一位对教育非常有追求的学者,邦普将家庭系统理论与读者反应理论相结合,参考了读书治疗、写作治疗的经验,并与心理咨询师合作,帮助学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疗愈家庭创伤。邦普认为家庭系统理论尤其适合研究英国维多利亚小说以及当代美国小说,因为二者都以大量叙写家庭为特征;他也就此撰写了多篇相关论文。在探讨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的文章中,邦普指出,这本书之所以有超越种族、性别、阶级的力量,即因为其对家庭情感动力的再现;莫里森通过对家庭关系甚至家中陈设的描写,再现了波恩所言的“情感场域”。佩科拉的疯狂并不是一己问题,而是家庭的疯狂,她只是家庭的带症者。同时,莫里森通过小说人物,替我们表达了我们未尝能言说的内心深处的“深深的被抛弃感、终极的异化感、作为一个孤儿在世界上的感觉”。邦普认为,通过阅读小说可以纾解与医治这种“孤儿感”(orphan feeling),这使得文学具有强大的心理力量。邦普的独特贡献在于将文学批评带出书斋,直接与教学实践甚至临床心理咨询相对接,这让家庭系统文学批评产生了极为可贵的社会服务价值——这也是此前的精神分析批评所欠缺的。
将约翰·纳普视为家庭系统文学批评的创始人并不为过。纳普对于家庭系统文学批评的推广发挥了最大的影响。他最早呼吁将家庭系统理论全面引入文学批评,并且近二十年来不断的撰写、编辑相关著作,尤其是努力召集更多学者参与这一新兴批评之中,促进了文学研究界对这一批评方法的了解。1996年,他的一本《当代心理学与文学批评》(Striking at the Joints: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and Literary Criticism)明确提出了心理学视角的文学批评应当全面超越精神分析。书中,他将心理学的多种新理论用于文学批评实践,如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其中一章《文学中的家庭系统》即用家庭系统理论研究了劳伦斯与亨利·罗斯的小说。1998年,纳普主编了美国文学期刊《文体》(Style)的专号,主题即为“家庭系统与文学/文学批评”(“Family Systems Psychotherapy and Literature/Literary Criticism”),本期中一批学者撰写了家庭系统文学批评的文章,这一领域始成气候。纳普主编的《阅读家庭:家庭系统与文学研究》(Reading the Family Dance: Family Systems Therapy and Literary Study)于2003年出版,成为家庭系统文学批评的奠基之作。该书收入十余位学者的研究文章,以家庭系统理论的视角探讨了从莎士比亚到拜厄特的不同文学文本。纳普在书的开端对家庭系统理论进行概述,为本著作奠定理论平台;十余位作者的论文则用家庭系统理论解读福斯特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勃朗特的《简·爱》、汤亭亭的《女武士》、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康纳的短篇等,分别聚焦于寻找自我身份时遇到的与家庭过度融合的问题、家庭系统对个人成长的阻碍问题、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家庭问题。汤亭亭一文探讨了在中国文化传统下,“分化”与“融合”二者间的剧烈冲突;简·爱一文中,作者修正了传统精神分析对小说的理解,谈到了简·爱如何在家庭中平衡“自我分化”与“连结感”的,认为其婚姻是简作为情感独立而有安全感的女性做出的选择,是她克服了缺乏原生家庭情感滋养的情况下努力构建自身的幸福家庭的结果。十年后的2013年,纳普又主编了《批评视角:家庭》(Critical Insights: Family),继续将家庭系统批评向前推进。在书中,纳普指出,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的主要批评家在20世纪90年代已然退出舞台,之后的精神分析批评则走入歧途;家庭系统作为当代心理治疗的主流理论之一应当在文学批评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本书将家庭系统理论更全面地应用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例如《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家庭系统》一文认为,娜拉在原生家庭中就是“玩偶”的角色,和丈夫的关系重复了和父亲关系的模式,而她的出走则是对家庭模式的一种打破;易卜生在剧末提到希望,而娜拉出走的行为正是提供了改变家庭模式、重建与丈夫的关系的希望,同时娜拉和其子女的关系也可以真正成为代际关系而非手足关系,娜拉可以成为孩子们“情感上的母亲而非姐妹”——从家庭系统心理学的角度,这样的一种打破模式,反倒是疗愈的开端。纳普的工作使得家庭系统文学批评由个别学者的碎片性尝试转变为被诸多学者所实践的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批评方法。
家庭系统文学批评超越了精神分析对个体心理的狭隘理解,用系统性眼光看待个人与家庭,将个体心理状况置于家庭的背景中加以理解,认为文学文本中的个体所表现出的心理障碍永远不是单独的、个人的现象。从系统视角审视一个家庭及其中的成员,能够发现隐藏在个体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与情感;家庭系统理论也能够在文学批评中理解个体、家庭与社会间的关系,发掘历史文化语境与个体心理的深层联系,为文学文本的解读提供崭新的视角。家庭系统文学批评出现较晚,尽管发展较快、也已有一定的成果,但其在文学研究界的影响力依然尚待提高,也需要更多的学者做出努力。主要值得的拓展方向包括:更清晰地建构家庭系统文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将在家庭系统理论与其他文学理论(如女性主义、后现代理论、叙事学、新历史主义等)之间展开更全面的对话;再次出现《女儿的两难》一样的大部头、成体系的学术著作等。与西方学界相似,国内文学研究界对心理学的理解也主要局限于精神分析,家庭系统视角进行的文学研究同样尚待发展。
家庭系统文学批评并不是试图用家庭系统理论替代精神分析而再次独占文学批评,而是为心理学视角的文学批评提供更多的可能,从而消除精神分析的(不合理的)垄断性地位。家庭系统理论是新兴的心理学理论之一,我们也期待其他的心理学流派进一步被文学批评界所认识、理解并从中获益。
注:
①④M.H. Abrams and Geoffrey Harpham,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 9th ed, Boston: Wadsworth, 2008, p.293,pp.289-295.
②③⑤John Knapp, Striking at the Joints: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p.28, p.28, pp.29-30.
⑥⑦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295页。
⑧Gerald Core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7th ed. Belmont, California: Brooks/Cole, 2005, p.422.
⑨Daniel V. Papero, Bowen Family Systems Theory, Needham Heights: Allyn and Bacon, 1990, p33.
⑩Irene Goldenberg and Herbert Goldenberg, Family Therapy: An Overview, 6th ed, Pacific Grove: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188。
〔责任编辑:青末〕
BeyondPsychoanalysis:FamilySystemsTheoryandLiteraryCriticism
GuYue
Psychoanalysis has long been the predominant voice in the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literature. Literary critics seem to be ignoring the new developments of psychology. Family systems criticism is a response to such neglect. Family systems theory holds that the family is the primary context for understanding how individuals feel and behave. Murry Bowen, Virginia Satir, and Salvador Minuchin have offered invaluable insights into literary criticism. Challenging the monopoly of psychoanalysis in psychological criticism, the fast-growing family systems criticism opens the door to more possibilities.
literary theory, literary criticism, family systems, psychological criticism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家庭系统理论与六十年代美国家庭现实主义小说研究”(2013EWY)、上海市“晨光计划”人才项目“《纽约客》作家短篇小说与战后美国家庭系统”(13CG33)的阶段性成果。
顾悦,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博士 上海 200083
I0
A
1001-8263(2014)10-013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