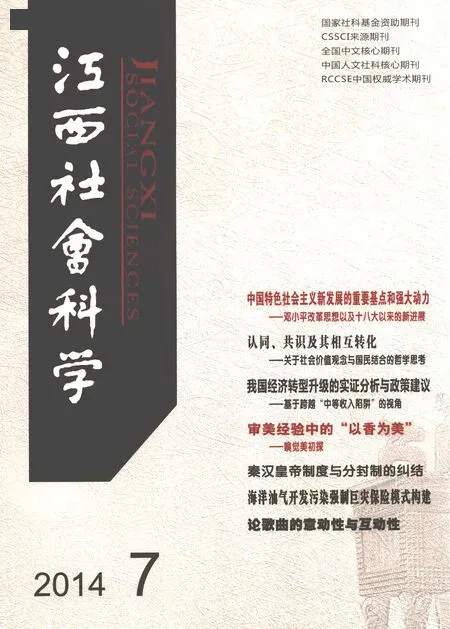论歌曲的意动性与互动性
■陆正兰
在所有的表意文本体裁中,歌曲有着特殊的文化功能。歌曲的起源与发生,充满了意动性。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经典《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名言一直被后世认为是中国诗学的纲领性开端。关于“诗言志”,整个一部中国文学史都在讨论这个“志”究竟是什么,这里不用再讨论了。关于“歌永言”,我本人提出过一个看法,认为它是指歌词“延长指称距离”[1],因为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尚书》里说的“诗”与“歌”,指的基本上是同一种文体,诗即歌即歌词[2](P120)。本文着重讨论的是最后一句“神人以和”,历来注意它的学者很少,更没有人指出其重要理论意义。
一、如何理解“人神以和”?
一般人认为这是指歌曲的礼仪性,或歌曲作为原始巫教的祷文源头,“让人神关系和谐,沟通顺利”。笔者认为对它的理解应更进一步:祭神歌曲的理想效果,是让神(意图中的接收者)与歌者共同歌唱,呼应“以和”而成歌。后世的歌世俗化了,但歌曲这种体裁的根本品质没有变:所有的歌曲,都希望取得接收者参与传唱的效果,这就是本文讨论的歌曲的“意动与互动”品格的由来。
文本的意动品质,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意向性联系。它是某些体裁特别注重的文化功能——期盼接收者在接收文本之后采取行动以“取效”。雅克布森著名的符号主导功能论指出:“当符合表意侧重于接收者时,符号出现了较强的意动性,即促使接收者做出某种反应”[3](P169-184),即本文说的“意动性”。赵毅衡在其专著中指出:“意动性是许多符号过程都带有的性质。”为此,他将符号文本“多少都有以言取效的目的”称为“普遍意动性”,把某些意动性占主导地位的体裁称为“意动性体裁”。[4](P120)歌曲的意动更注重“以言取效”,因此是典型的意动体裁。
“以言取效”来自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说。奥斯汀在探讨语句的品质时,将言语行为分为三种类型:以言言事,即说出一句有意义的话,表达一种意义;以言行事,完成交际的任务:说事、做事、起效;以言成事,通过说某事而造成或获得某种结果。[5](P37-42)这最后一个类型,即是本文着重讨论的:当一个或一种文本的意图性指向接收者时,语句目的是成事(perlocutionary),在接收者身上产生效果。[6](P5)雅克布森认为意动性最极端的形态是祈使句。它在歌曲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和频繁。比如歌曲《大刀进行曲》中唱出的呼吁:“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是再清晰不过的意动了。
歌曲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文字或图像文本。相反,它具有强烈的歌唱实践品质,只有歌众的歌唱实践,才让其成为一首歌。这正是歌曲这一文化体裁的特殊性体现,正如詹姆逊所论,体裁是一种“‘机制’,作家与特定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其功能是具体说明一种特殊文化制品的适当运用”[7](P93)。
歌曲这种不断反复实践的文本特性,实际上是通过歌曲的流传机制来实现的。笔者的观点是“歌必然以流行为目的,任何歌曲都是意图流传的”。[8](P7)更明确说,几乎每首歌创作出来,目的都是为了歌众传唱、意图流传的,歌的产生就是为了流传。
歌曲的这种意动品格非常明显。虽然阐释学也论述接受者主体和发送者主体之间的“阐释循环”,传播学也提出受众反馈的作用,但每种艺术文本意义的实现,即受众对文本的阐释性阅读,作为意义的锚定点是有争议的。有的阐释学家认为作者意图是解释的标准,有的认为“读者有权力使意义蔓生”[9](P321-334)。这场论辩已经延续了大半个世纪,至今结论仍不是很明确。但对歌曲这种体裁来说,阐述标准的种种讨论并不适用,对歌曲文本微言大义的阐释,是歌曲文本的文学性解释,而歌曲不完全是文学。歌曲的特殊性,并不在于读者对文本的阐释性阅读,它的主要文化功能,并不需要对歌词的多层历史文化含义作复杂阐释,相反,歌曲文本的意义必须落实在歌的传唱者身上。歌唱目的并不需要溯回意义发出者的原语境,而更注重应和在场的语境要求。歌众的传唱目的,在于他们进一步使用这些文本作自我表达,传唱是歌者对文本的再创造。传唱者可以抛开作者原意图,在自己现有的语境中重新开辟意义之径。
因此,歌众传唱让歌曲意义具体化为在场意义,歌众并不把作者的意图作为意义的指归,而让自己成为歌曲意义的主宰者。这一点,歌曲明显区别于其他艺术题材。
二、从意动到“无限意动”
文本的模态,就是文本的意图性,在文本中表现在两个地方:一是文本之内的词语意义,一是口气、场合、体裁等文本外语境条件。相比而言,文本内的形式品格虽然比较清楚,在主导格局上却是次要的;文本外的语境条件,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因为语态品格超出文本,是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一种文化意向性契约,由于这个契约,接收者愿意回应发出者标明的某种意图。
上述讨论似乎非常抽象,其实在歌曲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关系极为具体。例如汪峰作词作曲的《存在》这首歌它用一连串的悖论语句,陈述一种哲理,一种有关生存意义的观点:我们的生存目的与我们当下的境况经常是背离的,因此人们经常是无可奈何地做与愿望相反的事。这样一分析,《存在》的文本方式应当是“陈述式”。但实际上这只是语句的内部语义结构造成的假象。这首歌曲,不是用来讨论哲学的,而是用来意动的。它希望听到并传唱的人拒绝苟活,而是振作起来“保持愤怒”,是在号召歌众采取行动,勇敢地“展翅高飞”,过一种积极的人生。因此,即使再哲学,再“陈述”的歌曲,最终也不会丢掉它的意动目的。歌曲作为意动型的本文,总是在提供一种对话情境,此“对话情境”呈现出一种祈使式的呼吁。
请注意《存在》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言说方式很特殊,不是祈使句而是疑问句,这是歌曲常用的特殊意动方式,用疑问句掩盖要求对方采取行动的意图,以缓和命令的严厉或迫切程度。
比如陈小奇作词作曲的《涛声依旧》。歌者以“旧船票”自况,似乎是一首情歌,要“登上你的客船”。但是意动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就像作者本人所说,歌曲的“深层结构,表现的是这个时代人们的困惑。旧船票、客船是个象征,表现出新旧时代之间的矛盾、心态。”[10](P155)既然是一种象征,意义之门对每个歌众来说就是开放的。因此,意动表意是可以无限延伸,可以称之为“无限意动”。不同歌众可以将歌曲应用于不同场合,表现完全不同的意义。
歌曲的这种“无限意动”方式,符合符号学关于意义延伸的原理,接近皮尔斯所说“无限衍义”,即:“一个符号,或称一个表现体,对于某人来说在某个方面或某个品格上代替某事物。该符号在此人心中唤起一个等同的或更发展的符号”[11](P228)。符号的意义,就是被另一个符号替代的潜力。当“下里巴人”被一代代唱下去时,“阳春白雪”无法被传唱,这个歌曲文本便从此消失了。因此,歌曲的意义必须用不断传唱来实现,理想的“歌众”,应该作为一个新的符号文本的“再创作主体”,赋予歌曲新的含义。
三、从意动到互动
歌曲的这种意动性质,进一步造成社会交往的互相意动,互相影响,即歌曲的“互动性”。例如,某诗人喜欢模仿徐志摩的诗风,我们也可以说徐志摩会喜欢此诗人的诗风,这是对“意图循环”和“意图逆行”的一个很好解释。然而,这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态度,在诗的流传中出现的可能是极少的,毕竟不是每个读者都写诗。歌曲则不同,因为每个歌众都要唱歌,每个继续传唱的歌众都“被(原作者)感兴趣”,歌众看中某位作者作的歌,也就是他们自己被某位作者看中,因为歌众要做的不仅是接收一首歌,而且要在传唱实践中对这首歌进行再创造。
歌曲的这种互动品质,也暗合了现象学关于“交互主体性”的看法。胡塞尔对交互主体性概念解说如下:“我们可以利用那些在本己意识中被认识到的东西来解释陌生意识,利用那些在陌生意识中借助交往而被认识到的东西来为我们自己解释本己意识……我们可以研究意识用什么方式借助交往关系而对他人意识发挥‘影响’,精神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纯粹意识的相互‘作用’”。[12](P858-859)他已经意识到所有的“交往”是一种发挥意动性(“对他人发挥影响”)的方式。
因此,真正的意动取决于互动。文本背后的主体关注,是一种“主体间”关联方式。音乐社会学家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指出:“歌曲的本质是对话。”[13](P23)不同于一般日常会话,这种会话更注重理解、认同与协商。歌曲的意动要落实到各种传唱,因此歌众的传唱,对歌曲的发出者有一种回馈性的意动,实际上演唱是一种交换意动的过程。歌曲的意义在传达中重新编码,从而在歌者代表的创作主体与歌众主体之间,制造一种动力性交流。
在歌曲流传的五个基本环节(词、曲作者、歌者、制作传播机构、歌众)中,我们可把前四者看成是一个共同的精英制作集团,最后一环是歌众及其传唱。在其传播过程中,歌众会比一般符号受众表现出更明显的能动性。他们对歌曲的接受,不可能遵循制作精英理想的模式,而是就自己的客观条件和主观需要,予以利用和改造。推动歌曲文本流行的动力正在于歌众不断创造新符号的能动性,正如符号学家达内西所说:“每个人内心都有一股寻找意义和制造意义的冲动,这种寻找导致了符号的产生”[14](P186)。比如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一首耳熟能详的校园歌曲《同桌的你》(高晓松作词作曲):“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它被更年轻的一代,改编成更具当代感的《同班的你》:“你总是唱着不想长大/擦肩就是二十好几/谁拥抱活泼开朗的你/谁陪着犯二的你/谁听了我给你的微信/谁把它彻底清零。”
歌众的这种能动性甚至超过了霍尔的“对抗式解码”、费斯克的“生产者式的解码”,获得了更自由的“创作式解码”。这就是我们在歌唱活动中看到的自由的“翻唱”和“改编”现象。歌众对歌曲文本的传唱实践,实际上是一场情感狂欢。每个歌众都在“演唱中”进行一种个性操演。任何一个歌唱的符号运用者都无法完全控制其符号意义,意义通过在场与缺场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不断增值的新的符号。
四、歌曲是共同主体性的实践典型
尽管在上文中,我们说到了歌众是一种强力的能动受众,发挥着特殊文化功能,但歌曲作为一种特殊的意动体裁,在其生产和流传过程中,它的影响力也受制于歌曲创作——流传的每一环之间的深层互动。
我们看到在歌曲生产流传的全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创作意图性并不完整,前面的总被后面的不断修正,没有一个环节能享受意图的充分自由。换句话说,个体的选择都会受“歌众社群”影响,他们虽有在场的主体独立性,但不可能充分,只有融于一个社群,才可能实现主体完整性。对一首歌来说,流传不仅是每个环节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体现,更要演化成有效的“共同主体性”(com-subjectivity)。共同的主体性,就是激发歌众传唱,在意动中完成意义。
歌曲生产和传播流程中的所有主体,是依靠生活世界的情感经验相互关联,并据此建立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每个人貌似独自欣赏,实际上是在通过主体间性与社群相通。他们哪怕相隔万里,从未相逢,却在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完成一个意义,形成一种社会群体,即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通过这种内部活动,所有参与者都可以相互决定他们个人的行动计划。因此可以无保留地追求他们非语言活动目的”[15](P52)。歌者与歌众的互动,甚至能互相转化,即歌众与歌者互换位置。歌唱行为完美地体现哈贝马斯提出的共同主体论,能使自我与他者紧密地交融,它也是符号的社会性功能的最佳范例。
在歌词中,在演唱活动中,“我”与“你”的语境不断变化,歌词当中的“你”是飘移的,有时候这一句话落在一个人身上,下一句话就变成“我”就是那个“你”,再下一句话就感觉这是一个社会了,再下一句话又可能变成了一个旁听者,这个“你”是浮动的。
一部歌曲史就是一部歌众传唱的文化实践史,歌曲的文本存在品格,充分体现在歌众的传唱实践中。意动性与互动性,并不一定是非常具体的祈使,有时候歌曲请求对方实施的行动,可以很不可解,甚至荒谬。例如这首《祈祷》:“让地球忘记了转动呀/四季少了夏秋冬/让宇宙关不了天窗/叫太阳不西冲”。
这样祈使的目的,似乎离意动很远,只是一个象征姿态,一个促使歌者从凡庸的日常事务探出身来,企及表面上的“不可能”的某种超越,这时候的意动与互动,是一种想象的应和,也正是意动性才有可能做到这种超越。这就让我们回到了本文开头的“人神以和”命题上。歌者(歌曲的创作集团)与歌众(实现歌曲意义的传唱者集团),最终应和而形成的,是歌的“意义场”。歌曲作为一种文化体裁的最终问题,是如何保证一首歌的流传实践不停止,也就是落在歌曲的无限衍生意动性上,这就是歌曲的“人神以和”目的论:让神和人一道唱歌,让听者变成歌众,变成传唱者,成为歌曲艺术的神。
[1]陆正兰.论体裁的指称距离[J].文学评论,2012,(3).
[2]王小盾.诗六义原始[A].王小盾.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辑)[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3](俄)罗曼·雅克布森.语言学与诗学[A].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4]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5]邱惠丽.奥斯汀言语行为论的当代哲学意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7).
[6]John R Searle.A Classification of Illocutionary Acts.Suzame Romaine.Language in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7](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陆正兰.歌词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9]W.J.T.Michell(ed).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10]陈小奇,陈志红.中国流行音乐与公民文化:草堂对话[M].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8.
[11]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vol 2).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 -1958.
[12]倪梁康.胡塞尔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13]Simon,Frith.Popular Music:Music and Society.London:Routledge,2004.
[14](美)马塞尔·达内西.香烟、高跟鞋及其他有趣的东西:符号学导论[A].肖惠荣,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
[15]Juergen 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Cambridge:MIT Press,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