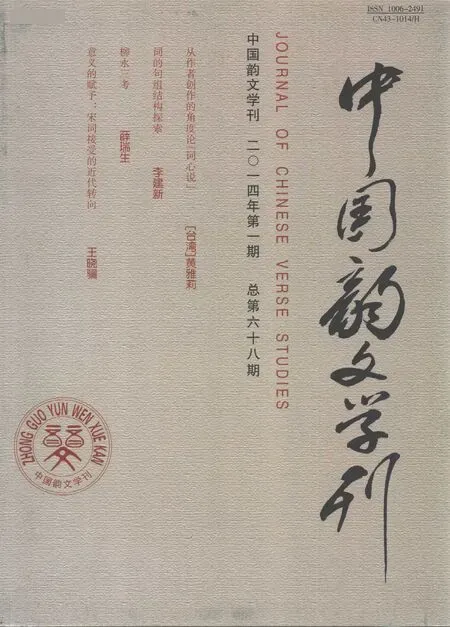意义的赋予:宋词接受的近代转向
王晓骊
(华东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1620)
意义的赋予:宋词接受的近代转向
王晓骊
(华东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1620)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宋词日益被视为与唐诗同尊的传统文学样式,词学也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宋词接受近代转向的完成依赖于接受者对宋词意义的赋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常州词派“寄托说”的基础上,通过对宋词隐秘“所言”的深入追索,赋予宋词更为深刻的内涵意义;第二,从“白话文学”的角度,赋予宋词通俗明晓的语言形式以文学“革命”的意义;第三,从“国粹”和“国学”的角度,从整体上赋予宋词保存“国魂”、振兴民族文化的象征意义。
接受;近代转向;意义赋予
词学研究的“现代化”或者“近世化”进程在最近十余年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杨海明教授曾经指出,20世纪词学研究最大的变化就是“与经、史、子、集的研究一样,正式跻身为‘国学’的一个门类。”词从唐宋时期的“薄伎”、“小道”一跃而成学术研究的“显学”,当然不可能缘自宋词的基本形态和审美风格的改变,而在于近代以来词学观念的转变,确切地说,是近代接受者从内涵、形式乃至文化精神等各个方面赋予早已存在的宋词文本以全新的意义,从而重新定位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宋词接受的近世转向并非由一人一派独立完成的,而是由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知识分子,从各自不同的学术思想、政治立场和社会理想提出各种不同的词学理论或观念,最终与社会文化大思潮合流,形成宋词接受群体、评价体系和接受方式的整体性改变。
一 寄托比兴:宋词内涵意义的赋予
寄托比兴是中国古老的诗歌文化传统,词学接受领域的尊体正是借助于这一传统而开始的。早在南宋,就有人专以比兴之意释词,比如鲖阳居士对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的解读:
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吴江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
再如南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评苏轼《贺新郎》“乳燕飞华屋”词:“兴寄最深,有《离骚经》之遗法,盖以兴君臣遇合之难,一篇之中,殆不止三致意焉。瑶台之梦,主恩之难常也。幽独之情,臣心之不变也。恐西风之惊绿,忧谗之深也。冀君来而共泣,忠爱之至也。”形成了“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的释词路径。
南宋文人的释词法对清代常州词派“寄托”说的形成有直接影响,而相比于南宋时期的零星表述,常州词派把“经世致用”的思想熔铸于词学研究,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并以薪火相继的传承方式,对词学研究产生持续影响。在常州词派的理论观照下,可以说无词无寄托,宋词因此获得了更为“正当”的存在“意义”——某种社会化、功利化的而非纯粹审美的价值,正是通过这一手段,词体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所以说,如果从源头追溯,宋词接受的近代转向应该始于此。
常州词派的“寄托”说所指并非一般性的托物言情,而是与时世紧密相关的政治感慨。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曾明确指出这两者的不同:
感慨所系,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沈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
在常州词派的词学观中,词之所寄,当以盛衰之慨为上,而不是在词中早已陈陈相因的身世之痛。换而言之,社会性的政治抒情高于个人化的情感表达。常州词派对(唐)宋词的解读往往从政治角度出发,把很多产生于花间尊前的游戏之作、声色之词都解读成政治词。比如张惠言《词选》对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词进行一番比附之后,认定“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这无疑是读者之意而非作者之意,可以说是对作品的过度解读。虽然后来谭献曾以其“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开放解读理念,试图为常州词派以比兴释词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但并不能完全弥补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词学理论的重大缺陷。
然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世巨变,却使这一解读方式获得了全新的生命。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社稷倾圮、文化危机都成为摆在世人面前的沉重话题,晚清文人面对内忧外患痛心疾首又无可用武的绝望抑郁,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相比于诗歌的长歌当哭,词委婉幽曲的抒情特质再次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获得旧式文人的青睐,写词权以抒愤,读词聊以舒怀。朱祖谋《半塘定稿序》:“痛世运之凌夷,患气之非一日致,则发愤叫呼,相对太息。……故郁伊不聊之概,一于词陶写之。”王闿运《论词宗派》云:“盖诗词皆乐章,词之旨尤幽曲,易移情也。诗所能言者,词皆能之;诗所不能言者,词独能之。”相比于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王闿运显然更推崇词“尤幽曲,易移情”的审美特质。文人们对词隐秘“所言”的深入体会,其实就是对词意义的追索,更进一步说,是为了崇尚温柔敦厚之旨,以正人心、厚风俗。
词如此重大的社会意义,光靠审美风格的外在表现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只有赋予词内在的醇厚之旨,才能将这种长期以来被归于“笔墨游戏”的文学形式与敦厚人品,重振世风这样的社会重任联系在一起。词人们对常州词派词学观的继承,对温柔敦厚词旨和寄托比兴词意的追索,都包含着他们力挽狂澜、重振世风的努力。有寄托之深意,才有醇厚之底蕴;用比兴之手法,才有温柔之品格。恢复温柔敦厚的诗教,才能厚风俗,振人心,重建民族文化的自信。值得重视的是,在当时大部分文人看来,词之内涵意义一方面仍在于词“可兴可观”的政治内容和教化功能,对宋词内在政治意义的探求仍是重要的解词方式。如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沈祥龙《论词随笔》则云:“词导源于诗,诗言志,词亦贵乎言志。词导源於诗,诗言志,词亦贵乎言志。淫荡之志可言乎哉?‘琼楼玉宇’识其忠爱,‘缺月疏桐’,叹其高妙,由于志之正也。若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则其志可知矣”,都试图从政治寄托的角度来赋予宋词以与诗歌相对等的文学地位。
另一方面词人们开始突破诗教的束缚,对“寄托”本身进行了拓展性诠释。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况周颐“词心”说。所谓“词心”,况周颐《蕙风词话》云:“吾听风南,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 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这种“万不得已”,是个体面对自然社会变迁的无力感和脆弱感,自魏晋以来就是中国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然而,必须承认这种感觉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局势和传统文化节节败退的特殊背景下显然更为突出。有学者曾分析况周颐“词心”的触发点:
……外部世界的风雨、江山,这里的风雨不仅为自然界的风雨,其含义更为宽泛,国家政事、情感曲折、恩怨得失等对一个敏感的词人来讲,无不是一种心灵上的风雨。同样,这里的江山也包含江山社稷的意思。风雨、江山是形成词心的外部条件,它们是形成词人思想的基本因素,同时又起到了一种感情触发器的作用。
词人所寄“词心”由“万不得已”的家国社稷所兴,却归于“无端哀怨枨触”(《蕙风词话》卷一)的个人化情绪,况氏继承了周济“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观点,推举“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蕙风词话》卷五)的涵浑境界。无独有偶,郑文焯也在给夏敬观的信中说:“尝以北宋词之深美,其高健在骨,空灵在神。而意内言外,仍出以幽窈咏叹之情。故耆卿、美成,并以苍浑造耑,莫究其托谕之旨。卒令人读之歌哭出地,如怨如慕可兴可观。有触之当前即是者,正以委曲形容所得感人深也。”[14](P4342)他提倡把词中托谕的“可兴可观”之旨(即社会教化意义),融化在“如怨如慕”的“幽窈咏叹之情”中,以达到“高健在骨,空灵在神”的“苍浑造耑”境界。如果说况、郑的思想在创作上有可能避免强讽美刺带来的刻板,那么在接受上则确实有助于突破以“微言大义”来强解宋词的局限。经过他们的诠释,“寄托”说对词内涵意义的求索,最终落实到“浑厚”、“沉郁”的审美理想之上,不仅使之在学理上更为完善丰满,而且也使宋词获得了与其审美特质相一致的内涵意义。
从宋词文本呈现的整体面貌而言,其盛行于歌馆酒楼、传唱于倡女乐工的传播背景使之带上了较为浓厚的“游戏”色彩。然而,“寄托说”的盛行,却把接受者对宋词的关注集中于其中数量并不占优势的家国情感之上,宋词经典在20世纪以后的确立往往与其“寄托之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寄托说”之影响,远不止于常州词派及其后学。如梁启超注重词的社会内容,他认为辛弃疾的《摸鱼儿》、《念奴娇》和《贺新郎》都蕴藏着与时事有关的“本事”,具有“一般伤春伤别”所没有的深意:“凡文学家多半寄物托兴。我们读好的作品原不必逐首逐句比附他的身世和事实,但稼轩这几首有点不同,他与时事有关,是很看得出来。大概都是恢复中原的希望已经断绝,发出来的感慨”;胡适虽然激烈批评王沂孙咏物词的晦涩,但也认为咏物诗词“最争托意”。而“五四”以后形成的重豪放轻婉约的接受倾向,实际上也与重视政治内涵和教化作用的释词理念一脉相承。
二 白话与民歌——宋词形式意义的赋予
词起于市井里巷,南宋以前语言俚俗的词作并不鲜见。不独敦煌词和散见于各类文献的宋代民间词,当时文人也多创作过俗词,著名的如柳永词“骫骳从俗”(陈师道《后山诗话》),长期被士大夫文人所排斥;秦观早期词深受民间词影响,不乏俚俗粗犷之作;黄庭坚词酷似曲,被后人称为“蒜酪体”(刘体仁《七颂堂词绎》)。两宋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文人化的过程,即用文人文化来改造词由市井民间带来的卑俗之气。
然而,在近现代宋词接受的演变过程中,对词的形式却出现了另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评价体系,那就是从词的白话语言特征和浅近自由的民歌风格入手,赋予宋词不同于文人诗歌的革命性的形式意义和文学地位,胡适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说:“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胡适把中国文学分成两大类:“我们仔细研究中国文学史,发现中国文学可以分成上下两层。上层文学是古文的,下层文学是老百姓的,多半是白话的。……上层的是无价值的,是死的,下层的是白话的,有生命,有力量。”他认为“以俚语为之”的词、曲、小说和戏剧才是“第一流之文学”,是“活文学”之代表。胡适把民间文学看作是“新文学”的重要来源。 词越接近民间,就越有价值:“词起于民间,流传于娼女歌伶之口,后来才渐渐被文人学士采用,体裁渐渐加多,内容渐渐变丰富。但这样一来,词的文学就渐渐和平民离远了。到了宋末的词,连文人都看不懂了,词的生气全没有了。词到了宋末,早已死了。”在胡适的评价体系中,宋词的地位并不取决于它与诗歌审美标准的符合程度,而在于白话语言载体和长短句的自由格式。他把词看作白话诗的起点,“白话韵文的进化到了长短句的小词,方才可说是寻着了他的正路。后来的宋词、元曲,一直到现在的白话诗,都只是这一个趋势。”胡适因此高度赞扬南宋以前的词:“词的进化到了北宋欧阳修、柳永、秦观、黄庭坚的俚语词,差不多可说是纯粹的白话韵文了。不幸这个趋势到了南宋,也碰着一个打击,也渐渐的退回到复古的路上去。”他还把唐宋词中李煜《长相思》、苏轼《点绛唇》、黄庭坚《望江东》、辛弃疾《寻芳草》、向镐《如梦令》、吕本中《采桑子》、柳永《昼夜乐》等七首近乎口语的词列为“活文学”的样品。 基于这一认识,胡适进而把白话宋词看作是初期白话诗歌建设的重要资源。他曾经创作了一些白话词,试图为旧体词向新诗的转换导夫先路。
需要注意的是,胡适等人对白话的提倡并不是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出发的,而是出于提升文学社会功能的目的。胡适的“白话运动”受梁启超“俗语文学”的直接影响。在目睹了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面前的全面败退之后,梁启超认为,中国之积弱积贫正源自于民智低下,启民智才能强国家,他们把白话运动当作救国存亡的重要文化手段。梁启超在1902年不无沉痛地指出,中国四万万人口中,“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以堂堂中国,而民智之程度,乃仅如此,此有心人所以睊睊而长悲也”。文学的普及和大众化被视为开启民智(梁启超把文学的这一功能称为“觉世”)的重要手段,文学语言也就必须向大众语言——俗语靠拢。胡适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白话载体的普及是挽救中国传统文化、挽救人心的重要手段:“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从这一角度出发,梁启超和胡适都把俗语文学或白话文学定位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未来。梁氏认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胡适在他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胡适等人对白话意义的高度重视使宋词因其相对诗歌而言的通俗性获得了青睐。他对诗词之别作了新的论述:“诗与词之别,并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言语之自然而一不近言语之自然也。”并由此认定,由诗而词是文学史的进化,是中国韵文史上的一大革命,宋词中部分存在的口语化特征就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价值和意义。
把国运之盛衰寄托于文学语言载体的革新之上,未免有些夸大了文学的功用,然而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白话的确能够提高诗词的影响力,加速其传播的速度,扩大接受群体的范围。白话诗词在当时确实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如1921年(辛酉)中华书局曾选有“唐宋人古体及五七绝之白描者各百首”出版,虽然在文人看来,“率直浅近都无是处”,但“购者接踵,未几而重版者再是”。在这种情况下,大东书局和文明书局于1923年和1925年分别出版了《历代白话词选》和《白话词选》。后者的编选者凌善清就认为:“词者……若善于倚声不加词藻,则其类于新体诗之处,实较白描之古体及五七言绝为尤近似也”。宋词接受领域对宋词白话形式的肯定无疑改变了宋词接受的途径:在案头阅读成为主要接受方式而使宋词接受越来越成为文人专利之后,白话再次把宋词带给了大众。通俗的语言,浅显的词意并不要求接受者必须积累深厚的文学文化素养,只要初通文墨,就可以欣赏宋词之美。
与文学领域各类“革命”不同,胡适等人的词学观念并不是建立在对词的整体性批判之上的,他们充分利用了宋词本身具有的通俗易晓的语言风格,赋予其新的革命意义,从而在宋词接受领域建立了与白话运动、文学大众化运动相适应的评价体系。平心而论,宋词的语言风格是不能用浅显易晓作“一言以蔽之”的概括的。然而通过胡适等人的表述,相对而言,通俗的、豪放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大众接受者视为宋词的代表作。直到今天,周邦彦、吴文英、王沂孙等以富丽精工或繁复沉郁见长的著名词家,虽然在传统宋词接受中备受推崇,却并不为今天的接受者所熟悉。从文学史观的角度来看,在胡适之后的文学史谱系中,词不再是诗的附庸,而是以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占据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重要地位。应该承认,胡适等人对宋词白话和民歌形式意义的赋予虽然并不完全符合宋词发展的实情,但却改变了大众接受和学术研究两大领域对宋词的整体定位。正如龙榆生先生所描述《词选》的影响:“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中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
三 国粹与国学——宋词民族文化意义的赋予
正如上文所述,宋词地位的上升与清末民初国家兴亡的大背景有直接的关系。从清季“四大家”以遗民心态全力从事词学事业开始,宋词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在当时文人看来,面对西方列国的军事入侵,比坚船利炮更可怕的是文化的溃败和人心的散乱。随着本土文化危机的日益加剧,文人以文学重振民心的努力不再限于某种具体的文学样式,而是上升到“国魂”和“国粹”的高度,对传统文学和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意义赋予。宋词也被纳入了这一体系。
1905年初,以邓实、黄节为发起人,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同年2月,其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创刊。而其宗旨,据最早的3名会员之一马叙伦说:“这个刊物有文艺复兴的意义,而提倡民族主义的革命很卖力,居然风行一时”,有着明确的“提倡民族主义的革命”的目的。《国粹学报》刊行七年,共八十二期,对我国传统学术进行了广泛的钩沉考订、阐述评论工作,涉及面非常广泛,包含了经史子集、音韵训诂、诗词歌赋、金石书画等各个领域。宋词和词学研究当然也被纳入到了“国粹”的范围之内,从《国粹学报》发刊开始,就专设“诗余”栏目,发表当时词人之作。《国粹学报》还刊载了一批在近现代词学研究中极有影响的词话,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最早就是在1908年10月至1909年1月的《国粹学报》上分三期(第47、49、50期)连载刊登的。其余著名的还有况周颐《玉梅词话》(第41、47、48期)、陈锐《袌碧斋词话》(第65、82期)、郑文焯《鹤道人论词书》(第66期)等。
1909年,南社成立,也以保国魂、存国学为其重要宗旨。南社领袖姚光《国学保存论》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魂是也。说文以魂为阳气,故国之有魂,犹人之有精神。”他以国学为国魂,“故一国必自有其学术,谓之国学。……国学亡,则语言、文字、礼俗、政教均随之而亡,而国亦不能独存。然则国学之不可不亟为之保存也明矣。且国存而学亡,则其国虽存,而亦必至灭亡;国亡而学存,则其国虽亡,而必能复兴。是以欲保国,必先保学也。”
高旭《南社启》进一步明确了文学在国学中的地位:“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中国国学中之尤为可贵者,端推文学”。 南社诸子同样把词看作“国粹”,并以此作为抗衡西方文化的精神武器。如冯平《梦罗浮馆诗词序》云:“若以文学论,未必不足以称伯五洲,彼白伦、莎士比、福禄特儿辈,固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先辈远甚。奈何不知希踪李、杜,取法辛、姜,精研而传久远,以光中国?尽弃其国学而学于人,不仅贻文学之羞,抑且为邻邦之鸿博所窃笑。”他把诗词一同纳入“保存国粹,商量国学”的文化事业之中,“谁谓诗词小道,无关于军国大势者耶!年来爱国好古之士,已尽知文学系国家之盛衰,而谋保存国粹、商量旧学,于是诗词歌曲,隐隐若死灰复燃,晦盲否塞之文学界,庶几有光明灿烂之希望”。
在“国粹”和“国学”的范围之内,近代以来的诗词接受彻底突破诗尊词卑的文化等级,形成了诗词同尊的共同认识基础,宋词研究成为学术的一个门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不仅如此,更多的传统艺术形式因“国粹”而与宋词结盟,更拓宽了宋词接受的途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绘画领域的宋词接受。
中国传统绘画历来有所谓“行、戾之争”,即画师画与文人画的对立。然而在西方绘画技法传入的大背景下,这种对立到清末民初已基本消弭,传统文人画家们坚守的艺术阵地所面对的是西方绘画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国画与古典诗词一样,都属于当时文人所努力保存的“国粹”。著名画家吴湖帆曾云:
或云夷画较胜于儒画者,盖未知笔墨之奥耳。写画岂无笔墨哉?然夷画则笔不成笔,墨不见墨,徒取物之形影像生而已。儒画考究笔法墨法,或因物写形,而内藏气力,分别体格。如作雄厚者,尺幅有泰山河岳之势;作澹逸者片纸而有秋水长天之思。又如马远作《关圣帝像》,只眉间三正笔,传其凛烈之气,赫奕千古,论及此,夷画何尝梦见耶?
他对“夷画”的批评隐含着坚持民族传统的苦心,以“儒画”来对抗“夷画”的态度与存国学、保国魂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民族主义的精神寄托使词画结合的艺术产物——词意画得到空前的重视。吴湖帆就是创作词意画的高手,数量既多,艺术水平又高,他的画甚至因“婉约的词意,风韵嫣然的娴静美”而享誉近代画坛,其余如张大千、陆俨少等人也都曾染指词意画。词意画自此成为中国画的重要题材,也成为宋词接受的特殊形式。耐人寻味的是道光以后绘画领域大量出现的“校词图”和“填词图”,更体现出当时文人对填词校词的慎重态度,他们希望通过传统“图史”的形式把词学活动转换成更为严肃的文化事业,载诸青史。
必须承认,宋词地位在近代的急剧上升固然由于文学接受者本身审美趣味的改变,但更多则来自于改造文化、重振世风的现实需求。正如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没有脱离过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大背景,接受领域中的这些非文学因素深刻影响了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说,传统宋词接受领域的“尊体”,是用诗歌的审美原则和价值标准来评判和规范词体,从而将之纳入到诗歌文化序列之中,那么近代尊体活动就更进一步,通过对宋词内涵、形式和文化意义的重新认识,直接把宋词定位为“国粹”,使之与唐诗一起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词学因此也跻身“国学”之列,在词的创作生命日渐衰竭之时,进入学术殿堂,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杨海明.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J].文学评论, 1996(6).
[2]鲖阳居士.复雅歌词[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一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项安世.项氏家说[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4]刘克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A].后村先生大全集[M].四部丛刊本.
[5]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张惠言.张惠言论词[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6.
[7]谭献.复堂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6.
[8]朱祖谋.半塘定稿[M].陈乃乾辑.清名家词[M].上海:上海书店,1982.
[9]王闿运.论词宗派[A].历代词话续编[Z](上),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10]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沈祥龙.论词随笔[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况周颐.蕙风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4]龙榆生辑.与夏吷庵书二十四则[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胡适.词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7]胡适.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A].胡适日记全编(2)[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8]胡适.白话文运动[A].胡适文集(1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9]胡适.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A].胡适文集(1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0]胡适.国语文学史[M].胡适文集(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1]胡适.谈活文学[A].胡适日记全编(2)[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2]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3]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A].胡适杂文集[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9.
[24]梁启超.小说丛话[A].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Z].北京:中华书局,1960.
[25]胡适.文学改良刍议[A].胡适文集(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6]胡适.答钱玄同书[A].胡适文集(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7]凌善清.历代白话词选序[A].凌善清.历代白话词选[M].上海:大东书局,1923.
[28]龙榆生.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9]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M].长沙:岳麓书社,1998.
[30]姚光.国学保存论[A].姚昆群等.姚光全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1]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32]戴小京.吴湖帆传略[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8.
[33]陆俨少.陆俨少自叙[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
[34]夏志颖.论“填词图”及其词学史意义[J].文学遗产,2009(5).
责任编辑 刘建国
I207.23
A
1006-2491(2014)01-0072-06
王晓骊(1970- ),女,江苏苏州人,文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论《历代闺秀词话》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