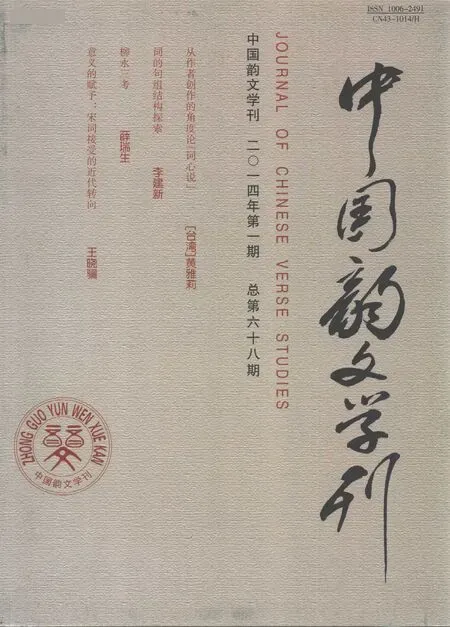皎然“作用”说再释
文 爽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作用”是唐五代诗格中一个极为特殊的范畴,始由中唐诗僧皎然在其论诗名著《诗式》中提出。其诗学意义重要,却因语言简奥而难以索解。众学者对其解说纷纭,至今未有确论。本文的解说将立足文本,以皎然在《诗式》中对于“作用”的解说为中心,以皎然诗论的整体思想为参照,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作用”进行一次源本溯流的探讨。
一 “作用”说的研究现状
皎然在其《诗式》“明作用”条云:
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时时抛针掷线,似断而复续,此为诗中之仙。拘忌之徒,非可企及矣。这是皎然对其“作用”说所做的最为直接的说明。在具体阐释诗歌创作中的诸多问题时他又前后11次使用“作用”一词,可见“作用”在皎然的诗学观念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后人对于“作用”一词的解读,大概可以分为两派:其一,将“作用”解释为与创作主体的能动性有关的艺术构思。这一派人数众多,以郭绍虞、李壮鹰先生等为代表,旁及一些后来流行的出版物如《中国诗话辞典》、《中国诗学大辞典》和《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等,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作用”说的解读虽有部分新意但也基本上从属于这个派别;其二,以“体用”论为方法解读皎然的“作用”说。这一派以徐复观、张伯伟先生为代表,后起的青年学者也有类似的解读。徐复观先生在《皎然〈诗式〉“明作用”试释》中不满郭绍虞的“艺术构思说”,引《诗人玉屑》卷十“体用”项中的材料作“明作用”的注脚,以“言用勿言体”、“言其用而不言其名”、“不名其物”中事物自身的“体用”关系来解释“作用”,徐复观先生认为:“‘体’是指某事或某物的自身,例如灯的自身是体,‘用’是指由某事或某物所发生的意味、情态、精神、效能等,例如由灯所发出的光明是灯的用。所以某事某物皆可谓‘有体有用’。所谓‘不言其名’、‘不名其物’即是‘勿言体’。所谓‘言用勿言体’是说应言某事某物所发生的意味、情态、精神、效能,而不直接说出事物的自身。”并具体解释文中“明作用”条壶公的故事说:“‘瓢’的自身是体,以喻诗的题材。瓢中的天地日月,是由瓢体所显出的作用,以喻由题材所显出的意味、情态、精神、功效等”。张伯伟先生则沿着徐复观的路子,主要根据晚唐五代诗格中出现“作用”的文本如《二南密旨》“论物象是诗家之作用”:“造化之中,一物一象,皆察而用之,比君臣之化;君臣之化,天地同机,比而用之,得不宜乎?”又“论总例物象”云:“天地、日月、夫妇,君臣也,明暗以体判用”;《风骚要式》“物象门”云:“物象者,诗之至要。苟不体而用之,何异登山命舟,行川索马,虽及其时,岂及其用。”,认为“诗人所写的某事某物是‘体’,而烘托、渲染某事某物之意味、情状、精神、效用的‘象’是‘用’。‘君臣之化’是‘体’,用以比况的‘一物一象’是‘用’;‘比君臣’是‘体’,‘天地、如约、夫妇’是‘用’。‘体’属‘内’,故‘暗’;‘用’属‘外’,故‘明’。文学批评中的‘作用’就是这个意思。”综观徐复观和张伯伟的研究,可以发现,“作用”虽是皎然首先提出来的,但二者在解释时都没有以皎然文本为主要依据,反而主要依据晚唐五代诗格以至更晚的宋人语例进行阐释,这多少有违语义训释的基本原则。但二者考检“作用”一词在佛学中的语例,认定“作用”一词亦可简称为“用”,应与“体”相对,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探索。其用“体用论”的方法来解释“作用”,也为研究皎然的“作用”说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
综观前人对“作用”说的研究,有这样几个问题。首先,郭绍虞、李壮鹰等人将“作用”视为与主体的能动性相关的艺术构思,这个说法是否有一定的道理?能否在对“作用”一词的语源探索中找到其根据?其次,徐复观、张伯伟等人用“体用论”的方法解读“作用”说,是依据皎然之后的材料作出的判断和分析,而“体用”是一对内涵丰富、外延广博的概念,能否用“体用”的方法结合皎然自己诗论的文本进行分析?最后,如果郭绍虞等人的说法有其根据,而“体用”论的方法又可以运用其中,那么这两种解说就应该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能够融合的。这样,依据皎然的文本所示,具体应该怎样融合,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 “作用”的语义分析
“作用”一词在皎然的《诗式》中究竟何解?已有研究虽然没有给出统一的解说,却给出了几个值得参考的意见。首先,众多学者往往检典佛学中“作用”的用法来进行阐释,而“作用”又的确多为佛典所用,这就给出了一个有力的探索方向。其次,有些学者从汉语中“作用”的本义出发来谈皎然的“作用”说,这不失为语义训释的一个基本方法。最后,张伯伟、徐复观等人依据晚唐五代诗格甚至更晚的宋人语例来谈皎然“作用”说,这虽然有违语义训释的基本原则,但依据中国古典诗学所常见的现象——一个范畴在被某个人提出之后后人总是不加解释地去使用,仿佛约定俗成地一般——在皎然之后的一些诗评家以“作用”论诗必然会带上他们对皎然诗论的理解,因此考索后人使用“作用”的情况,也可对皎然“作用”说的理解有所助益。
在用于佛典之前,“作用”这一范畴在中国自有文献中已有所记载。如:《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五引《说文》曰:“筋,体之力也,可以相连属作用也。”《初学记》卷二十一《文部·笔第六》引蔡邕《笔赋》曰:“昔仓颉创业,翰墨作用,书契兴焉。”《魏书》卷七十八列传第六十六《孙绍传》曰:“治乖人理,虽合必离;作用失机,虽成必败。”这里,“作用”一词明显带有主动性的色彩,而且大多可以分开解释为“作而用之”。第一句意思是说筋之所以可以形成人体的力量,是因为它们可以相互连接,从而共同运作产生效用和功能。第二句是说仓颉造字之后,笔墨的共同运作使用才兴起了文书。第三句是说统治一个国家,如果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即使现在国家是统一的,终究也会分崩离析,而运作行动若失去了机会,即使暂时成功最终也会失败。只是这种意义,与主体的精神联系得还不十分强烈。但足以为后来佛经翻译使用“作用”这个词埋下语义基础。
到了佛典中,“作用”一词开始具有了强烈的主观能动色彩。据《佛学大辞典》:“作用,有为法之生灭也。”“有为”,是梵文 Asamskrta 的意译,原意为“造作”、“有所作为”,亦译为“有为法”。《佛学大辞典》云:“为者造作之义,有造作谓之有为。即因缘所生之事物,尽有为也。”《俱舍论记》卷五云:“因缘造作名‘为’。色、心等法从‘因缘’生。有彼为故,名曰有为。”具体而言,在佛典中,“作用”是与色、心等法联系在一起的。《瑜伽师地论》卷二五有“四道理”之说:“何等为四?一、观待道理;二、作用道理;三、证成道理;四、法尔道理。”其中的“作用道理”,“谓诸蕴生己,由自缘故,有自作用,各各差别”。所谓“有自作用”,说的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分别相对于色、声、香、味、触、法六境而产生六识,六识分别具备各自的“作用”。《杂集论》卷十一云:“作用道理者:谓异相诸法,各别作用。如眼根等,为眼识等所依作用;色等境界,为眼识等所缘作用;眼等诸识,了别色等;金银匠等,善修造金银等物。如是比。”显然,“眼根”是“眼识”之所依,“色”为“眼识”之所缘。“作用”之得以实现,离不开所依之“眼根”,也离不开所缘之“色”。也就是说,佛典中的“作用”一词,实际上就是指一种认识活动,并且是在主客体双方相互对应的条件下进行的。
另外,佛典中还有大量使用“作用”的例子,这些语例中的“作用”也带有主体能动性的色彩。如:
王怒而问曰:“何者是佛?”提曰:“见性是佛。”王曰“师见性否?”提曰:“我见佛性。”王曰:“性在何处?”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提曰:“今现作用,王自不见。”王曰:“于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
释氏云:“作用是性。”或问:“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此是说其与禽兽同者耳。人之异于禽兽,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释氏元不曾存得。
上堂云:“上上之机,人法俱遣;中下之机,但除其问,犹有法在;下下之机,据问而行。若是出格道人,全体作用。诸上座尽是出格道人,老僧争敢作用?”
第一则提出了“性在作用”的命题,认为“作用”是“佛性”的表现,并且认为只有通过主体的能动性才能见到“作用之功”才能见到佛性,所谓“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是也。第二则朱熹老先生引用了佛家对“作用是性”、“性在作用”的解释。佛家认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即是“作用”,这正是对上文所说六识各有其作用的阐释。第三则区分了不同等级的僧人对于佛法领悟的级别,上等僧人对于人和法都能有很好的领悟,中等僧人有疑问但还可以对法有所领悟,下等僧人则只好带着疑问前行。在这之上还有一种“出格道人”,能够动用全身的力量共同发挥作用去领悟大道。
综上可知,佛学中的“作用”大致有以下几个规定:其一,“作用”是“佛性”的表现,经由“作用”,人才可以理解到“佛性”。其二,“作用”无所不在,所谓“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有其作用。其三,这万事万物的“作用”均需要靠主体的能动性去把握。由于主体能力的差别,导致“作用”也有所差别,其中,“全体作用”是最理想的状态。
作为一个诗僧,皎然有可能将佛学中的“作用”借鉴到自己的诗论中来。而众多学者将“作用”解释为与主体的能动性相关的艺术构思,就“作用”在佛学语源上的意义而言,也是有一定根据的,而不是像徐复观先生所简单认定的那样是不合理的。
皎然应该正是根据“作用”在佛典中的用法,将其运用到诗歌创作上来,认为“作用”是与“自然天成”相对的精心用思。《诗式》云:“五言,周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二子天予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他将自然天成的苏李诗与刻意用思的《十九首》相对比,认为《十九首》“始见作用之功”,这里的“作用”明显是带有主观能动色彩的。皎然之后的学者在使用“作用”一语时,也都带有“苦思用意”之意。如明许学夷的《诗源辨体》不仅沿袭皎然拿作用与自然天成相对比的做法,而且明确指明了作用的“苦思用意”意。其云:“汉魏人诗,本乎情兴,学者专习凝颔,而神与境会,即情兴之所至。否则不失之袭,又未免苦思以意见为诗耳。如阮籍《咏怀》之作,亦渐以意见为诗矣。”又云:“赵壹、酈炎、孔融、秦嘉五言,俱见作用之迹,而壹、融则用意尤切,盖其时已与建安相接矣。”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十第二六用“作用”一语评价山谷诗曰:“山谷之学杜,绝去形摹,尽洗面目,全在作用,意匠经营,善学得体,古今一人而已。”明确指出“作用”即“意匠经营”。可以看出,后世诗论家所用的“作用”一语也基本是指与主体的能动性相关的用意苦思。这也可以印证郭绍虞等人说法的合理性。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体用”的方法能否运用到皎然“作用”说的研究中。徐复观和张伯伟通过对文献的基本搜寻,均认为“作用”一词可以简称为“用”而与“体”相对。张伯伟论之甚详:“唐法藏《华严经探玄记》卷三云:‘道理有四,……二作用道理。……作用亦二,一缘起诸法各有业用,二真如法界亦持等用’;唐湛然《法华玄义释签》卷十七云:‘若尔即是用所依体,体能成用。’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将‘体’和‘用’的关系看作是相即相彻的,虽然可以上溯到王弼,但在佛教典籍中,尤其是华严宗的教义中,这一思想却最为突出。如唐良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卷上《蜜多经序品》云:‘性相名殊,体用无别。’又如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二十三云:‘体外无用,用即是体;用外无体,体即是用。’这是‘作用’一词在佛学中的原意和运用。”这些材料充分说明“作用”即与“体”相对之“用”。徐、张两位先生均用“体用”论去解读“作用”,却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原因何在?一方面是由于二者据以分析“作用”的文本不同:前者从《诗人玉屑》的文本出发,尚且又回归到皎然《诗式》;后者则主要从晚唐五代诗格出发,最后并未回到皎然《诗式》。另一方面恐怕也与“体用”这对范畴本身意义的复杂性有关。研究皎然的“作用”说自然应该从皎然自己的文本出发,那么如果以“体用”的方法直接观照皎然的文本,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三 从体用观看皎然的“作用”说
体用论是中国古代思想中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它萌芽于先秦,发展于两汉,成熟于六朝,是传统儒家、道家、佛家等各种文化形态最基本的思想方法之一,这是学术界的一般看法。体用范畴内涵丰富,外延广博,极其复杂,有学者曾指出:“体用二字在运用上极为灵活,概念的外延也就相当宽泛,除本质与现象的含义外,它还涵括了诸如整体与部分(一多)、内容与形式(形质)、主要与次要(本末)、原因与结果(因果)、具象与抽象(隐显)、常与变(动静)等概念的部分意义。”但总的来说,古人讲体用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其一,体表示事物的本体和本质,用表示本体的表现和作用(这里所说的“作用”不是指狭义的实用功能,而是指事物在各种具体条件下的运动、表现、特征等)。其二,体表示事物的实体,用表示事物的功用。但体无论指本体还是实体,都表示事物相对稳定内在的性质和特征;用无论指表现还是功用,都表示事物相对变化的性质和特征。
关于体用论,还有两个基本规定:其一为“体一用殊”,意为事物的本体是始终如一的,而事物本体的具体作用和表现却是变动不居、错综复杂的,“体一用殊”强调体用关系中的差异性;其二是“体用不二”或“即体即用”,意为体与用相互依存,不可分离,这是强调体用关系中的同一性。
这样,根据“体用论”的基本精神,就可以说:“体”是“用”的承载,“用”是“体”的实行。“体”的概念外延为一种法度与规则,它超越了绝对运动而达到相对静止,成为一种特定的范型,而“用”的概念则依附于“体”而存在,是“体”的“外化”与表现。具体到文人的创作,文体的各种规范就是一般性的东西,因其内在规定性而成为“体”的一部分,而“用”就是对于一般性规定的运用与表现。文人在遵循基本规范(体)的基础之上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将一般的规范化为具体的特殊文本时也便产生了主体的“作用”(用)。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论述《文心雕龙·体性》篇时曾云:“‘体’这个概念强调固有的标准或规范,它先于各种特殊表现,它携带一种参与到特殊表现之中的力量,你可以在特殊表现中把它认出来,但它本身不是那个表现的特殊所在。”这里虽然没有明言“体用”,但却蕴含了“一与多”、“一般规范与特殊表现”的体用思想。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所谓“文之体有常”,即可理解为某一种文类文体的规范性和统一性,而“变文之数无方”,则可理解为表现和运用文类文体规范的方法的多样性和变异性,这种多样和变化又无疑来源于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
对于文体创作过程中的这种“体用”规律,古人也有深刻的了解。明代顾尔行《刻文体明辨序》云:
文有体,亦有用。体欲其辨,师心而匠意,则逸辔之御也。用欲其神,拘挛而执泥,则胶柱之瑟也。《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得其变化,将神而明之,会而通之,体不诡用,用不离体。
明确指出了“文有体,亦有用”这一观点。所谓“体欲其辨”,是指创造具体文体之前要先辨明各种文类文体的基本特征和规范,这是个别文体创造的依据,如果不辨体制规范,过分“师心而匠意”,就会像御马脱了缰绳,无法控制。所谓“用欲其神”,则是指在创造具体文本时又不能拘泥陈规、胶柱鼓瑟,而应善于变化以至“出神入化”。二者合起来既强调了“体”的规范性和制约性,又强调了“用”的能动性和变化会通性。“体欲其辨、用欲其神”体现了文体创造过程中“体一用殊”的一面;同时文类文体又要在具体文体的创造中才能实现,此所谓“体不诡用,用不离体”,体现了文体创造过程中“体用不二”的一面。
由此看来,文体创造过程中的“体”是传统性规范,“用”则包含了主体的创造性。许学夷《诗源辨体·自序》云:
夫体制、声调,诗之矩也;曰词与意,贵作者自运焉。窃词与意,斯谓之袭;法其体制,仿其声调,未可谓之袭也。
这里虽然没有使用“体用”的字眼,但其所谓“体制、声调,诗之矩也”说的正是文类文体的特征和一般规定性;所谓“词与意,贵作者自运”说的则正是创作主体“用”的灵活变通。明陈洪漠云:“文莫先于辩体,体正而后意以经之,气以贯之,辞以饰之。体者,文之干也;意者,文之帅也;气者,文之翼也;辞者,文之华也。”这里“文莫先于辩体”,与上文顾尔行云“体欲其辨”意思为一,都是在强调文类文体的规范性,“体正而后意以经之,气以贯之,辞以饰之”,“意”、“气”、“辞”则都是主体的创造性。
根据这个原理,来看皎然对“作用”的说明。在《诗式》中,有多处说到“作用”的地方。其中直接解释“作用”的地方是:
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时时抛针掷线,似断而复续,此为诗中之仙。拘忌之徒,非可企及矣。
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
这两段话是理解皎然“作用”说的关键。其中,“壶公”典出《后汉书·方术传》。《后汉书·方术传》费长房传中载:“汝南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又《云笈七籖》载,施存为云台治官,夜宿壶中,壶中自有日月。自号壶天,人号为壶公。”“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声律为近体诗体的基本规范层面,属于这一类诗的本体层面的规定,也是写作这类诗体的基本要求。但皎然要求诗人在具体创作中,在遵循近体诗基本规范(声律)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诗人主观之“意”(作者措意)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声律的规范之中创造出一个自由开阔的艺术境界来。具体而言,“瓢”喻“声律”,属于诗体的基本规范,也是一种制约和限制;“壶公”喻诗人之“意”,能够遵循声律而不止于声律;而壶公于瓢中发现、开拓的天地日月这种诗歌境界,就是诗人措意“作用”的结果。所谓“时时抛针掷线,似断而复续”,正是“体”与“用”之间“体一用殊”和“体用不二”的表现。其中,“时时抛针掷线”指的是诗人的“作用”可以千变万化,变动不居,这是“体一用殊”的集中说明;而“似断而复续”则是指诗体的基本规范的制约作用,诗体的这些规范必须要在具体诗歌的创造中才能体现出来,而具体诗歌的创造又必须遵循诗体的这些基本规范,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这正是“体用不二”的表现。诗人写作诗歌,只有做到这两点,才可以称为“诗中之仙”。不遵循诗体的基本规范,写出的不叫“诗”,若只求合于一般诗律,所创造的诗歌又毫无价值。皎然在强调诗体规范的同时,显然更为强调的是诗人的“作用”,所谓“拘泥之徒,非可企及”是也。
那么按照“体用不二”的要求,“声律”如何体现为“意”(作者措意之“作用”)呢?“意”又如何从“声律”表现出来呢?这就需要对诗体的规范作进一步的说明。其实,“声律”(包含对仗)属于诗体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其“全体”,诗体本身还应含有对情的基本要求,《诗大序》言“诗言志”,陆机云“诗缘情”都是在说明这一点。皎然在论述谢灵运之诗时,称赞其能“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也是强调诗体中“情”的规范作用。这样,诗体的规范其实就包含了两重:其一是声律对仗等形式方面的规范,其二是诗歌“言情”的内在规范。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说法正好体现了这一点。其中,“缘情”是内在的规范,而“绮靡”则是形式外在的规范。皎然云“虽有声律,不妨作用”、“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那么诗人的“作用”,也就包含了两重,一是对诗体形式方面的基本规范的具体运用,二是对诗歌言情的基本规范的具体运用。在诗歌的具体创作过程之中,这两重规范是同时起作用的,只是“言情”的规范更为内在,已经化为所有诗歌创作“不言自明”的要求。也因此,近体诗体的规范更多地表现在“声律对仗”等形式方面。所以,皎然说“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只是用“声律”代指诗体的基本规范,并不是说诗体的基本规范只有“声律”。而此处之“意”,就是诗人的“作用”,即能够根据诗体基本规范,创作出能体现诗人艺术追求和趣味的诗歌作品的艺术能力的运用,包含立意、构思、表现等多方面的活动。
皎然论诗,强调“取境”,所谓“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而在论述“作用”时,他又强调“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彼天地日月,元化之渊奥,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授。”仔细对照这两句话,从后一句话来看,皎然所谓的“作用”至少包括两个方面:“放意须险”与“定句须难”,而这一险一难正好与“取境”时的“至难至险”形成对照,这样,皎然所谓的“作用”其实就有了一个指向:诗境。也就是说,皎然的“作用”说即是诗人在诗体的基本规范之下,使用各种手法创造诗境,大致包括对意的重视(放意须险),对物象的选取(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对势的追求(夫诗人作用,势有通塞,意有盘礴)等等,贯穿于诗人创造诗境的全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皎然的《诗式》之“用”还有一般之“用”与特殊之“用”(作用)两个层次。他论诗不仅使用了“作用”一词,还使用了“用”字。如:
不用事第一;(已见评中)作用事第二;(亦见评中。其有不用事而措意不高者,黜入第二格)直用事第三;(其中亦有不用事而格稍下,贬居第三)有事无事第四;(比于第三格中稍下,故入第四)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情格俱下可知也)
这里皎然依据诗歌中“用事”与否以及“情格”的高下将诗歌分作了五等。其中,“用事”之“用”与“作用”的关系值得一辨。皎然在分别第三等“直用事”与第二等“作用事”时,提到:
又宫阙之句,或壮观可嘉,虽有功而情少,谓无含蓄之情也。宜入“直用事”中,不入第二格,无作用故也。皎然认为,诗歌“用事”如果加入了自己的运思,并且有“含蓄之情”,就可以称之为“作用事”,反之,只能称为“直用事”。这样,皎然所谓的“作用”其实包含有“作用事”之“用”,而一般的“用事”之“用”则不属于“作用”。也即是说,皎然所说的“作用”和“用”在广义上皆可与“体”相对,都属于具体的诗歌艺术表现方法;但在种种“用”中又有层次之分,有一般之“用”与特殊之“用”(作用)的差异。皎然使用“作用”处,多是为了强调诗人要在立意、修辞、用事等方面精心构思,力争第一义,其实际指向是“诗境”的创造。简言之,在皎然意中,“作用”之“用”乃是一种最重要、最关键的“用”,以此有异于一般的“用”。
综上所述,皎然的“作用”说本身包含了“体用”论的思想。皎然云“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又云“真于性情,尚于作用”,明确指出近体诗对于声律、对仗的要求(包含“情”的要求)属于一般规范的“体”,而诗人在遵照这些基本规范的基础之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具体诗歌文本时便产生了主体的“用”。这种“用”有两个层次,其一是一般之“用”,其二是特殊之“用”,特殊之“用”就是皎然所谓的“作用”,其内容包括立意、选择物象、用事、比兴以及运句成篇(诗歌体势)等各个方面,贯穿诗歌创作的全过程。它要求诗人在这些方面精心构思,最终创造出无穷丰富、深远的艺术境界,简言之,就是“境思之用”。如此解释,既不违背“作用”在佛典中的原意(主观能动作用),又是从皎然诗论中总结出来、运用“体用”方法观照得出的结论,因此可以融合当今学界对于“作用”说研究的两种倾向。
[1]李壮鹰.诗式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3]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
[4]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徐坚等.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丁福保.佛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9]陈允锋.唐诗美学意味:初盛唐诗学思想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10]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朱熹著.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赜藏主编.萧萐父,吕有祥点校.古尊宿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4.
[13]许学夷.诗源辨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4]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5]景海峰.熊十力[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
[16]姚爱斌.协和以为体,奇出以为用——中国古典文体学方法论初探[J].文艺理论研究,2005(6).
[17]姚爱斌.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8]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9]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0]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辨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