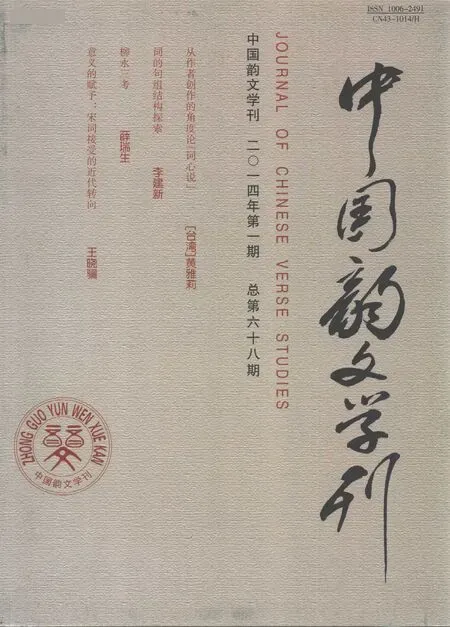论范当世诗学观念的形成
龚敏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9)
范当世(1854-1905),通州(今江苏南通)人,初名铸,字铜士、无错,号肯堂,排行第一,人称范伯子,是晚清诗坛的一员健将。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以“天猛星霹雳火秦明”属之,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以“天雄星豹子头林冲”属之,严迪昌《清诗史》称“在清末堪称名家,而且诗艺确实高的有范当世”,其人在当时就蜚声诗坛,获得时人崇高的评价,他也自视甚高,对其诗歌艺术有着良好的自信。究其根源,首先,范当世的家学为其诗歌艺术提供了良好的生长土壤;其次,他的师承为其诗学提供了宽阔的成长空间;最后,在与各方文学之士的交游切磋中,他的诗艺与诗学渐趋成熟,在晚清诗坛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 家族诗教门风
清咸丰四年(1854),范当世出生于通州范氏四步井老宅。范氏家族是通州的一个文儒世家,为北宋名臣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忠宣)一脉。虽至当世出生时,范氏家族已衰败,但范当世从家族所传承到的主要是绵延数代的孝悌家风和诗文德业并重的家学传统。范氏祖居苏州,经南宋覆亡及元代,范氏一支脉由盛甫公带领,举家迁居江苏南通,成为通州范氏之祖。盛甫公后七世为范应龙,为范当世九世祖,他是南通范氏有史可循的第一代诗人,也是开范家数百年诗教传统的人。
范应龙流传下来的诗很少,曾为庆云令一年,后“忽不乐,解组归,筑尊腰馆啸咏其中”,“尊腰”即取尊崇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之意。如此看来,范氏不恋科场仕途、淡泊名利的家风,从范应龙始肇其端。当世曾九试秋闱皆不第,三十五岁后遂绝意科举。撰《与张幼樵论不应举书》一文,视绝意科举这一举动为继承家声的表现。在范当世看来,范家虽世为寒家,却“显于郡国者四百余年,而载在志书者”,原因即在于“六世有文集”。在范当世心目中,继承并振兴家族的这一缕文脉,相对于科举及第更是自己的使命所在。
范应龙子范凤翼,后辈尊称为勋卿公,是范氏家族诗教传统的第一个高峰。曾与友人龚贤等结白门社,被推为社长,龚贤《寄范玺卿社长》诗称其“百二十人诗独雄”。有《范勋卿诗集》二十一卷,《文集》六卷。董其昌序其诗集称其“性情真,而学术、事功、气节出之为诗,故无之而弗真”,钱谦益序其文集谓其“为诗中和,且平穆如清风,有忠君忧国之思而不比于怨,有及时假日之乐而不流于荒”。范凤翼的诗出于性情之真,在提倡模拟复古的明代诗坛上保持了自己的诗歌个性。范凤翼的诗学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点:其一,他主张善学古人,不必与人同。以为“善学汉唐无汉唐”,“而我为我尔为尔”,“摹古何曾甘效颦,铸今时自标心匠”(《酒间与范穆其山人谈诗兼用为赠》)。其二,他认为诗既应道性情,又应当具有格调气韵,且应讲究诗法,追求既工且文。在《汤慈明诗序》一文中,他推崇汤慈明的诗“出之以性灵,而文之以渊博,研之以精凝,又干之以风力,而需之以功候,故能运今裁而符古法,极人巧而合天工”,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他理想中的诗的境界。第三,他认为欲为诗必先为学以培养性情,这个观点是较为“理学式”的。总的来说,他认为一首好诗的形成与诗人的才气、见识、法度、悟性、学养皆息息相关。范当世在光绪十六年(1890)写给他续娶的夫人姚倚云的家书中评价其六世祖范凤翼的诗“朴而古,与梅村、渔洋异趣”,且在称赞姚夫人的诗艺精进之时,所用的评语却是“酷似我家勋卿”,当世对范凤翼诗的欣赏与自豪之情,此中可见一二。
范凤翼子范国禄,号十山,是范氏家族中著述最丰之人,以诗文名震一时。范国禄交游广泛,与他往来酬唱的有李渔、孔尚任、冒辟疆、侯朝宗、王士禛、陈维崧等。他对于诗的看法与其父有一脉相承之处,如亦认为作诗需学力与天分才力相济,不可专托于性灵;亦注重性情的作用,“诗之为道也,根于性情,深于兴会”,“诗则流溢于性情,涵泳于书卷,陶铸于时命,未尝求工而自无不工”。
范国禄子范遇,有《一陶园诗》。亦以“诗者,言之情也;情者,性之器”,吴兴祚序其诗称“雄浑古茂,酷肖盛唐,悲歌感慨,得风人之旨”。范遇孙范兆虞为范当世高祖,光绪《通州志》列之《文苑传》,今只有《韶亭诗稿》寥寥数篇存世,当世《韶亭诗稿跋》称其为“吾家中流砥柱”。
韶亭以下两代并无大量诗文稿存世。范兆虞次子范崇简仅有《嬾牛诗钞》一册,且不令子孙为诗。这在以诗文传家的范氏家族内是很不寻常的举动。究其原因,许是崇简二十八岁那年(乾隆48年),如皋发生了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文字案,通州、如皋、扬州一带诗文世家皆谈文色变,纷纷焚毁诗文信札。此事对崇简必定影响极深,加上先祖范国禄亦有因文字贾祸流亡的经历,故使范崇简如此谨慎地对待诗文写作。
范崇简孙范如松,有《未信斋稿》。范曾于《南通范氏十三代诗文集序》称其为“范氏诗文世家关键性人物,上承八代诗人之高风,下启范氏诗文鼎盛之局面”。范如松对范氏家族的最大贡献是诗教有方,其三子范当世、范钟、范铠皆以诗文闻于晚清,时人目为“通州三范”。范当世在《〈通州范氏诗钞〉序》一文中如此记述:“自当世甫冠,大人则以此事相督勉,……吾斯集之撰也,岂但以授吾徒友,明吾先人有是学而已,亦俾范氏之子孙简而易诵,知昔人之艺如此其精,而名声利禄之际乃有如彼其澹然者也。不怨不惧,前修之从,则吾范氏之泽未艾乎?是吾父之志也。”文中清楚表明正是范如松保存发扬本家族诗文传统的志向激励了范当世的发愤向学和日后对《通州范氏诗钞》的编辑。这些诗集以文本的方式成为家族精神文化的象征物与凝聚力所在。
除了诗文的世代传承与浸染,范氏家族和大部分的文化世家一样都具有良好的母教之风,这对于这些文化世家的德业和家风的建立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一个家族内的女性是家族意识与精神的真正实行者和推进者。范氏家族内虽并无文学女性,即并无诗文作品流传,但范氏一门内却不缺言传身教,苦心教子的贤德女性。当世十一岁时,曾侍立祖父范持信之侧,听祖父说起高祖母曹孺人之事,曹孺人“尝缺衣食,拒其女弟所遗。雨雪夜,饥,发琴为曾祖鼓之,以释其意”,后范当世在写给其弟范钟的《书与仲弟以答来旨而言近事拉杂不休遂得六十韵》诗中亦提道:
昔我曾王父幼孤,高妣曹君淑以慧。弟兄适戴为高门,赠之衣裘弗加币。亦有短衣持与孤,教儿慎言母手制。高妣令孤往谢姨,便著此衣拜姨惠。谓我茕茕寡妇身,他人寸缕焉能系。此时北风吹敝帏,薄炊米汁看儿啜。夜雪沉沉火不明,孤儿读书不可锐。高妣欣然发旧琴,吾今一奏儿寒霁。他日吾儿不悔穷,乃肯教儿学此艺。嗟尔何曾在祖旁,听闻旧德馨于桂。宗罗陶翟三世誉,各诵所生不能继。
曹孺人身为“茕茕寡妇”,却能不卑不亢拒绝其妹的馈赠,甘于清贫,雪夜为儿鼓琴以为勉励,这些细节无不体现了一位母亲坚毅的品性和贤淑的清德。
范当世母成氏对幼年的范当世也有极深的影响。当世幼年家贫,父亲游幕在外,所得资金须全部奉养父亲,而家庭支出则全靠成夫人以纺纱所得艰难维持。范当世“事亲教弟,极于孝友,待朋友有终始”,其母温良孝顺勤劳的品格自然对幼年的当世形成了良好的榜样作用。这样一种在艰辛生活中依然奋发自励的精神自然地通过母教的影响,再通过一代代语言的追忆成为文本,日渐形成为凝聚家族精神的一种符号。
如上所述,通过对范氏家族自范应龙以来能文之祖辈的诗文作品及诗学观念的初步寻绎,我们不难看出范氏家学门风对范当世诗学性格形成的重要影响。严迪昌独具只眼,早就指出:“其实通州范氏自有诗文化之家法承传”,“读伯子诗,不明乎此‘门风’,必难得其精义”。范当世从父亲及祖先那里获得了良好家风的熏陶,诗文的浸染是其中重要的一面,而范氏家族的家风亦非徒博文而已,更重蓄德,良好的母教和兄友弟恭的孝悌家风与培植诗心文心一起成为范氏家族所始终固守的精神与价值所在。
二 刘熙载、张裕钊、吴汝纶——转益多师
(一)刘熙载
范当世自称“初闻《艺概》于兴化刘融斋先生”,融斋是刘熙载的号,他是清末重要的文学批评家,《艺概》一书是他晚年集大成之作,是他文艺思想的精华所在。当世在早年亲闻《艺概》于刘熙载,这对他将来的文学创作和思想的形成意义是重大的。
范当世在《祭刘先生文》中详细叙述了拜师的经过:同治十二年,范当世20岁,从好友顾延卿(锡爵)处得闻刘熙载大名,当即欲由顾引见,然好友以为当世当时之见识学问不足,故五年后,始与顾延卿同往兴化拜谒,并呈上自己所作诗文,得到刘熙载认可,始正式得列弟子门墙。光绪五年,范当世亲至刘熙载执教的上海龙门书院问业。可惜的是,范与刘相处时间殊为短暂,三年间,范当世亲见问业的机会只有两次。据当世祭文所述,这对师生的第二次会面是在一个风雨之夜,刘熙载“穷日夜之力而与之言”,当世记下的笔记足有七页纸、万余言。日后当世回忆平生十二大快事,其中之一便是这龙门雨夜师生相得的情景。
刘熙载的文学思想在许多方面与桐城派比较接近,如强调文道合一,以为“艺者,道之形也”、“诗品本于人品”,在艺术风格上也更加倾向于阳刚之美,这些文学理论都是趋于正统的,这对刚刚正式跨入文学之门的范当世而言,入门即正,打下了非常坚实的根基。
(二)张裕钊
范当世自述,于刘熙载之后,师从武昌张廉卿先生受古文法。廉卿,张裕钊字,号濂亭,人称“武昌先生”,为曾国藩弟子。光绪六年四月,范当世在江宁由好友张謇引见,在凤池书院谒见了张裕钊。七月,范当世又偕朱铭盘同往拜谒。张裕钊对来自通州的张謇、范当世、朱铭盘十分欣赏,曾感慨“一日得通州三生,兹事有付托矣”。
张裕钊是后期桐城文派的代表作家,主要以古文名于世,范当世问学于张,主要也是学习为文之法。张裕钊有《赠范生当世序》一文,以云作喻,为当世详解作文之道当本于自然的道理。张裕钊有《濂亭遗诗》二卷,其论诗主张主要见于《国朝三家诗钞序》、《复贺松坡》等文。概括来说,张裕钊的诗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清代诗人中最推崇姚鼐的七律、郑珍的七古和施闰章的五律;第二,作诗与作文的取径类似,也是首先强调立意,其次注重音节声音之道。第三,强调学诗可从韩愈、黄庭坚二家中专取一人入手,再镕铸诸家,取法广泛。范当世受张裕钊影响之处首先在于他论诗亦十分推崇姚鼐,作诗称赞“太息风尘姚惜抱,驷虬乘鹥独孤征”。当然他与桐城派的渊源不仅在此,后有详述。其次,亦认为诗文相通,“文之于诗又何物,强生分别无乃痴”,夏敬观《忍古楼诗话》评为“肯堂以文为诗,大都气盛言直,如长江大河,一泻而下,滋蔓委曲,咸纳其间”,切中肯綮。这一点上,张裕钊和范当世应该都受桐城诗学“以文法为诗”的影响。范当世作诗亦十分强调“创”、“生造”,在“声音之道”上范当世亦可谓得其师真传,其《况箫字说》一文,就是专门“发明声音之故”(吴汝纶《答张廉卿》)。在这些地方,我们不难看出范当世的诗学受张裕钊影响颇深。
范当世与张裕钊先后从处多年,曾同在湖北通志局撰辑《湖北通志》,又共往冀州教学三年,范当世称其为“知我爱我教诲我之人”。张裕钊对范当世的影响不仅及于古文、诗学,更在经世致用方面。张裕钊对西方文明持包容开放的态度,主张“穷则变,变则通”,向西方学富国强兵之策。范当世亦同其师,心系时事民瘼,究中外之务,以布衣的身份,对天下怀有无可推卸的责任感。
(三)吴汝纶
后期桐城派的“掌门人”吴汝纶对范当世的诗学影响亦非常深远,当世自称“北游冀州,则桐城吴挚父先生实为之主,从讨论既久,颇因窥见李杜韩苏黄之所以为诗”,在冀州时,当世发愤以编次家集,“尽发所携以北来之稿,连六旬日,废百事为之,既以粗具,以问吴先生”。由此可见,范当世学诗门径,有吴汝纶指点之功,且《通州范氏诗钞》的编纂也得到了吴的指导。
吴汝纶并非范当世正式的老师,当世曾愿执贽请业,被吴谢辞,但当世一直尊称其为挚父先生,两人处于师友之间。吴汝纶在冀州知州任上见到范当世、张謇、朱铭盘三人的唱和诗,遂贻书钩致,当世有诗谓:“吾昔山中年,恐惧畏人识。一诗落人间,遂为吴公得。苦作奇珍收,过求美珠匹。”日后,姚莹之孙姚浚昌嘱同乡吴汝纶为其女姚倚云选婿,吴首先想到的就是范当世,谓:“肯堂诗笔,海内罕与俪者,君为贤女择婿,宜莫如斯人。”(《与姚慕庭》)后果极力促成这段姻缘。吴汝纶尝评价肯堂诗“赋品在鲍(照)、江(淹)之间,此乃追还古风,非时俗所有”(《答范肯堂》),又谓其“海内文笔如范肯堂者,某实罕见”(《与姚慕庭》),评价极高。
吴汝纶的诗学集桐城诗学与湘乡派之大成,以姚鼐所选《古文辞类篡》、曾国藩所选《十八家诗钞》为后学唯一正鹄。其诗学观点与张裕钊接近,推崇施闰章、姚鼐、郑珍三家,亦主张学诗从黄庭坚入手,反对荡灭法则的性灵诗学。
范当世的诗学先后受张裕钊、吴汝纶影响而取道曾国藩,并直指桐城诗学(当然,他日后与桐城姚氏的联姻更是加深了桐城诗学对他的影响)。曾国藩论诗亦推崇姚鼐,同时亦推崇宋诗。范当世不只在一处表明他自己最尊崇的人是曾国藩,称自己是曾的再传弟子,“私淑平生无不在”。当然,他对曾的景仰也许不仅在于曾国藩的诗学,更在于他的事功。
三 文学交游
范当世一生虽科举不利,却以一介布衣,满腔诗才,名动卿相,尽交天下英才。在他创作的一千多首诗歌之中,与所交游的对象的唱和之作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因此,考察他的文学交游更有助于理解其诗歌面貌形成的外在因素。
(一)群人之所聚,能为风气先
青年范当世在家乡通州时就常与一群志气相投的好友游山玩水,组织诗酒集会,把酒言谈。这些青年时代结交的好友多与其相交一生,而故乡朋友酬唱往还之乐也成为范当世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快事之一,其《水心亭宴集》诗序道:“故乡朋友之乐,莫盛于光绪五、六年间水心亭宴集,盖常事也。大抵晨夕共者,吾与马勿庵、顾晴谷、王云悔,时时至者,顾延卿、顾涤香、裘英及吾弟仲林,二三至者,周彦升、张季直、朱曼君,若樵秋则一至而已。”诗中称:“群人之所聚,能为风气先。”可以想见当时这群年轻人的抱负与远见。
其中,范当世与顾锡爵的交情开始得最早,“十五逢延卿,十六知名字”,“少小无猜长无忌,乐群怨别真欢喜”。延卿是顾锡爵的字,他比当世年长七岁,如皋人。姚倚云《同夫子和顾延卿见贻原韵》诗谓“君之朋侪只顾、吴”,其中“顾”即指顾延卿。范当世就是由他引荐才得以列入刘熙载门墙。光绪五年,顾延卿应张树声之邀赴广州入其幕府,在广州得以拜清末岭南经学大师陈澧为师。临行前,当世为之设宴饯行,作诗十首以送别。光绪十六年,顾延卿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回国后投入维新变法运动。他与范当世在诗、文、思想各方面都很接近,两人集中互赠诗篇往来非常之多,堪称知己。当世病故后,他有《哭肯堂》七绝四首,其四云:“顾范交情世所知,幼同艰苦长同师。以君授我诚天意,来吊何须置一辞。”
范当世十八岁时结识张謇,张謇早年的日记中经常描述到两人联床话雨,倾心交谈立身救穷之道的情景。在他们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曾与朱铭盘一起共游江宁浦口,三人舟行联句,成《哀双凤》一诗,流传一时,王庚《今传是楼诗话》评为“哀感顽艳,荡气回肠,亦可见三君少年时才藻之盛”。
范当世与张裕钊、吴汝纶的缘份皆始于张謇的引见,在范当世由吴汝纶介绍进入李鸿章幕府后,张謇因对李鸿章不满,亦与当世异趣,两人遂数年不通音问,中日甲午开战后,张謇跟随其座师翁同龢,是主战派的首领,参劾李鸿章最激烈,他对依附于李鸿章的好友的不满可想而知。范当世在为张謇父亲所作的祭文中感喟“殆昔勤而今惰,岂今疏而昔亲”,已含蓄表明两人关系的疏远。但根据二人诗文日记,至少在光绪二十二年,两人已恢复了交谊。是年张謇有《纪梦》一文记到当世到他的纺织厂参观话旧。二十五年冬至,两人夜登狼山,探讨家乡的发展方向,当世有《同何眉孙、张季直夜登狼山,宿海月处》一诗记录此事。二十八年,范当世作《适与季直论友归读〈东野集〉遂题其端》一诗,此诗中消息耐人寻味,既论友,亦可论诗,诗中借论韩愈、孟郊诗之异同来论友谊之性质,“交友异性非所患”一语,当是从自己与张謇的友谊有感而作。两人之友谊虽中间亦有过罅隙,但走出“牛李党争”的局限后,他们的友谊更上了一个层次,求同存异,共同致力于乡邦建设,张謇致力于实业兴民利,当世究心于教育正人材,相辅相成,正如诗中所谓:“刚克柔克有二道,相成相反兹焉殚。”
张謇在《日记》中评价当世诗文谓:“非独吾州二百五十年来无此手笔,即与并世英杰相衡,亦未容多让。”老友张謇此论非仅出于私谊,更有基于整个文坛来作出的衡量。
与范、张齐名的朱铭盘是泰兴(今泰州市,当时属通州)人,即上文《水心亭宴集·序》中提到的“朱曼君”,他与范、张号为“通州三怪”,同拜于张裕钊门下学习古文。朱铭盘尤擅骈文,章太炎《桂之华轩诗文序》称“其文上规晋宋,下亦流入初唐”,刘声木谓其“诗笔横空盘硬,五言善学太白,七律亦有奇气”,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评其诗曰:“俊逸绝伦,泽古甚深,盖才人而兼学人也。”。
与其他青年时代的好友一样,范当世与朱铭盘保持着经常的书信往来,借诗歌酬唱,互诉衷肠。朱铭盘后弃文从武,客旅顺军幕,曾收到当世寄来的照像,题诗于后,诗中亦历数与范当世交往的种种往事:“水心亭上二十四,目长眉远丹肌肤。黄鹤楼边政三十,气充骨劲耐歌呼。论文不眠童仆怨,绝学锐讨门户孤。”
当然,与范当世有交往的同学少年不止于此,但顾锡爵、张謇、朱铭盘是与范当世交情最深的三位,也是对范当世的文学创作具有深远影响的三位友人。他们之间在文学上互相影响砥砺,但同时诗文又不是他们的最高追求,朱铭盘弃文从武,张謇以实业救国,范当世抱有经世之心,中年以后投身乡邦教育。可以说,虽然他们自青年之后的人生选择与轨迹不尽相同,但诗文上的相通与互相理解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慰藉,来自相同的地域乡土也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他们共同的文化和心理内涵,这使得他们之间常有更多不言而喻的共同语言。
(二)北方文学之盛
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间,范当世被吴汝纶招致冀州。吴汝纶在北方先后垂教三十余年,座下积聚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文学之士,当世在冀州三年,充分见识了北方文学的盛况,与吴汝纶席下文人雅士论诗作文,共同致力于书院教育,甚为相得。其中与范当世往来最为密切者,当属王树枏、贺涛与言謇博,下略分述:
王树枏,字晋卿,号陶庐,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称其亦师事张裕钊、吴汝纶,其文章“气骨遒上,实有得于阳刚之美”。他著述有四十余种,对群经诸子、舆地历史、外国载籍皆十分熟悉。范到冀州时,王树枏时任信都书院山长,数月之内,范当世尽读其诗歌、骈文、墨子注、古文,对王树枏“益服其无所不能”。
王树枏亦有诗《赠无错》,诗中称“君已变瑰怪,捷猎翔龙虬。君乃弗自伟,日日加鞭鞧”,对当世文学才能和努力极力称道。范与王的文学交往可谓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两人并常常直言批评对方诗文之不足,堪称君子之交。
范当世在冀州还结识了武强贺涛,吴闿生《晚清四十家诗钞·自序》称,贺涛与范当世时有“南范北贺”之目。贺涛时为信都书院主讲,长于古文,严守桐城义法。与当世从游时,常不肯为诗,当世有时便强拉他作诗。贺涛曾指出范当世的文才与通州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盖通之为州,江海所汇,形胜冠东南,君生长其间,恣山水之好”,再加上成年以后“远客四方以博其趣”,“故其文恢谲怪玮不可测量”。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范当世的诗歌与文章实属知人之论。
言謇博也是范当世在冀州结交的文学之士,但他是江苏常熟人,因随侍父亲言应千出任新河县令而来到北方,在当地得闻范当世大名,而以乡人之谊上谒,由此订交。言謇博的文才、性格与当世相近,两人由互相欣赏而成为至交。
范当世留下了大量与言謇博相关的诗歌和书札,许多内容皆探讨诗歌。当世视言謇博为论诗之知音,曾自道“三日不闻提壶庐,便愁吾友诗肠枯”。两人常互相赠诗改诗,言謇博面对范当世对其诗的修改,尝自陈“夙好义山,为之已久,不能骤改”,愿剂之以范说。两人又有几十封书笺往来,在《与言謇博书》之六中,当世指出诗歌“第一韵味胜,而气势乃次之,典实文雅或居其三”,并具体点评了言謇博寄赠的一些诗歌,以其“清极生映而故实亦不碍气”的诗歌为最佳。在与言謇博的书信中,范当世多处强调作诗要追求“清”、“奇”和“独造”,在立意用词上讲究独创性,范当世的诗学主张于此亦可见一斑。
(三)从妇氏,数门风
范当世与桐城派渊源甚深。他早年便心仪桐城正宗,在师事张裕钊、跟随吴汝纶的过程中得以上溯自曾国藩、桐城派,在之后与姚蕴素的联姻中,更是融合了桐城妇氏门风,直接与桐城贤嗣交往,与其妻兄姚永朴、永概、连襟马其昶等围绕在其岳父姚浚昌周围,形成了一个小文学团体。
范当世丧偶之后本不欲续娶,与姚氏联姻,吴汝纶极力撮合固有功,恐范当世本身对桐城正宗、惜抱贤嗣的倾慕亦占有极大的因素。姚夫人雅丽出众,吐属不凡,当世再婚后也不由得志得意满,作诗谓“结交颇尽东南美,娶妇能兼大小桥”,在赠给阳湖张仲远的女婿庄心嘉的一首诗中,他宣称:“桐城派与阳湖派,未见姚张有异同。我与心嘉成一笑,各从妇氏数门风。”诗中无不透露出以妇氏门风自得的心境。
光绪二十七年,当世作诗《戏赠沈童子》,谆谆告诫沈童子“息壤在桐城”,既是鼓励沈童子从桐城派中寻找文章精进的动力,也是道出自己文学的动力和渊源。范当世对桐城先贤皆充满敬仰,作诗称“有文支拄山与川,恍人有脊屋有椽”,肯定了姚范在桐城派中如支拄如屋脊般不可动摇的地位,且尤为赞赏他所开启的“不与时媚妍”的文风一直沾溉润泽着姚氏后人。又以姚鼐所开创之桐城派远超当时所见其余各派,不乏溢美之情。
范当世的岳父姚浚昌,号慕庭,姚莹子,其诗集有《远心轩诗钞》、《性余诗钞》等。姚浚昌沾溉家学,亦好诗,“其于诗独有天得,其诗冲澹要眇,风韵邈远,善言景物以寄托兴趣,能兼取古人之长,自成其体”。徐宗亮(姚永概岳父)甚至称桐城二百年诗史上,姚鼐之后推方东树,方东树之后首推姚浚昌,可见其诗自有所长,因此他与同长于诗的女婿范当世颇为投缘,常“吟咏无虚日”。
姚浚昌生有五男三女:长子姚永楷、次姚永朴、次姚永概,次永棠,次永樛;长女姚倚洁,嫁桐城马其昶,次女姚倚云,嫁范当世。姚永楷论诗取向与当世不同,当世谓两人“酌酒欣然对雨风,论诗各有千秋抱”,其诗当世称之曰:“大兄诗味好,王孟恰相宜”,风格比于王维、孟浩然间。姚永朴,字仲实,晚号蜕私老人,为桐城文派之殿军人物,其诗与古文风格“古淡”。姚永朴称“范君天下才,囊空学则侈。高吟动江海,李杜近在咫”(《闻仲妹将至皖作诗寄之》)。两人曾诗篇往复,共探讨“诗境”问题,当世诗中称“与子婆娑见真意,公然一蹴杜欧间”,可见与姚永朴的往还讨论,对当世诗歌路数的取径与走向有很重要的影响。当世去世后,永朴泫然成咏:“诗成泣鬼神,宁为近代束?”(《予交海内贤士甚寡偶怀逝者得五君泫然成咏》五首之四)这无疑是对范伯子诗歌的最佳总结与肯定。姚永概,字叔节,古文尽得桐城文章家法,诗亦为谈艺者所推服,姚永朴尝谓“继先考而起者,莫如吾弟”(《慎宜轩诗序》),可谓桐城诗派的最后代表。永概精于诗,亦擅评诗,当世去世后,永概为之作《范肯堂墓志铭》,文章写得情感真挚,其中对肯堂诗歌的评价尤为公允,从诗与史的角度指出诗歌从有明以降,即“兢兢于格律声色,公然模袭”,而清以来,“恃一国窳败不振之故习,不足敌彼族之方新”,以导致甲午庚子之乱,而范当世正是处于这个历史时期,“起江海之交,太息悲伤,无所抒洩,一寓之于诗,其诗震荡开阖,变化无方”。率先指出了范当世的诗歌与时代的密切关系,其诗非仅逞才使气之作,而是借诗歌来谱写在晚清日渐衰微的政事格局之中士人心路演变的真实历程。姚永概的诗学观点多保留在《慎宜轩文》、《慎宜轩日记》中,总括起来,大致为注重“才”、“学”、“境”的统一,尤为强调个人的“胸襟”与“寄托”,强调作品要有个人特色,有自立之处。这与范当世强调“独创生造”及力求“自立而不依人”的主张自有共通之处。
范当世与姚氏一门兄弟感情和睦,他在诗中抒发感慨道:“龙眠挂车妇氏物,犹许半子为家园”。正是在这种互斗文藻,切磋诗艺的环境中,范当世的诗艺也日趋精进。
(四)从桐城到江西
范当世续娶姚倚云之后,足迹开始游走于桐城与江西之间,在与江西义宁诗人陈三立结交后,他也更多地与江西派诗人交流,其诗学从桐城到江西,亦得到了更大的拓展与融合。
范当世与陈三立二人诗路接近,初识便一见如故,引为诗学上的知音,后更结为儿女亲家,范当世女孝嫦嫁给了陈三立的长子陈衡恪。两人诗集中有不少互为赠答酬唱之作。二人借着诗歌往来,各抒怀抱,同处末世,有许多共通的话题和情感。当世去世后,陈三立甚至有“牙琴为绝弦”之叹!两人之惺惺相惜,前人多有记载。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谈陈三立”条云:“‘公知吾意亦何有,道在人群更不喧。’又曰:‘万古酒杯犹照世,两人鬓影自摇天。’此‘使君与操’之胜概也。”意指陈三立对当世的诗艺极为叹服,引为知己对手之意。陈三立读到范当世的《中秋玩月》诗,发出了“吾生恨晚生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得有斯人力复古,公然高咏气横秋”(《肯堂为我录其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诵之叹绝,苏黄而下无此奇矣,用前韵奉报》)之感慨。范当世生前也对陈三立的诗歌作出过评价:“伯严文学本我之匹亚,加以戊戌后变法至痛,而身既废罢,一自放于文学间,襟抱洒然绝尘,如柳子厚也。此其成就且大于苏堪(郑孝胥)矣。伯严诗已到雄伟精实,真力弥满之时;所欠者自然超脱之一境。”所评实属肯綮中的。
四 结论
汪辟疆评伯子诗谓“渊源所在,则得力于李、杜、韩、孟、苏、黄为多,故能震荡开阖,变化无方”,所评甚确。观伯子诗,可谓转益多师,变化于规矩绳墨之中。他的诗学,早年以其天分才力加上家族祖辈诗文传承的熏染沾溉,而打下良好的根基,正式学习文学则得到刘熙载、张裕钊、吴汝纶的先后指导,上接桐城,得之桐城甚多。中年以后又与桐城姚氏联姻,更加融合了妇氏门风,尤其继承了桐城诗学的独创精神,自道其诗“无意于学人,出手类苏、黄,亦所谓近焉者”(《与俞恪士书》),主张学诗须自立。四十岁后又多与同光诗人交往,其诗艺和诗歌境界又得到了更大的拓展,形成了“盘空硬语真能健,绪论能窥万物根”的个人风格与特色。
在范当世诗学性格渐渐形成的过程中,尤为重要的可以说是以下两点:一是其自身通州范氏家族几代的文学积累对范当世产生了内在的已融在血缘中的深远影响,使其生出“诗是吾家事”的自信,并以此为内动力来整理家族诗文,传承与发扬家族的文化。二是通过联姻,他与桐城姚氏,江西陈氏两大文学世家产生了交往与融合,由此对其文学特质的形成也自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徐雁平所指出的:“婚姻中的门当户对,是选择性的‘类聚’,独木因此汇合成林,有树林才能形成或影响一地的气候。一个文学家族通过家族内部文学活动以及与当地的文学交流,确立其身份、建立其影响,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具体的场域;而联姻可以将数个类似的场域联系在一起,并经由文学、学术活动的整合与促进,从而形成较为明确的文学(学术)群体或文学(学术)流派。”从姻亲网络的角度去考察范当世诗歌特质的变化与形成,其脉络或许将更为清晰可见。从这个角度对范当世诗学作出的考察,也可以成为研究清代世家联姻与地域流派文化关系的一个极佳个案。
[1]严迪昌著.清诗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2]范当世著.马亚中,陈国安校点.范伯子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黄传祖辑.扶轮广集[M].清·顺治十二年张缙彦刻本.
[4]范曾编.南通范氏诗文世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5]寒碧笺评.范伯子诗文选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6]严迪昌著.范伯子诗述略[J].文史知识.2003(8).
[7]张裕钊著.濂亭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
[8]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9]吴汝纶著.吴挚甫尺牍[M].国学扶轮社,宣统二年印本.
[10]顾锡爵著.顾延卿诗集[M].民国23年排印本.
[11]张謇著.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2]朱铭盘著.桂之华轩遗集[M].1934年泰兴郑氏铅印本.
[13]刘声木著.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M].合肥:黄山书社,1989.
[14]汪辟疆著.王培军笺证.光宣诗坛点将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5]王树枏著.文莫室诗集·信都集[M].西北文学文献(第15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16]吴闿生评选.寒碧点校.晚清四十家诗钞[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17]贺涛著.贺先生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
[18]吴汝纶著.桐城吴先生文集[M].光绪三十年恩绂等刻桐城吴先生全书本.
[19]姚永朴著.蜕私轩集[M].民国十年秋浦周氏刻本.
[20]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1]汪辟疆著.张亚权编撰.汪辟疆诗学论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2]徐雁平编撰.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M].南京:凤凰出版集团,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