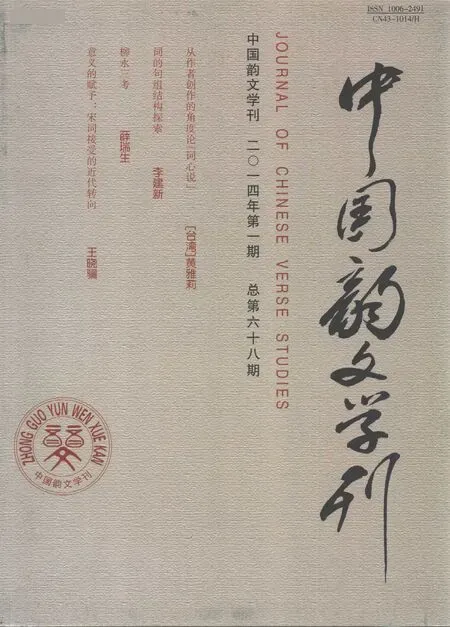追寻“学者”滋味:张栻题画诗的审美旨趣
杨万里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并促成“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的学术格局。为其学所掩,历来对张栻文艺思想的关注甚少。张栻提出了中国诗歌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个诗学命题,即“学者之诗”论:“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或问其故,曰:‘非学者之诗。学者诗读着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此后“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成为宋之后两种主要诗学范式,足见其影响之大。但对这一重要命题,学界的研究视野基本限于诗学范畴,殊不知对“学者”滋味的提倡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观点,不仅在他的诗文创作中有所体现,亦是他绘画思想的重要美学理念。张栻并无严格的绘画理论,也基本不作画,但我们可借助对其题画诗的分析,去探索他观画时所看和所感的视角与兴趣点,从而深入解读其品鉴旨趣和审美理念。题画诗是一种诗画融合的艺术,好的题画诗与画无论从创作构思、意境塑造与审美趋向上均达到了高度参融与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因此,分析张栻题画诗的审美旨趣,便可进而得出其画学思想对“学者滋味”的美学追求。
一 携山水而去:题山水画诗之创作动机
张栻虽不作画,但他是极其喜爱画的,尤其山水画,这主要源自他的山水情怀。张栻对山水有着近似痴迷的向往之情,他的内心有着强烈的陶氏情结,厌薄官场而本爱丘山。他在《清明后七日与客同为水东之游翌朝赋此》一诗中说:“平生山水癖,妙处只自知。夙约常寡味,邂逅惬心期。幅巾与藜杖,安步随所之。朅来坐官府,颇觉此愿违。”可见他在信步游山水的过程中能够体验到人生之乐,所谓“妙处只自知”。而从他其他的山水诗中可知,这种“妙处”非如传统文人游山玩水世俗之乐,实则是理学家于自然山水中悟道、得道的一种快感体验,如他《题城南书院三十四咏》中的以下几首:“秋风飒飒林塘晚,万绿丛中数点红。若识荣枯是真实,不知何物更谈空。”“和风习习禽声乐,晴日迟迟花气深。妙理冲融无间断,湖边伫立此时心。”“西风夜半摧炎暑,晓看云横天际秋。时序转移皆妙理,惟应及早戒衣裘。”均是在游览山水的同时观物穷理,从而获得体道之乐。对于“理”与“道”,理学家喜欢反复涵泳咀嚼,从而温故知新,因此张栻有一种将所游山水携之而去的冲动。能实现其愿望的只有两种艺术形式,即诗与画。对不擅作画的张栻而言也只能作诗了,他在《二使者游东山酒后寄诗走笔次韵》中云:“壮岁几成山水癖,年来袖手不能豪。忽传灯底诗篇好,但想云间屐齿高。”又云:“领略正应胸次别,吟哦更觉笔端高。”可见,对于多不擅画的理学家而言,唯有诗歌可以将山水之景与体道之乐集合一体,这也是理学家喜欢创作山水诗的一个主要原因。
谈完诗再来看画,张栻虽选择了诗来满足自己携山水而去的愿望,但有时又想将满眼青山绿水形之为画。即使他并不擅画,但正所谓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如他在《和朱元晦韵》中说:“一见琼山眼为青,马蹄不觉渡沙汀。如今谁是王摩诘,为写清新入画屏。”诗易于留山水之情理而难于留形,画难于抒发情理却可写形。如此则集二者于一体的题画诗最能慰藉张栻之心,且看他的《和元晦咏画壁》:
松杉夹路自清阴,溪水有源谁复寻。
忽见画图开四壁,悠然端亦慰余心。
这首诗被宋人孙绍远选入《声画集》,是他唱和朱熹的《壁间古画精绝未闻有赏音者》而作,原诗为:“老木樛枝入太阴,苍崖寒水断追寻。千年粉壁尘埃底,应识良工独苦心。”朱熹的诗是题壁间精绝的古画而作,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感慨议论。张栻的这首和诗也是如此,前两句写画之景,后两句抒发情感。不过前两句虽写景却蕴含着穷理探源的理趣,一句“忽见画图开四壁”,似有山水树木尽收眼底之感,此处亦真亦幻,画景如真景,而作者在见画入画的一刹那也似乎已然身处深山秀景之中,故而发出“悠然端亦慰余心”之感慨。张栻喜爱山水,以致“平生丘壑原,如痼不可瘳。”(《题榕溪阁》)因此他游览山水之后有一种“所历慰心目”(《静江归舟中读书》)之快感,如此可知他见画之幻与其游山水之真可以获得相同的视觉刺激,尤其是可以获得“慰心”的体道之快感,这也是张栻爱画并题画的主要原因。
如此则张栻的题画诗既有自然意象所带来的情韵意趣,又借景明理蕴含深刻之理趣,虽以平淡质朴的语言写出,却形成“闲澹简远”的美学风格并发溢着深长的“学者”滋味。
二 闲澹简远:题山水景物画诗之意境
张栻论诗主张读着似质却可以涵泳咀嚼出无限滋味,表现在诗歌的审美旨趣上则是对平淡冲和、含蓄简远诗风的追求。“闲澹简远”是其“学者之诗”(含题画诗)的审美旨趣,同时也是其画学思想的美学追求。
最早指出张栻诗歌这一美学特点的是罗大经,他在《鹤林玉露》中摘录了张栻六首诗,即《题城南》、《东渚》、《丽泽》、《濯清》、《西屿》和《采菱舟》,然后指出:“六诗闲澹简远,德人之言也。”这一观点也得到明人杨慎的认同,他在罗大经所选六首诗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去掉了《濯清》一诗,并说其它五诗“有辋川遗意,谁谓宋无诗乎?”将其与王维的山水诗列入同一高度,也是看到张栻山水诗平淡自然而意在言外的美学风格。而王维诗的一大特点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此有辋川遗意的不仅是张栻的山水诗,其题画诗更具有“闲澹简远”的审美旨趣,如他的这首《五士游岳麓图》:
闭门六月汗如雨,出门褦襶纷尘土。
文书堆案曲肱卧,梦逐征鸿过前浦。
西山突兀不可忘,勇往政须求快睹。
朝暾未升起微风,中流吚哑挟鸣橹。
长林秀色已在望,有如出语见肝腑。
意行爱此松阴直,眼明还喜碑字古。
高低梵释著幽居,深隐仙家开閟宇。
忽看宫墙高十丈,学宫峨峨起邹鲁。
斯文政倚讲磨切,石室重新岂无补。
危梯径上不作难,横栏截出可下俯。
惟兹翼轸一都会,往事繁华杂歌舞。
变迁返覆宁重论,昔日楼台连宿莽。
迩来人物颇还旧,岂止十年此生聚。
泉流涓涓日循除,华表何时鹤来语。
炎气知不到山林,茗碗蒲团对香缕。
鼎来杖屦皆胜引,季也亦复仙步武。
洛阳年少空白头,三闾大夫浪自苦。
一笑便觉真理存,高谈岂畏丞卿怒。
不图画僧圣得知,貌与儿童作夸诩。
请君为我添草堂,风雨萧萧守环堵。
所谓“学者”滋味无非是道德之味加上平淡冲和的美学风格,正是罗大经“闲澹简远,德人之言”的意思。那么接下来就从这两方面剖析此诗。先说道德之味。“文书堆案曲肱卧,梦逐征鸿过前浦。”此一句反映了张栻对自然山水的向往与对官府生活的厌烦,“曲肱卧”三字明显道出对孔颜乐处的追求。他在其他诗中也经常提到这一儒学典故,如在《题雉山禊亭》中云:“好风成我曲肱梦,起看飞云度碧天。”足见其对儒家圣贤气象的推崇。接下来写到“长林秀色已在望”,如此美景依然不忘借以明理,一句“有如出语见肝腑”道出对“修辞立其诚”、“诚者,天之道”等儒家信条的遵守。“眼明还喜碑字古”体现出作者博雅好古之儒者风范。随着游览脚步的深入,然后出现了“学宫”、“石室”,看到的应是岳麓书院,“斯文政倚讲磨切”道出学问须研磨切磋之工夫。随后对世事变迁、物是人非之景报以深沉的咏叹。一句“一笑便觉真理存,高谈岂畏丞卿怒”写出以穷理求道为人生事业的决心与快乐。张栻在诗歌最后一句则有一种以己入画的欲望,非仅因留恋于山水,亦是出于对观理于山水而安贫乐道精神境界的追求。一首题山水画诗竟出现如此多人文意象,读着似质,涵泳久之却愈觉意味深长,这不正是“学者”滋味、“德人之言”的体现吗?说完道德之味,再来看诗中的自然意象体现出的“闲澹简远”的审美旨趣。诗中写到突兀的西山、微风中初起的朝阳、水中咿呀摇荡的船橹、长林、松阴、危梯、涓涓的泉流、香缕中的茶盏等等意象,读完此诗立有置身岳麓山林之感。从表象而言,船橹咿呀、茗碗香缕之“闲”;涓涓泉流之“澹”;竹杖芒鞋、长林松阴之“简”;西山、朝阳之“远”,正组合了一幅“闲澹简远”之岳麓图。当然,“闲澹简远”还主要体现在诗歌语言的平淡自然,如同信步而行、信笔而图、信口而出,但全诗所塑清幽深远之意境却韵味无穷。观诗而见画,见画而卧游岳麓之长林秀色,以至于张栻见画图而生常住图中之冲动,发出“请君为我添草堂,风雨萧萧守环堵”之感慨。读者亦因这首题画诗而游于岳麓幽深的美景之中,从而徘徊于亦幻亦真之间,回味无穷。需要指出的是,“闲澹简远”亦是诗中人文意象的语言风格,而道德之味也蕴含在自然山水之中,二者本为一体,共同组成了“学者”滋味。
“闲澹简远”之审美旨趣重心应在一“远”上,诗画之旨远,方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发溢出深长之滋味。“远”在张栻题画诗中主要表现为对画意的补充和延展,从而提升画格。张栻题画不喜集中于对画面景物进行淋漓尽致地铺叙,而是沿着画面的构思继续进一步的发挥和创作。而经他补缀之画意往往比原画面更具意趣和韵味,《五士游岳麓图》以一句“请君为我添草堂,风雨萧萧守环堵”作结,写出了以我入画的冲动,画中加一草堂顿然提升了画之品格,使原来静谧清幽的岳麓山水一下变得更具人文气息和道学色彩。再看他的两首《墨梅》诗:
眼明三伏见此画,便觉冰霜抵岁寒。
唤起生香来不断,故应不作墨花看。
日暮横斜又一枝,水边记我独吟诗。
不妨更作江南雨,并写青青叶下埀。
墨梅属花鸟画,宋之前画梅多勾勒傅粉,以墨花作梅应始于宋释仲仁,人称华光长老。由于墨梅以水墨点染烘晕,不求形似只为意足,故而墨梅不尚多,如以几枝梅点缀于篱落间,更觉生出无限野逸之趣。宋代文人画兴起,文人墨戏观念流行,加上梅自始便以清介之高格为士人所赏爱,故尚意之墨梅成为宋人日常题咏之对象。张栻在第一首中主要突出了画面之“寒”气逼人与“生香”袭人,一触觉一味觉,均是画笔无法生成的,如黄庭坚见到华光墨梅后赞道:“如嫩寒清晓行孤山篱落间,只欠香耳!”张栻题墨梅并不对画中梅花作视觉上之渲染,而是将画面难以摹出的“寒”与“香”两种感觉以诗的形式加以补充,“寒”突出了梅之坚韧不屈之品格,“香”则使墨梅鲜活起来,真正达到气韵生动之境界。墨梅而散发生香,“故应不作墨花看”,如幻如真,可谓平淡冲和,“远”韵深长。第二首中写日暮时分自在横斜生长着的一枝梅,此时作者已在画中,正在画中作吟诗状。叙完画景后作者笔锋一转,指出画中应更添江南之雨,同时填补数片下垂状之绿叶。张栻为何要对画面作如此补充呢?正为加深画面“闲澹简远”之意韵。试想,日暮时分下起缕缕缕细雨,一枝横斜随意生长着的梅花伫立在雨中,数片叶子上点缀着几滴晶莹的雨珠,显得多么清新怡人。雨中的“我”却依然站立在水边面对眼前之梅而独自吟诗,该是多么惬意之画面。“我”与梅之间因雨而拉近了距离,画面也变得更加浑然一体。如此,更彰显了画面萧条淡泊、冲和清远之意境。
三 圣贤气象:题人物画诗之视角
张栻还有几首有关人物画的题画作品,数量不多,却具有明显特征,即均重在突出画中人物之心性涵养与圣贤气象,从而使诗画均散发着浓厚的“道德之味”。
人物画讲究传神,顾恺之曰:“传神写影,都在阿堵中。”这一观点对后代画学影响很大,如宋人论画也多重以形写神,突出画中物之神采气韵。如苏轼《传神记》也说:“传神之难在目。”又说:“其次在颧颊。”并叙述自己的经历,曾于灯下映影于壁间,使他人按影图之,惟不作眉目。本以为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却不料见者皆不识为谁。可见眉目对传神之重要。因此苏轼指出,传神在得人之天,即阴察人之自然天性,找出能彰显其神采之“意思”所在。而宋人陈郁在《藏一话腴》中更进一步提出“写心惟难”的观念:“写照非画可比,盖写形不难,写心惟难。”因为找准人物突出特征,“写之似足已,故曰写形不难。”但是“写屈原之形而肖矣,倘不能笔其行吟泽畔,怀忠不平之意,亦非灵均。写少陵之貌而是矣,倘不能笔其风骚冲澹之趣,忠义杰特之气,峻洁葆丽之姿,奇僻赡博之学,离寓放旷之怀,亦非浣花翁。盖写形,必传其神,必写其心,否则君子小人,貌同心异,贵贱善恶,奚自而别?形虽似何益?故曰写心惟难。夫善论写心者,当观其人,必胸次广,识见高,讨论博,知其人则笔下流出,间不容发矣。倘秉笔面无胸次,无识鉴,不察其人,不观其形,彼目大舜而性项羽,心阳虎而貌仲尼。违其人远矣。故曰写之人尤其难。”陈郁是南宋人,他在画论中将人物心性提升到制高点,转移了前人论人物画只围绕形神讨论的视角,这是南宋理学思想繁荣对画学思想冲击与渗透的结果。此后人物画更加重视对人物心性品格的塑造,而不再花大笔墨纠缠于似与不似之间,如清人郑绩提出“肖品”的观念,与陈郁“写心”的观念可谓不谋而合。
张栻在题人物画时即重在对人物心性品格、圣贤气象之歌咏。先看他的这首《跋王介甫游钟山图》:
林影溪光静自如,萧疏短鬓独骑驴。可能胸次都无事,拟向山中更著书。
前两句对画面作了诗意描写,宁静的山林中,树影横斜倒映在溪水之中,阳光照射在水面,一切显得那么安静祥和。此时有一个头发稀疏而短鬓的老者骑着驴正好经过,洒脱而萧然。短短十几个字将王安石游钟山图之画面映现在读者面前,“萧疏短鬓独骑驴”一句可谓写出王荆公之“意思”,达到以形传神之境界。而接下来话锋一转,“可能胸次都无事,拟向山中更著书”道出荆公学问胸次与平素性情,赞美了荆公安贫乐道、孔颜乐处的圣贤气象。传神而又能写心、肖品,可谓达到至高之境界,也使诗、图蕴蓄深秀,既有“闲澹简远”之韵味,又不乏“学者”之气息。说到对画中人物心性德业的重视,当属他的两篇人物画像赞更为明显与直接。《汉丞相诸葛忠武侯画像赞》:
惟忠武侯,识其大者,仗义履正,卓然不舍。方卧南阳,若将终身,三顾而起,时哉屈伸。难平者事,不昧者几,大纲既得,万目乃随。我奉天讨,不震不竦,维其一心,而以时动。噫!侯此心,万世不泯,遗像有严,瞻者起敬。
《于湖画像赞》:
是于湖君,英迈伟特,遇事若然,如箭破的。谈笑翰墨,如风无迹,惟其胸中,无有畛域。故所发施,横达四出,虽然,此固众人之所识也。今方袖手于湖之上,尽心以事其亲,而益究其所未及。则其所至又孰知其纪极者耶?己丑夏广汉张某书于湘中馆。
前者赞诸葛亮仗义履正、忠义爱国之心;后者称扬张孝祥英迈伟特而不乏儒者之雅,胸次宽广而进学不止之心。两篇赞均不从人物眉目衣物着眼,而是重在对人物平素性情与圣贤气象的阐发,真可谓“德人之言也”。
张栻画学思想中的品鉴旨趣与传统画工相异,这在他与朱熹讨论作画的两封书信中也可见一斑。在《答朱元晦秘书》第一书中写道:“画僧只是一到城南经营,即为刘枢闭在湘,春作图帐,到今未出。两纸只是想象模写,得其大都,其间有欠缺及未似处,今且送往,它时别作得重寄也。”他论诗主张道眼前实事并含蓄蕴藉,作画亦反对一味“想象模写”,只画得大概景致而徒有其形的图帐,当然有所“欠缺”而不能合张栻之意,欠缺的正是“闲澹简远”的画外之意味。在张栻看来,绘画之最高境界不是简单的画面模写,而更应具有纵深感,这种纵深感当然有别于宋人追求的“深远”之视觉效果,其间亦须具有学者滋味,合乎道德境界。这种“学者之画”是俗工所难以完成的,且看他答朱熹的第二书:“城南亦五十余日不到,昨一往焉,绿阴已满,湖水平漫,亦复不恶;方于竹间结小茅斋,为夏日计,雨潦稍定即挟策其间也。尝令画图,俗工竟未能可人意。俟胜日自往平章之,方得寄往耳。”在张栻的理想中,此图作出当如《王荆公游钟山图》,在写出清幽景色之余,亦要突出挟策其间的人物情态,更要写出画中人物高雅闲适、雍容祥和的陶氏风流与圣贤气象。如此则景为人物之衬托,写心、肖品方是画意之重心所在。俗工只可模写大都得其彷佛之形,怎能满足张栻心中之预想,难怪要亲自与之商量处理了。
综上,张栻在诗论中所提出的“学者之诗”的概念不仅是他诗学思想的基本观点,也是他综合文艺观的核心理念。张栻虽不作画,也无直接的画论提出,但我们从他的题画诗中亦可窥探其画学思想的审美旨趣。他在题画时之所看、所感无不彰显出对“闲澹简远”画意之推崇。在张栻看来,优秀画作之画面应具有平淡冲和之意境,给人以纵深感,洋溢着“道德之味”;俗工匠人之画如诗人之诗,是不耐咀嚼的,惟有那些具有闲澹简远之意蕴与彰显“道德之味”的画作才如“学者之诗”一般可以涵泳愈久愈觉滋味弥久深长。
[1]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M],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十,日本:株式会社中文出版社,1980.
[2]张栻.南轩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3]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杨慎.升庵诗话[M].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6]陈郁.藏一话腴[M].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