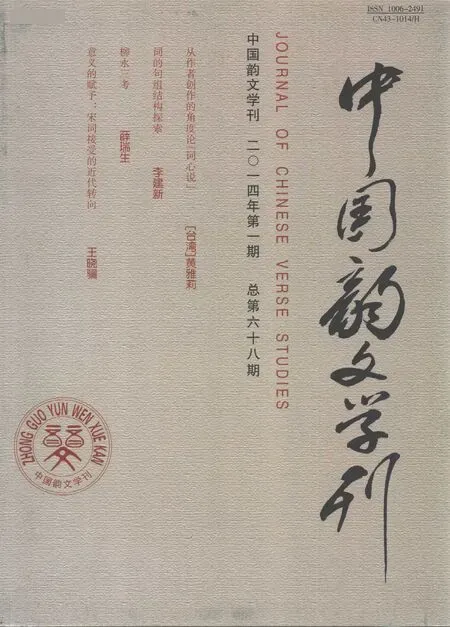论王闿运与曾广钧的诗学交流
何荣誉
(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王闿运是晚清汉魏六朝诗派的旗帜,也是湖南诗坛最富影响力的诗人。其早年与曾国藩私交甚好,虽多次干谒未果,但并不妨碍他对曾氏的感情。曾广钧,又名重伯,为曾国藩之孙,幼时便有诗名,享誉湘中。曾广钧颇好王诗,与王氏诗学交流也很频繁。在十数年的交往中,曾广钧的诗歌也带有了王诗之特征。这是他主动学习王诗的结果。曾广钧诗虽为晚唐体,然而也从王诗中汲取营养。王闿运诗歌拟古的方法、绮靡的文辞,都为他所学。
一 交游关系:亦师亦友
王闿运与曾广钧交游的背景是很特别的。光绪七年(1881年)十二月,王闿运从四川返回长沙,随即便因《湘军志》遭到湘人的非议、讨伐,处境尴尬。光绪八年正月,王氏还为此受到了曾广钧叔祖曾沅浦的当面诃斥。最终王氏迫于压力,将《湘军志》刻版交于郭嵩焘焚毁。在这样的背景下,曾广钧却主动向王闿运求教学诗,大有声援王氏之意。
从《湘绮楼日记》记载来看,王闿运、曾广钧的交往是十分相契的,谈诗论学是他们活动的重点。光绪七年十二月廿九日:“曾栗诚之子广钧前来,未见,复以书来,索观撰著,文词颇复斐然,与书勉之,并以《湘军志》及《诗笺》、少作诗借之。”
光绪八年正月三日:“佐卿来,言曾郎重伯欲来谈。遣约登楼,坐一时许,博涉多闻,较余幼时为知门径,语亦不放荡,美材也。惜生华膴,誉之者多,恐因而长骄耳。”光绪八年四月六日:“过午登楼,曾重郎来取《春秋笺》及《独行谣》去。”光绪八年六月十八日:“晨得重郎书,借《书》、《礼笺》及少作诗。”光绪八年七月二日:“重伯送诗来。”四日,王氏作和曾诗,即《苦热,和曾公孙登楼之作》(第十五卷)。光绪八年七月廿五日:“夜过曾郎,谈立身处世势利进取之道。”光绪八年九月十六日:“曾郎、陈伯涛均赋诗见示,意在索和。”光绪八年十月十二日:“申至重伯家,陪松生,守愚、伯涛、子政、验郎、筠孙、笠僧俱集,初更散。席间皆谈诗体例。”光绪八年十月十六日:“曾郎送诗,共看赏之,以为今神童也。”光绪八年十二月廿三日:“复过曾郎,谈文及《诗经》句法用典之例。”从以上记录不难看出,曾广钧问学之勤,王氏也是倾囊相授。
但是,曾广钧并不一味接受王闿运诗,对于不称己意者也提出来与王氏商量。如光绪八年九月十一日日记就记载了二人商讨诗歌的情况,曰:“曾郎来,言余所作《湖亭诗》尚有不尽纯者,颇中利病。因思‘僧雏’字,改作‘僧童’则可矣,而‘词客’二字无以易之。十月三日夜五更改‘词’字为‘酒’。”对于曾广钧提出的问题,王闿运虚心接受。然于曾广钧诗歌的弊病,王闿运也予以言明。王氏弟子杨钧在《草堂之灵》中就有相关记载:“湘绮先生谓重伯诗有凑杂之弊,譬诸讲话,一句京腔,一句苏白,不成体也。此论与余谓今人字为混合体同一意义。”
曾广钧是曾国藩之孙,因其特殊的家庭背景,且富文才,受到了湘人的特别关注。在《湘军志》事件的背景下,其竟然公开与王闿运交往,还主动向其问道求学,这招致了湘人的不满。王氏光绪九年二月十五日日记曰:“过罗梦子饮,成赞君、王君豫、二罗先在,多谈曾重伯。余言今人耻于服善,有高才者,众所不能及,则视其所善者而讥笑之,云非某人不能制也。如是以离两家之交,愈长一人之傲。余今闻人言,重伯唯服我,则惕然不喜。诚使能其材而益其善,虽自詘以推之,亦何靳哉。”王闿运并没有却步于时人的非议,对离间二人关系的言行表示了愤慨。而曾广钧也不理会这些,甚至公然称王氏为师。王氏光绪九年三月二十日日记曰:“重伯能记吾诗,见称以师,殊可佩服,以时人方激间之也。”
曾广钧私淑王闿运,毫不顾忌湘人的态度,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这种公然支持王闿运的举动,比郭嵩焘更加直接,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给四面楚歌的王氏以莫大的安慰。这也奠定了二人深厚的交谊,无论是师徒关系,抑或是诗友关系。
光绪十三年,王闿运结束北游返湘。曾广钧又能与王闿运论诗了。是年六月初三,王闿运组织开福寺集会。此集是王氏返湘后组织的一次大的集会,郭嵩焘、寄禅、陈三立、曾广钧等皆有参加,均有诗。曾广钧作《拟东城高且长同湘绮、伯严诸公开福寺作,呈玉池老人》。
光绪十五年,曾广钧会试中第。王闿运获讯以诗相贺,作《曾公孙广钧选入翰林,感寄二首》(第十二卷)。诗中对曾氏期许甚高,以冀能继其祖曾国藩之道德文章,曰:“祖德留江介,訏谟在讲筵。绪馀方略展,经术小心传。文苑终修业,荷囊莫倚年。五云深处静,清切念承先。”是年王闿运游玩天津后辗转到江苏,曾广钧作《赠送王壬秋丈之吴》诗。
随后数年,曾广钧旅居北京、武汉、南京、广西等地,与王闿运见面机会不多,文学活动也随之减少。而曾广钧的思想也随着时代而发生了一些变化。光绪二十年,曾广钧与康有为、梁启超结交,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很深。光绪二十二年,其与维新派组织南学社研讨新学。随后又积极投身实业,办矿场。曾广钧的这种变化,在《湘绮楼日记》里面都有反映。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日记载:“(曾广钧)说四始五际,兼及新学,取《论语》去。”曾广钧与维新诸子交游,不仅思想上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诗歌上也具有了新诗的某些特征,比如一些新名词、新概念进入诗歌,且时常有佛典充斥其间,以致黄遵宪也视其为同道。虽然曾广钧与维新派接触频繁,诗歌创作上也与王氏发生偏离,却无意间加强了他对今文经学的了解。曾广钧有《读公羊绝句》十一首,大抵反映出了其对公羊学的认识。
进入民国,曾广钧在上海、北京均与王闿运有集,可是其主要的文学活动对象则是与陈三立、陈衍、易顺鼎、樊增祥等人组成的超社,与王氏之诗趣已相去甚远了。
二 诗学联系:拟古与绮靡
曾广钧学习王闿运诗最勤时是在光绪八年前后。中期,曾广钧受到维新派影响颇深。进入民国,则又与唐诗派、宋诗派诸子游。因此,曾广钧的诗歌表现出了丰富的形态。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其二曰:“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风雅不亡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文章巨蟹横行日,事变群龙见首时。手撷芙蓉策虬驷,出门惘惘更寻谁?”引曾氏为同道人。而宋诗派陈衍则在其《近代诗钞》中评论曾氏曰:“重伯阅书多,取材富,近体时溢出为排比铺张,不徒高言复古。句如:‘酒入愁肠惟化泪,诗多讥刺不须删。’‘已悲落拓闲清昼,更著思量移夕晖。’‘宅临巴水怜才子,村赴荆门产羡人。’又作宋人语矣。”俨然又将曾重伯部分诗列为宋派。就连王闿运也承认其有以学运诗的特点。
尽管如此,曾广钧受到王闿运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就其古体诗而言,曾氏拟作六朝诗,并且拟作闺怨诗以抒己意,皆有王闿运的影子;就其七律而言,曾氏宗法晚唐李商隐,虽受其家学影响,但在形态上,又与王闿运相近。
王闿运认为曾氏诗“酝酿六朝三唐”。其在曾氏《环天室诗集》序中曰:“重伯圣童多材多艺,交接三十余年,但以为天才绝伦,非关学也。今观诗集,蕴酿六朝三唐,兼博采典籍,如蜂酿蜜,非沉浸精专者不能,异哉!其学养之深乎,湖外数千年唯邓弥之得成一家。重伯与骖而博大过之,名世无疑。”王闿运概括了曾氏诗歌的特点,一是其诗不出六朝三唐,二是学养深厚,博综兼采而能自成一家。王闿运将曾氏与邓辅纶并列,评价不可谓不高。吴宓《空轩诗话》也赞同王说:“《环天室诗》学六朝及晚唐,以典丽华赡、温柔旖旎胜。”
《环天室诗集》卷一收录了五古诗26首,其中多有学六朝诗的痕迹。《古意赠韩兵部》以宫体题材抒愤,借“妾”由受宠到遭嫉以致最终被弃的遭遇,来表达对韩兵部不遇的同情。《庚辰正月十四对月》是闺怨题材,通过想象嫦娥月夜久待知音而不至的场景,来传达诗人内心的情思。而知音是谁,其实诗中并不明确。这两首诗歌皆契合古乐府之旨。而《循昭山至暮云》、《石廪东一峰诗芙蓉最高顶》、《阻雪万岁湖》、《次韵胡子瑞游望乡亭》等诗,游山玩水,记录游踪,无论诗之结构,还是炼字选句,都似大谢诗。“云物变气候,阡陌交人烟”则直接化大谢诗句而来。《拟谢客从游京口登北固望蒜山》则模拟大谢诗。还有《拟招隐》是拟作左思诗,《拟东城高且长同湘绮、伯严诸公开福寺作呈玉池老人》则拟《古诗十九首》之意,写王闿运寻求施展才华机会之不易,并予以安慰,实次韵王诗。这些拟作,无疑是从王闿运处来。据《湘绮楼日记》载,王闿运将自己早年诗歌借与曾氏览阅,而曾氏竟熟悉到了能背诵的程度。而王氏早年诗多有拟作,曾氏能有这些作品,也在情理之中。
曾广钧古体诗受到了六朝影响,而七律则学晚唐,于李商隐诗颇有会心处。前人则颇纠结于曾广钧学晚唐诗是受家学影响还是王闿运的启发。持受家学影响者有汪辟疆,其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说:“奥缓逛莹称此词,涪翁原本玉溪诗。君家自有连城壁,后起应怜圣小儿。环天室诗多沉博绝丽之作,比拟之工,使事之博,虞山而后,此其嗣音。太傅、惠敏,并致力玉溪,至重伯则所造尤邃,可谓克绍家风矣。”汪氏将曾国藩对李商隐诗“奥缓”、“渺绵”特点的认识放置到曾广钧诗上,并具体表述为“比拟之工,使事之博”。而“使事之博”则有以学问为诗的意思,具备宋诗的特点。这点倒与王闿运的认识接近。他又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说:“曾重伯则承其家学,始终为义山,沉博绝丽,在牧斋、梅村之间。”而钱仲联先生则表示异议,认为曾广钧学习李商隐的路数与曾国藩、曾劼刚不同,并不是受家学影响。他说:“曾重伯为求阙斋主人之孙,早慧,王湘绮目为圣童。诗承求阙崇尚玉溪之论,而不学韩、黄,惊才绝艳,犹是楚骚本色。”钱钟书先生也支持该说。具体而论,曾广钧学习李商隐的诗歌在于其词艳、律细,而不是像曾国藩那般,着力发掘李诗与韩愈、黄庭坚等的相似处,侧重于发掘李诗与宋派诗的相通处。
《环天室诗集》中摹拟李商隐诗者颇多,拟《无题》者就有《和郑蕉龙无题》、《无题》,而最为世人称道者则是《庚子落叶词同李亦元王聘三作》。《桐城吴先生日记》辛丑年(1901年)十月廿四日记曰:“曾重伯来,并示所作《无题》七律十章。珍妃去年死于井,今遣人取出,尸不坏,面如生,重伯感赋此诗,甚得玉溪生风调。”此评甚是。现选取前三首刊于后:
甄官一夕沦秦玺,疏勒千年出汉泉。
凤尾檀槽陪玉椀,龙香璎珞殉金钿。
文鸾去日红为泪,轻燕仙时紫作烟。
十月帝城飞木叶,更于何处听哀蝉。
赤阑回合翠溣漪,帝子精诚化鸟归。
重璧招魂伤穆满,渐台持节召贞妃。
清明寒食年年忆,城郭人民事事非。
湘瑟流哀弹别鹤,寒鱼衰雁尽惊飞。
银床玉露冷金铺,碧化长虹转鹿卢。
姑恶声声啼苦竹,子规夜夜叫苍梧。
破家叵耐云昭训,殉国争怜李宝符。
料得珮环归月下,满身星斗泣红蕖。
此诗为感珍妃之死而作,用事隐晦,意境凄冷,用词绮靡,颇似李商隐诗。且诗中意象如红泪、紫烟、哀蝉、苦竹、子规等皆为李诗常用意象。
曾广钧诗终是唐诗,这点与曾国藩是不同的。但是,他的七律又与王闿运不尽相同。王闿运七律同样不落宋诗,相较曾广钧诗而言,少了几分凝重,而多了几分趣味,因为王诗七律少有寄托抒怀之意。虽如此,二人在学李商隐诗仍存在共同点,那就是用词绮靡。
王闿运对李商隐七律是颇为肯定的。他说:“七律亦出于齐、梁,而变化转动反局促而不能骋。唯李义山颇开町畦,驰骋自如,乘车于鼠穴,亦自可乐,殊不足登大雅之堂也。”王闿运认为唐诗七律源自六朝,而格局太小,成就不及七古。但是,他仍认为仅有李商隐能纵横自如,较他人技高一筹。王闿运《唐诗选》选李商隐七律12题,共20首,仅次于王维的22首。他手批了其中5题,共8首。批《圣女祠》曰:“义山诗专取音调字面,自成一家。”批《隋宫》曰:“‘口角’、‘天涯’对滞。”批《潭州》曰:“起句非‘潭州’不称,不可移‘咸阳’。”批《碧城》曰:(之一)“‘海韵’未知何意。‘星沉’、‘雨过’亦不可解。”(之三)“讥其招摇狼藉也。”(之四)“言与己约而无信,但樵以不能为力。”批《无题》(之三)曰:“能令雷妍艳,故是异事。”从以上批语可以看出,王闿运并不关注诗的内容,也没有在内容的解读上费过工夫,兴奋点皆在音调字面。
王闿运所选李商隐七律诗的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咏古抒怀之作,如《圣女祠》、《潭州》、《隋宫》等;二是咏物诗,如《野菊》、《蜂》等;三是主要表现自己心理的,如《无题诗》、《锦瑟》等。不管何种题材,李商隐诗皆词采妍丽,寄意深沉。这些皆符合王闿运“以词掩意”的观点,也合乎其崇尚俪词华采的审美趣味。
王氏《杜若集》中不乏与李商隐诗风格相近者,但是这种相似仅限于词采。王氏七律不尚用典,较李诗显得更为自然。以咏物诗为例。王闿运的咏物诗不似李商隐的以寄意为目的,而追求一种趣味性。但是在用词妍丽上,二者是一致的。李商隐《野菊》:“苦竹园南椒坞边,微香冉冉泪涓涓。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细路独来当此夕,清尊相伴省他年。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此诗为托物寄兴之作,名为野菊,却无一句写菊,皆写己怀,直指内心。其《蜂》也是如此。再看王闿运的《柳花》(卷十六):“澧浦晴波怅望时,日光烟影共参差。芊茸别树刚成朵,点絮随风偶上枝。魏殿衔春犹有恨,谢家看雪最相思。浩园墙角无人到,扑地漫天欲问谁?”该诗着力点则在于传达出柳絮漫天飞舞之情状,无甚深意。王闿运的其他咏物诗皆如此类。王闿运虽不好李商隐的古体诗,但是此诗末句确有李诗五古咏物《柳》、《蝉》末句的韵味,前者如“倾国宜通体,谁来读赏梅”,后者如“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曾广钧诗学李商隐,在路数上介于曾国藩与王闿运之间,有自己的特点。然所谓到底是受家学影响还是受王闿运影响的争论也是没有必要的。
探寻二人之诗学关系,既感知了王闿运对湘中后学的影响,又发掘光宣时期汉魏六朝诗派与晚唐诗派的交流沟通。这样的交流沟通则体现出了光宣时期诗学发展走向融合的趋向。
[1]王闿运.湘绮楼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6.
[2]杨钧.草堂之灵[M].长沙:岳麓书社,1985.
[3]黄遵宪著 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陈衍.近代诗钞[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5]王闿运.《环天室诗集》序[M].曾广钧.环天室诗集[M].宣统元年刻本.
[6]吴宓.空轩诗话[M].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六)[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7]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M].汪辟疆说近代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M].汪辟疆说近代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9]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M].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10]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1]王闿运.湘绮楼说诗(卷四)[M],湘绮楼诗文集(五)[C].长沙:岳麓书社,1997.
[12]王闿运.王闿运手批《唐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3]李商隐著.冯浩笺注.玉谿生诗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4]王闿运.湘绮楼诗集(卷十六)[M].湘绮楼诗文集(四)[C].长沙:岳麓书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