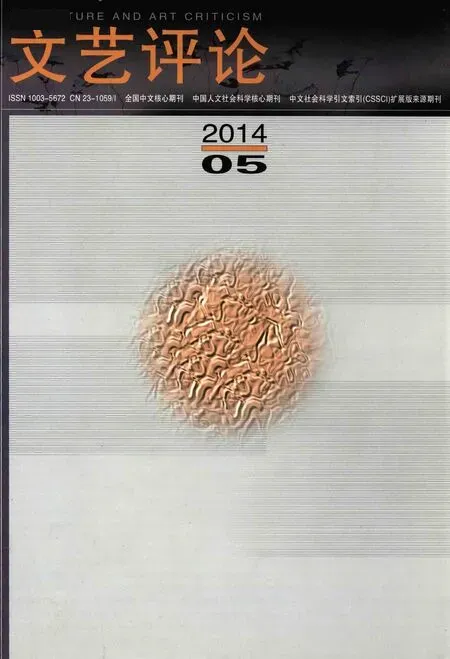为艺术而生活:荡子的美学意义
○杨金玉 陈 希
颓废是西方象征主义的重要范畴,被赋予美学新义。西方文学较先使用颓废(Décadent)这个词的是法国批评家德西雷·尼扎尔,1834年他以此批评浪漫派过分注重细节和雕琢而破坏了整体。后来象征主义颓废文学接受这个批评,并将其“雕琢”内涵发展为“精致”。19世纪80年代,法国出现颓废主义文学。一些诗人创办《颓废》(Décadent)杂志。在巴黎出现的“颓废派”事实上是象征派的前身,兰波、魏尔伦参与其中。当时《Décadent》杂志驰名文坛,声誉鹊起,活跃于巴黎拉丁区的青年诗人无不自豪地宣称自己是Décadent,“颓废派”引领时代潮流,摇身变为一个毫无贬义的先锋词汇。戈蒂埃1868年为《恶之花》所写的序言里,第一次将这个词赋予褒义,激赏、赞许颓废文体。颓废文学构成对经典或传统文学的修正和挑战,否认理性的价值,主张个性的极端自由,崇尚感官本能的放纵,追求艺术上的精致,是审美现代性追求的表现。
上世纪20年代,颓废风伴随西方现代文艺新潮吹来中国,对新诗创作和诗学建构产生深远影响。颓废是一种艺术精神和价值取向,但崇尚本能的放纵,在极端的感官享乐中体现精神的纯粹性。中国现代诗学立足于现实语境,受制于东方因子,大多将“颓废”阐释为堕落、怪诞,而不是诉诸先锋性、唯美性。作为一个中国现代诗学概念,颓废逐渐剥离原本涵义而呈现一种本土化的态势。①自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解志熙《美的偏至》②始,不少学者关注颓废问题,但是大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颓废产生的原因,将颓废研究意识形态化的偏向。原本一个艺术至生活都追求精致和纯粹、引领潮流的文艺范儿,却被“非艺术化”论说,出现严重错位。为数不多的,超脱社会学羁绊的文艺研究,侧重文艺创作和理论,很少将艺术与生活、文本与人本结合起来。颓废不仅是一种审美追求和艺术精神,而且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而颓废艺术家——“荡子”身上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和取向。
一、《金屋》的颓废之花
“荡子”dandy意义有二:一是华丽、时髦;二是指19世纪后期英国和法国颓废派的一种矫揉细腻的文艺风格。由此,可见dandy绝非指一般意义上的“花花公子”、“纨绔子”;dandy所代表的主要是贵族阶层中的艺术气质浓厚的群体,与汉语中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败家子式的“纨绔子”有别。郭宏安《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将波德莱尔的dandy译为“浪荡子”③,李欧梵《上海摩登》、《现代性的追求》将之译为“浮纨”、“美男子”。④据此,我们觉得不如将dandy翻译为“荡子”,这样音义兼收。
颓废艺术家多将艺术理想生活化,“为艺术而生活”,视生活为“最伟大的艺术”。他们衣着讲究,仪表堂堂,谈吐不俗,性格乖僻,放荡不羁,尽情享受,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表现出较浓的艺术气质。中国古代有不少气质型艺术家,被近人称为颓废派之荡子。譬如,徐嘉瑞《颓废派之文人李白》将李白的喝酒与法国颓废派“聚集在巴黎咖啡店痛饮彻夜”相提并论,说李白的生活和颓废派“很类似”,追求官能刺激。⑤朱右白《中国诗的新途径》认为唐代诗人的思想不出儒派(杜甫)、仙侠派(李白)、山林派(王维、孟浩然)、颓废派(杜牧)等四派,学李白不能得其真正思想便流入颓废派,颓废派“风流放诞,毫无拘束”。⑥
中国现代则不乏其人。1923年9月,郁达夫在《创造周报》发表长文《the yellow book及其他》,介绍了颓废派核心刊物《黄面志》和英国颓废派诗人、艺术家比尔利兹(Aubrey beardsley)、道生(Ernest dowson)和约翰·戴维森(John davidson)等。郁达夫称比尔利兹是“天才画家”、“空前绝后”,他“使《黄面志》的身价一时高贵”。郁达夫与病态的、沉溺肉体甚至有些堕落的比尔利兹等颓废派艺术家在精神上有相似之处。无疑,郁达夫作为中国现代颓废文学的始作俑者,很大程度上以《黄面志》及比尔利兹的作品为灵感之源。当时茅盾称其为“狄卡丹”(decadant)。之后,更多的另类文艺青年自甘“堕落”,打出“颓加荡”旗帜,聚集在唯美颓废倾向的群体“绿社”、“幻社”等周围,以《狮吼》、《声色画报》、⑦《金屋月刊》为园地,以金屋书店为核心,追求官能刺激,营造肉和色的艺术。他们宣称要打倒浅薄、顽固和有时代观念的工具的艺术,要“用人的力的极点来表现艺术”。⑧他们是唯美主义者,艺术方式和生活方式倾心并接近颓废派,主要代表有“狮吼”、“幻洲”、“绿社”、“金屋”等群落的滕固、叶灵凤、邵洵美以及章克标、林微音、腾刚等。
滕固(1901-1941),字若渠,上海宝山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颖,跟父亲学习古文和古诗,《秋祭》是他少年最早的诗作“下曝光千万卷,门前种菜两三畦,剧怜诗酒风流尽!空先旧题”。“五四”后不久,他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毕业东渡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美术考古,兼习哲学。期间与郁达夫过从甚密。1922年回国,加入文学研究会,为第50号会员。他一边和沈雁冰、陈大悲等组织民众戏剧社,编辑《戏剧》月刊,一边又热心参加创造社的活动。他的成名小说《壁画》写性爱的一厢情愿的苦闷,最初就刊载于1922年11月的《创造季刊》1卷3期。1926年,滕固与邵洵美、章克标、方光焘、张水淇、黄中、藤刚等同声相乞,成立“狮吼”社,创办《狮吼》半月刊。1927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滕固的《唯美派的文学》,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方唯美主义的著作之一。上世纪30年代初,滕固告别文学,赴德国留学,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南京金陵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中山文化教育馆美术部主任、昆明国立艺术学院院长、国民政府行政院佥事等。
章克标回忆说:“狮吼”社以滕固为中心,也许不是什么集团而只是乌合之众,各人思想倾向恐怕也不完全相同,精诚团结更谈不上。当时比较流行的世纪末趋势,叫做唯美主义,也叫做颓废派,引进了许多西洋唯美主义作家,如王尔德、魏尔伦、波德莱尔等等,我们也被迷惑了。那是西方在上个世纪末的一股潮流,否定传统思想,主张改革旧风俗、旧习惯,是有些反抗精神,但是勇气不够,毅力不足,因而堕入颓废消沉,所以是不健康的。欧洲的这股世纪末文艺风气传播到东方来,日本也有这流派的人,中国则开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了。对现实社会不满,缺乏正面对抗的勇气而采取逃避现实的办法,用自我麻醉来达到目的,就是此种表现、此种流派了,也有人为好奇而来,糊里糊涂跟着兴风作浪。总之是反对现实社会,同一般人的观念力求相反,以善为恶、以恶为善,以美为丑、以丑为美,说要从恶中发掘出善来,从丑中找出美来,化腐朽为神奇,出污泥而不染。相信“恶之华姣艳,盗贼中有圣人”,就是这一种思想倾向、作风做法,正同烂脚铁拐李是真仙一样。⑨
叶灵凤是一个与颓废精神相通的“另类”作家。叶灵凤(1904-1975),江苏南京人,原名韫璞,常用名“叶林风”、“霜霞”、“佐木华”、“LF”等。1925年,还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生的叶灵凤,因为创造社出版部人手短缺,加入创造社,与周全平、洪为一起,参加《洪水》半月刊的编务。真正有影响的是次年他与潘汉年主编《幻洲》。1929年,叶灵凤还作为主编之一编办过《小物件》,这份杂志只有1寸多宽2寸多长,四五十页,用道林纸印,封面插图皆讲究,可能是新文学历史上开本最小的刊物了。
“与众不同”是叶灵凤和潘汉年主编的《幻洲》的特色:四十八开横排特型本,体例分上下两部,上部为“象牙之塔”,多唯美的创作;下部为“十字街头”,多骇俗言论。更标新立异的是,他们竟然提倡“新流氓主义”,认为“生在这种世界,尤其不幸生在大好江山的中国,只有实行新流氓ism,方能挽狂澜于既倒”;“新流氓主义,没有口号,没有信条,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⑩潘汉年更多地将“新流氓主义”引向革命和阶级斗争,叶灵凤则多偏向文学一脔。叶灵凤公开声称自己的小说全是“象牙塔里的文字”。他翻译过王尔德鼓吹“艺术家是美的创造者”的《格雷画像序》和阐述艺术观念的《谎言的衰朽》(The Decay of Lying)。王尔德《心意集》谈到伦敦的迷雾演绎出艺术活动如雾如梦一般的特征,以及如同谎言一样“自己欺骗自己”的过程。叶灵凤的《雾》受到王尔德的启发,显示唯美倾向。叶灵凤曾经因为宣扬比尔利兹的图画而招致鲁迅谩骂。
《女娲氏之遗孽》是叶灵凤成名作,曾入选郑伯奇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小说写的是一个已婚女子诱惑青年在校学生的爱情故事。这类题材趣味似乎像张资平,但唯美主义导入自然主义,是叶灵凤区别于张资平的地方。叶灵凤笔下的女性似乎都有着荡妇的非理性徽记,在揭示人的一个方面的精神真实的同时,也批判和鞭挞了封建家族制度吃人的本质。而叶灵凤的《浪淘沙》和《浴》则引起关注和愤怒。《浪淘沙》写的是两个表亲姐弟的感伤恋爱故事,《浴》几乎没有情节,出现女人体的描绘,集中写了女主人公手淫的过程和感觉。
章克标(1900—2007),浙江海宁人,常用笔名岂凡,1918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二中学,翌年负笈东瀛,就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回国任职上海立达学院、暨南大学,兼《一般》、《时代》主编。1927年后,参加《狮吼》,又在开明书店、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任编辑。与邵洵美莫逆知交,共同编辑《十日谈》、《人言》等。他写过小说、散文,唯小品最当行。《风凉话》(开明书店1929)、《文坛登龙术》(开明书店1933)是代表作。鲁迅《登龙术拾遗》和《准风月谈后记》涉及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章克标也就被称为“富家儿的鹰犬”、“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的小说集有《恋爱四象》、《蜃楼》,多写男女性爱、多爱,长篇《一个人的结婚》表现上海既维持旧的又逼入新的情爱策略。中篇《银蛇》引人注目,影射郁达夫(邵逸人)与王映霞(伍昭雪)。
林微音(1899-1982),男,奇瘦,脸面尖削,鼻头红硕,江苏苏州人,笔名陈代。主要供职金融界。1932年一度代邵洵美担任新月书店经理。1933年与朱维基、芳信、庞熏琴等组织“绿社”,创办《诗篇》月刊,提倡唯美主义。林微音最当行的是散文,1936年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散文七辑》。1933年11月林微音以陈代笔名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连续发表《略论告密》、《略论放暗箭》,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里将他的所为与章克标所言的“登龙术”一起煮。林微音的小说多短篇,结集有《白蔷薇》(上海北新书局 1930)、《舞》(上海新月书店 1931)、《西泠的黄昏》(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另有长篇《花厅夫人》(上海四部出版部1934)。林微音小说空间有意味。滕固小说男女主人公约会安置“半凇园”,章克标作品男女主人公约会安置法国公园,林微音作品人物活动空间则几乎涉足当时上海滩所有最摩登的处所。《花厅夫人》madame de salon写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大学生孙雪非从家庭学校走出,走进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绚丽迷惑的新空间。小说出现的场景有小朱古力店、国泰戏院、福禄寿饭店、永安公司、福芝饭店、圣安娜、沧州饭店、惠而康饭店,水上游乐场有“open air”、“ rio rita”和“高桥海水浴场”。
二、中国dandy:邵洵美和白采
上述几位虽然也有“颓废”诗作发表,但主要是小说与散文创作。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颓废诗派最突出的诗人是邵洵美和白采。他们算得上是中国的dandy。
邵洵美(1906—1968),原名云龙,浙江余姚人。1906年生于闻名沪上的“斜桥邵家”,1923年冬赴英留学剑桥,后转法国求学。邵洵美是美男子,他有“希腊鼻子”,有出入上海文艺沙龙的美国情人项美丽(Emily Hahn)。但浪漫风流的邵公子婚姻很古典。1927年1月15日,与表妹盛佩玉在上海结婚。盛佩玉为晚清改良运动中最著名的实业家盛宣怀的孙女。而邵洵美母亲是盛宣怀的四女儿,盛佩玉的父亲为盛宣怀长子。1916年盛宣怀逝世,邵洵美在出丧期间见到盛佩玉,十分爱慕。遂取《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佩玉将将,洵美且都”之意,改名“洵美”,与佩玉相连。因爱成婚,非贪图嫁资。邵洵美仗义疏财,有“小孟尝君”之誉。上世纪30年代,鲁迅在《登龙术拾遗》和《准风月谈后记》里随手拉出邵洵美“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挖苦邵洵美能以乘龙快婿而“十分完满”地直登文坛龙门。
1938年,邵洵美在自己主办的中文刊物《自由谭》和英文刊物《直言评论》(candid comment)上推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文刊物《直言评论》1938年11月到1939年2月出版的连续4期刊载毛著的译文,且亲自将毛泽东的序言翻译成英文。(11)但1949年后高中课本说邵洵美是“反动御用文人”。上世纪60年代他被抄家,诬为“美蒋特务”。折磨不堪,无实据获放。晚年寂寞凄凉,1968年5月5日去世。当时夫人盛佩玉远在南京,凑不够路费赶回上海见最后一面,无钱置办衣裤,买了双袜子托长子送夫君上路。
邵洵美出版有三本诗集:1927年由光华书局出版第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1928年由金屋月刊社出版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1936年个人诗选集《诗二十五首》作为“新诗库”之一由时代图书公司出版。邵洵美还出版文艺论集《火与肉》,译诗集《一朵朵玫瑰》,编译过《黄面志》颓废艺术家比尔利兹的《瑟亚词侣诗画集》、乔治·摩尔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等。
邵洵美翻译乔治·摩尔(George Moore)的《纯粹的诗》,(12)既反对散漫的自由体的诗,认为它没有力量,也反对桎梏式的规律,认为形式是应当的,但不可过于雕琢。邵洵美《诗二十五首·自序》总结了自己诗学观,他试图以“形式的完美”为中心,提出了将西方唯美颓废诗潮整合中国颓废诗学,认为“只有能与诗的本身的品性谐和的方式才是完美的形式”。诗歌必须从胡适那样“只注重形式”的语言和诗体的革新中解脱、超越出来,寻求一种内在的、与内容不可分开的“肌质”的形式美。邵洵美还强调现代诗的晦涩品格,认为“一首诗,到了真正明显的时候,它便走进了散文的领域”。(13)
苏雪林《中国现代二三十年代作家》第一编“新诗”第十章《颓加荡派的邵洵美》,(14)认为邵洵美是中国颓废派诗的代表,别树一帜。诗集邵洵美《诗二十五首》“序曲”宣称,他的诗歌主要表现“色的诱惑,声的怂恿,动的罪恶”,抒写的爱是“颓加荡的爱”(《颓加荡的爱》),“我是个罪恶底忠实信徒”(《甜蜜梦》),“我们喜欢血和肉的纯洁的结合”、“我们喜欢毒的仙浆及苦的甜味”(《To Swinburne》),这种“结合”和“甜味”发生了变态。邵洵美诗追求官能刺激,以情欲的眼观照宇宙一切,沉溺女性肉体的描绘和赞美,多写女性的香艳,红唇、皓齿、丰乳、蛇腰,这些妩媚意象洋溢着浓浓的粉脂气。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说“邵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
颓废派以强烈刺激为促醒生存意识之唯一手段,所以显示一种义无反顾的堕落精神和沉沦气息,把丑恶当做美丽,罪恶当做道德,表现变态、病态。章克标说:“邵洵美在那名为《花一般的罪恶》的小小集子里,所表现的是一个近代人对爱欲微带夸张神情的颂歌。以一种几乎是野蛮的、直感的单纯,同时又是最近代的颓废,成为诗的每一章的骨骸与灵魂,是邵洵美诗歌的特质。”(15)邵洵美的诗《春》:“啊,这时的花总带着肉气,不说话的雨丝也含着淫意。”《花一般的罪恶》:“那树帐内草褥上的甘露,正像新婚夜处女的蜜泪;又如淫妇上下体的沸汗,能使多少灵魂日夜迷醉。”《颓加荡的爱》“爱”热烈、迷乱而消魂:
睡在天床的白云,
伴着他的并不是他的恋人。
许是快乐的怂恿吧,
他们竟也拥抱了紧紧亲吻。
啊,和这朵交合了,
又去和那一朵缠绵地厮混。
在这音韵的色彩里,
便如此吓消灭了他的灵魂。
颓废派诗人虽消沉、堕落、厌世,但并不如象征主义那样肯定和赞美死亡,而是向死而生,背转身及时享乐。邵洵美在《死了有甚安逸》中说道:“死了有甚安逸,死了有甚安逸?睡在地底香闻不到,色看不出;也听不到琴声与情人的低吟,啊,还要被兽来践踏,虫来噬啮。西施的冷唇,怎及XX的手热?惟活人吓,方能解活人的饥渴,啊,与其与死了的美女去亲吻,不如和活着的丑妇XXXX。”从审美方式上看,世纪末的痛苦、对现世的不满这些西方颓废诗歌的颓废特质在邵洵美那里转化为人间及时行乐,诗美的追求下放为感官刺激。
邵洵美的《火与肉》是一部唯美—象征主义倾向的批评论集,《贼窟与圣庙之间的信徒》在论述魏尔伦(万蕾)诗学时极尽赞美之能事,徐志摩说邵洵美“是一百分的凡尔仑”。他们的创作和诗学主张有点类似参加颓废主义运动时期的魏尔伦和兰波。
颓废派的作家偏重技巧,所以才情俱佳,文笔无不优美。邵洵美的诗有时造句累赘,用字亦多生硬,但作者天资很高,后来《蛇》、《女人》、《季候》、《神光》,都是好诗。而长诗《洵美的梦》,更显出他惊人的诗才。章克标回忆说:“我们这些人,都有点‘半神经病’,沉溺于唯美派——当时最风行的文学流派之一,讲点奇异怪诞的、自相矛盾的、超越世俗人情的、叫社会上惊诧的风格,是西欧波德莱尔、魏尔伦、王尔德乃至梅特林克这些人所鼓动激扬的东西。”“我们出于好奇和趋时,装模作样地讲一些化腐朽为神奇、丑恶的花朵,花一般的罪恶,死的美好和幸福等,玲珑两极,融和矛盾的语言”。(16)
另外一位特立独行的颓废诗人是白采(1894--1925)。白采原名童汉章(可能追慕尼采的超人哲学而改名),江西临安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少显才华,能诗善画,自治小印,镌“神童绝俗”,又用文言写了一部诗话杂论《绝俗楼我辈语》,由开明书店出版。后父母去世,离家漂泊,又身患羸疾,婚姻不幸,深受打击,四处游走,内心充满孤寂、矛盾和困苦。身世遭际和个性气质,使他接受西方现代哲学和艺术,致力文艺创作,呈现神秘、颓废情调。
白采曾将自己的“字号”取为“废吟”。根据1926年10月薰宇发表于《一般》杂志1卷2期上的《白采》一文介绍,白采1923年起在《创造周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一般》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白采开始时也歌颂着青春,企慕光明,对人生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后来因为家庭变故和疾病打击,一变而为颓废、悲吟,诗作中闪现“骷髅”、“棺材”、“恶魔”、“鸱枭”等意象,近乎恶魔派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风格;但白采之才情、个性和遭际,神似疲命奔走于热带大漠丛林中的天才而早熟的诗人兰波。
白采喜穿深黑色的西服,胸前佩戴一个大领结,那是当时艺术家的标记。他容貌清秀,风神俊朗,可以算得上一个美男子。苏雪林《中国现代二三十年代作家》第一编“新诗”第11章专论“神秘的天才诗人白采”,描述白采相貌:口角虽含微笑,眼光则颇忧郁,面目也像有点浮肿,认为这个人即使不自杀,也决非寿征。(17)白采案上常“陈着红漆小棺材,床旁边放着灰白人头骨”,张着两个黑洞洞的眼窟,露着一副白森森的牙齿。这显然是欢迎死神的表征。(18)诗人白采时常携着一壶酒到公园放歌畅饮,醉则卧花荫下直到天亮。白采的生活方式和创作姿态颇似颓废派的“荡子”dandy。
白采《羸疾者的爱》完稿于1924年,共七百二十余行,为中国现代难得的长诗,1925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羸疾者即肺病者,在当时是视为无药可医的绝症。白采生活放浪怪僻,大概也是因为疾病缠身,苦不堪言,不愿久生,故意乱加糟蹋,以期早日脱离尘世苦海。
长诗《羸疾者的爱》构思奇特,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羸疾者与村长老人、母亲、友人、少女等4人的对话。羸疾者偶然飘泊到一个山川秀美、环境安静的世外桃源山村,“遇见那慈祥的老人,/同他的一个美丽的孤女”。慈祥的老人乃一村长,意欲以美貌的独生女相许,那孤女“倾慕”他。但诗人自知患有羸疾,不能接受这“不胜负荷的大惠”,离开村子。诗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向母亲和友人叙述山村遭遇,母亲和友人都责劝他。最后,那“美丽的孤女”竟辞别父亲,“凭着爱神的保护”,长途跋涉,找到了诗人。少女认定“执拗的人”“自示羸弱”“比别人更强项”啊,苦劝他万勿为病“自馁”,甚至直言“为了爱,使我反厌弃了一切健全”!但“执拗”的羸疾者仍然拒绝,力劝“美丽的孤女”须向武士去找寻健全的人格;须向壮硕像婴儿一般的人去认纯真的美,因为羸弱是百罪之源,阴霾常潜伏在不健全的心里。羸疾者是不中绳墨的朽质,是不可赦的堕落者。诗人规劝姑娘“请早归你自己的故乡”,“记这莽莽天涯,有个人永远为她祝福”;而诗人自己“将求得‘毁灭’的完成,偿足我羸疾者的缺憾”。
白采这首《羸疾者的爱》雄浑阔大,气魄非凡,融入诗人的身世和真情实感,但是这首诗更多的是一种象征艺术建构。已患不治之疾的羸疾者坚决拒绝“美丽的孤女”热诚的爱,实际上是一种“私爱”的否定,“大爱”的皈依;故事人物的设置和环境的安排,也具有象征的色彩。(19)朱自清高度评价这首诗,称赞“意境音节俱臻督造,人物的个性颇带尼采式”,(20)并发表专文对《羸疾者的爱》作全面深入评论,指出长诗纵横铺张,以“深美的思想做血肉”,表达了对“生之尊严”的深切认识,“作者是超出了一般人,是超出了这时代”。(21)后来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列专段介绍。俞平伯认为白采的《羸疾者的爱》“是近年来诗坛中杰作之一”,“此作虽有六千言而绝不病冗长,正缘一气舒卷之故。我认为此为真的长诗,绝非拉长的充数伪品。在风格方面大略有几点特色:(1)不雕而朴,直写不描,故其详实分雄浑阔大。(2)有现代语言的自然音节,顿挫一样并妙。(3)诗中主人个性明活,显然自述其襟怀。思路之深刻,语意之沉痛,语气之坚决,正可作为现代青年颓驰的药石”。(22)白采诗如人生,人生如诗,率性而脱俗、唯美而颓废是贯穿并唱响其人生和诗歌的主旋律。
三、“荡子”的中国化
中国现代“荡子”,在衣着入时,风流倜傥,时尚风光,艺术流美方面,可堪伯仲。但是他们缺少西方dandy的贵族式的孤僻、傲慢和偏见,缺乏对现代性的批判。西方现代性的本质是创造资本主义文明的理性价值的显现,而审美现代性则是对这种理性束缚的质疑和批判,颓废主义正是审美现代性的表现。中国颓废诗学并未对资本主义理性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这两种意义加以区分,而是看作互相包含的现代性。中国颓废诗学也有某种程度的批判意识,但锋芒指向的是阻碍现代性的东西而不是现代性本身,譬如封建道德、社会现实等。有的论者注意到颓废诗学的非理性特征,譬如徐懋庸《文艺思潮小史》,(23)但是认为这种“反科学的倾向”是不值得效仿,应该予以否定。
从审美方式到价值取向上,中国颓废诗学立足现实人生观照,而不是像西方颓废诗学具有超验色彩。中国颓废诗人追求“爱和美”的世界,“不受约束的自然”,以此逃避、抗争传统旧道德和恶俗伪诈的现实社会,自我解放,在有限而短暂的人生里,寻找和开辟令人陶醉、新奇的世界。西方颓废诗学则抒写病态,爱好雕琢,反抗习俗,挑战道德,追求时尚,卓尔不群,自命不凡。西方颓废派诗人认为自己的艺术不反映现实,艺术创造将经验世界转化为审美存在,这种转化离现实越远越完美,离世俗和传统越远越新奇。诗歌艺术世界具有绝对的真实性,而现实受到放逐和贬斥。中国颓废诗学建构诗美天国,但是浸透时代感受,审美触角仍植于现实世界。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研究”(10BWW029)的阶段性成果]
①陈希《颓废:一个中国现代诗学概念的演变史》,《学术研究》,2014年2期。
②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③郭宏安《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99页。
④李欧梵《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46页;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2页。
⑤ 1927年6月《小说月报》17卷号外。
⑥朱右白《中国诗的新途径》,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1-72页。
⑦《声色画报》最初为邵洵美和项美丽合办,1935年9月1日创刊,为中英文对照的月刊,英文名称为vox,“评论”的意思。取名“声色”,非“声色犬马”或“纵情声色”,而是意欲将杂志办得有声有色。
⑧《色彩与旗帜》,1929年1月1日《金屋月刊》1卷1期。
⑨《滕固与狮吼社》,《文苑草木》,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版,第12-13页。
⑩ 亚灵(潘汉年)《新流氓主义》,《幻洲》创刊号。潘汉年总共在《幻洲》上发表总题为“新流氓主义”的单篇有《第一章》、《好管闲事章》、《骂人章》、《我们的性爱观念章》、《女读者与下部“十字街头”》等五篇。
(11)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80-194页。
(12)《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4期,1928年8月16日。
(13)邵洵美《诗二十五首自序》,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版,第6页。
(14)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湾纯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15)(16)(17)章克标《回忆邵洵美》,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编《文教资料简报》,1982年第5期。
(18)薰宇《白采》,1926年10月5日《一般》第1卷2期。
(19)参阅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74页。
(20)俞平伯的《批评〈羸疾者的爱〉的一封信》引述朱自清阅读白采诗的意见,俞文刊载1925年8月23日《文学周报》第187期。
(21) 朱自清《白采的诗》,1926年10月5日《一般》第1卷第2期。
(22)俞平伯《批评〈羸疾者的爱〉的一封信》,1925年8月23日《文学周报》第187期。
(23)徐懋庸《文艺思潮小史》,光华书店,1948年出版,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