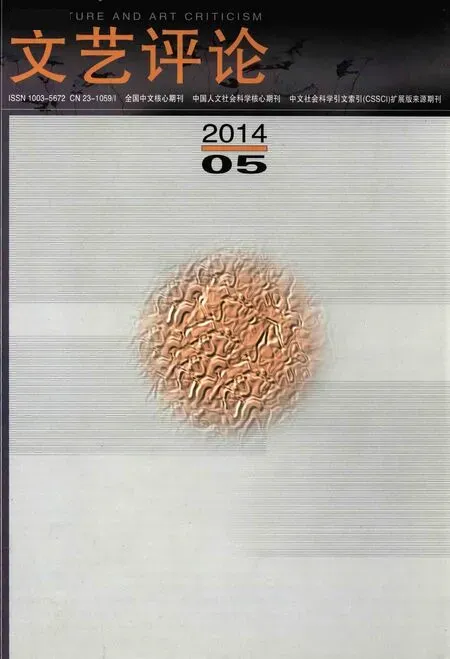真相是意蕴的符码——评长篇小说《盖棺真相》
○刘金祥
新历史主义理论认为历史追忆和文学表述同属于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精魂和文学的价值在质的规定性上并无区别。张育新的长篇小说《盖棺真相》(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以文献资料和今人回忆为依据和支撑,构建起行无辙迹、秘响旁通的艺术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抗日英雄郭跃珠历史事件真相,印证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某种合理性。
美国著名批评家詹姆逊指出:“人类无法接触终极意义上的历史,只能把历史文本化、寓言化,并通过对历史寓言的反复阐释来触摸历史。”张育新运用采访当事人的新闻手法和实地取证的考古手段,摒弃传统的以想象和虚构作为还原历史的话语依据,在文本世界中使历史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的努力取得明显成效。尽管小说《盖棺真相》设置了诸多叙事圈套,但作品最终把郭跃珠事件真相和盘托出,盖棺定论,言之凿凿,藏之名山,留传后世,兑现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创作技巧和对历史负责的科学态度。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但历史不存在绝对客观真相这一命题完全符合唯物史观,因为历史原本就是芜杂和凌乱的,既有很多旁逸斜出的枝蔓,也有诸多淤塞滞阻的支流,在事过境迁近一个世纪之后要廓清和厘定历史真相无异于缘木求鱼,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作品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将已经索解出的历史真相作为一个符码和钟摆,通过对其不断地透析和凝视,使其时刻提醒和告诫读者如果淡化历史、忘记昨天,就会与灾难不期而遇,就会与厄运劈面相迎。作者正是循着这一主旨,在纷杂的社会现实中开掘理性成分,对能够表征时代标识的郭跃珠历史事件这一重要历史符码进行系统打量和悉心点化,厘清它们的历史传承和现实流变,引领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主流接轨、向理性靠拢。
细节是作品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构成作品体系的重要基石。在长篇小说《盖棺真相》中,作者注重发掘和辐辏历史细节,意欲通过历史细节进入历史真相肌理,裸呈郭跃珠历史故事的全部。但历史仅仅是每个人记忆碎片中和自己相关的部分,即被学界所称的“历史的细节”。在作品中,许多人物提供了难以甄别和无法鉴定的历史细节,成为探求历史真相的基本依据。无论是穿针引线的古正中,还是指点迷津的陆鸣;无论是古道热肠的关三爷,还是矍铄健谈的郎石奇;无论是淳朴憨厚的沈福田,还是狷介耿直的柳士良;无论是练达老成的樊国章,还是爽朗开明的郭宇恒;无论是正直仗义的赵振鹏,还是细腻内敛的韩朝成,等等。这些叙述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讲述的故事作为历史细节,既相互关联,又互相抵触,叠加为一帧扑朔迷离、虚幻朦胧的历史符码。换言之,历史在这些人的记忆中注入了先验基因,融入了主观经验,每个人的讲述都是当事人的口头叙述,由于年代久远和记忆误差,他们讲述的内容充满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我”在向这些当事人的求证中既有历史中发生的事件,又有自己对历史人物的感受,以至于一种意识流式的思维理念贯穿和潜蕴于文本始终,读者对缺乏严谨逻辑支撑和充分史料佐证的郭跃珠故事似乎生发出一种疏隔迷离之感,而这正是历史题材小说的独特魅力,也是作者追求的一种艺术效果。
针对历史和现实的辩证关系,黑格尔曾经指出“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只有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密切相关,它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换言之,只有历史发生现实指涉并具有现代性内涵时,才能将主体和客体协调一致起来,才能将史性的“历史”转化为诗性的“小说”。在破译和解析郭跃珠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作者通过简要回溯在古城火车站抵御日寇的李杜等抗战英烈,把读者带回到那个黑云压城、阴霾笼罩的悲怆屈辱的特殊时代。海登·怀特说,一旦存在之物以延续的方式被置放在汹涌的时代大潮之中时,它们就只能通过类比而使彼此发生互相联系。长篇小说《盖棺真相》以郭跃珠慨然赴难近一个世纪为纵轴,以“我”在古城采访各色人等、踏察有关乡村为断面,建构起一个古城百年风云变换的时空坐标系。在这个坐标系上,人生遭际变幻莫测,社会景象五色杂陈,呈现出岁月弗居、人心驿动的历史图景。作品叙事方式既“以史带人”,又“以人带史”,二者兼用且偏重后者,这种“全知视角”,体现了历史与想象的糅合、真实与虚构的互补,既便于打破人物视角狭仄的囿限,展现广阔的历史场景,表达深刻的社会思考,又凸现了人物个体的思想旅程和生命历程,拉近当下与历史的距离,形成现实与历史融会渗透、交错叠合的态势,进而在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彰显主人公生命价值的巨大张力。由于作者是以第一人称入驻作品,所以提供当代理念和客观视角就成为作者进行小说创作的不二选择。在历史层面上,“我”扮演着事件打捞者的角色,为读者最大限度地提供历史信息,强化故事的真实性;在现实层面上,“我”发挥着亲历者的作用,摹绘一幅幅世俗生活画卷,增强读者的在场感。
人物是小说的主体,也是小说的核心要件。这部作品先后共出现四十多个人物,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历史人物发生着联系,但彼此在情感上又显得微妙和复杂,正是这种微妙和复杂折射出动荡年代中历史人物的悲壮人生和悲怆命运。张育新笔下的现实空间是古城农村的乡野民俗和田园风光,其行文旷达疏宕,惊鸿照影,本然纯挚,简洁省豁,散发着浓郁的东北乡野生活气息,别具一种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一旦涉笔历史切入旧事,笔触陡然凝重肃穆,直奔骨殖,独出机杼,深远淹博,简豁深透,于叙述中透逸某种警策,在描绘中潜蕴着为常人所忽略的深刻。解读《盖棺真相》,我们不难发现,活跃在小说里的各色人物,出现在小说里的各种场景,既经过了艺术化的处理,又呈示着某种原生态的韵味。作品中的人物,包括顾梅、郭开、关杏、耿先和、郎学才、王振才、沈令明、郭全武、刘四爷、韩启龙、梁鹏宇、王天枢、关百良,特别是县政协副主席古正中,在直接或间接参与、梳理、体验和感悟历史故事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将各自性格性情袒露出来,个个形神毕肖,神采卓然,这表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要比史学家们所想象的更能激荡出读者的深沉情感和悠远兴会。
历史不仅为当今人们生存和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经验与智慧,还能唤起人类个体与群体的归宿感和自信心,换言之,历史不仅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之一,也是人类守护精神家园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躬身向历史咨询和讨教是助推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历史小说创作关注现实生活的领域越宽泛,历史对现实的启发与触动就越强烈,正如美国华裔著名学者孙隆基所说“具有重要价值的观点,往往是文艺作品从独异视角出发,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构建起一座直抵对方心魂深处的桥梁后产生的”。张育新在小说《盖棺真相》中写下大量创作札记,这些札记大都不囿成宪,宏论迭出,剀切中肯,卓见发人,其主旨在于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审视和理性裁决,发挥文艺作品对社会心理的抚慰和引领、疏导和缓解作用。历史早已幻化成片片烟云,但在作者笔下,我们看到的是气韵生动的历史事件,见到的是性格饱满的历史人物。作者强化发生学观念和历时性意识,立足于生命本体,注重自由心性的抒发,在述说历史故事、叩问古人灵魂中,解析现实悖论,寻找人性出口,抵达澄澈的心灵深处和高远的人性界域,实现对珍藏人类圣洁灵魂的人文境遇的回归与守望。例如对郑毅、郭跃珠、万傻子、申甲丁、沈一夫等历史人物,作者紧扣六辔,敷彩用笔,中锋勾勒,测拖摹写,通过纾捆经历,铺叙故事,剖解人格,估衡事迹,彰显这些历史人物岳峙渊渟之气度、风光霁月之襟怀、磊落俊伟之人格,仿佛时光倒流,历史人物兀立眼前。小说《盖棺真相》追寻历史人物行迹以及揭橥他们和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撒盐于水中,化影响于无形,不露任何痕迹,收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张育新阅历丰赡,经历丰富,且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艺术感觉,诗歌的凝练,散文的抒情,小说的摹绘,多年创作经验的综合积累,使他养成从生活中透视人生况味,思考生命意义的审美能力,《盖棺真相》正是其人生履历和生命体验的结晶。小说的独到和深刻之处在于,郭跃珠事件只是作家感受历史生活的一个缩影,是作家认知中国当代农村社会的一个基因,但是,人性善恶、生命悲欢,又尽在对郭跃珠事件爬梳钩玄式的描写之中,表现出作家对中国社会民间英雄、民间信仰和民间智慧的膜拜、参悟和服膺,对社会历史演化轨迹的深邃思考。他通过《盖棺真相》努力传达的是对民间社会历史和生活逻辑的解读与认知,对价值规范的吁求和对人性道德的呼唤。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也是结构的艺术。小说的结构往往是作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作家不能为了某种理念刻意设置结构,更不能强化结构,如果结构得以强化,就会现出斧凿痕迹和雕琢窘态,就会将丰富的生活格式化、复杂的人物程式化。古今中外的优秀小说作品,其结构一如社会生活本身,自然妥帖,明晰贯通。至于采取何种叙述结构,一方面与作品的主题内容有关,另一方面取决于作家所秉持的叙事态度和叙事立场。《盖棺真相》采用复调式结构进行情节推进,一条路径是以“我”在古城探寻郭跃珠死亡历史事件,破译其身份之谜加以展开,统摄并涵盖作品整体结构;另一条路径则是借助陆鸣的电子邮件、古城县志和各方史料,寻找关于历史事件文字记载的蛛丝马迹。沿着这两条路径走来,读者有时会惊异于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有时会寓目被作者重新点绘的历史现象,在一种生气灌注的语境中获得新知和美感。对于作家而言,语言是创作的起点,也是进入深湛艺术境地的基本工具。经过多年创作实践的锤炼和磨砺,张育新驾驭语言的技巧已经比较娴熟老到。在《盖棺真相》中,作者从古典文学的深处汲取了优质语言元素,运用自如,妙造天然,简峭平实,古朴雅致,轻松中不失凝重,平实中不乏厚重,具有思想的硬度和美学的质感,为读者展现出一个深刻而丰赡、多维而鲜活的精神世界。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为文的优长还表现在对过滤后的东北农村方言、流行语和日常口语的综合运用上,凸显了作品的地方特色和地域风貌,这是张育新长篇小说趋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前,我国正处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衔接置换的特殊阶段,有关人本、人性、人道主义和人类前途命运等严峻问题,诱引当代人频频回首,去审视历史经验能否给处在历史豁口的人类以启迪。因此,如何从现代文化意义上尊重历史,从时代精神主流上返观历史,是“历史小说”创作实践中的关键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张育新的长篇小说在执著“守护日常生活世界”(昆德拉语)的同时,更应充分释放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调动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在小说情节的历史化和历史事件的情节化过程中,深入开掘并艺术地激活那些长期被忽略、被遮蔽的东北历史文化题材,创作出更多文质俱臻、衔华佩实的“历史小说”精品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