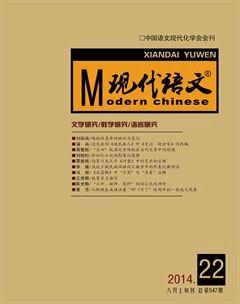历史和现实的契合与逃遁
摘 要: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批评,以怀特的元历史理论为支架,强调从政治权力、经济、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综合解读,分析文学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语言的关系,挖掘被主流意识压抑的它异元素,批判、对抗后现代意识形态霸权的物化、制度化、日常化及语言异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性特征。新历史小说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新的历史意识的创作思潮,但新历史小说并非新历史主义理论的阐释和说明,从历史观、观照视角、叙事方式三个维度表现出新的特征,实现对传统历史主义的拆解和颠覆。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历史观 新历史主义小说
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与文学界,它以反抗旧历史主义、清理形式主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批评,“它试图把在历史研究中被‘某些历史学家看作是‘形式主义谬误(文化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东西,与在文学研究中被‘某些形式主义理论家视为‘历史主义主义谬误(本原主义和指涉主义)的东西结合起来。”[1]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论,强调从政治权力、经济、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综合解读,重新将目光关注于文学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新历史主义跳出形式主义强调的文本视野,获得历史视野,去洞察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通过文本和历史的双重透镜,把握后工业社会中产生消费规律和意识形态控制的真相。
一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资源主要是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由于新历史主义的“开放性”,它既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福柯的权利话语、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成果,又从解释学和接受美学处获得启示。
(一)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怀特认为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虚构想象的、语言学的。“历史总是我们猜测过去也许是某些样子而使用诗歌构筑的一部分”[2]。怀特创新性地提出历史话语的三种解释策略:“形式主义”“情节叙事”“意识形态意义”。而每一种解释策略中,都有四种相对应可能的表达方式:用“形式论证”解释形式主义、有机主义、机械论和语境论;用“情节叙事”解释传奇原型、喜剧原型、悲剧原型、反讽原型;用“意识形态意义”解释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像诗人一样去预想历史的展开和范畴,使其得以负载它用以解释真实事件的理论”[3]。在这里历史意识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历史是不可重现和复原的,寻觅到的只有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所以历史就不只是一种,而是有多少种理论阐释就有多少种历史,人们选择某一种阐释往往出于审美的或道德的思考,“历史修撰的可能形式无非就是历史在哲学思辨意义上的存在形式”。
(二)新历史主义吸收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中的一些成分,尤其借用他的“权力话语”理论来分析作家主体历史和文本。福柯认为文本可以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植根于社会制度中并受其制约,体现着权利的关系。权利根据自己的需求制造出不同于对立面的话语声音,并将这种声音重新置于现存程序中,在打破权利的控制与再分配中延伸了权利,导致对立面丧失原来的控制、支配能力。福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在主导的、合法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外,同时存在着被压抑的它异因素。“昭彰它异不仅否定了统一意识形态的神话,而且通过历史定论对它类因素的压制过程和方式可以透视出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的机制运作情况”[4]。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卢卡契、葛兰西等人推行的意识形态研究模式对后现代文化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分析,批评、对抗后现代意识形态霸权的物化、制度化、日常化及语言异化。本雅明、伊格尔顿、马歇雷、戈德雷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理论,把文学艺术既看作一种意识形态,又看作是一种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阐释了消费社会经济再生产与文化表征的交换互动。新历史主义在这些理论主张的影响下,重新强调历史化、意识形态化,具有政治批判性。它“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并进而发现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异在的不安定因素,揭示出这种复杂社会状况下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以及它们与权利话语的复杂关系”[5]。此外,新历史主义吸收伽达默尔现代阐释学的“视界融合”的影响,认为任何文本都受特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主张从自己所处的具体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对文本进行建构和阐释。
(四)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诗学,将“大历史”化为“小历史”。它把目光关注于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趣事、偶然事件、卑微或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诸多不起眼的小地方,去破译、修正和削弱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心理及其它符码,窥探到权力运作的内在轨迹。新历史主义不是回归大历史,而是为实实在在地进入社会生活层面的小历史提供一种阐释。“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通过对‘小历史的发掘,重新修复了文学的社会流通的双重性”[6]。
新历史主义将文本与历史语境、文学与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文学文本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并重新阐释历史本身。新历史主义广泛吸取当代各种理论成果,跨越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界限,它变通整合各种理论,解读各种文本,关注非主流文化代码,在边缘处境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历史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声音。新历史主义将相对狭隘的文本中心批评和作家中心批评引向多元的文化批评,消解了话语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对立,得以用人类文化的全部知识审视文学,对各种相互对抗、抵制的文学批评流派加以概括和综合,从而使其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但也因理论庞杂,缺乏自己的中心范畴而遭人诟病。
二
新历史小说作为一种创作思潮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是转型期当代中国作家的历史意识与当代西方哲学方法和历史观念相融合而催生的。新历史小说这一概念至今并未有严格的辨析和界定,仅仅因其历史意识与新历史主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而得名,并非新历史主义理论的阐释和说明。新历史小说以鲜明的叙述视角和手法重新叙述历史,与传统历史小说还原历史为目的相迥异,表现出新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新历史小说从历史观、观照视角、叙事方式三个维度表现出新的特征,实现对传统历史主义的拆解和颠覆。
(一)消解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和必然性。新历史小说以偶然性、非理性消解理性主义的本质论、决定论,嘲弄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新历史小说作家们不再拘泥于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回顾,转而开始怀疑历史的可靠性和客观真实性,对历史哲学不断地进行反思,追问历史到底是什么。如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写1942年河南因大旱灾而引发的饥荒,历史在这里断裂成“零碎的”碎片,夹杂许多当事人的记忆错乱和本能地按个人兴趣的添枝减叶,可见历史是多么混乱和虚妄。所谓历史不过是历史叙述的文本而已,由此解构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
传统历史小说依据规律描绘的是一个充满必然性和有序的有定义的历史,新历史小说营造出充斥着偶然性,荒谬性和神秘色彩的历史迷宫,由偶然支配历史的发展,操纵任务的命运。格菲在《迷舟》中让人物的命运完全被一系列不期而至的人和事所摆布和捉弄,旅长萧在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偶然中被警卫员毙了命。由此可见新历史小说在历史观上体现出偶然性对历史决定论的解构。
(二)终结了超个人的政治视角对历史理解的垄断,以民间视角消解正史的庙堂性和主流性,以民间社会为主体构建历史文本,把带有野史味道的传说、轶闻、笔记、趣事推向历史的前台。在新历史小说中,地主、土匪、妓女、商人、黑帮首领等边缘人物一举占领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成为历史主角和言说主体,他们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家族恩怨、村落荣衰等世俗化生活代替正史重大政治事件,历史在这里回到了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平淡化、碎片化,但在某种情况下却还原了历史的原汁原味。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张炜的《古船》等这类家族史题材小说中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描写的中心,历史大事被消融在琐碎的生活中,通过普通家族和个人命运来反映时代和民族的命运。新历史小说通过平民视角把重大历史事件平淡化、碎片化,让人们认识民间也是历史,它既非政治史的图解和延伸,也非政治史的补充和点缀,它们本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只是表现的侧面不同而已。
(三)改变传统历史小说全知全能的历史叙事人模式,取而代之以“我”为叙述者的叙述方式。新历史小说作家心态的最好写照可以用福柯的名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表达,他们相信自己的切身感受要比那些人为编撰的史料更能接近真实,从而也就更接近历史。因此,新历史小说作家以“我”为中心的主观性时空框架改变了传统历史事实自我叙述的客观化现象,“我”作为一个符号,得以自由地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使历史与现实建立了对话关系。历史与现实互相融合到无法区分,即余华所称的“过去和将来只是现在的两种表现形式”[7]。历史不再是静态的客观的,而变为一种个人叙述话语,是在“我”的强烈历史感的话语过程中被给予的,所以历史一跃成为“我”眼中现实状态的历史,叙述人不再遮掩自己对话语的支配,直接由“我”来建构历史。在《红高粱》里,“我”作为叙述人亮出自己现代人的身份,以今天的眼光回忆“我爷爷”“我奶奶”乃至他们同辈人的生活,并且常用“我想”“我猜测”来填充历史过程的残缺,判断模棱两可的疑点,毫无保留地宣布这只是一部“我以为”的历史。
新历史小说打破客观历史时空的限制,构架一种主观的共时的时空,将现实与历史融为一体,这种灵活的共时态叙述使历史与现实相互碰撞相互渗透,彰显出历史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化思潮,它以边缘、颠覆的姿态拆解中心和权威,以怀疑否定的眼光质疑现存秩序,关注被压抑的它异因素,这种新的历史意识和批评方法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我国新历史小说正是因其历史意识与新历史主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而被命名,但它并非西方新历史主义直接影响下的产物,新历史小说创作思潮的形成早于新历史主义这个名词及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它的形成更多的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作家进行历史反思和冷静思考的结果。
注释:
[1][2]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第177页。
[3][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5年版,第409页,第405页。
[4]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6]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7]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90年,第5期。
(吕娟霞 甘肃兰州 兰州商学院长青学院 73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