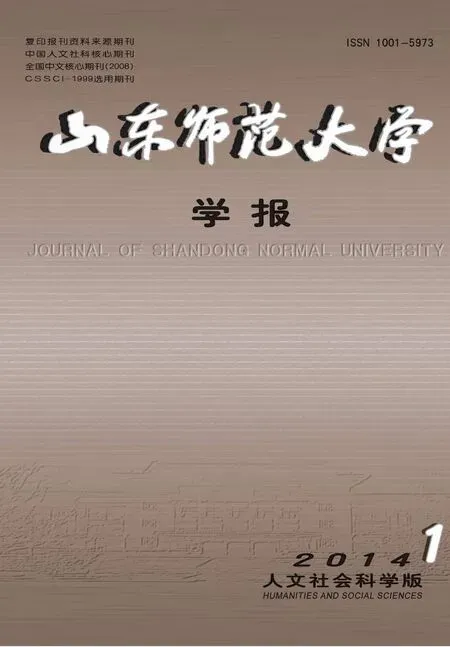《全唐文》初唐诏敕编年考辨*
张 超
( 河南工业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 郑州,450001 )
《全唐文》初唐诏敕编年考辨*
张超
( 河南工业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 郑州,450001 )
《全唐文》是研究唐代文学、文化的重要文献,但由于其编纂乃杂出众人之手,并且历经了漫长的辗转传抄过程,因而其收录的唐代诏敕文本存在很多的讹误,尤其是文本没有系年或系年错误。本文所举的编年考辨之例,包括对无系年的初唐诏敕文的订时,以及对有系年但年号、年份、月份存在争议的初唐诏敕文的考辨。
《全唐文》;初唐诏敕;系年;编年考辨
清代董诰等人编修的《全唐文》因其卷帙浩繁②[清] 董诰,等:《全唐文》,共1000卷。、文献来源广博③《全唐文》底本采用清廷內府抄本《唐文》100卷,同时还收录有《文苑英华》、《唐文粹》、《古文苑》、《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史子杂家等书及金石碑板中的文章。、辑录文章众多④《全唐文》共收录3000余位唐五代文人的18400余篇文作。,被誉为唐五代的文章总集。《全唐文》中收录的唐代诏敕文对于研究唐代文学、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全唐文》的编纂乃杂出众人之手,尤其是“制诰由词臣代笔而以皇帝名义发布,各史籍征引时繁简不已,或录原文,或撮大义,尤易致纷歧”⑤陈尚君:《述<全唐文>成书过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另外,《全唐文》还历经了漫长的辗转传抄过程,其中收录的唐代诏敕文在这一过程中也极易产生讹误,失去本来的面貌。
《全唐文》中的唐代诏敕文存在的讹误包括多种:未注明出处、未进行编年或编年错误、作者身份错误、诏敕文被漏收、已被收录的诏敕文则存在重出误收、讹脱衍倒等讹误。尽管历来已有很多的学者对此予以了关注,如清代陆心源父子《唐文拾遗》672卷、《唐文续拾》616卷,清代劳格《读全唐文札记》、《札记续补》130条,近代岑仲勉《读全唐文札记》6310条,当代学者陈尚君《全唐文补编》等,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将《全唐文》中所有的文本讹误都更正过来。尤其是其中的诏敕文本没有编年或编年错误,给相关研究工作带来很大不便。
西北大学2008年的三篇硕士论文:宋颖芳《<全唐文>唐玄宗李隆基诏敕考辨》、罗妮《<全唐文>唐代宗李豫诏敕考辨》、党秋妮《<全唐文>(晚唐诏敕)考辨》,分别对《全唐文》中的盛唐玄宗诏敕、中唐代宗诏敕以及晚唐诏敕的系年问题予以了考察,但并未关注初唐诏敕的编年考辨。
本文考察的重点正是《全唐文》中初唐六帝⑥初唐六帝,即初唐时期的六位皇帝: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周武则天、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诏敕文的系年问题。所举凡例皆为在多种相关文献记载中系年存在争议的诏敕文,并对其考订真伪,厘正讹误。对于参校出处仅为一处,或者多处记载基本一致者,则暂不列举。
一
《全唐文》卷一至卷三收录了唐高祖李渊的诏敕文。其中的《讨薛举令》亦见载于《册府元龟》卷一百二十二《帝王部·征讨第二》。《全唐文》收录此文,但并无订时。《册府元龟》卷一百二十二在此文前载曰:“隋义宁二年四月,金城贼帅薛举僣称尊号。(上)乃下令”*[宋] 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22,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本文所引《册府元龟》皆为此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将此文订时为“隋义宁二年”;然《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记载:“……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大赦,改元为义宁……(元年)十二月癸未……金城贼帅薛举寇扶风,命太宗为元帅击之。……癸巳,太宗大破薛举之众于扶风”*[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本文所引《旧唐书》皆为此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将此文订时为“隋义宁元年”。两处订时并不一致。《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则记载:“(隋大业)十三年……薛举起金城,号西秦霸王”,“武德元年五月……癸未,薛举寇泾州,秦王世民为西讨元帅,刘文静为司马……辛巳,薛举卒”*[宋]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本文所引《新唐书》皆为此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则将此文订时为“唐武德元年”。唐武德元年与隋义宁二年皆为公元618年,可见《册府元龟》与《新唐书》的记载是一致的。由于《旧唐书》乃五代后晋官修,《新唐书》、《册府元龟》乃北宋时期官修,按照多处文献记载史实有出入时,当依从时间最早的文献的原则,应遵从《旧唐书》的订时,此文应作于隋义宁元年(617)十二月癸未。
《秦王益州道行台制》,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旧唐书》卷二、《新唐书》卷二、《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唐大诏令集》将此文订时为“武德三年四月”,虽然已有确凿的年月,但仅为孤证。又检《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之记载:“(武德)三年二月……诏就军加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两书订时相去甚远,因而需要继续考订。《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载:“(武德)三年四月……高祖遣萧瑀即军中拜太宗益州道行台尚书令。”可见,《新唐书》之订时与《唐大诏令集》相同。再检,《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载:“(武德三年)夏,四月,甲寅,加秦王世民益州道行台尚书令。”*[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8高祖武德三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本文所引《资治通鉴》皆为此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因为《新唐书》毕竟是在《旧唐书》基础上重修的唐史,对《旧唐书》原有记载的讹误进行过订正,且其订时与《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的记载保持了一致,因而此文当作于武德三年(630)四月。
《秦王天策上将制》亦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五《诸王·除亲王官上》。《唐大诏令集》将此文定时为“武德四年九月”*[宋]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35《诸王·除亲王官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年。本文所引《唐大诏令集》皆为此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载:“(武德)四年……冬十月乙丑加秦王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此处订时为“武德四年十月乙丑”。两者系时有出入。《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载:“(武德)四年……十月己丑秦王世民为天策上将。”按照多处文献记载有出入,当依从最早文献的原则,《新唐书》中的“武德四年十月己丑”之“己”当为“乙”之误。又检《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唐纪》五《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之中记载:“武德四年……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印证《旧唐书》记载之实。此文当作于武德四年(621)冬十月乙丑。
《阅武诏》又见载于《五礼通考》卷二百四十、《唐大诏令集》卷一百零七。《五礼通考》卷二百四十记载“唐高祖武德元年十月诏曰”云云,即为此文。《唐大诏令集》卷一百零七载此文,并在文末标注时间为“武德九年十月”。按《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载:唐高祖于武德九年“八月癸亥,诏传位于皇太子。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弘义宫,改名太安宫”,已经不可能进行大阅兵。另外,根据《全唐文》所载诏书的内容“比以丧乱日久,黎庶凋残,是用务本劝耕,冀在丰赡。而人蠹未尽,寇盗尚繁,欲畅兵威,须加练习”*[清] 董诰,等:《全唐文》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页。本文所引《全唐文》皆为此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可知此文当作于唐朝开国不久。另外,《新唐书》卷一记载唐高祖于武德元年十月“辛丑,大阅”。因此,此文当作于武德元年(618)十月。
《置社仓诏》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一十一、《册府元龟》卷五百零二。然《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一十一中题为《置常平监官诏》。《册府元龟》卷五百零二记载此文:“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四日,令州县始置社仓。是年九月二十二日诏曰”云云,即为此文,订年为“武德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一十一记载此文,定时为“武德九年九月”。两者系年不一致。《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第二十九记载此事:“武德元年九月四日置社仓,其月二十二日诏曰”云云,即为此文。《唐会要》卷八十八记载此事:“武德元年九月四日置社仓,其月二十二日诏曰”*[宋] 王溥:《唐会要》卷8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本文所引《唐会要》皆为此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云云,即此文。《旧唐书》、《唐会要》记载与《册府元龟》一致。因而,此文当作于武德元年(618)九月二十二日。《唐大诏令集》记载的“武德元年”之“元”当为“九”之误。
《罢贡异物诏》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八。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停贡献诏》。《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录本文,定时为“武德元年十月”。 《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八载“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诏曰”云云,即为此文,订时为“武德元年十一月”,两者不一致。《新唐书》卷一载此事:武德元年“十一月……戊申,禁献侏儒短节、小马庳牛、异兽奇禽者”。《新唐书》印证《册府元龟》记载之实。此文当作于武德元年(618)十一月。
《每州置宗师诏》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册府元龟》卷六百二十一。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宗姓官在同列之上诏》。《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录此文,定时为“武德二年正月”。 《册府元龟》卷六百二十一载“(武德)二年二月诏曰”云云,即为此文。两者系年均为“武德二年”,但月份不一致。《旧唐书》卷一载此事:武德二年“二月丙戌,诏天下诸宗人无职任者,不在徭役之限,每州置宗师一人,以相统摄。”《新唐书》卷一载此事:武德二年二月“丙戌,州置宗师一人”。两唐书的订时均与《册府元龟》一致,且《旧唐书》当为文献最早出处。因而,此文当作于武德二年(619)二月丙戌。
《曲赦凉甘等九州诏》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三、《册府元龟》卷八十三。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曲赦凉甘等九州制》。《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三录此文,订时为“武德二年二月”。《册府元龟》卷八十三记载武德二年“五月癸未诏曰”云云,即为此文。两者月份记载不一致。《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记载此事:武德二年“五月庚辰,凉州将安脩仁执李轨以降。癸未,曲赦凉、甘、瓜、鄯、肃、会、兰、河、廓九州”。按孤证不立的原则,《唐大诏令集》的订时显然没有《册府元龟》、《新唐书》两者可信。因此,此文当作于武德二年(619)五月癸未。
《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诏》又见载于《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唐会要》卷三十五、《册府元龟》卷五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记载此事:武德“二年诏曰”云云,即为此文。《唐会要》卷三十五《褒崇先圣》条亦记载此文:“武德二年六月一日诏曰”云云。《册府元龟》卷五十亦收录此文,定时为“唐高祖武德二年”。《旧唐书》卷一记载此事:武德二年“六月戊戌,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新唐书》卷一亦载此事:武德二年“六月戊戌,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子监”。多处记载均认定此文当作于武德二年(619),而当年六月的“戊戌”按照干支推算,正是农历的一日。
《平王世充大赦诏》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三、《册府元龟》卷八十三。然《唐大诏令集》中题名为《平王世充复赦》。《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三记载此文,然未订时。《全唐文》正文中有“自武德四年七月十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发露未发露,悉从原免”。《册府元龟》卷八十三记载:武德四年“七月丁卯诏曰”云云,即为此文。根据《全唐文》及《册府元龟》记载,此文当作于武德四年(621)七月十二日(丁卯)。
《讨辅公祏诏》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一十九、《册府元龟》卷一百二十二。《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一十九收录此文,订时为:“武德六年九月。”《册府元龟》卷一百二十二记载此事:“(武德)六年九月,辅公祏遣其党徐绍宗侵海州、陈政通侵寿阳。(高祖)诏赵郡王孝恭水路趋九江,岭南道大使李靖引交广、泉、桂之众趋宣城,怀州总管黄君汉出谯亳,齐州总管李世绩出淮泗,以讨公祏。诏曰”云云。两者皆订时为“武德六年九月”。然而,《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记载:武德六年“八月壬子,东南道行台仆射辅公祏据丹阳反,僭称宋王,遣赵郡王孝恭及岭南道大使、永康县公李靖讨之”。此处订时为“武德六年八月”。 按照多处文献记载史实有出入时,当依从时间最早的文献的原则,《旧唐书》的记载应更可信。为避免孤证不立,又检《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的记载:武德六年“八月壬子,淮南道行台左仆射辅公祏反。乙丑,赵郡王孝恭讨之”。再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六年条的记载:“八月壬子,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祏反。……乙丑,诏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孝恭以舟师趣江州,岭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广、泉、桂之众趣宣州,怀州总管黄君汉出谯、亳,齐州总管李世绩出淮、泗,以讨辅公祏。”可见,《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多处记载是一致的。据此可以推断,此文当作于武德六年(623)八月乙丑。
《颁定科律诏》又见载于《旧唐书》卷五十、《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二。然《唐大诏令集》中题名为《颁新律令诏》。《旧唐书》卷五十记载:“……撰定律令,大略以开皇为准。于时诸事始定,边方尚梗。救时之弊,有所未暇。惟正五十三条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至武德七年五月奏上,乃下诏曰”云云,即为此文。《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二收录此文,订时为“武德七年四月”。两者订时均为“武德七年”,然而月份不一致。又检《旧唐书》卷一记载:武德七年“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颁行新律令。以天下大定,诏遭父母丧者听终制”,此为最早的文献出处,较可信。《新唐书》卷一记载:武德七年“四月庚子,大赦。班新律令”。《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七年条载:“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是日,颁新律令,比开皇旧制增新格五十三条。”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多处文献的记载均认同《唐大诏令集》的“四月庚子”。此文当作于武德七年(624)夏四月庚子朔。
二
《全唐文》卷四至卷十收录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诏敕文。其中,《置文馆学士教》又见载于《册府元龟》卷九十七。《册府元龟》卷九十七记载此事:“唐太宗初为秦王,征求草莽,置驿招聘,皆自远而至。於时海内初平,帝乃锐意经籍,怡神于艺文。因开学馆以待四方之士,又降旨曰”云云,然没有具体的订时。《旧唐书》卷二记载此事:贞观四年“十月,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旧唐书》作为记载此文最早的文献出处,较为可信。因而,此文当作于贞观四年(621)十月。
《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诏》又见载于《旧唐书》卷二、《唐会要》卷四十五、《册府元龟》卷一百二十八。《旧唐书》卷二记载:“(武德九年)九月壬子……长孙无忌封齐国公,房玄龄邢国公,尉迟敬德吴国公,杜如晦蔡国公,侯君集潞国公。”《册府元龟》卷一百二十八记载:“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九月己酉诏曰”云云,即此文。两处系年、系月均为武德九年九月,然具体日期记载不一致,一为“壬子”,另一位“己酉”。又检《唐会要》卷四十五对此事的记载:武德“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诏曰”云云,即为此文。按照中国古代干支纪年法进行推算,武德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当为“壬子”日,可见《旧唐书》为记载此事最早的文献,与《唐会要》是一致的。因此,此文当作于武德九年九月壬子。
《授房玄龄杜如晦左右仆射诏》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四、《册府元龟》卷七十二。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房玄龄杜如晦左右仆射制》。《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四收录此文,订时为“贞观三年二月”。《册府元龟》卷七十二记载:贞观“三年二月诏曰”云云,即为此文。两者记载一致,均为“贞观三年二月”。《旧唐书》卷二记载:贞观三年“二月戊寅,中书令、邢国公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兵部尚书、检校侍中、蔡国公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永康县公李靖为兵部尚书,右丞魏徵为守秘书监,参预朝政”。《新唐书》卷二记载:贞观三年“二月戊寅,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尚书右丞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两唐书记载一致,并进一步将时间具体到当年当月的“戊寅”日。因而,此文当作于贞观三年(629)二月戊寅。
《讨吐谷浑诏》又见载于《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五。《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五记载:贞观八年“十一月吐谷浑拘行人赵德楷,诏曰”云云,即为此文。可见,《册府元龟》的订时为“贞观八年十一月”。然而根据《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八年“十一月丁亥,吐谷浑寇凉州。己丑,吐谷浑拘我行入赵道德。十二月辛丑,命特进李靖、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等为大总管,各帅师分道以讨吐谷浑”。可见,此文之前订时贞观八年“十一月”可能实际为“十二月”。又检《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八年“十一月己丑,吐谷浑寇凉州,执行人鸿胪丞赵德楷。十二月辛丑,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任城郡王道宗为鄯善道行军总管,胶东郡公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以伐吐谷浑”。两唐书的记载一致,可以信从,此文当作于贞观八年(634)十二月辛丑。
《录先朝姻旧臣僚诏》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七、《文苑英华》卷四百四十。然此文于《唐大诏令集》中题名为《高祖山陵毕赐元从功臣及营奉百姓恩泽诏》,《文苑英华》中题名为《优奖太原勋旧德音》。《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七收录此文,订时为“贞观元年十一月”。《文苑英华》卷四百四十亦收录此文,订时为“贞观九年十一月”。两者系年不一致。又检《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记载:贞观九年“五月庚子,太上皇崩于大安宫。……冬十月庚寅,葬高祖太武皇帝于献陵。戊申,祔于太庙”。再检《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载:贞观“五月庚子,太上皇崩,皇太子听政。十月庚寅,葬太武皇帝于献陵”。根据《唐大诏令集》中的题名“高祖山陵毕”可知,这篇诏敕文当于贞观九年十月庚寅葬高祖于献陵之后颁布,应作于贞观九年十一月,而《唐大诏令集》中订时的“贞观元年十一月”,“元年”当为“九年”之误。因此,此文当作于贞观九年(635)十一月。
《九嵕山卜陵诏》又见载于《旧唐书》卷三、《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六。《旧唐书》卷三记载:贞观十一年“二月丁巳,诏曰”云云,即为此文。《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六收录此文,订时为“贞观十年二月”。两者系年不一致。又检《新唐书》卷二的记载:贞观十年“二月丁巳,营九摐山为陵,赐功臣、密戚陪茔地及秘器”。此处记载与《唐大诏令集》一致。此文当作于贞观十年(636)二月丁巳。
《大水求直言诏》又见载于《旧唐书》卷三十七、《唐会要》卷四十三。《旧唐书》卷三十七记载:“贞观十一年七月一日,黄气,竟天大雨。谷水溢入洛阳宫,深四尺,坏左掖门,毁宫寺一十九。洛水暴涨,漂六百余家。帝引咎,令群臣直言政之得失。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伏唯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为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必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畋游之娱;去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不求辟土。载橐弓矢,而无忘武备。凡此数者,愿陛下行之不怠,必当转祸为福,化咎为祥。况水之为患,阴阳常理,岂可谓之天谴而系圣心哉?’十三日,(太宗)诏曰”云云,即为此文。《唐会要》卷四十三记载:“贞观十一年七月一日,黄气,竟天大雨……其月十三日,诏曰”云云,即为此文。两处订时均为“贞观十一年七月十三日”。《旧唐书》卷三记载:贞观十一年“秋七月癸未,大霪雨。谷水溢入洛阳宫,深四尺,坏左掖门,毁宫寺十九所;洛水溢,漂六百家。庚寅,诏以灾命百官上封事,极言得失。丁酉,车驾还宫。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遭水之家,仍赐帛有差”。《新唐书》卷二记载:贞观十一年“七月癸未,大雨,水,谷、洛溢。乙未,诏百官言事。壬寅,废明德宫之玄圃院,赐遭水家”。两唐书订时为“贞观十一年七月乙未”。按照中国古代的干支纪年,当年当月的“乙未”当为十三日。因而此文当作于贞观十一年(637)七月十三日。
《图功臣像於凌烟阁诏》又见载于《旧唐书》卷六十五、《唐大诏令集》卷六十五、《唐会要》卷四十五、《册府元龟》卷一百三十三。《旧唐书》卷六十五记载:贞观“十七年,令图尽无忌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诏曰”云云,即为此文。《唐大诏令集》卷六十五收录此文,订时为“贞观十七年二月”。两者订时皆为“贞观十七年”,后者进一步确定为“二月”。《唐会要》卷四十五记载:贞观“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诏曰”云云,即为此文。《册府元龟》卷一百三十三记载:贞观“十七年二月戊申诏曰”云云,即为此文。《唐会要》及《册府元龟》的订时在“贞观十七年二月”的基础上进一步认定了具体的日期,按照干支纪年的推算,当年当月的“戊申”日即二十八日。因而此文当作于贞观十七年(643)二月二十八日。
《立晋王为皇太子诏》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二十七、《册府元龟》卷二百五十七、《文苑英华》卷四百四十三*[宋] 李昉,等:《文苑英华》卷443,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本文所引《文苑英华》皆为此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唐大诏令集》卷二十七收录此文,订时为“贞观十七年四月”。《册府元龟》卷二百五十七记载:贞观“十七年四月乙酉废太子承乾为庶人。丙戌,诏曰”云云,即为此文。两者订时皆为“贞观十七年四月”。《文苑英华》卷四百四十三收录此文,订时为“贞观十一年四月”。此处与前两者订时不一致。又检《旧唐书》卷三记载:贞观十七年夏四月“丙戌,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大赦,赐酺三日”。《旧唐书》为此处文献最早的出处,较为可信,并且与《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多处文献记载一致。因而此文当作于贞观十七年(643)夏四月丙戌。
《亲征高丽手诏》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三十、《册府元龟》卷一百一十七。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讨高丽诏》。《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三十收录此文,订时为“贞观十八年十月”。《册府元龟》卷一百一十七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十月,帝欲亲总六军以度辽海。进封事者皆劝遣将,不宜亲行……十一月……太宗皆亲加损益,穷其便易。乃手诏示天下”云云,即为此文。《册府元龟》订时为“贞观十八年”十一月,与《唐大诏令集》不一致。求证于《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壬寅,车驾至洛阳宫。庚子,命太子詹事、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出柳城,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副之;刑部尚书、郧国公张亮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以舟师出莱州,左领军常何、泸州都督左难当副之。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由此可见,《册府元龟》的订时无误,《唐大诏令集》所订“贞观十八年十月”乃为脱“一”之误,此文当作于贞观十八年(644)十一月庚子。
所谓就业观,具体就是学生在参加工作选择某一职业时所表现出的一种态度和观念,它是学生对自己就业的一种反应性倾向,由行为倾向、情感倾向和认知倾向三大要素组成。对大学生而言,就业并不意味着就是简单地找一份工作,还与学生后期的人生发展与职业理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因此,学生在校期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就业观是其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要体现,对大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理想以及就业认知和就业心态及其后期在职场上所体现出的态度和修养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伐龟兹诏》又见载于《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五。《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五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诏曰”云云,即为此文。《旧唐书》卷三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寅,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为琯山道行军大总管,以伐龟兹”。《新唐书》卷二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寅,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率三总管兵以伐龟兹”。两唐书与《册府元龟》的系年是一致的。因而,此文当作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十二月戊寅。
《册晋王为皇太子文》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二十八、《文苑英华》卷四百四十三。然《文苑英华》中此文题名为《晋王为皇太子册文》。《唐大诏令集》卷二十八以及《文苑英华》卷四百四十三均收录此文,然皆未订时。《旧唐书》卷三记载:贞观“十七年夏四月庚辰朔,皇太子有罪,废为庶人。汉王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并坐与连谋,伏诛。丙戌,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大赦,赐酺三日”。此处订时为“贞观十七年四月丙戌”。《新唐书》卷二记载:贞观“十七年四月乙酉,废皇太子为庶人,汉王元昌、侯君集等伏诛。丙戌,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大赦,赐文武官及五品以上子为父后者爵一级,民八十以上粟帛,酺三日”。订时与《旧唐书》一致,因而此文当作于贞观十七年(643)夏四月丙戌。
三
《全唐文》卷十一至卷十五收录了唐高宗李治的诏敕文。其中,《定乐舞制》又见载于《旧唐书》卷二十八、《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通典》卷一百四十七、《唐会要》卷三十二、《册府元龟》卷五百六十九。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用庆善曲破阵乐诏》。《旧唐书》卷二十八记载:“(麟德)二年七月制曰”云云,即为此文。《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录本文,定时为“麟德二年十月”。两者订时不一致,暂无法确认真伪。又检 《通典》卷一百四十七记载:“大唐麟德二年十月诏”云云,即为此文。再检《唐会要》卷三十二记载此文,订时为“麟德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诏”。此外,翻检《册府元龟》卷五百六十九记载,此文订时为“麟德二年十月壬戌诏”。 《唐大诏令集》、《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多处记载一致,可以信从。因此,此文当作于麟德二年(665)十月壬戌(二十四日)。
《赐谥皇太子宏孝敬皇帝制》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二十六、《册府元龟》卷二百六十一。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皇太子谥孝敬皇帝诏》。《唐大诏令集》卷二十六录此文,定时为“上元二年四月”,然孤证不立,真伪难辨。 《册府元龟》卷二百六十一记载此事:“太子弘,高宗第五子。初封代王,显庆元年立为皇太子。上元二年薨于合璧宫之绮云殿。诏曰”云云,即为此文。可见,此文订时“上元二年”是对的,但具体月份尚不能确定。又检《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之记载:“(上元二年)夏四月己亥,皇太子弘薨于合璧宫之绮云殿。时帝幸合璧宫,是日还东都。五月己亥,追谥太子弘为孝敬皇帝。”此处订时为“上元二年五月”,然孤证不立。再检《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记载此事:“(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杀皇太子。五月戊申,追号皇太子为孝敬皇帝。”最后检《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二上元二年条记载:“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酖之也。壬寅,车驾还洛阳宫。五月戊申,下诏:‘朕方欲禅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谥为孝敬皇帝’。”可见《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多处记载一致,可以信从,此文当作于上元二年(675)五月。《唐大诏令集》卷订时“上元二年四月”中“四”当为“五”之误。
《即位大赦诏》又见载于《旧唐书》卷四。《旧唐书》卷四记载:“(贞观二十三年)六月甲戌朔,皇太子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二。诏曰”云云,即为此文。《新唐书》卷三记载:“(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太宗崩,以羽檄发六府甲士四千,卫皇太子入于京师。六月甲戌,即皇帝位于柩前。大赦,赐文武官勋一转,民八十以上粟帛,给复雍州及比岁供军所一年。”两唐书的订时一致。因而此文当作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甲戌朔。
《详定刑名诏》又见载于《文苑英华》卷四百六十四。《文苑英华》卷四百六十四录此文,定时为“永徽二年闰九月十四日”。又检《旧唐书》卷四记载“(永徽二年)九月……闰月辛未,颁新定律、令、格、式于天下”。再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记载:“(永徽二年九月)闰月,长孙无忌等上所删定律令式;甲戌,诏颁之四方。”以上三处记载订时为“永徽二年闰九月”,按照干支纪年推算,当年当月的“九月十四日”当为“辛未”日。因而此文当作于永徽二年(651)闰九月十四日。
《恩宥囚徒诏》又见载于《册府元龟》卷八十四。《册府元龟》卷八十四记载:“(永徽)三年正月甲子诏曰”云云,即为此文。又检《旧唐书》卷四记载:“(永徽)三年春正月癸亥,以去秋至于是月不雨,上避正殿,降天下死罪及流罪递减一等,徒以下咸宥之。”两者订时皆为“永徽三年正月”,而在具体日期上,则存在分歧。再检《新唐书》卷三记载:“(永徽)三年正月癸亥,梁建方及处月战于牢山,败之。甲子,以旱避正殿,减膳,降囚罪,徒以下原之。”《新唐书》与《册府元龟》在日期上保持一致,均为当年当月的“甲子”日。因而此文当作于永徽三年(652)正月甲子。
《幸万年宫诏》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九、《陕西通志》卷八十四、《册府元龟》卷一百十三。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赦行幸诸县及岐州诏》。《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九收录此文,订时为“永徽五年二月”。 《陕西通志》卷八十四记载:“(永徽)五年三月,如万年宫,次凤泉汤。辛未,赦岐州及所过徒罪以下。”*[明]赵廷瑞:《陕西通志》卷84,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本文所引《陕西通志》皆为此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此处订时为“永徽五年三月”,与《唐大诏令集》不一致,然无法确定两者真伪。检《册府元龟》卷一百一十三记载:“(永徽)五年二月,戊午,幸万年宫。乙丑,次凤泉幸温汤。己巳至万年宫。辛未诏曰”云云,即为此文。此处可订时“(永徽)五年二月”,似乎《唐大诏令集》是正确的。然又检《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记载:“(永徽)五年春三月戊午,幸万年宫。辛未,曲赦所经州县系囚。”《旧唐书》订时为“永徽五年三月”, 按照多处文献记载史实有出入时,依从时间最早的文献的原则,当从《旧唐书》。为避免孤证不立,再检《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记载:“(永徽五年)三月戊午,如万年宫。乙丑,次凤泉汤。辛未,赦岐州及所过徒罪以下。”可见,《旧唐书》与《新唐书》、《陕西通志》等多处记载是一致的,可以信从。此文当作于永徽五年(654)三月辛未。
《曲赦醴泉县诏》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七、《陕西通志》卷八十四、《册府元龟》卷八十四。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亲谒陵曲赦醴泉县德音》。《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七收录此文,定时为“永徽六年正月”。 《陕西通志》卷八十四记载:“(永徽)六年正月壬申,(高宗)拜昭陵,赦醴泉,免县今岁租调。诏曰”云云,即为此文。《册府元龟》卷八十四记载:“(永徽)六年正月壬申,亲谒昭陵,还行宫。诏曰”云云,即为此文。《旧唐书》卷四记载:“(永徽)六年春正月壬申朔,亲谒昭陵,曲赦醴泉县民,放今年租赋。陵所宿卫将军、郎将进爵一等,陵令、丞加阶赐物。”《新唐书》卷三记载:“(永徽)六年正月壬申,拜昭陵,赦醴泉及行从,免县今岁租、调,陵所宿卫进爵一级,令、丞加一阶。”《资治通鉴》卷记载:“(永徽)六年春,正月,壬申朔,上谒昭陵;甲戌,还宫”。多处文献记载保持一致,因而此文当作于永徽六年(655)正月壬申。
《公主王妃见舅姑父母勿答拜诏》又见载于《唐会要》卷二十六、《册府元龟》卷五十九。《唐会要》卷二十六记载:“显庆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诏”云云,即为此文。《册府元龟》卷五十九亦记载此文:“显庆二年三月诏曰”云云。两处订时并不一致,暂无法确定真伪。又检《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记载的史实:显庆二年“三月戊申,禁舅姑拜公主,父母拜王妃”。可见,《册府元龟》订时较为可信。《唐会要》所系年的显庆二年“正”月当为“三”月形近之误。
《李义府罢相诏》又见载于《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三、《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四。《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四记载:“李义府,高宗龙朔三年四月除名,长流巂州。诏曰”云云,即为此文。又检《旧唐书》卷四记载:龙朔三年“夏四月乙丑,右相李义府下狱。戊子,李义府除名,配流巂州”。两者订时基本一致,均为“龙朔三年四月”。至于是否为当年当月的“戊子”日,则需要再考证。再检《新唐书》卷三记载:龙朔“三年四月戊子,流李义府于巂州”,从而印证《旧唐书》记载属实。因而,此文当作于龙朔三年(663)夏四月戊子。
《赦妄言灾异诏》又见载于《旧唐书》卷八十四、《册府元龟》卷四十三。《旧唐书》卷八十四记载:“咸亨初,高宗幸东都,皇太子于京师监国,尽留侍臣戴至德、张文瓘等以辅太子,独以处俊从。时东州道总管高侃破高丽余众于安市城,奏称有高丽僧言中国灾异,请诛之。上谓处俊曰”云云,即为此文。此处给出的只是一个粗略的时间“咸亨初年”。又检《册府元龟》卷四十三记载:“高宗咸亨二年七月,东州道总管高侃破高丽余众于安市城,侃奏称有高丽僧言中外灾异,请诛之。帝谓郝处俊曰”云云,即为此文。此处系年已经具体。因而,此文当作于咸亨二年(671)七月。
四
《全唐文》卷九十五至卷九十八收录的是唐高宗武皇后的诏敕文。其中,《释教在道法上制》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一十三。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释教在道法之上制》。《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一十三收录此文,定时为“天授二年三月”。《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记载:天授“二年夏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寇之前”。按照多处记载不一致,当依从最早文献的原则,此文当作于天授二年(691)夏四月。
《置鸿宜鼎稷等州制》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九十九、《文苑英华》卷四百六十四。《唐大诏令集》卷九十九收录此文,定时为“天授二年七月九日”。 《文苑英华》卷四百六十四亦收录此文,定时也为“天授二年七月九日”。两处记载一致。又检《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记载:天授二年“秋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分京兆置鼎、稷、鸿、宜四州”。可见,以上订时的年月已经可以确认为“天授二年七月”。再检《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记载:天授二年“七月庚午,徙关内七州户以实神都”。按照干支纪年推算,当年当月的“庚午”日即“七日”。因而,此文当作于天授二年(691)七月九日。
《暴来俊臣罪状制》又见载于《册府元龟》卷九百四十二、《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七。《册府元龟》卷九百四十二记载:“唐来俊臣,则天朝历雒阳令、司农少卿,恣行罗织,多所陷害。自侯王将相被其罗织受戮者不可胜计。复自称其才可比石勒,朝野闻而弥惧。又将诬告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衙将相谋反,翼因此倾动宗社自取国权。俊臣与其党卫遂忠饮,醉自纠发,繇是得罪。制曰”云云,即位此文。文后记载:“时年四十七。俊臣及伏诛,仇人皆脔其肉噉之,斯须而尽,远近莫不称庆。”来俊臣生于公元651年,按照《册府元龟》记载,他被治罪时47岁(古人多按虚岁),因而此诏颁布时间应为公元697年。又检《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记载:神功元年“六月,内史李昭德、司仆少卿来俊臣以罪伏诛”。再检《新唐书》卷四记载:神功元年“六月丁卯,杀监察御史李昭德、司仆少卿来俊臣”。两唐书的记载印证了以上推断。因而此文当作于神功元年(697)六月丁卯。
《令韦叔夏等刊定司礼仪注制》又见载于《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下、《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六、《册府元龟》卷五百六十四。《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下记载:“韦叔夏,尚书左仆射安石兄也。少而精通三礼,其叔父太子詹事琨尝谓曰‘汝能如是,可以继丞相业矣。’举明经。调露年,累除太常博士后属。高宗崩,山陵旧仪多废缺。叔夏与中书舍人贾太隐、太常博士裴守贞等,草创撰定,由是授春官员外郎。则天将拜洛及享明堂。皆别受制,共当时大儒祝钦明、郭山恽,撰定仪注,凡所立议,众咸推服之。累迁成均司业。久视元年,特下制曰”云云,即为此文。此处订时为“久视元年”,然孤证不立。又检《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六记载:“韦叔夏,迁成均司业。则天时,特下制曰”云云,即为此文。*[宋]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236,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此处并无具体订时。再检《册府元龟》卷五百六十四记载:“韦叔夏为春官员外。则天将拜辟雍及享明堂,皆别授制。其当时儒者祝钦明、郭山恽撰定仪注,凡所立义,众咸推伏。久之历迁成均司业。久视元年下制曰”云云,即为此文。《册府元龟》记载与《旧唐书》一致。因而,此文当作于久视元年(700)。
《授相王雍州牧制》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五。然此文在《唐大诏令集》中题名为《相王雍州牧制》。《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五收录此文,订时为“长安二年七月”。《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记载:“(长安)三年秋九月戊申,相王旦为雍州牧。”订时为“长安三年秋九月戊申”两者订时不一致。按照多处文献记载史实有出入时,当依从时间最早的文献的原则,当从《旧唐书》,故“长安三年”较为可信。又检《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七记载此事:长安三年 “秋七月戊申,以相王旦为雍州牧”。再检《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一记载:“三年七月戊申,相王旦为雍州牧。”*[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11,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故可确定月份当在七月。因而,此文当作于长安三年(703)秋七月戊申。
《授韦嗣立凤阁侍郎平章事制》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四。然此文在《唐大诏令集》中题名为《韦嗣立平章事制》。《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四收录此文,然未定时。《旧唐书》卷六记载:“(长安)四年春正月,造兴泰宫于寿安县之万安山。天官侍郎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此处订时为“长安四年正月”。又检《新唐书》卷四记载:“(长安)四年正月丁未,作兴泰宫。壬子,天官侍郎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此处订时与《旧唐书》基本一致,然是否当年当月是“壬子”日,尚需进一步考证。再检《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七记载:长安四年正月“壬子,以天官侍郎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此处记载与《旧唐书》一致,且《旧唐书》作为此文最早的文献出处,较为可信。因而,此文当作于长安四年(704)正月壬子。
《命皇太子监国制》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三十。然此文在《唐大诏令集》中题名为《则天太后命皇太子监国制》。《唐大诏令集》卷三十录此文,定时为“神龙元年正月”。《旧唐书》卷六记载:“神龙元年春正月癸亥,麟台监张易之与弟司仆卿昌宗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军桓彦范、敬晖等,以羽林兵入禁中诛之。甲辰,皇太子监国,总统万机,大赦天下。是日,上传皇帝位于皇太子,徙居上阳宫。”两处记载一致。又检《新唐书》卷四记载:“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等以羽林兵讨乱。甲辰,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新唐书》订时与《唐大诏令集》、《旧唐书》相同。因而,此文当作于神龙元年(705)正月甲辰。
《明堂灾手诏》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三。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明堂灾告庙制》。《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三收录此文,然没有订时。《旧唐书》卷六记载:“证圣元年春一月……丙申夜,明堂灾,至明而并从煨烬。庚子,以明堂灾告庙,手诏责躬,令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极言正谏。”此处订时为“证圣元年”的一月。《旧唐书》为记载此文最早的文献出处,较为可信。然孤证不立,又检《新唐书》卷四记载:“天册万岁元年正月……丙申,万象神宫火。”此处订时“天册万岁元年”的正月。按公元695年原称证圣元年,后改年号为“天册万岁元年”,实际是同一年。因而,此文当作于证圣元年(695)一月。
五
《全唐文》卷十六至卷十七收录了唐中宗李显的诏敕。其中,《大赦雒州制》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三、《册府元龟》八十四。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亲祀明堂赦》。《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三收录此文,定时为“神龙元年九月”。《旧唐书》卷七记载:“(神龙元年)九月壬午,亲祀明堂,大赦天下。”此处记载与《唐大诏令集》一致,且《旧唐书》作为记载此文最早的文献出处,较为可信。然孤证不立,又检《新唐书》卷四记载:“(神龙元年)九月壬午,祀天地于明堂。大赦,赐文武官勋、爵,民为父后者古爵一级,酺三日。”再检《册府元龟》八十四记载此文:神龙元年“九月壬午,(中宗)亲祀昊天上帝、土皇地祗于明堂。礼毕,制曰”云云,即为此文。另如《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记载:神龙元年“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地于明堂,以高宗配”。多处记载与《旧唐书》一致。因而,此文当作于神龙元年(705)九月壬午。

《金城公主出降吐蕃制》(P194下)又见载于《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二、《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八、《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金城公主降吐蕃制》。《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记载:“中宗神龙元年,吐蕃使来告丧,中宗为之举哀,废朝一日。俄而,赞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熏然来献方物,为其孙请婚。中宗以所养雍王宗礼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自是频岁贡献。景龙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赞吐蕃等来迎女,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中宗率侍臣观之。(景龙)四年正月制曰”云云,即为此文。”《旧唐书》作为记载此文最早的文献出处,订时为“景龙四年正月”,较为可信。然孤证不立,又检《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二收录此文,定时为“景龙四年正月”。再检《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记载:“(景龙)二年十一月,吐蕃赞普遣其大臣尚赞吐蕃来迎女。四年正月庚午,制曰”云云,即为此文。多处文献记载一致。因而,此文当作于景龙四年(710)正月庚午。
《相王及太平公主不得拜诸王公主制》又见载于《旧唐书》卷七、《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册府元龟》卷三十九。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令宗属姑叔不得拜子侄制》。《唐大诏令集》卷四十收录此文,定时为“神龙元年三月”。《旧唐书》卷七记载:神龙元年“三月辛巳,诏曰:‘君臣朝序,贵贱之礼斯殊……宜告宗属,知朕意焉。’先是,诸王及公主皆以亲为贵,天子之子,诸姑叔见之必先致拜,若致书则称为启事。上志欲敦睦亲族,故下制革之”。此处订时“神龙元年三月”与《唐大诏令集》一致,且《旧唐书》作为记载此文最早的文献出处,较为可信。然孤证不立,又检《册府元龟》卷三十九记载:“中宗神龙元年三月制曰”云云,即为此文。多处记载一致。因而,此文当作于神龙元年(705)三月。
《邵王赠皇太子制》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二。《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二收录此文,订时为“神龙元年二月九日”。《旧唐书》卷七《中宗睿宗本纪》记载“(神龙元年)夏四月戊寅,追赠邵王重润为懿德太子”,订时为“神龙元年夏四月戊寅”。两者记载不一致。按照多处文献记载史实有出入时,当依从时间最早的文献的原则,当从《旧唐书》。然孤证不立,又检《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神龙元年条记载:“(神龙元年四月)戊寅,追赠故邵王重润为懿德太子。”《旧唐书》、《资治通鉴》记载一致,可以信从。此文当作于神龙元年(705)四月戊寅。
《答敬晖请削武氏王爵表敕》又见载于《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旧唐书》卷七《中宗睿宗本纪》记载此事:神龙元年五月“癸卯,降梁王武三思为德静郡王,定王武攸暨为乐寿郡王,河内王武懿宗等十余人并降为国公”。《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中宗本纪》亦记载:神龙元年“五月壬午,迁武氏神主于崇恩庙”。两者订时皆为“神龙元年五月”。再检《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外戚传》的记载:“乞圣慈俯垂矜纳中书舍人岑羲之词也。上答曰”云云,即为此文。文末又载:“于是降封梁王三思为德静郡王,量减实封二百户。定王驸马都尉攸暨为乐寿郡王、河内郡王懿宗为耿国公、建昌郡王攸宁为江国公、会稽郡王攸望为邺国公、临川郡王嗣宗为管国公、建安郡王攸宜为息国公、高平郡王重规为郐国公、继魏王延义为魏国公、安平郡王攸绪为巢国公、高阳郡王驸马都尉崇训为酆国公、淮阳郡王延秀为栢国公、咸安郡王延祚为咸安郡公。中宗时嗣宗至曹州刺史,攸宜工部尚书重规、岐州刺史相次病卒,攸望至太常卿,左迁春州司马而死,延秀伏诛后,武氏宗属缘坐诛死及配流,殆将尽矣。”可见此诏颁布后武氏宗属遂皆被降封。因此,由武氏宗属被贬降的时间,可以确定此诏颁布的时间。因而,此文当作于神龙元年(705)五月。
《即位赦文》又见载于《文苑英华》卷四百六十三,然此文在《文苑英华》中的题名为《神龙开创制》,亦有作《中宗即位制》。《文苑英华》卷四百六十三收录此文,订时为“神龙元年二月五日”。《旧唐书》卷七《中宗睿宗本纪》记载:“神龙元年正月……乙巳,则天传位于皇太子。丙午,即皇帝位于通天宫,大赦天下,唯易之党与不在原限。”订时为“神龙元年正月”。按照多处文献记载史实有出入时,当依从时间最早的文献的原则,当从《旧唐书》,然孤证不立。又检《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中宗本纪》的记载:“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等以羽林兵讨乱。甲辰,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丙午,复于位,大赦,赐文武官阶、爵,民酺五日,免今岁租赋,给复房州三年,放宫女三千人。相王旦为安国相王、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再检《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七记载:神龙元年正月“甲辰,制太子监国,赦天下。以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赍玺书宣慰诸州。乙巳,太后传位于太子。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张易之党不原;其为周兴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没者皆免之。相王加号安国相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没者,子孙皆复属籍,仍量叙官爵”。可见,《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一致,可以信从。因而,此文当作于神龙元年(705)正月丙午。
六
《全唐文》卷十八至卷十九收录了唐睿宗李旦的诏敕文。其中,《加镇国太平公主实封制》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二。然《全唐文》中此文题名为《镇国太平公主加实封制》。《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二收录此文,但并未定时。《旧唐书》卷七记载:“(神龙元年正月)乙巳,则天传位于皇太子。丙午,即皇帝位于通天宫,大赦天下,唯易之党与不在原限。以并州牧相王旦及太平公主有诛易之兄弟功,相王加号安国相王,进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仍赐实封,通前满五千户。” 此处订时为“神龙元年正月乙巳”。《旧唐书》作为记载此文最早的文献出处,较为可信。因而,此文当作于神龙元年(705)正月乙巳。
《赠太子重俊谥节愍制》又见载于《旧唐书》卷八十六、《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一、《册府元龟》卷二百六十一。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赠重俊皇太子制》。《旧唐书》卷八十六记载:“睿宗即位下制曰”云云,即为此文。《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一收录此文,订时为“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似乎比较确凿。然《册府元龟》卷二百六十一记载:“景云元年制曰”云云,即为此文。《旧唐书》卷七《中宗睿宗本纪》记载:“(景云元年)秋七月癸丑,兵部侍郎兼知雍州长史崔日用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丙辰,则天大圣皇后依旧号为天后。追谥雍王贤为章怀太子,庶人重俊曰节愍太子。”订时为“景云元年秋七月癸丑”。《旧唐书》、《册府元龟》两者订时一致,可以信从,此文当为“景云元年”发布。在具体月份上,因《旧唐书》是记载此事最早的文献,应当遵从。因而,此文当作于景云元年(710)秋七月癸丑。
《令僧道并行制》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三、《册府元龟》卷五十三。然此文在《唐大诏令集》中题名为《僧道齐行并进制》。《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三收录此文,定时为“景云二年”。《旧唐书》卷七记载:景云二年“夏四月庚辰,张说为兵部侍郎,依旧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癸未,分瀛州置郑州。诏以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自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齐行道集”。此处系年与《唐大诏令集》一致,均认为是“景云二年”,《旧唐书》更进一步,订时为当年的“四月癸未”。又检《新唐书》卷五记载:景云二年四月“甲辰,作玄元皇帝庙”。此处订时为当年的“四月甲辰”,与《旧唐书》订时月份一致,但具体日期有出入。再检《册府元龟》卷五十三记载:睿宗景云二年“四月手制曰”云云,即为此文。这里只能印证两唐书记载的“景云二年四月”是正确的,但具体日期难以确认。因而,此文当作于景云二年(711)四月。
《立平王为皇太子诏》又见载于《旧唐书》卷八、《唐大诏令集》卷二十七、《册府元龟》卷二百五十七。《唐大诏令集》卷二十七收录此文,定时为“唐隆元年六月”。《旧唐书》卷八记载:唐隆元年六月“睿宗即位,与侍臣议立皇太子,佥曰:‘除天下之祸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平王有圣德,定天下,又闻成器已下咸有推让,宜膺主鬯,以副群心。’睿宗从之。丙午,制曰”云云,即为此文。文后又载:“(景云元年)七月己巳,睿宗御承天门,皇太子诣朝堂受册。是日有景云之瑞,改元为景云,大赦天下。”此处订时与《唐大诏令集》一致,且《旧唐书》作为记载此事最早的文献,较为可信。然孤证不立,又检《册府元龟》卷二百五十七记载:“睿宗唐隆元年六月丁未,以平王隆基有安社稷之功立为皇太子,制曰”云云,即为此文。多处记载一致,因而,此文当作于唐隆元年(710)七月己巳。
《命皇帝巡边诰》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九、《册府元龟》卷一百一十三。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睿宗令皇帝巡边诏》。《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九收录此文,订时为“先天元年十月”。《册府元龟》卷一百一十三记载:“睿宗先天元年十一月,睿宗命帝廵边,诰曰”云云,即为此文。多处文献记载史实有出入时,当依从时间最早的文献的原则。《唐大诏令集》成书于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而《册府元龟》编撰于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早于前者。故此文时间应当按照《册府元龟》的记载订时,当作于先天元年(712)十一月。《唐大诏令集》所订“先天元年十月”之“十”当为“十一月”脱“一”之误。
《命皇帝处分军国政刑诰》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三十、《册府元龟》卷十一。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睿宗令明皇总军国刑政诏》。《唐大诏令集》卷三十收录此文,订时为“先天二年七月”。《旧唐书》卷七记载:先天二年“秋七月甲子,太平公主与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等谋逆,事觉,皇帝率兵诛之。穷其党与,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骑常侍贾膺福、右羽林将军李慈李钦、中书舍人李猷、中书令崔湜、尚书左丞卢藏用、太史令傅孝忠、僧惠范等皆诛之。兵部尚书郭元振从上御承天门楼,大赦天下,自大辟罪已下,无轻重咸赦除之。翌日,太上皇诰曰:‘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后军国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处分。’”。此处订时与《唐大诏令集》基本一致,为“先天二年七月”,且《旧唐书》作为记载此文最早的文献出处,较为可信。然孤证不立,又检《新唐书》卷五记载:先天二年“七月甲子,大赦。乙丑,诰归政于皇帝”。此处亦订时为“先天二年七月”,并进一步确定当年当月的“乙丑”日。再检《册府元龟》卷十一记载:“先天二年七月乙丑,尚书左仆射窦怀贞等,与太平公主同谋,将议废立,期以羽林兵作乱。帝密知之,因以中旨告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等,定计诛之。丙寅,太上皇诰曰”云云,即为此文。此处记载印证《新唐书》确定的日期是无误的。因而,此文当作于先天二年(713)七月甲子。
《遗诰》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十二。然《唐大诏令集》中此文题名为《睿宗遗诰》。《唐大诏令集》卷十二收录此文,订时为“开元四年六月二十日”。《旧唐书》卷七记载:“开元四年夏六月甲子,太上皇帝崩于百福殿,时年五十五。秋七月己亥,上尊谥曰大圣贞皇帝,庙曰睿宗。冬十月庚午,葬于桥陵。天宝十三载二月,改谥曰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新唐书》卷五记载:“开元四年六月,(睿宗)崩于百福殿,年五十五,谥曰大圣真皇帝。天宝十三载,增谥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三处记载均订时为“开元四年六月”。《旧唐书》、《唐大诏令集》的记载进一步确定了具体日期。按照干支纪年推算,当年当月“甲子”日即“二十日”,因而此文当作于开元四年(716)六月二十日。
《册平王为皇太子文》,《唐大诏令集》卷二十八收录此文,订时为“维唐隆元年岁次庚戌七月庚申朔二十日己巳”。《文苑英华》卷四百四十三亦收录此文,订时为“维唐隆元年岁次庚戌七月庚戌朔二十日己巳”。两处记载基本一致。求证记载此文最早的文献出处,《旧唐书》卷八记载:景龙四年“六月,中宗暴崩,韦后临朝称制。韦温、宗楚客、纪处讷等谋倾宗社,以睿宗介弟之重,先谋不利。道士冯道力、处士刘承祖皆善于占兆,诣上布诚款。上所居里名隆庆,时人语讹以‘隆’为‘龙’;韦庶人称制,改元又为唐隆,皆符御名。上益自负,乃与太平公主谋之,公主喜,以子崇简从。上乃与崇简、朝邑尉刘幽求、长上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李仙凫、宝昌寺僧普润等定策诛之。……遂以庚子夜率幽求等数十人自苑南入,总监钟绍京又率丁匠百余以从。分遣万骑往玄武门杀羽林将军韦播、高嵩,持首而至,众欢叫大集。攻白兽、玄德等门,斩关而进,左万骑自左入,右万骑自右入,合于凌烟阁前。时太极殿前有宿卫梓宫万骑,闻噪声,皆披甲应之。韦庶人惶惑走入飞骑营,为乱兵所害。于是分遣诛韦氏之党,比明,内外讨捕,皆斩之。乃驰谒睿宗,谢不先启请之罪。睿宗遽前抱上而泣曰:‘宗社祸难,由汝安定,神祇万姓,赖汝之力也。’拜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押左右万骑,进封平王。睿宗即位,与侍臣议立皇太子,佥曰:‘除天下之祸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平王有圣德,定天下,又闻成器已下咸有推让,宜膺主鬯,以副群心。’睿宗从之。……七月己巳,睿宗御承天门,皇太子诣朝堂受册。是日有景云之瑞,改元为景云,大赦天下”。此处订时为“唐隆元年七月己巳”。多处记载一致,此文当作于唐隆元年(710)七月二十日(己巳)。

以上所举例子,包括年号考辨、年份考辨、月份考辨三种情况,这些仅仅是对《全唐文》中初唐诏敕文编年考辨工作的很小一部分。《全唐文》中还有一些诏敕文,由于参校出处仅为一处,或者多处记载基本一致,并无争议,则暂以文献记载为准,不再一一例举。
Textual Research on Release Dates of Early Tang Dynasty Imperial Edicts In the Entire Donovan
Zhang Chao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EntireDonovan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However, due to the fact that it was edited by various editors, and that different private copies were circulated for a long time, there do exist many errors in the Tang Dynasty imperial edict texts included in it, especially those with no or wrong release dates. The textual research cases on the release dates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imperial edicts cited in the present paper include revisal of those with no release dates, and the rectification of those with the correct release dates, but with disputed reign title, year and month.
EntireDonovan; Imperial edicts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release dates; textual research on release dates
2013-11-20
张超(1980—),女,河南安阳人,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
①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河南工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基金项目“唐代诏敕文化传播价值研究”(2013BS049)的阶段性成果。
I206.2
A
1001-5973(2014)01-0033-15
责任编辑:孙昕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