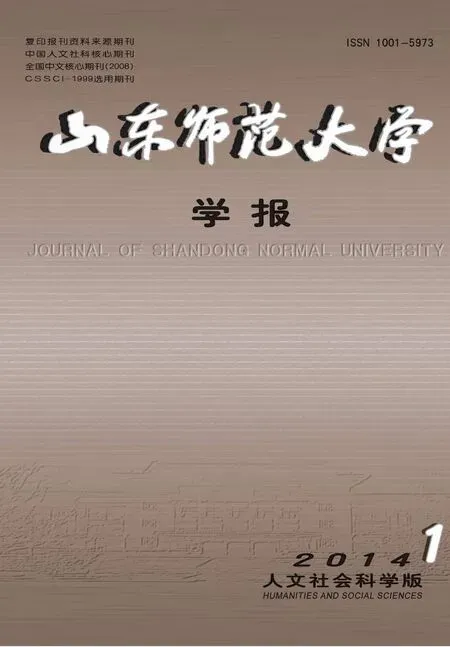“剩余价值的流转”与“自由王国”
——《资本论》美学维度的重构及其意义*
刘方喜
(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
“剩余价值的流转”与“自由王国”
——《资本论》美学维度的重构及其意义*
刘方喜
(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
围绕“剩余价值的流转”对《资本论》的整体理论结构进行梳理:第一卷考察了物质生产由“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构成,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出剩余价值;第二、三卷分别讨论了剩余价值在“流通”等领域的流转及在产业利润、利息、地租之间的分割——这些都是在“此岸”的“必然王国”中的流转,而第三卷有关“自由王国”的论述则揭示剩余价值也可以由“此岸”的“必然王国”向“彼岸”的“自由王国”流转——与此相关,第四卷揭示作为剩余价值的时间存在形态的“自由时间”,只有从“真正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并流转向“自由王国”,存在于“自由王国”中的包括艺术在内的“自由的精神生产”才能繁荣发展起来——此即《资本论》的美学维度。作为剩余价值流转的一种历史性方式,资本不仅阻碍剩余价值流转向工人阶级,而且也阻碍剩余价值流转向“自由王国”,这种“双向”阻碍,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对抗性的两种基本表现。
资本论;美学维度;剩余价值的流转;自由王国;自由的精神生产
不超越学科分化,我们就不可能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乃至马克思本人的整体思想。这其中,马克思在《资本论》及诸多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提到艺术,首先并不是为了创造出一套艺术美学理论体系,但也不是随意提及,而是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而不理解马克思在其中为什么会提到艺术,也就不可能全面、充分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学科分化的当代学术格局中,以马克思后日趋专业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资本论》显然并非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经济学”专著,而由此我们反而也可以得出更为积极的结论: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阐释《资本论》,恰恰会掩盖其非常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或者说,单纯的“经济学”的研究和阐释,对于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整体思想来说,是非常不全面的,乃至不尽准确的。我们强调《资本论》的维度并非“单数”,而是“复数”,“美学”当然并非其唯一的维度——但我们同时也强调问题的另一面:“经济学”也非其唯一的维度,只有在包括“经济学”和“美学”在内的诸多维度的交叉、融合中,《资本论》基本思想才能得到更为全面的揭示。
本文所谓《资本论》的美学维度,主要是通过对《资本论》第3卷有关“自由王国”的著名论述的注解式阐发来加以揭示的。而这段著名论述,出自其中的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之第四十八章“三位一体的公式”,即“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公式”。马克思强调:如果完全停留于这种“公式”,就会形成“假象世界”,而当“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也即把所谓“利润”、“利息”、“地租”的最终根源追溯到“劳动”创造出的“剩余价值”时,这种“假象世界”的宗教式的外观就被“揭穿”了。马克思描述道:“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在剩余价值中合在一起;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态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38页。——为了更彻底地揭穿“假象世界”、突出“剩余价值”的中心地位,《资本论》在总体结构安排上也颠倒了“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前后顺序:第一卷讨论的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第二卷再讨论“流通过程”等,第三卷最后才讨论剩余价值之被“分割”为“利润”、“利息”、“地租”。从“剩余价值的流转”来看:第一卷讨论的就是剩余价值在“生产领域”中的流转,即剩余价值的“创造”,其中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已开始在流转中被“分割”,即产业工人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被产业资本家完全独占;第二卷讨论的是在“流通领域”中的流转,即剩余价值的“实现”,其中,作为中介的商人(商业资本家)已开始从产业资本家手中“分割”剩余价值,而其中的“两大部类”理论可以说还涉及剩余价值在“消费领域”中的流转,并且还涉及剩余价值在“奢侈品”和“必需品”的生产、消费之间的分割;第三卷讨论的则是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银行家(货币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流转(分割)等——如此,《资本论》的整体结构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了。
以上我们以“剩余价值的流转”为主线,粗略梳理了《资本论》的整体结构,而这种“剩余价值的流转”既发生在不同的人(工人、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货币资本家、地主等等)之间,也发生在人的不同活动(生产、流通、消费等等)之间——这大抵已为中外相关研究者所熟知,但一般研究者往往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还强调,这种“剩余价值的流转”也发生在“此岸”的“必然王国”与“彼岸”的“自由王国”之间: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这段文字在中外相关研究中的引用频率是相当高的,但一般的认识和阐释往往脱离这段话的文本语境或上下文,视之为是对所谓“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关系的一般性论述,如此,其重大理论价值就得不到准确而充分的揭示。下面,我们将把这段话置于其逐步扩大的文本语境,即《资本论》的整体结构中来加以阐述和分析。
紧接着这段话之后的一句话是“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也就是说:“工作日的缩短”乃是“自由王国”繁荣起来的“根本条件”(下面的分析我们将揭示这与“自由时间的流转”相关),而许多引述往往不经意间不征引这句话。紧接着这段话之前,马克思还有如下一段很长的论述:
这种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而这个剩余价值存在于剩余产品中。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像在奴隶制度等等下一样,具有对抗的形式……由此可见,在一定时间内,从而在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内,究竟能生产多少使用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这种剩余劳动借以完成的优劣程度不等的生产条件。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5-927页。
以上引文表明:马克思是在“剩余价值”理论语境中来讨论所谓的“自由王国”的,而脱离“剩余价值”来宽泛地、一般性地理解马克思以上的“自由王国”论,在学理上是非常有问题的。马克思强调:“剩余劳动”及与此相关的“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必须始终存在”,“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末,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90页。,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等乃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以“对抗的形式”存在的;反过来说,马克思研究剩余价值,也正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性”。由此亦可见,“剩余价值”范畴绝非仅仅只适用于分析资本主义,也绝非仅仅只是用于揭示工人阶级被剥削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范畴,它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及其文明整体发展历史的重要而基本的哲学范畴。
在《资本论》中,与一系列“价值(财富)”范畴对应的,是一系列“时间”范畴:剩余价值的最终源泉是“真正物质生产”、“一般物质劳动”,“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即“工作日”,“工作日”又由“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使“必要劳动时间”也即维持人的生存基本需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缩短:假设开始的时候,必要劳动时间=3,剩余劳动时间=3,总工作日就=6,生产率的提高后,必要劳动时间可能降低为2,于是就出现了1个单位的“剩余时间”,如果总工作日不变还是6,则新增的1个单位的“剩余时间”就会转移、加入到剩余劳动时间中而使之变为4,进而剩余价值也就变为4——这就是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方式;但是,也可以“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剩余劳动时间保持不变而为3,则总工作日也即“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就降低为5——这就意味着:生产率提高使必要劳动时间所缩短的1个单位的或新增的1个单位的“剩余时间”,被游离出或流转出“一般物质劳动”了,而为榨取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家则把生产率提高新增的“剩余时间”重新投入“一般物质劳动”中——所以,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置“剩余时间”或者说“剩余时间”的流转方向,而对于“自由王国”的繁荣发展来说“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也就意味着:“剩余时间”从“真正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而流转向“自由王国”了。《资本论》第一卷还有如下一段相关论述:
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就越小,从而个人从事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9页。
请注意:“工作日的缩短”与“自由时间”相关,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王国”也与“自由时间”相关,而“自由时间”就是“剩余价值”的时间存在形态。如果局限于“理论部分”,《资本论》前三卷之中只使用了一次“自由时间”,可谓“孤例”或“孤证”,还不足以证明“自由时间”是《资本论》范畴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这就需要进一步扩大文本语境,把“理论史部分”即《资本论》第四卷也纳入考察范围。
《资本论》第四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二、三册)第二十一章“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之“(3)霍吉斯金”最后一段话是:“第一本小册子是以这样的命题结束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而“(1)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之“(c)小册子作者的功绩及其观点在理论上的混乱。他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对外贸易的作用以及‘自由时间’是真正的财富等问题的意义”——在这些部分的论述中,马克思专门、集中讨论了“自由时间”问题:
如果所有的人都必须劳动,如果过度劳动者和有闲者之间的对立消灭了,——而这一点无论如何只能是资本不再存在,产品不再提供占有别人剩余劳动的权利的结果,——如果把资本创造的生产力的发展也考虑在内,那末,社会在6小时内将生产出必要的丰富产品, 这6小时生产的将比现在12小时生产的还多,同时所有的人都会有6小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有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
……即使交换价值消灭了,劳动时间也始终是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财富所需要的费用的尺度。但是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
不言而喻,随着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对立的消灭等等,劳动时间本身——由于限制在正常长度之内,其次,由于不再用于别人而是用于我自己——将作为真正的社会劳动,最后,作为自由时间的基础,而取得完全不同的、更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自由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0-282页。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引述与前引“自由王国”的论述“互训”的话,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马克思的基本思路:“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而以上论述强调:这种劳动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而在不再为“外在目的”的真正自由劳动中,“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自由王国”只能存在于直接生产劳动的“彼岸”,就表现为:作为“自由王国”基础的“自由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要从“直接生产劳动”之中游离出来而“流转”向“自由活动”——再从“价值(财富)”的角度来看,“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就表现为:处在“必然王国”的直接生产劳动创造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自由王国”的基础,但是,“剩余价值”只有从直接生产劳动中游离出来而“流转”向“自由王国”,“自由王国”“才能繁荣起来”——总而言之,“自由时间”、“剩余价值”流转向自由王国,乃是自由王国得以繁荣起来的直接的必要基础或前提条件。
艺术与“剩余价值的流转”密切相关,而发生在艺术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剩余价值的流转”,可以从“自由时间的流转”中更清晰地看出。《资本论》第四卷有如下一段描述:
古代人连想也没有想到把剩余产品变为资本……他们把很大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用于艺术品,用于宗教和公共的建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03页。
为更清晰地理解以上这段话,我们不妨引述马克思为《资本论》所准备的手稿中的相关论述:
其次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不管这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
(剩余劳动创造出剩余产品),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5-216页。
“剩余产品用于非生产性支出”,可以转述为:“剩余产品(时间)”被从“生产”中游离或流转出来,而所谓“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剩余产品”从“生产”中游离或流转出来的时间——因此可以说:“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的“艺术品”存在于从“生产”中流转出来的“自由时间”中或者说是这种“自由时间”的产物——这就是发生在艺术活动与物质生产之间的“自由时间(剩余价值)的流转”,马克思在这种流转中、在“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框架中对“艺术”在人类社会中所作的重要定位,不同于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对艺术所作的定位,而这一艺术思想在过去的研究中被严重忽视了。
再进一步扩大文本语境,在为《资本论》所准备的许多手稿中,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四十六卷上、下册)有很多关于“自由时间”的讨论,如其中《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有如下一些条目:“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增加(人口)。人口可以随着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或者随着活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所需要的时间的相对减少而增加。剩余资本和过剩人口。为社会创造自由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资本的主要使命。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资本中的对立形式”,“真正的节约(经济)=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力的发展。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对立的扬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草稿》中也列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本主义生产的自我扬弃的限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劳动本身转化为社会劳动 ”,“真正的经济。劳动时间的节约。但不是对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26、533、543、545页。等等。由此可见,马克思已将“自由时间”问题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计划。该手稿还把“自由时间”与“艺术”联系在一起:“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1页。该手稿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生产资料的生产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下的自由时间”部分,更是集中、专门地讨论了“自由时间”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1-226页,限于篇幅,兹不引录)。这部分的论述表明:对“自由时间”的处置方式或者说“自由时间流转”方向的不同,乃是共产主义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该手稿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之“亚·斯密把工人劳动看作牺牲的观点。剥削的社会中劳动的对抗性质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真正自由的劳动”部分,马克思指出:
一方面是这种对立的劳动;另一方面与此有关,是这样的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这样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3页。
概括地说:把“自由时间”用于“真正自由的劳动”或者说使“自由时间”流转向“真正自由的劳动”这种处置方式,乃是共产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的社会制度特征之一。或者说,改变“自由时间”或“剩余价值”的流转方式或方向,乃是扬弃资本主义对抗性的重要途径——这与传统上所特别强调的从改变所有制上所作的扬弃,有紧密联系,但也不尽相同。那么,资本主义是如何处置“自由时间”的呢?“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我们可以将这句话跟《资本论》第4卷“‘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有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进行“互训”:“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也就是使“自由时间”重新“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或者说,使直接生产劳动创造出巨量的“自由时间”或“剩余价值”重新流转向直接生产劳动以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由时间”或“剩余价值”的处置方式或“流转”方向。
综上所述,“真正物质生产(一般物质劳动)”和“真正自由的劳动(自由活动)”乃是人的能动性生命创造活动的两个基本部分。在这两个基本部分之间,存在着“剩余价值的流转”:前者存在于“必然王国”,后者存在于“自由王国”,后者存在于前者的“彼岸”,而把“彼岸”与“此岸”连通在一起的是“自由时间”或“剩余价值”的流转。“真正物质生产”创造出“自由时间(剩余价值)”,而“自由时间(剩余价值)”只有从“真正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而流转向“自由王国”、“真正自由的劳动”,“自由王国”才能繁荣起来、“真正自由的劳动”才能发展起来,而艺术乃是存在于“自由王国”之中的“真正自由的劳动”的表现形式之一——此即《资本论》的美学维度。
揭示和重构《资本论》的美学维度,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资本论》第4卷有如下两段论述:
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
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像他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不考虑这些,就会坠入莱辛巧妙地嘲笑过的十八世纪法国人的幻想。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特》来代替《伊利亚特》。(以上黑体与引号为引者所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9、296页。
以上两段论述才是马克思艺术理论、美学思想的“总纲”,因为其不仅涉及到已为传统研究所强调乃至过度强调的艺术与物质生产、艺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还涉及艺术与经济、艺术与自由(自由的精神生产)等多方面的关系,使我们可以更全面、充分地认识和把握艺术活动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以此来看,流行很久、很广的文艺“意识形态(生产出观念)”论只是这一“总纲”的“一方面”,以这“一方面”为马克思艺术理论的全体,当然就是非常片面的;从文艺活动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来看,意识形态论只揭示了其中的一种关系(观念反映关系),另一种基本关系则是在“剩余价值流转”中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从“意识形态”这方面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因为作为“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的“艺术和诗歌”,总体来说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是相协调的而非敌对的;这种敌对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由的精神生产”之间的敌对——许多研究者认识到了这种敌对,但对这种敌对并未作出清晰的解释,而从“剩余价值(自由时间)流转”的角度,这种敌对就会得到清晰的解释。“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是:把真正物质生产创造出的“自由时间”重新投入物质生产中而非从其中游离、流转出来。如此,包括“艺术和诗歌”在内的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彼岸”的“自由的精神生产”所必需的客观物质基础“自由时间”就受到挤压,或者说,这种“敌对”就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阻碍“自由时间(剩余价值)”向“自由的精神生产”领域流转。
揭示和重构《资本论》的美学维度,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英国学者拉什、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一书,把融入了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因素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称为“符号经济”,而与物质生产相关的则是“实体经济”。文艺与经济的交融及由此形成的“符号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当然早已有之,到了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自然更是存在这种符号经济,但总体而言,这种符号经济在那时的整体经济活动中所占份量相对较小,对社会生活整体的影响也相对较小。总的来说,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还主要局限于“实体经济”,那时的经济危机确实也主要首先是由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或“产品过剩”造成的——作为对比,2008年以来肇自美国、蔓延全球的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就首先主要不是由实体经济中的物质产品的生产过剩引发的。但是,融入了越来越多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因素的当代资本主义“符号经济”,依然是一种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的活动,因而也就依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基本的内在对抗性。从剩余价值流转的角度来看,在从实体经济(物质生产)中流转出来的剩余价值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不断迅猛扩张的符号经济,依然处在“此岸”的“必然王国”。我们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只是在传统的“必然王国”(真正物质生产)外,另外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必然王国”(符号经济)领域而已,资本作为一种剩余价值流转和处置方式,依然把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之流转封闭在“必然王国”中,因而也就依然阻碍着财富“向上”向“彼岸”的“自由王国”的流转——同时另一方面也依然“向下”挤压底层大众由“必要财富”维持的生存空间,从而生产和再生产贫困、造成阶级对立——只是这方面与19世纪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符号经济”,是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的,而其很大一部分的实体经济被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同时贫困也被转嫁到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此形成的阶级对立,也就主要不再仅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与资本家两大阶级的对立了。因此,“剩余价值的流转”,依然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符号经济、揭穿各种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神话等重要而有效的理论立足点。
“Flow of Surplus Value” and “Realm of Freedom”:Reconstruc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Aesthetic Dimension in Das Kapital
Liu Fangxi
(School of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To analyze the overall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the four volumes ofDasKapitalwith the “transfer of surplus value” as the center, the first volume concludes that material production is constituted by “necessary labor (time) and surplus labor (time)”, and the latter creates surplus value; the second and third volumes discuss respectively the “flow” of surplus value in the fields of circulation and its split among industrial profits, interests, and rents—however, these are all the flow on this side of the “realm of necessity”; whereas the discussion about “realm of freedom” in the third volume brings to light that surplus value is at the same time able to flow from this side of the “realm of necessity” towards the other side of “realm of freedom”. In addition to this, the fourth volume reveals that “free time”, as the temporal form of existence of surplus value, is able to flourish only by freeing itself from “real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flowing to “realm of freedom”, and finds its existence in “free spiritual production”, including arts, of “realm of freedom”. And this is the very aesthetic dimension of Das Kapital. As one of the historical forms of the flow of surplus value, capital hinders not only the flow surplus value to the working class, but to "realm of freedom" as well. And this two-way hindering constitutes the two basic performances of inherent antagonism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he revel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ofDasKapitalis therefore of multiple significance.
DasKapital;aesthetic dimension;flow of surplus value; realm of freedom; production of free spirit
2013-07-15
刘方喜(1966—),男,江苏扬州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A122
A
1001-5973(2014)01-0100-08
责任编辑:寇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