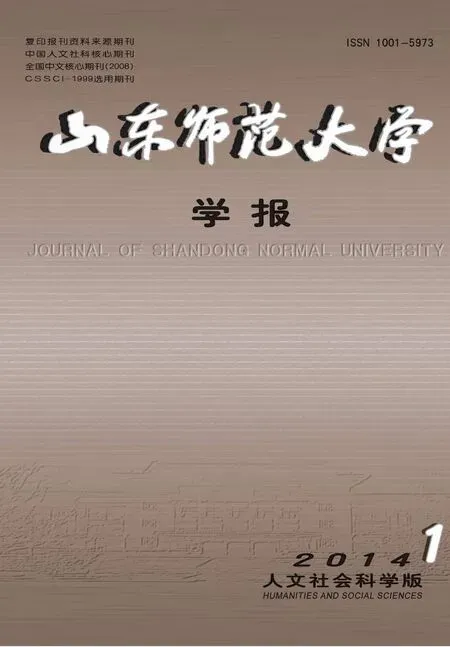1980年代文学中神秘文化思潮的发展轨迹*①
樊 星
(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湖北,430072 )
1980年代文学中神秘文化思潮的发展轨迹*①
樊星
(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湖北,430072 )
在当代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神秘文化思潮是重要的一元。它唤醒了人们的奇特生命体验,也向科学理性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它还在复兴的进程中一度跌入走火入魔的深渊。1980年代的文学,在反思历史悲剧中遁入了关于宗教、命运、偶然的神秘感悟;在对于神秘文化的叩问中发现了偶然对于人生的积极意义,在重新认识民间文化方面剔发了神秘文化的趣味性。
神秘文化;科学理性;民间文化;1980年代
在当代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神秘文化思潮的影响,不可小看。无论是在学术界的“宗教文化热”、“道家文化热”、“弗洛伊德热”,还是在文学界的“寻根热”、“新潮小说热”、“新写实小说热”中,或者是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气功热”、“特异功能热”中,都跃动着神秘文化的精灵。神秘文化的回归,意味深长:它唤醒了人们的奇特生命体验;它向科学理性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它也在复兴的进程中跌入了走火入魔的深渊。而这一切,也都在当代小说思潮的嬗变中体现了出来。本文拟对1980年代文学中的神秘文化思潮的发展轨迹,作一梳理。
一、从“反思”深入到“感悟”
新时期伊始,许多作家都是从控诉“文革”、反思“文革”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这样的控诉与反思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然而,也有作家从一开始就开辟了“反思文学”的新思路,例如礼平发表于1981年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小说一方面通过女青年南珊在“文革”乱世中因为悄然皈依宗教而平静面对磨难的心路历程,从宗教的角度反思“文革”之祸、“红卫兵”运动之教训,既表达了作家对于“文明和野蛮就像人和影子一样分不开”的宿命思考,也道出了在“文革”的废墟上重建信仰的出发点:“这个世界的希望,更多的是在人类自己的心灵中,而不是在那些形形色色的立说者的头脑中”。同时,小说还通过曾经狂热的“红卫兵” 李淮平在结识了泰山长老以后,被长老的深邃智慧、博大情怀所打动的情节,写出了宗教情怀的感染力:“宗教的意义也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宗教以道德为本”, 其“主旨却终不过是劝导人间,使强者怜悯,富者慈悲,让人生的痛苦得到抚慰,于灵魂的空虚有所寄托”。虽然礼平本人对自己的探索显然缺乏足够的自觉意识,以致在面对不难理解的诘难时却矢口否认作品中显而易见的宗教主题②礼平:《谈谈南珊》,《文汇报》1985年6月24日。,但此篇在“宗教热”复兴之前打开了重新认识宗教的新思维,揭示了理智的宗教对于政治狂热的免疫力,实在不易。虽然,从古到今,不同宗教之间的残酷战争也此起彼伏,大量的“邪教”也层出不穷,但《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南珊和泰山长老都怀有远离尘嚣的淡泊心灵,仍然揭示了发人深省的主题:在革命暴力肆虐,摧毁了公德与理智的年代里,如何才能保持心灵的坚韧与完整?重返“以道德为本”的宗教,不失为一个选择。
宗教是精神的奇迹。它能使弱者自强,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使强者仁慈,悲天悯人,厉行善举。在中国人中,佛教信徒甚众,伊斯兰教信众也为数不少。后来,随着西方基督教的传入,基督徒也渐渐多了起来。虽然在“文革”中遭受革命风暴的摧残,一时沉寂,却终于在浩劫过后渐渐复兴。《晚霞消失的时候》正好成为那一页历史的独特记录。而宗教,它的源远流长,它的神秘莫测,它关于心境、信仰、灵魂、来世、宿命的一系列理论,都是人类神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了1983年,周梅森在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中,通过民国八年一幕实业家、官府、乡绅、窑工围绕着开挖煤田导致的生死搏斗,写出了历史错综复杂的悲剧:实业家破产了,工人们失业了,乡绅没有得到好处……“那么,谁得到了好处呢?……这能量上哪去了?为什么看不见?”小说写出了社会矛盾冲突中的两败俱伤,写出了历史的“熵”结局,也就有力地质疑了“历史进步论”。小说还以嘲讽的口吻批判了古老土地抵抗工业文明的愚昧,唤起读者对近代以来“改造国民性”的启蒙呐喊的记忆,但作家的声调显然是悲凉。此后,无论是继续写清末民初的社会史(如《喧嚣的旷野》、《黑坟》、《神谕》),还是写国民党军抗战的历史(如《军歌》、《大捷》、《国殇》),他都以力透纸背的遒劲笔触揭示了“历史的合力”——历史是各股社会力量博弈、互动、共同作用、变化莫测造成的结果,是形形色色的人和欲望、稍纵即逝的偶然与事件在阴差阳错中角力、周旋的复杂活动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因为常常出乎所有参与者的意料之外而显得神秘。而当周梅森特别强调他写的历史是“一种反思的历史,是我们这代人眼睛中特有的历史,是带着我们这代人强烈个性的历史”*周梅森:《关于〈黑坟〉》,《文艺报》1986年5月24日。时,他也就表达了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看透了“文革”历史的复杂性、荒谬性的深刻感悟:有多少关于革命的美好许诺最终被证明是虚妄!有多少神圣的忠诚与牺牲到头来被证明是“现代迷信”的殉葬品!又有多少人事浮沉、命运更迭被证明是权谋、偶然、政治交易的产物!——周梅森就这样写出了历史的非理性。而这样的历史感悟足以启迪人们:应该远离那些似是而非的“历史规律论”,用更复杂的眼光去打量历史——有时,历史是难以理喻的;有时,历史有着令人不堪回首的晦暗面目。
此后,乔良在1986年发表的《灵旗》通过一个红军逃兵的故事表达了当代人的感悟:“历史是奇妙的。它总是在最不可思议的时刻改变面孔。所以它才不断给人以困惑。……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与生俱来地面临如此这般既定的命运”。“时间的一维性。历史的一次性。……一切都是偶然。……一切又都是必然。……这就是历史,你说得清吗?……一个人的命运就是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命运正是所有人的命运的总和。”*乔良:《沉思——关于〈灵旗〉的自言自语》,《小说选刊》1986年第11期。这些思考与周梅森的历史观不谋而合。黎汝清在1987年以后,连续发表了三部着力写“中共历史上的大悲剧”的长篇:《皖南事变》、《湘江之战》和《碧血黄沙》,致力于发掘历史的阴差阳错,追问历史的重重迷雾,发现“世界是不可知的……可知是有限的,不可知是无限的”。“历史功罪之所以难以分清,就是每个作决策与执行者都不是绝对自由的……自己所做的并不是自己想做的!”“万事莫不带有偶然性。”作家主张:“考察历史要从社会现象进入人的心态。世上多数人的名字叫真事隐,假语存。”*黎汝清:《皖南事变》,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44页。乔良、黎汝清的上述作品打开了“重写革命史”的新思维,写活了革命史的复杂与玄妙、偶然与神秘。
历史不再是“合乎理性”、“合乎规律”的。历史因此变得更生动、更混沌、更玄妙、也更神秘,人也因此显得更渺小。
也是在1986年,张炜发表了反思历史的长篇小说《古船》。小说通过两个家族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深刻揭开了历史的另一面:“阶级斗争”与“家族矛盾”纠缠在一起。尽管隋家人开明、厚道、处事周到,仍不敌赵家人的贪婪、凶残、阴险狡诈。问题是:斗争,为什么那么残酷?小说主人公隋抱朴的苦苦思索将苦难的根源引向了人性深处:“人要好好寻思人。……他的凶狠、残忍、惨绝人寰,都是哪个地方、哪个部位出了毛病?”这样的思考令人想起鲁迅关于“偶读《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1页。的感慨,想起历史上那些“血流漂杵”、“杀人如麻”、“草菅人命”、“株连九族”、“满门抄斩”、“斩草除根”的惨剧。其实,儒家不是也讲“恕道”么?可中国人(包括鲁迅)还是更认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睚眦必报”的复仇之道的。人为什么残忍?《古船》触及到一个令人惊心的历史话题,虽然没有深入下去,也足以发人深省。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残忍记忆已经根深蒂固,深深积淀在了国人的记忆中?还是别有人类学、民族学的解释?不得而知。隋抱朴的苦苦思索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要紧的是和镇上人一起”,通过“化干戈为玉帛”结束苦难。这种人道主义的结论能够结束历史的苦难吗?无数事实证明:很难很难。作家后来的小说《家族》、《柏慧》都足以表明:作家在复杂的现实矛盾的挤压下只能远离“化干戈为玉帛”的想法。
由此可见,无论是宗教角度的反思,还是历史角度的反思,或者是人性角度的反思,都体现出当代作家在反思的道路上不断挺进,却终于发现善良的无力、偶然的突变、人性的深不可测的思想轨迹。一切都与正统意识形态关于“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历史规律不可抗拒”、“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等等说法相去甚远;一切也都与当代人对于“文革”的痛苦记忆交织在一起。于是,一切都通向了“世事难料”、“人心叵测”的神秘浩叹。而那其实也是古往今来许多士大夫、老百姓参不透历史的玄机后曾经发出过的浩叹——所谓“天意从来高难问”。
二、从神秘中寻找希望
神秘,不仅仅与迷惘、失意相联。神秘,也常常昭示希望。我在 “寻根文学”与“新潮文学”中都发现了当代作家从神秘文化中发掘希望之光的可贵努力。
在“文革”中,已有“信仰危机”的流行。那当然是对于“现代迷信”的逆反。在“现代迷信”的狂热烟消云散以后,当代人开始“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一部分作家开始从生活充满偶然、偶然改变一切的神秘命运中感悟希望。
应该特别谈到张承志。他是当代理想主义的代表作家,作品散发出浓烈的浪漫气息。需要指出的是,他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都有从人民中寻找人生的启迪的主题,因此可以看出它们与“寻根文学”的息息相通。他发表于1982年的短篇小说《绿夜》就写出了一个富有唯美主义色彩的哲理主题:从“美丽瞬间”中找到希望。小说主人公重返草原寻梦,却发现旧梦已经幻灭。可就在他因为失望而痛苦之时,他发现了平凡生活中“那瞬间的美”——“生活总是这样……周而复始……”,然而,那只在雨夜中为他照明的手电给了他新的感动:“也许,人就应当这样。哪怕一次次失望。因为生活中确有真正值得记忆和怀念的东西。”到了1984年,作家又发表了短篇小说《美丽瞬间》,通过刻画一位学者在天山腹地观美景、遇美人、饮美酒、参加赛马的美妙体验,进一步强化了发现“美丽瞬间”的欣喜——“一生中能有那样一天,真是由于真主的美意。”“人生能有这样的一瞬是不容易的”。到1989年,他在中篇小说《错开的花》中也这样表述了自己的生命观:“仅有一瞬的辉煌生命。”这样的发现与唯美主义悠然相通。虽然唯美主义一向因为颓废的色调遭人批判,但唯美主义关于“人生不过是永恒中的一瞬,但在这短暂的瞬间里也有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人类有意义的生活,就在于玩味、利用这每一刻稍纵即逝的知觉,在于捕捉它最强烈、最纯粹的燃烧点”*[日]上田敏:《漩涡》,引自赵澧、徐京安编:《唯美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10页。的神秘体验仍然具有超越虚无主义的积极意义。在青春已逝、理想已破碎的岁月里,张承志的感悟是:“一切都无所谓有无,只有心中的激动价值千金。”*张承志:《暮春时节》,《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2期。他的理想主义因此而赋有了某种“现代感”,并因此不同于那些思想僵化的“左派”们居心叵测的“理想主义”。此外,在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金牧场》中,他还反复渲染了自己神秘的生命体验:“否认神示和心灵的感知是不对的”,“如果真有神明的话,人心就会发生感应”。“人与神的倾诉秘授确实有过,那种体验已经能串联起我的人生。”——那不仅体现在主人公与蒙古族额吉的心灵感应中,也体现在他与孤独的日本歌手、有着苦难家世背景的日本翻译的相知和息息相通上,还体现在“记得自己曾隐约意识到冥冥之中有一声神异的召唤,那呼唤发于中部亚洲的茫茫大陆,也发于我自己身体里流淌的鲜血之中”的真切体验中。一切都证明:“真情是一种神秘。”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所谓“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些神秘的体验都妙不可言。
“寻根派”作家郑万隆在系列小说《异乡异闻》中,“企图表现一种生与死、人性和非人性、欲望与机会、爱与性、痛苦和期待以及一种来自自然的神秘力量。更重要的是我企图利用神话、传说、梦幻以及风俗为小说的架构,建立一种自己的理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观念”*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在发表于1986年的中篇小说《我的光》中,老猎人库巴图信山神、信“山里的一切,树、草、鸟、兽、风、雨、雷电,包括石头都和人一样,都是有灵性的。‘他们’都认得你,你一定得把‘他们’当亲人一样对待”,并因此成为大自然的朋友和守护人。他的虔诚情感甚至感动了为了开发山林而进山考察的纪教授,使这位教授居然在库巴图的影响下,转变了观念,最后与大山融为了一体(小说里写纪教授在照相时掉进了山谷,但作家特别写到了纪教授死后“奇怪的是身上没有一处伤,脸上非常平静安详,半张着的眼睛里还有喜悦的神色悠悠地流出来”,可谓意味深长)。《我的光》就这样既写出了泛神论信仰竟然与“环境保护”的现代意识悠然相通,又写出了一个老猎人对于老教授的影响和改造(而不是“代表先进文化”的老教授对于笃信泛神论的老猎人的影响和改造),堪称不同凡响。在这样的发现中,我们可以对于“文明与愚昧”之间的微妙关系产生新的感悟:有时,“文明”会引人误入歧途(多少美好的自然都是被“现代文明”毁掉的),而“迷信”则鬼使神差地引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的奇迹、造化的奇迹吧。
“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马原也曾自道:“我比较迷信。信骨血、信宿命、信神信鬼信上帝,该信的别人信的我都信。泛神——一个简单而有概括力的概括。我深信我骨子里是汉人,尽管我读了几千本洋人写的书,我的观念还是汉人的。没法子的事。信庄子和爱因斯坦先生共有的那个相对论认识论,也信在全部相对之上的绝对——典型的形而上主义!”*马原:《马原写自传》,《作家》1986年第10期。这样的“迷信”引导他去探索人性的神秘、文化的奥秘。无论是写《海边也是一个世界》、《错误》、《上下都很平坦》那样的知青小说,还是写《旧死》、《回头是岸》那种扑朔迷离案件的“罪案小说”,或者是《喜马拉雅古歌》、《康巴人营地》、《大师》、《虚构》、《黑道》、《西海的无帆船》、《冈底斯的诱惑》那样的“西藏故事”,马原都能写出世界的匪夷所思、出人意料、神秘莫测。一切都昭示着“生活不是逻辑的”这一非理性的主题。一切都引导人走向怀疑主义。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荒诞不经的童话故事、传奇、神话、民间故事等等充满兴趣”。他自称“是个科学的泛神论者”*许振强、马原:《关于〈冈底斯的诱惑〉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5期。。另一方面,也正因为生活充满了偶然与神秘,“什么都是可能的”,“于是常有希冀”*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上海文学》1985年第2期。,于是完全“应该对下一张牌∕充满想象”*马原:《上下都很平坦》,《收获》1987年第5期。。马原一直对生活保持了好奇心,与这样的人生观密不可分。
余华也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他发表于1989年的小说《鲜血梅花》也写出了偶然的玄妙:武林高手阮进武遭人暗算,他虚弱不堪、“没有半点武艺”的儿子阮海阔却身不由己承担起复仇的使命。有趣的是,阮海阔“无边无际的寻找”、“虚无缥缈的寻找”居然非常偶然地于无意间通过传话使几位武林好汉替他完成了复仇的使命。小说中那些关于“在不知不觉中”“偶而相遇”、“毫无目的地漂泊,却在暗中开始接近……”、“依然是无知的行走使他接近了……”、“莫名其妙地走上了那条通往胭脂女的荒凉大道……又神秘地错开……”的描写都突出了阴差阳错、歪打正着的神秘意义。故事由此揭示了命运的荒诞:强大的不一定幸运(例如阮进武之死);虚弱的不一定无能(例如阮海阔的幸运);偶然可以改变一切;阴差阳错也可能催生奇迹。《鲜血梅花》因此耐人寻味。
是的,偶然常常改变一切。中国古代哲人讲“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讲“苦尽甘来”、“否极泰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讲“人生如弈棋”,都是人生至理。世事变幻莫测,历史充满偶然——人的渺小、人的希望、人的豁达,俱寓其中了!
尽管西方的现代派思想家(如尼采、萨特等)、文学家(如卡夫卡、乔伊斯等)给现代文化涂上了一层浓厚的灰暗色调,尽管他们发出的“上帝死了”、“他人就是地狱”、“人生如迷宫”的悲鸣在相当程度上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迷惘与生存困境,但中国有一部分现代派作家却成功地为“中国的现代派文学”涂上了一层暖色。除去上面提到的马原作品,王蒙富有诗情画意的“意识流小说”、莫言燃烧着生命激情的《红高粱》、史铁生积极探索人生的《礼拜日》、《务虚笔记》,都显示了中国的现代派作家与西方的现代派作家保持距离的良好心态。这也许与中国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乐天”精神有关。虽然,我们也不难在当代中国文坛看到无情的事实——有相当一部分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尽情宣泄了人生的苦闷与绝望,例如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余华的《难逃劫数》,还有韩少功的《爸爸爸》、王蒙的《加拿大的月亮》、莫言的《枯河》……
当迷惘、绝望的病态情绪一直在蔓延时,重新发现乐观的活法与道理,实在必要。
三、发现神秘文化之趣
人对神秘文化有天生的好奇心。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必然催生了人们对神秘文化的热情。1980年代此起彼伏的“气功热”、“宗教热”、“人体特异功能热”都显示了神秘文化回归的时代大趋势。而写出神秘文化的趣味也就成了一部分作家的自觉追求。那希望常常体现在作家对于神秘文化、未知世界的浓厚兴趣上。
贾平凹一直关注神秘现象,并从中得到了巨大的乐趣。他说过:“我就爱关注这些神秘异常现象,还经常跑出去看,西安这地方传统文化影响深,神秘现象和怪人特别多,这也是一种文化。”并说:“我作品中写的这些神秘现象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过,都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东西……我在生活中曾接触过大量的这类人,因为我也是陕西神秘文化协会的顾问。”他还说:“我老家商洛山区秦楚交界处,巫术、魔法民间多的是,小时候就听、看过那些东西,来到西安后,到处碰到这样的奇人奇闻异事特多,而且我自己也爱这些,佛、道、禅、气功、周易、算卦、相面,我也有一套呢。”*贾平凹、张英:《地域文化与创作:继承和创新》,《作家》1996年第7期。此外,他的朋友还告诉读者:“他认真啃过佛经……对佛教特别是禅宗饶有兴趣……他以童心般的好奇来探视神秘玄妙的佛教世界”,直至“自取一法号聊以自慰,曰:抱散居士。”“别人索他墨迹,常书‘禅静’、‘禅怪’以赠。”*白描:《趣味贾平凹》,《作家》1991年第1期。贾平凹自己也多次谈到学禅之事:“我跟一位禅师学禅,回来手书在书房的条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贾平凹:《四十岁说》,《坐佛》,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48页。“星期日……去寺院里拜访参禅的老僧和高古的道长……与历史对话,调整我的时空存在,圆满我的生命状态。”*贾平凹:《西安这座城》,《坐佛》,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77页。作家对传统神秘文化的好奇、“饶有兴趣”不仅使他的作品氤氲着浓厚的神秘氛围,“从佛的角度、从道的角度、从兽的角度、从神鬼的角度等等来看现实生活”,使文学创作“不要光局限于人的视角”(如此看来,文学就不仅仅是“人学”了),*贾平凹:《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坐佛》,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10页。也使得他的生命状态显得丰富、圆满;另一方面,贾平凹也将乡间的神秘传说写入了小说中,使小说赋有了魔幻色彩——发表于1986年的中篇小说《龙卷风》中能够料事如神的赵阴阳,不仅关于来年收成的预言能够应验,而且能够在40年前就预测到秃女之子郑老二的作孽,使其后来魂飞魄散。小说中还写了“鬼市”,并特别指明是“漫衍的传说”:人们在那里买的东西价格便宜,到家后却发现农具全变成纸扎的,牲口也都变成纸叠的了。还有发表于1987年的中篇小说《瘪家沟》中也讲述了一个个神秘的故事:侯七奶奶是基督教徒,患癌后料事如神,认定自己五天后的正午善终,天空中会出五个太阳,结果果然。此事使不信教的木匠也开始信教;木匠的爷爷善盗墓,不想盗墓时遇骷髅上有白绢,上书“X年X月X日夜盗我墓者亡!”盗墓者一看大惊:当日正与绢上日期相合。于是,“当下吓死在墓穴里”。如此料事如神,堪称奇闻。作家写这些神奇的故事,时而点明是“传说”,但更多的并未点明。类似的故事在民间到处流传,体现出百姓喜欢猎奇的特别心态。作家记录下这些传说,显然有回归古代“志怪”、“传奇”之意。*樊星:《贾平凹:走向神秘》,《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另一方面,参照作家有关“我作品中写的这些神秘现象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过,都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东西”的说法,也足以令人产生猜想:作家很可能是相信那些神秘现象的真实性的?既然这世上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巧合、直觉、层出不穷的奇事、怪事,还有某些难以为科学破解的“特异功能”,那么,贾平凹的上述作品也就有了奇特的文学价值——它们是富有中国乡土特色的魔幻之作。更何况,那些传说读来是颇有民俗学的趣味的。
只是,贾平凹的当代“志怪”、“传奇”毕竟显得“魔幻”了一些。相比之下,冯骥才、林希以“说书体”写出神秘文化的趣味,则更富有大众趣味。例如冯骥才发表于1988年的中篇小说《阴阳八卦》。作家写此篇,意在批判传统“认知世界的方式”——“把已知和未知放在一起,看来博大恢宏,包罗万象,它用阴阳五行、太极八卦一分,既含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有狡猾的雄辩,还有感情的神似的写意色彩,有不能自圆其说又能自圆其说的能耐,用这种方式认知世界,世界没有他不知道的问题。……气功、中医、相面、算卦、风水……人们在这种文化心理下容易产生惰性,在这样的常识熏陶下麻木而缺乏进取心,是障碍我们民族前进的心理的元素。”*《冯骥才谈民俗系列小说创作》,《文学报》1989年12月21日。在这段话中,体现了作家在1980年代“新启蒙”思潮影响下反思传统文化弊端的立场。然而,《阴阳八卦》充满了浓郁的天津民间文学趣味,读来令人捧腹,于无形中就淡化了作品的批判主旨,而还原了阴阳八卦的趣味性。小说开篇是一段说书体“闲话”,就颇得市井文学风趣:“……听了这故事,管保叫您信嘛就信嘛”。接下来,引出“一大堆奇事怪事邪事巧事真事假事绝事”——由二奶奶爱折腾摔出毛病引出“神医”瞧病那一套“治病不治祸”的含混“理论”、相士那一番“命是一码事,运是一码事”的玄谈、风水先生驱鬼时滔滔不绝的说道,有讽意也有噱头。有道是:“信也不信,不信也信,天下事都这么糊涂着。”乱糟糟中,“阴气到头,阳气回头”。一切慢慢好了起来。正所谓:“哈哈哈哈哈哈哈,何必眉头皱疙瘩?”小说因此“好看,有趣,可读性和娱乐性强”。*冯骥才:《关于〈阴阳八卦〉的附件》,《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5期。
与《阴阳八卦》相映成趣的,是林希发表于1990年的中篇小说《相士无非子》。有句俗语叫“倒霉上卦摊”,道出了相信算卦的特定心态。《相士无非子》写相士算卦,“干的是耍人的营生”,“在乱乎劲里发财”,也戳破了算命的要害,显示了作家的批判立场。但作家在介绍相士中的“上九流下九流”,以及“以易论世”、“以星宿论世”、“以史论世”的种种“秘籍”时,又写出了那一行里面的沟沟坎坎。小说主人公无非子,相貌奇特,从小眼力过人,在练就三寸不烂之舌、揣摩透世道人情之后,干起“专门吃军阀政客”的险活来。小说几度写他的高深莫测、可进可退,堪称妙笔:先以“九九”二字应对袁世凯,既可以作大吉大顺解,又可以在袁世凯登基八十一天失败后正好成为“九九八十一”的谶语,可谓无懈可击;再写他在军阀混战中以一个“進”字应对晋军败将,当晋军冒进大败,回头来找无非子问罪时,他又解之为“走为上”(走字上面是个佳字),也都言之成理。在这样充满巧合、妙趣横生的故事中,军阀政客的迷信心态,以及相士玩弄军阀政客于股掌间的心机,都跃然纸上了。
冯骥才、林希的上述作品虽然也有批判神秘文化的主旨,写神秘文化的落笔却常常在揭露神秘文化深处的莫测人心上,写神秘预言的应验也常常在“无巧不成书”的玄机中,但是,那些故事的妙趣横生、引人入胜还是能够满足读者的猎奇心态,也多少体现出了作家对神秘文化的留意与兴趣的。中国人喜欢美食华服、琴棋书画、花鸟鱼虫、吹拉弹唱,也喜欢探索神秘文化——关于鬼神、灵魂、得道成仙,关于占卜、命运、吉凶预测。其中不乏迷信与传说,却也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尚奇”心态。中国的古代文学中,从神话到志怪、传奇,都弥漫着浓厚的神秘氛围。即使是《红楼梦》那样基本写实的巨著中,也常常充满了富有神秘意味的描写,例如关于空空道人、太虚幻境、金陵十二钗判词以及那些梦境的渲染。一切都似有若无。一切也诱惑着人们去探索。有了这份情怀,就足以远离那些恐惧末日的情绪与理论。不过,另一方面,多少人生悲剧也是因为兴趣的走火入魔而生,从嗜赌、嗜毒到好色、行骗。
四、警惕神秘文化的另一面
一切事物都有多面性。神秘文化亦然。
神秘文化思潮的迅速高涨,其中不乏玄妙的智慧,也常有欺世盗名的妄说。有作家从发现新思维始,误入迷信的泥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柯云路便是其中一个代表。
柯云路曾是“改革文学”的重要代表。他的小说《新星》是当代“改革小说”中呼唤政治改革的名篇。然而,由于现实中政治改革的难以深入展开,柯云路续写《新星》的“京都三部曲”(《夜与昼》、《衰与荣》、《灭与生》)也始终没有完成。1989年,在风起云涌的“气功热”中,柯云路发表了气功题材的长篇小说《大气功师》。其中,《大气功师》宣传不可思议、荒诞不经的“搬运术”、“遁术”、千里之外发功治病、人体特异功能,并宣称“我的故事是真实的”(据说小说主人公尧臼是以气功师严新为原型的),言之凿凿,令人怀疑。另一方面,该书也在试图创建“真正伟大的哲学、宗教……揭示宇宙及人生的真谛”的同时,意识到新的忧患:“如果人的潜能都被开发出来……任何人都没有思想秘密可言了……而且,现有的财产关系、法律,都失去了神圣意义了……将是一个怎样的‘混乱’”?而该书最后写练功可能导致身体不适等“精神神经症”,以及尧臼叮嘱练功者不要随便表演功夫,一切顺其自然的情节,也隐隐道出了作家的担忧。此后不久,柯云路又发表了“科学哲学小说”《新世纪》,书中表明了作家一方面“反对对科学的愚昧的、盲目的崇拜”,另一方面也“反对对宗教、人体特异功能、气功的愚昧的、盲目的崇拜”的立场,可大量的篇幅还是描绘“宇宙语”、“宇宙自然功”、“扶乩请神”、“特异心理学”等等玄而又玄、却经不起事实检验的神秘体验。这些书的畅销既迎合了“气功热”的需要,也传播了大量误导读者的假想、谬说。而作家一再自我标榜要超越爱因斯坦,创建“人体—宇宙学”的狂想也终于贻笑大方。*到了1998年,柯云路出版了《发现黄帝内经》一书,通过推崇民间“神医胡万林”的行医奇迹宣传“真正重新认识中医,重新研究中医,重新发现中医的巨大潜力”,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着决定人类未来生存、健康、命运的意义”,其意可嘉。可没想到第二年,胡万林就因涉嫌非法行医、致人死命被捕,不久被判有期徒刑15年。《发现黄帝内经》也由新闻出版署发文停售、封存。此事在舆论界轰动一时,成为科学界声讨“伪科学”的著名案例。此后,柯云路回归了小说创作。他走火入魔的教训是令人深思的。在思想解放的洪流中,不乏因为走火入魔而误入歧途的人们。
理性的致命弱点是僵化,而神秘文化的致命弱点则是走火入魔。对于柯云路来说,从思想解放走入弘扬传统神秘文化、开发人的潜能,思路无可厚非;但是,将“惟恍惟惚”的神秘文化推崇为“真正伟大的哲学、宗教”,则未免过头了。事实上,气功可以强身,却不能包治百病;人体特异功能有待开发,“人体特异功能热”中产生的好些骗局一经戳穿也直接导致了此热很快成为过眼云烟;“宗教热”的回归的确慰藉了无数人的灵魂,可也使得一些邪教借势祸害轻信的人们,上演出许多惨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世上不可能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不可能有拯救世界的“真正伟大的哲学、宗教”。
On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Mysterious Cultural Zeitgeist in Literature of the 1980s
Fan Xi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2)
Mysterious cultural Zeitgeist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ntemporary diversified cultural landscape. For it has aroused people’s unique life experience and put forward a powerful challenge against scientific rationalism. More, in the process of its renewal, it has once fallen into the abyss which leads people astray. In the 1980s, many writers expressed their mysterious feelings on religion, fate and occasional mysterious inspiration. Meanwhile, they discovered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mysticism in life as well as the interesting taste in folk mysterious culture.
mysterious culture;scientific rationalism;Folk culture;1980s
2013-07-08
樊星(1957—),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I206.7
A
1001-5973(2014)01-0005-08
责任编辑:李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