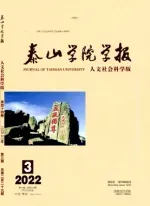论周代授受礼
李志刚
(泰山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泰安 271021)
两周时贵族间的婚嫁、聘飨等,均必执礼物以相见。所执礼物,称作“贽”。杨宽先生曾称执贽以相见之礼为“贽见礼”[1](P790)。实际上,在相授礼物之际亦有一套礼仪,即为“授受礼”。①由于双方尊卑的不同,所站位次、礼容、方式等方面均有不同。现根据先秦文献所载,力图恢复“授受礼”的某些礼仪,并阐述其间所体现的礼义。
一、堂上的授受礼
《左传》成公六年载:
六年春,郑伯如晋拜成,子游相,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郑悼公与晋景公皆为一国之君,地位相当。但郑伯在东楹之东授玉于晋侯,士贞伯讥郑悼公“自弃”,“不安其位”,预测郑伯必死。郑悼公在东楹之东授玉,何以是不安其位?
缘则古代堂上有东西两大柱子,即为东楹、西楹。堂上为礼,宾客东向,近西楹;主人西向,近东楹。东西楹之中,即是中堂。宾、主若地位相当,授受时位于两楹之间;若宾客身份低于主人,授受在中堂与东楹之间,即东楹之西。郑伯虽可尊晋侯为霸主,授玉也只应在东楹之西,今却授玉在东楹之东,远离其所应在之位,且“视流行速”,无谦和安详之态,所以士贞伯讥其自弃其位,预测其必死。
郑悼公过于自卑,远离其所站位次,被认为是弃礼自弃的行为,受到了批评与讥讽。然则在先秦时期古人于授受之际,所站立的位次,要以身份尊卑的差异而定。
《仪礼·士昏礼》“纳采”时,使者与主人“授于楹间,南面”,郑玄注:“授于楹间,明为合好,其节同也。南面,并授也。”此处使者地位卑于主人,授受却在两楹间,郑玄认为此是婚礼,为两姓和好之时,所以“节同”。郑玄所说似因婚礼而提高使者的地位,但使者实仅为中介,真正为礼的还是双方地位相当的主人。《仪礼·士昏礼》:“主人如宾服,迎于门外,再拜。宾不答拜。揖入。”郑注:“不答拜者,奉使不敢当其盛礼。”此处郑玄所言甚为明确。
堂上的授受位次,清儒胡培翚据《仪礼·聘礼》总结有四:
一为宾主敌体,在两楹间,宾面卿,是也。一为宾主虽敌体,而所趋者君命,则在堂中西向,归饔饩于聘宾,受币堂中西,宾问卿堂中西,是也。一为宾臣主君,则直趋君位,当东楹。宾觌,进授币,当东楹。公礼宾,受币当东楹,是也。一为宾主虽君臣,而所执者君之器,则在中堂与东楹之间。聘宾致命,公侧袭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是也。[2](P155)
胡培翚所言第一点,因聘宾也是卿,与主国卿尊卑同,授受时即在东西楹之间。第二点,主国卿以君命馈送饔饩给聘宾时,虽两卿地位等同,但聘宾必在中堂与东楹之间受。此时因在聘宾之馆,主人实是聘宾。第三点,宾主地位悬殊,则主不动,宾直接趋进到君前受。第四宾为臣,主为君,但是宾所执器为己国国君之器,则授受之法与第二点同,表明宾仅为使者,实为两国国君相授受。
从上等可知,堂上授受的地点,以东楹、西楹、中堂为节,无不体现着尊卑秩序。授受之时,尊卑同则双方位移同,均到楹间堂中授受;若尊卑异,则卑者位移大于尊着,就尊着授受;若尊卑过于悬殊,卑者直趋尊者处,尊者不动,相授受。但是,若一方为使者,则以其所代表主人的身份与对方相授受。
礼除堂上授受外,亦有在它处施行者。《士相见礼》:“主人揖,入门右,宾奉贽,入门左。主人再拜,受。宾再拜,送贽,出。”郑玄注:“右,就右也。左,就左也。受贽于庭,既拜送則出矣。不受贽于堂,下人君也。”此处双方身份为“士”,授受在庭中。另亦有阶上授受者,如《士冠礼》宾西阶上降一等,执冠者升一等,授受冠。诸如此类,据时据需而有。
总的来说,堂上授受应为“授受礼”之最隆重者。而授受双方在堂上的位次,无不体现着尊卑秩序的差异。礼所以别尊卑,于此所见尤为明显。
二、授受礼的礼容
前揭郑悼公事,士贞伯讥其“视流而行速”,章太炎先生据《贾子·容经》,认为“视流”即是不端视,流而不端;“行速”即是不从容。[3](P436)杨伯峻先生亦认为郑悼公快步过谦,视流如水,不端正,东张西望。[4](P826)郑悼公与晋景公行礼时,不仅所站位次有误,其礼容也不正。可见,古人在行授受礼时,若违背礼容就可能遭到讥讽。
《左传》僖公十一年载:
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惰。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国语·周语上》所记与此类似,其言晋惠公“执玉卑,拜不稽首”。[5](P31)可见,“受玉惰”与“执玉卑,拜不稽首”意思相同。授受之际的礼容,郑玄在注《聘礼》时曰:“受授不游手,慎之也。”孔颖达疏云:“游暇一手,不慎也。”不游手意为不能单手授受,使另外一手“游暇”。杨宽先生以晋惠公受玉时执得很卑下,释“受玉惰”,甚确。“授受游手”与“执玉卑下”应俱为失礼行为。玉乃受命信物,晋惠公却对之不敬,内史过讥其“先自弃”也就不难理解。
晋惠公遭到的讥讽,与郑悼公如出一辙,均在授受玉器时礼容出现了问题。
古人在“执玉”时的礼容,杨宽先生已有精到的论述。[6](P81)《仪礼·士相见礼》曰:“凡执币者不趋,容弥蹙以为仪。执玉者則惟舒武,举前曳踵。”郑玄注:“不趋,主慎也。以进而益恭为威仪耳。惟舒武者,重玉器,尤慎也。”此等可见,在“授受”前的“执玉”阶段,正如杨宽先生所言,其身体的姿势、神色、脚步,都要郑重其事,战战兢兢,合乎一定的规矩。不然,就会被讥为无礼。《左传》定公十五年载邾隐公朝见鲁公时,两公执玉的方式,亦被子贡作为预测两公命运的依据:
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
邾隐公、鲁定公相朝授受玉器时,邾隐公执玉太高,且容貌仰昂,子贡认为是骄傲的表现;而鲁定公执玉过低,容貌卑俯,认为是废惰有病的表露。过于仰昂或过于卑俯,均不合于礼仪,故子贡预测二君皆不能长久;且还认为因鲁公为主失礼,必先亡。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郑悼公、晋惠公,还是邾隐公、鲁定公,在《左传》中均被预测所测中。因礼容预测施礼者的命运,足见其在春秋时期的重要性。但其所依以判断的根据,似可从下两方面予以讨论。
第一,春秋时期,礼仍然是判断社会行为与个人行为正确与否的准则之一。如《左传》隐公元年云:“豫凶事,非礼也。”《左传》隐公五年云:“公矢鱼于棠,非礼也。”《左传》隐公八年云:“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左传》桓公二年云:“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左传》桓公十五年云:“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左传》庄公十八年云:“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瑴,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礼容作为古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可以用来判断是否合礼的依据。
第二,礼容是施礼者内在性情的反应。《礼记·杂记》云:“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即谓人的情感与外在礼制相称合。《周礼·地官·保氏》中把礼容分为六类,即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车马之容,郑司农对此六种仪容均有描述,如“祭祀之容,穆穆皇皇;宾客之容,严恪矜庄”等。[7](P1010)彭林先生据郭店简的《性自命出》、《成之闻之》、《语丛》诸篇等,再结合传世文献,在“性、情与礼容”方面,已有精彩的论述。其认为“一定的礼,都要体现一定的情感,如冠礼之喜悦,祭礼之诚敬,丧礼之哀痛等等,从而使中心之性外在化,使体态、容色、声音随之变化,舍此则不成为其礼”。[8](P138)在“据情以制礼”的理论下,通过外在的失礼行为来推测施礼者内在性情的失序,再预测其命运,似不难理解。
三、授受礼的方式
《礼记·曲礼》曰:“授立不跪,授跪不立。”郑玄注:“为烦尊者俯仰受之”。《礼记·少仪》亦云:“受立授立,不坐。”即是说,授物于尊者时,尊者站立时,不跪着授;尊者跪坐时,不站立授。授受双方应保持同一的姿势。实际上,“授受礼”中,授受双方的面向,接受物品的方式有多种。
(一)同面并授受
清儒淩廷堪曰:“凡授受之礼,同面者谓之并授受。”[9](P60)淩氏所言甚是。同面并授受,包括两种,即同南面授受与同北面授受。
前引《仪礼·士昏礼》“授于楹间,南面”,郑注:“授于楹间,明为合好,其节同也。
“南面,并授也。”此言使者与主人在堂上楹间,俱南面而授受。再如《仪礼·聘礼》曰:“宾自碑内听命,升自西阶,自左南面受圭,退负右房而立。”郑玄注:“听命于下,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并受也。必并受者,若向君前耳。”此为主国国君使大夫还玉于聘宾的仪节。聘宾与大夫在堂上,俱南面,且聘宾在大夫之左而受圭。必为南面者,郑玄认为是“若向君前耳”,宋儒李如圭亦云“并受者,若在主国君前受也”。[10](P249)再郑玄注《礼记·曲礼》“向与客并,然后受”时云“于堂上则俱南面”,则在堂上时,授受俱朝南,以南为尊。
堂下则同北面授受,此在文献中较为常见。《仪礼·聘礼》:“宰执书,告备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书,授上介。”郑玄注:“其授受皆北面。”再《聘礼》:“使者受圭,同面,垂缫以受命。”郑玄注:“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并授之。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此两处为聘宾受己国君书与圭的仪节,国君在负依处,同北面授受,意亦是向君。同样的例子《聘礼》中还见“士受马者,自前还牵者后,适其右,受。”郑玄注:“适牵者之右而受之也。此亦并授者。”宋儒李如圭曰:
马在庭,北面,西上。牵者各在其西,士受马者从东方来,由牵者之前绕其后,于人东马西受马。受不由其左者,欲牵者已授马,右还而出,便也。[11](P232)
综合郑玄、李如圭所释,此处亦是同北面授受马。但却非“授由其右,受由其左”的授受通例,即非授方在受方的右边,而是受方在授方的右边,因为此乃方便授方(即牵马者)在授讫后右还(实左转)而出。此是授受礼通例中的变例。
(二)讶授
讶,《尔雅》云“迎也”。《诗·召南·鹊巢》:“之子于归,百两御之。”郑玄笺:“御,本亦作讶,又作迓。”此处言以百辆之车迎娶新妇。又《周礼》有“掌讶”、“讶士”等官,贾公彦认为其职为掌迎宾客。淩廷堪云:“凡授受之礼,相向者谓之讶授。”[12](P62)淩氏所言甚是,讶授即为迎面而相授受。
《仪礼·聘礼》“劳宾”节云:“劳者奉币入,东面致命。宾北面听命,还,少退,再拜稽首,受币。”郑玄注:“北面听命,若君南面然。”此时劳者奉主国君命来慰劳聘宾,虽主国国君不在,但聘宾仍得如君在之礼授受。李如圭曰:“劳者授币当南面,卑北面讶受之。凡卑者讶受,敌者并受。”[13](218)授受双方地位同,则同面并相授受,若尊卑不同,则以讶授。李氏所言本自郑玄、贾公彦。但清儒淩廷堪对此稍有异议,其认为“授受之例,统观《礼经》全文,当云:‘行礼于尊者之前则同面受;不于尊者之前,则讶相授受。”授受的方式,不是据授受当事人的身份,而是据授受时是否有尊者在场。淩氏此说实有不确之处,且自己已有疑惑:
惟《士昏礼》纳采,授雁“于楹间,南面”,注以为“并受”。此非行礼于尊者之前,而亦并受,则与此例不合。然《聘礼》傧归饔饩使者,宾面卿,经文皆云“受币于楹间,南面”,与《士昏礼》纳采同。而注又以为授者北面,受者南面,非并受。经同注异,窃疑《士昏礼》之注非也。盖郑贾之说以讶受为尊卑相受之法,并受为敌者相受法;敖氏之说则以讶受为行礼之事,并受为相礼之事。皆与经不合。今仍依郑氏注释之,而附鄙见于此,俟深于礼者择焉。[14](P64)
淩氏因《士昏礼》与《聘礼》经文俱言“受币于楹间,南面”,但郑注一言“并授”,一言“讶授”,故怀疑郑注有误。实际上,《士昏礼》的纳采,前已言使者仅为中介,真正行授受礼的为双方主人。双方主人地位相当,故同南面并授。《聘礼》此处郑注明言“尊君之使”,此处使者亦是君与聘宾的中介,实则乃是君归聘宾饔饩。郑注并非有误。“尊君之使”,实乃尊君。君的地位高于聘宾,故此处讶授,就不难理解。
(三)侧授
关于侧授的记载,《聘礼》所记最为明确。如“公侧授宰玉”,郑玄注:“使藏之,授于序端。”再如“公侧授宰币,皮如入,右首而东”、“公升,侧受几于序端”、“宾降,出。公侧授宰币,马出”等,授受均在君与宰之间施行,且地点在序端。贾公彦曰:“公授受皆于序端。”是也。
君尊,授受之时,多有相者赞助。②《聘礼》“公侧袭,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郑玄注曰:“侧犹独也。言独,见尊宾也。他日公有事,必有赞为之者。”据此郑注,此侧授为公无相之授,其目的在于尊宾。
侧有独义,此在经文中常见。如《士冠礼》“侧尊一甒醴”,郑玄注:“特设一尊醴也。”此处侧,为一、特义。《仪礼》有《特牲馈食礼》篇,特牲即只用豕一种牲。此处侧授,虽在君宰之间,但授受之物,或来之聘宾,如玉、币、马,或为宾而设,如几。君为尊重聘宾,而亲历亲为,是可以理解的。
(四)不起身而相授受
前引《曲礼》与《少仪》两篇,均谓授受双方要么同立,要么同跪,无一立一跪者。但翻诸《仪礼》,此言实有不确之处。
《聘礼》曰:“贾人东面坐,启椟,取圭垂缫,不起而授上介。”下经郑玄注云“上介北面授圭,进,西面授宾”,无言上介有兴起的动作,则其不跪甚为明确。此授受之礼,一跪一立,是为不起而授受之例。此例还见于《仪礼·有司》中:
主妇自东房荐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妇赞者执昌菹、醢以授主妇。主妇不兴,受,陪设于南,昌在东方。兴,取笾于房,麷、蕡坐设于豆西,当外列,麷在东方。妇赞者执白、黑以授主妇。主妇不兴,受,设于初笾之南,白在西方。兴,退。
主妇与妇赞者之间的不起而授受之例,《有司》中多见。不过,此与《聘礼》贾人与上介间的授受还有稍微不同。后者是受方站立、授方跪坐,前者时授方站立、受方不兴。
上面已讨论的并受、讶授、侧受,授受双方均是同时站立授受,与《礼记》所记相合,但此处何以有不起而授受之例?
郑玄在注《聘礼》时认为:“授圭不起,贱不与为礼也。”贾人仅是“在官知物价者”,而上介乃大夫,两者地位过于悬殊,不宜相为抗礼。《有司》在“尸酢主妇”仪节有同为卑者“不起而授受”之例,曰:“妇人赞者执麷、蕡以授妇赞者。妇赞者不兴,受。”《有司》为《少牢馈食礼》的下篇。《少牢》为大夫礼,若妇从夫爵,妇赞者的地位低于主妇,为士一级或更低。妇人赞者,郑玄注以为是“宗妇之少者”,则地位亦不会为高。那么,此妇人赞者与妇赞者的“不起而授受”,不仅是不能参与抗礼,更是无礼可言。《礼记·曲礼》曰“礼不下庶人”,或可释此例。
(五)不亲相授受
《礼记·坊记》曰“男女授受不亲”,郑玄注云:“亲者,不以手相与也。”男女之间,不能亲相授受。《内则》又云:“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则男女若要授受,必以篚为中介,若无篚授方先奠于地上,受的一方再取,不过除丧祭在例外之中。
关于男女授受不亲,讨论最为热烈者,见于《孟子·离娄上》,其曰: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这是孟子用礼的经、权理论,破解礼制规定与人性人情矛盾的著名公案。礼经规定男女授受不亲,但是突发情况下,如嫂溺于水中,则要求权变,必须以手救之于危难之中,否则人与豺狼无异。于此可见强烈的伦理色彩。在《仪礼》一书中,除了男女不相因袭爵外,不相授受的例子亦能见到。《仪礼·士昏礼》载“妇见舅姑”仪节云:
妇执笲枣、栗,自门入,升自西阶,进拜,奠于席。舅坐抚之,兴,答拜。妇还,又拜。降阶受笲腶脩,升,进,北面拜,奠于席。姑坐,举以兴,拜,授人。
据上可知,妇见舅所执的枣、栗,见姑所执的腶脩,均是先奠于席上,舅姑方才或抚之、或举以兴,妇与舅姑没有亲相授受。此处妇与舅的授受,合乎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但妇与姑亦授受不亲,令人费解。
郑玄对舅、妇不亲相授受的解释是“舅尊不敢授”,对姑、妇不亲授受没有解释,似亦可以“姑尊不敢授”推之。姑尊稍低于舅,故仪节多于舅,先坐下再拿起腶脩站起来,授于有司,而舅只坐下抚摸一下,再由宰撤走。李如圭云:“姑举之,若亲受之。”[15](P69)正是此意。姑尊于妇,但又稍低于舅,所以只能是若亲受,而实未亲受。
因尊卑不同而不亲相授受,于《仪礼·觐礼》中亦有所见:“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升致命。王抚玉。”郑玄注:“卑见尊,奠贽而不授。”诸侯觐见天子,授王以玉。但是诸侯并没有亲授王以玉,而是奠玉于地上,王也没有亲受,只是抚摸一下而已,与妇见舅礼同。由上可以看出,不相亲授受者,似有两种情况:一为性别差异,男女不相亲授;二为尊卑差异。但却有一疑问,明言“男女授受不亲”者的《礼记》与《孟子》均为战国时期文献,“男女授受不亲”是否源于战国儒家的总结,在春秋或春秋以前,并无特别的强调?
一般而言,《仪礼》早于《礼记》,但是《仪礼》中虽有男女不相因爵的规定,其关于“不相亲授受”却既有舅妇式的不相亲授受,亦有姑妇式的不相亲授受,更有君臣式的不相亲授受,强调尊卑差异明显浓于性别差异。且我们发现,《诗经》中有大量男女赠送礼物的记载,如《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静女其娈,贻我以彤管。”此处似很难以想象赠送彤管时,会男女授受不亲。再如《郑风·遵大路》:“遵大路兮,执子之祛兮。……执子之手兮。”传统认为此是求贤之诗。朱熹却认为是“淫妇为人所弃,故于其去也,揽其袂而留之”,“亦是男女相悦之词也”。[16](P51)若祛除伦理道德色彩,此诗或如葛兰言所云实乃男女情歌。[17](P51)那么,在执祛、执手之间,更不会有“男女授受不亲”之事。
从上述讨论可以得出,男女间的授受不亲,在战国时期得到儒家的特别提倡,因而闻名于史籍。春秋前的不相亲授受者,似更强调尊卑。且男尊女卑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就不相亲授受而言,性别差异似可包括在尊卑差异之内。
四、余论:授受礼与尊卑观念
尊卑观念是中国古人的重要思想观念,主要表现有天尊地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等;在方位上,有尚右、尚左、尚东、尚西;个人地位上,有尚德、尚爵、尚齿。观念必通过制度、礼仪来表现。可以说,尊卑观念是古礼的核心观念之一。“授受礼”实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接、周旋中,把尊与卑已展露无遗。
前文讨论的堂上“授受礼”,就谈到授受双方在堂上的位次全依其身份而定,若尊卑同就授受于两楹间;若授方为客,受方为主,授方卑于受方,就授受于东楹之西,靠近受方主人处。堂上尊者位移小,卑者位移大,以卑者就尊者为礼。
再如授受的礼容问题,似与尊卑无关,实乃不然。礼容是施礼者表露在外的神态、姿势、动作、仪容等,前已论到其是人内在性情的表现。通过礼容的观察可以察知其内心所思所想,更甚者如《左传》所记可以预测施礼者的未来命运。礼体现着尊卑,郑悼公过于自卑,越过其应站位次,又神态游移,不合尊卑法度。邾隐公与鲁定公执玉姿势不中,容貌不是过于傲慢就是过于卑俯,更是违礼行为。
“授受礼”中体现尊卑最为明显者,实乃授受的方式。授受的方式,按前论有五种,即同面并受、讶授、侧授、不起而相授受与不亲相授受。地位尊同者则同面并授,南面或者北面仅据堂上、堂下而定。后四种,均是尊卑不同者之间的授受,其间的不同,又以地位悬殊程度而定。相差不大则讶授;若一方地位低到是庶人,双方不以抗礼,则不起而相授受;侧授用于君与宰之间;不相亲授受,用在君臣之间,或在男女之间。
总之,无论“授受礼”举行时所站位次,还是施礼者的容态,抑或是授受的方式,均是古人尊卑观念体现。周人以“尊尊”纲纪天下,制定礼仪,“授受礼”自在其中。本文正是通过对礼仪制度的恢复,来探视周人的思想观念。不过,“授受礼”决不会是两周突然产生的。“授受礼”的溯源以及其在战国后的演变,是需进一步考察的课题。
[注 释]
①钱玄先生曾就《仪礼》一书略排比授受方式的材料,但并未展开论述。载《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40—542页。
②贾公彦认为《仪礼·大射仪》“公卒射,小臣正赞袭”,可证公在他事中有赞者。
③《左传》成公三年载有贾人欲谋助荀罃,未及而楚国让荀罃归晋。后贾人晋国受到荀罃的善待,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贾人自称谓小人,可见春秋时的贾人之地位低。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816页。
[1][6]杨宽.“贽见礼”新探[A].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胡培翚.仪礼正义[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3]章太炎.春秋左传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彭林.论郭店楚简中的礼容[A].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集[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9][12][14]淩廷堪.淩廷堪全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9.
[10][11][13][15]李如圭.仪礼集释[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7]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闵 军)